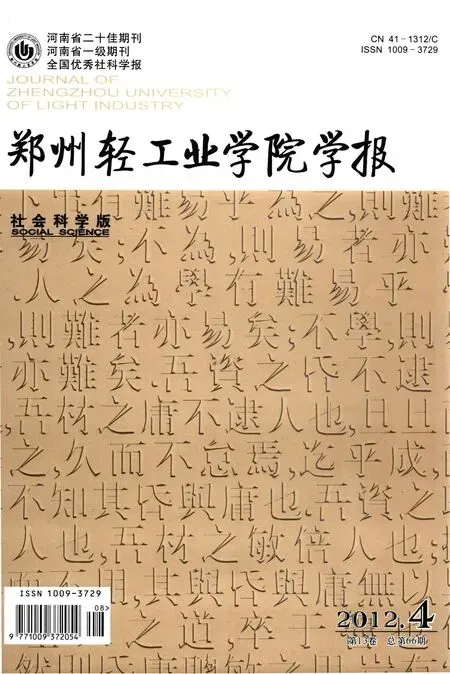王阳明的实学思想及其对新实学研究的启示
胡海桃
(军事交通学院政治部,天津300161)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早已为人所熟知,但很少有学者提及他的实学思想。学界普遍认为,王学(心学)与实学是两种对立的社会思潮,王学非实学。王夫之明确指出,王氏后学“废实学,崇空疏,蔑规矩,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1]明清之际的实学家们认为王学末流将经世致用的儒学变成了空谈心性的腐儒,是导致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他们对王学持彻底的批判态度。但事实上,王学并不等于王阳明本人的思想,王氏后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超出阳明心学的范畴。当今学界将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学思想进行专门研究者并不多见,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葛荣晋[2]曾提出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蕴含着“实心实学”的思想,并认为这种“实心实学”思想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理论源头之一。而贾庆军[3]认为,王阳明的实学就是辨义利之学。显然,学界对王阳明的实学思想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拟从实学的含义出发来界定王阳明思想中的实学意涵,在概括阳明实学思想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清理近代实学思潮之流弊,并进一步探讨阳明实学思想对构建新实学的启示与意义。
一、实学的思想界定
在中国思想史上,实学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实学一词在经典文献中最早出现于东汉王充的《论衡·非韩篇》:“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这是王充引用的韩非对俗儒的批评之语,斥责俗儒们借实学之名以假乱真、贪慕虚荣,背离了真正的儒者之道。这里的实学概念以“伪说”为对,内设了一个“虚”的、“伪”的学问作为参照系,这也是后来实学研究的共同取向。
至唐代,礼部侍郎杨绾针对唐代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以实学取士的主张。二十五史《旧唐书》卷119《杨绾传》中记载:“取《左传》、《公羊》、《谷梁》、《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通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义……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所冀数年之间,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敦庞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可见,杨绾的奏疏是针对唐代科举制的浮竞之风而言的,所指的实学内容大体包括通经、用世和修德三个方面,这些内容基本构成了以后实学研究的理论框架。
到了宋代,在思想界掀起了一股针对佛老空无思想的“崇实黜虚”的文化思潮,实学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范畴。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河南程氏遗书》第4卷)“治经”须是“实学”,必须在“进德”上下工夫,如果“治经”只是将“居常讲习”挂在嘴上,则为“空言”而非“实学”。程颐所谓实学,是通经与修德的统一。朱熹《中庸章句题解》说:“尝窃病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而常妄意天地万物人伦日用之外别有一物,空虚玄妙,不可测度,其心悬然惟侥幸于一见此物,以为极致。”朱熹的所谓实学也主要是针对佛老的空无之学而言的。
宋明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理学流派,到了明代后期,理学逐渐变为空疏无用之学。明朝中后期,在批判宋明理学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股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杰认为:“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对理学的空谈心性而言,主张经世致用;对理学的束书不观而言,主张回归儒家原典。”[4]现在大多数研究者所用的实学概念就是指这个时期的经世致用之学。
从1980年代我国实学研究再度兴起以来,围绕实学的各种问题争论不断。追源溯流,梳理实学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实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并未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存在过。正如张学智所说:“实学实际上是一个标志学术转型的价值性名称,不是一个有确定内容并因之与他种思潮区别开来的学术概念。”[5]可见,实学并不是与理学并列的学术流派,只是一种学术取向,理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实学思想。进一步讲,“从反对佛老出世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角度看,宋明理学家,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实学”[6]。
从中国思想史上关于实学思想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实学”一词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即崇实黜虚、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在《王阳明全集》中,“实学”一词共检索出11处,从上述三个角度来考量,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实学思想。
二、阳明实学的特征
1.知行合一
阳明实学的思想基础是知行合一。知与行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思想史的一对重要范畴,主要涉及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也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从先秦到当代,学者们对于知与行之先后、轻重、难易等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孔子认为“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主张知行结合,学以致用。老子持“不行而知”的观点,认为“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道德经·第47章》)。荀子认为行比知重要:“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篇第八》)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认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王夫之认为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尚书引义·说命中二》)。而王阳明反对把知行分裂开来,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之一·传习录上》)。而知行之所以能合一,是因为本体工夫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之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这种知行合一的特征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反映就是主张“心即理”:“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显然,王阳明秉承了儒家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其心学思想是一种实心实学,与传统“崇实黜虚”的实学意涵基本一致。
2.力行实践
王阳明认为,要将实学推行于日用之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之一·传习录上》)。“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之二·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道德的最高本体,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到万事万物之中。“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达到知行合一。所以王阳明并不主张离开具体的事物空谈心性修养。他驳斥佛家那种逃避君臣、父子、夫妇的修养路径,认为“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在《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之三·传习录下》中记载,有个官吏经常听王阳明讲学,但认为王阳明的薄书讼狱又多又难,学了没用。王阳明听后就对他说:“我何尝教尔离了薄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在《知行录之六·公移三·揭阳县主簿季本乡约呈》一文中,王阳明提出“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这一经世思想,赞扬揭阳县主簿季本兢兢业业、实事求是地为民办事的精神,所以在他治下才能息盗安民,使他治下之民归于厚道。王阳明主张“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之三·传习录下·附朱子晚年定论》),所以学问要落实在“钱谷兵甲,搬柴运水”、“应接俗事”、“民人社稷”等政治、经济、社会实践中,走修齐治平之路,延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所以,王阳明力行实践的思想正是对传统实学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意涵的继承与发展。
3.辨明义利
王阳明认为,讲实学就要摒除功利之心。实学是一种“崇实黜虚”的心性道德修养,如果怀着功利之心,读圣贤之书却为求官进爵,道德仁义却只在嘴上功夫,这些并非实学。如他在《静心录之一·文录一·与陆原静》中说:“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诗、文之类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则虽日谈道德仁义,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诗、文之类乎?”王阳明在《静心录之一·文录一·寄薛尚谦》中说:“数年切磋,只得立志辨义利。若于此未有得力处,却是平日所讲尽成虚语,平日所见皆非实得,不可以不猛省也!”在他看来,“义”就是良知,就是天理,“利”就是人欲,而“天理人欲不并立”,所以要正人心,就应灭人欲、存天理。从功夫上说本体,“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之三·传习录下》),如果动一分功利之心,有意为善就不是真善了。可见,王阳明“致良知”的实学也是辨义利之学,是对传统实学崇实黜虚、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
三、阳明实学思想对新实学研究的启示
近代实学思潮是以强调“有无用处,是否能解决社会问题”为切入点的经世致用学风,其特征是功利性和实用性。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将学术视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虽然对西学的引进有功绩,但是对空谈心性之学却矫枉过正,过分追求所谓“有用”之学,否认纯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思想上的混乱与肤浅,使学术难以独立。新中国成立后,“打倒孔家店”,对传统文化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并未认真反思近代实学思潮的流弊,致使传统实学在面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时束手无策。在新形势下,中国能否重建一套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实学,完成实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对中国实学发展至关重要。葛荣晋认为:“‘新实学’主要新在两点上:一是必须准确地全面地把握时代精神,从哲学价值观高度,回答与解决时代提出的各种新问题;二是必须超越‘旧实学’的理论架构,吸纳人类各种新的哲学思维成果和新的研究范式,构建中国的‘新实学’。”[7]
结合前文对传统实学意涵的梳理和对阳明实学思想的探讨,笔者认为,阳明实学在处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新实学构建中出现的道德危机、浮竞之习等问题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特别是新实学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借鉴阳明实学在道德修养与人心教化等方面有价值的思想内容。
针对道德危机,阳明实学提出要重视道德修养,知行合一。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道德权威逐渐衰弱。习俗道德权威的衰弱使职业道德、家庭道德以及公共道德等失去了应有的约束,政治腐败、商场失信、考场作弊、子女弑亲、笑贫不笑娼等道德问题层出不穷,终于从昨日的“道德滑坡”演变成今天的“道德危机”。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同样面临严重的道德危机,他深感当时僵化和教条化的程朱理学与佛老思想无法应对危机,提出要重振儒家的伦理道德,把“正人心”当作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主张从“格心”入手,延续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的道德修养功夫,首先端正心性,树立高尚的品德。儒家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人从内在德智修养到外在社会价值实现的连贯过程,今人却往往本末倒置,居其位而不具其德,修养基础尚未扎实就已经亟不可待地投入功利实践,这就是当今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要化解这种危机,可以借鉴阳明实学思想,在知行合一、辨明义利的基础上力行实践,从“正人心”的根本处着手,对儒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核心道德观念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继承与发展。这些观念简洁、贴近生活而不陌生,便于大多数人记忆、理解和接受,且很多思想与“八荣八耻”的相关内容保持一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有促进作用。端正了道德认知,才能在经世致用中实现知行合一。
针对浮竞之习,阳明实学提出要辨别义利。王阳明曾批判所处时代的浮竞之习,指出学子们“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之一·传习录上》)。针对这种现象,他指点迷津:“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之一·传习录上》)功利之心难除,缘于人欲的阻碍,所以要去人欲,存天理。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因为过分追求“利”已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很多人把文凭当做升官、谋职、发财的敲门砖,一旦走上领导岗位或是积累了一定社会财富之后,就将回报社会的理想和承诺抛之脑后,导致教育和学问的虚伪化;不少人只讲赚钱不讲道德,只讲“利”不讲“义”,在法制不完善和监管不严的情况下投机钻营,于是出现了毒奶粉、毒胶囊等危害民众生命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这些唯利是图现象的普遍发生根源于功利主义价值观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蔓延。要改变这种浮竞之习、见利忘义的状况必须诉求于人心的教化和价值观的重塑。可当今社会已经默许了逐利的正当性,反而认为不图名利甚为虚伪。马克思主义认为,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需求的背后就是私欲,就是利。阳明实学要求彻底摒弃功利之心,但基于人性出发,太过理想化且缺乏人性关怀的价值理念反而很难大众化。今人虽然不能做到彻底去人欲、摒弃功利之心,但至少可以借鉴阳明辨明义利的实学思想,在教育中加强“重义轻利”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使人们不会因为社会现实与教育理想的强烈冲突而彻底抛弃理想,甚至走上危害国家、危害社会的道路。辨明义利,才能在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中保持身心和谐,才能改善社会风气、重塑社会公德。
[1]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4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1:1468.
[2] 葛荣晋.王阳明“实心实学”思想初探(上)[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2):93.
[3] 贾庆军.王阳明实学思想刍议[J].船山学刊,2010(3):110.
[4] 王杰.论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J].文史哲,2001(4):44.
[5] 张学智.中国实学的义涵及其现代架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17.
[6] 张践.实学与心学的交融与错位[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2):93.
[7] 葛荣晋.构建中国“新实学”[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