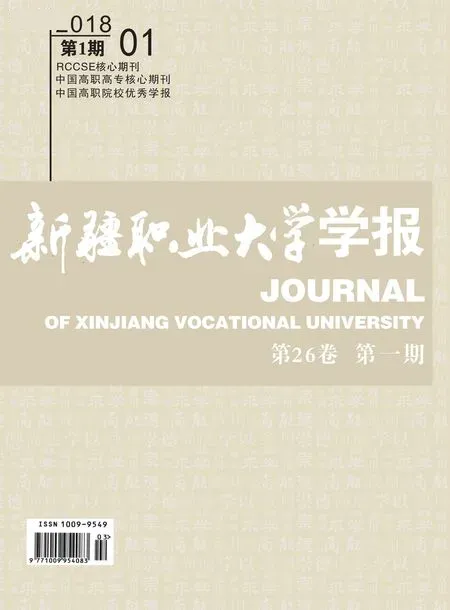戏剧性情境中的人性表达和美学原则
——以戏剧改编电影《驴得水》为例
汪雨薇,成湘丽
(新疆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开心麻花”为代表的戏剧改编电影在国内获得了审美价值与票房价值的双丰收,这一系列的戏剧改编电影获得巨大的成功颇值得关注和研究。中国戏剧改编电影历来有传统,甚至可以说中国电影的序幕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影戏”的方式打开,从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开始,“影戏”起初只是单纯地满足记录需求,后来演化为逐渐借助戏剧的冲突来推动和发展故事情节,如影片《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上世纪80年代,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现代化》一文对电影的戏剧化模式提出深刻批评,讽刺中国电影只有拄着戏剧的拐杖才能行走,提出“丢掉戏剧的拐杖”的口号,掀起反对戏剧改编电影的浪潮。时至今日,中国电影的视听语言相比之前已经取得了极大的丰富与进步,电影可以凭借镜头语言讲述单一舞台上发生的故事,从而更好地将电影语言与戏剧情境、戏剧冲突结合。近些年,以开心麻花系列话剧IP电影改编获得的巨大成功,将戏剧与电影的“联姻“再次推向高潮。
一、假定性情境与社会讽喻主题表现的艺术真实
《驴得水》剧情看似荒诞不经,实则透视人性,台词调侃幽默,却又发人深省。影片讲述了一个以戏谑喜剧外壳包装的荒唐故事:1942年,在西北地区的一所三民小学,校长为学校生计,谎报一头驴当英语老师,“驴”名为得水,原是学校从二十里外驮水的主要工具,片名《驴得水》由此而来。恰逢教育部特派员视察,情急之下校长用铜匠冒充英语老师,结果谎言越编越大,为不断弥补漏洞,事态发展越发具有闹剧性。
在影视美学中,假定性情境一般指戏剧通过认识原则和审美原则对作品的加工,使作品异于并高于生活,在影片中,导演通过一系列的偶然性经过艺术的加工使得故事情节转换为必然性,使得影片更具真实可信性。如影片中铜匠原本只是来修铃,他并不想冒充别人,却阴差阳错被特派员认为他是真正具有留学背景的农村教育家。铜匠假扮吕得水老师,特派员丝毫没有看出来半点端倪,感叹他真是“原形毕露”,认为只有铜匠能扛起振兴中国教育这杆大旗。这一幕剧情使那些特派员显得愚不可及,刻画了丑陋愚蠢的官员形象。《驴得水》好比一面镜子,照见民国时期官场的种种丑态。美国人罗斯先生资助了十万法币给农村教育,特派员竟私吞了七万法币之多,鞭挞了整个民国时期官僚政治的丑恶、贪污腐败的严重。这一系列滑稽剧情仿佛都是偶然的,但促使特派员参与更大的谎言编织中,同校长一起欺骗罗斯先生的正是他的贪婪与恐惧心理,既希望得到七万法币,又害怕平时贪污受贿的行径被暴露,才使得戏剧冲突有了极大的可信性,仿佛一切顺理成章,荒诞不经,实则有着必然的依据,形成了真实可信的戏剧性效果。
影片中特派员和罗斯先生一同来视察吕得水老师时,矛盾冲突一时间全部汇聚在学校。一方面铜匠老婆突如其来的闹事,同时,特派员与罗斯先生即将来视察,铜匠很可能“原形毕露”,学校即将面临巨大的危机的外部矛盾;另一方面,学校内部裴魁山对张一曼因爱生恨,个人私欲无限膨胀,学校也不再团结。这一假定性情节将所有矛盾高度集中在同一时间和空间里,使得故事更为集中,将影片故事情节推动到“高潮”。此时铜匠如救世主一般回来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句“nice to meet you”逗乐了观众,紧接着导演采用逆光仰拍角度,铜匠高大形象立刻凸显出来,然而反讽的是铜匠并不是回来“救场”,而是回来疯狂“报复”,铜匠说出的几句蹩脚英语不仅增强了戏剧的喜剧特色,更是让角色顿现原形,显露铜匠小人得志的本性。当“驴得水”事件败露,特派员私带枪支准备枪毙周铁男,影片设计了第一枪没有打死周铁男这一假定性情节,使得剧中周铁男由原来铁血男儿的形象转为跪地求饶、贪生怕死的形象,显露出真实卑怯的人性。民国背景让这一切荒诞行径也都有了可以解释的理由,时代背景使得故事情节变得情有可原,可见那个年代人命如草芥,同时也讽喻民国时期制度的不完善、人权的丧失。
电影《驴得水》的剧情是滑稽可笑的,但却是合理的,剧中的矛盾是尖锐的,但最后的结局是一切照旧,学校保留下来,体现了“一种解决”,而观众明知这种解决是一种假定性,但这种假定性却是戏剧性的合法手段[1],它的运用有力嘲笑了教育制度、官僚贪腐以及人性自私。影片在影视语言上的流畅叙事让人在嬉笑中丝毫不觉影片人物情境有不合理之处,使得前半部分诸多滑稽可笑的行为取得了令人可信的喜剧效果。
二、喜剧情境和悲剧意蕴构成的审美张力
影片前半部分在音乐、音响、人物对白上颇下功夫,影片前半部分的“滑稽可笑”多有讽刺的意味,犀利无比,锋芒毕露,使得影片中假、丑、恶顿现原形。戏剧与电影有很大不同,戏剧依赖对话、情境交代叙事,而电影则是光影与视听的艺术,电影的表达依赖于对话及声画蒙太奇的组合。影片中,导演将声音和画面有机结合起来,使得对话(音乐、音响、对话)与画面形象相辅相成,互相配合,镜头稳健朴实,剪辑流畅,叙事完整得益于林良忠的摄影(也是李安“父亲三部曲”的主要摄影)以及廖庆松的剪辑(也是杨德昌、侯孝贤团队的主要剪辑成员)。
影片的悲喜交织突出体现在电影语言中声画对立的处理。张一曼被校长剪头发时,画面内容是昏黄的暖色调,紧接着画面交叉淡化,闪回的是张一曼挽着校长胳膊跳舞、帮校长减掉新衣服上的最后一颗纽扣、大家穿上新校服在摄影机前面照相的场景。画面看起来温馨感人,背景音乐《Firefly Waltz》也是欢快动人的,音译的意思是“萤火虫华尔兹”,节奏欢快明亮,烘托一种温暖气氛。导演运用欢快的声音和明亮画面淡化出张一曼眼中含泪的特写镜头,更加烘托出张一曼绝望无助的内心世界,同时也与影片的宣传标语“给你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异曲同工。当头发剪完后,又一个特写镜头给向校长手里的剪刀,暗示校长就是谋害善良人性的刽子手。影片没有用悲伤的音乐渲染张一曼悲凉的心情,而是用欢快的音乐以及温馨的画面来渲染她的内心世界,声画对立的运用更能凸显剧情前后的反转,以及人物内心世界的崩塌。影片在视听语言的“反讽”上,进一步拓展了电影的审美张力。
导演用拉镜头逐步展示了从张一曼满含泪水的眼睛的特写镜头到无地自容地钻入桌底的全景镜框。在电影语言中,“照注视镜子”这一行为作为人物表达内心状态的经典表达方式,戏剧改编电影赋予凝视镜子戏剧性、重旨性、内指性的新型符号内涵和美学观念。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人总是在镜子中认知自我,在“他者”中建立自我认知,裴魁山对张一曼的侮辱和校长亲手剪灭了她的精神世界,让原来活在男人竞相逐爱的自我想象中的张一曼在“他者”自私本性暴露后的冷酷注视中失去自我,以致无法正视自己。采用“镜中”手法拍摄张一曼的形象,一方面可以避免画面的二维平面感,通过镜子这一媒介将观众的视线范围扩大至360°,从而使镜中的画面更具纵深感;另一方面,导演通过拍摄扭曲的镜中人物,在镜框这一狭小而封闭的空间运用中突显张一曼的窘迫、压抑、无助和绝望。同样在封闭空间中的还有校长,拿着剪刀低着头的校长在这封闭的“秩序”中,已被训规与收编,道德的无力感已被现实的功利心所吞没。
影片的悲喜交织集中体现在张一曼前后命运的反差中。张一曼原本活泼开放,向往自由与爱情,结尾却以一声沉闷的枪声暗示了她的自杀。她是剧中最有争议的形象,表面看起来生活最为混乱、行为最为放荡,但却又是灵魂的干净度和理想性最纯粹的人物。张一曼的渴望爱情和向往自由,集中体现在剧中黄花这一意象。当张一曼参加铜匠的婚礼时,混乱之中张一曼被撞倒在地,花散了一地,导演给了一个低角度特写镜头——张一曼护着花,怕花被踩。黄花象征着纯洁的感情,影片中有三次出现黄花意象,第一次出现时,铜匠离开学校与张一曼告别,满山的青草与篮子里张一曼刚摘的鲜花相应,画面干净温馨。第二次出现场景是一大片黄花场景,是张一曼被减掉头发后,裴魁山诬陷她是“疯女人,快把他关起来!”,校长告诫“衣服做不好别出来”,是校长与裴魁山彻底将张一曼囚禁起来,对于渴望并向往自由的张一曼来说,无形中等同于扼杀。渴望爱情,向往自由的张一曼最终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个被囚禁的、被迫沉默的女人,关于张一曼的一切和她的阐释是男人们给出的,她被命为疯女人,因而永远地剥夺了话语权与自我陈述的可能[2]。
影片结尾以一声沉闷的枪声暗示了张一曼的自杀,但背景音乐并未延续悲凉的色彩,而是以希望结尾,影片再次响起《我要你》的背景音乐,画面则是五颜六色的弹力球滚落山崖。《我要你》在影片中也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出现在裴魁山向张一曼表白爱情之时,裴魁山的那句“你真可爱,我喜欢你”呈现的更多不是爱情,而是性和欲望,这一缺位的“爱情”与浪漫化情歌间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反讽。第二次浮现《我要你》是在铜匠离开学校与张一曼告别时,铜匠问:“我们是什么啊?”张一曼笑而不答,张一曼也是拒绝与裴魁山谈爱情的。第三次则是以张一曼的自杀彻底否定了《我要你》的浪漫情调和张一曼的爱情梦想。
影片前半部分以一系列的噱头、笑料构成影片的喜剧情境,让人在观影过程中笑的酣畅,台词的幽默感提升了影片的娱乐性,提高了影片的魅力。在影片后半部分,由先前令人捧腹的情境转而成为砭人肌骨,引人深思的情境中,影片中的假、丑、恶被揭露,人物命运转变成影片后部分的悲剧意蕴,使得影片主题不仅停留在表面的笑料,而是得到了上升到人性的反思。
三、非常态情境和合理人性反织的讽刺结构
在特殊情境下,我们日常标准下对善恶好坏的评判就失去其有效性,同时,也只有在脱离日常的极端情境下,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辨清人性之根本驱动力。“三民小学”恰恰是以“学做人”作为办学宗旨的。学校在雨神庙,校门口的对联颇具讽刺意味——进来彬彬有礼,出去步步生风。随着剧情的发展,裴魁山披上了兽皮;周铁男变成特派员身边的一条狗;铜匠小人得志,忘恩负义;校长看似最善,但他才是一切的始作俑者。剧中的人变得一步步泯灭了最初的人性。
影片开始的一场大火,为整个故事的剧情埋下伏笔,同时揭示民国时期的时代背景。这场大火好似处在战火中的中国,四位知识分子来到西北地区创立三民小学为了改变中国农民的贪、愚、弱、私,但他们的救助对于整个大火而言,显得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剧中的“老师”驴得水其实是一头驴,其余的四位知识份子政治上都是有污点的,只有这个“吕得水”清清白白,讽喻现实社会中教育良心的缺失。学校发展之根本已经不是培养学生、教书育人,而是怎样筹得资金、改善条件、增加工资,学校的最大任务不是教育学生而是算经济账,包括张一曼的最大梦想不是学生成才而是缝制漂亮校服。到底是为了农村教育之未来,还是为了一己之私欲的实现?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农民的贪、愚、弱、私,而是有知识、受过教育的人更需要改变自己的贪、愚、弱、私。
表面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办学信仰——团结、乐观、奋斗。影片以四人组合贯穿始终,更能体现人物性格的转变轨迹。只有开始时四个人聚在一起,一直至影片结尾,原先有过农村教育兴国梦想的孙校长为了给学校谋发展,不惜以自己女儿和张一曼的尊严为代价;曾经对张一曼怀有真爱之心的裴魁山在尊严被侮辱后,摇身成为唯利是图的小人;正义化身的周铁男在生死存亡之际,不再有任何反抗或异议;原本对他人怀有善意、对学校充满希冀的张一曼在校长被捆绑之后最终也选择了只求自保。
铜匠原本没有一点文化,校长鼓励铜匠有教无类,可是当第二次特派员来视察吕得水老师时,周铁男说“现在的铜匠和以前不一样了,整个假期佳佳都在教他”,果然铜匠再次回到学校时已与之前的自己完全不同,新的“感觉结构”决定了其阶级身份感的转向和错位。怀着对农村教育实验梦想,校长自称自己是“当代武训”,可是最终却为实现自己的一己之私不惜牺牲所有人的利益,成为没有原则与底线的人;裴魁山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在得知张一曼“睡服”铜匠后,强烈想要报复身边的一切,以“你凭什么拿你的道德去绑架我的利益”为基本价值观,将个人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周铁男原是正义感的化身,一次枪声后苟活下去的周铁男成为一具唯唯诺诺的驱壳,这一形象讽喻了在面对生活中不公平、不正义之事没有反抗而变的麻木不仁的人。在导演周申、刘露视频采访录里,他们谈到:不能为了一个美好的目的去做错误的事儿,不能将美好的愿望作为突破自己底线的借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确并坚守住自己的底线[3]。
《驴得水》勾勒出社会各个角落里的人物群像,每一种形象嬗变的背后都是社会真实的写照,影片深刻性表现在揭露人性。人性不是先验主宰的神性,它是感性中有理性,个体中有社会,知觉情感中有想象和理解[4]。在影片中,人的真、善、美、自私、懦弱、丑陋被放大,我们感叹人性的丑陋同时对剧中的人物投以深深同情,的确,人性前后的变化不能用简单的是与非、对与错来衡量,剧中每个人的行为在“人性”观照的背后一方面有了可以被理解的理由,但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反面的参照:做人不能小人得志,自私自利;面对恶势力的打压,不能轻易低头屈服;面对困难,不能没有原则,失去底线。
四、结语
戏剧的单位是幕,而电影的单位是镜头,戏剧的空间有限,而电影表达的空间无限。导演周申、刘露将电影的戏剧性与电影性巧妙融合起来,立足于中国电影观众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欣赏惯例,对电影的戏剧化情节,加以继承、改编和创新,使得影片获得一致好评。电影在戏剧改编电影过程中,更需要重视“声画组合”的蒙太奇运用以及影片的空镜头运用,才能使戏剧改编电影更为流畅。影片改编多少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比如影片开始的那场救火,导演采用固定镜头用中近景的取景方式拍摄,这种“乐队指挥机位”让观众有一种舞台即视感,使得影片话剧性略强,削弱了影片的电影性。对于一部戏剧改编电影而言,好的剧本才是其真正的灵魂,视听语言只是将故事讲述得更符合观众视听习惯的一种手段。
张艺谋对这一系列问题有过强烈反思,他曾说,“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恐怕不是在一部影片里就能完成的,叙事难关是要用一辈子来完成。[5]”《驴得水》的成功在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目前国内一些大明星、大场面、大制作、无内涵的MTV拼贴式的电影,并对国产电影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艺术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