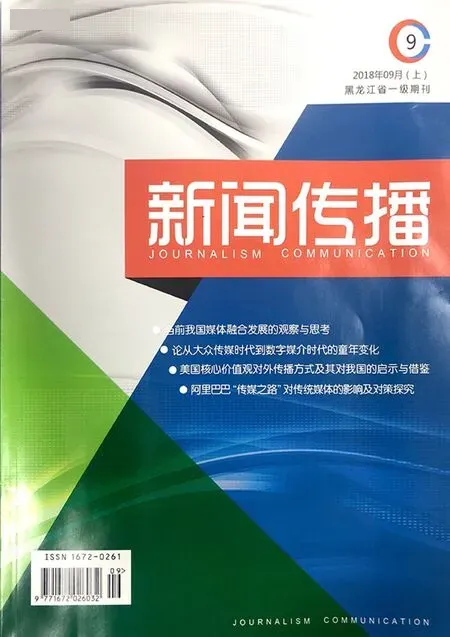影视人类学视野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嬗变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影视人类学作为新兴学科,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1],其成果为人类学纪录片。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倡导文化没有界限,各民族文化的和谐相处应追求天下大同的境界,少数民族文化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影视人类学具备着保存和记录人类文化的功能,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时代诉求相契合。少数民族题材的人类学纪录片,通过描摹少数民族文化事项书写少数民族风俗人情,观众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民族的文化变迁、比较民族间文化的异同。
一、影视人类学以少数民族文化内容为题材
学界普遍认为,国内影视人类学纪录片的开山之作,是20世纪50~60年代,在人类学家和影视工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化抢救式的影像记录中诞生的15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由此可见,国内的影视人类学在发展初期就与少数民族题材并蒂而生,对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群文化的展示成为这一时期影片的主要内容。由于是政府主导调查下的产物,影视人类学纪录片早期的创作以民族识别和文化救险为目的,影像功能体现在对文化的挽留性刻录上,其流程一般为影视工作者在田野进行观察采访,依据人类学者原有研究基础撰写提纲,设计和修改分镜头脚本,在拍摄原则上遵循如实记录,创作者以鲜明的他者身份进行文化勘查,用镜头绘制少数民族社会组织、婚姻丧葬、村规民约,素材送审后在人类学学者的指导建议下剪辑完成。随着影视人类学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和技术的进步,近年少数民族题材的人类学片在创作策略上有了更成熟的人类学理论和多元化表现语言,以影视手段提喻民族文化符号,传播文化的深层内涵,在人类学片对不同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的共时性扫描下,体现出各民族在同一历史时期相似的命运和困惑,如《兰屿观点》里雅美族人面对核废料遗置在岛上的抗议、《最后的山神》中鄂伦春族孟金福夫妇选择在山林里坚持原始的生活方式。创作理念的嬗变使人类学片的主体叙事框架由诉诸视听向直击心灵跨越,与人类学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向叙事、阐释和象征的转变[2]暗合,在理论层面上由科学实证主义过渡到人文主义,扩充了人类学信息,愈加具有时代意义。
二、影视人类学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提供了手段
民族文化中的民族性和人类性,只有经过书写和传播才能被大众熟知,影视人类学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提供了手段。第一,人类学中的整体观赋予纪录片在整体视野下展现民族的文化变迁,视其中的文化为统一体,在影片的时空表现下注重信息之间的相互关联。导演顾桃在对生活在北方的鄂温克族历时近十年的探访中,将拍摄超过500个小时的素材剪辑成鄂温克三部曲纪录片——《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在连续和共时性的多点地域中详尽展示了鄂温克族文化环境和生存风貌的变迁。第二,创作者融入少数民族族群中,积淀生成本真的文化直觉,获得其真实的系统文化信息,如书云导演在创作人类学纪录片《西藏一年》的过程中,重点选取西藏江孜八位普通藏族人,每天与拍摄对象沟通以获取素材,该片获得国内外媒体的高度认可。第三,影视人类学中的研究视角,有着主位和客位的区分,主位视角强调通过文化持有者的眼界观察,客位视角则是以研究者自己的理论来反馈。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而言,主位视角的运用能够传达最直观的文化系统内部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让观众明显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引起对本文化的反思。
三、新时代影视人类学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3]在当下的融媒体语境中,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是传播民族文化和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对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们观察世界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加速交流,影视人类学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在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坐标下寻找结合点,使得大众可以透过荧屏沟通民族情感,增进文化认同。
(一)交与式拍摄方式的话语赋权
影视人类学对少数民族的文化阐释是文化内涵与影像语言的整合,它在人文视角下讲述温情故事的同时,也在潜层次暗含了对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呼唤。新媒体时代,大众身份由受众向创作者转变,影视人类学赋予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以内部视角表达本民族文化的话语权,交与式的人类学片拍摄方式使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成为持机主体,占据主位创作,挖掘在大众视野下不具备传播价值但实则为当地文化系统中日常元素的题材。在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发起的“乡村之眼”公益影像计划中,第一次拿起摄像机的藏族牧民兰则创作的纪录片《牛粪》,在独特的内部视角下,讲述了藏族人密切利用牛粪的日常生活,记录了他们利用牛粪生火、筑墙乃至制药的文化事项,展示了藏族独特的文化行为。基于少数民族群体文化自觉意识的发聩,交与式拍摄方式使文化持有者朴素、真实的原生态创作在文化立场上比他者的视角更贴近本文化的表述,更具有本土性和民族性的价值意义。
(二)互联网+语境下的传播技巧
在互联网+语境下,伴随着新技术的升级,纪录片有了新的表达形态,对于以影像为手段的影视人类学纪录片来说,这些新形态可以更好地提供文化信息的记录、表达和传递,深度挖掘人类学理念。早期人类学片中的镜头,因摄制条件的不足存在诸多局限,如《佤族》中对佤族人生活点的呈现只能通过横移镜头的跳接、简单的高点俯拍,不能连贯、宏观地呈现文化环境的整体形貌,但如今借助航拍的鸟瞰视角或VR技术,可以使田野得到全景式的扫描。2015年央视拍摄的藏地题材纪录片《第三极》由6集构成,第6集《高原相遇》用一整集讲述了摄制组田野工作的经历,这种将花絮剪辑成正片的工作方式带有浓厚的影视人类学色彩,观众透视荧幕看到摄制组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既了解了幕后拍摄的技巧,也在他们其乐融融的相处中感受到了各民族无间隙的情感汇聚,使剧中普适性的内容表达更容易得到传播。此外,在全民参与、共享经济的浪潮下,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也为人们拍摄与人类学相关议题的短片展示提供了平台。
结语
在当下的文化传播中,既要有学者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深度挖掘,也要影视创作者以精美的声画语言在影像中实现对民族文化内容的构建,协同实现大众跨民族的文化认同。以文化为本体、以影视为手段的影视人类学,在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其发展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