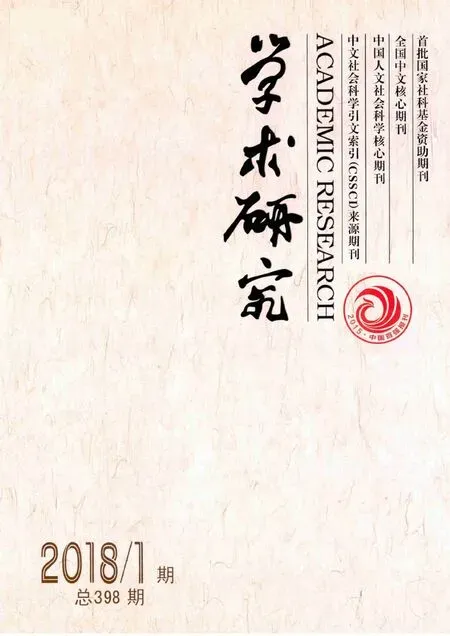气韵范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维阐释
——以宗白华、邓以蛰、钱钟书、徐复观为例*
曾 肖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西方的文化艺术如潮如涌地进入中国,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艺术发生了强烈的冲突。面对西方蓬勃发展的美术,有人深感我国宋元以后的文人画、写意画处于颓败之中,感慨道:“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盖由画论之谬也。”a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序》,顾森、李树声:《百年中国美术经典文库》第1卷:《中国传统美术:1896—1949》,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此言一出,激起了无数争论。在中西绘画差别、中国绘画史、历代画论等论题当中,中外学者们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其中,对于谢赫“六法”的认识和“气韵生动”的阐释,肯定了以表现气韵为主的中国绘画的价值所在,也为当代的学术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最早对气韵进行现代阐释的是以金原省吾为首的一批日本学者。他与伊势专一郎、园赖三等人研究中国绘画的著作不久译介到我国。丰子恺结合立普斯移情说来分析“气韵生动”,引入日人观点:
中国早有南齐的画家谢赫唱“气韵生动”说,根本地把黎普思的“感情移入”说的心髓说破着。这不是我的臆说,更不是我的发见,乃日本的中国上代画论研究者,金原省吾,伊势专一郎,园赖三诸君的一致的说法。……他说“气韵生动”是艺术的心境的最高点,须由“感情移入”更展进一步,始达“气韵生动”;他赞美恽南田的画论,谓黎普思的见解,是中国清初的恽南田所早已说破的。a婴行(即丰子恺):《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百年中国美术经典文库》第1卷,第71页。
当时另有一批欧洲学者如陶德曼、布朗恩等人对中国美术亦颇有研究。其中英国艺术史家布朗恩(Percy Brown)在他的《莫卧儿人治下的印度绘画》(Indian Painting under the Mughals,Oxford,1924)一书中,推测中国绘画六法受到了印度佛教绘画六支的影响。此说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议。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接受此观点,刘海粟的《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和刘纲纪《“六法”初步研究》则持否定态度,金克木的《印度的绘画六支和中国的绘画六法》和阮璞的《谢赫“六法”原义考》对“六法”并非源于印度“六支”作了专门考证。中国学者多认为六法的渊源出自本国思想。b参见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卷,台北沧浪出版社,1986年,第213页。
我国专门探讨气韵问题的有余绍宋、胡佩衡、岑家梧、滕固、刘海粟等人。余绍宋从气韵的起源、解释、价值、与形似之关系、产生途径等各方面来讨论,指出:气韵并非只有笔墨写意画有之,今后中国画仍应注重气韵。c余绍宋:《中国画之气韵问题》,《百年中国美术经典文库》第1卷。胡佩衡分析了山水画的气韵d胡佩衡:《中国山水画气韵的研究》(《绘学杂志》第2期,1921年),《百年中国美术经典文库》第1卷。;岑家梧用道家思想和栗伯斯(立普斯)的移情说做比较,解释物我两忘的境界,用布罗氏(布洛)的心理距离说来分析气韵和形似的问题,得出:“气韵就是画家把他的人品注到画里去,使其成为画家自我生命的表现。”他联系老庄思想、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精神来分析气韵。e岑家梧:《中国画的气韵与形似》(1940年3月在昆明),《百年中国美术经典文库》第1卷。滕固提出了气韵是“感情的节奏”,分析气韵与生动的关系:
董其昌气韵生动,缩做气韵二字。到了方薰,才把这四个字成了一贯之辞,其真义始得出现。照他的意思:万事万物的生动之中,我们纯粹感情的节奏(气韵),也在其中。感情旺烈的时候,这感情的节奏,自然而然与事物的生动相结合的了。事物是对象,感情是自己;以自己移入对象,以对象为精神化,而酿出内的快感。这是与Lipps的感情移入说(einfuhlungstheorie)同其究竟的了。f滕固:《气韵生动略辨》,《百年中国美术经典文库》第1卷。
滕固指出其思想渊源是周易与道家。刘海粟1931年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详细分析了六法的含义和关系:他先解释“笔致、写实、结构、模仿”说了以后,再说“气韵生动”,认为气韵生动是其他各种要素的复合。他不赞成把“气韵生动”拆开来解释:“气韵生动是整个的名词,不能分开来讲的。至多说,含有气韵的生动,或弥漫着气韵的生动。实际上宇宙间的生动无处不弥漫着气韵,气韵必然托着生动而表显的。”g刘海粟:《谢赫的六法论——二十年三月十九日在德意志佛朗克府大学演讲》,《百年中国美术经典文库》第1卷。刘海粟用“节奏”(rhythm)来喻“气韵”,认为生动之中必有气韵,气韵必定由生动来显现。
其中,对气韵范畴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宗白华、邓以蛰、钱钟书、徐复观的学术成果最瞩目。宗白华连续发表了《徐悲鸿与中国绘画》《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数篇关于绘画艺术的文章,以其中西融通的文化底蕴、较为客观的态度和优美流畅的文风,条分缕析,层层展开,充分展示了中国悠久而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与独有的美学思想。与宗白华并称“南宗北邓”的邓以蛰,立足于中国美术,并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观照,对中国书画研究作现代阐释,专文论述“气韵生动”。钱钟书的《管锥编》、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都对气韵问题做了专门探讨,创见迭出,影响深远。
一、“生命的节奏”:宗白华论气韵和气韵生动
20世纪初流行于德、法等国的生命哲学思潮,对于曾经留学德国的宗白华有深刻的影响。在《看了罗丹的雕刻以后》(1920年)一文中,宗白华意识到:无时无刻都在动中的自然精神,需要艺术家直接去体会,并将自我的精神贯注到物质中,借物质来表现,使物质精神化,这种来自于自然的活力是一切美的源泉。对生命哲学的思考,与中国《周易》的宇宙观、老庄的道家思想相结合,宗白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生命美学思想。以此来考察中国绘画艺术,宗先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气韵的诠释深中肯綮。他在《徐悲鸿与中国绘画》(1932年)一文指出:
此宇宙生命中一以贯之之道,周流万汇,无往不在;而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老子名之为虚无;此虚无非真虚无,乃宇宙中浑沦创化之原理;亦即画图中所谓生动之气韵。画家抒写自然,即是欲表现此生动之气韵;故谢赫列为六法第一,实绘画最后之对象与结果也。
宗白华把气韵比喻为道,无时无刻都在运动中,“生动之气韵笼罩万物,而空灵无迹;故在画中为空虚与流动。中国画最重空白处。空白处并非真空,乃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1935年,他在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时,更提出了“气韵生动”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这一卓见a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40多年后,宗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讨论谢赫的美学思想,进一步指出:
气韵生动,这是绘画创作追求的最高目标,最高的境界,也是绘画批评的主要标准。
气韵,就是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和谐。绘画有气韵,就能给欣赏者一种音乐感。
音乐感即“韵”。在这里,宗白华引派脱(裴德)“一切的艺术都趋向于音乐”来加以引证。气韵生动,是绘画所能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由此涉及音乐和意境的关系问题。宗白华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长文中,讨论了中国绘画的节奏美与生动性。他认为节奏是艺术境界生成的源泉,而舞是最高度的韵律节奏和艺术境界的典型,书画艺术都体现了这种飞舞的美学特征。“中国画是一种建筑的形线美、音乐的节奏美、舞蹈的姿态美。……中国画真像一种舞蹈,画家解衣盘礴,任意挥洒。”在这飞舞中,表现出形与象、色与光、明与暗、动与静、虚与实交织而成的境界。气韵生动不仅是中国绘画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西洋绘画的一种效果与追求,但在中西绘画艺术中具体表现不同。
(西洋)画家用油色洪染出立体的凹凸,同时一种光影的明暗闪动跳跃于全幅画面,使画境空灵生动,自生气韵。故西洋油画表现气韵生动,实较中国色彩为易。而中国画则因工具写光困难,乃另辟蹊径,不在刻画凸凹的写实上求生活,而舍具体、趋抽象,于笔墨点线皴擦的表现力上见本领。其结果则笔情墨韵中点线交织,成一音乐性的“谱构”。其气韵生动为幽淡的、微妙的、静寂的、洒落的,没有彩色的喧哗眩耀,而富于心灵的幽深淡远。
西方的油画填没画底,不留空白,“画面上动荡的光和气氛仍是物理的目睹的实质,而中国画上画家用心所在,正在无笔墨处,无笔墨处却是飘渺天倪,化工的境界”b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美学散步》,第145页。。化工的境界是中国人的宇宙观点和生命情调的反映。
宗先生结合中西美学理论分析中西绘画对心灵的表现,指出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艺术强调在无限空间作无限活动,而中国绘画“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c宗白华:《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美学散步》,第250页。其境界虽动而静,其对象充满生命的动,即气韵生动。他追根溯源到《周易》的哲学思想,《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一文指出:“谢赫的六法以气韵生动为首目,确系说明中国画的特点,而中国哲学如《易经》以‘动’说明宇宙人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以中国艺术精神相表里。”人的心灵节奏,与宇宙生命节奏相合,表现在中国画就是由阴阳二气交织成有节奏的生命。
二、“一气运化之自然”:邓以蛰论气韵和气韵生动
邓以蛰论气韵,立足于他对中国艺术发展史的独特认识,从“体”来考察建立系统结构论。他认为:艺术可以分为体、形、意三类,中国艺术的发展轨迹正是“体—形—意”组成的结构,相对应的是“生动—神—意境(气韵)”的结构,因而,气韵成为艺术至高无上之理。在《画理探微》一文中,邓以蛰把中国绘画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强调汉代文化艺术生动入神,而宋元以后的山水画则表出意境,气韵生动。“至元人或文人画则不徒不拘于形似,凡情境、笔墨皆非山水画之本色,而一归于意。表出意者为气韵。是气韵为画事发展之晶点,而为艺术至高无上之理。此就艺术之发展以寻其根本原理而言也。”
气韵和气韵生动是什么?邓以蛰引述宋代董逌言:“且观天地生物,特一气运化尔。其功用秘移与物有宜,莫知为之者,故能成于自然。”说明:“气韵生动之理若自大处言之,则气实此一气之气,韵者言此气运化秘移之节奏,生动盖言万物含此气则生动,否则板滞无生气也。”指出气韵与节奏的关系。他更联系移情说来分析,“山水画取动静交化,形意合一之观点,纳物我、贯万物于此一气之中,韵而动之,使作者览者无所间隔,若今之所谓感情移入事者,此等功用,无以名之,名之曰气韵生动。”a邓以蛰:《画理探微》,《邓以蛰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3页。
邓以蛰结合不同时期绘画来分析气韵和生动的关系。他在《六法通诠》指出:“生动可以有气韵,而气韵不能涵盖生动,盖不能一切生动皆有气韵也”。他认为生动是生物的活动:“夫生动者,乃缘生类之有动作也;凡一动作之起讫,必有其始终先后之变迁,其或从朝至暮,自春徂秋,莫之能止也。”气韵、生动在不同时期的艺术中或为二事,或合为一事。宋人的山水画与元人比较,“宋人以丘壑为胜,偏于生动者也,故逼近自然;元人以笔墨为胜,优于气韵者也,故不落畦径。以笔墨为胜者往往以丘壑为轻”。宋元山水画的气韵、生动各有偏重,但气韵生动是一个整体。而唐以前绘画的生动与气韵是客观之二事。
邓以蛰深受克罗齐的影响,在论述中国山水画与现代美学的关系时指出:“盖表现者,美之活动也;言语诗歌者,具体而直接,有自在之感情价值自内发出者也。”(《六法通诠》)把“表现说”拓展到书画艺术的分析。邓以蛰重视画家的人品、修养和心地,“气韵为天赋,为生知,此与希腊大哲柏拉图爱美先天之说相近也。且亦有赖于薰陶。后之有视气韵出于书卷气者盖是矣”。(《画理探微》)
与宗白华一样,邓以蛰以老庄哲学作为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思想基础。他在《画理探微》说:
六朝以后之诗与山水画皆所以继承老庄者耳。……故在诗画必曰直寻、妙得、玄解、明赏云者,盖以之为探求宇宙玄理之事耳。然则山水画岂游戏而已哉?其所表现之理诚大矣。人为飞动之伦,能观天地之大,岂曰以大观小?以大观小乃就艺术之规律与义法而言,若乃画理,则当立于艺术之外观吾人之明赏、妙得可也。赏者何?得者何?曰:气韵而已矣。古人画家者流果期以天地之心,画者之心,鉴者之心为一心,求其画逼近于此心,方号成功。此心为何?吾犹曰:气韵生动是也。欣赏山水画要靠个人的感悟与直觉把握,从中探求宇宙玄理。邓以蛰认为,中国绘画创作采用以大观小的方式。在鉴赏中,自然、主体与客体连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天地万物合一的心灵空间,这是一气运化之自然,是宇宙生命交融而有节奏跳动的活跃状态,即气韵生动。在《南北宗论纲》一文中,邓以蛰指出气韵生动的哲学基础是道家的泛神论。
三、“生气远出”:钱钟书论气韵
钱钟书在《管锥编》第四册论“气韵”,首先是从它的最早出处来考释文义,从文理意旨上对《古画品录序》重新断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述谢赫“六法”的句型为“一曰气韵生动”。钱钟书认为张的读法“以四字俪属一词”,后面皆缀六个“是也”即属多余,这是破句失读、文理不通。从而提出一种新的解读方式,把四字拆成两两一词,后一词是前一词的诠释:
盖“气韵、骨法、随类、传移”四者皆颇费解,“应物、经营”二者易解而苦浮泛,故一一以
浅近切事之词释之。各系“是也”,犹曰:“气韵即是生动,骨法即是用笔,应物即是象形”等耳。b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53页。
钱钟书认为:气韵一词抽象难懂,谢赫以生动来解释。他引述《古画品录》评丁光语、《续画品》评“谢赫”条,指出气韵“即图中人物栩栩如活之状耳”。联系南朝时以“气韵”来品藻人物风度和唐代画论以人物为对象,得知谢赫的“气韵”仅以品人物画。
钱钟书认为“气韵”即“神韵”,结合诗论与画论的发展历史和各种学说,分析气韵、神韵的内涵演变。“谈艺之拈‘神韵’,实自赫始;品画言‘神韵’,盖远在说诗之先。”“神韵”和“气韵”最早都是出现在谢赫的《古画品录》。气韵“盖初以品人物,继乃类推以品人物画,终则扩而充之,并以品山水画焉。风扇波靡,诗品与画品归于一律。……诗文评所谓‘神韵说’匪仅依傍绘画之品目而立文章之品目,实亦迳视诗文若活泼剌之人”。古代论者常以“韵”之一字来代指神韵、气韵。从司空图的“韵外之致”,李廌的“朱弦有余韵、太羹有遗味”,严羽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姜夔的“语贵含蓄”等说法来看,“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皆须留有余地,耐人玩味,俾由其所写之景物而冥观未写之景物,据其所道之情事而默识未道之情事。取之象外,得于言表,‘韵’之谓也”。钱钟书认为,谢赫以“生动”诠“气韵”重在气,忽略韵,而司空图《诗品·精神》中“生气远出”一语可用来诠释“气韵”,“庶可移释,‘气’者‘生气’,‘韵’者‘远出’”。
中西贯通、博洽融会的丰富知识,使钱钟书的研究呈现出旁征博引、善于比较的特点。在论述谢赫以“生动”释“气韵”时,钱先生联系古希腊谈艺的特点及西方翻译“六法”的几种情况进行评论。他说:“古希腊谈艺,评泊雕刻绘画,最重‘活力’或‘生气’,可以骑驿通邮。旧见西人译‘六法’,悠谬如梦寱醉呓,译此法为‘具节奏之生命力’者有之,为‘心灵调和因而产生生命之活动’者有之,为‘生命活动中心灵之运为或交响’者有之,为‘精神之声响或生力之震荡与生命之运动’者有之;其遵奉吾国传讹,以两语截搭,不宜深责也,其强饰不解以为玄解,亦不足怪也,若其睹灯而不悟是火,数典忘祖,则诚堪悯嗤矣。”在讨论“韵”具有“因隐示深,由简致远”的美学特征时,钱钟书联系古印度说诗亦主“韵”,西方古师教作文谓“幽晦隐约则多姿致,质直明了则乏趣味”,以及后世名家狄德罗、儒贝尔、利奥巴迪、叔本华、希腊诗句、法国诗句、爱伦·坡、马拉梅等话语,加以佐证与参照。分析“韵”出自声音之道时,钱钟书结合儒贝尔论诗、让·保罗论浪漫境界、司当达论画这三种说法,指出:“三人以不尽之致比于‘音乐’、‘余音’、‘远逝而不绝’,与吾国及印度称之为‘韵’,真造车合辙、不孤有邻者。”
与宗白华、邓以蛰将气韵的哲学基础归于老庄思想不同,钱钟书更多的是揭示气韵和佛教、禅宗的关系。他引述明初沈颢《画麈》倡“禅与画俱有南北宗”之说,指出:“宋人言‘诗禅’,明人言‘画禅’,课虚叩寂,张皇幽眇。苟去其缘饰,则‘神韵’不外乎情事有不落言诠者,景物有不着痕迹者,只隐约于纸上,俾揣摩于心中。以不画出、不说出示画不出、说不出,犹‘禅’之有‘机’而待‘参’然。”钱钟书从《永乐大典》卷八0七《诗》字下剔抉出北宋范温的《潜溪诗眼》论“韵”的一段长文,发掘了一则珍贵的史料,深入拓展了韵范畴的研究。他肯定了范温论“韵”的重要价值:“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指出范温以韵为声外之余音遗响,“足征人物风貌与艺事风格之‘韵’,本取譬于声音之道”。严羽“以禅喻诗”,范温进一步揭示“韵”与佛禅之关系,钱钟书在现代学术史上首次拈出严范之关系,指出范温是首位以“韵”通论书画诗文者。
四、“传神”:徐复观论气韵和气韵生动
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专门论述了“气韵生动”,对古代的“传神论”进行了新阐释。在考察了气韵生动一语出现的文化背景后,徐先生指出:“气韵的根本义,乃是传神之神,即是把对象的精神表现了出来。”“而‘气韵生动’四字,正是‘神’的观念的具体化、精密化。”a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徐复观认为,气韵生动“是积累了当时许多人的体验始能出现的一句话;它是作为艺术自身的一种存在,而被谢赫加以陈述”。从书画关系入手,徐复观分析了文字与绘画的发展,在魏晋时代书法艺术化了,这是魏晋玄学对艺术的启发与成就。以玄学、庄学为基础,人伦鉴识完成了从政治实用性向艺术欣赏性的转换,美的自觉由人自身形相之美延展到文学书法绘画方面,绘画以人物为主,魏晋及其以后的人物画“通过形以表现被画的人物之神”。徐复观认为顾恺之的“传神写照”是“要把当时的人伦鉴识对人所追求的作为人的本质的神,通过画而将其表现出来”。神是人的本质和特性,徐氏把“传神”推举为中国绘画艺术不可动摇的传统,从而推出谢赫的画论受到顾恺之的影响:“‘气韵生动’,乃是顾恺之的所谓‘传神’的更明确的叙述。凡当时人伦鉴识中之所谓精神、风神、神气、神情、风情,都是传神这一观念的源泉、根据,也是形成气韵生动一语的源泉、根据”。由此看来,徐氏传神论是从书画的结缘—艺术精神的自觉—玄学的影响—人伦鉴识的艺术化—人物画的传神—气韵生动,这样一步步论证得来的。
如何由传神演进到气韵生动?这是徐复观要解决的关键性一步。他从六朝文学用语入手,引述《典论》《世说新语》《诗品》《文心雕龙》等关于气、韵的用语,证明气与韵应各为一义。再把气的观念从宇宙本体论切入到与人身有关的“生理的生命力”,气便成为装载人的观念、感情、想像力的表现物,从而得出“气升华而融入神,乃为艺术性的气”的说法。这时的气是综合性的说法;而气韵的气是分解性的说法。徐氏认为:分解的气“常常是由作者的品格、气概,所给与于作品中力的、刚性的感觉;在当时除了有时称‘气力、气势’以外,便常用‘骨’字加以象征。”气韵之气与骨法用笔包含的气容易发生混淆,徐复观着重分辨了两者之不同,气韵之气属于精神方面的,是由作品的统一形成的,而骨法之气属于技巧,要形成气韵的气则“要经过精神的升华,和画面各部分的统一”。关于气韵的韵,徐氏追源溯流,分析韵的古字和变化,肯定韵与音乐的关系。又引述了日本大村西崖、金原省吾、小野胜年、英国李德等人的观点,把韵律的观念用到绘画线条方面。对此,徐复观加以辨析,西方言画的韵律、律动,是就线条来讲;中国画的韵是“超线条而上之的精神意境”。他从气韵与形似相对立的关系,推导出韵律不可能由线条的调和而来,而是应该从“形相上而言韵”。又列举了大量的例子,分析“韵”在当时更多地用在人伦鉴识上,“他指的是一个人的情调、个性,有清远、通达、放旷之美,而这种美是流注于人的形相之间,从形相中可以看得出来的。把这种神形相融的韵,在绘画上表现出来,这即是气韵的韵”。把气与韵都归于人的形相方面,徐复观完成了传神—气韵生动之间关系论的重要步骤,而其中起桥梁作用的是玄学。他说:气与韵,都是神的分解性的说法;藉玄学——庄学之助,在人的第一自然的人伦鉴识,顺理成章地发现了表现人的第二自然的传神;“气韵生动,正是传神思想的精密化”,气与韵都是“直接从人伦品鉴上转出来的观念,是说明神形合一的两种形相之美,与音响毫无关连”。
徐复观进一步分析了谢赫的气韵观念和顾恺之的传神观念之间的关系。谢赫的气“指的是表现在作品中的阳刚之美”,韵“指的是表现在作品中的阴柔之美”,“气韵系代表绘画中之两种极致之美的形相”。气和韵的关系,在表现上各有偏至,在理论上是相互补益不可偏废的。结合绘画的发展,徐氏指出,用墨技巧出现后,偏向于韵的这方面发展。气韵观念用在山水画,是为山水传神,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山水中“必有精神聚处”。徐复观说:“山水的可游可居,乃人的超越世俗的精神可以寄托之处,即山水精神所聚之处,有如人之目颧,这是画家为山水传神的要点所在。”而山水画在两个方面可以说是人物画的发展:一是骨法用笔与气有关,随类赋彩与韵有关,山水画常在笔上论气、在墨上论韵;二是以淡为韵,追求清远、虚无的美学特点,徐氏认为这是庄子的艺术精神的落实。无意之韵,是庄子的心与物忘,手与物化的境界,是技而进乎道的境界。
徐复观考察了气韵和生动、气韵和形似的关系问题。徐氏指出:在谢赫当时,气韵是主而生动是从。生动是气韵的自然效果,没有独立的意味;气韵是生命力的升华。有气韵一定有生动;仅有生动,不一定有气韵。而清人方薰、邹一桂等强调生动,把生动观念直接接合于生意或生气上,气韵不仅是笔墨技巧上的气韵,还包含了作者的精神和自然的精神。“作品中的气韵,是作品中所表出的对象的精神。而对象的精神,须凭作者的精神去寻觅”,徐氏得出“气韵的问题,乃是作者的人品人格问题”的结论,从而推举人格修养的功夫,重视人格的修养和精神的解放。
总的来看,宗白华的研究“主要从美的欣赏的角度对中国书画作一种感性直觉的把握,从审美体验中展现中国书画的美的特征,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揭示中国艺术同中国古代哲学的密切联系”a刘纲纪:《中国现代美学家和美术史家邓以蛰的生平及其贡献》,《邓以蛰全集》附录一。。他以生命精神来诠释气韵,强调其“动”,并运用于分析中西不同的绘画艺术,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哲学的独特价值,其观点影响广远,在今天仍为学者称述。
邓以蛰强调史论结合,把西方的科学精神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宏阔的历史观照与细微的概念辨析结合起来,运用中西哲学美学理论来进行史料分析,阐述中国的传统艺术,进行现代转换,从而构建了一个自成系统的中国艺术的美学体系。邓以蛰对气韵和气韵生动的诠释,是以老庄哲学为立论基础的,以克罗齐的表现美学为论说方式,密切结合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史而作出富于独创性的判断。
钱钟书对气韵的研究在纵向源流考辨和横向门类贯通上均有开拓。他对“六法”句读的重新标点,为理解“六法”提供了一个新角度。a关于“六法”的断句,主要有三种做法。一、前四字俪属一词,各系“是也”,如:“一、气韵生动,是也。”这种读法被认为是张彦远提出的。二、前四字两两一词,后一词各缀“是也”,如:“一、气韵,生动是也。”该读法早见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全齐文》卷二五,钱钟书对此赞同采纳。三、六字全部连缀成句,如:“一、气韵生动是也。”目前较为常见的是第三种读法。他引述中外对气韵、神韵、韵的大量说法,考查厘测,衡定评价。其中首标出范温《潜溪诗眼》的一段韵论,为今天研究气韵范畴提供宝贵资料。钱钟书通过对谢赫的“气韵、生动”及司空图美学思想的辨析,提出气韵的含义是“生气远出”,寥寥数字却一语中的,抓住了气韵的美学特征在于气之动、韵之远。他对气韵的考论,是现代研究中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成果。
徐复观构建了以庄子人生哲学为核心的中国艺术精神,在思想史的框架下研究中国古典美学问题,他以玄学、庄学作为气韵范畴的哲学基础,推衍出“气韵即是传神”的观点,肯定了作者的气韵与作品的气韵合二为一。徐先生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考察气韵的原典意义,探明气与韵各为一义,论证从传神到气韵生动的演进及在山水画中的表现,最后落实到修养功夫的体认。徐先生对气韵内涵特征的判定与界说十分独到,明确指出气为阳刚美,韵为阴柔美,把握了气韵的审美属性。他对气韵的阐释,20世纪70年代被引介大陆之后,研究影响甚广,当代学人多方引述,在其基础上增补或辨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