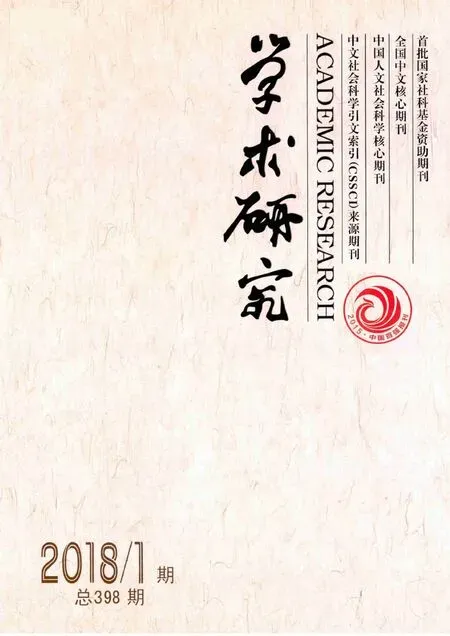指示关系的建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交往的民族志研究
姬广绪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的10年,我们见证了无线通讯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扩散,10年间,手机从一种其最初被定义为精英阶层的身份象征转变成为时尚的小玩意儿,最后又变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要元素。无疑手机的普及速度是历史上所有通讯技术中最快的。在全球范围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当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主线数的比例由1∶34(1991)提高到1∶81(1995)的时候,移动电话的确开始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腾飞。a[美]曼纽尔·卡斯特尔、[西班牙]米里亚·费尔南德斯-阿德沃尔、邱林川、[美]阿拉巴·赛:《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2003年,全球移动电话用户数首次超过了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不再是仅仅被作为固定电话的替代品而存在了,而是在更大程度上扮演了固定电话系统补充者的角色。
中国的移动电话发展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手机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固定电话的安装增速。到2016年5月,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2.966亿,b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www.miit.gov.cn/n1146312/n1146904/n1648372/c4967278/content.html,2017年6月28日。成为目前为止世界上拥有最大移动电话用户规模的国家。中国的手机通讯快速发展及强进的市场需求与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城镇化有着密切关系。加速
20世纪90年代,同手机的快速普及几乎同步,珠三角借由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每年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入珠三角寻求赚钱的机会。三来一补企业的低就业门槛成就了这些洗脚上田的农民工,他们在珠三角迅速找到了就业机会,在东莞、佛山等城市的企业中开始扮演起工人的角色。进入到新世纪后,珠三角地区开始迎来了新生代的农民工,这些年轻人无论是在年龄结构上还是素质结构上同上一代的农民工相比都占据了明显优势,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同过去一代农民工截然不同的身份特征。这个群体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是低年龄和高素质的,而且他们不愿像父辈那样把自己束缚在土地上,向往城市的生活和文化,对外部社会有着强烈的向往和留恋,对家乡的情感随着在外时间的增长而逐渐淡漠。a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手机用户群,同以往的关于手机的群体研究来看,这个群体的手机使用方式既不同于商务职业人群,也不同于那些经商的生意人。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教授将其称为“信息贫乏阶层”(information have-less),他们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构成了一支至关重要的劳动力,尤其是在远程通信的发展中,他们构成了一个手机使用模式与众不同的庞大用户群。b[美]曼纽尔·卡斯特尔、[西班牙]米里亚·费尔南德斯-阿德沃尔、邱林川、[美]阿拉巴·赛,《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1页。
选择手机消费和使用模式作为本文的切入点,是因为生产和消费是现代社会,尤其是都市社会运转的基本保证,任何个体,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移民,其生存都必须围绕这两个方面来组织和安排。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上,他们必须学习如何通过市场将自身的劳动力出售给有计划的生产单位,这样的标准化劳动同乡村社会的散漫的自律性劳动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即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学会了如何规训自己的身体。通过有计划的劳动他们获得报酬,并且再次通过市场购买产品和服务,习得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同过去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是极为不同的,生产和消费严格分开。就是在这样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完成了都市性和现代性作用在其原有身体上的改造。选取“生产—消费”这样一对概念链接,将其二者同时放置在同一社会空间的同一个群体上,从日常生活中的手机使用模式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性和都市性的双重作用下建构起的自我认同是本研究的基本面向。这样的阐释逻辑可以避开以往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中既有的预设视角,跳出二元对立的前提,避免理论层面的无意义重复讨论。
作为中国社会改革进程的生力军,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可以折射出中国正在经历的现代性图景,作为在工厂劳作的农民工,他们来自农村,身份上带有浓重的乡土性,而这种乡土性的存在空间却是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工厂、工厂区的标准化生活与农业社会的乡土性并置。同时在文化形式上,乡土社会的传统惯习与都市社会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并存,工人们迫切地通过消费来靠近和认同都市文化。在社会形式方面,巨大的贫富差距凸显出农民工与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之间的差异。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消费和使用研究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现实空间是如何借助新的传媒技术被加速压缩的,而工厂中工人们的人际关系依旧是嵌合在传统的关系网中,借助手机和移动互联网,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进入到网状的、更加发散的、特殊化的、以趣缘或消费为主导的新型社交网络中。“符号—空间经济”共生,线上线下的指示关系是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网络社交生态的真实写照。
网络与现实、线上与线下的共生和指示关系是新生代农民工手机应用策略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是在现代性的形塑下个人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做出的理性选择。这既是主动选择,也是现代压力所致。因此,吉登斯说,现代性在非常私人和亲密的层面上重建了日常生活。c[英]安东尼·吉登斯、[英]克里斯多夫·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96页。在现代中国的珠三角地区,当新生代的农民工带着凝固的传统生活形式面对日益流动的都市性体验时,他们也开始反思自身,开始逐渐脱离传统,形成一套新的能够适应都市体验的生活经验。这也就是贝克所说的强迫的现代性,每个人都无法回避。他们必须快速掌握都市文化的运作法则,加入到现代性的行列,而社交网络的重构必以个人为构想和实践的单位。
人际交往是笔者所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规划的重要内容,因为对于所有人来说,生活的规划都是以身份为基础的,对这群从农村走出,进入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都市中生活规划的重建包含了相当多的社会关系的维系和重构。本文的研究,无意于在传统的批判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争论中偏向于工厂对于农民工到底是发展还是剥削的站位,笔者想要试图跳脱出传统农民工研究中浓重的政治经济学的宏大叙事,更希望贴近这个群体的日常生活,利用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方法,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状态和日常交往的过程。从乡村到都市的这个群体如何在这样的快速且流动的现代性中借助互联网规划自己的生活是研究重点。
手机社交应用软件是农民工互联网交往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主要考虑到在中国,手机是最为重要的互联网交往的使用平台,这同欧美国家的互联网发展实践中个人电脑作为互联网使用的主要平台是不同的。a[美]马克·格雷厄姆、[美]威廉·H·达顿:《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胡泳等译,成都: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29页。由于手机具有的私密性特点,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无法完全通过观察和访谈的方法检视到工人们手机详细的信息和通话内容,因此,为了同时兼顾人类学一贯以来对“实际生活中无法解释的事情”的兴趣和田野的伦理,笔者尽量选择从手机应用的选择和使用层面来展开研究。从手机到社交网站,应用软件可以算是当今社会网络生存的个体生活中最为“日常”的东西。学术界和互联网行业对手机媒体的讨论,围绕着从空间重组到弹性时间,从虚拟社区到现实空间,从虚拟货币到数字版权等问题争论,然而在这些争论中大家仿佛都忽略了一个观察的角度,那就是关于手机的基础应用程序的讨论和分析。手机应用是所有用户使用偏好和习惯的具体表达,安装在手机上的软件及每个软件的使用频度是测量使用者和手机之间关系以及使用者如何赋予手机以文化意义的重要指标。本文想要讨论的,就是手机社交应用的实践是如何展开的。新生代农民工手机社交应用的使用偏好的人类学研究可以有效地解决人际互动的问题,从中可以揭示出这个群体如何利用手机来理解都市文化、组织生活策略。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交往生态:“链接”与“断开”的策略
一般来说,多数人对农民工的认识普遍都是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工作环境恶略等,因此对于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的刻板印象也往往都是他们不会在移动通讯上支付太多的花费。而恰恰相反,以往研究,印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都会很积极地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各种通讯工具,而且与本地人相比,他们用于支付通讯消费的开支占每个月收入的比例要比当地城市居民的比例还要高。b杨善华、朱伟志:《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解读》,《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在笔者调查的东莞市A箱包工厂,所有工人,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工人每个月的工资一般在2500—3500元之间,而每个月在手机上的花费大概在400—800元不等,平均占到他们每个月工资收入的20%。当然这样的花费还不算投资在手机设备更新上的费用。在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有6成以上的人表示会在一年左右更换一次手机,更新的手机平均价格为1800—2200元。高昂的通讯信息费用主要发生在同远在家乡的亲人和朋友之间的通话上,长途通话费用占到他们每个月平均通讯费用的一半以上。这样的消费不难理解,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离开了父母、朋友,背井离乡涌入陌生的城市,在其充满了希望和焦虑、恐惧与彷徨、交织着悲欢的日常生活中,手机成为了他们保持与家人朋友联系,纾解情绪的唯一途径,只有在这个虚拟的场景里,他们才能体会与家人在一起的欣慰和轻松,而通讯的经济成本考量被放到了一个次要的位置上。a曹晋:《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
新生代的农民工进厂的工作主要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高强度、技能简单、重复性高、经常性加班成是主要特征。笔者调查的A厂有时因为接到了大宗的外贸订单,急着出货给客户,就要求工人必须加班,甚至有时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天长达18小时。即便是平日不急着出货的时候,每天10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长也是常态。扣除掉必要的休息时间,根据笔者的观察,工人们每天能够用于休闲的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而这三个小时通常又都集中在晚上的八点以后。因此,每当夜幕降临时,很多工人就会挤在工厂办公楼周围,利用免费的WIFI“蹭网”下载自己喜欢的歌曲和视频到手机上,留存日后慢慢看。在征得工人同意后,笔者检视了他们的手机,发现在他们的手机上,安装的手机应用中排名第一名的是“WIFI万能钥匙”。他们坦言利用万能钥匙能够轻而易举地破解工厂周围大多数的无线网络密码,免费蹭网。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节省很多预付手机卡套餐中的无线网络使用流量。
工人们会将短暂的三个小时左右的闲暇时间中的大部分都用在手机上,其中用于打游戏、收看视频及听歌上的时间会占到两个小时,而剩下的一个小时他们会选择在网上社交。同样,通过安装的手机应用排名我们可以发现,QQ是他们选择的使用最多的社交应用,其次是QQ空间,排名第三的是微信。QQ在所有的社交类应用中排名第一,是这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通过访谈可以发现,这个群体其实同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了电视等媒体,同样对于互联网的感知和触碰也比他们的父辈早,而他们中的多数人“触网”就是从QQ开始的,他们在QQ上结识网友、将线下的朋友转化到线上并维持关系。而今他们离开了家乡,QQ上原来积累的很多基于地缘的朋友关系也随着QQ被他们带到了城市里,因此QQ织就的社交网络成为了他们重要的交往空间,虽然今天微信井喷式发展,很多人开始弃用QQ,转而将社交空间转移到微信。对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来说,QQ并不仅仅意味着网络上虚拟的社交空间,其中还承载着相当多的依托于地缘空间而结识的朋友,因此成为这个群体使用得最多的即时通讯工具。
排名第二的社交软件“QQ空间”也是这个群体媒介生态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又一个重要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年轻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卫生条件用恶劣来形容并不为过。一个8平方米左右的宿舍挤住着12个工友,每个楼层只有一个洗漱的水房和公共厕所,为了防止火灾,所有宿舍中不允许使用插线板,工人们的手机必须拿到一楼统一的图书阅览室充电。这些现实的生活工作场景同网上美轮美奂的“QQ空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女孩子们会将自己的空间装扮得丰富多彩,将憧憬中自己未来的“家”的场景在网络中尽量实现,配以或优雅、或时尚的音乐。这空间正是她们和朋友在网上社交的重要空间,她们在这里编写、转发着各自感兴趣的故事,并与朋友分享。这里成了打工者们唯一可以发泄生活不满的地方,也唯有在这里,他们才是主人。无论是在机声隆隆的车间,还是酷热难耐的工地,只要有手机,有网络,人们似乎总能逃离劳作,在虚拟的世界中找到片刻回“家”的感觉。b[英]丹尼尔·米勒、[澳]希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排名第三的社交应用是时下最受欢迎的微信。微信的社交功能在效用的实现上对于农民工来说与QQ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在这个群体中“附近的人”这样一种微信自带的随机交友功能成为这个群体网络社交的一种重要样态。在调查的厂区中,无论男工女工,无论年龄高低,都使用过这样的随机交友的功能。而通过与他们的访谈,笔者发现,在选择“附近的人”作为一种网络交友模式时,他们的动机是同线下交友的动机完全不同的,并且在这种动机下所采取的实践策略也完全不同。
【个案一】小勇,男,1987年出生在四川省重庆市酉阳县,土家族,2014年和家乡几个年轻小伙子结伴来到东莞打工。作为已经到广东打工一年多的工人,他自认为已经很熟悉广东的文化以及当地的人文环境,在聊天过程中经常表现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在同小勇做观察时,笔者发现每天放工后,他都一个人坐在宿舍楼下靠近办公楼的台阶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不停地摇着手机搜索附近的人。每当搜索到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时,他都会热情地和对方打招呼,加对方好友。“美女在哪里?美女吃饭了吗?美女要不要一起吃饭?”这三句话是小勇每次和一个陌生的女孩子打招呼时必用的问候语。当笔者问道为什么每次都用同样的话语还和不同的女孩子打招呼时,小勇回答说,“我每次这样不停地摇,每次不停地和对方打招呼,总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会回答我,这样我们聊起来就好了。我不用每次都换不同的花样,这样没必要的,反正我又不想和她怎么样。”
【个案二】生哥,男,1986年出生,湖南人,单身。之所以单独说生哥是单身,是因为生哥说自己是个很传统的人,娶妻生子是他来东莞打工的重要目的。他说在他的老家,尽管地处偏僻的农村,村里娶一个媳妇回家,最少也要30万块钱,其中包括了盖房、彩礼以及办酒席等一系列费用。生哥的人生目标很明确,他说他希望能够踏实地在工厂做工,最好能够谋个一官半职,这样他就可以在厂里找一个女普工回家结婚生子。生哥平时不太用“附近的人”这个功能结识陌生的女孩子,原因是2015年元旦前,生哥通过“附近的人”结识了一个自称也是湖南的女孩,两人在微信上逐渐熟络了起来。元旦后的一个周末,两个人相约在镇上的一个公园见了面,见面后生哥觉得女孩子无论是性格还是长相都很符合自己的择偶标准。当女孩子提出想去镇上的商场逛逛时,生哥也欣然同意了。当天生哥在镇上的商场花了将近1000元给女孩子买了衣服和鞋子,可就在第二天,女孩子竟然将生哥从自己的好友中删除了,从此杳无音讯。生哥伤心了好一阵子,从此之后他便不再相信任何网上的交友。
在厂区生活中,无论是上工时在流水线上,还是放工后在饭堂和宿舍,被骗、被讹诈、被偷被抢的话题每每出现在这些工人的聊天内容中。作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对这样的新闻已经见怪不怪,并且从这样的信息中总结出了一套自我保护的策略,所以个案一中小勇对于网络随机交友的态度就不难理解。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随机交友,维系友情和婚恋相亲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甚至可以在同一款手机应用上完成,例如微信。然而这三种交往行为的实践过程是完全不同的,首先随机交友是一种利用媒介和网络打发闲暇的手段,在这个实践中,交往主体之间往往将交往集中在线上,并谨慎地保持各自信息的隐秘性。线上与线下的关系相互转化的成本会变得很高,尤其是在时间成本的投入上。小勇说通常他都会在和对方聊过一阵子之后才会考虑要不要见面,而且即便见面了也就是到公园附近逛逛,顶多吃个饭,买点零食,不会投入太多的成本。
在维系友情的交往模式上,多数的工人选择了线上和线下互动相结合的实践方式。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A工厂中以地域认同结成的老乡群体众多,其中规模比较大的当属四川同乡和湖南同乡。以地域为基础的家乡认同是一种成本极低的交往实践,由语言、生活习惯等文化同一性所带来的信任是这种交往实践的基础。同乡的工人们会在微信上建立老乡群,平日闲时在群里无目的闲扯,分享一些家乡的信息。另外本地就业机会的信息也会首先在老乡群里传播,地缘认同会进一步得到巩固。除了线上关系以外,同乡之间也会将交往延伸到线下,周末闲暇的聚会成为了线下主体活动。厂区周围的小餐馆成了线下活动的重要场域,因为处于相对偏僻的厂区聚集区,因此这些地方的餐馆聚餐成本并不高,而且轮流做东请客也不会对这些工人的生活造成太大压力,平均每个人每个月的聚餐开销大约在150—200元之间,因此这种低成本的线下关系维系和频繁密集的线上关系互动成为了农民工们维系友情、拓展朋友圈的重要媒介实践方式。
婚恋相亲动机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社交实践中呈现出一种新特点,在笔者的调查中,工厂中的男普工普遍希望找到一个女普工作为自己的配偶,而反过来,工厂中的女普工普遍不希望找厂里的男普工作为自己的婚配对象。这样一种选择的不对称性使得社交软件,无论是QQ还是微信在作为婚恋动机的交往中都无法胜任。因此婚恋网站以及网络相亲等新兴的媒介手段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实践中应用度不高,他们还都是依赖于基于三度链接关系的朋友圈来获取交往对象的信息。
高额的婚姻支付以及传媒中被大量报道的关于网恋骗婚的新闻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将老乡作为理想的婚配对象,毕竟文化相通,家人比较容易接受。个案一中的小勇表示,在广东拍拖和结婚是两码事,拍拖的人可以有很多,但结婚的人只能有一个。他说广东这边的女孩子都比较“开放”,尤其是在网上,所以平时如果玩玩就可以到网上找人聊天,但是如果是谈婚论嫁的话,就绝对不能在网上找。高流动性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是这群年轻人必须面对的日常,而婚嫁则是终身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儿戏。在流动和传统并置的时代,在婚姻问题上,这些年轻人中多数选择了更加富有弹性的策略,在消遣玩乐时选择以链接的手段在网络中寻求满足,而在婚姻的问题上选择以断开的方式回归传统和道德。
三、指示关系的建构——理解农民工手机社会交往的理论进路
从上述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交往中不难看出,互联网带来了空间的多样态,虚拟与真实成为了当下社会交往研究中随时都会出现的概念。随着互联网与日常生活发生愈发紧密的关系,线上线下的互动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关于解读线上线下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其中有的研究不再把虚拟和现实视为彼此独立的空间。科尔曼在《通往数码世界的民族志方法》一文中提到,“大部分的研究不再将现实生活与网络生活区别对待,明显的区分不复存在。”aE. Gabriella Coleman,“Ethnographic Approaches to Digital Media”,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39, 2010.他察觉到,在学术界对于数码世界的讨论中虚拟和现实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而这融合的趋势变得越来越强。这样的趋势也恰好被现实的互联网和数码实践所印证。人们对于互联网的所有的实践经验都指向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融合,因此这样的融合论不需要任何的批判就开始在学术界蔓延开来。bRichard Rogers, The End of the Virtual: Digital Methods, Amsterdam: Vossiuspers UvA, 2009, p.29.在学术界我们能够发现,虚拟与真实从一开始就被一种天然的二分法结构起来,现实世界被形容为真实的,网络世界则被形容为虚拟的,而即便出现了所谓的“融合”,虚拟与真实的对立也是根深蒂固地烙印在研究者和实践大众的头脑中。而该如何正确看待互联网所承载的线上世界和线下世界,人类学家爱德蒙·利奇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给了我们启发,他在《反思人类学》一文中说:“我们的任务是理解和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社会如何运作。这就像一个工程师试图向你解释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原理,他不会花时间和你细分每个螺母和螺栓。他关心的是原理,而不是东西。他会用最为简洁的数学方程,如0+1=1; 1+1=2 等等来表达这些原理。这些数字代码代表了信息传输中的正冲与负冲。”cEdmund R. Leach, Rethinking Anthropology, London: Robert Cunningham and Sons Ltd, 1961, pp.1-27.螺母和原理的关系对于在当今互联网世界我们该如何看待虚拟和现实的关系颇有见地。互联网和物理空间的关系如果用利奇所说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来加以阐释,相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前文所说的简单二元论的论断。
相应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教授汤姆·毕昂斯托夫(Tom Boellstorff)在探讨建立数码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时提出了一套和利奇所说的能指所指的理解方式类似的方法——指示理论(indexical theory),用来理解和反思数码人类学。指示性理论来源于语言人类学,强调符号与被指示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同时将特定的时空环境联系到指示关系中,讲求在情景中获得和理解意义。dAlessandro Duranti,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7.由语言学中的“情境性指示关系”推演,互联网人类学可以利用此种关系来思考互联网世界中的真实和虚拟的关系。虚拟和真实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区分,而是共同作用于同一情境下,面对多元空间的多元身份建构起的一种新的社会现实。指示性关系超越了线上和线下二元对立的同时,又可以很巧妙地避开简单“融合论”。
A工厂里的农民工在珠三角的交往实践体现出的正是个体在面对多元的空间中的多元身份时,利用在不同空间的移动来策略地组织自己的生活,更好地面对都市现代性的典型案例。他们虽然使用同样的社交应用,但却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利用多元身份建构起了一种新的社会事实,这其中既包括线上的社交空间,也包括线下的社交空间。这里所展示的两种空间并不是以往的互联网研究中虚拟和现实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在具体的社会时空情景中的指示性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的线上社交关系的构建和交往中的策略实践并不是简单的线下关系的象征。实际上,线上关系是由线下关系所引发的结果,无论体现在网上的随机交友行为还是QQ空间上的社交行为。由于工人们所处的珠三角地区工厂的社会时空情景的特殊性,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半径就被局限在厂区周围的1.5公里的范围内,工作的劳动强度大、闲暇娱乐活动单一、用于闲暇的可支配收入有限等因素决定了这个群体的社交实践更加看重维系成本较低的线下同乡群体交往,体现出物理空间社交的深层化特点。物理空间的交往能够实现和满足农民工群体大部分的社交需要,例如信息共享、情感联络以及极为重要的文化认同。而在网络社交的实践呈现出了浅层化社交的特点,因为他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投放其中,泛化的交往往往是出于闲暇和娱乐的目的,支持的功能被弱化了。虚拟世界正在崛起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而这样的社会现实无法仅从物理世界的现实中推断出来。例如,农民工在社交应用上的互动,情绪及各种社交活动,是无法被一一对照于物理世界的,因为他们在网上的身份往往与物理世界中的不同。这是一种规避互联网交往风险的策略手段,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利用现有的知识水平和生存技能无法娴熟驯化互联网技术的一种保护举措。他们策略地不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带入到网络中,选择一种最大的安全距离维持线上同线下的关系。
四、结语:虚拟与真实的交互——互联网人类学的方法进路
人类学对互联网的研究开始关注的是对于互联网的使用,也即通常所说的科技驯化(domestication of technology)a。在对互联网的技术驯化过程中,移动互联网的使用,表现在手机的使用上是最为明显的。珠三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手机及手机对他们的社会交往产生的影响时,会主动地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情景将手机及移动互联网赋予新的意义。人类学关于手机的个案研究已数量不菲,然而理论进路的创新却踟蹰不前,近年也未见有所突破。本文尝试从指示性的关系角度理解互联网文化,理解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力图从一种新的角度建构起人类学理解互联网的文化模式。人类学的研究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就强调整体论和情境论,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也需要延续人类学的传统。指示性理论的应用可以在关于手机和互联网的研究中建构出一种广泛存在的网络情境,在情境中关注意义的生产将是互联网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