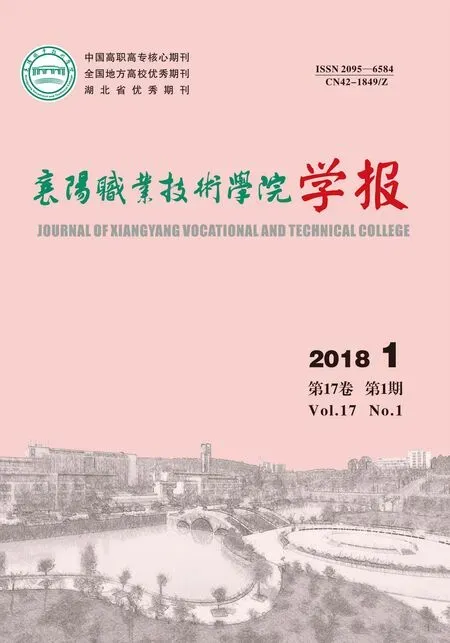重写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四大视角
王姗姗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 重庆 400715)
中国文学思潮开化给知识分子更多自由。当代文学史家致力于不断开拓新视角来探究中国20世纪文学史,以求呈现具有全新意义的文学史成果,这也是20世纪兴起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浪潮的原因之一。重写文学史,狭隘上指《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至1989年第6期所开设的“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专栏,使“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特指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第二层意义指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的再认识。从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建构的基本话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这对中国近百年传统文学史视角造成了强大冲击。
时至今日,当代重写文学史中最为突出的视角暂大致总结为四种:人性化、纯文学、性别化、科学化。(每种视角暂且只以一部名人代表作品为例分析,以求较为详尽解释各个角度的具体所指)
一、人性化视角
要在重写文学史中突出新意,就需打破人们对于文学史的传统看法,甚至重估已被接受的定论。这要求研究者有独到视角,发现常人所不能发现。在重写成果中存在突出的人性化视角,即发现人类发展进程中愈加丰富且深刻的人性,且以动态性方式去探究已成为历史的文学。当代社会日新月异,人须保持自身变化以求适应。而当下极富个性化的时代,传统注重的集体性、普遍性,逐渐让位于人性化、私人性。
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就是从人性化视角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的典范,呈现出全新文学史。李欧梵把中国新文学杂志的涌现、社团流派的产生、浪漫作家的成长等都归结为人性化因素。李欧梵没有从历史必然性去分析社团的宗旨、意义、刊物、思想等,也不归纳其系统和中心,而从人的关系、兴趣和私密情感等方面出发。甚至新文学发生之后一系列文学论争,李欧梵也论证为主体在人际关系上的矛盾。其实关系不和的背后必定隐藏个人学术思想和教育背景的差异。但李欧梵并不遵循传统,而是从人性化出发。说到底,辩争和组合都是由于人的因素。[2]李欧梵从每个文学人物的具体生活、兴趣和背景出发,重新解读新文学,让新文学更具人性化、个性化。
在文人形象塑造上,李欧梵采用的虽是传统纪传体框架,却以文人个人情感变化为主线去总结其思想形成原因。如李欧梵不从“翻译家”既定头衔解读林纾,而从其个人家庭入手,看林纾如何构建起饱满的人格。并将其所受文化教育、外来影响融入情感和道德,以分析林纾内心构筑的英雄主义世界。同样,在塑造苏曼殊文人形象时,李欧梵注重剖析他的人生情感历程,并与其小说创作中的幻想性结合,挖掘他性格上的激情、主动、放纵,及对女性情感上的主观和热烈。在探究为人熟知的徐志摩时,李欧梵也从感性起源分析,归结为“林氏妇女”对其感性上的牵引和发展,如此另辟蹊径,就不难理解其作品的自由、情感和理想主义。
李欧梵在对现代文人的解读时,努力挖掘其人性化潜能,探究想象、英雄主义、感性等方面的可能,以打破传统思维对人造成的生存和思考困境。如此就揭去了中国文人、事件等标签性,也使中国新文学变得可触可感。文学史被人性化解读,变得具体丰富,且使读者减少对文学作品和人物的误读与偏离。李欧梵从浪漫主义出发,探究中国现代文人在感情与道德上体现的主体性、冒险精神、英雄主义等,提供全新视角去发现文学史参与者不同于其时代、流派而独具特性的人性。
二、纯文学视角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理论研究不可逃避的问题。新时期以来,文学思想进一步解放,且试图远离政治场域,给文学以全新的解释。于是一批以纯文学观念为指导的新文学史文本不断涌现。研究者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把更多精力放在文学本身,从而拓展文学本身拥有的广袤与丰富。
纯文学至少有三种既相关又有区别的含义。第一是指与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相对的现代独立的文学学科观念。第二种则是与工具论文学观相对立的自律的审美的文学观。第三个层面,与商业文化相对抗的纯文学观念,讲究文学的单纯性。[3]要求远离政治,注重文体形式特征、文学情感、语言等本体性因素,甚至排斥分析文学作品思想意识。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以诗画结合为美学宗旨,以情感为尺度,以诗情为关键词。司马长风打破以往按历史政治分期的习惯,批判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是“削文学之趾,以适政治之履”。他按照文学内部自身发展节奏,将其分为诞生期、成长期、收获期、风暴期、沉滞期。中国新文学史大都习惯以《新民主主义》分期为准,但司马长风认为文学不可能与政治和历史完全保持一致,力求把文学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评价文学作品和作家时,司马长风以“诗情”为理念。小说类,中长篇小说七大家中最被其称道的是“独立派”,包括沈从文、巴金、老舍、沈从文、萧乾、陈铨等。诗是文学的结晶,也是品鉴文学的具体尺度。[4]从沈从文的诗情、巴金的人性人情、再到李劼人牧歌式的抒情,司马长风以诗的标准一以贯之。而紧跟时事政治的茅盾和《革命前的一夜》的陈铨也受到司马长风高度评价,原因是两人以超脱政治的姿态对社会忠实描写,用非政治话语描写时代,并在描写中展示史诗般的鲜明独创性。当然,这并不是司马长风文学观的犹疑,而是他意识到与政治彻底绝缘的文学是不存在的,既如此,一旦与政治交会,文学应保持独立性,即不粉饰政治。
诗情不仅是评价小说的标准,更是评价诗歌应有之准则。如果说在研究小说时,司马长风不得不提及政治的话,那么在评价新诗时,其基本完全远离政治,主要关注审美观念和创作技巧。他强调诗要含蓄表达情意,即以有限的字句,表达不尽的情意。具体说,是以意象暗示等手法表达诗情。其对闻一多的评价最高,认为有感有歌,既情感丰富深刻,又保留古代诗歌创作的音律和谐,形式工整。但他对卞之琳评价仅以“苍白晦涩”总结,认为其质薄而艺奢,只罗列了李广田对《白螺壳》的解读,自己并没有参与卞之琳诗歌的分析。当然这种评价有失偏颇,但也表现出司马长风对于诗情的看重。
文学不可能真空,远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作家奥威尔认为:“没有一本书是能够真正做到脱离政治倾向的。”[5]如果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作为来源于生活的文学也必然会将政治写进文学。但既然是写文学史就必须保证文学性的主导和主线地位,且不再为政治服务,不粉饰。这些归根结底是为了追求文学独立地位。
三、性别视角
从20世纪女权运动开始,女性主义逐渐被广泛运用到文艺理论研究中。1953年波伏娃的《第二性》凸显女性在反抗中的重要性,也让女性视角走入研究者视野。凯特·米勒特在1970年著的《性政治》中首先提出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从此,女性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研究被提到女性主义日程的中心位置。[6]尤其是1990年以来随着宏大叙事以及相关文学中心话语的消解,文学进入“无名”时代,女性话语格外活跃。[7]伴随着伊利格瑞的后结构主义女性,女性逐渐成为一种解构话语权力和传统艺术的方法所在。在哈贝马斯看来,妇女运动就是新社会运动,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使其再生长。而在拉康看来,后结构女性主义中,女性因为其语言的不确定性、非线性而代表着想象界,是用来解构象征界的重要方法。简言之,女性视角的出现成为研究者解构传统思想、构建新世界的途经,具有相当丰富的方法论意义。
意义在于,首先,从女性视角能够看到问题的丰富性,尤其是原本看似已成定论的问题,因女性视角的切入而变得新鲜。其次,是一种比较的方法,因女性总是拿来与男性相对比,其所代表的新视角与传统的父权视角进行交锋,具有话语思维独特性。性除因男女生理构造的不同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对方的好奇之外,性也因西方中世纪禁欲主义及东方封建时代灭人欲而变得令人着迷。不仅如此,伴随不断发展着的人所拥有的猎奇心理,性也不断被人重新发现,且赋予更多意义。
以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为例。刘剑梅创作时受西方学院派影响,擅长用解构学,解构革命文学大传统,同时,她也弥补解构学的不足,用自己的理论进行构建。这些得益于她对女性视角的运用。刘剑梅从女性作家和作品中的女性表现为线索,重新讲述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史,并探索文学中的女性话语,以此对抗长久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话语权。刘剑梅能清醒认识政治革命话语和情爱话语之间的差异。由此探索中国新女性在文学作品的逐渐成长,即由女性、到新女性、再到革命女性。
左翼作家因为“政治”介入,常被诟病,但夏济安、李欧梵等发现左翼作家的丰富人性,刘剑梅也不例外。她以女人的敏感性,利用在西方学习到的女性主义理论,从女性视角出发,从情爱和革命关系入手,进一步强调中国现代作家的分裂性。中国现代作家身为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土崩瓦解,以及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冲击时,其充满责任感的内心是矛盾和痛苦的。即便小说在创作方法上显示出早期实践的幼稚简单,也不能完全掩饰住人性的复杂。刘剑梅认为“革命加恋爱”公式的一再重复,体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性困境,即虽得到集体认同,但在面对现代与传统、理想与现实、个人情爱与集体愿望时,现代人的分裂与孤独感使其内心焦虑。
通过探讨权力与性别、政治与文学的交织,我们希望能给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女性批评的视角,[8]特别是抓住“女性身体”中介,说一些以往现代文学史家未说过的话。这是刘剑梅的目的。刘剑梅认为女人的身体与内心紧密联系,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在欲望的表层下隐藏着内心强大的情感力量,理应包括对父权社会的压制的反抗和愤怒。女性,正是代表了个体生命在大革命时代下充满艰辛与内心搏斗的精神历程。
四、科学视角
周晓风认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追求科学方法,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区别于传统文学研究的重要标志。[9]事实上,从周作人起,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就已经开始运用科学方法。他在《人的文学》中曾说,“我所说的人乃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很明显,这是受到了西方进化论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
科学在文学中到底是什么?泰勒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到“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因素,其贡献在于把社会学科学纳入文学视野,用实证方法代替较为含糊的文学理论概念。
中国传统文论也有理性,然主体上为人所熟知的还是印象式研究。以主观性为主导,缺乏系统和理性总结,且要求研究者具有丰富且高深的知识储备,虽给接受者以美感享受,却不易被准确把握和操作。
金介甫在《沈从文传》新版序中就说,对中国历史、地理感兴趣是吸引他研究沈从文的原因之一,并希望通过对历史、亲属和当时所处环境的研究使得对沈从文的研究更深入一步。金介甫认为不应该把沈从文的生活只写成作家传记,而应该作为进入中国社会历史这个广阔天地的旅程。[10]社会学视角下,金介甫分析沈从文从乡下人到城市人身份转变及由此带来文本中人物设置变化。湘西有明显的地域性、种族性,特色鲜明,充满了神秘色彩,金介甫用西方变态心理学分析湘西尚武的民族个性,部落猎奇心理等。此外,金介甫也总结沈从文受到的西方科学影响,比如人种学、存在主义、自然主义和心理学等方面知识,且以具体作品为例分析,如金介甫在《龙珠》中找到许多沈从文运用社会学的语句。而沈从文对家乡的原谅和爱恋也在金介甫这里归结为因其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热爱生活的影响。这些都不置可否,毕竟沈从文做过社会学的教授,且信奉社会科学本来就是五四精神的重要内容。
金介甫为创作《沈从文传》来到中国,走访湘西和苗族,掌握第一手原始资料,这种材料举证的实证方法,使得沈从文的经历和思想来源确实可考,令人信服。他称赞沈从文是一个完全中国气派的作家,没有一点西方色彩,他想要强调沈从文是因受其特定社会、时代、种族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足以见得社会学视角的分析是其得出如此定论的原因所在。但秉持着实证方法,金介甫也不得不依实记录。在沈从文看来,较高的文学评论是要采取一种美学角度,显然这种科学方法的介入,并不是沈从文的最高追求。
五、结束语
虽然这四大视角各具特色,被用来研究出众多杰出的成果,而这四个视角却不会因此而相互独立。相反,甚至在同一部学术作品中经常会出现各种视角交融而用的情况。如此才不会在主讲某种视角时以至于偏废文学的丰富性,也能兼用其他视角弥补本身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总之,这些视角为传统既定文学史开辟了全新的视野,在呈现不同文学史的同时,也为文学的独立性作出了重大贡献。
[1]张颐武.“重写文学史”:个人主体的焦虑[J].天津社会科学,1996(4):76-80.
[2]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27.
[3]刘小新.“纯文学”概念及其不满[J].东南学术,2003(1):140-142.
[4]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M].香港: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37.
[5](英)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M].董乐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01.
[6](美)本·阿格.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M].张喜华,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47.
[7]丛鑫,突围的陷阱:女性的写作反思[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3-6.
[8](美)刘剑梅.革命与情爱[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
[9]周晓风.现代文学研究科学方法的反思[J].文学评论,2006(3):177-182.
[10](美)金介甫.沈从文传[M].符家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1.
[11](德)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J].查明建,译.中国比较文学,2010(2):2-6.
[12]刘丹,流散语境中的后殖民批判[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2-7.
[13](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M].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