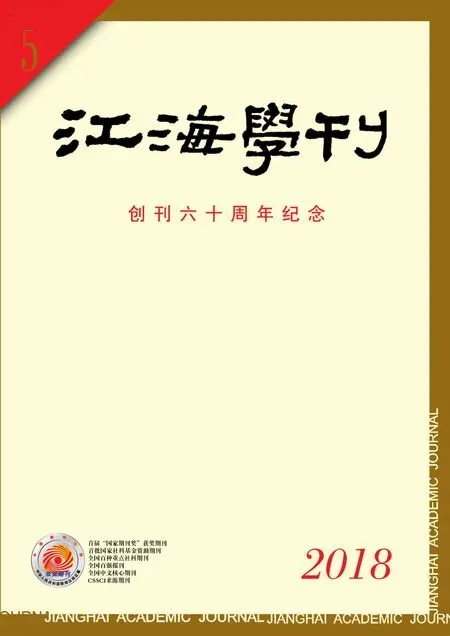围绕京杭大运河之“蓄清刷黄保漕”的反思*
——以淮源、洪泽湖、高家堰、泗州城为例
内容提要 京杭大运河作为“人”加诸大地的符号、象征或标志,值得进行系统的“正思”与“反思”。以明清两代言,具有积极意义的淮源的探寻、难以评说的洪泽湖的扩大与高家堰的成型、酿成悲剧的泗州城的淹没等例,即与其时京杭大运河“蓄清刷黄保漕”的国家大政密切关联,而彼此之间也是相互勾连。如此,当今如何客观认识、全面考察曾经的京杭大运河之利弊得失、功过是非,可谓极为复杂、又极为重要的问题。
就笔者的感觉言,京杭大运河作为“人”加诸大地的符号、象征或标志,不仅其“文化”——“人文化成”的意义特别典型,而且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等等复杂的联系与广泛的涉及,也堪称典型。唯有系统地“正思”与“反思”这样的“典型”,辩证地肯定或质疑这样的“人文化成”,或才不失学者的初心与士子的责任吧。只是兹题甚大,故此谨就文题所示范围,先行举出四例,以见笔者的某些认知与思考。
“蓄清刷黄保漕”的插曲:探寻淮源
从现代人的思维来说,探寻淮河之源,是个“科学”问题,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多次组织科学考察队探寻黄河之源。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语境,那么诸多江河的探源活动尤其是国家层面的探源活动,其实多与“科学”无涉。①比如由于黄河决口泛滥,难以堵塞,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派遣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务穷河源告祭”(《河源纪略》)。因为在中华传统理念中,告祭江河之神最合适的地点,或在源头,或在入海口。换言之,中国古代官方的这类活动及其取得的“科学”成就,往往是“迷信”的结果。淮河之源的探寻,也复如此,是为京杭大运河“蓄清刷黄保漕”的一个插曲。
淮河之源何在?历代史籍对此多有记载。如《尚书·禹贡》云:“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即大禹疏导淮河是从桐柏山开始的,这是有关淮源最早、最权威的记载;《山海经·海内东经》云:“淮水出余山,余山在朝阳东、义乡西,入海淮浦北”;又《汉书·地理志》“平氏县”下云:“《禹贡》桐柏大复山在东南,淮水所出,东南至淮浦入海,过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与《禹贡》《海内东经》相比,《汉书·地理志》的可贵之处在于记载了淮河的流经里程,这是关于淮河长度的最早历史记录。虽然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参照依据。及至三国,《水经·淮水》云:“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东北过桐柏山”;北魏郦道元注曰:“淮水与醴水同源俱导,西流为醴,东流为淮,潜流地下,三十许里,东出桐柏之大复山南,谓之阳口。”郦注对于淮源的记载可以说已经比较详尽了。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引文献中,桐柏山、余山、大复山、胎簪山云云,并不一致。对此,清人胡渭《禹贡锥指》卷十一指出:余山是桐柏山的别名,大复山和胎簪山皆为桐柏山的高峰,远望犹如一山。也就是说,史籍中的桐柏山、余山、大复山、胎簪山等等,虽然记载有异,或就主峰而言,或就支峰而言,但都可统称为桐柏山。
淮河发源于桐柏山,应该无疑。然而淮源究竟在桐柏山的什么位置呢?“眼读”显然不能解决问题,还得依靠“脚读”。目前所知最早的淮源“脚读”活动,发生于北魏孝文帝年间(471-499年)。《魏书·韦阆传附韦珍传》:“高祖初,蛮首桓诞归款,朝廷思安边之略,以诞为东荆州刺史。令珍为使,与诞招慰蛮左,珍自悬瓠西入三百余里,至桐柏山,穷淮源,宣扬恩泽,莫不降附。”韦珍的淮河探源,既不是游玩也不是探险,而是招抚蛮左的政治活动中有意无意的一个副产品。遗憾的是,因为史书记载的阙略,韦珍“穷淮源”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是不得而知。
延及清朝,淮源似乎逐渐清晰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脚读”活动,就是乾隆皇帝两次命令臣下踏勘淮源。乾隆第一次命令踏勘淮源的臣子,是河南布政使江兰。但江兰办事有些马虎,接命后可能并未认真踏勘。他来到固庙②,发现在禹庙东边有三大井涌出三泉,认为这就是淮源,便加以简单的淘浚引导后,又绘制了一张淮源地形图,匆匆复命了。孰料乾隆对此事万分关心,既拿出《大清一统志》核实,又查阅地图比勘,结果发现江兰的报告于文、于图都相距太远,“予思《一统志》载,淮水有伏流数里、涌起三泉为井之文,且阅今图中冈涧稠复,知所谓三泉者,未必即真源也。”(乾隆五十四年御撰《淮渎神庙碑记》)
有鉴于此,乾隆又命河南巡抚毕沅亲往查勘。毕沅从桐柏山麓迤逦而上,大约翻越了十六、七里,来到中峰胎簪山,这里有一潭清水,波光粼粼,询问当地土民,说是“淮池”。再沿着险象丛生的羊肠小道爬行十多里,到达山顶。顶上巨石盘踞林立,姿态万千,占地十余亩,气势十分壮观。旁边洼处有渊水辉映,泉流从石间奔涌而出,淘沙涤砾,取之不竭。毕沅认为这便是真正的淮源。对于这一结论,乾隆甚为满意,说它与《水经注》中淮水出胎簪山、潜流复出的记载“印证悉合”,四千多年前“导淮自桐柏”的说法果然不虚,“是为淮渎其源也已”(《淮渎神庙碑记》)。
然而这仍非淮河真源所在。③问题在于,乾隆皇帝“推求精确,不惮再三”地探寻淮源,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这绝非乾隆一时头脑发热、心血来潮,更非“科学”探索精神所致,而是另有特别用意,这在其亲撰的《淮渎神庙碑记》中说得很清楚,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为了京杭大运河的“蓄清刷黄保漕”。
按中国自从唐宋以来,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都发生了重大变迁。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华北平原的北端,经济中心则偏居江南。又就元明清三代论,除了明初短暂奠都南京,其他时间都在北京建都,这种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格局,使得王朝背上了莫大的包袱。京畿自为人口集中之地,麇集于此的皇室、贵族、官僚、军兵仆役及其他人员,或挥霍无度,或山珍海味,或绫罗绸缎,或亭台楼榭,官奉日用,常规消耗着难以计数的民脂民膏。然而京畿北部及东北为游牧狩猎之区,华北平原又太贫瘠。如此情势之下,政府只得仰仗江南。滔滔运河之水,昼夜舳舻相继,载输着江南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京都。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这并非亘古不变。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后期,“国之大事”实在运河及漕运。运河及漕运沟通了南北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解决了两者分离所造成的窘困,打破了“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自然规律,从而成为王朝的经济维系线和政治生命线。
然而,京杭大运河在给王朝带来种种实惠的同时,也引出了无尽的忧患与难解的麻烦。由于运河纵贯南北,而淮河横亘东西,北方的黄河又长期夺泗入淮,交相会聚于清口(在今淮安市西南),再加上黄、淮、运三者河性水情各异,因而其间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为了保证运河及漕运的畅通,乾隆皇帝真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所谓“江南三大政”河、漕、盐,河、漕即居其二。形象些说,运河的畅通与否就是乾隆脸色的晴雨表。运河塞了,乾隆哭了;运河通了,乾隆笑了。
那么,如何确保漕运的畅通呢?明季以来,一直沿用的是潘季驯开创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蓄清刷黄”(《河防一览》卷八)的治河策略。可是黄高淮低,黄强淮弱,要使运河畅通,就必须保证淮河有足够的流量,洪泽湖有足够的水位,于是治淮成为刷黄保运的首务。乾隆对此当然深有感悟,他说:“往岁黄河安澜循轨,专藉洪泽湖蓄淮之清水,以刷沙敌黄,而粮艘经山阳清河间,亦资淮利济。”(《淮渎神庙碑记》)然而一旦豫皖两省雨泽愆期,淮河水量下降,淮河弱势便形明显,洪泽湖水位便会降低,清口即有淤塞之患,黄河即有倒灌之虞。为了解决刷黄保漕这个自然难题,乾隆夙兴夜寐,思虑重重,最终还是想起了四千年前的大禹。他以大禹自居,以承继禹业为使命,声言治水必须像大禹那样,从源头开始疏导,所谓“盖治水者,先疏其源,而后可以达其流,此古今不易之至理也”,故此“予于必发源之地亟加疏浚,祗迓神庥,夫亦宗大禹之志而已。”(《淮渎神庙碑记》)既要疏浚淮源,就需明确淮源所在,所以他委派藩臣探寻淮源,虔往致祷,调拨资金重修淮渎神庙,并亲撰《淮渎神庙碑记》,以示对长淮大神的感恩和崇仰,期望求得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乾隆认为淮河势弱、洪泽湖水浅,“意其初源必有沙石壅塞致遏,经流者不浚其本,何以畅其末”(《淮渎神庙碑记》)。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淮河与洪泽湖“蓄清刷黄保漕”的重大使命能够顺利实现,就必须从淮河源头做起,疏壅导滞,本末皆筹。④
要之,乾隆皇帝组织的淮河探源活动,本来无关今人习称的“科学”,而只是其导演的“蓄清刷黄保漕”政治大戏的一个小插曲。表面上看,乾隆皇帝是欲承继大禹余绪,着意于自然的疏川导河,实则完全服从和服务于其“蓄清刷黄保漕”的真实政治目的。
“蓄清刷黄保漕”的产物:洪泽湖的扩大与高家堰的成型
淮河探源是为了运河的“蓄清刷黄保漕”,这项洵属国家大政的成效则在洪泽湖水位,而控制洪泽湖水位的关键又在高家堰的高度、长度与闸坝。换言之,洪泽湖的扩大、高家堰的成型,可谓“蓄清刷黄保漕”的产物,然则京杭大运河引起的“连锁反应”,就是如此的复杂!洪泽湖一带原本地势低洼,分散着一些小的陂塘湖群,见诸记载者有富陵湖(又称阜陵湖)、白水塘(又称白水陂)、破釜塘(又称破釜涧)、羡塘等,其中破釜塘是洪泽湖的前身。“洪泽”之名始见于隋代,并与隋炀帝杨广有直接的关系。杨广是隋朝第二任皇帝,在位仅14年,即兴建四大工程(营洛阳、筑长城、凿驰道、开运河),前后十次征巡,可谓志存高远,雄心不已。隋大业中,杨广游幸江都,途经破釜涧时,大雨倾盆,洪水肆泛,因将破釜涧更名洪泽浦。明成化《中都志》卷二追述此事云:
洪泽浦在县北三十里,旧名破釜涧,隋炀帝幸江都,时久旱,遇水泛,遂更今名。
“洪泽湖”之名的出现,则大概在明代初年。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二云:
堰西为阜陵、泥墩、范家诸湖,西南为洪泽湖。
尽管明初已经出现洪泽湖名称,但此时洪泽湖面积尚小,仅相当于今洪泽湖区南部一隅之地。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之前,由于黄河始终迁徙无定,呈多股夺淮,泥沙被分散在各个泛道,徐、泗一线的来沙量不是很大,淮安以下淮河河道的沉积也十分有限,因而洪泽湖的扩展速度比较缓慢。大体说来,两宋时期的洪泽湖区是湖涧并存的沼泽区,元代洪泽湖的大部分湖区仍在兴办屯田,明代嘉靖之前在平水期仍然呈现出一派湖涧分明的态势。洪泽湖的最后形成,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
其一,黄河长期夺淮造成淮河下游河道的严重淤积。嘉靖二十五年以后,黄河由多股夺淮改为全河单股夺泗入淮,这成为加速洪泽湖扩张的有力催化剂。黄河单股夺泗入淮,全部泥沙滚滚而来,淮河下游的淤积急剧增加,尾闾水位抬高,排泄不畅,于是淮水逐渐在洪泽湖一带潴积漫溢,湖面自然越扩越大。当降及清口的门限沙严重堆积扩展时,又出现黄水倒灌现象。黄水倒灌,不仅增加了洪泽湖的来水量,而且淤垫湖底,抬高水位,扩大了水域面积。
其二,明后期以来高家堰的大规模修筑。高家堰始建者,当推东汉末年广陵太守陈登。当初陈登建堰,意在阻障淮水东泛,然而此一策略,为后世治水者所遵用。北宋庆历年间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曾修过高家堰,明初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再度修治。陈瑄所修的高家堰,北起武家墩,南至阜宁湖,相当于今堰的北段。明隆庆年间,总督漕运王宗沐又招募淮民修堰,捍淮东侵。不过,此时的高家堰规模仍然不大,大约高度在三、四米上下,长度在30里左右,即约相当于今洪泽湖大堤的1/4。
万历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清时代由于国都在北京,经济中心在江南,因而黄、淮、运之间的关系至为错综复杂,治黄、治淮总是与治运、保漕联系在一起。对于这种现实,潘季驯看得可谓透彻深刻。1578年,潘季驯第三次被起用后,亲自对黄、淮、运、海作了细致的实地踏勘研究,提出了综合治理的主张:
我国家定鼎北燕,转漕吴楚。其治河也,匪直祛其害,而复资其利,故较之往代为最难。然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故较之往代亦最利。(《河防一览》卷六)
潘季驯治水的基本方针,一是加固黄河堤防,以“束水攻沙”,二是大修高家堰,以“蓄清刷黄”。这样,筑高家堰既可以保障淮扬地区的安全,更是治黄、治淮的关键所在。《行水金鉴》卷一六〇记载:
高堰者,淮扬之门户,而黄、淮之关键也。欲导河以入海,势必藉淮以刷沙。淮水南决则浊流停滞,清口亦湮,河必决溢。……是淮病而黄病,黄病而漕亦病,相因之势也。
万历七年(1579年),高家堰筑成,北起武家墩,南至越城,长60里。次年,又向南延伸20里至周家桥。至此,淮河来水被大量拦蓄起来,担负着刷黄的巨大使命,洪泽湖也基本形成。此后洪泽湖的水域面积与水位,随着黄淮水情及高家堰的蓄泄变化而时有盈缩与高低。
清康熙时,河臣靳辅基本沿袭潘季驯“蓄清刷黄”的“金科玉律”,修堤筑堰仍在进行。1677年,挑浚清口,开挖引河,堵塞高堰决口,培修残破堤岸,最后又将大堰向南延伸25里至翟坝。三年后,再在高家堰大堤修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唐埂及古沟东、西六座减水坝。经过靳辅的一番治理,洪泽湖面积进一步扩大。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坝关闭,洪泽湖盛极一时。
总之,高家堰可谓明代以来“蓄清刷黄保漕”的产物,而高家堰的成型,又是洪泽湖最终形成的关键所在。对于高家堰的意义和作用,《高家堰碑文》(《皇清文颖》首卷八)有云:
黄河为运道民生所关,而治河以导淮刷沙为要。高家堰者,所以束全淮之水,并力北驱以入河。河得清淮,则沙不积而流益畅。故考河道,于东南以高堰为淮、黄之关键。淮自中州挟汝、颍、涡、汴诸水,汇注于洪泽一湖,荡激潆洄,浩渺无际,而淮、扬两大郡居其下流,惟恃堰堤以为障御,所系讵不重哉!
按这段碑文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高家堰关乎运河漕运,关乎政治中心的经济安全与民心稳定,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由于政治中心远僻北鄙,所以运河漕运乃是国命所系;漕运一段假道黄河,以此黄河又为运道民生所关;而黄河畅通与否,有赖高家堰蓄清刷黄,因此高家堰为保障黄、运畅通的关键。其二,高家堰关乎淮扬地区的国计民生。洪泽湖水位既高,淮扬地域相形卑下,所以一旦高家堰溃决,淮扬地区将汪洋恣肆,而百姓尽成鱼鳖矣。
客观地说,《高家堰碑文》的概括是语重心长、颇为精当的,它不是简单地将高家堰看作一般意义的水利堤防工程,而是重在指出其特别的政治意义。质言之,高家堰实为明清两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安全工程。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为人们始料所不及,高家堰的修筑就可以算作典型的一例。
首先,高家堰修成后,淮、扬其实已经沦为鱼鳖之地。帝王们重在保漕保运,所谓“淮、扬两大郡居其下流,惟恃堰堤以为障御,所系讵不重哉”,乃是粉饰是非,因为真实的情形是,湖东里下河地区从此便以受灾为常,而一旦淮湖暴涨,政府更会“舍小家,保大家”,即不顾百姓死活,开坝放水,听任洪水横决泛溢,此诚如夏实晋《避水词》所云:
一夜飞符开五坝,朝来屋上已牵船。田舍漂沉已可哀,中流往往见残骸。
乾隆皇帝《下河叹》一诗更是细致描绘出了淮湖并涨、高堰危殆、河臣束手、百姓遭殃的真实图景:
下河十岁九被涝,今年洪水乃异常。五坝平分势未杀,高堰一线危骑墙。宝应高邮受水地,通运一望成汪洋。车逻疏泄涨莫御,河臣束手无良方。秋风西北势复暴,遂致冲溃田禾伤。唉哉吾民罹昏垫,麦收何救西成荒。截漕出帑敕大吏,无遗宁滥丁宁详。百千无过救十一,何如多稼歌丰壤。旧闻河徙夺淮地,自兹水患恒南方。复古去患言岂易,惄焉南望心徬徨。
淮、扬既然大水,百姓遂视江南为避风港,于是背箩提筐,挈妇将雏,成群结队,纷纷南下。饥肠辘辘的灾民,先是风餐露宿,既而无视法纪,夺粮攘羊,打家劫舍,江南社会秩序为之混乱,这又成为政府新的忧患,正如赵翼《逃荒叹》所云:
男拖棒,女挈筐,过江南下逃灾荒。云是淮扬稽天浸,幸脱鱼腹余羸尪。百十为群踵相接,暮宿野寺朝城坊。初犹倚门可怜色,结队渐众势渐强。麾之不去似犬吠,取其非有或攘羊。死法死饥等死耳,垂死宁复顾禁防。遂令市闤白昼闭,饿气翻作凶焰张。黔敖纵欲具路食,口众我寡恐遭殃。侧闻有司下令逐,具舟押送归故乡。却望故乡在何所,洪荒降割方汤汤。
其次,洪泽湖演变成了地上“悬湖”。高家堰大堤虽然修建起来了,但毕竟黄高淮低,黄浊淮清,黄强淮弱,真正实现“蓄清刷黄”谈何容易!于是乎,大堤一步步地增筑,洪泽湖底一日日地淤高,水位一层层地抬升。如嘉庆十五年(1810年)五月一日吴璥奏云:“伏查黄河底淤垫,其来已久,而近数年愈淤愈高,当日洪泽湖存水七、八、九尺,即能外出清口,近年蓄至一丈二、三、四尺,湖为黄水所阻,实属受病已深”(水利电力部水管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8年版)。及至道光八年(1828年),洪泽湖水位蓄至一丈六、七尺,仅能与黄相敌,蓄至一丈八、九尺,始能畅出。而从道光十一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的21年中,洪泽湖水位均在二丈以上,最高时达二丈三尺四寸,约合今16.91米。大抵自道光初年以来,洪泽湖底已从嘉庆初年的一丈有几淤至二丈开外,一旦大水,洪泽湖水位即高出高宝湖7米左右,高出里下河地区更达13米左右,洪泽湖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悬湖”。⑤
如此的“悬湖”高矗地上,真是危如累卵,一旦溃决,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无疑成为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泗州城的悲惨淹没,就成了这柄掉落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牺牲。
“蓄清刷黄保漕”的牺牲:泗州城的淹没
泗州城的最后淹没,同样与明清时期“蓄清刷黄保漕”的治河方略密切相关,更是高家堰大规模修筑以来洪泽湖迅速扩张的必然结果。自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将泗州治所从宿预(今宿迁市东南)移至临淮(在今盱眙县淮河乡境内),直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泗州城淹没于洪泽湖,泗州治所历时近千年未变。按泗州城的重要性,在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泗州城之兴盛由此,泗州城之颓敝与淹没也由此。
先是隋代开凿通济渠后,盱眙对岸的汴口地位日显重要。唐宋时代,江淮财富全部经由汴口北上,于是为了方便管理漕运,武周长安四年(704年)析置临淮县,其地西枕汴河,南临淮水。及至唐代中期,随着漕运任务的加重,汴口更是成为关乎国家命脉的咽喉,于是唐玄宗又将泗州州治迁到临淮。临淮直临汴口,位据汴、淮之要,舟楫往还,商旅四冲,为交通必由之路、兵家必争之地,泗州城也从此拉开了辉煌灿烂的大幕。发展至于明代,泗州城已经盛极一时,号为“衢闾整饬,栋宇毗连,百货之所集,人才之所钟”(光绪《泗虹合志》)。其时泗州城内外,街巷纵横,贸易发达,官署众多,文教昌盛,各色建筑林立。⑥
然而,泗州城也有其最大的不幸,即地势低洼,排水不畅,极易遭致洪水的袭击。泗州西有汤汤汴渠,南有滔滔淮水,有如环水孤城,水患史也是由来尚矣。如唐代泗州城建成不久,便屡遭洪水侵灌淹没,其中最大的一次当发生在德宗贞元八年(792年)。据《新唐书·五行志》载,是年六月,“淮水溢,平地七尺,没泗州城。”又据淮河水利委员会伍海平、曾素华《黄淮水灾与泗州城湮没》(第二届淮河文化研讨会,2003年,宿州)文中的统计,自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至金明昌五年(1194年),历459年,泗州被淹29次,平均15年一次;自1194年至明万历六年(1578年),历384年,被淹43次,平均8.9年一次;而自1578年至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历102年,被淹29次,平均3.5年一次。可见,历时千年的泗州城实在是辉煌与灾难并存,泗州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洪水抗争的历史。
细究起来,泗州城水患又可以分为洪泽湖基本形成之前后两个阶段。在明朝万历初年洪泽湖基本形成之前,虽然淹城事件频频发生,但持续时间一般不长,灾后不久便得以恢复重建,即并未造成彻底淹没的危险。而在万历初年洪泽湖基本形成之后,不仅水患越来越严重,而且几乎无有休时,这种形势的出现,则仍与明代中期以来“蓄清刷黄保漕”的治河策略和大修高家堰直接相关。前已述及,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以来,黄河不再多股南泛,而是固定夺泗入淮入海,所以淮河下游河道淤积大为加速。其后果是,一则排水不畅,容易引起黄流倒灌,二则直接威胁运道的畅通,这又成为明清统治者心头的最大忧患。为了保运保漕,于是大行“蓄清刷黄”之策,然而“蓄清”的前提是筑堰,筑堰的后果是洪泽湖的迅速扩大、水位的岁岁抬高,洪泽湖也就始终高悬在泗州城之上。对于此隐患,泗州的官员及百姓最为清楚不过。就在高家堰筑成的第二年即万历八年(1580年),泗州进士常三省愤然上书,在其《告北京各衙门水患议》中,他忧心忡忡,如诉如泣,力陈潘季驯“蓄清刷黄”带给泗州的沉重灾难:
冈田低处受淹,湖田则尽委之洪涛,庐舍荡然,一望如海,百姓逃散四方,觅食道路,羸形菜色,无复生气。且近日流往他乡者,彼此不容,殴逐回里,饥寒无聊,间或为非,出无路,归无家,生死莫保,其鬻卖儿女者,率牵连渠路,累日不售,多为外乡人贱价买去,见之惨目,言诫痛心。
不过在明代时,虽然泗州水患频仍,但因统治者在保漕的同时还要护陵,这就给泗州城留下了可以指望的一点“福音”。按明祖陵坐落在泗州城东北的淮河之滨,其处地势卑下,随时有淹没之患,尤其是洪泽湖形成以来,更如置于釜底,危在旦夕。出于容易理解的原因,迁葬朱元璋高祖、曾祖、祖父的祖陵自然事关重大,必须与运道一样,坚决予以周全的保护,所谓“祖陵国家王气所钟,祖陵被患,岂唯列圣龙蛻之藏不安于地,而千万年圣子神孙托根基命于何所?彼庶民衣食之流,尚恐伤及先茔,爱及一草一木,况皇帝之家,动关宗社,亦切圣躬,最不可缓图者也”(《明神宗实录》卷三三六)。因而明代治河的基本原则,是合漕运与陵寝皆筹之,尽量保证祖陵的安全,而这便使得与祖陵命运息息相关的泗州城,多少得到了一些顺带的呵护,延缓了其被彻底淹没的进程。
然而,及至明清鼎革易代,大明祖陵的特殊政治意义自然不复存在,于是一切的治河治淮措施,又皆服从和服务于漕运的需求,至于区区泗州的百姓生灵,更是何足挂齿,泗州城的淹没已在预料之中,而且来得很快。先是顺治六年(1649年)六月,淮河大水,东南堤溃,水灌泗州城,深及丈余,平地一望如海。康熙初年,泗州已经犹如水中之城,遭受大水侵灌之年,数来就有元年、四年、五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7个年份。泗州城最后的厄运则是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开始的。是年十月大水,水势汹悍,冲决州城东北石堤,外水灌注仿佛高屋建瓴,人民多遭溺毙,城内外汪洋一片。还未等到泗州人缓过神来,更休提城中大水消退,又逢第二年(1680年)淫雨连绵、黄淮并涨、势如滔天,于是泗州城内水深数丈,千年泗州城终于被彻底淹没在洪泽湖水之下,时任泗州知州的莫之翰在其《泗州志》中慨叹道:“嘻,甚矣哉!官若浮鸥,民皆抱木而逃,自是城中为具区矣!”至于终结了泗州城的洪泽湖,则是“湖界日巨,汪洋几三百里,延袤皖、苏二省”(《清史稿·地理志》)。⑦
温故然后求真
以上,笔者主要以明清两代之京杭大运河“蓄清刷黄保漕”的国家大政为中心,叙述了淮源的探寻、洪泽湖的扩大、高家堰的成型、泗州城的淹没四例。这四例既与“蓄清刷黄保漕”密切关联,彼此之间也是相互勾连。其实这样的关联与勾连,还能继续延续下去。如就自然地理层面言,曾经漕深、流急、水清的淮河,成了上游“脑溢血”、中游“肝腹水”、下游“肠梗阻”、近乎无法施治的淮河;又如就人文哲学层面言,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本来是以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为文化底色的中华传统农耕文化,何以走到了“人定胜天”、违逆自然的境地?再如就历史鉴戒层面言,若是综合考量政治、经济、交通、自然环境、百姓民生、地区发展等等,那么曾经的京杭大运河,如何权衡利弊,怎样评说功过,也是极为复杂与纠结的问题。然则立足当今,展望未来,对于传统帝制时代留下来的这份说不清、道不明的遗产,我们还是应当以史家的智慧、哲学的关怀、文学的感情,予以辩证的思考。然则走笔至此,我想起了革命导师的一段经典论断,检出了两位恩师的两段客观批评,这里恭录如下,意在温故而知新、辩证以求真吧。
一百多年前,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30多年前,谭其骧师在上海历史学会1982年年会的讲话中提道:
其实历史上的运河有些并没有开成,有些开成了也并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可言,有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是只有利于封建统治者,却害苦了运河沿岸的人民。这些具体情况怎么可以不讲?说在封建王朝时期开凿运河取得的成就如何辉煌,只是到了解放前由于反对政府的腐朽才年久失修而被破坏。这些同志竟然忘记了封建统治也是反动统治,与解放前的反动统治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这些同志也不想一想,封建时代要是已经有了海运(指轮船运输)和铁路运输,封建统治者还会费大力气去开运河吗?反之,民国时代要是还没有海运和铁路运输,这些反动统治者会任凭运河破败淤废吗?(《对今后历史研究工作的四点意见》,上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同样也是在三十多年前,邹逸麟师提交“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1982年,上海)的《关于我国运河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摘要)》之全篇如下:
我国历史上的运河是举世闻名的伟大工程之一。它在我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已为世人所公认。因其受所流经地区地理环境的影响,尚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今试以三点论之。
(一)历史上运河的地理条件及其航运价值。我国历史上运河大多修凿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气候比较干燥,雨量贫乏而又集中于夏秋之际,且有大面积黄土覆盖,故流域内河流普遍具有水少沙多的特征。沟通其间的运河亦因水沙条件不利,每年通航时间仅止半载。如不按时疏浚,即告淤废,如汉唐之关中漕渠、唐宋汴河等等。又因东部平原系东西向各大河流冲积扇交叠而成,南北地势有高差,非置闸堰水,不能通航。如元明会通河,每年耗资亿万,而效率极低,为人民的沉重负担,其航运价值则极有限。
在音乐剧演员拿到剧本时首先应该明白——我是谁,经历了什么事?他是带着什么样的情绪进入这一场次的?他的下一步行动又是什么?亦即角色之过去、现在和未来。当年在兰陵剧坊的某次公演中,我看到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画面:饰演家庭主妇的某位女演员,上场前站在侧台边,挽起袖子佯作炒菜的样子。我当时不能完全理解“到底她在干吗”,后来等她一转身上台,我就看懂了:这位女演员上了舞台之后,拉了两下袖子,用手轻拭额头的汗水——活像在厨房忙进忙出的样子。就是这两个细微的动作,让我们知道这个角色“从哪里来”。这样的表演不但具有说服力,也让我们知道角色和空间的关系。
(二)运河开凿后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我国历史上运河大多修凿在东部平原上,由于运河含沙量高,年久河床淤高,形成高于两岸平地的地上河,它影响了沿线地面沥水的排泄,出现了不少浅沼和洼地,使土壤盐渍化,如战国时代的鸿沟,唐宋时代的汴河等。近数百年来,河北平原、豫东鲁西南地区,洪涝之灾,连年不断,均与元明清时代南北大运河犹如一道地上长城,屹立在平原东部有关。
(三)运河的通航与农业生产的矛盾。先秦至南北朝时期,运河亦兼有农业灌溉渠道的职能。隋唐两宋时期,运河的漕运职能日显重要,因水量缺乏,航运与灌溉用水开始发生矛盾。元明清时代南北大运河中尤以会通河水源最为贫乏,故惜水如金,涓滴归公,有私决沿运湖泉者,判以重刑,严重影响到沿运的农业用水,造成土地荒芜,人口逃亡,故历史上运河作用应作全面的考察。
又顺着两位恩师的谠论,笔者也在“以半个甲子的治史感悟”而写成的《读史入戏:说不尽的中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道具举例:自然的象征与人文的符号”中,言及这样的“反思”:
这些年来因为“申遗”而大热的京杭大运河,虽然在历史上起到了沟通经济重地与政治中心的作用,弥补了内地农耕社会地域空间里自然河流多为东西流向的不足,密切了相关地区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因而迄为明显的中国历史之“道具”;但是另一方面,大运河的负面影响——恶化了生态环境,极大浪费了社会财富,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江南的发展,往往牺牲了民众的利益,等等——却在无意或有意之间被忽视了。这种认识上的偏颇,或许会损及当代,譬如避难就易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就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成本浪费问题。
然则在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即将成立之际,谭师、逸麟师与笔者——或可称为历史地理学界的三代学人——基于“常识”而提出的这样的批评、提醒与反思,应该不是多余的“废话”吧……
①探索和考察江河源头,尽管饱含着艰辛、险境、不测,但它融求知、游玩、探险于一体,又充斥着神秘感,所以热衷此道者代不乏人;至于有些特殊的江河,其探源更是或具有国家政治意义,或具有思想解放价值。前者如黄河,《汉书·沟洫志》记载:“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出于农业民族与统一国家“朝宗”的目的,历代王朝官方性质的黄河探源活动,不绝于史;后者如长江,徐霞客在《江源考》中“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江为首”之语,不啻于一道闪电,击向“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禹贡》经说。
②固庙,现名淮源镇,在今河南省桐柏县西30里处,古籍中称为“阳口”。远在秦代,此处即建有淮祠,后又称淮渎庙、淮源庙、禹庙。镇旁石栏水井有三泉涌出,井旁有明代《重修淮渎庙碑》,不远处有涓涓小溪,这口井通常被称为“淮井”。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桐柏知县高士铎命令工匠在碑阴镌刻“淮源”两个大字,即认此处为淮源。其实据前引《水经注》的记载,阳口(固庙)是淮河在“潜流”三十里后所流经之地,并非淮源。
③关于淮河源头的确切位置,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淮河纪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一、导淮自桐柏·太白顶探源”描述如下:“在固庙镇向南,有一沿溪小道。顺小道溯水而上,道路渐渐变成一条飘带,忽进谷底,忽缠山腰,要走十八个山坳,当地群众叫‘十八扭’。走完十八扭,悬崖陡峭,古树参天,遮得天空只剩一条长带,人们叫做‘一线天’。脚下溪流时隐时现,斗折蛇行,上下跌岩[宕],哗然有声。走完一线天,再攀两座山头,前面就是太白顶。山顶有一古寺,名曰‘云台禅寺’,为唐代所建,清朝乾隆年间重修,现寺院犹存。古寺东方,有一眼井,清澈明净,久旱不竭。细观之,井内有泉眼三处。淮河的源头就在这里。泉水从井旁石壁中沁出,流不多远,又潜入地下。约半里,在那枯藤盘绕、青苔覆盖的峭岩间,又钻出了地面。一二里许,无数细流汇聚成一条小溪,向前奔流。又过三四里,无数小溪又汇成一条欢跳的小河,撞击着山间石头,往山下流去。盘来绕去,潜入钻出,直到固庙镇形成河床。一泻千里的淮河,就是这样开始举步前行的。”
④有趣的是,探得淮源、重修神庙以后,还真是“效果”立马显现,《淮渎神庙碑记》有云:“向之洪湖有时稍弱者,近岁澄澈。诰弥潴泄应节,以济重运,则舳舻相接,衔尾遄行。而涤黄流、迅洪波,尤以见锡佑之功。景烁昭彰,诚有不可思议而得之者。夫以长淮为川泽之灵,而宅奥栖源,惟神实司其契。……百川于是效顺,万民于是蒙福。然则贲祀报功,其庸可以已于言乎?”
⑤如今,洪泽湖平水期高出东部苏北平原4~6米,洪水期则高出6~8米,即仍然保持着悬湖的态势;而其东部宽50米、长67公里的大堤,则成为苏北2000万人口和3000万亩农田的捍御。
⑥如言街巷,有大街15条,巷道34条,大桥16座;如言贸易,有市场5处;如言官署,有州衙、都察院、巡监察院、理刑厅、泗州卫、馆驿、课税局及邮传总铺等,同时又有庐、凤、淮、扬、滁、徐州之钦差及监察御史、凤泗兵备道、江北提刑按察使等官署;以言文教,有儒学署、训导署、学正署、社学、决科书院、龙泉书院及泗水书院等;以言各色建筑,有钟楼、鼓楼各1座,寺、庙、庵、祠53处,坛、堂、亭、阁12处,表、坊、碑、碣24处,等等。
⑦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保存相当完整的一座原汁原味的水下古城,不见天日已经300多年的泗州城,竟然获得了“东方庞贝城”的“美誉”,其特别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与旅游、探险、猎奇潜力,吸引着海内外考古学家与旅游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这是对桑田而沧海的泗州古城的祭奠?抑或是已经失去鲜活生命的泗州古城另种意义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