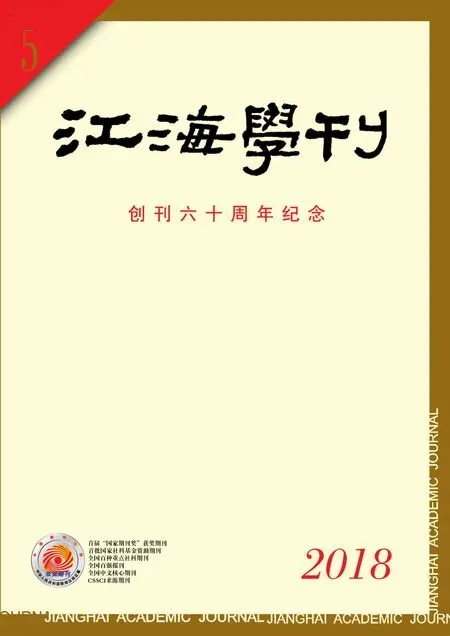专家政治论与现代中国:从孙中山说起*
内容提要 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在强人威权与专业技术官僚(technocracy)领导下,经济社会得到较好发展。这些专业技术官僚得以跃升舞台,实有其错综复杂的思想/历史过程。本文取观念脉络的研究手法,论证专业技术官僚的面世,特别与孙中山构思权能区分,主张专家政治之论述密不可分,同时也得到知识界的呼应。专业技术官僚的角色在1949年之后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藉由整体历史的脉络进行观察,对孙中山的思想世界及其遗产,应可提出更恰当的认识。
* 本文系笔者日文文稿之改寫版:潘光哲(著),望月直人(訳),〈孫文「専門家政治」論と開発志向国としての現代中国国家の起源〉,日本孫文研究会(編),《孫文とアジア太平洋ネイションを越えて》,《孫中山記念会研究叢書》(東京:汲古書院,2017),頁54-71。
一
在20世纪中国宪政史上,张知本(1881-1976年)的地位众所公认。①然而,仔细清理他的“宪政想象”(constitutional imagination)②会发现,孙中山的学说,其实是张知本的思想资源。在张知本看来,五权宪法是孙中山“在政治学说上一个伟大的发明”,其根本精神为,对于一国的政治,把“权”与“能”分开,使人民有“权”,一切政治的设施,都要以全国人民的意志为依归,而政府不敢专制独断,故谓之“全民政治”;孙先生又主张政府有“能”,“则治理政事的人,便非政治专家不行”,故谓之“专家政治”。张知本本乎“专家政治”之意,更抒发个人独创的见解,认为军人的技能是战术,要军人当大总统,便是使之“弃其所‘能’,而强为其所不‘能’,结果便是一无所‘能’”,因而宪法应该规定“军人非退职三年后,不得当选为大总统”。③张知本立基于孙中山学说开展的这等“宪政想象”,意义所在,是否引发回响论争,并不重要;反倒是他诠释孙文的学说,袭用诸如“权能区分”和“专家政治”等等概念,却是意蕴丰厚,毕竟,反观孙中山的论说文本,他确曾使用过“五权宪法”和“全民政治”这两个词汇,④“权能区分”和“专家政治”却不是他本人使用过的概念。⑤相对地,即以“专家政治”一词而言,⑥那是中国知识界同识共晓的“规范词汇”(the normative vocabulary)⑦;如罗隆基(1896-1965年)早在1929年就倡言“只有专家政治,才能挽救现在的中国”,⑧笔锋所指,其实乃是建立党国训政体制的国民党政府。⑨即使用心方向和罗隆基有如南辕北辙,张知本诠释孙中山的遣词用语,却是与时代思潮合拍同调。
这样说来,在当时的思想气候里,即便各种政治力量,各方有心之士,对中国未来的前景所向,自有认知,各有期待;彼此之间的理念交锋,汇聚而成的意识形态之争,根本上都在这些“规范词汇”开拓的思想空间里,相互冲激。然而,“专家政治”这个概念之理论与实践,在当时的场景里,即令众说纷纭,同争共竞;群声并唱之际,竟尔成为“公民认识论”(civic epistemology)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⑩历时既久,传承繁衍,“专家政治”竟至“概念延展”(conceptual stretching)之局,诸如专业技术官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概念,已然成为诠释理解历史的概念工具,不证自明。就现实言之,身受专业(科技)技术教育者,大量跃升领导阶层,专业技术官僚掌握国政权力,已是共同现象,至今依然。因此,我们应该超脱既定的历史认识框架,放宽视野,不以1949年为限,掌握整体历史的脉络,才能更为恰当地理解孙中山的思想世界及其遗产。
二
留学日本,尔后回台湾担任过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的陈鹏仁,因翻译日本学界研究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及现代史的成果而蜚声于世,却也因为职务的关系,必须扮演孙中山的诠释者的角色。如他声言,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之民主政治是全民政治与专家政治,而不是欧洲民主政治的代议政治与阶级政治”,基本论调,和当年张知本的阐述没有太大的差距。
在1930年代的国民党阵营里,鸣唱同样音符者比比皆是,他们注疏申论党国意识形态,好似“文化御林军”的角色。本来在1910至1920年代论坛上居有一席之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着有贡献的高一涵(1885-1968年),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委员,倡言现代政治变成专家政治之必然,以“政治专门化”“政治技术化”作为今日政治的标语,仍复引据孙中山“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与“国家,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等等述说。担任过立法院代理院长的邵元冲(1890-1936年),则说孙中山主张“政府要有能”,那么,“要使政府方面有能,就要使政府方面任何服务人员都有能”,所以“主张专家政治”理所当然。杨幼炯(1901?-1973年),早年既以撰述《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党史》等专著而知名,也是孙中山思想的诠释者,在孙中山百岁诞辰时,他便有《国父的政治学说》之作,同样也申论孙中山权能分开的学说就在实现专家政治,并呼吁“今后政治的革新,是以实现‘专家政治’为旨归”。担任过台湾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并长期出任逢甲大学董事长的高信(1905-1993年),在1930年代是还未入政界而任教于国民党党校中央政治学校的青年教授,依复引据孙中山“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的界定,论证“管理众人的事”,当然必须“委于具有深究的专门家”。因此,他批判国民党政府居然“收揽一班‘门外汉’来当治党治国的‘专家’”,结果“弄成现在这个失了革命性的党政府!令热心的革命青年,只有放声一哭”。笔锋虽然激烈,其用心所至,还是以国民党必须实现“专家政治”之理想为期望。
身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更需要以对孙中山之诠释,使他作为“革命接班人”的地位愈趋正当。蒋介石教导参加峨嵋军训团的学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与必须遵奉的中心思想”乃是我们总理的遗教。特别开展诠释,关于孙中山五权宪法部分,他即强调孙中山所说“权与能的分别”之用心,是既让“人民要有充分的控制政府管理国事的‘权’”,又要使“政府要有万能的治理政事造福全民的‘能’”,前者可以“实现‘全民政治’的理想”,后者能够“推进政治,增进效能而实现‘专家政治’的理想”,因此“从根本上调和历史上人民与政府间自由与专制冲突,而建立一个完全为‘为民所治’的万能政府,为全体人民谋最大的福利”。
总体而言,孙中山营构的“革命政治论述”,期可产生说服力量,并重行建构政治/社会世界之意义所在,确实涵括簇新的“革命语言”与“政治实践”,确实曾经得以熔铸群体,打造认同。如胡适的观察,国民党在孙中山去世后,依旧把他的遗教奉作一党的共同信条,极力宣传,立为“共信”,北伐成功的革命历史,“证明了只要能奉行一个共同的信仰,革命的一切困难都可以征服”。不过,后继者的再诠释,遣词用语必然未可跳脱世众同识共晓的“规范词汇”之网罗,对于“专家政治”之诠释与想望,正是一例。
三
倡言“专家政治”的罗隆基,笔锋矛头,当然指向国民党政府的党国训政体制。可是,正如他自己的标榜,“只问行政,不管主义”,如孙中山所言,“政治的目的,是在管理众人的事”,那么:
什么人有管理的知识及能力,我们小民就欢迎谁来管理。“党治”亦可以,我们先问问谈“党治”的人,是否先能“治党”。“训政”亦可以,我们先问问训练我们的人,他们政治上的知识,是否可以为训。换言之,我们要问问管理众人的事的人,是否为管理上的专家。
同样倡言“专家政治”的胡适,向约见自己谈话的旧友宋子文提出“改革的意见”,就将“充分实行专家政治”(凡是交通、考试、卫生、农矿等部门“均宜用专家”)作为“改组政府”的原则之一,他更坦白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可以说,罗隆基与胡适立论的基础,都不是绝对否定党国训政体制的现实。所以,国民党人以“专家政治”之期望来诠释孙中山的理论,与它的批判者设定的理想,彼此之间的距离,其实并不那么遥远,甚至于可以汇聚合流,软土深掘,将“专家政治”的观念,深植厚栽为“公民认识论”的要素,复且传承相衍,似无终点。
同是党国训政体制的批判者,着重的面向,各有千秋,却都是“专家政治”的鼓吹者。胡适声言,不该将孙中山的一切学说奉为“金科玉律”,如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就是“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的护身符”,因为“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重要的技术”,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绝对不可能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解决之道,“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而罗隆基批判的现实是:“中国目前政治上紊乱的状况,根本的罪孽,是在不懂政治的人,把持国家的政权,不懂行政的人,包办国家的行政”,遭受“武人政治”与“分赃政治”这两种“恶势力”的“夹攻”。所以他主张:“只有正当的选举和公开的考试,才能产生真正的专家政治。只有专家政治,才能挽救现在的中国。”
较诸基本上以笔代剑来批判国民党政府的胡适与罗隆基,张君劢(1887-1968年)与张东荪(1887-1973年)则进一步组织政党——国家社会党,以谋出路,绝不放弃联合各党派组合“举国一致”政府以抗御外敌的理念。他们就算曾主张“国民党以政权还诸国人,退为普通政党之一”,不完全承认国民党党国训政体制独霸政权,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他们倡言之“修正的民主政治”,还是看重“专门家”的地位:
我们主张不仅是借重专门家的知识;并且必须使专门家占有地位,这个地位是不为党派作用所左右,或政潮所冲动。这样的主张不仅在于使政务各部都由专门知识来处理;并且亦在于使政务的大部分因为由专家设计,便可坚实稳定,不至于时常发生无谓的变化。
张君劢更强调与构想专家的决策者角色。他主张,为实现“集中心力之国家民主政治”,自应组织由公民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会议”,而且“国民代表会议之议员,宜规定其中之若干成,须具有农工商技术家或科学家之资格”;“关于行政及经济计划,除国民代表会议议定大纲外,其详细计划由专家议定”,因为“议员中加入专家,行政计划由专家定之,所以使行政趋于专家化或科学化也”。综言之,对张君劢这些积极参与实际政治活动的人物来说,当他们号召与说服群众支持一己,从而扩张势力之际,“专家”的作用与地位,乃是必须列入思考立论的必有之义。
既不是党国训政体制的思想敌手,也非“文化御林军”的一般论者,也不质疑“专家政治”之意义,对其内容与应用,则往往认为有他山之石,可供采择。署名“腾霞”者,始终是《国闻周报》的重要写手,就是一例。他发表《整顿吏治模范之美国专家政治制度》一文,认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标榜以“刷新政治,整顿吏治”为大政方针,确实必要之至,即自美国名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Beard,1874-1948)主编的《趋向文明》(TowardCivilization)一书里撷取精要,特别是基本上摘译改写了收录于华莱士(L.W.Wallace,1881-?)的“政府管理工程”(Engineering in Government)一文,藉以阐释“专家政治”为什么是近代政治上必然的趋势。为了强化立论,他还自做文章,如述说美国国务院的海外领事馆,“每月收到国内商人的询问,平均五千份”,还算忠于原著表述;接下来一句,“腾霞”话锋一转,称誉曰:“美国的这些领事都有商业的专门知识,都受了长久的训练,故能胜任,美国对于国外贸易如此重视,商业组织如此完密,无怪金元的势力统治了全世界”。其实,这句话根本就是原著没有的论说。总言之,“政府统治的工具,厥为组织、技术同科学方法”,如何以这些“工具”来管理众人之事,“都非专家不能讨论执行”。所以“腾霞”呼吁建立起这样的共识:“政府应切实推行考试制度,选拔真才”,青年应该“务实求学,自能致用……全国人民应养成尊崇专家之风气,相信专家政治”。“腾霞”的心血与观念,想来也是《东方杂志》编者认可的,所以摘录了他的这篇文章,还加上按语表示能够“供注意整顿吾国吏治者之借镜”,期可流传广播。
一般报刊之评论,同样为“专家政治”之理想性大张旗鼓。1931年的《申报》批评说中国“今日之政治,盖可以一言为断,曰:‘官僚政治’”。任官者“是否有为政之能,为政之才;是否才能称其职,职能尽其才,非人所问,尤非小民所敢问”。要打破此等局面,只有“从政必以专家……从政者应各有专长,各有专责。有才必为国用,而国亦必用其才。使从政者各能称其职,各能尽其能,夫然后庶政尽举,国家之机能得以灵活而无碍”。因之呼吁“党政领袖能以绝大之努力,下绝大之决心,摧毁官僚政治之根基,厉行专家政治。慎勿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徒令人感喟怆伤于无穷”。
约略而言,自从1930年代起,展现于中国言论舞台上的“专家政治”论说,既是国民党党国训政体制本身,也是这个体制的批判者乃至一般论坛中人,都不会否定的理想追求。从此,在“公民认识论”的天地里,“专家政治”的价值意义,绝对占有一席之地。只是“专家政治”之实践万一落空或失败,又该如何?连自组政治势力的张君劢与张东荪在立言之际,似乎都不曾思考要依据“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何等原则,让“专家”负担“政治”责任?至于以“专家政治”为至高理想的论者,乃至于被奉为一代民主宗师的胡适,大概都不会设想“专家政治”是否可能仅仅会是一场梦幻。“民主实践”与“专家政治”之间的落差,更在他们的思考之外。
四
“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的李平心(1907-1966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里,应该都占有一席之地,仔细阅读他的史学著作,其实往往也带有浓烈的战斗意味。如他的《中国现代史初稿》(1940年),居然辟有一节讨论“‘专家政治’能够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吗?”俨然质疑仿佛为世众共识咸信的“专家政治”论说,即为一例。在李平心看来,“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现代国家,必须要有许多贤能的专家”。然而,“专家政治说”之实际,却只是“用新式的寡头政体来代替真正的民主政体”,绝对必须批判,因为“假如民众不成为国家的本位,只是无条件的信任专家,怎能担保他们不背叛自己的利益?”所以,必须“让人民发现和选举自己的治国专家”,更必须“在民众中间培养和训练专家”。那么,“使一切人民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有接受实际政治训练的平等机会,同时有参加竞选和服务国家的平等资格。这就必须用真正人民本位的民主宪政来代替官僚主义的包办制度或所谓专家政治”,便是应有之义。质言之,李平心其实不是怀疑“专家”与建立“健全的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期待在真正人民本位的民主宪政架构里落实“专家政治”。
比较李平心的思考与孙中山的关切,旨趣意蕴基本并无二致。反观孙中山本来的思路,用今天的话来说,乃是“民主实践”的阙限与其补救方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是:
欧美学者现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不对,应该要改变,但是用什么方法来改变,他们还没有想到,我现在把这个方法已经发明了,这个方法是要权与能分开,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
政府的一动一静,人民随时都是可以指挥的。要像这种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发展,人民的权力也可以扩充。有了这种政治和治权,才可以……造成万能政府,为人民谋幸福。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就理论上说,“专家政治”与真正“民主实践”之间,应该存在着这样的辩证关系:公民能够有效且尽责地控制政府的决策,而政府能够充分满足公民的集体需求。孙中山和李平心的思索主张,意趣庶几近之。但既有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处境却是“专家政治”与真正的“民主实践”背道而驰,水火不容。专家政治只会是那些仅仅胜任和擅长一个领域的专家的政治;民主则是每一个人依据自我的经验来参与制定决策,而不是靠什么技术专长。偏偏在现代社会里,“众人之事”的决策,技术色彩越来越凸显,公民的的主权日渐受到侵犯。呼唤民主,扩大民主,意味着希望人们将参与决策视为一己之责任;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下,人们却日渐失去制定决策的资格,显明易见。在民主理论的脉络里,约瑟夫·舒姆派特(Joseph A.Schumpeter,1883-1950)对民主的讨论广受重视,被认为是竞争式民主精英论(competitive elitism)之宗师。他视民主不过是一种方法与程序,乃是藉由竞取人民的票选而获得决策权力的一种制度安排,选民不能决定议题,也无法支配政治精英的意向,这是现代社会专业化的必然现象。“民主实践”濒于此局,如何补缺弥失,则在关怀之外。在世界脉络下,孙中山和李平心的主张,其实是对“民主实践”之问题所在,思索拟构补救方案。
对比之下,现代中国“专家政治”之诠释与想望,实以牺牲孙中山的本来关怀为代价,仅止侧重“专家政治”的一面,对于如何落实真正的“民主实践”思考不多。在当下的生活世界里,描述专业技术官僚得以掌握国政权力的历史过程,勾勒“发展型国家”概念的历史进路,固然有助于我们开展历史的诠释理解。但是,专业技术官僚、发展型国家等等概念,同样往往对如何落实真正的“民主实践”,置于九霄云外,向无关怀,展现“凡存在必合理”的阙限。那么,反省讨论专业技术官僚、发展型国家等等概念,不能不注意它们应该是由“专家政治”之理论与实践的“概念延展”的成果,绝非不证自明,它们作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需求相互纠缠的产物,应该被历史化,予以理解。
* 本文勾勒孙中山“专家政治”论的诞生问世与其流传广播的历史过程,当可显示,如果以“脉络化”的进路,或能更为恰当理解孙中山的思想世界及其遗产。对关心“孙中山研究”的学界同好而言,本文之作,“野人献曝”,希望略具这样的提醒作用。
①張知本與二十世紀中國憲政史之關係,以中村元哉之研究為精要:中村元哉:《中華民国憲法制定史にみる自由.人権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張知本の憲法論を中心に―》,《近きに在りて》,号53(東京:2008年5月),頁16-28;中村元哉:《国民党“党治”下の憲法制定活動——張知本と呉経熊の自由.権利論―》,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中華民国の模索と苦境1928-1949》(東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10),頁43-80;中村元哉:《相反する日本憲政観美濃部達吉と張知本を中心に》,劉傑、川島眞(編),《対立と共存の歴史認識:日中関係150年》(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頁171-190;中村元哉:《世界の憲政潮流と中華民国憲法張知本の憲法論を中心に》,村田雄二郎(編)《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東京:有志舎,2011),頁225-244。
②宪政想象,意指宪法在为什么会构成现代政治权威之泉源的脉络里,吾人对于思想、文本与行动之间的多重交错关系,究竟如何认知的方式,从而成就了某个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宪法,也使得宪法文本得以拥有“创造世界”(world-making)的力量,参照:Martin Loughlin,“The Constitutional Imagination”,TheModernLawReview, Vol. 78, Issue 1(January 2015), pp. 1-25.
③张知本:《宪法问题:怎样才是五权宪法》,《东方杂志》第31卷第8期(1934年4月),第7-15页。
④“五权宪法”见孙中山“五权宪法”(1921年3月20日),《国父全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3年,第2册,第412页;“全民政治”,如“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参见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六讲(1924年4月26日),《三民主义》,《国父全集》第1册,第151页。
⑤兹举原文一例:“……欧美学者现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不对,应该要改变,但是用什么方法来改变,他们还没有想到,我现在把这个方法已经发明了,这个方法是要权与能分开,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见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年4月20日),《三民主义》,《国父全集》第1册,第136页。
⑥研究讨论中国“专家政治”的成果,以邓丽兰之研究为精要,如邓丽兰《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变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政》,《中国社会史研究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余例不详举。
⑦“规范词汇”借用自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表述,参见:Quentin Skinner,TheFoundationsofModernPolitical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Vol. 1, pp. x-xi(当然,昆廷.斯金纳提出“规范词汇”的论说与他的思想史方法论密切相关,本文不详述)。
⑧罗隆基:《专家政治》,《新月》,卷2号2(上海:1929年4月10日),收入《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第169-184页。罗隆基《专家政治》一文收入《人权论集》之版本,与《新月》原刊版本略有出入,本文引用时,据引文需要,注明出入所在。
⑨参考刘志强《中国现代人权论战:罗隆基人权理论构建》,《人权硏究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⑩Sheila Jasanoff以“公民认识论”这个词汇来表达那些在特定文化里,基于政治和历史而产生的公众知识方式,并透过一套制度化的实践,用以测试与布导那些将成为集体选择的知识要求(knowledge claims),见:Sheila Jasanoff,DesignsonNature:ScienceandDemocracyinEuropeandtheUnitedState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49,p.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