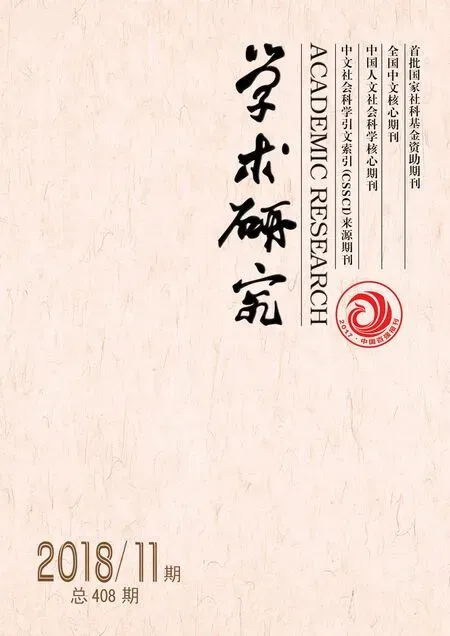康德美学痛苦本体论及其影响再认识
蓝国桥
康德的作息生活,有如时钟般准确。严格的作息时间,加之六根清净,确也成就了康德的学术辉煌。康德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批判哲学体系的建构上。他为创建批判哲学体系,所书写的“三大批判”,其行文的艰深晦涩,思辨的纯粹高严,多被世人视为畏途。刻板的生活与高蹈的思辨,展现给人的康德形象显得极度空洞抽象。如此的康德形象,犹如精灵般存在,他不食人间烟火,缺乏血肉温情。康德虽隶属于唯理论哲学阵营,拥有着高度的理性,但他的思想生成与影响,表现出相对明显的历史性,这使得他的思想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还原具体而完整的康德形象,从而捍卫他作为“人”的丰富性,成为笔者近十年来的“心事”。笔者在长期的思考中,有些新体会、新想法,需要得到补充、强化。现对康德美学痛苦本体论及其影响问题,作出再认识,以求教于学界方家。
一、康德对情感的类型划分
在康德看来,对象需依建构原理,方可形成知识与道德,而且,经过规定判断之后,它们才能为人所掌握。知识与道德建构的对象性指向,表明它们之妥当把握,所紧紧依靠的规定判断,所制造的多是情感的“飞地”。知识与道德中的规定判断,之所以排斥、驱逐情感,个中缘由倒是不难理解。情感是感性的重要材料,科学知识的呱啦落地,虽需感性材料的有效输送,但它最终不受情感支配,否则所形成的科学知识,将是极端的不可靠。人格想变得独立不依,进而拥有人性尊严,与行动中道德事项的成就息息相关,恰是由于怜悯与同情等情感的滋长,将威胁到人格的独立与人性的尊严,从而败坏行动中的道德事项,因而,若想让行动绽放道德的光芒,必先牢牢扼制住情感的蔓延。然而,整个世界假如只按知识与道德来安排,固然会显得井井有条,但同时也会变得索然寡味,如此毫无温情的世界,将使人难以再驻足留恋。康德虽处处按规则行事,但他提出有情世界观,实是三种力量共同交织、叠加的结果。康德熟悉西方文化传统,他知道在他之前的英国经验论者,已将人类大脑三分为知、情、意结构。重视情感,说明他的哲学批判不是凭想象的任意捏造,而是以传统作为出发点。身为批判哲学家,康德已对知与意,进行了考古式的清理,为完善哲学体系建构,情感挖掘的相关著作书写,随之也就被提上日程。反思情感问题,是康德“反思判断力批判”的题中之旨,它能将知识与道德活动中被洗刷掉的情感重新召回。康德与其他人一样,均是为普通父母所生,他同样也有情感上的细微体验,并经历着情感变化的喜怒哀乐。哲学家的康德与作为凡人的康德,在情感上能达成高度一致。
情感的状貌如何,实在是恍惚迷离。康德因而指出,在人类的心灵整个版图上,“模糊的领域”占据着最大区块,①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5页。情感的世界当属“模糊的领域”,因此,情感具有模糊性,乃是在情理之中。情感的模糊性大概由于两种原因,一是情感的世界飘忽不定、渺茫难测,二则是情感的体验带有极强的内在性、个体性。情感虽因变动不居、个别性极强而显得模糊,但康德着手批判反思判断力,当中透露出来的重要信息却是,情感的反思与把握,还是存在着可能性。遵循康德的理论言路,情感厘定往纵深方向推进的标志,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情感作出类型划分。逻辑与事实两方面可共同表明,康德把情感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康德反复告诉我们说,反思判断特别是鉴赏判断,会给人带来快感或不快感。于是,鉴赏判断在逻辑上将涉及到三种情感反应,一是快感,愉快、快乐、兴奋等与此相关;二是不快感,痛苦、烦恼、忧伤与此相涉;三则是介于前后两者之间的情感,变得不痛不快、亦痛亦快。批判哲学视野中(优)美的鉴赏,能给人带来快感;而引起痛感的,则多是丑的现象;不是纯粹的快感或痛感,而是两者掺杂的复杂情感体验,常是在崇高的鉴赏中获得。介于快感与不快感之间的不痛不快感,以及其他两种苦乐感,事实上在康德对情感所做的进一步说明中,更是有所涉及。面对人类情感三种不同的反应,康德在不同场合均有所挑示。康德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一直在讲授人类学课,他在课堂上一再强调说,快乐使人喜欢,令人不喜欢的则是痛苦,而介于喜欢与不喜欢之间的,则是不快乐不痛苦的“无所谓”。②康德:《实用人类学》,第137页。情感对成就道德的实践理性而言,虽只带有消极的作用,但康德还是相当意外地讨论了情感问题:“可是我们对于任何一种对象表象,都不能先天地知道它是什么,它是与快乐结合,还是与痛苦结合,还是非苦非乐的。”③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页。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唯有真实地接触对象表象,才能确切地知晓情感反应状况,而情感反应不外乎三种情形,一是“快乐”,二是“痛苦”,三则是“非苦非乐”。无论从逻辑上看,还是从事实上看,情感均可划分为快乐、痛苦、不痛不快(亦痛亦快)三种类型。
康德对情感所进行的类型划分,无疑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我们若以情感的流动状态为尺度,情感可相应分化出三种类型,一是顺情感,二则是逆情感,三是中性情感。顺情感与康德的快感对应,它指是情感在流动中变得畅通无阻。逆情感则是指情感在流动中受阻,出现了淤积、倒流的不顺畅现象,包括烦恼、苦闷、悲伤等在内的痛感即是,大致与康德所说的不快感相当。而当面对不顺不逆、非苦非乐的情感,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此类如湖水般平静的情感,姑且将之称为中性情感,中国人对它也有着较好的描述,陶渊明说那是“纵浪大化中,不悲亦不喜”,范仲淹也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后来王国维索性说是“无我之境”。生活与文艺的双重体验,都可进一步指证情感三种类型划分自有其理论上的正当性。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纷乱繁杂,但情感的体验变化还是有章可循,大致上喜乐属于顺情感,哀怒则是逆情感,而一切平平如也没有喜怒哀乐的显现,便是中性情感,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那样,“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页。文艺是对生活体验的升华,与生活体验相适应,文艺所表达的也大概是这三种情感,对此,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大致相似。抒情文学中,情感的状态与节奏的快慢,构成一体化的对应关系,快节奏多是顺情感;逆情感多与慢节奏相关;而山水田园诗中的节奏,则已经变得不快不慢,它们所表现的因而是中性情感,叔本华就此指出,山水田园诗里的主观成分相对比较少,它属于“待描写的完全不同于进行描写的人”之表达方式。①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44页。在叙事文学当中,有关戏剧的类型划分可与情感流动状态联系起来考虑,喜剧与顺情感相关,表达逆情感的多是悲剧,而正剧是不悲不喜,则与中性情感相涉。在此,顺、逆、中性三种情感的划分,是以康德的理论为出发点,它便于我们观察文艺活动,康德理论的价值由此也可见一斑。康德属于抑郁气质类型,因此在三种情感类型当中,康德最重视逆情感,即苦痛之情感,有赋予其本体论身份的强劲趋势。
二、康德对痛苦的本体确证
面对顺情感(快感)、逆情感(痛感)、中性情感(“无所谓”“非苦非乐”)三种情感,康德似乎只对逆情感(痛感)情有独钟。他赋予痛苦的逆情感以重要地位,并把它提升到本体论高度。痛苦本体论在这里的使用,大致可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说痛苦带有“本根”性,显得极端的重要,第二是说痛苦作为内在体验,具有明显的流动性,两者合起来可相当于痛苦存在论(Ontology)。整体上逆情感(痛感)的本体(存在)论性格,可以从三方面看出:鲜活流动而不凝固,是生命存在最突出的特点,而保持生命旺盛不衰的刺激力量,不是别的而是痛苦;人不仅限于生命存在,而他更高大庄严的要求是“成人”,痛苦恰是“成人”的必要担当与重要仪式;“人”还需进行审美活动,而审美活动中痛苦的因素不可或缺,痛苦是审美活动的必备条件。作为首先与动植物等一样的生命体,人获取生命存在感的可靠路径,便是痛苦体验。人毕竟与动植物不太相同,“成人”的标志之一,是人格变得独立不依,而人格想变得独立,需切断与感性欲望的万般纠缠,而扼制住感性欲望,必使人痛苦不堪。审美是人少不了的活动,但审美活动并非时刻都与快乐相伴,审美判断活动中的痛苦因素,同样挥之不去。从生命到成人再到审美,是一条艰难的上升之路,这条路延伸到哪里,痛苦便延伸到哪里。叔本华受康德影响,他在康德之后继续书写着痛苦本体论的辉煌篇章。深刻领会过康德、叔本华思想之后,王国维则将痛苦的本体论旗帜,安插在中国辽阔的文化疆土上。痛苦毕竟是现代性的核心体验。
痛苦是生命的刺激力量。站在康德角度看,生命过程的一般展开,是快乐与痛苦的交替上演,可形成奇特的双重奏:“快乐是生命力被提高的感情,痛苦则是生命力受阻的感情。但也正如医生们已经报道过的,生命(动物的生命)是这两方面的一个连续不断的相颉颃的活动。”②康德:《实用人类学》,第138页。康德在这段话中提出的问题值得留意:快乐是生命力的提高,而生命力的受阻则是痛苦,生命力舒展的姿态与情感流动的状态,乃是密不可分。生命活动虽是苦乐相伴,但相比之下,痛苦对生命力的刺激作用更带有根本性。这首先表现在轻重上,指针向痛苦一边倾斜。快乐对生命力的提高不具有绝对化性质,生命力的提高到达不了无限高度。生命力提升的无限边界既然是不可逾越,那么,这无形中便给生命力的受阻铺设了通道,承受痛苦必是生命的常态。绝对快乐不能实现,痛苦与生命如影随形,康德对此这样写道:“那么,在生命期间的心满意足(acquiscentia)又是怎样的呢?这种状态是人所到达不到的,无论是在道德的立场上(由于为人正派而对自己满意)还是在实用的观点上(对他自认为是靠熟巧和聪明所挣得的舒适感到满意)都达不到。大自然在他身上放进了痛苦来刺激他活力,使他不能摆脱这种痛苦,以便不断地向完善化迈进。”③康德:《实用人类学》,第142页。康德在这里是想指出,人在血肉生命展开的过程中,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幸福上,都做不到绝对的心满意足,就是说,人到达不了“至善”的境地;人有向“至善”迈进的冲动,但他又到达不了这种境地,落差的永远存在,痛苦必永远伴随在他的左右。其次体现在顺序上,痛苦比快乐一般先行。康德讨论痛苦,涉及正与反两个方面内容:从正面的角度看,生命力重要的刺激力量是痛苦,假如没有痛苦的刺激,生命力就会走向衰竭;从反面的角度看,快乐如果被“提高到超出某种限度”,那将是对生命力的恶性耗损,假如只有快乐相伴始终,生命力也会走向衰竭。正与反两方面一起表明,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时间上,痛苦都必先行于快乐,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刺激、呵护生命。最后表现在推进当中,快乐与快乐之间必夹着痛苦。人类很多的现实活动,都在遵循这样的原则。作为游戏的赌赛活动,它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在活动行进中,不停地交替着担心与希望,充满着诸多的可能性。爱情的甜蜜享受,必夹杂着痛苦,康德引用菲尔丁的话,说“爱的痛苦的结束就是爱的结束”,没有痛苦就没有爱情。综上三个方面可知,生命活动虽然是苦与乐相交替,但两者相比较而言,痛苦对生命的刺激作用,比快乐要强大得多。
痛苦是“成人”的庄严仪式。人从亘古中蹒跚走来,勇敢站立于天地间,最终成为大写的“人”,他必经历生与死的考验,因而为人敞开的门,必写着“痛苦”二字。是人必经历自然、文化、道德的三重磨难,他需在这三重磨难中,破茧成蝶般地“道成肉身”。康德说人并不是自然的宠儿,人与其他动物一样,都在遭受自然的侵扰:“外界的自然远不是把人变为它的一种特殊的宠儿,或者是厚待他过于一切其他的动物。因为我们眼见在自然的毁灭性的作用中——如瘟疫、饥荒、洪水、冷冻、大小动物的攻击,等等——自然却没有使人不遭受,正如没有使任何其他动物不遭受一样。而且除这一切以外,内部自然倾向的不和谐还使人陷入他的自作之孽,而且使他自己的同类通过统治的压迫,战争的残酷,等等,受到这样的苦难,而人自己反尽其所能来对同类施行毁灭。”①康德:《判断力批判》(下),韦卓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4页。自然对人的毁灭性侵扰,可分为外在与内在两种情形。面对像瘟疫、饥荒、洪水、动物攻击等,诸如此类的强大自然力量侵扰,人有时只能任由其横行肆孽,它们对人实施的毁灭性打击,人显得很是无力并无助。内在自然是指残留在人身上同样强大的动物性力量,由它们酝酿出的压迫、战争等不和谐因素,毫无疑问也能把人引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李泽厚受康德思想的影响,指出人的历史恰可表明,人可依赖自身的理性力量,将外在与外在两种自然加以征服与改造,而且在征服与改造中,创造出专属人自身的文化。文化因此是对自然的扼制与超越。真正有趣的地方是,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虽成功超越了自然,但它却不能有效根除痛苦。文化越是往前演进,人的痛苦越是深重,无论是上层人士,还是底层民众,都是难以避开得了的:“随着文化的进展——其高峰是在于致力于多余的东西开始变为有害于致力于必需的东西时,那就称为奢侈——双方都同样地越来越多烦恼了。就下层阶级来说,烦恼是从外来的暴行而来的,而就上层阶级来说,烦恼是来自内部的贪求无厌的。”②康德:《判断力批判》(下),第96页。康德深知人生而向往自由,但外在的暴行与内在的贪求,却给人增添了不尽的烦恼,换言之,文化反而给向往自由的人套上了异常沉重的枷锁。冲破枷锁的决定性力量,是人德行的有效操练,根本原因是,德行的有效操练能使人变得独立自主。人想变得独立自主,需压抑住喷涌的欲望。但欲望越是遭受压制,人的痛苦就越深。没有痛苦就没有道德,为了使现实行动绽放道德的光芒,人必先支付痛苦这枚硬币。自然、文化、道德给“人”制造的多半是痛苦的牢笼。一部“成人”史是痛苦的血泪书写。
痛苦是审美活动的必备要素。审美活动的原生状态,根据康德的基本意思,是对象为主体所消融之后,表现出明显的非对象性,达到主体与对象的浑然未分的状貌。不过,为方便理论分析与问题表述,我们可相应区分出主体与对象,这种区分只能是种权用而已。审美活动区分出的主体与对象,展现出来的是较为丰富、复杂的面相。审美活动与痛苦密切相关,正源于活动中的主体与对象面相呈现的丰富性、复杂性。自然与文化的对象,有美丑之外还有崇高。对象的状况与主体的能力密不可分。(优)美对象直接能使人愉快,而丑则往往令人直接感到痛苦,康德因而习惯于把鉴赏判断中的情感,统称为苦乐感。崇高对象较为特殊,它有苦也有乐,它因此处于美与丑之间。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丑与崇高、优美的对象,在最深层的意义上,都可激起作为鉴赏的主体或直接或间接的痛感。无论是自然还是文化,皆可出现丑的现象。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带给人的是不尽的麻烦。而给人增添了麻烦的自然,只能是丑的现象。自然全美形同梦中呓语。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产生不平等的渊薮,它带来的严重后果,是社会中的矛盾与纷争频现。助长了冲突的文化,也只能算得上是丑的现象。文化虽超越了自然,但却无法超越丑恶。自然与文化中频繁涌现丑的现象,带给人的多是不堪忍受的痛苦。能忍受痛苦,则显示出崇高。事实上,崇高的对象多显得凌乱而无形式,面对如此的对象,主体终将难以把握。崇高对象的不可把握,给主体的肉身是沉重的打击,而肉身的打击则是一种痛苦。说来很惊奇的地方是,主体却能因肉身的挫败、痛苦的承受,唤醒了沉睡中的理性,转而陷入某种动人的心境当中。康德没有从理论上讨论悲剧,原因主要是他认为“悲剧不同于喜剧,主要地就在于前者触动了崇高感,后者触动了优美感”。①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页。悲剧与崇高显然较为接近,它们都是由于支付了肉身的痛苦,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与感动。没有痛苦的体验感受,就没有对理性的陶醉沉迷,从而也不会有崇高(悲剧)感的获得。(优)美与痛感的联系相对间接。优美判断作为反思活动,留下了修养的浓重痕迹。审美修养的结果是,经修养之后获得的快乐,可有效替换感官的快乐,扩大开来便是以“道心”规范“人心”,更高的品味扼制低级趣味,使前者的需求成为习惯。修养过后的替换与规范,为感官欲望的恣意扩张修筑起来的稳固防线,能给人带来隐形的痛苦。另外(优)美还以非功利的承诺,甘愿忘掉现实苦难,优美因而是苦难的象征。可见,丑与崇高(悲剧)、优美等对象均能引起若干程度的痛感,痛苦隐藏在审美活动的最深处。痛苦的本体论地位,随之便得到确立。痛苦本体论以痛苦体验为本体,以痛苦体验为本体,即是无本体。康德的痛苦本体论,在中西方美学界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三、康德痛苦本体论的影响
康德审美的痛苦本体论,转换成更凝练的语言,便是“我痛故我在”。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推进,中西方的知识精英,都在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回应着康德美学这一潜在的命题。康德美学的重大影响,同样可以体现在中西方美学界对“我痛故我在”命题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呼应上。整体上来看,由于身处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西方对康德命题的回应,表现出来的状貌不尽相同。西方美学的发展,在从知识论向存在论推进,体现在审美活动上,便是关注人的有限性体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美学的现代演进,则缠绕在与传统的复杂关系中,审美活动中的痛苦体验便是面对西方时的焦虑与彷徨。中西方美学表现的面貌虽然有所不同,但生命个体的痛苦体验在加深,却呈现出趋同性。
最先对康德的潜在命题作出创造性转换并强化的,是他的德国同乡叔本华。叔本华指出,康德哲学的划时代贡献,是把对象区分为现象与物自身,与此相应的主体机能便可划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叔本华深知,在康德的视界中,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相应地物自身的价值也就在现象界之上,但实践理性面对的物自身是知识之箭穿越不透的厚墙,因此它不可知。康德关于物自身高于现象界、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阐述,为叔本华所接受,但他对康德有关物自身不可知的说辞,却流露出明显的不满。在叔本华眼中,物自身想从不可知变成可知,它就不能是自由意志、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等信仰对象,而只能是意志(欲望)及其表现。整个世界,从无机界到有机界,有机界中从植物、动物到人,都只是意志(欲望)不同程度的外化,而且对象结构越复杂,意志(欲望)就越强烈。有了意志(欲望),就会有痛苦,人的结构最复杂,意志(欲望)最强烈,痛苦也就最深,因为意志(欲望)得到不满足,人就会感到痛苦,而意志(欲望)如果暂时得到满足,人也会感到空虚无聊,这也是变相的痛苦。意志(欲望)与世界同在,痛苦也就挥之不去。因为意志(欲望)与痛苦每个人都能真切感受到,所以,康德的物自身不可知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审美与艺术为消除意志(欲望)与痛苦,也就具有了存在的本根性、合法性。有限的物质性肉身,以及由肉身滋生的痛苦,便成为审美与艺术的本体。
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是叔本华对康德学说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由他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人与世间万物,都充满了欲望(意志),因而,也就充满了痛苦。叔本华之后,尼采、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等人,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继续深化着欲望与痛苦的理论叙述。如果说人的欲望是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尼采发现的是欲望的权力维度,马克思发现的是劳动欲望,而佛洛依德则重在揭示性欲。他们的理论研究表明,人类恰是在满足这些欲望的过程中创造了文明。由于这些欲望的满足,会使欲望的有限个体陷入巨大的痛苦当中,因此文明的创造必与痛苦相始终。之后,海德格尔凸显痛苦的本体论地位。海德格尔指出,人的此在受时间限制,人逃不出时间的如来佛掌心,因而,人是在向死而生,并且人是唯一意识到自己有死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的有死性,人的此在便是不尽的烦、畏、操劳等,显而易见,痛苦已发生在意识的根部。如果说康德对人的认识有时还纠缠于有限与无限的追问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只在意人的有限性一极,人刻骨铭心的痛苦体验,也随之得到强调。西方现代的痛苦理论叙述,在间接上可追溯到康德这里。
在汉语思想界,最先对康德与叔本华等欧陆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能自觉进行钻研,取得了许多创造性贡献的,是被誉为“世纪苦魂”的王国维。王国维是在个人与社会危机爆发中,才强烈需要攻研欧陆哲学,这样哲学与人生、社会的救赎,在王国维身上便发生着内在的联系。他既忧生又忧世,传统士大夫的文化使命与时代担当意识,更增强了他内心的紧张与痛苦。他苦痛的情感体验,急需得到理论上的解答,叔本华学说在开始时满足了他的需求。他喜好叔本华学说,原因之一,是叔氏学说的佛学渊源,与他所接受的传统佛教文化有相符合的地方。原因之二,是叔氏以具体事例来阐述哲学义理,与他所继承的理事不分的传统思维方式有着非常高的吻合度。原因之三,是叔氏对痛苦的本体论阐释,与他在现实中的痛苦体验相通,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三者当中,叔氏的哲学学说直接揭示了痛苦产生的根源在意志(欲望),能解除他的困惑,是他喜欢叔氏学说最为重要的原因。叔氏学说源于康德。王国维在翻译桑木严翼著作《哲学概论》时得知,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一书中,“于经验上论述人生苦痛之多,而构成厌世观”,①桑木严翼:《哲学概论》,王国维译,《王国维全集》第17卷,杭州、广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这无疑会进一步强化他对痛苦的认同。实践与理论的一致,使得王国维对悲剧有着高度的评价。他多是以悲为美。在他看来,无悲无美,有悲则美,最悲最美。小说《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因而是人世间第一大著作。他写作《人间词话》,是因为词中有悲情。宋元戏曲是俗文学,表面上是给人带来世俗的欢乐,但实则有大悲在。他以悲衡美,而且他发现中国文学中的悲剧美,是以康德、叔本华的理论,作为内置眼光审视的结果。事实上他也承认,中国文化精神是一种大团圆式的乐天精神,与西方文化中的悲剧精神,还是很不一样。
王国维受康德、叔本华等西学的启发,对中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异所作出的乐天与悲剧的划定,是个颇具探究性的学术话题,一直在刺激着后人巨大的理论热情。中国知识精英的热情回应,表现出相对复杂的面相。民国时期的鲁迅与胡适,分别在实践与理论上拒斥中国文学的大团圆结局,他们在价值上明显向西方的悲剧精神靠拢;刘小枫则以“拯救与逍遥”之名来区分中西方文化,具有诗意而不失深刻。与他们不同的是,一心想为故国文化招魂的史学大师钱穆,一再流露出对乐天文化的眷恋;而港台大儒牟宗三,则以高蹈的哲学思辨,直指文化传统的形而上特质,乐天作为文化形态,已隐藏在他的观念当中。李泽厚与前两种情况不同,他肯定了传统乐感文化的价值,但他说在现代意义上,他却更喜好悲剧。因而,李泽厚所倡导的情本体,实是或以悲情为本体,或以乐感为本体,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摇摆。他们基于不同立场,对王国维做出的回应,表现出来的面相就是复杂,这标明中国自近现代以来在价值选择上的困惑。但不管怎样,他们的理论回应,在间接的层面上,也可追溯到康德(叔本华)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