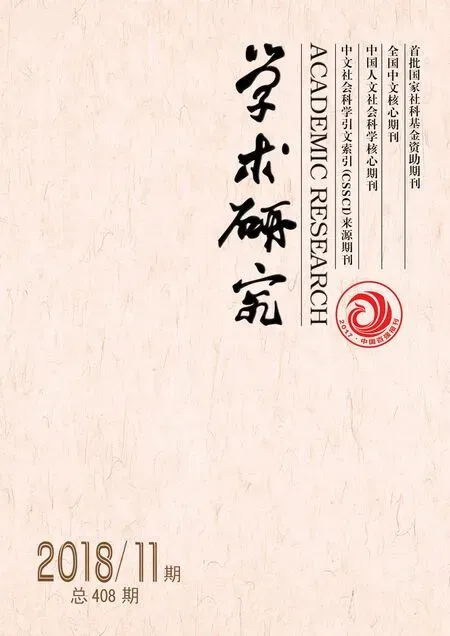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野中城市经济空间的演进路径与地理趋势*
刘 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进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目标。这些发展策略和目标是建立在对全球城市经济空间发展的演进路径和地理趋势的规律性认识之上,并设想通过国家和政府的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制度引导助推中国部分区域形成“多中心协同状网络化”的聚合型区域城市经济空间的地理趋势。区域城市经济空间的地理趋势是当今世界城市经济空间演进的一个地理表现。那么,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城市经济空间演进的推动力、路径和地理趋势是什么?把握了这些演进的历史规律和地理趋势,对中国进行城市空间生产实践的意义又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试图通过“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来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地理升级,“强调诸如空间、位置、时间、环境这些地理学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的重要位置,①胡大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来研究了城市空间地理的演进,指出要让空间处于运动状态, “如此便可展现出城市演进的新历史地理学”。②唐晓峰:《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 [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序言IV。沿着哈维开创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一分析框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结构和具体进程中来分析城市经济空间演进的历史规律和地理趋势,一方面探寻城市经济空间“地理”演变的规律,从“地理”维度印照、丰富和扩展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把握当今全球城市空间地理变迁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更科学更有效地规划、组织、引导和培育中国各类城市的经济空间。
一、城市经济空间演变的历史动因:生产方式的地理反映
城市经济空间是生产、流通、交换等经济活动展开的场所总和,包括了生产空间以及衍生出来的流通空间、交换空间和消费空间等。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分析视野中,城市经济空间演变的历史动因是生产方式在地理上的反映。
(一)技术进步推动城市经济要素的地理集聚和空间延展
空间是生产劳动及其相关经济活动展开的场域,在生产中经济要素的空间聚集和配置,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发挥的效能。技术的进步提供了人口聚集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人口集聚,劳动力、消费人口数量增大,生产资料、流通设施增加,实现了经济要素的地理集聚;同时经济集聚又刺激人口聚集,空间中生产设施、流通设施更精细化,这就进一步提出了对这些更复杂的空间经济要素的聚集、组合、连接以提高空间生产效率的问题,客观上提出了城市经济空间延展的地理必需。
原始社会末期“犁耜的发明和金属工具”的出现,使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口加速繁衍集中,方便发展大型水利工程、粮食生产、公共设施和初始的交通运输。这些要素形成了空间聚集点,使城市最终在与乡村的空间区分中“脱胎”出来。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城市中,房屋建造、给水排水、公共交通、手工业生产等技术进一步发展,为城市在更大规模上的人口集聚、物品贸易、公共生活提供了技术条件。当然在机器大生产出现之前,只存在少量的政治首都、港口城市和分散的农业小城镇,城市手工业生产空间、流通空间和商业空间缓慢地延展着。直到蒸汽机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出现,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经济空间的规模和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蒸汽机是工业城市之父”。以蒸汽机为核心的科学技术促进了生产原材料的加工、储存和运输,生产设施和流通设施的加速发展,劳动力远距离的居住以及流动,土地等劳动对象的深层次立体开发,形成了厂房、仓库、铁路、商店等城市生产性和流通性物理景观在地理上的空间延展,“生产的扩大超过这种界限,也就要求扩大土地面积”。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80页。这极大地需要对原有的封建手工业城市的经济空间进行重塑,最终形成现代化大工业城市经济空间的规模、形态和结构,如曼彻斯特、利物浦、伦敦等早期大工业城市的加速膨胀。正如马克思所说,大机器工业“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当今,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空间的集聚与分散同时进行”。生产过程的跨国分散促进了城市跨国性经济景观出现,如连接到全球经济体系的大航空港、跨国公司总部和分公司、跨国金融机构、跨国贸易公司等。同时,跨国资本通过信息技术网络对分散在全球各个城市的经济要素进行全球集中管理,通过信息技术网络来操纵各城市中经济要素的空间安置、流转、连接和组合。城市经济空间虽然在地理空间范围上并没有实际“扩展”,但是通过信息技术与全球经济网络的连接将自身的空间边界 “发散式辐射”到全球范围。
(二) 分工发展塑造了城市经济空间区隔地形和空间整合
技术进步引起了城市经济空间的经济景观的增多和空间地理上的延展,描绘的是一幅经济空间地貌图;分工发展则引起城市经济空间内部的地理区隔以及空间部位的整合连接,描绘的是一幅经济空间地形图。分工意味着生产劳动的分类化、专门化和协作性,是生产劳动在空间中的具体运行方式,必然会在空间上引起地理反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分工的细化导致经济组织在地理上的分化,刻画了一幅城市经济空间“区隔”“纵形”的地形图。
个人之间劳动分工促进了对生产组织的空间集中管理。同一劳动部门中个人之间的分工导致了生产中的协作劳动,将“许多同时劳动的工人在同一个空间(在一个地方)的密集、聚集”,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91页。对空间中的协作劳动进行“管理、监督和调节”变成了生产力的要素。这就需要对人口、技术、厂房、土地、设备等空间元素进行位置匹配、协调空间流程、进行技术的空间编配、改变空间的劳动组合形式等空间管理活动,这些活动产生了对同一生产空间内部生产组织的空间分区与布局,形成了众多空间“小纹路”。
生产部门内部的分工牵动着对区位空间的整合。在当今基本的生产部门内部又分化出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如金融业、房地产业、信息技术产业、休闲娱乐业、服务业等。这当然也要涉及在一个大的经济空间中新产业部门的空间规划和区位布局,如形成新的产业园区、科技园区、经济开发区、商务办公区、金融中心、大型主题娱乐区等条块状分隔,同时通过交通网络对各类生产空间、流通空间、消费空间进行沟通、连接和整合,形成城市经济空间中的地理区隔和交通线路构成的“圈层状”地形图。
分工还意味着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国际化分工。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马克思已经指出“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107页。随着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不同部位还形成了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弹性专业化”分工,如伦敦、纽约和东京郊外的金融业、房地产业,洛杉矶郊外的电影产业、航天科技业等,这样就形成了跨国资本对全球经济空间的专业化分工的选择、布局和协调,城市经济空间直接受到全球经济网络的辐射状控制而被“牵扯”着进行区位形塑,形成了若干从事专业化生产的经济活跃的多核状“中心点”,“点”与“点”之间通过信息技术和交通网络连接形成大型跨城市的“网状”区域经济空间。
(三)生产方式变迁推动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整体演变
技术进步和分工都是生产力的表现,生产力必须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才能显示在城市经济空间结构性、整体性变迁中的意义。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会根据所有制形式、生产的协作组织形式、生产技术来“生成”一个带有自身烙印的城市经济空间结构,也会根据生产方式内部技术特征、分工组织形式的变化局部化地“重塑”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形成适合生产关系的新城市经济空间结构,这就是城市经济空间变迁的“历史协同—地理重塑”机制,正如亨利·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③Henri Lefebvr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i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p.46.
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城市也经历了“原始初城”—“城邦城市”—“封建政治城市”—“资本主义城市”不同类型的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路径。在“原始初城”和奴隶制“城邦城市”中存在着一些孤立的“点状”的交换空间和手工业生产空间,在封建政治城市出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聚集的“片状”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部变化,早期“大工业城市”的城市经济空间呈现“同心圈”结构,“垄断城市”的城市经济空间呈现“中心—边缘”结构,再到“后大都市”遍地开花的“多核”的“扩散型”的城市经济空间结构。这是“自都市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以来一直在塑形(或重塑)城市空间的危机产生的重构过程和地理性历史化的崎岖发展。”④[美]Edward W. Soja:《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2页。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一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城市,由于计划手段和公正原则形成了“均质、规则、秩序”的城市同心圈空间结构,城市行政机关、政治广场是城市核心区,与工业—居住区、休闲区和外围加工区呈四个同心圈分布。⑤赫曦滢:《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理论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重构和分异了原有同心圈层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经济空间普遍向郊区“环状化”扩展,在内部沿着“轴线扩散”,在诸多大城市生成了圈层、多核、多轴混合的城市经济空间结构。
二、城市经济空间变迁的活动机制:人的“空间生产”实践
城市经济空间的变迁根本上由生产方式的变迁引起,这是一条“隐形”的历史主线。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空间还反映了社会政治权力关系,不同生产关系下掌握生产资料的城市权力阶级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进行“空间生产”实践。“空间生产”即对空间本身的生产,意味着城市权力阶级不断利用地方政府权力、城市规划专家、城市设计者对城市空间进行组织、布局、设计、划分、规定、意义化等活动,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组织城市经济空间,“生产”出新的经济空间结构、空间地貌和空间地形。这是一条“显形”的城市经济空间变迁的人的活动“主线”。正如列菲伏尔所说,“城市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被社会行为塑造、塑形和投资形成的空间。”①Henri Lefebvr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i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p.73.
(一) 空间布局:生产要素的地理空间选择
空间为物质生产提供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提供人员协作、交往的空间集结域和产品交换的场所,生产力运行的地理条件、具体方式、组织形式都要受到空间的制约,因此生产资料所有者一开始总是选择具有优势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和交流便利的地理初始空间位置进行生产。这是生产力运行需要的初始地理空间选择。同时在这一个过程中政治权力也聚合进来,强化对初始选择空间的布局、重组、优化,为生产力的运行提供更优势的生产空间位置。“生产关系在生产要素集结的一定空间位置上建构,又反过来塑造、强化其运行的这种空间位置。”②胡潇:《生产关系的地理学叙事——当代唯物史观空间解释的张力》,《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通过对经济空间的功能区进行布局、场域细化和区位化、优化交通运输条件、建设消费配套设施,城市统治阶级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合谋”对空间区位进行了优化,形成一种更“有效率的经济空间结构”。
在原始社会末期,一部分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的人群选择了“旁”集市而居,同时商人阶级推动集市成为固定的交换场所,集市就是早期城市中经选择形成的经济空间区位。从“原始初城”到“古典城邦城市”“封建城市”,城市的经济空间狭小、孤立,和生活空间混杂在一起,这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共同选择的空间位置。一直到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对都市结构的入侵剧烈重组了城市空间。”③[美]Edward W. Soja:《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第97页。
“现代经济的规划倾向于成为空间的规划,都市建设计划和地域性管理只是这种空间规划的要素”。④[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页。哈维指出,开始于1848年的巴黎“奥斯曼”城市重建项目中,“占有巴黎的却是奥斯曼、土地开发商、投机客、金融家以及商场力量,他们依照自己的特定利益和目的来重塑巴黎”。⑤[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第99页。奥斯曼政府根据资本生产和流通需求对原有城市空间景观进行了拆除,重新设计巴黎的城市空间布局,动员了金融力量和土地开发商去开发、建设、经营空间,开辟了市中心林荫道,建立了纵横交错的给排水系统,修建广场、商场、公园、医院、火车站、图书馆、学校、纪念物等,优化了生产要素的布局、便捷空间交往、畅通消费渠道,完善了“生产—流通——消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马克思也指出,“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21-722页。
当前生产部门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生产部门,如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电子、宇航和生物医学等,以及以工艺为基础并且劳动和构思高度密集型的工业,从服装、家具和珠宝生产到导弹和电影生产。⑦[美]Edward W. Soja:《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第214页。城市政府、规划设计专家、建筑设计师根据资本的生产需要来选址、定位、规划、布局以及调整城市的中央商务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金融机构区、大航空港、大型国际航运码头、休闲娱乐城、高速公路系统等新的经济空间点、流通空间和消费空间,并综合考虑各单元空间的区位、各单元空间的分隔布局、空间之间的交通连接设施和信息高速通道,以形成更有效率的整合性经济空间结构。
(二)空间划级:城市经济空间区域的等级设定
空间并不是均匀同质的容器,而是有着不同空间部位的区隔和等级,掌握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的阶级及其城市代理政府对城市空间进行等级划定,使一些空间部位优位于另一些空间部位而在其中获得空间分异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权益,因此不同空间的分割、区隔和划定都蕴含着社会权力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①[法]亨利·列斐伏尔:《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第48页。
在原始城市、古代城市和封建城市,城市空间等级性主要表现为政治空间压倒经济空间,政治空间如城堡、宫殿、教堂、公共广场、市政大厅和法院等,处于最高等级,而生产空间、商业空间在这一城市空间格序中是处于低序位的,是“被贬抑”的空间。列菲伏尔指出,这是“一个等级化的空间,从最低贱的地方到最高贵的地方,从禁忌之地到最高统治之地。”②Henri Lefebvr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i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p.292.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城市政府积极对土地进行分类划分和分级使用。哈维指出,1970年代初,纽约通过城市政府的财政管理、土地市场、房地产投机以及在“最高产出和最好使用”的旗号下,按照能产生最高经济回报率的方式对土地进行了分类,鼓励“高层土地”使用。空间分级形成对一些空间部位的优先和高等级开发,在优先部位布局新型产业和高端产业部门、优化生产辅助设施和公共设施、制造优势空间的稀缺性与昂贵性,造成优势空间土地升值和区位价值提升。建筑商、金融资本、房地产商在城市“黄金地段”打造高档购物中心、高档住房、娱乐休闲中心、办公楼和信息总部等,获得因空间位置级差带来的超额地租,而被划为“劣等”的空间则遭受了资本流出、产业凋零、设施缺乏、土地贬值的危机。马歇尔·伯曼(Marshell Berman)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纽约城市建设策略是“消灭大街”,“金钱和精力”被政府引导到开发公路、娱乐公园、购物中心和郊外住宅区的建设上,而原有的内城大街成了污浊、破败和过时的象征。③[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22页。
当今,跨国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根据地方的地理差异选择跨国公司的海外制造基地。发展中国家城市政府为了迎合跨国资本在全球的空间选择条件,有意识地进行诸多“城市重建项目”,积极打造“国际化”的空间区域,以便吸引跨国资本来自己特定空间内部发展。④[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70页。这也就形成了城市空间内部“国际化”的经济空间,如国际航空港、国际流通港口、国际产业园区、中央商务区等形成的城市新核心区域,从而形成了和“本土”经济空间如低端制造业、加工业和老区作坊小铺等区域空间的等级划分,产生了城市内部经济空间“不平衡的地理发展”。
(三)空间架设:城市生产和生活空间的一体同构
城市政府通过政治权力规划、设定、等级化生产空间,并以生产空间为中心向其他空间拓展和泛化,以便将其他空间如生活空间、消费空间统一纳入社会生产的整个体系而发挥经济功能。这样就达到了对整个城市经济空间的一体化同构,既显示出“具有粉碎、分割以及区分空间的力量”,又具有“制造空间差异同时又架设空间桥梁,密切空间联系的能力”。⑤胡潇:《空间的“生产性”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空间理论多维释义之一》,《哲学动态》2012年第9期。
列菲伏尔指出,在20世纪50、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城市政权围绕垄断资本循环需要,规划出一个“中心—边缘”的生产生活一体化的城市空间结构。在城市中心区布置新的商业、娱乐业、文化艺术业以及各种政府机构、信息中心、公司总部,在郊区则开发大型集居区、新城和卫星城中心这些由“被雇员、技术人员和体力劳动者”居住的生活空间。同时,大力发展高速公路、航空、通信网络等公共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将居住在城市郊区的人群安排到城市中心进行休闲、娱乐、购物等消费活动,“中心”地区对边缘地区进行延伸性控制和整合,形成一个“具有复杂内部秩序、等级层次和弹性”的一体化城市经济空间结构。雷勒·史密斯(Neil Smith)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建造项目越来将居住与消费空间整合起来进行同构,“城市中心重建欲来越多地将与居住有关的各种土地使用——办公室、零售业、娱乐、运输整合起来”。①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tita Press, 2003,preface 21.人们在城市中心兴建各类综合性的集办公、零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建筑区域;打造城市外围空间的旅游休闲景观和郊外大型主题娱乐公园等所谓的“后花园”休闲娱乐空间,采取多节点、网格状的密集轨道交通网络来实现人员的远距离休闲娱乐等消费活动;将“城市传统、集体记忆”赋予在街道、公园、楼盘中,打造象征“身份”“地位”的高档住宅产品和生活空间,力图促进居住、生活与消费空间的一体化同构。
三、 城市经济空间演进的地理趋势:多中心协同状网络化
城市经济空间和生产方式存在着相互创造、双向同构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空间作为生产的“容器”,生产力的发展如新的生产部门的涌现、新的专业化分工、新的生产技术带来空间专门化和分异化的需要,形成了人类对空间的类型化和纵深化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本身作为生产的要素,对空间的组织和管理也会影响到生产的具体运作形式进而影响到生产的效率,这就必须运用恰当的形式来对空间进行集合化和连合型利用。当今世界的城市经济空间正在呈现“分异”和“连合”的辩证演进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形成城市经济空间三种推进的地理趋势:“多核”的专业化生产空间——“带状”的区域化经济空间 —— 经济空间的全球“接入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这一城市经济空间的地理趋势也正在加深,并且向不发达的城市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蔓延。越来越广泛的地方城市,越来越深入地卷入全球经济网络之中,被“拉扯”“牵动”着进行经济空间的“外扩”和“内爆”。我们应该顺应这一城市经济空间演进的历史地理趋势,积极推动对中国各类城市经济空间的合理规划、组织、引导和培育,以提升中国城市经济空间的专业化、聚合性和全球“接入度”。
(一)“多核”的专业化生产空间
当前,跨国资本依靠信息技术对全球生产空间采用灵活细分策略,以适应分化的生产部门、灵活“分包”的分工形式对特质化、类型化、差异化空间的需求。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的空间部位凭借一些新兴的生产部门,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承担着“弹性专业化”的生产分工,凭借竞争优势成为全球经济网络的新中心,在原有的城市边缘地带生出经济活跃的多“核”状的生产“小中心”。如洛杉矶城市郊区从事专业化电子、宇航和生物医学、电影生产的多个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各个小中心之间通过信息、交通网络形成“扩散型”的城市经济空间结构,戈迪纳( Godina)提出了“多核心大都市区域”,以及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使用了“合成的扩散型城市”一词来描述这种拼凑式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城市承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的转移,成为了跨国资本的海外加工基地和制造业中心,如中国珠三角的各个城市,各自以电子信息、服装、家具生产等专业化生产参与到全球制造业生产体系中,成为专业化的代工产品加工基地。在珠三角城市区域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江门等“多核”的小生产中心,经济和人口高度集聚在这些核心城市,同时在这些“核心城市”之下又形成了更小的次级“中心点”或者说“亚中心”,各中心点之间已经通过功能分工和资金流、劳动力流、信息流、技术流密切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功能上的城市经济区域,这是规划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已有的空间物质基础。
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大部分城市虽然并不直接服务于全球经济体系,与全球经济网络的联系并不太紧密,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入到国际区域经济网络中,因此在城市空间发展战略上,应定位城市不同空间部位的专业化生产优势,积极承接跨国资本和沿海企业转移的工业和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并通过区域内现有大都市集聚点的带动和辐射,培育若干 “遍地开花”的专业化生产小“中心”甚至“亚中心”。
(二)“带状”的区域化经济空间
经济活跃的“多核”小中心之间由于生产集聚产生的集合效应会辐射到更大的空间范围,相邻的从事相关产业的小中心会不断增加,形成产业集聚乃至带状的城市集聚带,各小中心空间单元彼此间共享资源、技术、信息等要素,形成一种竞争合作、分工协作的互动式关联,形成整体的区域竞争优势。“在发达国家产生了都市圈、全球城市区域、全球性巨型城市区、巨型城市区等各种城市群体空间聚集的地域景观”。发达国家的城市群主要有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其中又包括了多个城市区域,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是美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商业贸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包含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城市区域。“都市圈、都市区、城市群等,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①张京祥、罗震东、何建颐:《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在中国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中,也需要培育功能互补、专业化凸显、整合效应的点连网、网连圈、圈套圈的大型聚合型经济区域,优化区域城市群的空间聚集、整合和辐射效应,提升城市空间整体的经济效能和边际效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进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对这一城市经济空间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还需要在这些目标基础上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稳步推进、积极实施。
(三)经济空间的全球“接入性”
跨国公司凭借信息网络技术对全球分散的生产进行“集中控制和管理”,导致了一个“由网络和都市节点组成的新地理学的诞生”。②[美]曼纽尔·卡斯特:《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刘益诚译,《国外城市规划》2006年第5期。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指出,一些城市凭借跨国金融业、新型高科技部门、专业化的跨国生产服务业上升为“全球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的“节点城市”,“由日益增多的全球城市形成的跨国网络,构成了全球经济的组织结构中的关键组成部分。”③[美]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周振华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依照与全球经济网络的“接合”紧密程度的不同,形成了城市新的全球等级体系,“处在这些城市的等级体系之外的那些城市和地带,变得边缘化了”。同时萨森指出,“全球城市是逐渐培养、发展和建设起来的”,④[美]萨斯基娅·萨森:《城市的专业化差异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至关重要》,董宏伟译,《国际城市规划》2011年第2期。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城市也融入全球经济网络中去,城市的经济“全球性”程度也在加深。如香港,萨森认为它已经是“全球城市”,北京和上海直接服务于全球区域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全球性”,而大多数城市处在“全球城市体系”的边缘和之外。为此要积极推进“全球城市”的建设,在2016年最新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已经首次提出“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对一些发展得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要根据条件提升经济的“全球性”,以提供独具的专业化产品和服务“接入”到全球各种经济圈,如制造业圈、金融圈、航运圈、科技与文化产业圈等圈层中;一些边缘的城市可通过与发达城市间的经济联系间接加入到全球或者国际区域经济圈中,如通过旅游业、特色文化产业加入全球旅游经济圈和文化圈,提升经济空间的“国际接入性”。
穿过城市的历史,我们看到城市经济空间由孤立的“点状”到“块状”,再到“圈层”“带状”发展,甚至形成了隐形的全球“网状”。这一方面显示了经济空间的分异和连合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显示了人类对空间的组织、管理的主体能力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空间的演进中也包含着空间等级化、空间设施不平衡、劳动分工的不平等、弱势群体空间权利缺失等社会关系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我们必须把握城市经济空间演进的趋势以顺势而为,并运用制度的优势优化城市空间关系,实现“高效、公平、和谐”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