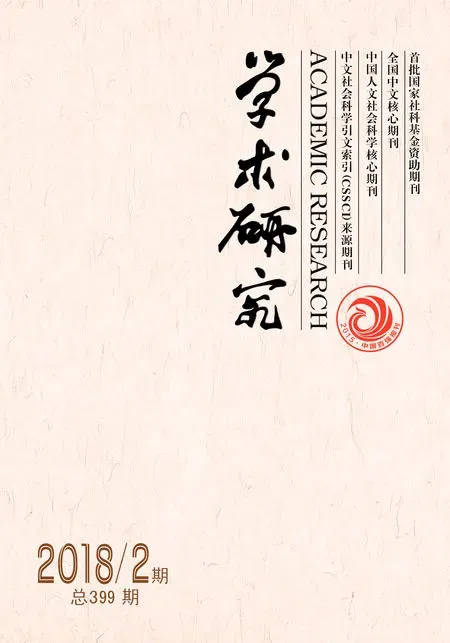析汤用彤对中国真精神之玄解
——再谈《理学谵言》*
李兰芬
一、引言:学术何为
对于近现代大多数中国学人,为学,尤其是为国学之目的是为保卫文化,保卫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其时,有学人曾喊出这样一句口号:“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a黄节:《〈国粹学报〉叙》,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43页。
20世纪上半叶,各种形式的国学研究逐步复兴。在强烈的民族情怀驱使下,在明确学术必须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统继承,当做与国家民族重振关联的大问题为为学之目的共识下,用何种最有效(或最恰当)的学术方式,来挖掘及重现中国文化精神中自生、自强、自尊、自重等的品格,是各种形式的国学研究,甚至是每个国学研究者首先要自觉解决的问题。
几乎伴随儒学、佛学等同时兴起的玄学研究(尤其是魏晋玄学研究),面对的问题可能要稍为复杂。历史上的魏晋玄学,因其特别的学术风格及生活方式,更因其经典之源上对道家思想的偏重,不为儒家道统所接受。其学术风格甚至被一些儒家批评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b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就不断有儒者从生活方式、学问方式及思想内容上批评玄学家。如果作为国学复兴中的一种学术努力,玄学研究者是否具有维护中国精神(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品格?如果有的话,他们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历史上受争议的特殊方式,来体现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的努力呢?
本文尝试通过对汤用彤《理学谵言》的再理解,分析汤用彤选择玄学研究方式时的独特文化情怀,以及他运用这种学术方式对儒家思想的独特解读。
二、独特的文化保守情怀及“玄学”方法
“玄学”一词,首先是指汤用彤曾在学问上用心且成就卓越的研究对象——魏晋玄学,属传统学术(国学之一种)。同时,在近现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语境中,它也泛指与广义的哲学、宗教观念相联系的思维特点或思想取向,兼有新学术的特征。汤用彤在近现代文化背景中,为联结两者的重要学问人物。因此,汤用彤的玄学研究应有双重含义:重新解释玄学作为传统中国学术之一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发掘玄学这种传统学术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及对现代问题解决的作用。
将汤用彤的双重“玄学”含义,重新置放在近现代中国文化交流、激荡的情势下,可以看到“玄学”或“玄解”,正是汤用彤本人实现自己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方式。
汤用彤选择“玄学”作为自己卫道的学术方式,在其最早的长文《理学谵言》中已有清晰的表述。
首先,我们来看汤用彤为学目的之自述。
在汤用彤后来享誉学界的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他动情地述说自己学术的志向。他说,自己所做之学术,无非是为了让“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a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的努力。
而什么是汤用彤心目中的“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呢?汤用彤在《理学谵言》中明确:“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b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这一看法,汤用彤后来在王弼圣人论及王弼《论语释疑》的研究中,有进一步的论述。参见《汤用彤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这种“真文化真精神”,汤用彤特别强调它与那些盲目的“全盘西化”主张者所崇尚的物质文化不一样,是“精神”性的文化:“不置夫以古之理学与今之科学比,则人咸恶理学而求科学矣,不知理学为天人之理,万事万物之理,为形而上之学,为关于心的;科学则仅为天然界之律例,生物之所由,驭身而不能驭心,驭驱形骸而不能驱精神,恶理学而乞灵科学,是弃精神而任形骸也。”c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第1页。
要捍卫这样一种精神性的文化,从学术方式的选择上,汤用彤自觉为:“哲学”或“玄学”。
尽管汤用彤获得其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史实求证的严格方法,d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研究是奠定其崇高学术地位的标志性成果。而这种研究成果一直被认为是史学和文献学的。晚年汤用彤先生除继续用心佛教史料和文献资料的证研外,还用力于道教史料和文献资料的考证。参见《汤用彤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张申府先生、汤用彤先生、梁漱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赵建永:《汤用彤与现代中国学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但就汤用彤本人而言,他最独特体现的是其自觉的“玄学”方法。e本文所用的“玄学”方法,与“玄学”有关。“玄学”不是指泛义的哲学、宗教,而是专指在维护中国文化命脉的努力中,对中国魏晋南北朝玄学的研究。它与泛义的哲学、宗教,甚至人生观有关,但更与对中国某一时期学术、思想风格的探索有关。而“玄学”方法,则既指哲学、宗教的研究方式,又指魏晋玄学的学术风格。这是一种对精神进行玄解的独特学术方式。汤用彤自己作这样的描述:“中国华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人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f参见汤用彤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所写的《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这样评论汤用彤方法论的自觉及佛学、玄学研究上的特色:“他尝说,真正高明的哲学,自应是唯心哲学。然而唯心之心,应是空灵的心,而不是实物化或与物对待之心。这已充分透露出他的哲学识见了。他的佛教史虽采用了精密的考证方法,然而却没有一般考据家支离繁琐的弊病。据作者看来,他得力于第一以分见全,以全释分的方法。他贵在汇通全时代或一个哲学家整全的思想。他每因片言只字,以表证出那位大师的根本见解,并综合一人或一时代的全部思想,以参证某一字句某一章节之确切的解释。第二,他似乎多少采取了一些钱穆先生所谓治史学者须‘追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他只是着眼于虚心客观地发‘潜德之幽光’,设身处地,同情了解了古哲,决不枉屈古人。既不抨击异己之古人,亦不曲解古人以伸己说。”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在汤用彤后来的学术研究中,玄学或哲学的方法,始终是他体现自己学术志向(独特文化保守情怀)的最重要方式。或者说,正是透过玄学研究(不是纯粹的“哲学”研究),汤用彤找到了恰当言说中国真文化真精神的学理方式。佛学固然是一种具驭心驭身大作用的玄远之学,但于中国切身的问题解决而言,汤用彤仍认定:“本国之学术实在孔子”(《理学谵言》)。理学作为孔子之道统的承继者,其形上学特质与佛学有关,而追溯得更远一点说,起码中国佛学作为玄远之学的驭心驭身作用,与玄学的影响分不开。a汤用彤在魏晋玄学研究中,就已将佛学中国化的最初努力看做玄学发展的其中一个阶段,参见氏著《汤用彤全集》第4卷。他还开出专门课程强调《玄学与中华佛学》,参见氏著《汤用彤全集》第5卷。汤用彤将儒家理学与魏晋玄学关联起来考虑的做法,也可在任继愈先生对自己一篇早期论文的写作渊源的追思中,得到旁证。任继愈先生在《理学探源》一文中,提到文章是在汤用彤的指导下做成的。“这篇文章使人联想起四十多年前某些知识分子在漫漫长夜中梦想‘学术救国’艰难前进的状况”,“本文所论为探研理学之渊源”,“宋兴百年儒学复振于五代禅学鼎盛之后。袭魏晋之玄风,承孔孟之余绪,于理气性命心体善恶之问题作一空前之总结束,内之如心性之源,外之如造化之妙,推之为修齐治平,存之为格致诚正,无不尽其极致。两宋以迄清末,八百年来哲学界逐为理学所独擅,岂为偶然?然亦须知此固一种思想之自然演进,非为被动,亦非自葱岭带来也”。《燕园论学集——汤用彤先生九十诞辰纪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02、302、307页。贺麟说,这是汤用彤独特的对“中国哲学的道统”、中国精神之“持续性和保存性”的“新颖而深切的看法”。参见氏著《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正是为求明有这样一种妙用的学说的真面目,汤用彤开始他对玄学的深悟妙发。b孙尚扬在此评论前,转引了一段汤用彤对哲学的界定(由贺麟记载的):“真正高明的哲学,自应是唯心哲学。然而唯心之心,应是空灵的心,而不是实物化或与物对待之心。”孙尚扬:《汤用彤》,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96年,第205页;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
下面,我们通过《理学谵言》,看看汤用彤对中国文化真精神的“玄解”。
三、《理学谵言》形成的“玄解”风格
《理学谵言》是汤用彤第一篇阐述其对中国文化真精神理解及玄解这种真精神的论文,c发表于20世纪初。也是汤用彤极少几篇现存的、正面讨论儒家思想的论文之一。d据孙尚扬整理的《汤用彤学术年表》记载,汤用彤的《理学谵言》自1914年9月至1915年1月连续刊布于《清华周刊》第13至29期,参见孙尚扬:《汤用彤》。除这篇正式刊发的讨论儒家思想的论文外,汤用彤还曾在1913年达德学会主办的《益智》杂志“文篇”栏目发表了阐述儒家政治思想观的《道德为立国之本议》一文,在1917年《清华周刊》第三次临时增刊的“课艺”栏目发表《论成周学礼》一文。两文均由赵建永整理,重刊于《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4期。除此之外,汤用彤还有一篇尚待整理、发表的讨论儒家思想的文章。与这篇文章相关的演讲,在吴宓日记中被提到。《吴宓日记》第8 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汤用彤未刊文稿整理者赵建永在《汤用彤未刊稿的学术意义》一文中提到,汤用彤未刊的、在1941年于武汉“儒学会”所作的演讲稿为《儒家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所在》。参见氏文《汤用彤未刊稿的学术意义》,《哲学门》2004年第2册。我们从主题看,应该是回应他1914年发表在《清华周刊》杂志上的《理学谵言》的主张:“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另参见汤用彤:《儒学·佛学·玄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6页;赵建永:《汤用彤与现代中国学术》。实际上,这不是一篇严格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针对当时中西之争、理学与科学之争而作的感言。它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也毫不掩盖个人特色。e笔者另篇论文《理学的另类解读——析汤用彤〈理学谵言〉》(《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对汤用彤这篇长文有较仔细的文本分析。
在文章里,可以看到,汤用彤对理学(他喻为中国真文化真精神之所在)的理解,既与他自己选择的文化守成主义的立场相关,也与他在后来学术研究中显现出来的“玄学”情结有关:他较为侧重儒学的心性、精神方面的作用。
《理学谵言》全文一共分成三个部分:“阐王”、“进朱”及“申论”。这三个部分的安排,汤用彤颇费心思:“阐王”是重新阐明阳明之学,以纠自明末以来腐儒对心学的曲解;“进朱”除了梳理朱子之学的深奥外,更重要是从治时弊的角度来强调朱子学说的精神更为可贵;“申论”则再次回应他在文章开头的文化守成主义态度,表明对理学的这种弘扬、解释是他自己的体会与感言。在这三部分里,汤用彤对理学作为中国真文化真精神的实质,作了颇为特别的“玄”解。
首先,汤用彤从心性、形上角度,理解儒家思想和理学作为中国文化真精神的缘由。在他看来,万事万物之根本在精神,在形而上学之理。“理学为天人之理,万事万物之理,为形而上之学,为关于心的”(《理学谵言》)。也即是说,在汤用彤看来,儒家之“理”与“心”(精神)合,不在形下而在形上(“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a《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2页。更在理与心合,体现天人合一。这种合一,一在于使人有了可使心致良知之大用(人的精神在契合天理时的功用),二在于更有促人“修身必始自格物”的“克欲”之功(以天理制约人理或人欲的泛滥)(《理学谵言》)。从根本上说,“玄”解,强调中国文化之真精神即儒家的“理学”不纠缠枝末,不为人欲所驱。
其次,汤用彤认为,“玄”不意味着空与虚,它必须是真“知”实“学”与“存养省察”,以及“克己”结合的“为学工夫”(阳明);必须是朱熹所倡的心性养成相关的主敬工夫与对事物各理穷尽、通明的为学工夫,还有反躬实践的省察工夫三者结合的“穷理之学”(《理学谵言》)。或者说,于一国文化之真精神而言,儒家对天理与人心合一的强调,仅意味着儒家赋予其中的各种人努力、用心的可能,于己、于家、于国、于文化、于天下有共同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与省察修身齐家治国天下之道德功夫和学风相关。“故吾辈有志救国不可不发愤图强,发愤图强不可不除偷怠之风,除偷怠之风不可不求鞭辟入里之学,求鞭辟入里之学,求之于外国之不合国性,毋宁求之本国。本国之学术实在孔子。孔子之言心性者,实曰理学。况治弱病,必择学术中之最谨严,行动言语之间丝毫不使放松,无可推诿无可怠惰,日日慎独,时时省身则可。如此之学术舍理学外罕见其他,故理学者医弱症之良方也。”“欲求实学,欲求毅力首在道德,求之本国,舍朱王何以哉!”
四、汤用彤“玄解”的独特与严谨
可以看出,汤用彤玄解理学(中国文化之真精神)的独特,在于他强调理学的形上之心性品格,必须与切己的、严谨的道德践行(学风)(修身)结合,与齐家治国天下的担当结合,只有这样,理学才是中国文化精神之真的完全体现。
这两方面的强调,使得汤用彤在解读中国文化真精神的时候,其“玄解”方法自觉区别开片面地空谈心性的“唯心”做法。不纠缠事理,并不意味不严肃、认真学习,不意味不明事理,不意味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不担当。
在《理学谵言》前言中,汤用彤曾提到,他对理学家原本抱有厌恶之心,厌恶的缘由与一些明清理学家所展示出的理学的偏激风气有关。从汤用彤的传记资料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对理学态度的转变与主观臆想无关。b如他在《理学谵言》开篇及结语中所说。汤用彤受父亲雨三公(汤霖)喜汉学的深刻影响,对学问一贯持严谨或谨慎的求证态度。c参见孙尚扬:《汤用彤》,第13页。另参见胡适日记,其中记述了他与汤在如何为学上的分歧。《胡适日记》1937年1月17日记载:“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文为他校阅。”“此书极好。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另在隔天日记中胡适继续记载和评论:“到北大,与汤锡予先生畅谈。他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这是谦词,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据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所以,他首先不是从道德或玄理上批评当时的理学家,而是从学风上唾弃他们。“学者唯心太甚,流于荒诞妄为,不顾细行,不恤人言,阳明之学至李卓吾等一派而大决裂,以致其始,徒侣偏天下,学说风动一时。明祚,而谈者辄疾首痛心恶之矣。故吾国不患无学术,不患无高尚之学说,而勇于开山难于守成,勇于发扬而难于光大,时至今日,数千年文明之古国亦遂学绝道丧,寂寂无人矣,未尝非学者之罪也。”另外,他对理学的推崇也不仅仅是意气用事。受父亲的感召,他对中国文化不仅满怀深情,而且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及坚守有自觉的责任担当。a参见麻天祥(麻天祥:《汤用彤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孙尚扬(孙尚扬:《汤用彤》)为汤用彤所作的评传。及参见汤一介追忆汤用彤的纪念文章及著述(汤一介:《我们三代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等。而以严谨的学风来重新阅读及体会理学的真义,则得益于他在顺天学堂、清华学堂时国学老师的启蒙。b展现当时在顺天学堂、清华学堂国学学习情形的是吴宓。参见吴学昭:《吴宓与汤用彤》,《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可见汤用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认同及解读方式,都与其严谨或谨慎的求证态度和学术方法相联。
实际上,在《理学谵言》中初步形成的对中国学术的态度和方法,成为了后来汤用彤继续研究佛学和玄学的特殊文化观念方法。在他的研究中,文化保守的价值立场和相对包融外来文化,还有长远的历史眼光是相辅相成的。用他与学衡派同仁所自觉的话来说,便是“融合新旧,撷精之极,造成一种学说,以影响社会,改良群治”。c吴学昭:《吴宓与汤用彤》,《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汤用彤的玄学研究,是他继《理学谵言》后,对中国文化真精神作系统玄解的重要学术成果。d相对而言,汤用彤佛教史的研究,基本被看做是他学术风格中小心、严格求证的史学类著作,他在解读中国佛教思想时所体现的文化保守及价值立场虽有被提及,但并不认为汤用彤自己对此有特别阐发。而魏晋玄学研究,则被认为影响了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魏晋玄学研究中主义理派一系。参见陈明:《六朝玄音远,谁似解人归》,《原学》第2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汤用彤对魏晋玄学,以及中国玄学的解读,既与他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更与他独特地企图通过玄学研究来挖掘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空灵”之哲学精神的妙用有关。e这一点在前面引述任继愈先生的话已提及。
在玄学研究中,汤用彤不仅从历史角度追溯了与理学有渊源关系的魏晋玄学之发展,而且他通过概念的重塑以及对魏晋玄士解释经典风格的分析,从理论上相对完整地表述了他对何为中国文化之真精神的看法。f《汤用彤全集》第4卷,展现了汤用彤对玄学研究的几个组成部分:研究文章、系统讲课稿等。其中,从汤用彤的研究文章对人物经典解释风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汤用彤不仅是在呈现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新眼光、新方法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呈现这种新眼光和新方法对于儒家思想从文化、价值立场上被解释的重要作用。汤用彤对王弼新圣人观的解读时,所表现的深厚价值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应是汤用彤本人对何为圣人的一种文化保守意义上的期待。另外,在汤用彤的中英文玄学讲稿里,可以看出汤用彤企图通过几组既有形上精神性特点,又有中国文化、价值特色的概念,来体现中国思想的“哲学”本性。也即是说,汤用彤不纯粹是通过魏晋玄学研究在做学术史的工作或狭义的哲学解释工作。
只是,汤用彤在后来并没有将这种研究进行到底,他所期待的从玄远维度重现中国精神之源并同时能融会新知的愿望,多少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被渐渐淡漠。原因所在,是另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