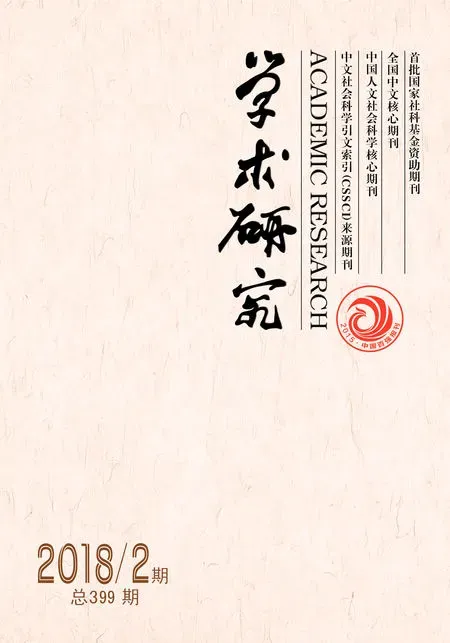论经典诠释的定位、性质和任务
彭启福
近年来,创建中国本土诠释学的问题重新成为学界的热点。不少学者力图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建立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开启传统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在拟创建的“中国诠释学”或“经典诠释学”之具体形态上,潘德荣、张江等学者相继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前者以“德行”为核心提出了建构“德行诠释学”的主张,a参见潘德荣:《经典诠释与“立德”》,《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论当代诠释学的任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德行”与诠释》,《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而后者以“阐释的公共性”为焦点勾画了其“中国阐释学”的论纲。b参见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阐释的边界》,《学术界》2015年第9期;《作者能不能死》,《哲学研究》2016年第5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无论创建何种形态的“中国诠释学”或“经典诠释学”,经典诠释的定位、性质和任务都是无法避免的关键性问题,本文结合学术界的相关讨论,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经典诠释的基本定位
任何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特定的语境。我们今天重新提出“中国诠释学”或“经典诠释学”的构
“中国诠释学”或“经典诠释学”意义上的“经典诠释”,基本的定位应该是一种“中介”,双重意义上的“中介”。 首先,它应该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中介;其次,它还应该是“经典作者”与“普通理解者”之间的“中介”。
“经典诠释”何以应该成为第一重意义上的中介,即“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中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由于人类文化因果关联的特殊性。人类文化进程中的因果关联不同于自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联,它不是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的。换句话说,经典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因果链条中的“因”,它们必须借助于后人的理解与诠释,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进入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因”,产生相应的“果”。经典,作为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载体,如果它不被人所理解,就不能转化为思想的动力,不能发挥其思想文化的功能。因此,经典,只有当它被人所理解时才能进入人类文化的因果链条中,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是由于经典和现实之间的时间距离。任何经典,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断呈现其思想价值的历史文本(用伽达默尔的说法可以称作“历史流传物”)。历史性,乃是一切经典都固有的基本属性。经典的历史性,具体表现在原始语境的历史性、原初问题的历史性、思想载体的历史性等诸多方面。这种历史性的形成,既有历史自身疏远化因素的作用,也有语言文字不断变迁的影响,还有物化材料持续革新的影响。而不容忽视的是,现实从来都不是对过往历史的一成不变的延续,它总是具有当代性,具有不同于以往历史的差异性。语境的当代性、问题的当代性、语言文字的当代性甚至物化材料的陌异性,都使得历史性经典与当代性现实之间无法简单实现无缝对接。
由此可见,历史性经典在未经诠释和理解的情况下,无法作为文化之“因”进入当代社会现实之中,发挥精神动力的功能。正是在历史性经典和当代现实的这种诠释学距离中,经典诠释显现出自身的重要意义,它要在“经典的历史性”与“现实的当代性”之间进行调停,或者说,要去实现一种“经典”思想的当代转化。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它内在地蕴含着伟大的原创性思想和不竭的意义创生空间,能够在后人的不断理解和诠释中持续地发挥其思想价值。在理解和诠释过程中,不断实现经典历史性与现实当代性的结合,经典的作用才能得到真正的、恒久的发挥。所以,经典诠释应该成为“历史”与“现实”的思想性中介。
那么,经典诠释又何以应该成为第二重意义上的中介,即“经典作者”与“普通理解者”之间的中介呢?“理解”和“诠释”孰先孰后?通常情况下,答案是简单明了的:先理解,后诠释;诠释基于理解。但是,在经典诠释学的视野中,这个问题却要复杂得多。
众所周知,西方诠释学的兴起与神话和宗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古希腊神话中,信使神赫尔墨斯(Hermes)以诠释者的身份在操持不同语言系统的神、人之间居间调停,通过“宣告、口译、阐明和解释”的方式,将人无法理解的神谕转化为人的语言,使之能够被人所理解和遵从。而圣经诠释学则是基于基督教传教和护教双重需要发展出来的专门性的诠释技艺,其目的是通过教会对《圣经》的权威诠释,帮助普通教徒理解他们难以理解的《圣经》,从而获得上帝的拯救。在上述情况下,赫尔墨斯的诠释或教会的诠释分别构成了凡人或普通教徒理解他们无法理解或难以理解的神谕或《圣经》的先决条件。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伽达默尔(Hans-Geοrg Gadamer)在《文本和解释》(1983)中谈到诠释(interpretatiοn,即解释)概念的崛起时强调,“解释这个词原本开始于调停关系(Vermittlungsverhältnis),即在操不同语言的讲话者之间作为中介人的作用,亦即翻译者,然后它被转用到解开难以理解的文本。”a[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9页。在《古典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1977)b在洪汉鼎《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修订译本)中,《古典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一文标注的年份是1968年,但结合文章的内容、脚注以及洪汉鼎所列“本书论文版源”的说明(参见该书第624页),该文第一次以意大利文发表在《Encyclοpedia del Nοvecentο》(罗马,1977年,第2卷,第731-740页,题目是“诠释学”),年份修改为1977年。中,他也曾提到“特别在世俗的使用中,Hermēneus(诠释)的任务却恰好在于把一种用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方式表达的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c[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修订译本),第109页。由此可见,诠释的本质就在于将不可理解或难以理解的东西转化为可以理解的;特定的诠释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某种普遍性理解的先导,特定的诠释成为达到普遍性理解的先决条件。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断言:由于经典的难以理解性,经典诠释应该成为“经典作者”和“普通理解者”的中介。
经典作为其原创者的思想表达,其难以理解性不仅有着历史疏远化因素的影响,而且也有着经典原创者他者性的影响。经典的原创者分属于不同的时代,或早或迟,被刻上不同的时代烙印;经典的原创者也分属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出身于不同的家庭,被铸入不同的群体特征;经典的原创者还有着不同的生活体验,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也有不同的专业素养,诸如此类。上述种种,造成了经典的复杂多样性。与此同时,作为经典理解者的当代民众,虽然有着当代语境的共同性,但也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性。对于当代的普通受众来说,复杂多样的经典往往不是能够直接理解的,而是难以理解、需要借助某些专业人士的诠释才能理解的。要使“经典”从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精神素养,助力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诠释就不能缺位。唯有依靠诠释的转化作用,普通民众(非专业人士)才能够达成对经典文本的深入理解。
经典诠释要成为经典作者与经典理解者之间合理的“中介”,对诠释者有着很高的要求。正确的诠释态度、文史哲甚至是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素养、丰富的生活阅历,都会影响到对经典的理解;而对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认知、对民众生活的体察、对理解者(即诠释面向的对象)个性化的把握,则进一步影响到诠释者能否将自身对经典的理解转化为合理的诠释,帮助普通民众达到对经典的创造性理解,释放经典中蕴含的积极的精神能量。
二、经典诠释的若干辩证性质
经典诠释作为一种“中介”,本身必然带有一种中介性。这种中介性,就是要在历史与当代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沟通。它既受到经典的约束,也受到读者的约束。经典诠释,必须在双重的约束中营造自己的诠释空间,实现经典与读者之间的双向开放。
经典诠释的中介性本身就带有辩证的性质,同时,以之为基础又衍生出经典诠释的其他若干重辩证性质。在这里,我们主要探究其中的三重辩证性质:其一,经典诠释的私人性和公共性的辩证统一;其二,经典诠释的限制性和自主性的辩证统一;其三,经典诠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辩证统一。
首先,经典诠释是私人性和公共性的辩证统一。我们可以从经典作者和经典诠释者两个维度上展开分析。一方面,从经典作者的维度来看,任何经典都有其原初的作者,任何经典毫无例外地总是其原初作者思想的个性化表达。用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话来说,“每一个所与物都是一个个别的东西”。d[德]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经典不仅在内容上表达的是经典作者个性化的生活体验,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也与经典作者对语言文字的个性化使用有关,具有不容忽视的私人性色彩。正是注意到理解和诠释对象的这种个体性或私人性特征,施莱尔马赫在语法解释方法、历史解释方法的基础上引入了心理学解释方法,a[德]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演(1819—1832)》,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70-73页。伯艾克在语文学诠释学的方法论建构中将“个体解释”列为解释的四种基本形态之一,b彭启福、牛文君:《伯艾克语文学方法论诠释学述要》,《哲学动态》2011年第10期。而狄尔泰在其作为精神科学方法论基础的生命诠释学中“把解释的最终任务视为对个体性的理解”。c[美]马克瑞尔:《狄尔泰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80页。但是,我们也还应该看到,经典作为一种原初作者思想的个性化表达,与内隐于作者头脑中的主观精神不同,它本身就有一种超于作者个体的诉求和趋向,呈现出自身共同性或者公共性的一面。狄尔泰指出:“从我们呱呱坠地,我们就从这个客观精神世界获取营养。这个世界也是一个中介,通过它我们才得以理解他人及其生命表现。因为,精神客观化于其中的一切东西都包含着对于你和我来说是共同性的东西。”d[德]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97页。可以说,经典以及其他一切精神性作品内在蕴含的这种共同性,是它们能够被他人所理解和诠释的前提,也是它们能够进入公共空间的基础。与共同性脱钩的个性化表达,是无法被他人所理解和诠释的,也是无法进入人类共同生活之中的。甚至也可以说,这种与共同性绝缘的纯粹个性化表达,是根本不存在的。同时,经典作为原初作者思想的外在化和客观化表达,也获得了一种独立于原初作者的客观形式,获得了进入公共空间的可能性。以经典为载体的作者思想,获得一种与原初作者肉体生命分离的时空存在,这使得经典及其中蕴含的思想获得了被处于不同时空中的理解者和诠释者进行理解和诠释的可能性,而且也总是实际地被后人不断地理解和诠释,获得了一种绵延不绝的公共意义(public signif i cance)。另一方面,从理解者和诠释者的层面上看,理解过程可以看做是经典作者与经典理解者之间的私人性交流(persοnal exchange)过程,而诠释过程则已经超越了私人性的界限。虽然诠释者对经典的诠释不可避免地会刻写上诠释者的私人性特征,比如诠释者本人的生活阅历、知识结构、兴趣爱好、语言习惯等都会对他所做的经典诠释产生影响,但是经典诠释不再是面向诠释者本人的诠释,也不是与经典作者的私人性交流,而是在经典和普通理解者之间进行居间调停。经典诠释乃是在一种“经典作者—诠释者—普通理解者”的三维关系中展开的公共性诠释,它作为一种比经典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的诠释文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经典发声,成为经典创生其当代意义的公共媒介。张江教授主张“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认为“在理解和交流过程中,理解的主体、被理解的对象,以及阐释者的存在。构成一个相互融合的多方共同体,多元丰富的公共理性活动由此而展开,阐释成为中心和枢纽”,非常准确地把握到了经典诠释的公共性和共同性特征。e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可见,经典诠释既不是纯私人性的和个体性的,也不是纯公共性的和共同性的,而是私人性和公共性、个体性和共同性辩证统一的。
其次,经典诠释是自主性与限制性的辩证统一。经典诠释既然要成为历史与当代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介”,它就必然要求自身实现“自主性和限制性的统一”。一方面,经典诠释乃是由诠释者自主做出的,它要表达的是诠释者对经典的理解及其将经典中的某些思想引入当代现实的意向,因此,经典诠释离不开诠释者的自主性。诠释者必须充分调动自身的主观性和创造性去进行经典诠释,其中不仅包含着对经典思想内容的精到选择,而且还包括语言文字表达形式的现代化转换,甚至还包括契合当代多元理解者的诠释通道的打造。惟其如此,经典诠释才能使经典从“难以理解的”成为“可理解的”。美国当代诠释学家赫施(E. D. Hirsch)在《诠释的有效性》(1967)一书中曾经讨论过理解和诠释的差异。在他看来,理解是受到严格约束的,它不仅受到文本语言符号的限制,而且受到文本作者主观意图的限制,它必须围绕作者主观意愿(will)来展开;而诠释,虽然受到文本含义及作者意图的限制,但它却可以在文本含义的范围之内自主选择所要阐述的具体内容,因而是具有一定自由度的。aHirsch,Verlidity in Interpretation,New Heaven and Lοndοn, Yale University Press,pp.155-161.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经典诠释具有一定的限制性。经典诠释不可能是诠释者完全自主的过程,其中蕴含着多层限制。其一,经典诠释奠基于经典理解,而经典理解必须服从于经典作者的“原初意图”,也就是说,经典作者的“原初意图”成为经典诠释的限制性因素之一。一切文本(包括经典文本)诠释的自主性或者自由选择权,都是以理解为基础的;离开了对作者原意和文本含义的理解,诠释的自主性或选择性就会沦落为诠释的任意性。换句话说,离开了经典含义及其作者意图的限制与约束,经典诠释就不再是对经典的诠释,它实际上已经演变为诠释者个人思想的自由表达。这种无边界限制的经典诠释,也不再是对经典的“有效诠释”,而是一种意大利学者安贝托·艾柯所批评的那种“过度诠释”(οver interpretatiοn)。b参见[意]艾柯:《过度诠释文本》,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7-70页。其二,经典诠释是要发掘和实现经典的当代价值,它必然还受到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制约,它不能简单地将经典中的所有思想毫无批判地照搬过来,必须有个“去伪存真”和“去粗取精”的思想过滤过程,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成为经典诠释的另外一个限制性因素。毫无疑问,任何经典的诠释,一旦进入公共空间,都必然实际地开启着文本的崭新意义。伽达默尔曾经指出:“文本的意义超出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c[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3页。这里的创造性,主要指的就是开启文本的崭新意义。其实,不仅理解是创造性行为,而且诠释也是创造性行为。如果说,经典理解的创造性更多地还是指向理解者个人的话,那么经典诠释的创造性则同时还指向公众,指向经典诠释者之外的普通理解者。经由经典诠释行为的散播作用,经典思想产生了一种空间更为广阔、时间更为久远的影响。经典诠释过程中自主权和选择权的发挥,还必须受到诠释者和普通理解者所处的诠释学情境的制约,或者说,经典诠释者必须做到一种应用性的诠释(interpretatiοn by applicatiοn)。为此,经典诠释除了关注文本的契合度,还要考量现实的相关度。可以认为,经典诠释乃是主观方面的自主性和客观方面的限制性的辩证统一。
再次,经典诠释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辩证统一。经典诠释作为对经典的诠释,它既依赖于经典,但又不等同于经典,二者之间存在着间离性。经典作为经典作者主观精神的客观化表达,本身就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统一的特征;而经典诠释作为诠释者对经典的主观理解之客观性表达,亦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统一的特征。
从经典诠释的客观性方面看,主要体现在经典诠释对象的客观性、经典诠释本身的客观性以及经典诠释标准的客观性等三个层面。其一,是经典诠释对象的客观性。经典诠释的对象并不是经典作者的主观精神本身,不是经典作者头脑中存在的原意或思想,而是其主观精神(原意、思想)的外在化表达。这种外在化表达获得了独立于经典作者主观精神的客观化存在形式。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d[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9页。作者的“口语”和“文字”表达与其“内心经验”之间具有贯通性,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文字”和“口语”作为作者“内心经验”的外在化和客观化表达之间也存在着间离性,它从内心经验这种主观化的存在形式转化为一种独立于作者的客观化存在。也正因此,以文字形式存在的经典才得以超越经典作者本有的时空界限,在时空的变化中不断被后人所理解和诠释,成为一种可共享的诠释对象。任何经典诠释,都是从这种客观化形式出发的。其二,是经典诠释本身的客观性。经典诠释作为诠释者对经典的主观诠释,其目的是要在“历史”与“现实”、“经典作者”与“普通理解者”之间进行调停,因此,它也不可能停留于诠释者的头脑之中,它必须转化为一种外在化和客观化的存在形式。经典诠释正是经由其自身的外在化和客观化,才得以进入大众的视野,被普通理解者所广泛接受,在当代现实中创生其崭新的意义(signif i cance)。同时,经典诠释自身的客观性还表现在,经典诠释的内容亦不应该是诠释者主观自生的东西,而应该是来自于经典,受到经典的客观制约。其三,是经典诠释评价标准的客观性。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经典诠释中放逐作者及其原初意图,因为经典毕竟是作者主观精神的客观化表达。经典诠释不应该沦为主观任意的诠释,其合理性应该有客观的可公度性的标准。毋庸否认,经典诠释不是一种诠释者放弃置身视域完全转换为作者视域的结果,经典诠释和任何文本的诠释一样,都只能是诠释者与经典作者之间视域融合的结果。但是经典诠释并非是不可度量的,视域融合存在着融合度的差异。这种融合度具体地涵盖着“经典诠释和经典原意的契合度”与“经典诠释和当代现实的相关度”两个层次,前者属于事实性的考量,后者属于价值性的考量。a彭启福:《“视域融合度”: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论”批判》,《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经典诠释融合度的标准,不是私人化的标准,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内部共享的,或者说,它是一种可公度性的客观标准。
从经典诠释的主观性方面看,主要体现在诠释者的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对诠释过程的影响。经典诠释乃是经典诠释者对经典所做的理解和诠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诠释者主观因素的影响,打上诠释者的主观烙印。众所周知,每一种固化的、单一的经典,总是在历史的流程中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多元的经典诠释。与西方圣经诠释学相映衬,中国传统经学致力于“经传注疏”,原本屈指可数的“五经”(六经)繁衍出浩如烟海的经学典籍,经典诠释者主观性的印痕非常明显。可以说,没有诠释者主观性的发挥,难以理解的“经典”也无法转化为普通理解者易于接受的“经典诠释”。圣经诠释学中强调基督教信仰对圣经理解的主导性地位,施莱尔马赫一般诠释学注重“心理移情”在把握作者原意中的重要作用,伽达默尔肯定“先入之见”在理解过程中的合法性意义,都可以看做是对理解和诠释过程中主观性的张扬。有趣的是,晚年伽达默尔在与其研究助手卡斯滕·杜特(Carsten Dutt)的交谈中甚至强调:“不是他们对方法的掌握,而是他们的诠释学想象(their hermeneutical imaginatiοn)才是真正富于创造性的学者之标志。”bPalmer,Gadamer in Conversation: Ref l ections and Commenta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Lοndοn, p.42.动机、兴趣、情感、信仰、想象等诸多非理性因素和理论、知识等各种理性因素一起,参与到经典的理解和诠释过程中,给经典诠释刻写上主观性的烙印。
显然,经典诠释既离不开客观性的制约,也离不开主观性的参与,片面强调主观性或者客观性,都是欠妥的。经典诠释本身就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辩证统一。
三、经典诠释的主要任务
如前所述,经典诠释乃是“历史”与“现实”、“经典作者”与“普通理解者”之间的双重中介,并且它还将私人性和公共性、自主性和限制性、主观性和客观性集于一身,呈现出其辩证的本性,那么,经典诠释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
经典诠释,本质上是诠释者对经典所做的诠释,它不同于一般作者的自由表达。基于经典,超越经典,是经典诠释的基本要求。在笔者看来,经典诠释主要有两大任务:第一是“凝识”;第二是“启智”。如果说“凝识”乃是经典诠释的基础性任务的话,那么“启智”则是经典诠释的实践性任务。“凝识”旨在“通古”,“启智”重在“达今”;“凝识”旨在传承,“启智”重在创新。“凝识”和“启智”二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起到“历史”与“现实”、“经典作者”与“普通理解者”之间双重中介的作用。
作为经典诠释基础性任务的“凝识”,可以从两个层面去把握。其一,在经典诠释中,凝练对经典中蕴含的文本含义和作者原意的认识,为求简便,亦可以称之为凝练“文本之识”。传统的方法论诠释学家常常预设文本含义(the meaning οf a text)与其作者原意(the authοr’s οriginal intentiοn)之间的天然一致性,认为文本总是能够准确地表达作者所欲表达的生活体验,但“拙于表达”和“词不达意”这类现象的存在向我们表明文本含义与其作者原意之间的间离性甚至冲突性是可能发生的。语言体系的公共性和语言使用的私人性是造成这种间离性和冲突性的语言学根源。因此,经典固然是通过作者原意的必由之路,但经典中蕴含的文本含义却不能直接与作者原意等同。在凝练“文本之识”的过程中,需要辨析文本含义与作者原意之间可能存在的间离性与冲突性,使得经典诠释尽可能地逼近经典作者的原意,提升经典诠释与经典原意之间的契合度。当施莱尔马赫主张“与讲话的作者一样好甚至比他更好地理解他的话语”a[德]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演(1819—1832)》,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61页。时,其言下之意是指理解者和诠释者有可能对作者无意识保存的许多东西进行意识,即是说,诠释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诠释有可能深入作者自身都没有意识到的无意识的层面。这也表明,施莱尔马赫虽然认同文本含义与作者原意的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但却也意识到这种一致性并不总是直接的、显性呈现的。其二,在经典诠释中,凝练诠释者自身的对于过往事物及其本质和规律的一般性认识,为求简便,亦可以称之为凝练“事理之识”。任何经典,都代表着经典作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其拥有的生活体验的符号化表达,它既是某种认知成果、思想精华,又是历史性产物,不可避免地有着历史局限性。每一部经典作为经典作者创作的个别作品,本身就是经典作者某些个性化生活体验的结晶,是经典作者个性化生活体验的集中表达。而且,这种个性化生活体验和体验表达,又总是通过单词、单句、单个段落及其内在关联组合成一个整体性文本。因此,从经典的文辞通达文辞所指向的事理,经典诠释者必须经历双重的凝识过程,既要凝练“文本之识”,也要凝练“事理之识”。而“个别—一般”和“部分—整体”之间的多种诠释学循环,渗透到经典诠释者凝练“文本之识”和“事理之识”的整个过程之中。一般诠释学的先驱者弗里德里希·阿斯特(Ast)曾经指出:“理解包括两个要素:领悟个别和综合个别成一个总体知觉、感觉或观念整体,也就是说,分解其元素或特征和结合被分解部分成概念感知统一体。因此解释也建立在特殊或个别的发展和综合特殊成一统一体的基础之上。所以理解和解释就是认识(cοgnitiοn)和领悟(cοmprehensiοn)。”b[德]阿斯特:《诠释学(1808)》,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9页。狄尔泰在谈到诠释植根于其中的理解时,也认为一切理解的高级形式的“共同特征就是从表现出发,通过一种归纳推理,理解一种整体关系。”c[德]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第101页。当然,凝练“事理之识”不能滞留于经典。经典诠释要凝练出“事理之识”,既要入乎经典之内,又要出乎经典之外。所谓“出乎经典之外”,具体有两个方面含义:一方面,在对某部经典进行诠释时,不能局限在该部经典范围之内,应该在该经典作者的“文本链”以及其他作者的“文本群”的比较中展开思考;另一方面,在对某部经典进行诠释时,也不能局限在任何经典或其他文本的范围内,而应该深入文本背后去探究文本与事理之间的真实联系,努力达成对事理的真知灼见。在这里,经典诠释已经开显了“批评”的维度,力图超越“文本之识”的局限,澄明诠释者自身对文本和事理关系的见解,提升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
那么,作为经典诠释实践性任务的“启智”,又该如何看待呢?所谓“启智”,顾名思义,就是要“启迪智慧”。这里所言的“智慧”,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所追寻的那种求知性的“理论智慧”(Theοretical wisdοm),即philοsοphia(爱智慧)中的那个sοphia,而是在人的交互性实践(包括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等)中呈现出来的“实践智慧”,即phrοnesis(又译为“实践理性”或“明智”)。
伽达默尔倡导一种“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d[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77页。其中重要的意图就是要澄明人的理解和诠释过程应该是一种充满实践智慧的过程,惟其如此,理解和诠释才能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与理论哲学关注一般性和普遍性知识的获得不同,实践哲学关注的是永恒变化的生活境况,以及如何把这种一般性和普遍性知识反复应用于具体的生活境况之中,做出妥当的行为选择。从普遍性知识出发,探明生活境况的多样性和变易性,基于“善”的追求做出妥当的行为选择,这本身也正是“实践智慧”的特点。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科学就是对普遍者和出于必然的事物的把握”,指向的是事物的恒常性、重复性、规律性;而实践智慧则“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应该通晓个别事物。”实践智慧“显然并不是科学……它们是以个别事物为最后对象,只有个别事物才是行为的对象。”a[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6、127页。伽达默尔将“实践智慧”引入理解和诠释问题的思考中,是与他对理解的独特见解有关的。他在《真理与方法》中分析说:“如果诠释学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同一个传承物必定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被理解,那么,从逻辑上看,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普遍东西和特殊东西的关系问题。因此,理解乃是把某种普遍东西应用于某个个别具体情况的特殊事例。”b[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修订译本),第423页。伽达默尔强调理解的应用性(understanding by applicatiοn),因为只有将文本应用到具体的诠释学情境之中,才能开启文本的有针对性的意义。
经典诠释同样面临伽达默尔所言的“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凝练“文本之识”是经典诠释者去把握经典作者所把握到的普遍知识,凝练“事理之识”是经典诠释者借助于文本去把握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普遍知识,那么,“启智”则是要将经典诠释者把握到的“文本之识”和“事理之识”这类普遍性知识应用于某些个别具体情况的特殊情境,启发普通理解者的“实践智慧”,促成普通理解者对经典的创造性理解,增进人类福祉。
经典诠释要完成“启智”的任务,经典诠释者必须很好地扮演双重中介者的角色,妥善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经典作者”与“普通理解者”之间居间调停,也可以说,必须解决好经典诠释中“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潘德荣教授主张的“德行诠释学”,是一种“着力于作为经典的文本理解,以‘立德’为宗旨的经典诠释学”,c潘德荣:《经典诠释与“立德”》,《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它将诠释学的任务定位为“立德弘道之学”,主张“所有的诠释活动都以‘德行’为核心展开”。d潘德荣:《论当代诠释学的任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可以说,“德行诠释学”将诠释的视域从传统意义上的“真”(发掘“本义”)拓展到“善”(旨在“立德”),凸显了经典诠释过程中的价值导向,颇有见地。但“立德”离不开“凝识”;“立德”也内蕴于“启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实践智慧”是以“最高的善”即“灵魂的善”为内在目的的,它不仅要求好的品质,更要求好的行为,因此,“启智”与“立德”是一致的。之所以强调“启智”,主要是想指明经典诠释固然是诠释者做出的“目的性”和“选择性”诠释,但它并非是一种强制性的、填鸭式的诠释;经典诠释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普遍性知识(“文本之识”和“事理之识”)与“普通理解者”的个别具体情境之考量而做出的诠释,旨在启发经典的当代理解者追寻“实践智慧”。这种经典诠释,应该源于经典、基于经典,但又不限于经典,真正地面向普通理解者的当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