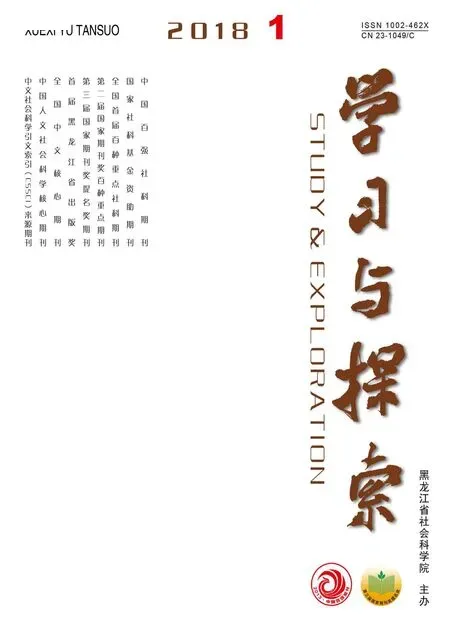制度性羞辱及其克服
姚 尚 建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政治制度的逻辑直接影响着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社会变革与治理转型时期,在正向激励与负向制裁并行不悖的制度设计中,羞辱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在于众多混合型治理工具仍然在诸多领域发挥着极其复杂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制度转型与社会预期的巨大张力。
一、制度性羞辱及其边界
在《体面社会》中,阿维沙伊·马加利特区分了体面社会与文明社会:“一个体面社会就是一个其社会组织不羞辱人民的社会。我不认为体面社会与文明社会相同。文明社会是一种成员之间互相不羞辱的社会,而体面社会则是一种社会组织不羞辱人民的社会。”[1]引言在组织对于民众的羞辱中,马加利特认为,组织的羞辱分为法律的羞辱和运行方式的羞辱两种。马加利特的判断从横切面上剖析了羞辱的一般性情况,也为社会羞辱的形成与运作提供了批判的切入口。
首先,羞耻感知的制度设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羞耻不能算是一种德性。因为,它似乎是一种感情而不是一种品质。至少是,它一般被定义为对耻辱的恐惧。它实际上类似于对危险的恐惧。因为,人们在感到耻辱时就脸红,在感到恐惧时就脸色苍白。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为身体的某些变化。这种身体上的变化似乎是感情的特点,而不是品质的特点。”[2]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羞耻感乃是基于善的警示,一个拥有德性的人是不会去做坏事的,只有当一个人做了坏事并感到羞耻的时候,才能说这个人是存在德性的。
虽然羞耻感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情绪感知,但是在制度层面,羞耻感往往被建构在制度之中。在东西方的政治传统中,法律或诸多制度本身就隐藏了个体性的人格羞辱的内容。在专制国家的权力结构中,纵向授权无法克服上级对下级的高度不信任,也无法消除下级政府对于民众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往往通过制度设计来加以体现,于是,制度性羞辱应运而生。中国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在已有的郡县之上,又分州设立刺史监察郡县,这种制度设计既明示了权力的归属,也告知官员最高统治者对于各级官僚的怀疑;更为严重的是,在专制体系中,进入官职体系本身就意味着羞辱的发生。《吕氏春秋》曾有以下的记载:“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黄,踞于堂而与之言。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故贤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实者其礼之。”[3]在魏文侯看来,既然已经赋予了官员职位和俸禄,再要求得到尊重似乎是过分的欲求。
托马斯·潘恩深刻地揭露了在集权主义的政治体系中,君主与朝臣的关系“不管表象如何,任何哪类人都不像朝臣那样地蔑视君主。不过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其他人都看得像他们那样清楚,把戏就玩不下去了。他们所处的是一种靠作秀为生的境地,他们对作秀的愚蠢了解得如此透彻,自己也觉得可笑;但如果让使观众跟他们一样明白,那么作秀就作不下去了,红利也没了。共和主义者与朝臣对君主的差别在于:前者反对君主,认为它不容小觑;后者取笑君主,知道它不名一文。”[4]
这些进入集权官职体系中“自取其辱”的、长于“作秀”的官员承担了政治制度的设计者与运行者的功能。在维系政治统治的制度设计与运行中,激励未必带来尊严,但惩罚往往伴随着羞辱。在人类社会很长时期的刑罚设计中,示众通常是重要的一个环节,直到今天,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公开逮捕、公开宣判、公开认罪甚至公开处决等现象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当然,羞辱的历史伴随着人类的社会活动而发展,其本身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历史学家常说的‘事实明摆在那里供人使用’的假定无疑是错误的。实际上事实并不是像卵石那样,单纯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而分离出来,经过冲刷磨损而成型,最终积存在那里,等待着历史学家拾起来使用。历史学家也不是在过去中散步时发现沿路存留的事实。事实就像是经过打磨的燧石或烧制的砖。人的活动对事实的形成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果没有人的活动,事实就不会有人们看到的样子。”[5]但是在人类对于羞辱性制度的设计中,往往伴随着特定的时代内容。在传统的羞辱性制度设计中,羞辱者往往以道德或法律的名义对被损害者进行公开羞辱:在道德的高地上,无论是宗教裁判所,还是世俗法院,那些违背国家秩序的个体往往被视为异类;在法律的高地上,法律作为惩戒的手段超越了规范与教育的功能。
其次,制度性羞辱的道德惯性。“无政府主义认为,一切管制组织包括个人的代议制民主都羞辱人,因为它们把主权从个人手中夺走,集中到代表他们的代表人手中。”[1]13诚然,在政治运行过程中,任何秩序优先的制度安排都会涉及个人自由的侵犯,但是制度性羞辱不仅仅体现在国家层面,在社会治理的进程中,这种羞辱的存在往往意味着一种社会性秩序的正当性。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从社会涉及的个体来看,由于政治过程往往是制度的运作过程,为了维持政治秩序,公共政策既体现为正向的激励作用,也可能体现为负向的惩戒。在政治转型的进程中,制度性羞辱日益表现为普遍性安全感的丧失。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的第一章,福柯记载了1757年3月2日谋刺国王而“在巴黎教堂大门前公开认罪”的达米安被残酷处死的过程[6]3-6。David Nash和Anne-Marie Kilday通过对1600—1900年间的犯罪与道德观进行分析,认为以往的对于羞耻的研究忽略了情感和行为方面的历史,在诸如示众等惩罚性手段上,羞耻的使用有一个明显的报复性功能。在今天,许多观点认为,羞耻感是一种野蛮的、原始的社会控制的工具[7]。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公开认罪在法国于1791年和1830年被两次废除,法国、英国的示众刑柱先后在1789年和1837年被废除[6]8,此后,欧洲国家普遍建立了现代法律制度。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转型往往并不同步,在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的世俗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但是,在历史上,让违反秩序的人在公众前自证其罪、接受舆论审判等羞辱性措施,在广场狂欢的背后,同时蕴含着政治社会化的内容。无论宗教政治还是世俗政治,制度设计的背后是一个公众的接受程度。一个逐步开放的社会有可能日益拒绝剥夺女性接受世俗教育或自由恋爱的制度,但是在一些特定社区或族群,女性接受世俗教育或自由恋爱仍然是不可接受的,违背这样制度的女性个体有可能付出人格甚至生命的代价。
第三,制度性羞辱的行为边界。在国家统治的单边思维中,政策工具无疑建立在单边权力结构之上,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中,国家拥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上,马加利特指出组织可能形成社会羞辱。但是正如前文David Nash和Anne-Marie Kilday所分析的那样,形成羞辱的文化内容除了组织,还包括心理和行为。因此,当组织、行为和心理都不再明示或暗示羞辱的发生时,制度性的羞辱就到了行使的边界。
从组织层面上看,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判断否认了政府的合法性,但是当政府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恶”时,政府往往通过更加具有弹性的、扁平化的政府形式来减少“恶意”,促进政府与社会的互通。在中国的近期司法制度改革中,强制遣送、劳动教养等制度相继撤销,这些制度的执行机关也开始转向流浪救助、社会纠正等新功能的履行,这一功能的变更否定了在流浪人员和轻微违法人员管理上的“有罪假设”,撕掉了贴在类似人员身上的羞辱性标签,消弭了政府与特定群体的隔阂。
从行为层面上看,普遍性制度性羞辱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差异性对待。人类社会的历史往往存在着等级和阶级的差异,公共政策的施行也多建立在这样的差异之上。以中国长期施行的户籍制度为例,20世纪50年代以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开始实施,并逐渐成为中国众多物资分配、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的基础。户籍制度往往意味着福利、机会的差别,一些超大城市的户籍尤其难以获得。有些城市在控制人口的政策导向下,将一些与城市功能“不符”的低端农贸市场、小商品批发市场进行清理,一些人群的“居住证”到期后无法续签而被迫离开城市。户籍制度撕裂了社会,也分割了社会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合力。
从心理上看,惩罚性手段将日益剥离羞辱的内容,惩罚与纠错、教育日益相连,从而消弭从形式到内容上的、以惩罚为目的的管理措施;而对于丧失自由的个体来说,自由的限制并不比财产的剥夺更具有羞辱意义,但是随着人们对自由的尊崇,对自由的侵犯日益激起人们的不满甚至反抗。行为罚如此,声誉罚亦然,当人们深刻感知到公共政策的羞辱时,类似的公共政策实施就日益困难。
二、制度性羞辱的逻辑批判
制度性羞辱的存续既蕴含着传统治理的历史性记忆,也可能体现了社会转型中的工具性不足。西方政治学关于善与权利关系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从制度设计上看,“光荣革命”以后,现代政府制度建基于权利之上,从而为法治拓宽了道路。
首先,权力的傲慢与德性的侵蚀。“凌辱的种类很多,但所有各式各样的凌辱所造成的结果则同样是受辱者的忿怒。凡是在忿怒狂热的时候直接冒犯君主的人们一般都不是有什么野心,而只是怀有私恨,志在复仇而已。”[8]281羞辱往往导致反抗,从而导致德性的侵蚀。在《政治学》第五章中,亚里士多德论述了不同政体为何走向失败:平民政体的政变起因于群众领袖的放肆;寡头政体的失败源自执政者对平民的虐待和执政团体的自相倾轧;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颠覆则由于它们偏离了建国的正义[8]248-264。从这些失败的政体中不难看出,仅仅由于失去尊严有可能成为导致城邦失败的一种原因。因此,把权力建立在道德羞辱之上的城邦存在着失败的风险。
按照韦伯的分类,传统的政治体系建立在君权神授的天命之上,这种神秘主义的权力来源在中世纪以后已经无法让人信服。在当代,在支持国家扩大范围的人那里,国家已经被剥离了神秘主义的色彩,“人们常把国家占有或国家控制当作是补救所有因私人竞争而带来的弊病(诸如贪婪、权力欲、毫无限制的个人主义或更准确地说是自私)的良方。国家被认为是代表正义和道德进步的机构。国家应当倡导谦卑,抑制自负”[9]217-218。但是同时需要看到,虽然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抽象的存在,现代国家日益成为一个组织化的官僚集团,传统国家基于权力私有的君主的随意性支配权已经衰落,但是国家的运行仍然建立在官僚集团的政策制定之上。在制度的制定中,那种无法遏制的权力的傲慢仍然比比皆是,例如限购房屋、限制落户等公共政策的实施就在一些大城市迫使很多夫妻蒙受“假离婚”“假结婚”的羞辱,这类政策的出台本意试图扩大购房的道德成本,但是却在客观上导致了一些家庭的瓦解,既损害了公序良俗,也损害了国家正义。
除了政策制定,官僚化的政府体系也原则性地规定了官员的行为内容和行为程序,也授予了后者一定范围的自由裁量权,因为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官员和职员组成的。“可以肯定,他们都相当优秀,然而无论他们如何具有责任感,如何尽忠职守、爱岗敬业,他们都是凡人,有凡人的优点,也有凡人弱点……他们也会变得自负、怠惰、贪婪、浮华。他们也会有爱憎、敌友,有激情和利益,其中之一就是保住自己的位子,甚或不失时机求得升迁。”[9]218当政府行为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行为之上,公职人员的主观认知就可能延续传统国家权力的人格化特征,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注入个人情绪化的判断,从而扭曲中立理性的政府行为。
其次,权利的丧失与抵抗的乏力。公民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内容,在阿维沙伊·马加利特看来,人权并不仅仅等于公民权利,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照样可以通过侵犯公民权利以达到羞辱的目的。“例如投票权。不给予妇女以投票权(瑞士前几年仍属这种情况)是一种与体面社会不相称的行为。不给予妇女以投票权意味着把妇女当作未成年人对待,也就是当作一个不完全的人对待。”[1]30
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个人主义的崛起,这种个人主义以个体权利的名义要求国家必须遵循平等、对话与捍卫自由的原则,从而成功地遏制了封建主义的国家扩张。在现代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个体的权利日益具有丰富的内容,对社会的宽容、对个体的关怀既合乎道德,也符合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惩罚是体面社会的试金石……每个人,即使是罪犯也都应受到人应当得到的尊重,因为他是人。对人的尊严的伤害就是羞辱,因此即使罪犯也应享有不被羞辱的权利。体面社会必须不为罪犯提供认为自己尊严被践踏的充足理由,即便对他们的惩罚给他们以充足的理由认为其社会荣誉被损害。”[1]193在19世纪以后,西方国家不再对罪犯进行示众,这些变化既与罪犯的权利捍卫有关,也与社会对这一“令人作呕”的制度的尖锐批评有关。
在今天,权利已经与公民身份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日益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人们在追求权利的同时形成了联盟,与专制政治进行一致性对抗。巴黎示众柱在今天看来已经无法接受,因为这一刑罚本身不仅无法震慑个体,还拷问着社会的共同权利意识;而在权利结盟之后,权力的行使就可能日益退缩,并形成碎片化的治理模式。
最后,制度的反噬与管理的退化。在威权主义的政治体系中,权力的行使无视个体的尊严,更无视个体的权利主张。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种羞辱性的制度日益遭遇强烈的抵抗。从形式上看,亚里士多德就指出早已存在的一种个体的复仇现象:“许多人以受到体罚为凌辱;身被鞭笞的人们以不胜羞耻的心理,激发起一时的恼怒,便勇往直前地进行阻击,或竟然杀死了课罚他们的王室官吏,甚至把剑锋加于王族。”[8]284从工具上看,痴迷于羞辱性制度不但难以形成对被统治者的震慑,“请君入瓮”式的制度反噬可能形成制度自身的羞辱,从而加剧了制度合法性的丧失。
从治理手段上看,羞辱性制度的存续显示了国家对于传统治理工具的文化记忆,也显示了新兴治理工具的匮乏。应该指出的是,羞辱性制度如示众在很多场合仍然作为一种深层次制度不时浮现出来,这一现象的反复出现显示了管理者对于传统工具的高度依赖,也反映了治理手段不足的现实焦虑。这种焦虑排斥了其他治理力量的介入,因此也排斥了羞辱从制度中抽离的渠道,从而导致治理工具的功能性退化。
在世界范围内,国家都可能遭遇失败,帕特里克·邓利维和布伦登·奥利里认为,现代国家的政治危机存在三种可能性:国家解体、长时期的政治困难和非最佳的表现、能够被解决的短暂政治问题。除此以外,在一些自由民主国家中潜在的危机还来源于政府超载、不适当的政治问责制和对社会发展的控制[10]。而对于传统国家而言,虽然表现形式各有差异,但是相关困境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同时,由于传统国家仍然处于治理转型之中,一个转型的政治体系应该意识到,治理工具的功能性退化还可能导致政治体的结构性退化。为了克服这种退化,一些试错性的公共政策与治理工具一定会大量出现,但这种错误本身未必能够导致政治停滞,一个封闭的治理工具系统才有可能加深国家转型的困难,而羞辱性制度只是其中一个表现而已。
三、制度性羞辱的克服
正如马加利特所强调的那样,一个充满羞辱的社会是不正义的,在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转型中,我们无法充分排除制度史的重演,但是这种重演是工具意义上的还是价值意义上的却值得推究。从个体自由、社会宽容、权力公有、权利私有的角度出发,一个包含不断排斥羞辱的法治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具有现代国家和社会的逻辑起点。
首先,荣誉的感知和权利的赋予。无论人类社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合乎德性的治理可能长期不会被排斥在选项之外。充满羞辱的制度为什么能够存在?在黑格尔看来,同样的体罚,在东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心理印记:“各种刑罚通常是对肉体的鞭笞。对于我们,这简直是加在荣誉上的一种侮辱;在中国就不同了,荣誉感还没有发达。一顿笞打原是极易忘怀的,但是对于有荣誉感的人,这是最严厉的刑罚”[11]128。在欧洲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中,效忠与契约支持了荣誉感知,而在效忠之前,人是作为自由的个体的存在。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羞辱必须建立在感知之上,当个体的羞耻感从肉体的裸露到荣誉的捍卫时,就是个体追求更大生存空间的政治起点。
“光荣革命”对于欧洲社会来说不仅仅是废除了示众柱,更是确定了分权之后的公民权利,而权利对于权力的制约形成现代宪法的逻辑起点。黑格尔曾经这样论述中国传统政治:“我们不能够说中国有一部宪法:因为假如有宪法,那么,各个人和各个团体将有独立的权利——一部分关于他们的特殊利益,一部分关于整个国家。但是这里并没有这一种因素,所以我们只能谈谈中国的行政。在中国,实际上人人是绝对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连带发生,任何人都能够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在我们西方,大家只有在法律之前和在对于私产的相互尊重上,才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同时又有许多利益和特殊权限,因为我们具有我们所谓自由,所以这些权益都得到保障。”[11]125
其次,法治工具对于权力人格化的规范。“自由与权力的关系是公法的基础性问题,东方人治的公法是以权力为中心展开的,它关注的是权力的宣示与权力的贯彻,它以限制自由为核心价值;现代西方的公法则以自由为核心价值,它关注的是如何控制权力,它的源头是西方源远流长的个人权利思想和法治思想。”[12]74其实在东西公法价值差异的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与东方人治相适应的是基于义务本位的社会结构;而西方法治为核心的是基于权利为本位的社会结构。在共和制度建立之后,基于义务的东方社会结构日益失去其合法性,学界基本认为,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法律则是平衡不同权利的重要手段。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在现代法律面前,国家基于人民授权而存在;国家与个体是并重的,因此人民的概念并不抽象,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组成的。因此,对于任何个体的尊重就是基于对于人民整体的尊重。
在自由民主主义政治学看来,政治发展既包括权力的民主获得,也包括权力的民主行使。在民主制度下,选举既是一个国家政治体系产生的路径,也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利器。在选举之下,强制性的对选举结果的服从,回避了社会抗争的暴力化趋势,也规范了人格化的国家权力。法治成为测量政治发展的尺度,这种测量既体现为社会结构的法治化,也体现为国家治理的实体与程序的双重控制。
从社会层面上看,羞辱未必只发生在国家对于社会个体的权力滥用上,也可能体现为一切有权者的权力滥用。在一些地区,民间法仍然支持了如同国家行为式的羞辱;但是在公法理论看来,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并不具备平等的内容,任何民间治理及其民间法必须建立在统一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内容之上。当然,马加利特担心,如果人们无法表达内心的厌恶,是否可能形成虚伪的、表面上尊重的社会。这样的问题并不难以回答,法治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国家的惩罚排除了民间对于个体犯罪的同态复仇,社会参与治理并不意味着任何社会组织能够取代惩戒中的国家角色,行为罚如此,名誉罚亦然。
最后,政治发展的文化支持。制度性羞辱的背后是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是主流政治制度与主流政治文化的分离。“文化中羞辱人的表象问题与社会中的主流文化沉浮相伴,因为只有主流文化才有能力从社会整体上接收和排斥人。”[1]127中世纪以后,自由平等的观念在西方国家深入人心,而在东方中国,秦汉以来的集权政治使国家捆绑了社会,国家的主流文化取代了社会的文化自治。在国家层面,严格政治等级的存在削弱了社会的包容和平等,并主导了社会文化。而当市民社会兴起以后,社会成为国家政治过程的最终的制约方,国家的衰落就不仅仅停留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层面的认知上,而有着更加深刻的结构反抗的内容。
既然政治发展意味着权力滥用的遏制,意味着政治理性的建立,那么权力的分置就是国家层面上的制度选择。传统的政治中,国家是君主的私有物,官员是君主的家臣,即使通过法律的形式,政治统治仍然表现为人身的依附与个体的统治:“此时,立法者是单个自然人,立法也是一个个人独断(颁布诏书)的行为,而没有‘议’的组织与程序。”[12]174如果说议会的形成是中世纪中期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其主要意义一定在于社会分享了国家权力,明确了国家权力的社会来源,实现了权力的公共控制,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通过公共讨论实现了互构:一个理性的、非羞辱的国家政治制度既是政治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诉求。
结 语
羞辱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和惩戒形式,在很长时期内都标志着国家权力的滥用与公民权利的丧失。在国家与社会双重转型的时期,权利逐渐得到了拓展,羞辱性的制度逐渐从政治统治的核心内容转变为政治管理的外在形式,并日益成为一种政治学的批判对象。羞辱重新回归德性、回归社会内在价值,不再体现为肉体或名誉上的虐待,而体现为个体对于违法遭受惩戒的羞愧与自省,从而内在地弥补了刚性法律的不足,并与抽离了羞辱的政治制度共同论证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建立在由自由主义自由和社会共有权利所创建的社会存在基础上的私人自治,在现代社会中形成了个人自由的一种特殊类型:个人对外享有国家保障的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权利,因而保证了他免受国家或其他的活动者侵犯的权利;而同时在个人的内部却展开了一个对他人生目标进行纯粹的自我反省。”[13]
[1] 阿维沙伊·马加利特:《体面社会》,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4页。
[3] 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上),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87页。
[4] 托马斯·潘恩:《人的权利》,戴炳然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8-59页。
[5]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
[6]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7] David Nash and Anne-Marie Kilday,CulturesofShame:ExploringCrimeandMoralityinBritain1600-190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174-175.
[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9] 加埃塔诺·莫斯卡:《政治科学要义》,任军锋、宋国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 帕特里克·邓利维、布伦登·奥利里:《国家理论:自由民主的政治学》,欧阳景根、尹冬华、孙云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11]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12] 周永坤:《宪政与权力》,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3] 阿克塞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