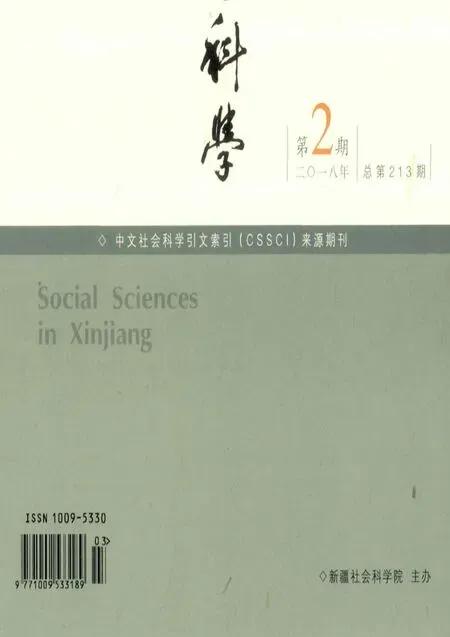文化空间视阈下宗祠的美学意蕴*
徐俊六
一、问题的提出
宗祠即宗族祠堂,在中国社会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如,先秦时期的宗庙、汉魏时期的墓祠、隋唐时期的家庙、宋元时期的家祠、明清时期的祠堂等。宗祠的研究具有人类学、文化学、艺术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意义与价值。国内的宗祠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是1929年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其中较多内容涉及宗祠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宗祠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国内以林耀华为代表,他认为家族研究应从祠堂入手,因为家族的祠堂,原为家族的宗教机关,家族渐渐发展到宗族,祠堂也渐渐扩张为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的机关。国外以科大卫与莫里斯·弗里德曼为代表,他们以中国华南地区的汉族村落为调查对象,对中国传统宗族制度与社会关系进行深入调查、分析与研究,著作丰沛。这些著作虽未冠名为宗祠研究,但在其研究中广泛而深刻地论述了中国宗法制度下的各种宗祠,这为后世的宗祠研究提供了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视野,对宗祠的现代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纵观当下的宗祠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宗祠宏观理论与历史梳理的研究以及对宗祠建筑相对集中的区域性研究,在这些成果中宗祠研究的学科属性模糊不清且缺乏清晰的研究视角,这对宗祠的深入研究与整体性研究带来一定障碍。我国的宗祠少量分布于都市社区,而大多数分布于乡土民间, 有一村一祠、一村多祠与多地共祠等格局,无论是独祠还是群祠均在一定的空间内。宗祠周边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构筑宗祠的外部空间,其建筑内部的宗族历史与家族传统构建宗祠的内部空间;宗祠文化的传播在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展开,共同建构宗祠的文化空间,文化空间成为研究宗祠与宗祠文化的新视角。在文化空间视阈下,宗祠被置放在一个宏大的文化环境中考察,采用整体观与统一观的方式对其观照、运用审美主客体原理与美育理念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为宗祠研究提供新的维度、开辟新的路径。
二、文化空间中的宗祠与宗祠的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学术语最早出自20世纪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他提出包括文化空间在内的“社会空间”理论,空间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集知识、权利与符号的能指系统,是一种空间再生产理论。文化空间为国内学术界所熟知源于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其中明确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另一类是文化空间。此后,文化空间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形态出现。我国于2005年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以下简称《意见》),其中这样解释文化空间,“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随后,文化空间形态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乌丙安认为:“凡是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古老习惯确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场所举行传统的大型综合性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形式。……遍布在我国各地各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 、集市(巴扎),等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他对何谓文化空间给出了一个十分明晰的概念,且列举了相关的非遗事项,是中文语境下较早的文化空间定义。高丙中认为:“文化空间是体现意义、价值的场所、场景、景观,由场所与意义符号、价值载体共同构成。有核心象征的文化空间区别于一般的文化空间,它具有集中体现价值的符号,并被成员所认知,是共同体的集体意识的基础。”*关昕:《“文化空间:节日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7年第2期。向云驹认为:“文化空间从其自然属性而言,必须是一个独在的文化场, 即具有一定的物理、地理空间或场所,文化空间从其文化属性看,则往往具有综合性、多样性、岁时性、周期性、季节性、神圣性、族群性、娱乐性等。”*向云驹:《论“文化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陈虹认为:“‘文化空间’是一个源自人类学的概念,既不是单纯的文化与空间的组合体,也不是某种固定的文化或艺术表现形式,而是文化+时+空一体化中的某些濒危文化传统。”*陈虹:《试谈文化空间的概念与内涵》,《文物世界》2006年第1期。在最近对文化空间的研究中,陈桂波在阐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文化空间指的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周期性出现的、多种相互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空间,其特征是综合性、周期性与整体性”*陈桂波:《非遗视野下文化空间理论研究刍议》,《文化遗产》2016年第4期。。
综上所述,文化空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空间是文化性、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统一,包括现实的传统文化举办的各种场所,也包括文化传统在传播中营造的各种非现实的空间范畴,从遗产类型上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狭义的文化空间特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范畴,且是在同一区域内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的共同体,整体性与区域性是其显著特征。
从宗祠建筑与其他实物来看,宗祠是古代社会遗留的产物,具有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从宗祠文化及其传播看,宗祠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因此,宗祠是文化空间的一种类型。文化空间中的宗祠是指宗祠建筑与宗祠文化处于一定的时空格局中,宗祠建筑与宗祠文化归属文化空间类型,文化空间统属宗祠。具体地讲,我国南方社区与北方社区地理空间中的宗祠呈现不同的特点:北方地区由于朝代更迭频繁与战事多发,人口大量迁移至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相对北方战事较少,加上自然地理与气候条件适宜,迁徙的人群逐渐定居于南方各区域,他们通常是同姓聚落而居,形成大大小小的同族村落,在这些村落中分布着各姓氏宗祠。统观我国现存宗祠的分布格局,在数量上南方多于北方,且主要集中在华南、中南等地,以广东、福建、江西、安徽、江苏、湖南为最多;在风格上南方与北方各有特色,宗祠的区域性特征比较鲜明,有些宗祠兼具中原文化、本土文化与民族文化特色。宗祠的文化空间是宗祠社会影响的一种指称,既包含宗祠的建筑风格与艺术内旨,也包含宗祠祭祀礼仪的文化传统、家族信仰、家风家训与社会功能等,宗祠的文化空间突出的是宗祠文化的核心功能。在宗祠集中的区域,宗祠的文化空间属性更为凸显,如广东肇庆与番禺宗祠群、福建漳州云霄宗祠群、江西婺源汪口宗祠群、安徽绩溪宗祠群、江苏无锡惠山宗祠群、湖南汝城与邵阳洞口宗祠群、云南腾冲宗祠群等。
文化空间中的宗祠与宗祠的文化空间是研究宗祠文化空间的两个维度,前者是宗祠所处的地理环境空间,后者是宗祠文化的传播空间,两个维度的结合是宗祠整体性研究的需要。
三、文化空间视阈下宗祠的美学意蕴
明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上《请定功臣配享及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伏望皇上推恩因心之孝,诏令天下臣民,许如程子所言,冬至祭厥初生民之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桂洲夏文愍公奏议》卷二十一,光绪十七年江西书局刻本。明世宗采纳其奏议,允许民间建立家庙,从此,宗祠遍天下。明清时期是宗族祠堂最为兴盛的时期,从全国现存宗祠的建筑样式看,大多属于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宗祠建筑是宗祠文化的物质载体,宗祠文化的承传与传播又为宗祠建筑增添无限魅力与意蕴。
(一)宗祠凸显中国古典建筑的形式美
宗祠是中国古典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礼祭是其核心作用。宗祠祭祖祀神的功用是其建筑区别于其他建筑的内在原因,宗祠内供奉家族先祖圣贤或神祇,因此,宗祠总体格局显得庄严肃穆,而在严整的建筑结构中又显示出中国古典建筑的美,主要体现在宗祠的形制、风格、选址、用材、传统元素等方面。
在《礼记·王制》中有“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王云五主编:《礼记今注今译》,王梦鸥,注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55~456页。。这是文献中关于宗祠建筑规制的最早记载,从于周制。宗祠建筑的建造虽有了宏观的规定,但并无建造的法式。到了南宋时期,朱熹在《家礼》中绘制了标准的祠堂建筑图,“君子将营营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复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服、祭器及神厨等室于其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门。……正寝为前堂也。……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为四龛,每龛内置一桌。……神主皆藏椟中,置于桌上,南向。龛外各垂小帘,帘外置香桌于堂中,置香炉香盒于其上。两阶之间,又设香桌亦如之。”*《朱子全书》第7册《家礼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75~876页。由于朱熹理学的社会影响,《家礼》中祠堂的建造规制逐渐成为民间建祠的主要依据,南宋以来、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民间可以在房屋以外的地方建造宗祠,《家礼》依然是宗祠规制的主要参照。纵观当下中国乡土社会现存的宗祠,无论是建造的规模、还是建筑的风格均与《家礼》中规定的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宗祠的一般形制特征与建造风格看,主要有中国古典园林式、中国古典家居四合院式与中西合璧式三种,其中又以前两种为主;现存的宗祠大多为单体建筑样式,选址考究、一体严整、中轴对称、进阶均匀、层级分明、井壁结合、草木相映、雕花刻画、通幽肃穆,这些特点均是中国古典建筑特征。宗祠的选址较为考究,在文化空间格局中凸显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进而增强宗祠的社会影响力。如,江苏无锡的惠山宗祠群,东临京杭大运河,背靠惠山山脉,又坐落于太湖风景名胜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宗祠建筑格局一般分为三进式,一进为宗祠大门,是整幢建筑的门面,各宗族为了显示在本地的地位、权势与威望,宗祠大门均用优质木材或上等石料建造,大门由单门或三扇门组成,要么飞檐八角琉璃铺筑、要么雕龙画凤镶嵌石砌。一进宗祠大门后,是一个天井院落,种植草木,东西两侧为厢房;二进为宗祠的休息厅或客厅,作为家族成员聚会商议的场所,也是一个天井院落,两侧也为一层或两层厢房;三进是宗祠的正殿,过廊往内即是正殿中最重要的享堂,是供奉祖先神主牌位的地方,家族成员在此祭拜先祖。有的宗祠正殿后留有石寝,是祖先的坟冢之处。这是宗祠一般的建造样式,各地因传统不同建造风格亦不同。
宗祠是乡土社会中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其建筑形式美的展现是中国古代建筑辉煌历史的见证,也体现了古代社会人们的审美情趣,因而有着较高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
(二)宗祠集中展示中国传统装饰的艺术美
宗祠的建筑样式给人以严整、对称、雄伟与肃穆的美感,而在宗祠建筑内部,“祠堂文化蕴涵的审美意识形态主要表征两个方面,一是敬祖,二是旺族,且本质上是借助祠堂这种意象促进族群的发展”*韦祖庆:《祠堂文化审美意识形态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南宋以来,程朱理学盛行,儒学教育在民间社会得到广泛强化,宗族为了弘扬先祖遗风荫庇子孙,一方面,把宗祠营造为家族文化的展示厅或小型博物馆,悬挂家族先人遗像、遗书、遗画、各种牌匾,门柱上书写社会名人撰写的诗词楹联,收藏各种雕刻作品;另一方面,在宗祠内兴办学堂,鼓励家族子弟学文通儒,把家族中有名望的子弟的事迹也陈列其中,以供后人学习与瞻仰。因此,宗祠成为一个文化习得场所,一进宗祠就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就是宗祠内部传统装饰的效果,是中国传统装饰文化艺术美的体现。
考察现存的宗祠,有很多已然成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典型受到保护,很多宗祠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和旅游景点。如广州的陈家祠与昆明的升庵祠。陈家祠又名陈氏书院,坐落于广州市区,是最具岭南建筑艺术特色的宗祠。陈家祠除了建筑富丽堂皇、规模庞大之外,最具文化特色与艺术价值的就是祠内的各种雕刻装饰,从陈家祠外整体观察,最鲜明的就是房梁之上树立的一排石雕,各种动物石雕栩栩如生,为陈家祠增添无限艺术气氛;除了石雕外,还有各种木雕、砖雕与泥塑,雕刻中既有大量纤巧的花草动物纹饰、也有几十米长的巨型泥塑,这些雕刻装饰使陈家祠成为最具岭南特色的雕刻艺术建筑。升庵祠即明正德年间状元杨慎祠,前临滇池,背靠昆明西山,坐落于西山山麓下的高峣村,整幢建筑采用中原佛教传统寺院的建筑样式,各种花草树木遍布于各个角落,常年绿树环绕,十分清幽与宁静;各种石刻、书法、绘画与楹联充盈整个祠内,是滇中文人雅士经常光顾之地。升庵祠经过多次整修、扩展,现与徐霞客纪念馆合建,称“昆明杨升庵徐霞客纪念馆”。升庵祠内楹联数量众多、雕刻类型丰富,如著名的楹联,“议大礼面折廷争情系滇云名士名作千秋在,计遐征山迥路转涉足苍洱奇人奇书万里行”,以杨慎与徐霞客的生平事迹作为祠门联。升庵祠内正殿前柱书写“颠沛一生胸襟照放真名士,精深百著文采风流大状元”;内侧柱书写“夫子之道鸢飞鱼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内两侧书写“当年抗张桂廷争一念不欺名教扶持忠孝重,此地合杨毛祠祀九京可作大招迎送主宾欢”,等等。升庵祠内置有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各种石柱础与石碑,石碑如《碧峣精舍记》《明嘉靖丁酉四月七日成都杨慎书》《重修曹溪寺记》《楚雄府定远县新建儒学记》等,大都为嘉靖三年西蜀杨慎题;祠内还陈列杨慎书写的大量碑刻,为“碑刻荟萃”,如《西麓继周集》《黄太史精华集》《俗言》《晁氏琴趣外集》《滇载记》《滇海曲》《滇南月节词》《玉名诂》《杨升庵夫妇散曲》《温泉诗》《滇候记》《高峣十二景诗》《云南山川记》《杨升庵年谱》等。
宗祠内的装饰以塑造传统文化氛围为目的,以文学类型、雕刻技艺、泥塑手艺与书画作品为基本形式,使宗祠成为一方文化汇集地,也为宗祠文化的传播与家族优良传统的承传搭建了文化空间。宗祠传统装饰的艺术美是其建筑形式美之外的又一大美学特征,充分体现出古人高超的技艺水平与高尚的审美情操,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
(三)宗祠蕴含中国传统祭祀礼俗与道德伦理的社会美
宗祠的社会美即宗祠对社会的美育功能,是指宗祠文化在传承与传播中对社会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主要通过宗祠传统祭祀礼俗与宗祠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内容实现。“祠堂关系重矣,祀先祖于斯,讲家训于斯,明谱牒于斯,会宗族于斯,而行冠告嘉莫不于斯。”*〔明〕骆尧知:《骆族祠堂记》,谭棣华、曹腾诽编:《广东碑刻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4页。这充分说明宗祠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在文化空间视阈下,宗祠的社会美是其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积极发挥其能动作用,可以培养人们对宗祠发展与社会历史关系的认知能力、承传尊祖敬宗的家族教化意义,同时也可以为健全与完善和谐社会治理体系与民间社会治理实践提供经验与路径。
西周时期的宗庙是宗祠的最初形式,宗庙祭祀也成为后来宗祠祭祀的滥觞。商周时期,祭祀是国家与社会的大事,国君继位、军事战争、农业生产等均需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以告慰天地神灵、祖先,所以《春秋》中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秋左传集解·成公十三年》,李梦生,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68页。。祭祀礼仪与规制有明文规定:“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礼记译解》,王文锦,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72~173、674~675、704、717页。规定天子诸侯的四季之祭与祭祀对象,即“春礿、夏禘、秋尝与冬烝”。“王下祭殇五:嫡子、嫡孙、嫡曾孙、嫡玄孙、嫡来孙。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嫡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礼记译解》,王文锦,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72~173、674~675、704、717页。规定社会各阶层祭祀的代际以及祭祀对象种类。“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译解》,王文锦,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72~173、674~675、704、717页。国家建立后,在王宫之右设置社稷神位,之左设置宗庙神位,两者同为国家象征而常以祭祀。“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礼记译解》,王文锦,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72~173、674~675、704、717页。这就是现今宗祠供奉神主牌位的规制,按照“左昭右穆”的次序排放,左边放置二世祖、四世祖、六世祖等牌位,右边放置三世祖、五世祖、七世祖等牌位,可知祭拜者与祖先的亲疏远近。“以昭穆次序为核心的宗庙建制是为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分封制度服务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王鹤鸣、王澄:《中国祠堂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4页。《礼记》开创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仪规范,其中关于祭祀的诸多规制成为后世宗祠祭祀一贯遵循的义典。后来,儒家思想与儒家文化不断融入宗祠,《孔子家语》《颜氏家训》、司马光的《书礼》与朱熹的《家礼》等儒家经典为国人留下千秋仪范,为宋元以后传统家礼的范本,并逐渐形成“祠堂之制”。“所谓‘祠堂之制’,是指祠堂在宋至明中前期被士大夫作为思想生产和传播空间( 包括立儒和抑佛等) ,以及作为行道的工具和场所而进行文化再造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礼仪和秩序的建构、士大夫设计的祠堂士庶化以及基层社会的宗祠创造,形成了相互借力、相辅相成、互为主体的共主体性。”*张小军:《“文治复兴”与礼制变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礼的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祠堂之制”的形成是宗祠变迁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表征。宗祠是宗族的表征,宗祠的兴衰与宗族的发达与没落直接相关。明清之前,宗祠是上层社会权势与地位的象征;明清以降,宗祠是民间社会家族兴旺发达的象征,宗祠得到广阔的社会发展空间,因而当下现存的宗祠建筑大多为明清时期所建。
宗祠的美学意蕴不仅包含传统的祭祀礼俗,也包含家族教化功能与社会治理功能在内的诸多伦理道德内容,成为家族传承的重要源泉,同时宗祠内化的家族传统也对民间社会治理提供富有成效的实践经验。宗祠以上功能的实现,首先是通过家族祖先祭拜的程式得以完成。“家族崇拜通常在培养家系观念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祖先崇拜,家系将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联系在一个共同体中。”*〔奥〕迈克尔·米特罗尔、雷音哈德·西德尔:《欧洲家族史》,赵世玲、赵世瑜、周尚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1页。宗祠因供奉共同的始祖而聚集宗亲族人,可以达到提高成员凝聚力、聚族共事的功效。“民间祠堂融血缘、亲缘、情缘三者为一体的先祖崇拜方式是超越其他任何本土和外来宗教,是更容易、更适合、更自然地被华夏民族认同的群体最大、历史悠远真正原生的宗教信仰力量。”*孙建华:《漫步祖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宗祠中的祖先崇拜依靠一个祖灵把宗族成员汇集在一起,从而达到告慰先祖、实践孝道与“亲亲族人”的目的,所以《礼记·大传》中讲“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礼记译解》,王文锦,译解,第487页。。随着宗祠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宗祠中汇入了儒家、佛教、道教等思想,使宗祠成为一方文化的汇集地,宗祠文化也得以极大地彰显。在宗祠文化中,家族观念与家族传统是核心组成部分,是宗祠家族教化功能与民间社会治理功能的基础。家族观念与家族传统又以家风、家训、义理等方式在宗祠建筑内部或宗谱内出现,这对于家族教化与国家社会治理均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云南腾冲和顺现今遗存有著名的八大宗祠:刘氏宗祠、李氏宗祠、张氏宗祠、钏氏宗祠、寸氏宗祠、杨氏宗祠、贾氏宗祠与尹氏宗祠,每一个姓氏宗祠内均刻有大量的家风家训。如:寸氏宗祠刻有:“忠孝,诚信;礼仪,谦卑”;“五岳宗山百川赴海,千秋报本万古流芳”;“立德立功愿万世子孙书香还继,有源有本问两川父老祖泽犹存。缅千古之故家罔不本于积德,编万代之宗法无能告夫成功。”*摘录于云南腾冲和顺寸氏宗祠内。
钏氏宗祠照壁上刻有家训:“我钏姓乃有功之族人代奉先人之遗训耕读人伦教子传得男纲女训笔墨书香清白堪夸子孙有能承替祖职者应培之袭职为国建功别无违疑勤俭耕读士农工商各为生计无始无荒古人云金正衣冠史明兴衰荣辱从来事之不朽奠谓先人之美彰纪族谱启后代知已往为国效力而大焉无费先人之业绩寥寥遗训凡我族人子子孙孙须谨遵祖先之教诲忠孝仁义为本份为官者公正廉洁光明磊落勤政为民勤俭守信无奸无欺武官或民堂堂正正亦不可因正直清贫而后悔改心易行而懈了为善之志”*摘录于云南腾冲和顺钏氏宗祠内。。
杨氏宗祠房檐下的木雕内刻有遗规与遗箴。遗规:“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安家两字曰让与忍防家两字曰盗与奸亡家两字曰淫与暴休存猜忌之心休听离间之言休做过分之事休专公共之利。”遗箴:“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读书行善积德存仁隐恶扬善谨言慎行省心改过清操立品诚实无欺吃亏守拙清心寡欲安命知足谦和忍耐敦伦睦族怜孤恤寡敬老尊贤戒怒除暴节饮禁贪淡泊宁静知机恬退勤慎俭朴;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为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则家礼行家礼行则百事兴;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六句包尽做人的道理凡为忠臣为孝子为顺孙为圣世良民皆由此出不论智愚皆晓得此文义只是不肯着实遵行故字自留于过恶祖宗在上岂忍使子孙辈如此”*摘录于云南腾冲和顺杨氏宗祠内。。
以上宗祠内撰刻的家风、家训、遗规与遗箴均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人伦思想与社会生活理念,也是先祖们对后世子孙的殷殷期望与教导。宗族成员通过代际承传优秀传统与优良家风,建构后世子孙与先祖相通的心灵空间,达到薪火相传的目的。宗族成员在祭拜先祖中这些观念与传统得以内化,并在现实中不断践行,这就是宗祠文化的社会意义。“尊祖敬宗、亲缘团结和宗族( 社区) 声望,这些是典型的宗族社会结构下所形成的人的行动理念。”*焦长权:《祠堂与祖厝——晋江精神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东南学术》2015年第2期。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之所以允许民间建立宗祠,是欲利用此力量以维护其自身的统治。“宗祠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是社会教化的有益支撑。其次,宗祠文化凝结着深厚的血缘亲情,是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宗祠文化内含丰富的治理经验,更益于中国式社会治理实践。”*吴祖鲲:《宗祠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治理逻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4期。现代社会已没有支撑宗祠发展的义庄、义田等物质基础,但民间立祠、修祠的现象十分普遍,说明宗祠的社会传承并没有完全消失,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重塑宗祠的社会影响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平安乡土贡献民间智慧。
宗祠是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制度的产物,来源于祖先崇拜与神灵信仰,发端于西周宗庙,承继于汉晋墓祠,发展于唐宋家祠,兴建于明清祠堂,宗祠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极佳视野。宗祠不但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还可以从文化学、人类学、美学等学科研究。曾经辉煌的中国文化与艺术类型及其形态在其他领域已经消失不见,但在民间社会的宗祠中还得以大量保存。宗祠建筑是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瑰宝,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社会高超的建造技能与精湛的艺术水准,宗祠内的各种木雕、石雕、砖雕、泥塑等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精巧的雕刻技艺,宗祠中的诗词、楹联、书画等充分显示了民间社会文化,宗祠内蕴含的优良家族思想与家族传统是后裔子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从遗产学上看,宗祠具有鲜明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特征,应该作为重要的遗产类型进行保护与传承。但从当下宗祠的现状看,存在兴建宗祠与遗忘宗祠、开发宗祠与毁坏宗祠并存的现象。特别是中国当代三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几乎把民间宗祠摧毁,宗祠文化也随之没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恢复,宗祠得以重建、宗祠文化得以传播,宗祠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目前,一些地域原有的宗祠得到了大规模修葺,出现富有传统文化意涵与地方文化特色的宗祠群;但从全国范围看,宗祠的修建主要依靠家族后裔的捐助,而国家与地方政府在修建宗祠与传播宗祠文化中存在失位,导致大量的民间宗祠被闲置、毁坏或被挪作他用,多数处于倒塌的边缘,宗祠文化在很多区域几乎无任何影响力。宗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诸多宝贵的社会智慧,应大力挖掘宗祠文化的当下意义,重塑宗祠文化与重构宗祠文化传播路径,为审美再造、家庭教育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传统智慧资源。
参考文献
林耀华:《义序宗族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英〕科大卫、萧凤霞:《植根乡土:华南地缘关系》,帕罗奥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
〔英〕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Maurice Freedman,ChineseLineageandSociety:FukienandKwangtung,Berg Publishers,1971。
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李秋香:《乡土瑰宝——宗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丁贤勇:《祠堂·学堂·礼堂:20世纪中国乡土社会公共空间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刘华:《百姓的祠堂》,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
张开邦:《明清时期的祠堂文化研究》,2011年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殷名伟:《家族、乡土与记忆——被遗忘的祠堂》,2015年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肖明卉:《世俗化祠堂与适应型宗族:宗祠的结构与功能分析》,2011年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罗艳春:《祠堂与宗族社会》,《史林》2004年第5期。
邓启耀:《谁的祠堂?何为遗产?——古村落保护和开发中的问题与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郑建新:《解读徽州祠堂:徵州祠堂的历史和建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
广东省文物局:《广东文化遗产——古代祠堂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商明:《无锡惠山祠堂群家训集萃》,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2015年。
田友国、黄强、唐冠军:《铁规铜宗:长江流域的礼教与祠堂》,武汉:长江出版社,2013年。
尹文、张锡昌:《江南祠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韩振远:《山西古祠堂:矗立在人神之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
刘晓艳:《桑植白族祠堂的文化变迁研究》,2013年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寸炫:《云南和顺镇的宗教祭祀活动及其功能研究》,2010年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张兴年:《从村寺、祠堂看宗族对土族乡村社会的控制——基于景阳镇李氏土族的田野调查》,《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