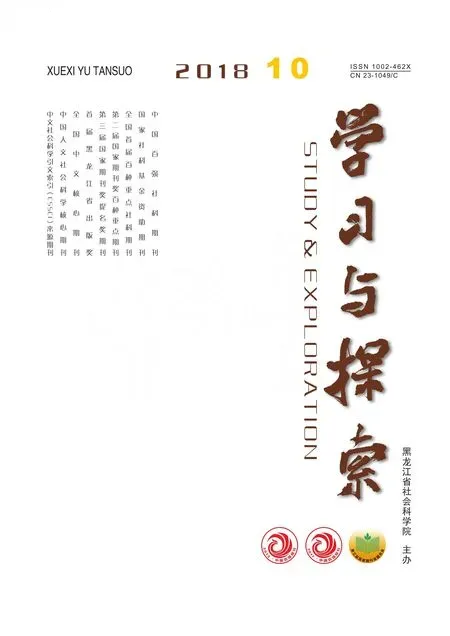历史叙事是否有真假?
——论安克施密特的“历史叙事不能为真(假)”
于 萍,段小凡
(1.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150080;2.哈尔滨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哈尔滨150001)
安克施密特在《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一书中提出“必须拒斥‘叙述之真(假)’这样的短语”,认为在哲学论证中这样的短语并不能表示叙述的性质。在他看来,在分辨叙述的质量时,真假并不能成为判断标准。他提倡用“主观的”和“客观的”来取代。本文意在梳理安克施密特提出此论断的理论依据,辨析其论辩过程,发现其合理性及不足之处。
一、理论依据
从安克施密特所使用的narratio一词可以看出其理论依据和立场。narratio一词最早作为古希腊和古罗马演说练习(progymnasmata)的第二部分出现,意思是对事实的陈述。紧随着介绍或引入论题(Introduction/Exordium),在叙述(Narration/Narratio)部分,演说者将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并简要解释事件的本质。接下来分别是Partition (Partiotio)-Confirmation (Confirmatio)-Refutation (Refutatio)-Conclusion (Perroratio),最后一项由昆体良(Quintilian)补充,最终形成修辞中的经典六大样式。西塞罗在其《论演说》(De Oratore,55 BC)中对演说的这几大样式进行了评述,他认为“对案例的叙述必须简短”,但反对“只采用那些最核心的,绝对最少化的词语”,因为后者“对于陈述案例的事实是不利的,不仅是因为这会导致晦涩,还因为它抹消了叙述的最重要价值,即使人娱乐和使人信服”[1]445。
首先,西塞罗以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剧作家泰伦提乌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的喜剧《安德罗斯女子》(Andria, or The Girl from Andros)中的一句话为例,比较了一行“自从那天后他成人了”(For ever since the day he came of age)和两节 10音节诗行“葬礼——我们开始,我们来到墓地/尸体被放置在柴火堆上——”(The funeral—we start, we reach the tomb, The corpse is placed upon the pyre—),指出后者与前者相比虽然未能做到最简,但是却达到了文体上的优雅。在他看来,在叙述中加入一些人物描写和对话可以使叙述“栩栩如生”“更有说服力”[1]447。由此可见,西塞罗并非因此舍弃了叙述的简明扼要,而是从修辞及其效果来考查简要的程度,更加强调陈述本身的句法、修辞、风格及效果。
其次,从安克施密特抑柏拉图而扬智者派(Sophists of Classical Antiquity)的做法我们可以管窥其理论立足点。在“导言”部分,安克施密特引用了斯特拉尔的话指出,“智者们的声音被柏拉图对‘永恒之真’(Eternally True)的寻求窒息了”[2]57。不言而喻,安克施密特是站在智者派这一边的。事实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智者派怀有深刻的敌意,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影响后世。例如,柏拉图在其《智者篇》中指出:“智者的技艺是制造矛盾的技艺,来自一种不诚实的恣意的模仿,属于制造相似的东西那个种类,派生于制造形象的技艺。作为一个部分它不是神的生产,而是人的生产,表现为玩弄辞藻。这样的血统和世系可以完全真实地指定给真正的智者。”[3]亚里士多德在《辨谬篇》也对智者派作了否定性的界定:“智术只是智慧的假象而实际上不是智慧;智者就是通过这种不是智慧的智慧之假象来挣钱的人。”[4]101
从公元5世纪中叶开始,希腊逐渐兴起了启蒙运动,而科学文化的发展推动了对教育的渴望。智者派在这种情况下应时而生。为了更好地推进演讲术,智者派首先从语言着手,专注于词及其语法功能,并进而延伸到逻辑学的领域。这一点正好与安克施密特试图从语句和语义的角度探讨其与叙事之间的关系相契合。后者指出,“叙述主义哲学当然处理的是语言问题”[2]57。此外,智者派的怀疑主义和强调关联性也在安克施密特的论述中有所体现。作为智者主义的理论核心,怀疑论指向的是一种反思的哲学,即对普遍有效的真理或任何确定的知识的怀疑。在他们看来,针对同一个事情,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证明,其中叙事起着关键的作用。安克施密特将这个观点引申到历史叙事中,认为“任何一种试图解释(部分)历史事实的努力都只可能满足部分历史学家,却永远不可能让全部的历史学家满意。也就是说,语言——也就是叙事——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永远无法以一种为所有历史学家接受的方式确定”。
关于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智者派所强调的关联性更是在安克施密特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普罗泰戈拉认为:“单个事物不但处于瞬间的生成过程中,而且还处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之中。个体事物并不完全被绝对的‘存在’所吞没,因此,事物彼此之间的临时作用才导致事物的性质。性质是运动的产物,而且总是属于两种互相关联但是方向相反的运动。”[4]106而安克施密特虽然表面上借用的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对语句之语境的强调,但他自己也表示,“然而维特根斯坦更愿意用语言外的条件来定义这个语境”。也就是说,安克施密特更倾向于智者派从语句内部来探讨其关联性的说法。更重要的是,普罗泰戈拉和安克施密特都借用了原子论的观点,认为语言哲学中语词和语句的层次被称为“原子”层次,而后者有关语句与叙事之间关系的论证就是建立在原子论的基础之上的。可见二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遗憾的是,自柏拉图以降,人们不再对叙事以及与叙事相关的问题感兴趣,其中起阻碍作用的还有笛卡尔。在安克施密特看来,笛卡尔成功破坏了文艺复兴主义对修辞学和叙事的兴趣。由此反观文艺复兴主义,尤其通过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我们不难看出安克施密特的第二个理论基础。洛伦佐·瓦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意大利雄辩家,他认为“语言既不展现现实,也不反映现实,而是构成现实”[5]309-310。在他看来,人们用词语命名事物,以人类的方式来创造词语,并将其使用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中,这一切“构成并维持着人类的所有事务,并一起导致了修辞的形成”[5]311-312。瓦拉将词语(修辞)提升到了构建人类社会活动、甚至“产生智慧”[5]312的高度,给予了叙事以充分的关注。作为一个反亚里士多德逻辑传统的人,瓦拉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智者派的遗风,形成了与亚里士多德等传统经典模式相对立的另外一种模式,可以简单地称之为语言学模式。事实上,由福柯等人推动的当代语言学转向就是这一传统的发韧。“他(福柯)的全部工程都彻底地反柏拉图主义,而亲古典时代那些诸如智者派和犬儒学派,后者一直被西方哲学的官方历史边缘化。”[6]
最后,从安克施密特提出此论断的文化环境来看,叙事一直为历史学家所重视,甚至被认为是史学话语的根本属性。克罗齐著名的论断“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就是个证明。劳伦斯·斯通也认为,历史学家“非常关心他们陈述的修辞方面。不管历史撰写中成功与否,他们都毫无疑问地追求一种文体上的典雅、才智和箴言”[7]。无论他们多么声称自己的科学性,历史学家都不会选择将词语毫无艺术地堆在那里。怀特在其《元史学》中指出,“历史学被普遍认为是科学和艺术的混合物”,然而“分析哲学家们在成功地澄清了历史学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科学的同时却很少有人关注它的艺术性成分”。这也是他“试图确立历史著作中无可回避的诗性特质,并在历史叙述中具体展示出那些使得其理论概念得以认可的预构性元素”[8]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哲学发生“叙事的转向”(或修辞的转向)的基础。正如劳伦斯·斯通在《叙事的复兴:对于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中和霍布斯鲍姆在《叙事的复兴:一些评论》中所肯定的,叙事是历史编纂学的核心要素。当下所做的理论反思和实践,一方面反映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广泛流行并占据统治地位的对经济/社会决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及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派等所谓“科学的历史”的不满;也反映出重估传统历史中的叙事问题显示了历史哲学朝着多元化和多维度繁荣的决心。而这正是安克施密特提出“历史叙事不能为真(假)”命题的背景。
二、叙述非真非假?
安克施密特是从陈述与叙事之间的区别入手来探讨叙事之真(假)的。在他看来,陈述和叙事并非一回事,而是后者包含前者,前者以一种方式构成后者。这样,陈述之真与叙事之真之间的关系“就比我们最初设想的要更模糊一些”[2]61。在他看来,“如果叙事的内容不能被还原为叙事中的特殊语句的意义”,即如果叙事的意义不能还原为单个陈述的意义,那么叙事的真假就很难界定。从这点出发,安克施密特借助于反驳还原论者和真理论者的观点来论证其关于“叙事不能有真和假”的论断。
还原论“是指把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或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去替代高级运动形式的现律的理论。它把每种东西都视为一种更为简单的或更为基本的东西的集合体或组合物”[9]。在安克施密特看来,“叙事之真或假”对于还原论者而言是不言而喻的事,因为叙事之真实是叙事中个体陈述之真实的真值函项。但是,安克施密特指出,这样会遭遇与常识不符的困难,即若陈述的合取中的其中一个陈述为假,那么整个叙事就是假的。他进一步举17世纪自然法的两个叙事为例,证明了还原论者在这种状况下遭遇的尴尬。对此,还原论者试图以个别陈述的重要性来判断其真假,但这在安克施密特看来也是“无望的”,因为还原论者据此提出的两个标准,即“(1)叙事的个别陈述的真或假;(2)在个别陈述中报告的证据对于正确理解叙事之所叙的必要程度”可能会自相矛盾。接着,安克施密特分别以费恩和格曼二人对标准(2)的辩护为立论依据进行反驳。
费恩认为,“当人们试图讲述相关真理时,人们对世界所拥有的概念性知识起着主导作用”。以智力拼盘为例,人们可以将拼盘有图的那一面朝下,然后根据各个小片的形状将拼图拼在一起,也可以根据各个图片载有的信息与整个画面的关系来组装拼图。类比到历史学家所做的叙事,费恩认为如果历史学家没有辜负人们的预期,人们就会认为这种叙事传达了相关真理。对此安克施密特提出质疑。他认为,人们对拼图所载有的信息会有整体认知和预期,但是对过去却不同。这种对过去的认知和预期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也是人们对历史学家的期待,因而人们无法在这种情况下判定哪些是与历史真理相关的历史现象。他总结道:“如果关于历史现象P的相关真理主要包含关于P的真理,读者并不知道这些真理对于理解这个现象来说是相关的,那么费恩的智力拼盘玩具比喻就明显是令人误解的。”[2]63格曼在费恩的基础上试图找到确定个别陈述与叙事之相关性的“理性标准”。但是安克施密特却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费恩“除了提到科学中关于这种‘理性’标准的一些没有多大用处的离题话以外,对这个问题没有说出任何有实质意义的东西”[2]63。
关于对真理论者的批判,安克施密特试图从四个方面进行,即符合的真理理论、融贯的真理理论、实效的真理理论和执行的真理理论,但实际上只论述了前三个真理理论。他的核心观点有三:其一,陈述与叙事不同,因而我们可以用上述三种真理理论来探讨陈述之真或假,但却不能应用到叙事;其二,叙事没有也不可能有可参照的“标准”;其三,叙事的描述性和隐喻性之间存在差异。在他看来,上述真理理论难以在语义的层面对叙事之真或假做出合理的辩护,因而“不能被有效地应用于叙事”[2]64,即“叙事之真或假”这个命题在哲学论证中是毫无意义,且不应被提倡使用的。
首先,也是安克施密特一以贯之的观点与理论立足点,即陈述与叙事存在差异,陈述之真不应指向叙事之真。在安克施密特看来,叙事“也有某些描述性约定决定着”[2]67,然而这种描述性规定下的叙事却不能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一个叙事就有点像只说一次的词。或者更确切地说,尽管叙事包含真陈述,尽管可以做出关于叙事的真陈述,叙事却不能被用来做出真陈述(像词语那样),因而我们不能想象出叙事之正确使用的‘描述性约定’”[2]67。在这里,安克施密特从根本上否定了叙事表征真实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与语句和陈述不同,叙事不拥有某种可以做决定其真或假的标准的叙述‘意义’”[2]67。在叙事和它所表征的过去之间缺少了一种不变性,即在人们阅读完一部历史著作后,人们不能确切地、或不确切地确定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陈述可以准确地表达其意义,但是叙事却不能。“在叙事中,陈述显然比仅仅将单独的意义连接起来‘做着更多的事情’。它们给予叙事的认知价值应当区别于个别陈述意义的总和”[2]69。自此,安克施密特将陈述与叙事之间的鸿沟鲜明地展示了出来。这个鸿沟直接导致了符合和融贯的真理理论无法应用到叙事中去的结论。
其次,在安克施密特看来,由于叙事不存在任何标准,因而难以通过实践证明或类比相容性来判断其真或假。真理实效论主张,“对由一个特殊信念所引起的行动的正确评价,是确定那个信念之真的最好标准”[2]65。将此应用到历史叙事中,安克施密特认为,由历史书写的实践可以推断出历史学家关于什么是真或假的看法。但是他指出,“某人持有某个信念这个事实对于被相信者之真来说并非充分的证据”[2]65。也就是说,倘若历史学家A1与历史学家A2在同一个历史事件上持有不同的观点,那么他们的历史实践必然存有差异。以差异化的历史实践去衡量历史学家的观点之真假是不充分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由于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历史实践或历史阐释,人们便无法判定所有的这些历史实践为真或假。在批判符合真理理论时,安克施密特也是从标准的难以树立和界定出发,论证了叙事难以从相容或不相容这个角度去判定。由于标准叙事的缺失,相容或不相容就成了无稽之谈。
最后,关于叙事的描述性和隐喻性之间的差异安克施密特并没有过多阐述,他自己也声称,“现阶段我还不可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做出全面的阐述”[2]69。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安克施密特对于叙事之隐喻性的看法与怀特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前者看来,由于历史叙事必须有语言参与,而语言除了对历史实在进行表征之外还会提出隐喻式的看法,这就导致了历史叙事与历史实在之间难以达到一种“不变性”[2]67。也可以说,由于兼具了描述性和隐喻性,且两者对历史实在的表征方式明显不同,历史叙事变成了一种不纯粹的历史表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安克施密特认为,讨论叙事为真或者为假是没有意义的。
三、何为真实?
安克施密特关于“叙事不可以为真或假”论断上存在引起争议的地方。首先,他的真实观易于引起歧义。如果说叙事不存在标准,“真”也是同样,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真”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叙事不可以为真或假到底是不可以为什么样的、什么程度的、哪个意义上的“真”呢?难道“真”的概念仅仅在于与历史存在的完全契合吗?由此引向了他的论证的第二个方面,即过于纯粹和理想化,忽略异质与多元。倘若仅仅是从哲学的范畴进行探讨,那么他关于“绝对标准”的缺失、叙事对实在的表征意义等显然指向的是实践和具体应用。而在应用中,任何人都无法抹消概念的动态性和历史性。最后,安克施密特似乎也落入了智者派所受的指责,即诡辩中去了。
纵观安克施密特的论证,我们不难发现,他将“真”等同于独立的“实在”。在发表于2010年的《历史与文学的真实》一文中,安克斯密特提出用“可确认的独立物体”来阐释真实的概念。在他看来,历史叙事只是呈现了物体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是实在物体的一种概念化,而非真实的物体本身,因而无所谓真假。他举“这个木板的中间”这个例子论证了叙事与实在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个木板”可以与实在的某一木板相对应,即当人们说“这个木板”时确切地指称某一实在的、唯一的物体。这个木板的中间也可以用具体的数据如位于东经北纬多少度、距离地面多高等来确认。但是“这个木板的中间”既可以指木板上的中间位置,也可以指木板中间位置的一个疙瘩。安克斯密特认为,由于语言的介入,能指与所指之间难以对等,历史实在与历史叙事之间也无法对应。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真实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是实在的物体本身。
在安克斯密特阐述其真实观时,语言与表现是两个核心关键词。1967年,理查德·罗迪出版了著名的《语言学的转向:哲学方法文集》(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一书,并在导言中对这种转向做了定义:“(语言学的转向可以看作是)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哲学的问题可以通过改革语言,或者更多地理解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来解决(或消失)。”[10]之后,怀特声称:“一个特定历史场景的成行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精妙技艺,他将一个特定的情节结构与一系列历史事件相勾连,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填充一种特定的意义。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的操作,是小说创作的一种方法。”[11]至此,历史书写与文学创作无异,成了一种隐喻化操作。也正是立足于此,安克斯密特提出,“在历史编纂学中,不存在作为叙事基础的过去,也不存在支撑历史叙事的翻译规则。”[2]92在他看来,历史实在几乎是碎片化的,需要借助于历史学家的语言,即隐喻性的语言来指代过去发生的事件碎片,并将这些碎片重新组合起来,呈现在后世人的眼前。在这样再加工的过程中,“真”是必然会消失的。这种做法显然局限了“真”的概念外延。
从隐喻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安克施密特在“真”的概念上的自相矛盾。在安克斯密特看来,“隐喻远远不是一种语言的修饰或者尝试着用字面语言表达的、潜在的东西。如果将隐喻的维度从语言中消除,我们关于世界的看法立刻就会分解为互不联系的、难以处理的信息碎片,隐喻综合了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至少,一旦我们丢弃了隐喻,我们由于自己的历史意识而赋予世界的一致性和我们在现实中识别同一性的能力也将随之而去”[2]212。也就是说,隐喻是建立在语言机制基础之上、但又超越了这种机制的所谓元机制。它赋予了人们以某种看待世界的观点和视角。但无论如何,隐喻是无法逃离语言本身的约束的。既然如此,“真”作为语言的一个量,自然要遵循隐喻的各项基本法则。那么,将“真”之概念真空化似乎就不太恰当了。安克施密特认为,“历史叙事是一个持存的隐喻”[12]41,已经超越了被判定为真假的层面。然而,“真”和“假”本身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隐喻,又如何能够承载安克施密特所谓的超越呢?按照安克斯密特的观点,历史叙事并不指涉过去,而只是关于过去的一种视角,历史叙事无法与过去发生的事件相对照,因而无所谓真假,也无法判断为真或为假。也就是说,不与过去相对照,所以不能为真或为假。这种判定标准显然过于狭隘,容易陷入虚无主义。
任何历史解释/历史表现都是当下的,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和过去存在的人物所做的一种阐释,严格意义上都难以与过去相对照。而且,单就历史文本而言,也很难判断此一陈述/叙事与过去相对照。除非借助于考古学的发现,以及其他历史方法,否则真假难辨。如果真要分得那么清楚的话,对历史的真实的追寻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真实已经随过去埋葬在时间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克斯密特做出叙事不能为真/假的论断有些过于吹毛求疵了。既然承认历史陈述的真实性,那么真实性就是有必要的。在进行历史叙事的时候,即便不能判断所有的历史叙事为真,也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其为真或假的可能性与程度。更何况,在具体的历史文本中,历史陈述与历史叙事并不是泾渭分明、那么容易分辨清楚的。
过去真实发生的一个个历史事件是真,以最优化的方式对历史实在进行叙述的历史叙事也是真。安克施密特这样谈道,“最好的历史叙事是最具隐喻性的历史叙事,有着最大涵盖面的历史叙事。它还是最‘冒险’或者最‘有勇气’的历史叙事。相较而言,非叙事主义者只会青睐没有内在条理而缺乏意义的历史叙事”[12]41。他所谈到的最好的历史叙事,也应是最真的历史叙事,因为这种叙事首先经得起实证的推敲,不是毫无根据的瞎编乱造,它给人以最真实的感觉。既然任何后世的人都无法进行穿越,那么这种最真实的感觉就应当是判定历史叙事优劣的其中一个标准。在这方面,由于安克施密特缩小了“真”的概念外延,他才做出了历史叙事不能为真或假的论断。
最后,历史的真实受制于很多条件,但正因为其多变性和多元化才更加真实。安克斯密特批判但丁对文艺复兴这个词的定义,但是但丁对文艺复兴的界定充分地反映出了但丁及其历史文化背景的真实性。这就像我们批判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为女性作传一样,是一种历史的苛求。司马迁若为女性着墨太多,反而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是随时间而变化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但这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否定历史文本或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正如历史上的智者派遭人误解一样,倘若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硬要拿这样的问题问安克施密特:“‘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和‘日本没有发动侵华战争’这两个表述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都不是真的,或者都是真的,或者无所谓真假”,不知他会做何回答?历史叙事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还至少牵涉到政治问题。倘若被认为流于语言游戏,那么它对于人类、对于社会的发展都将没有多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