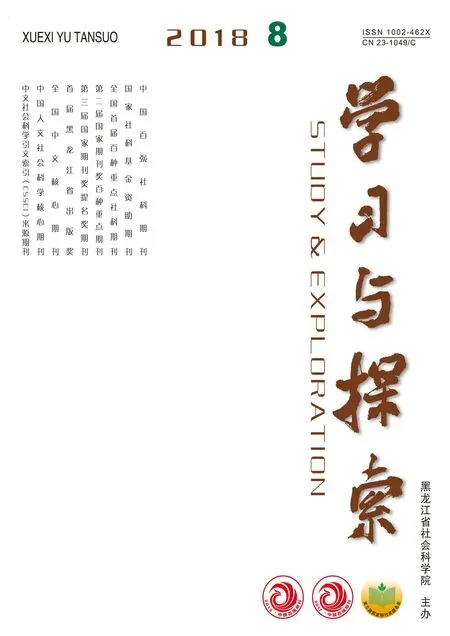图像文化语境中的文艺镜像及其理论面向
黄 继 刚
(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阜阳236041)
一、“图说”“语象”和文艺的视觉属性
自原始时代始,图像的创造活动和言语活动相伴而生,无论是格瑞威特时期(Gravettian)的狩猎者雕像还是玛格达林时期(Magdalenian)的洞穴图像,都隐藏着“从图像到命名乃至言语符咒的奇妙之链”[1]。而如何解读这两个不同的符号表征和指意体系之间的交互转换,探寻并归纳出图像的语言化和语言的图像化两者的可能性及其视觉属性,则需要借助两个核心关键词——“图说”(Ekphrasis)和“语象”。
“图说”也被译为“图示”“符象”“艺格敷词”“造型描绘”等,这个古希腊词汇原指“纹章”或“图案符号装饰”,后来被引申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学修辞用语,强调的是文学语言再造画面的视觉能力,即语言不仅能够叙事讲述,而且还能如绘画图像一样的展示。这种打动听众内心深处情感的说服技巧,通过对缺席事物的生动描述使其能栩栩如生地再现,影响受众的主观情感并进而左右其理性判断,甚至能造成受众罔顾事实而选择“视觉偏信”,这正是古希腊公众演讲追求的修辞目标。后来,米歇尔在《图像理论》中“图说”分为三个层面[2]151-157:第一是“‘图说’的冷漠”(ekphrastic indifference),也就是语图之间的不可沟通性;第二是“‘图说’的希望”(ekphrastic hope),也就是在尊重艺术门类差异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尝试跨越艺术之间的鸿沟;第三为“‘图说’的恐惧”(ekphrastic fear),“图说”使语言文字对意象的再现失去了唯一性,并有消融文字的倾向。由此不难看出,“图说”是借由符号的转换,以语言文字来阐释和呈现图像之内涵。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图说”是建立在图像结构之上的,是图像言语化的早期模态,其释义的深度和广度必然会受限于图像自身,尤其是对宏大主题的阐释方面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法烛照出图像文本的“微言大义”,也无法推翻已有的图像因素来进行视觉叙事,所以,“细读苦品”既是其特色,也是其局限。
“语象”是20世纪新批评学派在研究诗歌语言中经常提及的术语,卫姆塞特将之定义为“词语的形象符号和对象属性”[3]。后来的俄国形式主义将其视为建基于客体存在之上的艺术经验,强调的是文字自身的形象属性,这和索绪尔的洞见不谋而合,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的“声音形象”是带有主观“心理印记”的[4],而非是一个物质的客观存在,这一观点既独辟蹊径而又切中肯綮。在20世纪80年代,赵毅衡在向国内译介新批评理论时,将“icon”翻译为“语象”,即“在同一瞬间表现理智和情绪的复合体”[5]。“语象”是由语言能指构型出来的视觉形式,是物的图像和人的主观意象的融合。后来陈晓明在其论著中认为“语象是诗歌存在世界的基本视象”[6],是唤起心理表象的最小意义单位,其展呈自身,不表明任何于己无关的意义或事物。
词语和形象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历程中的“元理论”。西方语言学理论中的概念“仿拟”“隐喻”“讽喻”“挪用”都和符号象征相关,而中国文字学中的“六书”也“包含了语源(历史)、图像(形似)、观念(语义)、比喻(类比)、互借(结构)等因素”[7],尤其是汉字以比类、会意、类推的方式使其从“象形”之“象”上升为文化逻辑之“像”。《说文解字》认为“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8],换言之,天地、鸟兽、身物都是文字产生过程中法象取类的依据,并帮助文字显迹赋形。从“形”至“象”,语言完成了对事物的命名,而汉字左提右按、对应制衡的表意范式更是建构出整饬有序的审美逻辑世界。学者程抱一认为汉字以象运思,表达出与西方迥然有别的审美意念。诸如王维《辛夷坞》中开篇第一句“木末芙蓉花”,读者依照视觉顺序来把握这行字的意义,语象上已经呈现出一株树开花成长的全部过程。“第一个字是一颗光秃秃的树,第二个字树枝上长出一些东西,第三个字出现了一个花蕾,‘艹’是用来表示草或者叶的部首,第四个字为花蕾绽放开来,第五个字是一朵盛开的花”[9]。就此而言,中国文字自身结构上就具有十分丰富的形象视觉性,而正是这一特性使得汉字能够完成从“视见之物”到“未见之物”的过渡。就此议题,张祥龙先生总结过汉字的形象性、隐喻性和动态性等特点,他认为“汉字笔画的裂隙性就在于,它总在无形有象之间引出对于自身的赋义”[10]。
除此之外,语言和图像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还体现为“一方面表现为文艺对于世界的‘语象’展示;另一方面表现为语象向视觉图像的外化和延宕”[11]。这恰如曹庭栋的判断:“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12]事实上,自北宋以来,朝廷选拔画师都采用援诗入画的方式,也即考核一名画师对文学语义的理解能力以及对图像呈现的平衡技巧。根据陈善《扪虱新语》记载,某年面试画工的题目便是根据诗词“嫩绿枝头红一点”来作画,大多数画工都是在绿树红花的比例结构上大费苦心,“唯有一人画危亭缥缈,绿杨掩映之处,一位美人凭栏而立”[13]。再如一题目为“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众人冥思苦想后,大半都是画“系空舟岸侧,或拳鹭舷间,或栖鸦蓬上,而魁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长笛,其意非无舟人,而无行人也”[14]。上述两例中,画作对“红”和“无人”的阐释都没有拘囿于语言层面的实义,而是以图像来突破了诗文表达的界限同时又没有背离原义,这种语图之间的错位阐释,看似“貌离”,实则“神和”,两者互彰使得意义表达和视觉呈现都趋于极致。
二、图像的本源性和语图分野
“图像”一词,源自于希腊语“Iconographia”,由“eikon”(image)和“graphein”(writing)组成,其原义为图像之记述和描述,即以概念来还原图像本来的意义。现代图像学滥觞于19世纪末期德国的瓦尔堡学派,这是一个以美术史学者瓦尔堡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团体,他们将图像作为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并侧重图像的文化历史阐释。后来的潘诺夫斯基则在这一领域建构出相对严整的理论体系,并区分了两个研究分支:“图像学”(iconography)和“图像志”(iconology)。他用“本源性”(authenticity)概念确定了图像存在的特殊性,这词汇是“original”与“authoritacivc”的叠加,这也确立了原创性图像艺术的绝对权威。至20世纪末期,米歇尔用“picture”取代了潘诺夫斯基的“iconology”,这一核心术语的替换实则表明研究立场的转换,“iconology”来源于宗教艺术研究中的“圣像”(icon),潘氏研究强调图像艺术的多层次解读和符号学阐发,尤其是他建构并完善的“图像层次解读法”;而米歇尔侧重的是图像的现代传播和技术话语议题,并将研究视域从“艺术的图像”(artistic image)扩展到电视、电影、摄影等领域。就此而言,图像传播的范围可谓是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其被纳入到艺术哲学、现象学、文字学、政治学这一“大载体”中。针对图像本源性议题,海德格尔曾经有一个经典判断,他认为“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在出现世界图像的地方,实现着一种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本质性决断。”[15]这一审美逻辑的前提是“人作为主体”,主体只有按照自身的尺度来审视世界,才能将世界描绘成为存在的世界,世界图像才能够作为对象。世界通过主体的视觉建构显现为世界图像,这一图像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摹仿,而是通过主体的审美建构,将不可见变成可见,将眼中所见转化为“有意味的形式”。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本源就隐没于艺术作品世界当中,并向真理探索者无限敞开,在这种思之虔诚的追问过程之中,精神境遇和生存境遇将融通汇合,存在进入到去蔽澄明之境,主体找寻到安身立命的诗意栖居之处也成为可能,这是海德格尔所谓“把握”的要义,即主体对客体的“意象性”认知建构活动。无独有偶,维特根斯坦也在《哲学研究》中提出对语言与逻辑、语言和思想、语言和世界等相互关系的理解只有通过图像这一途径来完成,也就是说“一个事态是可思的,意即我们可以给自己绘制它的图像,图像即在语言之中”[16]。换言之,图像不是我们表情达意的符号,而是我们体验存在的重要方式,我们凭借它的本源性存在来拥有世界。换言之,图像的界限就是主体的界限,它和世界的事实相对应,并建构出有关于世界的逻辑形式。在柏拉图的“洞穴譬喻”中就形塑出这样一个图像空间,无法转身的囚徒面墙而跪,身后的火堆投射出长长的身影在他们面前的白墙上,他们一直将这投射的图像当作真实的全部存在,并对自己背离真实状况的事实习焉不察,图像的反作用力正如柏拉图的阐释“人们宁愿把以图像为出发点的影子的连续镜头看成太阳的光芒并紧随其后”[17]。在这则譬喻中图像(影子)比思想真理散发的光芒更加有力。
但如若我们细细考究,不难看出柏拉图已然阐明图像化自身所具有的二重性:纯粹精神方面的理性活动必须借助图像来分辨自己,但图像化的后果却又往往只是拘囿于感官层面。由此,图像再现的真实性问题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起来,其方法就是用视觉真实来代替掩盖物理和哲学的真实,这也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空间透视技法营造出来的视觉幻象。“透视法使那独一无二的眼睛成为世界万象的中心”[18]。从“洞穴譬喻”到达·芬奇的“镜子说”,以及启蒙主义运动对可见性的偏爱,都可以看到视觉的优先地位,视觉隐喻成为真理话语的一种表征,这正如赫拉克利特的判断“眼睛较之‘耳朵’是更为精确的见证人”[19]。这种依照视觉经验和判断来确认知识理性的倾向,可谓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体现。这是典型的理性法则,是有序的欧几里得空间提供把握世界的方式,艺术家为观看提供了一个秩序井然的“视域画框”,而观看者在此处投注目光。所以,透视技法成为图像真实的代名词,其在很长时间内都支撑起人们的视觉认知,包括像拉斐尔《雅典学院》这样的宏大结构一度代表着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观者的解读要求能够将图像当中的“故事、概念、主题、象征,和民族、时代、大众的基本史实联系在一起”[20],从客观外部世界抵达主体视觉所穿透的对象内心世界,从而将描述转为阐释,从感知过渡为体验。就此议题,高名潞先生已着先鞭,他在《西方艺术史观念》中做出了比较权威的解释,作者在此就不再赘述。
语图分野一直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矛盾性话题,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建构出拼音文字言说的权威性,语言的实指性使得精准“命名”成为现实可能,语言表达往往代表着一整套与之相匹配的文化秩序和生活方式,文字阅读是以寓意性、认知性和理解性的内容来传递思想的,其过程表达上是连续的线性方式,文字的上下文之间有着确定的前因后果关系;而图像表征因为相对缺乏这样的规定性而呈现出视觉的暧昧。正如杜尚的作品《泉》,语言标题的艺术指涉和观众视觉辨识的图像风马牛不相及,这一标题强势将马桶从生活功能的秩序中隔离开来,并将之置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语境中,这使得我们的图像经验无法返回到常识中来,话语的阐释也完全逾越了视觉把握的范畴。静默的图像会导致意义的游移,而图像只有凭借语言阐释才能够获得意义并使其权威化。这种语图互文的形式被福柯视为可以进行后现代阐释的“图形文”,文字相当于图像的组成部分,这不仅更新挑战了传统知识,并且更新了图像的定义。关于图像和语言之间的不对称性,福柯曾经说过,“我们的所见从不在我们的所言中”,他认为画家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的《这不是一只烟斗》可谓是“语图悖反”的典型,这幅作品质疑并解构了视觉经验和艺术再现的传统稳定关系,画面中明明是一只大号烟斗,但是在下面文字中画家却标注为“这不是一只烟斗”,这种所言非所见,所现非所指的“急转弯游戏”使得语言与图像之间“词不达意”的断裂关系彰显的明白无误,传统绘画艺术依靠“确认”建立起来的相似性关系也荡然无存。这种“真实”观念颠覆了我们传统的视觉秩序。艺术家借此提醒我们,图像再现并不仅是指涉视觉表象的意指行为,而且也可以是象征和指示,或成为超越事物表象的非具象再现。而在《形象的背叛》这幅作品中,就图像和语言的空间比例而言,无疑是图像画面占据着视觉优先性的地位,包括观者的视觉经验也是从上到下,从图像再到文字。但是为何下方的一小行文字反而彻底推翻了观者之前的视觉经验,这不得不归因于语言符号的“实指”功能,文字的强制命名开启着对象的可能性。
当图像与文字同存于一个平面却又“表里不一”时,观者都相信了语言的“实指”而对图像产生了怀疑,随后完成对其的驱逐。他们“在‘PIPE’烟斗中的‘P’的形状与所画的烟斗之间看到了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中隐含了一幅诗画”[2]61。尽管两者相似,但是A不等于a,图像逻辑和文字指涉并非全然重合,表面上看这幅作品,无论是认知图像还是语言文字都是简单透明的,但是画家设置的“图形文”又形成了“自我解构”的张力。而维拉斯凯兹的《宫娥图》更是从图像话语中找到符号的隐喻,并再次激活了对话的力量,其借助古典宫廷的日常情境表征出视觉再现的悖谬之处,也即栩栩如生的生活场景只不过是艺术家“以画论画”的自我引证和天才假想。福柯后来将这种视觉的错位(不确定性)看作《宫娥图》的文化要义,在这幅图像中语言的指涉无效性昭然若揭,否定判断阻断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关联,并借此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语言的偏狭之处。同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视觉再现也会出现意义的暧昧之处,图像尽管和原物在外观上一模一样,但只是停留在静止的视觉再现层面,没有阐释的话,意义生成也将会受限。而文字再现则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历时性过程。维特根斯坦曾经用一幅登山的图片区分了上述差异,画面中有个人正在费力地爬山坡,但是面对这幅只能表现“瞬间”的图像,就一定确认为他向上爬吗?可不可以认为是这个人倒退着下山呢?上述质疑提醒我们关注视觉再现的虚假性和局限性,而图像这一短板恰恰是语言陈述可以弥补。
由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我们仅仅依靠文字的“准确性”来描述图像的“生动性”无异于缘木求鱼,语言作为一种概括方式,是时间线性的先后呈现,这一过程中“准确性”必然会受制于个体的局限性,包括罗生门现象业已证明语言的传递以及畸变的过程势必将会导致真相的遗失,后来维特根斯坦的“观看”和“言说”的表述,以及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引述的“鸭兔图”都进一步论证了现代哲学之后语言文字的有效性和局限性。而图像是在观看的同时就已经有了一个整体性的构图,之后是细节性的同时展开,就此而言,文字是“描述”,而观看是“描绘”,我们描述作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侧重的是作品和思想的关联,关注的是语言如何匹配和捕捉图像意义的可能性,或者说是通过图像来阐释图像背后存有的语词意义,就此而言,图像对事实描述并没有兴趣,其兴奋点还是在对待事实的立场。
三、图像研究范式及其审美归趋
从图像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对图像的认知一直交织着审美主体的眼光,而我们对图像文化范式的审视也成为反思文化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理论面向。自“图像转向”之后,视觉文化研究将触角延伸到精英艺术之外的文化现象,并改变了传统艺术研究的理念和范式。图像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逐渐划分为两种研究范式,其一是注重主体性和语境意义的现象学研究;其二是依照社会应用模式展开的意识形态研究。
首先是“图像现象学”,其秉持“从瞳孔走向世界”[3]131的原则,并以自己的眼睛、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来捕捉真实的场景,主张意义经验化、内容图像化,将诸多形而上学的东西还原为可睹可感的经验。我们从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中亦不难看出胡塞尔现象哲学影子,胡塞尔认为我们对事物本质的探寻不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也不能用主观形而上学,而应该让对象脱离历史成见和主观判断,成为纯粹的“自在”,“唯有通过内心体验去认识对象在我们意识经验中呈现的方式,才能揭示出对象的终极意义”[21]。这种研究范式的一个典型个案就是海德格尔和夏皮罗之间持久的学术争论。这场争论起源于海德格尔对梵·高作品《农妇的鞋》的经典评论,并将作品中的“鞋”建构成为一双表达了“普遍性的鞋”。而1968年夏皮罗在《静物作为一个私人物品:关于海德格尔和梵·高》一文中指出了海德格尔是“指鹿为马”,并釜底抽薪式地推翻了海德格尔所做出了的艺术评价。根据他的考证,梵·高创作了8幅同题材的作品,海氏只是选择其中之一就上升到艺术真理和普遍性,实为罔顾丰赡的图像本身;不仅如此,这些“鞋”都是梵·高本人的,而并非农妇的,海德格尔是典型的张冠李戴;最后这些“鞋”是画家梵·高的“私人物品”和“自画像”,带有画家本人强烈的个人印记,海氏没有尊重基本史实就自我发挥,“这些联想并非是绘画本身所支持的,反倒是建立在他自己的那种对原始性和土地有浓重哀愁情调的社会观基础上的”。包括海德格尔在谈论“文艺作品本源”时所描述的农妇走在田埂上的艰辛劳作、分娩的阵痛以及大地的馈赠,都是理论家一厢情愿的诗意想象,阐释者拥有太多形而上学的阐释权力,却完全忽略了梵·高和图像本身的“在场”,他预设了一个错误的理论前提,“假定物的外在性遮蔽了内在的真理,然后再去求证隐蔽的真理和外在假象之间的符合逻辑的对应关系”[22]。这就必然导致解读的偶然性和局限性。夏皮罗的质疑体现出艺术史家的图像证史和哲学家玄学思辨之间的矛盾,也由此斩断了图像和思想之间的虚妄关联,要求悬置先入为主的哲思而真正回归到图像自身。后来德里达加入到这场论争,他在《绘画中的真理》中认为任何阐释都是个体经验的描述,并把这场论争视为思想家该如何掌握对艺术作品的解释维度以及如何把控艺术品的最终解释权。
在艺术哲学中关注图像的语境意义及生成这一维度的当属阿瑟·丹托,他引入“风格矩阵”来解释图像的本源问题,要求还原出图像现场并以此来探究文艺风格的嬗变关系,他认为文艺演进关系史中每增加一种全新的理论思想都会直接导致(2n+1-2n)种文艺风格的出现。在这些排列组合的风格矩阵中,艺术品是能够呈现(a,b,c……n)种艺术属性的存在物,在不同的时代精神中,艺术图像展开了某一种可能性的风格维度,以应对当时世界的文化逻辑要求,而所有崭新的文艺风格都不过是矩阵中的重新组合。由此,艺术图像和寻常存在物的区别并非是物理属性上的差异,而是它们各自应对的文化关系,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属性”。
“图像意识形态”这一研究范式,是指图像研究走出艺术史、视觉史和形式主义的窠臼,进入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分擘考辨当中。图像作为“时代眼睛”(period eye),隐身于其后的应该是社会时代的精神符号。巴贤道尔(Michael Baxandall)就认为图像的风格理应当成研究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线索,艺术家从“绘画笔迹”来反观“社会货币”,这和早期学者提出的“图像权术”的研究思路一脉相承,其具体体现为将主观的情绪心理用图像的方式表达宣泄出来,这其中描绘的角度和眼光往往就决定了图像的象征意义。例如,在9世纪的英国文学中,爱尔兰人都被塑造成一个“弗兰肯斯汀”(Frankenstein)的非人类猿形怪物,并建构出一整套类似表现“次人类”(sub-human)的普遍性视觉符号;而滑托绘制的《中国皇帝》当中的人物全部都是画了妆的欧洲人。图像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符号运作的繁复体系,其间包含着各种不同解读的“裂隙”(Ruptures)甚至也包含着对既定秩序的颠覆和僭越。换言之,图像本身也可以产生颠覆性力量来表明一个时代的完全终结。正如任何一次政治革命成功后,往往都是先从捣毁政治领袖的雕像或其他建筑物开始。诸如公元8世纪,拜占庭就发生了圣像之争,反圣像派提出种种理由来破坏圣像;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拿破仑雕像的被毁;俄国十月革命时期沙皇铜像的被毁;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布达佩斯大广场上斯大林雕像的被毁等等。符号学者罗兰·巴特在《神话修辞学》中曾经谈及“图像意识形态”的运作和建构,他分析了1955年6月25日的《巴黎竞赛画报》上的封面图片并说明了图像的文化表征以及形成的符号体系是如何运行的。图片上一个身穿法国制服的黑人士兵,面容庄重地朝向三色国旗行注目礼,巴特称这是标准的“视觉神话”,从图片引申到外部现实,其背后内蕴的含义是“法国是个伟大的帝国,根本不存在肤色歧视,她的全体儿女都忠诚地服役”[23]。符号的任意性表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而变化,能指只是一个空洞的、等待意义填充的容器,而这种符号指涉进入文化思想领域,会潜移默化地对接受者的观念和信仰产生作用。此外,图像还可以成为国族地理空间的文化确认,这其中最典型的要算卡尔顿·沃特金思(Carleton Watkins)了。他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就开始出入塞米特峡谷,用画笔纤毫必见地呈现出西部粗犷的景观,这种雄伟而不乏野性的图像写真,代表了新兴美国的蓬勃朝气和巨大野心。不仅如此,在图像载世行道的过程中往往会引发历史性的转折。譬如米歇尔所谓的“图像战争”(war of images)正是基于“有图有真相”这一预设,对战双方都是依据图像来攻击对手,美国的布什总统发动战争的主要依据就是“9·11”袭击中世贸中心正在燃烧爆炸的图像,这也是战争合法性的有效视觉证据;而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则紧紧抓住美国士兵在阿布格拉监狱中的虐囚照片大做文章,其中的一幅俘虏张开双臂,手持两条接通电源的电线,这张照片公布后引起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并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战人权运动,同时也激发了公众对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重新审视。嗣后,美国苹果公司则根据这张照片发布了新产品消费广告,其中将受刑的俘虏替换为戴着耳机的ipod消费者,并借此表达了他们的反战立场。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图像已经逾越了形式主义的范畴而介入到当代纷繁复杂的文化政治和商业消费当中,成为现代生活中绕不开的话题。这些事例也告诫我们在具体的图像意识形态阐释实践中,要集中在深层次内涵解读上,要求对图像本身的审视愈加细致,并要和文化历史形成多重参证和相互呼应,唯此才能更加接近图像意义的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