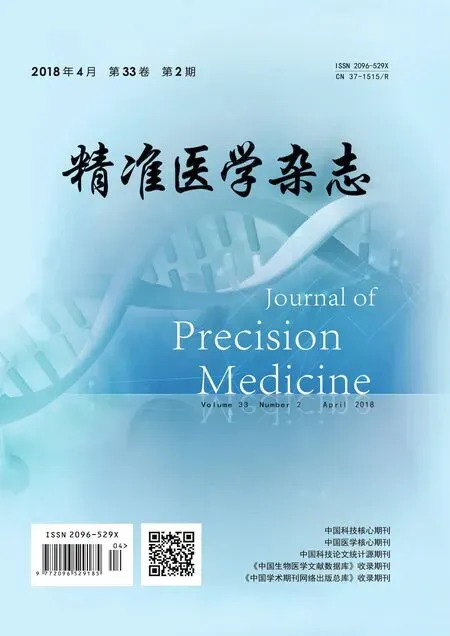病理学在精准医疗时代的发展
(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系,第三医院病理科,北京 100191)
随着后基因组时代的来临,高通量和高敏感性分析技术的兴起、与信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以及各种新兴技术向医学各领域的渗透,医学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新的医学模式不断地被提出和定义。个体化医疗以及最新的精准医学(Precision medicine),旨在通过分子组学为患者提供个性化和更有效的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手段。在肿瘤分子靶向治疗的推动下,分子病理学的诞生使病理学从单纯的疾病诊断延伸到临床治疗的全过程,重新定义了病理学在现代医学中基础研究与临床之间的桥梁作用,而同时传统病理学的诸多领域,包括解剖、组织、细胞以及超微病理在整合性(Integrative)、系统性(Systematic)、智能化、大数据化的指导下,正在经历学科的重新布局和改造,迎接精准病理学(Precision pathology)的建立。
1 传统病理向形态组学的发展
病理学,尤其是解剖病理学主要是形态学,即肉眼观察的大体病理或显微镜下的细胞/组织病理学,以及电子显微镜下的超微病理学。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以及各种新型成像技术的发展,形态组学(Morphomics,morphome)被提出:包括从传统放射、超声、磁共振,到大体器官改变的宏形态组(Macromorphome),到组织病理为核心的微形态组(Micromorphome),以及超高分辨显微技术和电子显微技术支持的纳米形态组(Nanomorphome),以接近连续的方式实现从器官、组织、细胞、亚细胞/细胞器以及分子水平的形态展示[1-2]。
目前,形态组学正在多个方面努力:首先通过关联显微技术(Correlative microscopy)实现不同观察尺度下视野一致;其次以超高分辨显微(Super-resolution microscopy)技术弥补光学显微镜到电子显微镜之间的由于光衍射限度所造成的分辨空白区域,即实现对亚细胞器、分子复合体或大分子的直接观察。尤其是超高分辨显微镜弥补了电子显微技术所缺乏的对多种分子、形态以及活细胞状态下的动态观察。目前超高分辨SIM、STED显微镜已经进入实验室,PALM/STORM技术已经有商品化的产品。另外,多重标记,或高通量的标记技术,如利用计算机技术辅助实现电子显微镜的多重标记,即以不同大小的胶体金颗粒、不同直径量子点以及不同存在形式(如膜结合、游离等状态)为区分的成像差异实现电子显微技术的多参数检测[3];或者新的质谱免疫组化 (MSIHC),即利用金属元素标记抗体,然后进行质谱分析,可以同时采用上百种抗体检测。较之荧光素,金属元素具有更好的光谱区分度[4-6]。新型生物成像技术,如组织透明 (Tissue clearing)技术不断涌现,可以实现无标记或无染色成像技术。同时,计算机辅助下的数字显微成像,可以实现不同图像之间的模拟转换,如荧光图像、明场图像、相差、HE图像之间的自由转换,为不同领域工作者提供不同的图像形式。
尤其重要的是,形态组学的发展将实现对疾病改变在不同观察层面的整合性认识,即从影像学到病理学,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集合观察。最近有学者将前列腺MRI图像与病理数字切片图像进行关联分析,实现对前列腺癌的分析。同时,也实现了图像与其内在分子改变的关联分析,即图像的功能化[2]。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揭示不同尺度下图像之间的有机联系。多模式成像(Multimodal imaging)的概念已经被提出,旨在利用放射、超声、光学镜、MRI图像,结合质谱、分子检测等技术获得有关疾病全面的形态及相关分子功能信息。
2 分子病理学的拓展
分子病理学是近十年来病理学的一个最具活力和最重要的发展领域,使病理学进入了肿瘤靶向治疗、个体化医疗或者精准医疗的领域。在新技术的不断引进和渗透下,分子病理学将会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发展。
2.1 单一分子靶点到分子组学
目前分析石蜡组织或者细胞学样本中HER2、C-KIT、PDGFRA、EGFR、BRAF、ALK、ROS1、VEGF、CD20、BCR-ABL等分子生物学改变已经成为常规的病理治疗靶点检测项目;而新的靶点正不断被鉴定[7]。通过对治疗靶点、分子分型、组织病理学分级及病理临床分期等方面的深入分析,病理学检查为确定肿瘤的分类及分层治疗提供了依据。然而,多数肿瘤分子分型,或者预后因素涉及多个基因改变,这既是驱动基因突变带来信号通路激活的结果,同时也是肿瘤普遍存在异质性的原因。另外,部分肿瘤会发生具有背景基因的突变,如目前已经明确的BRCA1/2、MMRs、P53、PTEN、RB等基因的突变。肿瘤组织学分级和临床分期也反映了基因改变的差异。因此,分子谱、分子组检测将成为必然。
尤其是近些年来,以二代测序技术(the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作为标志的高通量(High-throughput)检测技术的普及,标志着生命科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8-9]。二代测序、基因芯片、蛋白质组、代谢组、NanoString等高通量分子检测技术使生物医学研究可以大量分子同时检测,同时获得分子间功能调节的网络效应信息,因此生物医学进入了组学(-omics)时代,即包括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转录组学、外显子组学、微小RNA组学、代谢组学、表观遗传组学的全基因组分析(Whole Genome Analysis)的大数据时代。分子组学的兴起催生了生物学领域系统生物学(Systems Biology)的诞生。病理学界也提出建立系统病理学(Systems Pathology)这一新的方向:即基于病理形态变化,以新一代测序技术等高通量分析技术为基础,整合定性与定量、动态与静态信息,建立起具有连贯性的模式来阐明疾病、重复预测疾病过程以及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等[10]。
2.2 静态到动态,或诊断到全程监测
由于非侵入性检查理念和分子病理学的进展,以及高敏感性检测技术的诞生,如数字PCR技术、超深度二代测序技术等,病理学分析材料正不断从依赖活检、切除标本,向更多利用脱落细胞学和针吸细胞学,尤其是血液、尿液、脑脊液等体液分子的检测,即液体活检(Liquid biopsy)方面发展。尤其在肿瘤治疗过程中靶向分子的治疗反应、耐药性、继发突变确定,液体活检正在迅速开展,其检测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从循环肿瘤细胞(CTC)、循环肿瘤DNA(CTD)到最近确立的肿瘤外泌体(Exosome)、肿瘤修饰血小板(Tumor educated platelet)的检测,以及单细胞分析及相关技术也将是病理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期待被广泛应用于疾病的诊断、预后判断、治疗反应预测与疗效评估、甚至于疾病的易感性评估[11-12]。
2.3 分子检测与病理图像的整合
疾病通常涉及多种组织或者多种类型的细胞,即使肿瘤也通常由形态各异的肿瘤细胞排列成多种组织构象,其反映了疾病中细胞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肿瘤细胞分化程度、演进的差异等等。如何将分子改变与组织图像有机联系是一个当今正在发展的领域。一方面通过对于分子检测与图像的相关性进行海量的数据分析而实现。而另一方面,保留图像的原位分子分析技术同样是更容易理解的方式。与之相关的技术包括目前正在兴起的单细胞测序、组织原位高通量测序(in situ-NGS)、原位蛋白质组学或质谱图像技术(MSI)。无论是对大量数据分析,或是通过这些所谓原位技术的成果将促进分子病理学与传统病理学的融合,即分子组学与形态组学的融合,从而解决肿瘤异质性、肿瘤演进、致病基因突变与组织发生、分化途径的关系等肿瘤分子分型的依据等重要问题[13-14]。
3 从数字切片到计算病理学和智能化病理学
本世纪初,信息技术渗透到常规病理检查实践,产生了最初的远程显微镜(Remote microscope)以及虚拟切片(Virtual slide)技术,为病理图像交流提供了便利。经过多年发展, 全数字切片(WSI)得到实现,不仅运用于远程病理 (Telepathology)诊断,也正在逐步改变着病理诊断的工作模式。同时,包括语言、文字等多种方式的人机交流系统也进入病理诊断辅助系统[15]。
数字切片技术的发展使图像的定量分析成为了可能,即计算病理学(Computational pathology)逐渐兴起。无论是基于手工指导性特征(Handcrafted features)或是非指导性特征(Unsupervised feature)的定量分析都成为计算病理学的分析途径。目前基于全数字切片已经尝试应用于移植病理等常规病理学的定量化分析[16-17]。
计算病理学的发展使得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正进入病理学领域,以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或者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方式建立自动人工智能系统不仅可以实现计算机辅助诊断,即服务于病理医师的辅助诊断系统(SMILE),还可以实现诊断的客观性、均质化及标准化。目前,国际病理学会、相关学术机构以及有关企业正在利用深度学习开发智能化的图像分析与识别:如细胞核、病原体(结核杆菌)、淋巴结转移癌、癌细胞、肺癌类型的自动识别。不仅如此,进一步结合分子检测,将人工识别与分子病理学相结合,即实现病理图像功能化:图像与临床资料、分子检测一体化已经初见端倪。最近,有学者开发出FusionGP系统(2016),对乳腺癌采用数字图像与ER表达、基因表达谱、拷贝数变异相结合,预测患者化疗敏感性、临床预后与结局[18-19]。除此之外,更应该看到基于数字病理的人工智能化病理技术将为未来病理图像数据库的建立提供契机,实现“以图搜图”,即实现类似基因序列比对的图像比对(Image blast)。
4 病理大数据——精准医学的重要节点
分子组学的成果、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改变着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基于多种数据的挖掘、揭示其内部规律与联系的全新的大数据分析方式正在形成。近年来,提出了分子病理流行病学(MPE) 的概念[20]。其内涵在于建立一种从基因、疾病及社会、人文等因素三个主要方面探索疾病发生、治疗、转化规律的大数据分析模式。其中,可以预测包含形态组学、分子病理组学、信息以及智能化病理大数据系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病理大数据构建的核心内容。
5 总结
发展精准病理学将是当今生物医学时代的重要内容。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的发展,宏观与微观的图像技术有机结合,信息及智能技术的进步将推动病理宏观与微观领域的深入发展,实现各形态层次的整合,形态与功能的整合(形态组学与分子组学),病理与临床的整合,病理与社会、人文的整合,推动临床病理大数据与MPE的实现。
在精准病理学时代,病理诊断应当努力做到:①诊断的客观性、重复性、一致性;②疾病分类、分层;③疾病治疗的评估与新的治疗提示;④诊断到治疗全程监测;⑤新的疾病类型、疾病谱的认识;⑥从目前MDT的一员,到精准医疗网络的一员。病理学必须在生命科学与临床医学间寻找自身的发展坐标。不断吸收新的技术创新与生命科学新的发现,依据精准医学计划下各个领域带来的新模式,拓展病理学的内涵,找到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从而不断发挥生命科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作用,实现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精准病理学。
[参考文献]
[1] LUCOCQ J M, MAYHEW T M, SCHWAB Y, et al. Systems biology in 3D space--enter the morpheme[J]. Trends Cell Biol, 2015,25(2):59-64.
[2] MAYHEW T M, LUCOCQ J M. From gross anatomy to the nanomorphome: Stereological tools provide a paradigm for advancing research in quantitative morphomics[J]. J Anat, 2015,226(4):309-321.
[3] MAYHEW T M, LUCOCQ J M. Multiple-labelling immunoEM using different sizes of colloidal gol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test for differential distribution and colocalization in subcellular structures[J]. Histochem Cell Biol, 2011,135(3):317-326.
[4] LEVENSON R M, BOROWSKY A D, ANGELO M.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mass spectrometry for highly multiplexed cellular molecular imaging[J]. Lab Invest, 2015,95(4): 397-405.
[5] ANGELO M, BENDALL S C, FINCK R, et al. Multiplexed ion beam imaging of human breast tumors[J]. Nat Med. 2014, 20(4):436-442.
[6] GIESEN C, WANG H A, SCHAPIRO D, et al. Highly multiplexed imaging of tumor tissues with subcellular resolution by mass cytometry[J]. Nat Methods, 2014,11(4):417-422.
[7] DIETEL M. Molecular pathology: A requirement for precision medicine in cancer[J]. Oncol Res Treat, 2016,39(12):804-810.
[8] APARICIO A S, HUNTSMAN G D. Does massively parallel DNA resequencing signify the end of histopathology as we know it[J]? J Pathol, 2010,220: 307-315.
[9] MOCH H, BLANK R P, DIETE M, et al. Personalized cancer medicine and the future of pathology[J]. Virchows Arch, 2012,460: 3-8.
[10] ROSS S J. Next-generation pathology[J]. Am J Clin Pathol, 2011,135: 663-665.
[11] CHI K R. The tumour trail left in blood[J]. Nature, 2016,532(7598):269-271.
[12] HOFMAN P, POPPER H H. Pathologists and liquid biopsies: To be or not to be[J]? Virchows Arch, 2016,469(6):601-609.
[13] LONGUESPEE R, CASADONTE R, KRIEGSMANN M, et al. MALDI mass spectrometry imaging: A cutting-edge tool for fundamental and clinical histopathology[J]. Proteomics Clin Appl, 2016,10(7):701-719.
[14] LIU J, OUYANG Z. Mass spectrometry imaging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J]. Anal Bioanal Chem, 2013,405(17): 5645-5653.
[15] PARK S, PARWANI A V, ALLER R D, et al. The history of pathology informatics: A global perspective[J]. J Pathol Inform, 2013,4(4):7.
[16] ISSE K, LESNIAK A, GRAMA K, et al. Digital Transplantation Pathology: Combining whole slide imaging, multiplex staining and automated image analysis[J]. Am J Transplant, 2012,12: 27-37.
[17] AL-JANABI S, HUISMAN A, VAN DIEST P J. Digital patholog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J]. Histopathology, 2012,61(1):1-9.
[18] MADABHUSHI A, LEE G. Image analysis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digital patholog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J]. Med Image Anal, 2016,33:170-175.
[19] YE J J.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pathologists is not near--It is here: Description of a prototype that can transform how we practice pathology tomorrow[J]. Arch Pathol Lab Med, 2015,139(7): 929-935.
[20] HAMADA T, KEUM N, NISHIHARA R, et al. Molecular pathological epidemiology: New developing frontiers of big data science to study etiologies and pathogenesis[J]. J Gastroenterol, 2017,52(3): 265-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