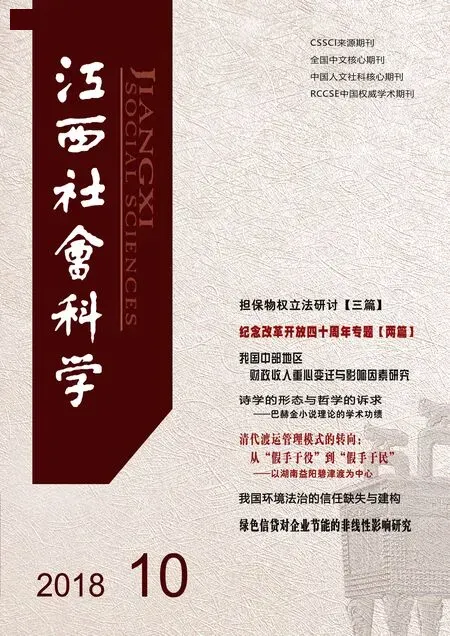有限的自主与统一:1906—1937年中国铁路运价权的构建
铁路运价权指铁路运价的制定、管理和监督实施的权力,它是运价管理体系构成的核心和先决,其归属对客货运价制度、运价政策和运价水平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近代,中国铁路运价权为外国资本集团和地方路局干涉至深,运价乱象丛生,为此历届铁路主管机构均试图构建自主与统一的运价权。对于该问题,学术界抱有一些偏见,忽视铁路主管机构为此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实效,比如陈晖在其《中国铁路问题》一书中认为:“试观中国的铁路运价机构,内容支离破碎,不要说毫无国民经济政策的精神,连统一的系统都感缺乏,甚且反实为主,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事事迎合外人意旨,适应外人利益。南满、中东、滇越等外人直接投资的铁路,其运价制定权几完全操纵于外人之手,用不着说满溢着经济侵略的精神,处处以适应其本国的经济利益为原则;就是所谓国有铁路的运价制定权,表面上虽全属中国,实则各债权国凭藉政治外交的优势,条约合同的曲解和滥用,常参与或干预各路运价制度的厘订,致事实上形成割据局面,而有‘协定运价’之诮。此种种乖谬的真相,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至深且巨。”①宓汝成也曾指出:“中国历届反动政府既被剥夺(或甘受其束缚)制定运价之权,铁路运价便任由控制这些铁路的帝国主义分子制定。”②对此,本文不拙浅陋,略作一二,以纠偏补正。
一、运价乱象之根源:运价权的旁落
1906—1937年,特别是晚清至北洋时期,中国铁路运价乱象丛生。首先,各路客货运价混乱,形式多样。晚清至民初,中国各路运价制度均移植于别国,其中沪宁、沪杭甬、京绥和道清等路以英国铁路运价为蓝本,京汉、正太和汴洛等路则挪移法国铁路运价模式,以至于“各路基本运价既各不同,而各等间之比率,全线段落之划分,递远递减之比率,与夫整车与零担间之比例,亦均彼此互异”[1](P323)。比如,在货物分等上多数路局分为4等,也有分为5等或6等;货物运价计费的单位里程和重量也很不一致,英资所系各路铁路运价有英里与华里之分、担和吨之分,而法资所涉各路则以法里为标准,并有零运和整车两种计量单位。其次,不公平运价普遍存在。主要体现在外国资本集团为所在国在华经营产业及外国货品提供优惠运价。比如,在早期中国铁路推行货物特价和专价优惠制度时,优先获得照拂的是具有外资背景的工矿业。京奉铁路,从1900年起就对渗入英国资本的开平煤矿所产煤品,给予降低运费的特价待遇。后来该线附近煤矿企业增多,它们都要求享有运煤特价的待遇,在此情形下1923年夏京奉路局又与开滦煤矿增签了一个专价合同,将运费再予削减,使开滦煤矿煤的运价特受优惠,“最为便宜”。[2](P184)相反,对于中国本土产业则不予运价优惠。第三,运价水平高昂。外国资本集团和地方路局,不是根据铁路运输成本和客货实际负担力为运价制定依据,而是根据铁路营利的需要。结果使得,1920年以来各路运价水平不断上涨,以津浦铁路为例,1921年该路6等货物基本运价率整车每吨每公里为0.01元[3],1924年较之前加价10.00%,1926年较1924年加价20.00%,1927年又较1926年提高30.00%,竟达0.01716元。[4](P2792-2793)
运价乱象的根源在于铁路运价权的旁落,即不自主和不统一。不自主表现为外国资本集团操控了中国铁路运价的管理权。晚清至民初,中国已建成运营的国有铁路包括京汉、正太、汴洛、津浦、沪宁、沪杭甬、胶济、道清、株萍和北宁等十条,这些铁路的经营管理权虽名为国有,实则清一色落到外国资本集团的手中,铁路运价权也不例外。京汉铁路为中国最早建筑的国有铁路,筑路期间比利时公司凭借债权人的地位,先后攫取设计、施工和行车权。据《平汉年鉴》记载:“光绪三十二年二月(1906),全路次第工竣,虽先后设置北路南路行车监督、黄河北岸南岸工程督办,然选材购料、行车管理多委之比公司,重要职务亦多由法比人充任,华员特坐拥监督节制之虚名而已。”[5](P11)当时,掌握全路大权的为法籍总工程师普意雅(G·Bouillard)[6](P693),下设的文案处、车务司务处、养路司务处、工务司务处及其下所属各机构,洋员众多且居要职。正太铁路是借法国公司资本修筑的,因此从筑路开始即为法国人掌控。1907年通车以后,正太铁路设立行车总管理处,置总工程司1名,下设车务、机务和工务三处及其他机构,中国政府派出的总办(监督局)名义是最高的管理机构,对管理处进行监督,但实际上从总管理处到各部门及各基层单位,正职都是由法国人担任。正太铁路的中国员司,除监督局长和各处副处长、总核算、材料委员等由主管机构任命外,对于其他的职员,监督局长只有提名的权力,都得经过法国总工程司同意才能调用,就连铁路上的一切往来行文,使用的也是法文。[7](P23)沪宁铁路早期也是洋人控制下的国有铁路,该路运营初期成立了总管理处,负责全路行车事务,总管理处有华洋高级职员共计5人,洋员占3名,英国人担任总管理处代表。1908年起英籍总工程司兼管理处总管(也称洋总管),为“本路员司之长”[8](P3090),权限最大,勘测选线、人事任命、购置设备和行车管理等均在其权限之内。除上述三路外,其他国有铁路包括运价在内的管理权也受制于外人。汴洛铁路为法国人操控,胶济和津浦铁路北端为德国人操控,英国人掌控的路权最多,除沪宁之外,还包括津浦铁路南端、北宁和道清等路。
不统一主要表现为地方路局拥有运价的自定权,且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近代时期,中国地方路局拥有运价的自定权,始于外国资本集团的操控。当时,由于中国政府尚未进行铁路管理和运营的实践,所以一切管理和运营制度悉数由外国资本集团的代理人制定,以至于各国有铁路均照外国资本集团所涉国的铁路管理制度制定各自的运价规章。比如,在京汉和正太两路,路局各依照法国模式制定《京汉北段行车运货价章》[9](P1233)和《正太铁路载客运货章程》[10](P76);在沪宁铁路,路局于光绪三十三年经该路议员会议议决,仿照英国蓝本制定客货运价规章[4](P3328-3329),同一时期的道清和株萍等路局也是如此。
这种业已形成的地方路局运价自定现象,在民初至国民政府初期,又因地方军阀势力的介入而更加突出,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地方势力为获取铁路收益,纷纷出手掠夺路局管理权。京汉铁路,在1920年至1926年间为直系军阀吴佩孚所控制,其心腹赵继贤长期被委派为该路局长。[9](P864)第二次直奉战争,吴失败后,该路管理权随之易主。1929年中原大战爆发后,该路管理权一分为三,铁道部仅能管理南段(武胜关以南),中段和北段则分别为冯玉祥和阎锡山所管辖。[11](P443)1930年奉系入关后,张学良曾一度抢得平汉铁路北段的管理权,北段正、副局长均由其委派担任。[5](P26)东北各路的管理权则长期掌控在奉系军阀手中,1924年奉系军阀设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东三省各路包括京奉铁路在内均由其管理。[12]1928年东北易帜后,东三省铁路管理权仍归于东北交通委员会(1929年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改组而来)经营管理。[13](P1-3)此外,正太和同蒲两路管理权在晋系军阀控制下,京绥铁路管理权则受制于西北军阀。
地方势力通过掠夺管理权,间接把持路局的运价权,使地方路局成为其利益的代理人。为满足其不断的财源需求,地方势力通过路局不断提高铁路客货运价,或者在客货运输中增加名目繁多的各项费用,实际也是变相地提高运价。20世纪30年代,地方势力对于地方路局管理权的侵凌仍在延续,以至于铁道部长顾孟余曾有过这样的抱怨:“铁道部名为管理全国铁道的机关,可是能完全管理的,全国中不知有几条铁道,就广东讲,广九、广三、广韶三条铁路,半年来就与铁道部脱离关系,营业情形如何,中央不得而知,用人情形如何,局长是谁,也不得而知,叫他们报告,他们不理,可是那三条铁道的外国债务,却要中央为之偿付的。次言湘鄂路,中央费了大半年的力量才派去一个局长,再其次说北宁路(北平至榆关),平绥路,这两路中央几全不能管,如整理营业、整理财务等,中央都不能过问。”[14](P18-19)
因此要消除运价乱象,构建自主和统一的运价权就成了铁路主管机构治理运价的核心目标。
二、自主与统一:运价权构建的目标
从清末开始,历届铁路主管机构均围绕构建自主与统一的运价权这一核心目标,进行两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通过赎路废约、裁汰洋员和取缔不公平运价收回外国资本集团对运价权的操控,取得运价权的自主。
赎路废约,就是通过归还借款、废除合同,收回铁路运价权。京汉铁路运价权落入比利时公司手中,主要凭借着1898年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和行车合同,合同规定:“由比公司选派妥人,将该路代为调度经理。”[15](P65)1907年,邮传部尚书陈璧主张通过赎路收回路权[9](P666),次年邮传部通过多种方式凑足赎路款交给比利时公司,1909年1月1日比方交出该路全部管理权[9](P685)。正太铁路因借俄、法资本集团的贷款,与之签订合同,而丧失铁路管理权。双方约定中国必须在借款合同满10年,即1911年之后,“无论何时可将借款全数还清,一经全数还清,所有合同即时作废”[16](P133)。但1911年之后,中国政权更迭,战乱不断,社会经济凋敝,国家财力不敷,根本无法筹集到还本之款,以至于正太路管理权一直掌控在法人之手。直至1932年3月,正太铁路借款才全部还清,1933年1月28日该路运价权得以收回。[17](P3)
裁汰洋员。赎路废约只是从合同层面取消外国资本集团对中国铁路运价的管理权,但在实际中许多路局均以洋员经营铁路,运价规制也多出于其手,这也影响到中国铁路运价权的自主。为此,铁路主管机构有意于逐渐裁汰洋员。在正太铁路,邮传部以“正太铁路事权牵制于借款公司之手,洋员恒居多数,失权糜款,窒碍殊深,亟应及时整顿,以免事权”为由,先后裁去洋员20余人。[18](P5-6)在京汉铁路,邮传部借1909年路权赎回之机,陆续裁汰包括总工程司在内高级职员13人,均以华人担任。[19](P180-181)“在中国收回铁路后,中国人逐渐替代了外国技术员。他们的数量从1904年的249名下降到1910年的91名和1913年的61名。”[20](P191)铁道部时期,裁汰洋员的决心和力度增强,一方面取消沪宁、沪杭甬、京奉等铁路总管理处,裁撤洋总管,逐步聘用中国职员,减少外国雇员。[21](P339)另一方面规定除保留由借款合同及办事规章所规定用洋人外,“其余普通洋员之任免,着与其余路员同样办理,未订合同者,不得再订,已订合同者,俟期满取消之”[22](P331)。通过裁汰,洋员人数下降明显,以沪宁沪杭甬路为例,1914年该路洋员54人,此后长期在40人以下,1929年后人数锐减至25人。[23](P2)
取缔不公平运价,包括规范特价专价和抵制“不实施差别运率”。一是规范货运特价专价。在外国资本集团的操控下,中国铁路运价是中外有别的,而这种有别并非国货享受更加优惠的运价,而是指外国货品及带有外资性质的工矿产品获得更多的特价专价优惠。为此,1923年交通部在第五次全国铁路运输会议上提出限制专价两项原则[24](P304),但最终没有执行。直到铁道部时期,铁路货物特价专价的适用原则才渐趋统一,1929年,铁道部召开货等运价委员会议议决适用专价特价原则六条。[25](P64-65)1931年,在铁道部召开的全国铁路商运会议和第八次全国铁路运输会议上,又重新议决货运特价原则七条。[26](P238)上述特价或专价原则,均以“扶值本国产业”和“奖励国产工业”为核心[27](P210-211),对于各路煤运价格,1931年商运会议特别声明:“国产煤斤运价,应根据各路运输成本,及各矿出煤成本销煤价格之最低可能范围为标准,在一路线上经营之煤矿,应一律平等待遇,不得因互惠情形减轻运价。”[28](P11)由是,20世纪30年代各路局工矿业、农产品特价专价,特别是铁路沿线华洋煤矿的煤品运价趋于一致。二是抵制“不实施差别运率”政策。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日、英等国为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将“不实施差别运率”写入《九国公约》[29](P377),并对《九国公约》第五款:“中国政府约定中国全国铁路不施行或许可何种待遇不公平”的内容进行蓄意曲解,抗议中国铁路在征收运费时区别中国货和外国货,要求中国铁路“不实施差别运率”。对此,交通部进行了坚决抵制,并致外交部转英、日等国,声明:“制定铁路运价,中国有完全主权。九国公约第五条平等待遇之规定,乃因中国门户开放及对外机会均等而发生,所谓不施行或许可何种不公平或歧视者,自系指中国承运各国间之货物而言,中国土货当然不包括在内。”[6](P786)铁道部时期,继续实行中外货物的“差别运率”,在1930年修订的货物分等表中仍区别国货和洋货,1931年召开的第八次全国运输会议上则将“货等区分中外”,“定为原则”。[30](P323)此后,铁道部迫于帝国主义压力,将中外货字样取消,改称普通和优等[31],但仍坚持中外有别的“差别运率”,将中国货列低等,进口货列高等。
第二,通过建立规章制度、筹办运输会议和货等运价委员会谋求对各路运价的统一。
一是建立规章制度。清末时期,针对地方路局乱发免票和随意减价,邮传部先于1906年拟订《铁路免价减价章程》5条[32](P439-440),后于1908年又重新拟订《铁路免价减价变通办法章程》8条[32](P1070-1071),规定:“所有各处局所若因公取免票,均向本部呈请才能发给。”[33]宣统元年(1909)邮传部收回京奉等路局的寻常免票权。[34]邮传部还要求,地方路局或地方督抚在变更运价时,也必须向邮传部备案,经其审批后方可施行。宣统三年九月,邮传部为谋得对路局运价的进一步监管,起草编定《路律·车务编》,涉及铁路运价计有七条[35](P1394),但《路律·车务编》尚未经资政院讨论,清政府即已土崩瓦解。北洋政府时期,交通部未能通过规制确立运价主导权,仅在1916年9月颁布的《交通部厅司分科章程》中规定路政司营业科具有“增减运价”的职责[36](P242-243),至于“增减运价”是审核监督,还是订立决定模糊不清。直至国民政府时期,铁道部在运价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才得以确立。1928年颁布的《国民政府铁道部组织法》规定,铁道部管理司(1929年改称业务司)为主管铁路运价的行政机构,负有“铁道运价之规定”的职权。[37](P3)《铁道部分掌事务章程》中则更具体规定业务司掌有“客货运价之规定及审核并修改增减各事项”的权力。1932年7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铁路立法——《铁道法》颁布,该法不仅确立铁道部对全国铁路的管理全权,针对铁路运输与运价其第11条规定:“铁道运价等第、联络运输或交互通车,除依法律规定外,应依铁道部所定之规章办理。”[38](P12-13)
二是筹办运输会议和货等运价委员会,谋求对各路运价的统一。1917年,交通部路政司营业科长黄赞熙以“本部直辖各路局同属国有,所有分等运价实未便任其自为风气,以妨碍营业之前途,自应及时改张以谋统一实行监督”为由,提议交通部牵头,集合各路局成立铁路交通运输会,由铁路交通运输会负责妥议一致铁路运输办法,再由各路渐次实施。[35](P1333)黄赞熙的提议得到交通部的认同,同年10月28日,交通部颁布《运输会议章程》,赋予交通运输会议“讨论铁路运输及附属运输各业务之改良统一及进行”[39](P1-2)的职责。1928年3月运输会议职责改为“谋各路客货运输之统一改良及进行”[40](P6)。运输会议职责的变化,说明交通部前期注重运输制度改良,后期注重运输制度统一,但都体现交通部试图以其收拢地方路局的运价权。1918—1928年,在交通部主持下,全国铁路运输会议共召开7次,1931—1935年,铁道部时期召开2次,其重要成果是制定并施行《客车运输通则》和《货车运输通则》,使部分运价制度在各路得到统一。
铁道部时期,曾在部中筹组货等运价委员会,其职责是就“旅客行李包裹等件之运费、运价及客车运输章程之制度”和“货物产销及市价情形、货物运价、货物分等及货车运输章程之制度”等运价问题,进行“调查”、“审订”,并向铁道部提供“建议”。因此,货等运价委员会是研究和咨询性质的智囊机构,但在实际中由于该委员会委员均是部、路高级职员,其关于运价制度的建议对铁道部的运价决策影响很大,是铁道部时期谋划运价统一的主要机构。在该委员会的主导下,1929年铁道部施行“整车”与“不满整车”两种运价计量单位[41](P27),制定货物特价与专价适用原则六条[25](P64-65),1930年统一平汉、平绥、陇海和津浦四路的旅客基本运价率为0.017元每人每公里。[42](P20-21)
另外,铁道部时期还召集临时性运输会议,与路、商各界进行协商和沟通,推动各路运价制度走向统一。诸如,1931年的全国铁路商运会议,以及1934年和1935年的第一、第二届联运运价研究会议。铁道部通过这些临时性会议,征询运价业务机构、各路局和商界人士及团体对铁路运价的意见,集中讨论,以谋各方都认可的运价制度,在“货等区分中外”“货物特别运价原则”[30](P341-342)及“改订联运运价递远递减办法”[43](P122)等方面达成一致。
三、运价权构建的结局:有限的自主与统一
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铁路主管机构在运价权构建方面取得了有限的自主与统一。
首先,运价权自主方面,结束了外国资本集团对中国国有铁路运价权的操控。铁路主管机构通过赎路废约和裁汰洋员收回包括京汉、正太、陇海和沪宁沪杭甬等在内的国有铁路运价管理权;通过取缔不公平运价,使外国资本所获得的特价专价优惠受到限制,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铁道部时期,在“扶值本国产业”和“民生主义”运价政策主导下,国货受到更多的特价和专价制度照拂。③针对英、日等国假借《九国公约》条款,提出中国货和外国货运费上“不实施差别运价率”的无理要求,北洋政府交通部与国民政府铁道部均坚决抵制,使帝国主义企图干预中国铁路运价的阴谋没有得逞,有力维护了中国铁路运价权的独立。
其次,运价权统一方面,颁布和实行客货运输通则,使国有铁路运价制度在诸多方面实现“划一”。比如,旅客运价制度方面包括:普通旅客票等分类制度,孩童免票及半价制度,定期票、回数票、国内周游票、学生团体票减价优惠办法,以及行李、包裹超出免费部分的运价办法等。货物运价制度方面则包括:货物分等制度,货物运价计量单位、起码重量规定,货物特价与专价的适用原则,货物“递远递减”的减价原则及联运货物运价递远递减办法。此外,铁路主管机构还统一了铁路运输成本的计算公式和方法,以及各路客货基本运价调整、特价及专价优惠和货物分等表更新的法定手续。
再次,自主与统一运价权格局初步形成。20世纪30年代中期形成的运价权新格局,是以部、路共同管理铁路运价权为基础的,在管理体制上呈现“两元”,铁道部业务司是国有铁路运价的最高管理机构[44],地方路局虽然机构设置比较复杂,但在1929年《铁道部直辖国有铁路管理局编制通则》颁布后,均以车务处(或称运输处)负责该路运价管理事务;在运价权分配上两者是“统分”结合,铁道部拥有对地方路局运价制度改变的审核和监督权,以及部、路都认可情况下修正和编印客货运输通则、货物分等表及其他运价制度的权力。地方路局则可以根据自身运输成本、有无竞争等差异,确定该路客货运输的基本运价率,可根据商旅的请求推行客货运输特价与专价办法,可根据路局自身情形确立“递远递减”率、区间段及距离等。
尽管在运价权新格局中,部、路两者共同管理运价权,但主导权在铁道部,且运价权有向铁道部集中的趋向。这在于,第一,铁道部凭借《铁道部组织法》和《铁道法》赋予的权力,在法律层面上拥有对铁路运价管理的全权,为其推行运价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第二,在实际运价管理中,铁道部通过召集全国铁路运输会议和设立货等运价委员会等方式,积极谋划铁路运价制度的统一,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甚至于各路原本牢牢控制的基本运价率也出现了松动,在北方四路(平汉、陇海、平绥和津浦)旅客基本运价率先实现了划一,这使得地方路局在运价管理方面的权力空间日渐缩小,相反铁道部的运价权得到扩张。第三,基于20世纪30年代巩固中央集权和应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需要,地方路局运价权向铁道部集中也是必然的趋向。
当然,至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铁路主管机构运价权离完全和真正的自主与统一尚有距离,只是有限的自主与统一。一是外国资本集团虽然丧失了对国有铁路运价权的操控,但其对国有铁路运价仍有一定影响,况且他们还始终把持着滇越、中东和南满等铁路的运价权;二是地方路局仍有一定的运价自主权,包括客货基本运价率,“递远递减”运价制度,以及特价专价优惠办法等在内的运价规制仍由各铁路局自行确定。这表明,外国资本集团和地方路局所代表的地方势力对于铁路运价权的染指是根深蒂固的,铁路主管机构要想完全实现运价权自主和统一,在近代政治动荡、中央势微、强邻环伺的环境中是根本做不到的。
尽管这个结局并不理想,但其对维护近代中国铁路运价权独立,促进运价制度改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其一,摆脱了外国资本集团对国有铁路运价管理权的操控,为实现近代中国铁路运价权的独立自主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二,改变了中国铁路运价制度原来混乱、繁杂和多样的乱象,使得铁路运价制度逐步走向统一。运价权的不独立、不自主,是近代中国铁路运价制度乱象的根源,随着铁路主管机构在运价话语权方面的逐渐增强,外国资本集团和地方路局在运价话语权上的不断减弱,铁路主管机关主导的运价制度在各路逐步实行,推动中国铁路运价制度渐趋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铁路运价权终于实现完全独立和自主,运价制度也随之实现完全统一。
其三,促进了近代铁路运价政策的调整,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外国资本集团和地方路局主导运价权时期,他们为掠夺铁路经济效益,施行“营利主义”④运价政策,在此运价政策主导下,铁路主管机构不断提高客货运价水平,以50公斤6等普通货物运价率为例,1921年至1932年平汉铁路从0.0015元上涨至0.004017037元[45](P41-54),津浦铁路从0.00085元涨至0.0012870元[46](P256-257),沪宁铁路则从0.00048元涨至0.001584元[27](P98),正太铁路从0.00167元涨至0.0022元[47](P303-306)。运价水平的不断上涨,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随着铁路主管机构运价权的增强,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铁路运价政策步入调整,“营利主义”政策被摒弃,以经济和民生为要旨的“民生主义”⑤政策得以广泛施行,各路局纷纷就“救济国煤”“复兴农村”和“移民实边”等推出了诸多运价优惠措施,比如在“国煤救济”方面,铁路主管机构采取包括“暂停各路煤斤加价”“重订煤运特价制度”“临时核减国煤运价”和“制定煤价回扣办法”等多项减低煤运价格的方略;在“农村复兴”方面,主要采取降低农产品货等和颁订农产品特价方案,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运输支持。
注释:
①陈晖:《中国铁路问题》,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95-96页。
②参见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 1847-1949》,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页。
③参见俞棪:《最近三年铁路减低运价述略》,《铁路月刊—津浦线》第5卷第10期,1935年10月31日,第11-25页。
④所谓“营利主义”即“认铁路为完全商业机关,以营业为前提,其运费之订定完全以本身事业发达得有余利为目的。至于社会经济、国民负担以及奖励各种工商业皆非所关心也”。参见章勃:《统制经济下之铁道运价政策》,《交通杂志·铁路运价问题专号》第2卷第2-3期合刊,1933年1月,第36-37页。
⑤所谓“民生主义”即“国家经营铁路,不以营利为目的,其要旨在便利交通,开发实业,以谋社会经济之发展,全国民众之福利”。参见韦以黻:《民生主义的铁路运价政策》,《交通杂志·铁路运价问题专号》第2卷第2-3期合刊,1933年1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