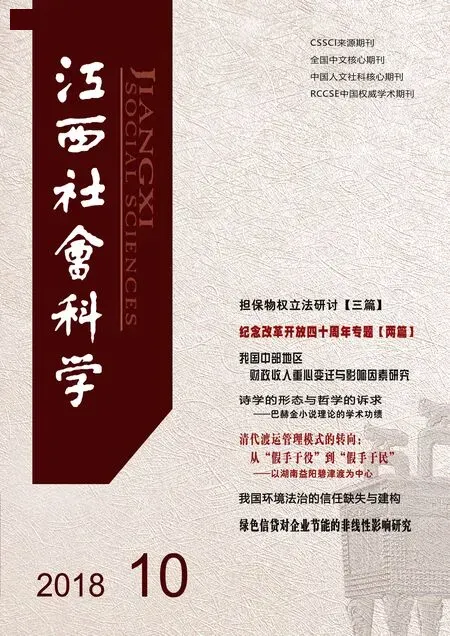女性文学传统与现代意识:希尔达·杜丽特尔的“感性”诗学
20世纪上半叶,英美诗坛新思潮迭起、流派纷涌。“意象派”诗歌即是现代诗歌演进中滋生的一朵奇葩。它几经嬗变,汇入“先锋实验派”的创作主流当中。尽管“意象派”有昙花一现之嫌,然而其创作理论中对“核心意象”的捕捉与塑造,对于表达的精炼性、浓缩性及音乐性的倡导极大地革新了诗歌创作的传统。
虽然学界一贯推崇庞德为“意象派”的创始人,然而他曾坦承对“意象”最初的认识和感受来自希尔达·杜丽特尔(Hilda Doolittle)几首以自然为题的小诗。尽管庞德自诩为杜丽特尔的导师和发现者,并将她的名字改成颇具“意象”色彩的“H.D.”,然而后者诗歌中独特的感性与想象并未引起以庞德为首的男性诗人的关注。[1](P243)不仅如此,庞德、艾略特、劳伦斯及威廉姆斯等人建立的男性诗歌的“智性”传统成为主宰现代诗坛的正典,长期左右着现代诗歌创作与评介。
男性诗人与多数评论者对杜丽特尔的评价反映出男性权威对文学史建构的影响。杜丽特尔、门罗、斯泰因等女性诗人的实验性诗歌无法进入现代诗歌正统之中,暴露了现代诗歌演变中的偏颇性观念:现代主义并非发源于女性诗人。[1](P233)由此,杜丽特尔建构在女性感性之上的诗歌探索或被男性诗人狭隘地归为“模仿男性现代诗人之作”[1](P234),或被简单地框定为“意象诗”,无法对其诗歌旨趣与文学创作理念进行公正评价和全面把握。
杜丽特尔的诗歌与诗学以女性独特体验为思维起点,以自然界生物的孕育为隐喻,提出从“爱域”到“想象域”再到精神世界的思维路径,形成其开创性的感性思维图景。从女性的爱欲、激情和孕育生命的身体“感性”出发,杜丽特尔发现了连接身体与意识及超意识的隐秘通道,颠覆了男性中心主导的理性传统及权威对美学、历史、艺术、精神等诸多问题的成见。
女性的生命体验贯穿杜丽特尔的自然诗,女性的视角善于发掘自然中的“爱欲”与“激情”,其与生命的神秘联结成就一种审美的感性秘仪。传统审美范畴中美的标准与偏见被打破,男性智性传统的狭隘规定性被解构。女性的爱欲及激情非但不应成为被男性权威压制、扭曲和迫害的借口,而应是成就女性力量的源泉,女性之美的根本所在。不仅如此,女性的生命力也是重审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另一入口。以女性生命之美为核心线索,通过重写海伦等经典女性形象,杜丽特尔不仅清算了男性历史书写对女性的认知与审美暴力,而且探索了女性历史书写的可能性。女性生命力构筑历史与文明发展的原动力,是高居在历史、文明之上的“无时间性”的“神谕”和“密码”[2](P13),跨越时空的限制,成为历史时间和个人命运的最终决定者。
杜丽特尔感性思想的核心为“水母体验”与“子宫想象”,两者的经典表达是:蓟与蛇。[3](P13)这一对偶的意象在象征层面上展现了女性的性本能、生育体验与“想象力”和“超意识”的密切关系。不仅如此,杜丽特尔还在上述意象基础上展开对艺术创作的独特构想:蓟象征认知并接受死亡、痛苦及绝望后的生命;蛇则意为将“生之痛楚”转化为“最高生命”之永恒。水母的体验代表由爱欲向超意识的转化,而蓟与蛇的关联意象则成为实现超意识、超越生命的荆棘之痛、通达艺术之境,从而获得美与重生的核心隐喻。
杜丽特尔的“感性”思想还体现在她对实现精神超越与拯救的探求当中。如何在个人创伤与人类浩劫当中仍能保持生命的激情、突破时空的限制、创造并传递某种超越性的永恒属性,是诗人历经磨难之后的精神诉求。女性之爱与艺术之美成为阻隔战争创伤和死亡阴影的屏障,突破悲苦的现实藩篱,实现精神拯救。
一、爱欲、激情与创伤:自然意象诗中的“感性秘仪”
对杜丽特尔来说,“意象诗”或“意象式”写作(imagistic writing)是一种编码和解码复杂感情与感性的方式,其目的并非单纯制造某种意象。杜丽特尔的自然意象运用具有连贯性,其意象诗大多通过对爱欲、激情与创伤的象征性呈现,表达对女性感性的关注与塑造。
在诗歌《俄瑞阿德》中,女性的爱欲与激情分别以“海浪”与“松锋”的意象出现,而尚未觉醒的身体官能仿佛“岩石”等待冲刷与撞击。[4](P395)诗中“海浪”象征的欲望一经出现便势头迅猛,它不再是流动无形、无法捕捉的液体,而是凝固成庞大的松锋、集结成森林,一次次以超乎想象的力量冲击、席卷着潜伏的感性与肉体,并最终“用其绿色松锋的”潮涌将我们淹没。[4](P395)爱欲神秘汹涌、变幻莫测、难以捕捉,而激情将其凝固成巨大而无法抗拒的具象力量,以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压迫与征服蒙昧的肉体。“翻滚、泼溅、席卷、覆盖”[4](P395),四个动词的连用仿佛模拟一次充满力感的性爱体验,而感觉迟钝的“我们”也经历了一次激情的洗礼、感情的启蒙。
全诗如同一次自然事件引发的感性仪式。诗中的俄瑞阿德是山岳女神,其神力召唤爱欲与激情的动态转换,实现对诗中人身心的激荡,完成了一次异乎寻常的感性启蒙。同时,她也是被召唤者队伍中的一员,诗中的“我们”意指所有等待觉醒的女性。在此仪式中,自然所代表的巨大生命力与女性的诸感官相通融、其巨大的能量使诗中人俯首称臣,不由得赞叹与崇拜此神秘的力量。自然之力变形为爱欲与激情,从而直达女性的身心,而激情对女性的俘获使后者仿佛经历一次宗教狂喜,在此巨大的愉悦中进入忘我的狂欢。有趣的是,只有在此忘我的激情中,“我们”才找到“自我”,获得某种从身体通向灵魂的“感性”。不仅如此,感性发出新的体察方式,突破寻常的认知,显现自然与人性的深层奥义。正如诗歌中奇妙意象的获得依赖于瞬间升华为想象力和艺术表达的感性,源于生命力与激情的感性是形成意识与思想的原动力。
如果说《俄瑞阿德》中的感性启蒙是在山岳女神的主宰与操控下完成的,《深潭》则展现女性身体意识的自主萌发与觉醒,并揭露在男性权威操控下女性身心遭受的奴役。诗歌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我”与“你”在想象层面的一场“对话”。“我”与“你”分别表征发展程度不同的女性感性:“我”为主导、操控性的,它具有自觉、自主、自发的特性,其生命意志与生命强力因此彰显;“你”则被动、迟钝、意向不明、缺乏生命活力。“我”对“你”的引导和激发通过一次象征意义上的激情鼓动实现:“我触碰你,你如海中之鱼颤抖不已。我用自觉的网将你覆盖。你现在是什么,禁锢之物?”[4](P395)“你”原来只是沉睡在感性深潭中的“爱欲之鱼”,“我”的激情促发和强力支配则达成某种“仪式”。混沌而蒙昧的爱欲被捕捉、在混乱中被赋予形状,在痛苦中达成自我认知。该诗中的感性仪式及其引发的认识并非愉快,而是伴随惊恐、疑虑、牺牲、自我否定的过程。然而,此过程是女性成熟的必经之路。从另一个角度看,“你”的无知、被动也暴露了男性话语和认知体系下女性欲望的边缘化。
在《海玫瑰》《海罗兰》《花园》中,杜丽特尔探讨了另一种感性仪式:经由创伤和绝境洗礼后升华的强韧之美。“玫瑰”“紫罗兰”等传统审美范畴中“娇艳、脆弱,仅供观赏的温室之花”被“命运之风”弃之于海边岸滩杂石、贝砾当中。[4](P397)它们“花瓣凌乱、颜色苍白、枯叶稀少”[4](P395)。命运的背弃、与同伴的分离和恶劣的环境使花朵的姿容凋零,但也催生了它的独立和坚韧。这一过程如同“毁灭而新生”的仪式,将脆弱与无力转换成力量,且散发出寻常花朵不曾有过的芬芳:“装饰性的玫瑰岂能如此将浓烈的香气镶嵌到枝叶里?”[4](P395)花朵与女性在象征层面上是同构的。尽管经历了创伤与摧残、危害与压制,获得独立感性的花朵(女性)之美具有依附型女性不具备的生命强力、独立意志和独特视角。在创伤中的自我成就形成特殊的感性仪式,其结果是卓越的生命体缔造的不凡美学:“罗兰:你绽放在沙山边缘,摇摇欲坠,但你捕捉光明—风霜,灿如火焰的星辰。”[4](P397)
这三首诗中的花朵意指经历苦难而获得独立意志、饱经沧桑历练之后的女性,她们拥有独立而独特的感性,无须借助“神”或他人的力量而完成自我建构的过程。在逆境中生发的生命强力形成坚不可摧的“美之力量”,足以撼动表面强悍的男性权威:“若我可以摧毁你(玫瑰),我就可以摧毁一棵树。”[4](P397)历经创伤而变得强大的力量来自女性内在的生命力:“若我可以激发搅动你(玫瑰),我的力量就可以折断一棵树,我就可以摧毁你。”[4](P397)
杜丽特尔通过颠覆男性审美传统对美之标准的界定,发掘了被边缘化的“美”,并揭示其中暗藏的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暴力认知与对待。自然意象在象征层面与女性同构,开辟自然诗中意象的巨大审美空间,展现意象诗独特的审美张力与批判精神。
二、女性生命力与历史重构:对希腊海伦的重写
杜丽特尔的作品中存在两类女性人物:第一类以海伦和大地母神为代表,第二类以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为标志。两类女性均为男性写就的历史、神话、宗教中被妖魔化的形象,暴露了男性权威对女性的文字暴力,也展现了女性历史书写的空白。在所谓的权威文献中,上述女性或是男性欲望的牺牲品、成为男性原罪的替罪羊,或是男权统治的工具、沦为失去本真的异化存在。
希腊海伦是杜丽特尔着力拯救和重塑的女性形象。在杜丽特尔的笔下,海伦虽在男性的历史与神话中被压制和误读,却以蓬勃的生命力和强悍的自我意识屹立于男性话语体系之外,以她独有的视角重审文明与历史的构成因素,以“爱欲”的“非时间性”与生命力的永恒性反思突破传统历史观,重写西方文明史。杜丽特尔对于希腊海伦的重塑主要通过两个作品:短诗《海伦》、长诗《希腊的海伦》,前者点明海伦悲剧命运源自男性对其生命力的仇恨和对其天然欲望的诋毁,后者则从女性视角、以神话重写的方式探求被男性历史书写遮盖的女性历史。
《海伦》一诗以悖论的形式揭示了两个被男性书写遮蔽的事实:第一,希腊对海伦的仇恨与妒忌来源于其生命之美:“整个希腊都在憎恶那张白皙面孔上平静的眼睛,她伫立时如橄榄油一般灵动滑润的姿容、她那双皎洁的玉手。”[4](P398)第二,海伦为宙斯与丽坦的女儿,宙斯的爱欲与丽坦的孕育能力结合的瞬间就开启了历史的神秘时刻。海伦作为强大生命力之美的化身,在孕育伊始便已参与到人类文明与历史进程当中。希腊人将海伦之美与对女性欲望和生命力的恐慌与仇恨对等起来(原诗中“希腊”指的是希腊城邦,即由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海伦的女性之美源于其勃发的生命力及其所引发的神秘诱惑力,而这恰是希腊人将男性欲望的原罪归咎于海伦的借口:“整个希腊却在敌视其苍白脸颊上的笑容,当回想其曾经的迷狂和厄运变得更为苍白时,希腊人的仇视有增无减。”[4](P398)
在诗歌的最后一节,诗人提出一种颇具女性主义和神秘色彩的历史观及文明观:在历史与文明建构中,男性往往担任暴力与欲望的主谋,而女性的生命力或许才是推动和改变历史及文明进程的根本动力。希腊人对海伦的“他者”化与对女性生命的否定互为因果,他们对海伦不可剥夺的神秘之美采取了亵渎和扼杀的态度:
希腊对上帝之女、爱之结晶无动于衷,
那拥有冰凉小脚和纤细脚踝的美人。
只有当她变成了一堆白骨埋葬在柏树之中,
希腊人才会爱她。[4](P398)
在诗人看来,海伦身上展现了历史的必然:神圣和神秘的爱欲成就了历史性时刻,而女性(丽坦和海伦)所展现的生命力和孕育力恰恰是成就历史的必由之路。在希腊人塑造的历史与神话中,海伦是文明悲剧的肇事者,是引发战争、导致混乱的元凶,而争夺海伦的男性却无人诟病。男性的暴力征服和强取豪夺似乎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女性的自然本性却成为男性欲望的牺牲品和替罪羊。诚如叶芝在“丽坦与天鹅”中所表明的:历史往往呈现为某种神秘的男性暴力(如:宙斯化身为天鹅,强暴了少女丽坦,后者由此怀上了海伦和另外三个孩子,埋下了之后希腊历史事件的伏笔)。女性在历史的创造中能力卓越,却被男性贬低为载体和工具。杜丽特尔利用女性独特的感性视角,修正了以往男性话语体系对女性历史作用的误读和异化,以女性为核心刻画了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另一副面孔。
《希腊的海伦》中的海伦已全然不是短诗《海伦》中缄默不语的“他者”或希腊神话中的“独语者”,而化身为文明、历史、宗教等诸多话语系统互文性文本中的探求者和解说人。[5](P2)在其爱恨情仇、颠沛流离的命运辗转中始终贯穿着海伦对于自己命运的追索、对于女性自我的建构和对于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别样认知。全诗以希腊海伦对于自身谜之命运的探求为线索,以海伦的精神成长作为贯穿整个叙事的动力,以其最终的“启蒙”作为故事的完结。虽前有希腊诗人斯特希克鲁斯和欧里庇德斯为海伦正名的作品为借鉴的范本,但《希腊的海伦》一反传统男性历史叙事的范式,跳出线性时空的窠臼,以超时空、超现实的叙事手法重新建构海伦的个人历史,并以此为基础重审、重构西方文明史。
《希腊的海伦》对真实的渴求旨在探索一种“无时间性的永恒”。“真实”与“无时间性的永恒”恰是杜丽特尔借助海伦的重塑探讨人类文明演进的初衷与目的。海伦是一个文明密码的“解语者”,在其身份与命运之谜的背面是男性历史对于某种“神谕”的恐慌与压制,而海伦的使命却是将此“神谕”解码再重新编码,以古老而崭新的面孔重启历史与文明之门。正如贺拉斯·格里高利(Horace Gregory)在其为《希腊的海伦》所做的序言所阐明的:杜丽特尔的揭示与其追求“真实”的诉求紧密相连,其在短暂的抒情时刻的流动与诗歌意象的塑造中唤起某种“无时间的永恒性”。[2](Pix)海伦作为杜丽特尔的代言人,在其前世今生的追忆中,跨越生死的界限与战争的硝烟,透视人类文明的又一真理。
在海伦的探寻和精神成长过程中,以海伦和海神(Thetis)为代表的女性生命力与生殖力形成了历史与文明发生、发展的原动力,这一相当于女性“感性”的“知识”便是受到男性话语历史性压制的“启蒙”。无论是海伦自己,还是与之建立关系的三位男性:阿喀琉斯、帕里斯、希修斯的命运起伏;也无论是人生的永恒主题“生与死”“爱与恨”,还是超验的“永恒”与“解脱”,都由爱欲与生命力决定其性质与走向。
海伦将女性的生命力及爱欲引发的巨大吸引力称为:爱之箭矢,而爱神恰是隐藏在所有历史事件和个人命运之后的最终决定者。海伦的自我探寻之旅便在揭示此凌驾于历史、文明、人性之上的永恒“密码”之中展开。海伦作为大地母神、海神的象征与化身,唤起人们对生命最深邃的尊崇和礼拜,这就是“海伦精神”或“希腊精神”的内核。海伦在诗中叹道:“身体为希腊神祇的主宿,然而它却是钢铁般的牢笼,上帝派我来将其计划向世人昭示,将世人成就成新人,挥洒上帝的荣光。”[2](P9-10)海伦所承载的神话和文明密码使其自身成为希腊悲剧和重写历史的核心象征。
在海伦与三位男性的关系模式中,男性权威的历史与文明观遭到女性感性认知的全面解构。海伦以卓越的生命力和爱之能力跨越历史的迷雾和文明的阻隔,也超越短暂的人类关系和历史事件,以爱与永恒生命的寻求探索构建人类历史与文明的永恒性。[6](P127)阿喀琉斯、帕里斯、希修斯等男性无不被海伦无与伦比的生命之美所吸引而卷入战争当中。男性所写就的历史是建立在欲望之上的争夺,以仇恨与死亡作为终结。无论是阿克琉斯还是帕里斯都成为男性历史的牺牲品,唯有希修斯彻悟了关于“爱、历史与历史的三重关系”,发现人类文明螺旋之梯的基塔为“爱”。他的认识恰恰是在男性排斥女性于历史之外而后的领悟。海伦作为前历史的爱与生命的象征,早在出生之前的某个神秘的时刻就为人类文明奠定爱的根基。她成为横亘在男性与历史“真实”之间的“鬼魅”,永远无法跨越,为男性所恐惧。
杜丽特尔通过对海伦形象的重写,不仅为海伦正名,而且颠覆男权话语体系中对女性参与历史构建的抹杀,以独特的女性“感性”,成就历史的又一维度,探索构建女性历史的可能。她对文明的反思是对男性历史书写传统的背离,引发读者对于文明的重审与反思。
三、思维与想象:超意识与艺术创造
杜丽特尔在1919年写作的《关于思维与想象的记录和智慧的萨福》一书(以下简称《关于思维与想象的记录》)是其“感性思想”的集中表达,也是其艺术论的巅峰之作。在此之前,女诗人经历了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历经情感背叛、痛失亲人、死亡威胁的杜丽特尔在挚友布莱尔的精心照料下安全诞下女儿,并且获得后者伴随终生的友情。杜丽特尔劫后余生的神奇经历与她特殊的生命体验幻化为其艺术论与诗学中的独特表达,正如阿尔伯特·盖尔皮(Albert Gelpi)为《关于思维与想象的记录》所做的序言中揭示的:杜丽特尔的生命图示定义了她的写作模式,她试图将其个人生活的创伤性及矛盾性与某种超验的启示相结合,以天堂般超越性的想象包容地狱般的黑暗体验。[3](P11)杜丽特尔的感性诗学和理念并非自下而上,由身体到灵魂单一走向的论说,而是包裹在生命体验、意识活动、超意识想象三维立体环绕当中的平衡与超越。
在《关于思维与想象的记录》一书中,杜丽特尔刻画了一对意象——蓟与蛇,描述了一个体验——水母体验,阐明了一组想象——子宫的想象、大脑的想象,提炼了一个意识——超意识。上述包含身体与精神、子宫与大脑、情感与思维、无意识和自我意识、男性与女性等诸多二元因素被诗人放在女性的生命体验中重构,消解其虚构的对立,形成关于生命意识与艺术想象的全新论说。
在杜丽特尔的意象话语体系中,“蓟”为了解并接受“生而必死”之真相后的生命状态以及由死亡之前景引发的此世生命的痛楚和绝望,它由“意识”所代表,所有与日常苦恼以及真实关系相伴而生的不幸和绝望均由“蓟”的意象所包含。“蓟”所代表的意识与“大脑的想象”相关联。[3](P39)与此相对照,“蛇”则象征死亡将“生之荆棘”转化为“最高生命”的可能性,即经由死亡而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提纯,变“生之苦”为“永恒”和“重生”,这便是杜丽特尔感性思维体系中的“超意识”。在杜丽特尔看来,超意识具有独特生命品性和超越性的艺术价值,而源自女性生命体验的“水母体验”更是从女性的视角探索身体与意识、超意识与艺术想象的话题,以迥异于男性的视野和逻辑构建其生命诗学和感性艺术论。
杜丽特尔将生命的呈现状态分为:身体、意识、超意识。[3](P17)而超意识的概念是诗人基于女性生命与生育体验提出的有关艺术发生学的核心理念。“超意识”本就寄寓于身体之中、潜伏在“爱域”之所、通过身体的“触角”激发头脑的想象力,从而形成艺术想象。超意识来源于身体的神秘萌动,与身体的创作力和“爱之感性”密切相关,通过大脑的意识传导,形成艺术与美的超意识塑造。“子宫想象”与“水母体验”均为杜丽特尔关于“身体—意识—超意识”这一感性艺术逻辑的象征性意象。在艺术家看来,伟大的艺术家皆为“超意识”型艺术家。其艺术创造的动力和卓越的艺术想象无不来源于身体内部的“超意识”萌动。正如杜丽特尔在描述自身的“超意识”体验所表明的当“水母(即超意识)”在体内涌动之时,我便有了子宫想象或“爱域想象”。[3](P20)
“超意识”催生的艺术想象首先是“爱的想象”。因此,理解“爱”并产生“爱”是理解和获得想象力的前提和基础。诸如弗罗吉奥、达·芬奇、苏格拉底等旷世奇才,其艺术想象的全部原则即为爱的原则。爱欲由美之外表或爱之对象所激发,它释放的能量会抵达头脑或意识,使后者形成“水母意识”或“爱的意识”。如同诗人感知到的身体内“水母”的涌动:“仿佛覆盖了大脑、前额以及部分眼睛的透明体,在固定的空间以固定的形态流动。此时,超意识便如透视镜,将整个想象的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3](P20)
在杜丽特尔对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评介中,更强化了“爱欲”与“超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的核心地位。萨福对于现代诗人的巨大影响来源于她所创立的“古老的抒情传统,其中女性的爱欲关系促使她们创作,并因此获得美感和创作的生机”。[7](P3)无论是想象力的获得、美的塑造和艺术感染力的形成及艺术品价值的呈现,由“爱域”而生的“爱欲”转化为触动欣赏者身心感性的“超意识”电波,被无条件地接收。
虽然杜丽特尔这一艺术论带有强烈的心理学和神秘主义的倾向,但无疑打开了理解现代诗学的又一扇大门。与爱欲共生的超意识诗学存在于每一个诗人的精神层面,深深植根于诗人未能表达或未被认识的情感当中。[7](P4)而女性对此种创作力的感知也来自男性文化及诗学对其创作力的压抑。在此意义上,杜丽特尔感性诗学与艺术论并立于由庞德、艾略特等男性诗人打造的智性传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诗歌的研究,并为后世女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诗歌创作道路。
四、囚禁与自由:女性之爱与艺术拯救
《围墙之内与我爱什么》是杜丽特尔的又一力作,收录其在“二战”被困伦敦时写就的短篇故事和诗歌作品。《围墙之内与我爱什么》是由《围墙》和《我爱什么》两个子集构成,两者共同形成总集的核心主题:如何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实现对人性的反思与信仰的重建,14篇看似独立的故事和三首长诗以哀而不伤的笔调讲述了伦敦平民在德国法西斯长达四年的围剿中摆脱死亡威胁、实现精神拯救的艰难历程。女性独有的细腻情感和观察视角使得杜丽特尔能够在惨淡和无望的死亡氛围中透视生命在重重威胁中焕发的不凡力量。
“围墙”既象征被德军围困伦敦、生命时时处于危机之中的生存境遇,又指身陷精神困顿的艺术家心灵的求索历程。伦敦作为现代文学的发源地和诸多美国现代作家崛起的重镇,也正经历着世界观与艺术理念的重大转折和裂变。逃避、绥靖甚至投靠纳粹的态度与做法在作家中也时有表现:弗吉尼亚·伍尔夫不堪忍受战争的残酷与混乱,选择投水自尽;以庞德为代表的极端主义男性诗人成为“可憎的小丑”,为包括杜丽特尔在内的现代诗人所唾弃;而另一些年轻的作家则斥责前辈现代诗人懦弱的“逃避主义”,认为他们不敢面对战争的现实,已被现代文学的新环境所抛弃。杜丽特尔选择留在其文学生涯的启蒙地伦敦,用生命的代价换取对“新艺术”的体验与塑造。
《围墙》收录的所有短篇都是以杜丽特尔和周遭的女性群体为原型的故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浩劫中,他们非但未被终日笼罩四周的死亡氛围震慑,反而超脱了狭隘的自我牢笼。女性以男性鲜有的情感、生命体验与艺术感性自建屏障,隔离了死亡对内心的摧残,筑就爱与艺术的内在壁垒,成为超越死亡恐慌的巨大力量。在“战前”“仓库”“逃避”“最后一天”“潮汐”等故事中,杜丽特尔以真实与虚妄的概念为时间坐标,以死亡与重生的意象为空间指向,达成由艺术的超越和爱的复苏为生命意义的终极拷问。无论是《逃避》中女主人公(即战时身处伦敦空袭和爆破危机中的作者本人),还是《战前》中写自传的“红玫瑰一般”的小女孩(杜丽特尔的女儿),抑或在废墟中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母亲遗留的艺术品的毕(杜丽特尔的挚友布莱尔),他们超越了生死的限制、以爱与对艺术之美的追求开拓比死亡威胁中的生存更“真实”的“存在”。[8](P116)
1943年4月,杜丽特尔的朋友斯特威尔发起了“著名诗人读诗会”,当时重要的现代诗人纷纷响应,杜丽特尔在会上朗读了她的新作《古老智慧群山回唱》,诗中的智慧女神吟唱着艺术与美的永恒价值,并发出拯救战后精神创伤的祈祷:
记住这些,
你说,
即使轰炸撼动他们的城市,
当狂飙与战火冲击他们脆弱的门楣,
不要遗忘美。[8](P80)
正如诗人在“圣诞树”一诗中写到的:
虽然琥珀已经给了别人,
雨燕也在别处安家,
钟表似乎停摆,
小猫也变成了幻梦和记忆。[8](P175-176)
他们构筑的美与艺术空间却成为永远的“庇护”,即使战争让我们“短暂眩晕和疯狂”,也只不过是“曾拜访了云层的某种空间”。女性之爱和艺术之美的联结,已经超越死亡对人类的戕害和捆绑,实现了超越肉身存在之外的信仰:“女性艺术家的想象凝结成回忆和幻梦,成为实现救赎的途径。”[9](P141)
五、结 语
英美现代诗歌作为现代文学的先锋表现,本就形态各异、难以框定。然而,男性权威写就的所谓“正典”长期禁锢并左右着对现代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介。杜丽特尔生于现代诗歌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但其作品与诗学中独特的“感性”传统却被极大地忽略和误解了,她也被当作昙花一现的“意象派”诗人鲜被诗歌研究者关注。事实上,她继承和重建的“感性”诗学不仅是自古希腊文学就已有之的厚重传统,更是透视人性本真和文学本质的不二法门。杜丽特尔的作品及诗学从女性感性的层面开辟了重审现代文学和现代文明的入口,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文学史和文学创作的定式和定论,为开启新的研究方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例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