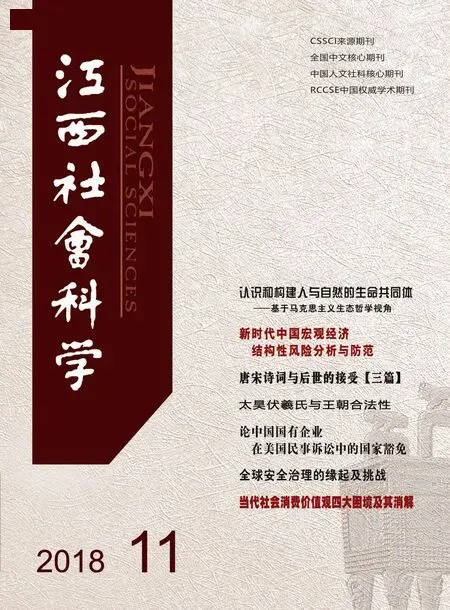建构与再接受:闻一多与当代唐诗文献学的形成
闻一多在唐诗文献学研究中,改变了古典形态唐诗文献学的研究方式,扩展了唐诗文献学的史料范围,给唐诗整理与研究特别是清编《全唐诗》的整理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以作家考证、作品甄辨、作品辑补为核心内容,采用史料爬梳、文献整理、文字训诂等文献考据的方法进行研究,建构了崭新的唐诗文献学学科体系。这种新的研究理路对当代阐释唐诗历史风貌与诗学艺术,对唐诗在新文化背景下的再接受都带来重大启发,也对当代唐诗文献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唐诗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闻一多的唐诗文献研究涉及作家生平考辨、唐诗选本的编纂、《全唐诗》的整理等方面。研究范围涵盖了唐诗文献学的各个领域,深入唐诗文献整理与研究领域的核心区域。他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学术视野确立了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唐诗文献学发展的基本路径,构建了当代唐诗文献学的学科框架,并为后人以新的视角接受唐诗带来了启发。他在唐诗文献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引起了当代学者的重视。1986年,傅璇琮发表《闻一多与唐诗研究》一文,全面介绍闻一多唐诗学研究的成果和特点,指出闻一多对唐诗的整理是基于对唐诗文献的爬梳和整理,但并未展开论述其唐诗文献学。21世纪初,陶敏 《闻一多与唐诗文献研究》《闻一多唐诗文献研究的学术史批评》二文,分别探讨了闻一多在清编《全唐诗》整理工作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全唐诗人小传》所取得的成就,但亦未对其唐诗文献学的整体成就及影响进行阐述。2003年,杨天保发表《闻一多整理唐代文献的一般思路及特色》一文,将研究对象定位于闻一多对唐代文献整理的总体考量,并未深入论述闻一多的唐诗文献学思想及成就。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拟对闻一多在唐诗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涉猎的文献范围、研究方法以及构建唐诗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尝试等方面进行探析,揭示他在唐诗文献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做出的重大贡献。
一、文献范围的扩大
传统形态的唐诗整理与研究所运用的文献资料范围较窄,一般包括唐人作品文本、正统史书、笔记小说及诗话等。王国维在评论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时曾批评清代以前“注玉溪诗者,仅求之于二书(按指新、旧《唐书》), 宜其于玉溪之志,多所扞格”[1](P4)。明末清初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唐诗文献学的史料范围,但也基本上不出上述各种文献之范畴。康熙、雍正年间,王琦撰写《李太白文集》,除上述文献外,还采用了《楚辞》《文选》等文学总集,《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地理志以及《初学记》《艺文类聚》《文苑英华》等类书。而清人所编唐人年谱,如:温汝适《张曲江年谱》、赵殿成《王右丞年谱》、汪立明《白香山年谱》、黄本骥《颜鲁公年谱》、朱鹤龄《杜工部年谱》、钱谦益《少陵先生年谱》、顾嗣立《昌黎先生年谱》,等等,所用文献范围也仅仅从两《唐书》扩展到了诗文集和部分诗话、笔记之中。直至清末民初,这种情况方有所改观。正如在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中所说的,此时的唐诗文献整理,在资料上“旁蒐远绍,博采唐人文集说部及金石”[1](P4)。在此基础上,闻一多从多领域进一步拓展了唐诗文献学的史料范围。
第一,闻一多扩大了唐诗整理与研究中可资利用的地理书范围。除两《唐书》中的《地理志》以及《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大型综合地理文献外,他还关注各种方志。唐宋以来的地方志质量良莠不齐,加之地方文献传播不广,因此治唐诗文献者大多不关注这些史料。但方志中本地先贤的生平史料、名家的诗文作品、文学典故的历史背景、地理名胜资料等记载,足以弥补史传、别集、总集、类书等文献的缺憾。近代以来,随着交通运输方式的进步,公共图书馆的普遍建立,为学者获取方志提供了便利。闻一多撰写《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时,除前辈学者常用的地理文献之外,还利用了《巩县志》《河南府志》《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志》等方志资料,为考证杜甫生平提供一些重要证据。如杜甫之籍贯,历代撰谱者皆引《旧唐书》本传,称自襄阳迁徙至河南巩县。而闻一多则考证说:
《河南府志》:“巩县东二里瑶湾,工部故里也。故巩城有康水去瑶湾二十里,与逸事合。”又曰:“康水,即康店南水。工部故里在瑶湾,去康店南二十里外。”[2](P39)
这一新材料的运用,为杜甫占籍巩县提供了新证据,更加准确地定位了杜甫故里在巩县的具体位置,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杜甫提供了文献支持。
在编纂《全唐诗人小传》时,他运用了更多的地方志材料。诸如《成都记》(薛稷传)、《雍录》(沈佺期传)、《长安志》(王翰传)、《嘉定镇江志》(张晕传)、《大清一统志》(祖咏传)、《南昌郡乘》(王季友传)等。这些方志记载了一些名声不甚显赫的中小作家,弥补了正统史传记载的不足,对纠正清编《全唐诗》诗人小传中存在疏漏、舛误、失考等问题具有极重要的价值。此外,他还从方志中寻求辑佚的资料,如从《漳州府志》所载《白石丁氏谱》中辑出了丁儒《归闲二十韵》一诗。
第二,闻一多在唐诗整理与研究中,大量利用石刻文献,尤其是刚出土的实物。除了利用常见的《金石录》《集古录》《广川书跋》《宝刻丛编》、《金石文字记》《古刻丛钞》《金石萃编》《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等石刻文献资料之外,闻一多还十分注意发掘新的金石文献。他在1933年曾致信饶孟侃说:
河南有新出土的唐碑务必请觅一张拓片寄给我。这类东西一到北京就贵了,所以我在这一方面没有下手工作。但我信如果得到这类的材料,我必能利用,充分的利用他。[3](P267)
20世纪30年代初,张钫曾在河南洛阳建立了千唐志斋。这一时点恰与闻一多此信件时间相近。显然,闻一多注意到了当时金石考古学的最新学术进展,十分渴望获得这些新出土碑志文献。
第三,闻一多重视类书、敦煌文献、海外文献、书画文献等材料的价值。闻一多认为类书在诗歌从六朝向唐诗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他在《类书与诗》一文中提出:“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4](P7)又说:“太宗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4](P9)因此,闻一多在开展唐诗文献整理工作时,十分重视从类书中发掘材料。他在《类书与诗》中列举了《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初学记》《玉藻琼林》《笔海》《文馆词林》《兔园册子》等十余种类书。对类书的重视,使他在进行唐诗选本《唐诗大系》的编纂时,有了不少新发现。如《全唐诗》卷5、卷6收录王勃《别薛华》一诗,历代王勃诗集刻本亦多作《别薛华》,闻一多则据《唐书·宰相世系表》与本集的《秋夜于绵州群官席别薛昇华序》一诗考证此处薛华疑为薛昇华,而《文苑英华》(卷286)中此诗题恰做《秋日别薛昇华》。
闻一多还从古代书画艺术类书籍中发掘唐诗文献。他在《全唐诗人小传》薛稷传中,引用了多种书画文献,如:唐人韦续的《续书品》《九品书》、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北宋人编纂的《宣和画谱》、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董逌的《广川书跋》,等等,内容较之《全唐诗》小传丰富了许多。如毕曜,《全唐诗》中其小传仅提及“官监察御史,与杜甫善”[5](P643),而闻一多则从颜真卿《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中发现该人曾任司经正字一职。
此外,闻一多还将研究视野投向海外汉籍文献。编《唐诗大系》时,他据《文苑英华》收入了王勃《圣泉宴》一诗,此诗传世诸本皆无序。闻一多乃据日藏卷子本《王子安集佚文》补入。在《全唐诗汇补》中,除了日本学者市河世宁的《全唐诗逸》之外,闻一多还充分利用日本人大江维时编纂于中国唐末五代时期的《千载佳句》,该文献成书较早,保存了不少诗歌的原始文本,是唐诗整理的珍贵资料。
从其《唐风楼捃录》所列举文献来看,闻一多在唐诗文献研究方面涉猎的文献甚至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所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涉及的范围,可以说,唐代唐诗文献学的史料范围在闻一多那里已经得以确立。另外,新史料的发掘,必将导致我们站在新的角度去重新认识作家、接受作品。
二、研究方法的新变与唐诗的再接受
面对浩如烟海的唐诗文献,闻一多总能不拘一格地运用各种方法分析文献材料来支撑其研究。他通过建立公式体系来检索唐诗的重出误收情况,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他在《〈全唐诗〉校读法举例》一文中,初步尝试了这一研究方法。他提出,《全唐诗》中存在“甲集附载乙集,其题下的署名并入题中,因而误为甲诗”[4](P467)这种普遍的错误现象。并以“钱起诗误入王维集”等五个误例证明了这一公式的合理性。这一研究方法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公式”二字并非我国传统学术体系中的词汇。闻一多大胆引入这一西方学术概念,将其嫁接入唐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性意识。后来,他的学生李嘉言在此基础上将《全唐诗》中存在的错误类型细化为七个公式。这七个公式成为当今学界对《全唐诗》重出误收情况进行考辨甄别的重要理论依据,为彻底解决《全唐诗》重出误收问题带来了希望。可以说,闻一多的公式法不仅使唐诗的甄辨工作产生了一次大的飞跃,更使唐诗文献学的方法超出传统考据学的范式,引发了一次研究方法的革命。
闻一多极重视对文献的掌握。为了全面挖掘存世唐诗文献里有价值的史料,他采用了“普查”这一最基本,也是最“笨”的手段。在文献普查过程中,闻一多不仅大量查阅唐宋以来的书目文献,还编纂了多个文献目录,列举出所能找到的所有文献,避免出现疏漏。众所周知,宋代是唐集得到系统整理刊刻的重要时期,后世流传的唐集几乎都源于宋人的整理本。宋人书目文献里的记载对梳理唐诗文献,尤其是别集、总集的刊刻、流传情况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诸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放翁题跋》等宋人书目文献还有宋人撰写的题跋、叙录。这些题跋、叙录中包含有大量作家事迹、诗歌甄辨的内容。不少史料为其他类型史料中所不见的,利用这些早期文献研究唐诗的原初面貌,其价值更加不可估量。他的《全唐诗人小传》凡遇到上述诸目已经著录的唐集,皆抄录原文。虽然《全唐诗人小传》并非成稿,我们无从考察闻一多将如何裁剪、处理这些文献,但这足以说明闻一多对书目文献的重视。
针对全面整理唐诗计划,他编纂了几个大型唐代文献目录:《见存唐人著述目录》(包括《本编所见丛书汇目》)《研究唐代用书目录举要》。在其未刊手稿中,还有《唐人遗书目录标注》《唐人九种名著叙论》等多种唐代文献的综合性目录,这些目录涵盖了传世的大部分唐代文史文献。利用这些大大小小的目录,即可按图索骥,爬梳其所需要的文献。在计算机检索技术出现之前,这一方法是史料搜集整理的最佳方法。民国至20世纪末期,不少学者都采用这一手段治唐诗文献,唐诗文献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大批目录索引,诸如《唐集叙录》《唐诗书录》《唐五代人物资料传记综合索引》《全唐诗诗句索引》(未刊)等。佟培基即据《全唐诗诗句索引》梳理出大量重出误收情况,完成了《全唐诗重出误收考》这一集大成之作。目录索引的编纂为学者的文献检索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为他们更深入挖掘新的唐诗文献史料提供了线索,推动了20世纪后半叶唐诗文献的研究。
闻一多还善于从新的角度去解析旧材料,让大家熟知的文献产生新的学术价值。比如在面对书画史料时,他不仅从中寻找文献资料作为考据材料,甚至还从这些史料出发,试图去阐释、还原作家性格、诗文内涵。他在《孟浩然》一文中引用张洎题写的王维画孟浩然像:
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4](P80)
从这一文字转述的孟浩然画像出发,闻一多从孟浩然诗歌中看到了诗人那种白袍布衣,“颀而长,峭而瘦”的形象,并由此推测出孟浩然的诗歌特点与人物形象的一致:
王士源应是和浩然很熟的人,不错,他在序文里用来开始介绍这位诗人的“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八字,与夫陶翰《送孟六入蜀序》所谓精朗奇素,无一不与画像的精神相合,也无一不与孟浩然的诗境一致。[4](P80)
这段文字的表述实质上反映了他对孟浩然的理解,可视为孟浩然接受史研究的一部分。在《全唐诗人小传》的《常建传》中,他也提到房从真所画的《常建冒雪入京图》,可惜《全唐诗人小传》未完能成,不知闻一多将如何利用这一资料展开研究。中国古代书画文献尚有不少存世,但迄今受到的重视仍然不够,闻一多这一方法应当对我们有所启发。
在研究形式上,闻一多的唐诗文献研究亦不拘于论文这一种形式,他最早有关唐诗的著述《李白之死》是一首现代诗。诗歌的内涵显然是用李白的悲剧人生来抒写大时代背景下,作者个人甚至那个时代众多诗人的孤独感。诗歌充满了感性色彩,并非严谨的论文,但闻一多将个人情感与李白诗句融为一体,突破了旧时代文人对李白及其诗歌的一贯认识,真实反映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诗人对李白及其诗歌的崭新认识,展现出当时人们对唐诗的一种崭新的接受形态。
闻一多在运用传统学术方法进行唐诗史料爬梳与考据的同时,敢于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的窠臼,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文献进行分析利用。其研究方法和裁剪史料的角度突破了唐诗文献整理的传统研究形态,更新了学界旧有的传统研究理念,促使唐诗文献学完成了从古典形态走向新形态的学术转型,也启发后人在一个新的视角中重新接受唐诗。
三、学科体系的建构
当代唐诗文献整理与研究包括三大基本内容,即作家生平事迹研究、作品辑补和作品辨证。在20世纪上半叶,闻一多已全面深入唐诗文献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在唐诗文献研究的三大核心板块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并确立了当代唐诗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唐代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证与研究是闻一多下手最早、用力最勤、成就最高的研究领域,对当代唐诗文献学的影响也最大。在现代诗《李白之死》和传记散文《杜甫》之后,他开始进行更具学术性的研究。《闻一多年谱长篇》称: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杜甫》传记发表于《新月》第一卷第六号。收《闻一多全集》。这是一篇只完成了一半的传记散文,试图给杜甫做一画像,它是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尝试之一,但此后没有接着写下去,而是着手去做杜甫的年谱会笺。[6](P372)
1930年4月,《杜少陵年谱会笺》发表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此后,他先后完成了《少陵先生交游考略》《岑嘉州系年考证》《岑嘉州交游事辑》等文章,对杜甫、岑参的生平事迹和交游情况进行了深入考证。这些研究得到了同时代学者的高度评价。朱自清即认为闻一多是唐诗考据家,其研究的视角集中在对诗人和诗歌中有关年代错误的考证上,并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证来改变人们对诗歌理解的认识。[6](P476)
1933年他曾致信饶孟侃说:“《全唐诗》作家小传最潦草,拟订其讹误,补其缺略。”显然他试图重订唐代所有诗人的传记。为此,他对唐代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用力甚勤,曾先后完成《唐诗人生卒年代考》《唐诗人登第年代考》等著作。其《全唐诗人小传》集中体现了他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就,虽然该著收录不足二百位诗人,且有不少作家的生平考证仅为材料的罗列,并未成文,其中甚至还存在一些考证的错误。但从他已经完成的部分较成熟的小传来看,无论是元代的《唐才子传》还是清代《全唐诗》的作者小传,都没有他的研究丰富、翔实。如果以学术史的眼光来看,闻一多研究的重要价值并不止于正确考证、完善这些作家的生平事迹,更在于通过这一研究提出了彻底整理唐代诗人生平事迹的学术构想,给当代唐诗文献研究带来了重要启发。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仍未实现先生整编全部唐代诗人传记的宏伟构想,但不少学者都曾投身到这一学术领域中,涌现出像《唐才子传校笺》《唐代诗人丛考》《全唐诗人名考》《全唐诗人名考证》这样一些优秀的研究著作。这一研究领域受到了当代唐诗文献学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并成为当代唐诗文献学学科体系的三大核心板块之一。
闻一多在诗歌辑补与考辨方面的研究对推动唐诗文献学的进步和学科体系的完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继市河世宁、孙望、王重民等学者之后所编的《全唐诗汇补》收录作家135人,《全唐诗续补》收录作家157人。两者相加,已经超越了前述诸位学者的成就,可谓晚近以来《全唐诗》辑补方面的集大成者。是陈尚君《全唐诗补编》成书前最为重要的著作。在唐诗考辨方面,闻一多的《全唐诗辩证》,对三百余首诗歌的真正作者、创作年代进行了考证。这一研究将自刘师培《全唐诗发微》开始的唐诗考辨工作推进了一大步。在佟培基的《全唐诗重出误收考》一书出现之前,闻一多对唐诗重出误收以及辨伪方面的研究是最为深入的。再加上他对作家的考据,闻一多的研究涉及了唐诗的整理与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并将各部分研究整合成了一个学科体系。
陶敏曾评价闻一多的唐诗研究,认为他打破了传统唐诗学研究孤立、封闭的研究局面,形成了综合性的、全方位的研究模式。[7](P157)这一论断同样可用来评价其唐诗文献学研究。唐诗文献领域三个核心内容的研究本就不应该是割裂的,他们能成为一个严密的学科体系是由学科本身的性质特点所决定的。但我们绝不能忽略闻一多对唐诗文献学学科体系形成过程中进行的勾连、捏合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把这三项研究围绕在《全唐诗》整编工作的周围。这使得这些研究有了一共同的目的,研究内容可以互相渗透,研究成果可以互相利用,避免了三者研究各自局限于自己狭小圈子的孤立局面。
闻一多这一研究思路,恰恰是当代唐诗文献学者公认的研究形态。这是一个包含作家生平考证、诗歌文字校勘、诗歌辑佚、笺注在内的完整的学科体系,可以说今天唐诗文献学学科所有的核心内容已经在闻一多手中建构完毕。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们都在围绕这个学科体系不断拓展唐诗文献学的研究领域。从学科建设上说,闻一多毫无疑问是当代唐诗文献学学科的奠基人。
四、结 语
闻一多在唐诗研究中,非常重视诗歌形成的背景。他提出了唐代“全面生活的诗化”。这一观点与当代学者龚鹏程在《唐代思潮》中所提出的唐代已经成为“文学化社会”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唐代的种种社会现实,作家的人生轨迹,包括科举、教育、政治关系在内的唐代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变迁等唐诗形成背景就得到了他的特别关注。他在各项唐诗文献研究中都非常重视文献史料的开掘与利用,大力拓展唐诗文献的史料范围,将新的研究方法与传统文献学方法相结合,极大的推动了唐诗文献学的发展,引领唐诗文献学从古典形态演进到现代形态,初步建立了现代唐诗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另一方面,将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学的生成联系起来,是迄今仍被人们所常用的一种诗歌阐释手段。这种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诗歌的接受方式,启发学者们从新的视角去重新理解诗歌的内涵。闻一多对新材料、新文献的重视和发掘始终在提醒我们,方法与材料的更新是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唐诗,开启唐诗文献研究新局面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