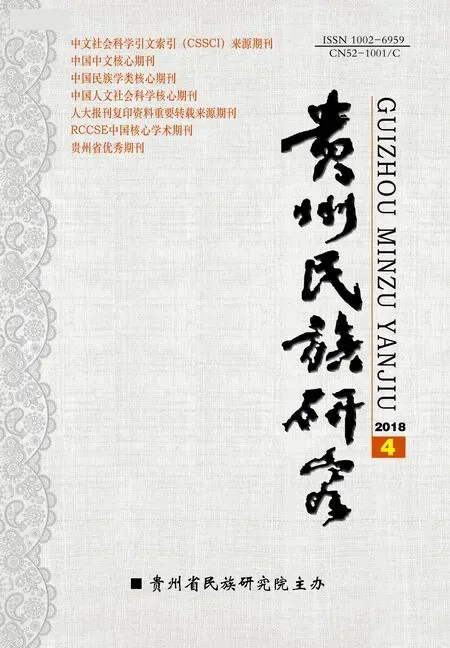清代索伦部族群演变溯源
黄彦震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系,陕西·西安 710100)
一、清代索伦部落族群的历史演变概况
“索伦”原是达斡尔人对鄂伦春人的称呼,明末清初时期,由于索伦人性情强悍,雄于诸部,其他民族往往也愿意借助索伦族的名气自壮,自称为索伦人,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所谓的“索伦部”实际上是对黑龙江地区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几个土著民族的合称。直到清代中后期,索伦人才成为鄂温克人的专称。索伦部与满洲人在语言、习俗、发源地等方面的诸多共通点,深得清政府的信任,加上很多索伦人在清朝进入满洲八旗成为满族人,最终促成了索伦人和满洲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两者血脉相连的紧密关系,当时清朝还专门成立了索伦营。在清朝掌控中原之后,满洲八旗的战斗力逐渐下降,一直效忠于清朝的索伦人由于其极强的战斗力成为清军平定内乱、开疆拓土的先锋部队,如平定西北准噶尔部、三藩之乱以及攻打大小金川、大小和卓等战斗中,都有索伦部叱咤疆场的身影。由于索伦人在清政府统治时期的重要影响,以及清政府对索伦部的倚重,索伦部成为清朝时期东北重要的民族部落群体。
民族融合一直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主题,在清朝时期,索伦部族群发生了重要变迁,虽然索伦部落分布地带和满洲的形成地辽东地区有较远的距离,但是在清朝历史发展过程中,原本分布于东北北部黑龙江地区的索伦部落和东北南部辽东地区的满族形成了密切关联,主要原因是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父子先后采取征服与招抚并用的手段,把大量索伦人迁入辽东,编入八旗之中,使索伦人直接参与了满洲民族的形成。后来由于清政府的东征西战,部分索伦人奉命迁徙伊犁,驻防卡伦,促成了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族三个东北世居民族在新疆地区的分布。因此从总体来说,索伦部落在清朝时期的发展经历了形成满族、分散迁居他乡,最后分化为新民族的演变过程。虽然索伦部族在清朝历史中有重要影响,但是学术界有关索伦部族的研究并不够深入,索伦部落的融合演变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历史融合的一个重要范式,蕴含着少数民族融合发展的共性规律,以古鉴今,其中相关问题的探究,对于当前民族问题的处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清代索伦部族群演变原因分析
清代索伦部落能够从多民族发展至部分融入满洲,最后能够以独立民族的姿态和满洲联合,一方面是由于建立清政权的满洲和当地民族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索伦民族和满洲各种共性特征,使得这些民族在思想意识上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意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清政府多样化的民族政策,使索伦人的生产生活和满洲人形成了深度交互,从不同方面加强了索伦部族和满洲的融入和亲近,另外,外敌入侵也在客观上强化了索伦部族和满洲的亲近关系。
(一)良好的民族共性基础
索伦部族能够由多个民族形成一个大的部落,并在后来部分融入满洲,是由于各民族之间本身在亲密地缘关系的同时还具有一些历史以来形成的民族共性基础,如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相同等,这为索伦部族的融合演变提供了现实基础。
首先,从索伦部和满洲的历史渊源来看,满洲的主体是女真族,是在此基础上和汉族、蒙古族等民众融合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而从女真族来看,其具有悠久历史,以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等部落民族为民族主源,而根据史料记载,肃慎族主要发源于黑龙江流域,因此可以说黑龙江流域也是满洲直系族系的发源地。而索伦部本身就是黑龙江流域杂居民族的总称,这种历史上的地理渊源使得索伦人和满洲人有了天然上的亲近感。因此在清朝扩充人口时,索伦人自然就成为其人口扩充的必然选择。在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从索伦部落征迁人口时就派人向索伦人宣谕“尔之先人,本是我一国之人”,并以此为名义,招抚俘获了大量索伦部落人员迁往辽东地区。[1](P39)
其次,东北大部分民族都信仰萨满教,萨满教也是索伦族和满洲人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少数民族重要的思想意识基础,索伦部族和满洲人在宗教信仰上的一致性,使得两者在思想意识深处有了达成共识的思想基础。
再次,在东北黑龙江流域,索伦部族是多民族的泛称,很多东北民族人以索伦人自称,这使得多民族之间在形式上形成了密切关系,这为民族之间的联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各民族形成了紧密的联姻关系,清代初期,满洲人同样通过联姻保持对索伦部落的羁縻关系。联姻关系使得索伦部族内部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基础,也为满洲和索伦人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最后,索伦部落和满洲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语言、习俗方面的共性。这一点从皇太极的话语中便可知,皇太极认为,黑龙江中上游地区民众与其国家民族语音一致,可以征用。而索伦部族本身的形成也是由于相互杂居的各个民族长期友好相处,互相吸收对方语言词汇,互相学说对方语言,从而使得各民族能够互相通晓语言,从而加强了各民族的沟通,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从形式上促进了部族内部形式上的统一。
(二)清政府得力的民族策略
索伦部族与满洲融合是清朝时期该部族历史演变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时期,索伦部族形成了其在历史的重大影响,同时满洲也由于对索伦部族的吸纳而极大地扩展了民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的民族政策策略对于这种民族融合现象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作用。[2]
1.军事征讨
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黑龙江流域的步伐。之后皇太极对黑龙江流域的三次进入,各有不同的效果。在天聪八年(1634年) 第一次进入黑龙江流域时,皇太极以语言相同为借口,使人宣称索伦部族原和满洲为一体,且已经计入史册,只是由于索伦部族不知而已,在军事力量的辅助下,索伦部族的巴尔达齐、博木博果尔等部族首领纷纷到满洲朝贡;在崇德四年(1639年),由于博木博果尔对满洲政权政治认同淡化,不再朝贡,皇太极派人对索伦部族开始第二次征讨,在民族意识兴起下,当时大部分索伦人开始对满洲政权进行反抗,索伦部因此被俘获了大量人口;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又派人征讨黑龙江流域的索伦部族,结果仍然是大量的索伦人被俘获。在不断的军事征讨中,一方面大量的索伦人被编入满洲名册,成为事实上的满洲人;另一方面,通过军事力量的震慑,进一步加强了索伦部族对满洲的政治认同。
2.朝贡赏赐
在清兵入关以前,由于后金政权对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征讨,从天命十一年(1626年) 包括索伦部族在内的黑龙江各部族都频繁到后金政权朝贡,同时索伦部也从清政权的赏赐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种朝贡关系的建立,实际上就意味着索伦部族对清政权的政治认同。朝贡赏赐可以看作是清政权军事征战的结果,这种结果反过来又促成了索伦部族和清政权关系的交流。无论这种朝贡赏赐关系的建立是自愿还是胁迫,都加强了索伦部族和清政权的联系和思想意识上的认同。
3.联姻策略
虽然在明朝时期,后金政权就开始了和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联姻,但是这种联姻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当时的后金政权军事力量不足。在清政权建立后,清政权多次以大臣之女和黑龙江地区的各个部族建立联姻关系。天聪十年(1636年),巴尔达齐与清朝建立了联姻关系。清政权和黑龙江各个流域部族的联姻,进一步加强了索伦部族等民族和清政权的血缘关系和交往程度。
4.编旗设佐
在清政权平定博木博果尔之后,满洲势力进入索伦部,索伦部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愿意接受招抚南迁的人群,另一部分人是留在江北的人员,对于前者,清政府对其编旗设佐进行管理,有的人直接进入满洲八旗,成为满洲人,也有的人被编入布哈特八旗和黑龙江驻防八旗,对于继续留在江北的人,则继续实施朝贡政策。这种对于不同部落的编旗制度主要是按照当时各部落对清政权的认同程度,巴尔达齐对于清政权的积极认同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因此对于该部族主要是以贡貂形式朝贡,而对于博穆博果尔主要采取编入索伦牛录和编入满洲八旗的方式。无论是编入索伦牛录,还是进入满洲八旗,很多索伦人在生活上都不断满洲化。另外不仅被俘获的索伦人被编入满洲八旗,清兵入关以后,清政府还在不断挑选索伦人入京。居住在京都的索伦人由于影响力弱小,和满洲人的边界逐渐淡化,以致最终消失,两个民族逐渐形成了融合。
可以说,在清政府军事、政治、文化各种政策手段的软硬兼施下,索伦部在有意无意中加强了与满洲人的联系,增进了对满洲文化的认同。
(三)共同抵御外敌
在清兵入关后,东北地区的边防逐渐空虚,沙俄趁虚进入,顺治六年(1649年),派出了以叶罗菲·哈巴罗夫为首的“远征队”,殖民者凭借武力,在攻占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的雅克萨城后,以此为据点,四处烧杀攻略。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入侵,从最初的几十人到上千人,从临时驻扎到建立永久城堡,侵略规模不断扩大,这给索伦部族带来巨大灾难,不仅使索伦人在物质上遭受极大损失,也通过各种方式践踏了索伦人的民族尊严。在危难时刻,赫哲人和朱舍里人派代表到宁古塔求援,清政府开始派出军队对殖民者进行反攻,最终使沙俄的远征军计划破产。为了帮助索伦部族,清政府一方面组织军事力量与沙俄殖民势力对抗,另一方面又伸出援手,帮助索伦人南迁至嫩江流域。虽然清政府的插手并没有从根本上断绝沙俄对东北地区的侵扰,但是与沙俄带来的破坏不同,清政府的援助给予了索伦人极大的精神安慰和物质帮助,拉近了满洲和索伦人的心理距离,两者的配合作战更是加强了两者之间的情感意识。而在南迁嫩江流域之后,索伦部族完全处于清政权的势力范围内,索伦人很快被纳入到清朝的管理体制中,满洲和索伦部由原来的羁縻关系转变为主属关系。
三、清朝时期索伦部族群演变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清朝时期索伦部落的民族融合演变过程中,经历了战争和民族迁徙诸多曲折,最终才形成了新的民族格局。民族融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索伦部族的融合演变对于当下的民族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一)文化认同是民族融合的基础
索伦部族和满洲的融合并不完全是政权统治者的外力强制,这一点在皇太极第一次进入黑龙江流域时便知,其利用相同的语言从思想意识上拉拢索伦部人,同时采取优待俘虏的政策,以同一族源来争取索伦人的文化认同,以文化上的认同奠定了政治认同的思想基础,也奠定了民族融合的意识前提,因此才有了部分索伦人自愿接受招抚、加入满洲共同体的结果。虽然在索伦部落的族群融合中,不乏武力、战争和利益驱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相同的文化基础为民族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3]
(二)民族政策影响民族发展走势
索伦部族本是多个民族的泛称,虽然这些民族相互往来、使用共同的语言,且形成了联姻关系,但是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并没有紧密融合在一起,只是名称上使用了一个统一的泛称,而在满洲进入索伦部落后,索伦部落就和满洲紧密融合,这主要得益于清政府正确有力的民族政策,无论是联姻还是编旗,都在一步步地以政策外力的方式推动索伦人向满洲人的意识和行为上的倾斜。因此可见,在民族融合发展历程中,民族融合大多是一个缓慢的长期过程,但是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外力的方式来推动这种融合进程,关键在于,必须要采取合适的政策才能促进民族融合的正向发展。
(三)共同利益是民族联合基础
索伦部从最初的外族,不仅融入满洲,且成为清政府可以倚重的军事力量,和清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推动有关,也和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渊源不无关系,但是这种实质性的融合、联合格局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索伦人和满洲人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形成了休戚相关的利益关系,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无论是沙俄入侵时,清政府对索伦部族的帮助,还是索伦营在清政府各种重要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两者实际上都是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点进行合作。因此,从民族融合来说,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方面的民族联合意识加强,最终的落脚点都在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上,只有寻求共同利益,才能使这种融合形成实质性的进展。
总之,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索伦部族在清朝时期形成从部族到民族、从异族到满洲的新民族发展格局。虽然从整体上来说,索伦部族的历史演变是由于国家历史发展潮流裹挟所致,但是能够形成民族融合、联合发展的结果,还有着具体的历史原因。只有从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来解读,才能抓住索伦部族历史演变的客观规律,最终在理解历史的同时也对当下民族问题的处理有更为清醒的认知。
[1]黄彦震.清代中期索伦部与满族关系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
[2]郭军连.清代招抚索伦部族入旗考论[J].满族研究,2013,(4).
[3]王娜,张小飞.大西南少数民族间的跨文化渗透与融合[J].贵州民族研究,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