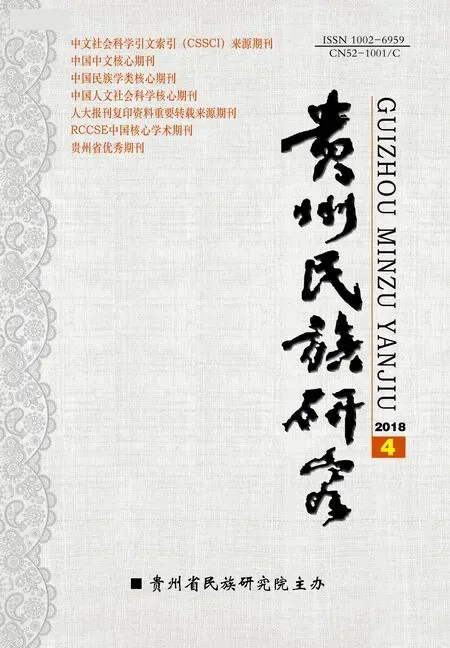新时代语境下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创新
鄢秀丽 戎龚停
(阜阳师范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安徽·阜阳 236041)
新时代语境下,外部音乐文化在与独特、鲜活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接触时,呈现出相互颉颃的面貌。由于历史原因,外部音乐文化在改变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环境的同时,以其强势的传播模式和传播速率引发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模式的变迁。相对于外部音乐文化作为异质文化,在接触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时,会引发其原有文化模式变化的这一涵化过程,包括文本化在内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自觉而非自发的传承,则多的是被动、抢救性质的保护,是面对飞速发展的技术手段与剧烈变迁的社会环境的一种抗御。本文试图通过厘清新时代语境下外部音乐文化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涵化及新时代语境下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对外部音乐文化冲击的抗御这个一体两面的传播过程及影响这个过程形成的因素,探索新时代语境下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传承与创新之道。
一、新时代语境下外部音乐文化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涵化
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语境下,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弘扬和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这其中不仅包括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由于独特性、少数性和异质性所面临的个别问题,还包括在面对外部音乐文化强势冲击时,由于通讯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所导致的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一)冲出封闭区:弥平区域传播隔阂的媒介传播
长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分布在崇山峻岭、高原低谷间,天然封闭的地理区隔造就了其文化艺术独特的形态、样貌和别有风情、自成一脉的形式。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作为少数民族文艺的最主要形式之一,承担着区域及族群内部情感交流、生活娱乐、宗教祭祀的重要作用,形塑和强化了少数民族内部的地缘感和亲缘感,并以其不仅融汇少数民族特色语言和特色内容,而且具有超语言、超民族表达的交流能力的优势,作为民族名片声传广远。可以说,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对内起到加强该民族内部个体对族群认同及少数民族人民对自身民族身份体认的作用;对外则起到塑造、介绍该民族的民族形象、民族性格的作用。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是民族生活情境的反映,是民族生活的重要研究素材。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封闭的地理环境都成为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存留和传承的天然屏障,在高山深谷中杂居或聚居于偏远边陲的少数民族,通过自然传播的方式保存和积累了大量颇有价值的原生态音乐。
然而,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地理上的区隔被迅速弥平,新媒体真正实现了麦克卢汉“地球村”的创想,外部音乐文化以不可一世的姿态无差别地随着电波流动投射到每个用户的终端上,作为强势文化的外部音乐文化挤占了原属于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注意力,同时随着信息总量的增加,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淘洗、保存和传袭纯粹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难度越来越大。这些珍贵而稀少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作品不仅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自然风化,在空间上也不再具有因封闭空间所形成的遗世独立的自然保护,甚至由于受众零和的注意力,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新时代语境下,媒介传播弥合了空间障碍,导致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难度不断提升。
(二)话语权刚需: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失根断流的巨大隐患
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所依赖的自然传承和自然传播不断被外部音乐文化侵蚀,如火般的攻势间,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保护已经由自发进入到自觉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文本化等工作在内的记录工程速度越来越赶不上其消失的速度,文本化项目工程、系统性的志书编纂作为一个个系统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原始形态仍在流失,面临后继无人、失根断流的窘境,其主要原因是无法有效利用媒介传播、教育传播等手段,桥接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日常化的传承、传播与项目化的保护工程与措施,这二者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使保护工作事倍功半,费力而不讨好。
教育传播为这种外部音乐文化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攻城略地,一律化、标准化的义务教育因目前条件所限而缺乏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少数民族适学龄儿童作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潜在传承者一旦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就开始脱离原来的语言环境与生活环境,学习普通话和西方音乐、现代流行音乐,这种系统化、程序化的义务教育使校园内的艺术教育在起到提升适学龄儿童音乐素质、音乐素养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却也异化为“遗产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可直言,僵硬的艺术教育导致了全民缺失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可能在艺术地位上失去话语权的警惕,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警钟不断鸣响,在新时代语境下,越来越刺耳的嗡鸣在催促和召唤学者和业者做出努力,从政策层面、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重视重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传承主动权和总体音乐评价体系话语权的问题,推动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创新发展。
二、新时代语境下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对外部音乐文化冲击的抗御
(一)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志书编纂
“盛世修史,明时修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程成为进入少数民族传统文艺形式与内容记录和保存的“后集成时代”的时间节点,至今的三十余年以来,不少学者一直笔耕不辍,致力于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积累采风,记录下了大量珍稀的优秀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本。这种自上而下展开的系统工程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上的优势,赶在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消失前先将其进行文本化,就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抢救意义上讲,对保存和传承难以为继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的这次大规模的音乐记录与保存工程,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对变迁中的中国的数字化和城市化的抗御过程。伴随通讯技术发展和社会变迁,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赖以为生的自然传播环境被破坏,传播形态被迫改变和延伸,学者和业者逐步意识到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传承需从自发到自觉,重整困境下传承创新的新思路。因此,无法否认的是,尽管在三十年来志书编纂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留下许多不可替代的成果,这次“后集成时代”的志书编纂工作,仍不可避免地带有越来越明显的抢救性,我们所得到的成果,正是迅速消逝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迅速退出历史现实的表征。
这种被动的抗御充满着衰弱的气息,尽管这种抗御是必要的,但却并非积极的,这提示我们,在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和保护中,还要另找新路。
(二)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元素参与外部音乐文化
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是否也尝试主动参与过同外部音乐文化的合作与竞争呢?事实上,就竞争层面来说,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相对于外部音乐文化作为弱势异质文化,并不具有竞争的量级,多数时候,尽管二者共同分享了受众的注意力,但由于其比重的悬殊,学者和业者也难以就竞争的角度来分析二者的关系。但许多业者却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参与外部音乐文化的合作频频尝试,这当然不仅是源于业者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的社会责任感,而且还源于当代外部音乐文化的商业性、多元性和包容性等特征,使其可以包容也愿意包容这些色彩鲜明、具有生命力的优秀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元素,许多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元素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特点被引入到流行音乐中,成为丰富流行音乐曲调和乐感的元素。长调和呼麦被音乐人发掘,加入到《歌手》等音乐竞演电视综艺节目中,在音乐真人秀中作为音乐元素和宣传元素双管齐下,起到了丰富节目内容的作用。
勾连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外部音乐文化的主要共同利益点其实仍是在于具有商业效益的媒介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歌手》等极具商业效益的媒介产品需要足够的传播力度,因此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元素作为看点被纳入了现代流行音乐中,在编曲风格一致、意境相协的作品中,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元素成为作品主体锦上添花的存在,但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所能主宰的部分相当有限,多是作为音乐元素参与到竞演节目中,因此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元素和作品背后的内容、思想、文化意涵均难以展现。简单来说,这个过程是现代流行音乐、外部音乐文化为主,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元素为用的过程,它的确使一些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元素被普通人所知,但力量非常有限,因为它背后的逻辑还是商业逻辑,于商业利益有用的部分就会被拿来,没有用的部分则会被摒弃,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作为参与者,事实上则缺乏话语权。
三、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传承与创新策略
(一)少数民族传统原生态音乐与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元素区别对待,分开保护
面对外部音乐文化强势东渐,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成为了当务之急。学者、业者对于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与面对市场时的态度分为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认为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保护最重要,少数民族音乐的特色和魅力就在于其原汁原味、独一无二的本来面貌。保持少数民族音乐原有乐器和语言演绎、原有曲调记录是少数民族音乐传承和保护的必由之路。即使加入创新,进行再创作时也绝对不能喧宾夺主,应该在保留其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进行较少的修饰,绝对不能盲目迎合流行与市场。另一派则认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保护和创新先要使其得到传承,无法使这些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声音声传广远,无法使更多的受众认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魅力,主动成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者,就无法进行下去。因此应该与市场达成和解,首先要推广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元素,使其具有传播力。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冲突,其实质和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上留存这些珍稀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内容。只不过一方的观点颇具精英眼光,充满了对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纯粹性的渴望;另一方则更现代、更圆融,更具传播者的视角,渴望桥接传播力与少数民族传统音乐。
笔者认为,现代的一些概念可以被引入到分析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保存及传承的思路中来,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也应当被“细分”。在学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志书编纂、文本修订的过程中,可根据该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功能进行辨别和分类,对于具有传播潜力的音乐元素,可以参照长调和呼麦,进行流行化推广。对于濒危的乐器、器乐、音乐文本、技巧等则要考虑早做记录,保持其原生态性。这二者怎么辨别?可以从功能等角度来区分,用于生活娱乐、表达感情的“娱人”类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一般来说更适宜大范围传播,主要功能用于宗教、祭祀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如傩戏则多形式肃穆、沉重庄严,气氛可能难以与现代流行音乐相适应,当然,这只是较粗略的辨别手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需要有经验的学者和业者进行深入和仔细的辨别与思考。
(二)注重技术传播,充分桥接新媒体与少数民族传统音乐
新媒体的参与的确弥平了外部音乐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播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区隔,致使强势文化的涵化效用进一步延展,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生存空间,带来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传播与发展的危机。但同时,新媒体使用的门槛广泛降低,这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新媒体具有声、视等多种表现形式,作为“人神经的延伸”相较于以往的传播形式而言具有无与伦比的表现力,在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传播中,这种丰富的表现形式可以用于在进行音乐表演本身时同步显示字幕、并配合专题记录、弹幕互动等方式推广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背后的文化意涵。此外,大数据可以抓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表演视频观看的基本数据及进度条拖动的情况,技术人员可通过搜集这些数据及时将受众的观看反应及时反馈给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学者和业者,在此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充分桥接新媒体与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实现传播闭环。
(三)依托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资源,加强战略部署
在制度层面和战略层面,我们已依托少数民族丰富优秀的传统音乐资源取得了一些成就。“支持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突出高等院校教学特色和民族文化传承”作为教育部在2007年制定的国家教育事业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的11个专题之一被纳入研究视域,标志着对于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国家级层面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纳入音乐教育体系,桥接志书编纂工作与教材编写工作成为当务之急。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就在编纂文艺集成志书,但是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编志书,仅仅将这些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本尘封起来就觉得完成任务,无异于让珍珠蒙尘,是资源的二次浪费,那么志书有何用、怎么用,就成为在推动经典传承工作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因地制宜地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开设艺术教育试点,依托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资源,同时使志书成为艺术教育试点教材的指导书目,将二者工作勾连起来,真正让志书活起来、动起来,同时为重塑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在艺术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积极准备。
总之,在新时代语境下,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实质上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在抗御外部音乐文化的冲击并利用外部音乐文化及传媒技术自我丰富、自我改革的过程。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需要学者和业者积极创新思路,在厘清当前问题的前提下,寻求解决之道,在开拓中谋发展。
[1]田元.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创新[J].贵州民族研究,2016,37(11):99-102.
[2]葛姝亚.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J].贵州民族研究,2014,35(12):68-71.
[3]李松,等.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反思——“第三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J].中国音乐学,2013,(1):12-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