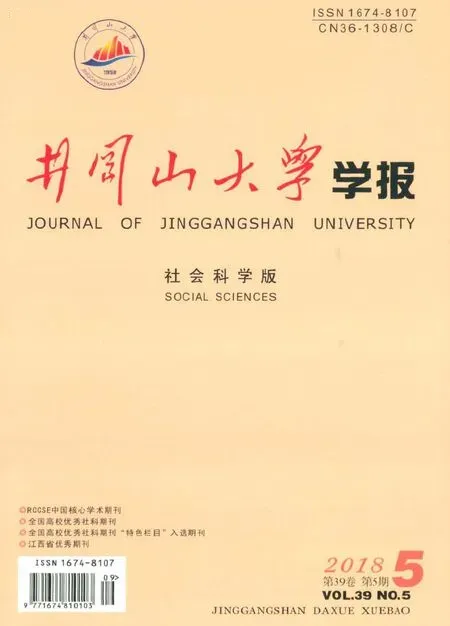论周必大的文学思想
李光生,李 旎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号省斋居士,江西庐陵人,是南宋孝宗朝名相、学者及文学家。绍兴二十一年(1151)登进士第,历仕高、孝、光、宁宗四朝,屡参机要,官拜左相,时称“周揆”,封益国公,以少傅致仕,卒谥文忠。作为文学家,周必大有“文中虎”[1](P466)之誉,又俨为当时文坛领袖。[2](P245-246)不仅如此,周必大的文学思想亦颇具卓识,对当时文坛风气的健康发展有促进之功。其评诗论文之语多散见于序跋中,虽不成体系,然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本文拟从文章功能说、理气说、才性论、文体观等四个维度对周必大的文学思想进行剖析,期能对其文学思想作出客观的定位。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文章功能说:观风教化与明道见性
周必大注重文章的政教功能。其《刘彦纯和陶诗后序》云:“歌诗之作,在国则系其风化,在人则系其性习,勤而不怨,忧而不困,以至泱泱乎沨沨乎之类,识者一闻遗音,不待入国,风化固已可知。”[3](本文所引俱依此本,后文仅标示卷数)周必大认为“歌诗之作”可观“风化”,观风俗民情和振纲纪人伦。“观风”说最早见于《礼记》,其《王制》篇云:“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4](P173)《汉书·艺文志》明确表述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5](P1708)汉儒阐释《诗经》,最大特点就是发明教化讽谏之义,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周必大以诗观风的认识,应该说带有传统儒家政教观的历史烙印。然另一方面,由于宋代士人普遍具有的忧患意识与淑世情怀,又远非汉儒的政教说所能拘囿,不仅蕴含着复兴儒家文化的时代精神,而且显示出士大夫对人生存在困境的自觉超越。
也因此,周必大强调文章政教功能的同时,也强调“明道见性”,重视道德规范与人格修养。其《跋严汝翼所藏张丞相诗》云:“……诗律清远,有乐道忧世之心;笔法妍楷,无震矜怠惰之容。观此忠献公气象略可想矣。”(卷一八)文章不仅要“忧世”,也要明道(“乐道”),还要见性(“无震矜怠惰之容”);而“性”成于道德,《傅忠肃公察文集序》中云:“乐至于乐则义精仁熟,和顺于道德而性成焉。”(卷五二)有德者其言自然清雅,“有德之人其辞雅,有才之人其辞丽,兼是二者,多贵而寿”。(卷二○《张彦正文集序》)周氏的这一言说,与孔子“有德者必有言”、欧阳修“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如出一辙,都强调作者的思想道德修养对于文章的决定性作用。
周必大强调道德对文章的作用,尤其强调“文行”。《临江军三孔文集序》云:
或疑文、行、忠、信之序,是不然。……居家孝悌,行己谨信,莅官敬,事上忠,其行美矣。……天下共称其文,号曰三孔。……虽曰存一二于千百,然读之者知为有德之言,而非雕篆之习也。……昔太史黄鲁直颂当时之人才,有曰“二苏联璧,三孔分鼎”。张丞相天觉在元符中诋元祐词臣,极其荒唐。谓两苏为狂率,则刚直也;谓公兄弟为阔疏,则高古也。夫鲁直于苏氏分兼师友,天觉于眉山心伏其能,皆以公兄弟配之,文行何如哉!(卷五三)
清江三孔(即: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在北宋以文知名于世,在新旧党争中因其蜀党殿军身份遭到新党张商英(字天觉)诋毁。周必大极力推崇三孔,认为其高古,不仅在文,更在行,是文品与人品相统一的典范。三孔之能“文行一致”,乃在于其文中之“道德”:“虽曰存一二于千百,然读之者知为有德之言。”周必大对“文行”问题的阐述,流露出对文人道德修养的重视。
关于文人道德修养的论述,早在六朝即已滥觞。但不论是魏文帝曹丕“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的历史考察,还是简文帝萧纲“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的双重标准,无不昭示着六朝文学批评家对“文人无行”的默认乃至提倡。潘岳望尘而拜的卑劣行为,不妨害他写出高情远韵的作品。[6](P138)唐人提出“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7](P4088-4089)的口号,在宋代才普遍得以实现,正如司马光《赵朝议文稿集序》中云:“玉蕴石而山木茂,珠居渊而岸草荣,皆物理自然,虽欲掩之,不可得也。 ”[8](P187)文品与人品相统一,成为宋人共识。唐季以来改朝换代的悲剧,不仅在于政治的失误,更在于道德的失范;靖康之乱的国破家亡,中兴恢复的乍暖还寒,亦有着道德失范的症结所在。周必大倡导“文行一致”,无疑蕴含着砥砺士风的深层动机。
周必大还对欧阳修“穷而后工”理论进行了重新诠释与补充。该理论源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尔后杜甫有“文章憎命达”之叹,白居易称“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韩愈亦云“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古代失志之士人怀不遇之才,忧思悲愤,进而兴于怨刺,以诗文鸣其不平。他们的境遇愈是穷顿,生活体验和现实感受就愈是深刻,发而为文,自然因思想深刻而易引起普遍共鸣。“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确实是许多优秀作家在创作上获得成就所走过的痛苦道路。周必大一方面承袭欧阳氏说,其《跋陆务观送其子龙赴吉州司理诗》中云:“吾友陆务观得李、杜之文章,居严、徐之侍从。……‘诗能穷人’之谤,一洗万古而空之。”(卷五一)另一方面,周必大又认为“诗不可以穷达论”。其《跋宋景文公墨迹》云:“柳子厚作司马、刺史词章,殆极其妙,后世益信‘穷人诗乃工’之说。常山景文公出藩入从,终身荣路,而述怀感事之作,径逼子厚。……殆未可以穷达论也。”(卷一六)说宋祁比肩柳宗元,未免稍嫌过誉,然认为仕途达者亦能成就好文章,却不无道理,这既是对欧阳修“穷而后工”理论的补充乃至反拨,亦是宋人对诗文功能的认识由政治关怀渐向道德心理层面倾斜的表征。
二、“理气说”:《宋文鉴序》的解读
出于对文章的政治和道德功能的要求,宋人常常作出政治方略和伦理问题的思辨,体现出月印万川的理性精神。在诗文理论方面,宋人在传统诗学的“志”、“情”之外,还特别尚“理”和重“气”。这在宋人著述中随处可见:
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为文者,无所复道;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9](P829)
善说诗者固不患其变,而患其不合于理,理苟在焉,虽其变无害也。[10](P99)
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此二子(按:孟子和司马迁)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11](P477)
周必大论文亦尚“理”,如云“文务体要,辞约而理尽”(卷五二)、“酷嗜吟咏,词赡而理到”(卷五三)、“其论思献纳皆达于理而切于事”(卷二○)之“义理”等;也重“气”,如云“友人杨廷秀学问文章独步斯世,至于立朝谔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当求之古人。真所谓浩然之气至刚至大,以直养而无害,塞于天地之间者”(卷一九)。不过,上述所论“理”、“气”俱为陈说,并无新见。周必大在作于淳熙六年(1179)的《宋文鉴序》中提出“气全理正”的“理气说”才是度越前辈时贤之处。序云:
臣闻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养而教务异习。故其气之盛也,如水载物,小大无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烛照物,幽隐无不通。……刚大之不充,而委靡之习胜;道德之不明,而非僻之说入。作之弗振也,索之易穷也。……时不否则不泰,道不晦则不显。天启艺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为事。……盖建隆、雍熙之间其文伟,咸平、景德之际其文博,天圣、明道之辞古,熙宁、元佑之辞达。虽体制互异,源流间出,而气全理正,其归则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汉之文也,实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皇帝陛下天纵将圣如夫子,焕乎文章如帝尧。万几余暇,犹玩意于众作,谓篇帙繁夥,难于遍览,思择有补治道者表而出之。……盖鱼跃于渊,气使之也;追琢其章,理贯之也。(卷一○四)
《宋文鉴》原名《皇朝文鉴》,是南宋孝宗朝吕祖谦奉旨编纂的一部北宋诗文总集。关于该书编选宗旨,叶适曾总结道:“合而论之,大抵欲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而不以区区虚文为主。 ”[12](P695)在序文中,周必大反复强调“理”与“气”,并以此作为文章的两个主要标准,认为上古之下包括汉唐文章在这两方面有所欠缺:“刚大之不充,而委靡之习胜;道德之不明,而非僻之说入”。出于宋人特有的自尊与自信,周必大分别对北宋建隆、雍熙,天圣、明道,咸平、景德,熙宁、元祐等不同时期不同文体的文章分别用“伟”“博”“古”“达”加以概括,认为“体制互异,源流间出,而气全理正,其归则同”。尤为重要的是,周必大认为上古之下的文章“理”、“气”无法兼擅根源在于“上之教化容有未至焉尔”。潜在之意是,北宋文章之能“气全理正”,是因为“上之教化”。周必大强调帝王治乱对于文运盛衰的决定作用,标榜赵氏受命之后,天下大治,教化兴隆,文运昌盛。也基于此,周必大认为《宋文鉴》编选的各类文体包括作为国家取士之源的律赋经义这类科举文体皆“有补治道”,可使孝宗追武祖宗的文治。
作为北宋诗文总集的序言,《宋文鉴序》乃奉旨而作,难免带有御用色彩,很大程度上也确实代表了南宋孝宗朝官方的文学观念。然而,时任翰林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周必大在南宋中兴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极力强调“理”与“气”,实乃当时政治形势和文坛状况的投影,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众所周知,恢复是当时国家最大的政治。面对这种形势,政治、军事措施之外,文坛上也应有足够的反映,既要有道德精神做支柱,又要有浩然之气鼓荡其中,以振作军心民气,“修我长矛,与子同仇”。当时文坛名曰中兴,实则气脉衰颓,正如陆游《陈长翁文集序》所云:“我宋更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帝受命中兴,虽艰难颠沛,文章独不少衰。……流落不偶者,娱忧纾愤,发为诗骚,视中原盛时,皆略可无愧,可谓盛矣。久而寝微,或以纤巧摘裂为文,或以卑陋俚俗为诗,后生或为之变而不自知。 ”[13](P2117)作为中兴时期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周必大的理气说,隐然寓含着对国家社稷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具有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理气问题本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朱熹在《答黄道夫》中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14](P2947)朱熹认为理气问题,其实就是宇宙观中的道器问题,这无疑是一种创见。只是朱熹并没有把理气之辨运用于文学理论的建构中。就文学批评角度言之,周必大首次把理气作为一个完整命题提出,客观上是宋代“尚理”说和“文气”说的统一,体现出全面圆通的文学识见。
在理与气关系上,周必大并无轩轾之分。这与尔后理学家的理气说迥然有别。如朱熹后学王柏在《题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后》中云:“学者要当以知道为先,养气为助。道苟明矣,而气不充,不过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气虽壮,亦邪气而已,虚气而已,否则客气而已,不可谓载道之文也!”[15](P143)王氏认为道是根本,气起着辅助作用。这无疑是朱熹在哲学领域中的理气之辨的文学翻版。元代吴澄、刘将孙俱持此论。如吴澄《东麓集序》云:“诗文以理为主、气为辅,是得其本矣。 ”[16](P6347)刘将孙《潭村西诗文序》云:“文以理为主,以气为辅。 ”[16](P7814)如果说王柏等人以道为本的理气说是典型的理学家文论,那么周必大理气并重的理气说则代表了政治家的文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三、才性论:“学”与“气”的突显
周必大“理气说”之“气”还涉及了创作主体个性问题。《杨谨仲诗集序》云:“文章有天分,有人力,而诗为甚。才高者语新,气和者韵胜,此天分也。学广则理畅,时习则句熟,此人力也。二者全则工,偏则不工。工则传,不工则不传,古今一也。”(卷五二)在周必大看来,文章风格与作家情性密不可分。文章的好坏与否(工与不工)决定于作家个性,即天分(才、气)与人力(学、习)。好的文章是天分与人力的结合,两者不可偏废。
很多时候,周必大特别拈出“气”与“学”以替代天分与人力作为作家个性的标志。《衫溪居士文集序》云:“……盖得于天者气和而心平,勉于己者学富而功深,故于所谓至难者既优为之,则其制诰有体,议论有源,铭志能叙事,偈颂多达理,固余事也。”(卷五四)作家心平气和,又能博学以致功力深厚,则文章“余事”而已。周必大在《王元渤洋右史文集序》中明确说道:“文章以学为车,以气为驭。车不攻,积中固败矣;气不盛,吾何以行之哉?”(卷二○)以学识喻车,即文章的工具材料,以气喻驾车者,即对材料的驾驭组织,两者相辅相成,文章自然水到渠成。
关于作家情性“才、气、学、习”之问题,南朝刘勰早有精辟之论:
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其心,其异如面。[17](P505)
刘勰认为文章风格决定于才、气、学、习。毋庸置疑,周必大“学气”说渊源于刘氏,然两人各有侧重。刘勰更强调才气,认为气是根本性的,是才能和志意的基础,所谓“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17](P506)、“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 虽美少功”[17](P615)。 周必大则更倾向于后天的“学”。如当世人称赞杨万里“天生辩才,得大自在”时,周必大极力强调杨氏的积学功夫,“由志学至从心,上规赓载之歌,刻意《风》、《雅》、《颂》之什,下逮左氏、庄、骚、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本朝,凡名人杰作,无不推求其词源,择用其句法,五十年之间,岁锻月炼,朝思夕维,然后大悟大彻,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夫岂一日之功哉”。(卷四九《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杨万里诗歌亲近自然,所谓“处处山川怕见君”,故活泼清新,号为诚斋体,然周必大却认为乃积学深厚所致,可谓独具慧眼。
周必大重视“学”,实乃宋人博学的时代风尚所致。宋人好学嗜学,“读书破万卷”已非少数学人的自我标榜,实为宋代整个士人阶层的真实写照。诗人要想名家,便不能不具备深厚的学问功底和学识修养。这种功底和修养也可通过行万里路而获得,但宋人更相信读书学问的奇效。赵蕃“江山真末助,学问本深基”可代表大多数宋人的观点,即读万卷书为根本,行万里路为枝末。苏轼批评孟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18](P308),就是指孟诗缺乏经典故事,虽有高情远韵,却才疏学浅。黄庭坚《论作诗文》亦云:“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 ”[19](P1684)要使“词意高胜”,就必须要有学问,必须精熟古书中的各种语言材料。就连“胸中无千百字书”的戴复古,也曾“搜猎点勘自周、汉至今大编短什、诡刻秘文、遗事瘦说,凡可资以为诗者,何啻数百千家”。[20](P322)也因此,“资书以为诗”乃至“以才学为诗”的旨趣,理所当然成为宋诗学的必然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及天分与人力时,多数宋人往往以“才”、“学”并举。如谢尧仁《张于湖先生集序》云:“文章有以天才胜,有以人力胜。出于人者,可勉也;出于天者,不可强也。 ”[21](P1)同样的理论命题,周必大却以“气”与“学”相对,这既与其“理气说”遥相呼应,也反映了“气”在其文学思想中的突出地位,体现出独到的文学识见。
四、文体观:诗文之辨与其他
周必大文才卓越,著作达八十一种,共200卷。四库馆臣云其“著作之富,自杨万里、陆游以外,未有能及之者。”“著作之富”不仅在于卷帙之浩繁,也在于文体之繁富。毫不夸张地说,周必大翰墨涵盖了当时的各种文体。一个作家能驾轻就熟地使用各种文体,前提应是对各类文体的特点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周必大对各种文体的观点在宋代颇具普遍性,尤其在诗文之辨这一问题上,抑或不够深刻,却体现了他在文体学领域的努力尝试。
中国古代的文体之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六朝的“文笔之辨”、唐人的“诗笔对举”及宋人的“文与诗对”。[22](P402)周必大对诗歌、散文这两种文体的区别有较为明确的认识。《朱新仲舍人文集序》云:
艺之至者不两能,故唐之诗人或略于文,兼之者杜牧之乎!苦心为诗,自其所长,至于议论切当世之务,制诰得王言之体,赋序碑记,未尝苟作。(卷五二)
在众多唐代作家中,周必大认为惟杜牧兼擅诗和文两种文体,“文”包括论、制诰、赋、序、碑、记等。抑或缘于序跋的局限,周必大对“文”这一文体的范围并没有详加划定。《送黄伯庸畴若序》亦云:
唐三百年间,文章钜公如韩、柳、刘、白及名世诸贤,诗文两极其至,学者不当置论。……古律诗用意高远,属辞清新,摹写物象,莫能遁形。杂文一编,持论正大,古赋恢宏,碑志详雅,四六温醇,是可争文士之衡矣。(卷五五)
“诗文两极其至”明确了诗文对举,此处的“文”包括杂论、古赋、碑志、四六等。在周必大看来,与诗对举的“文”范围很广,似乎除诗(包括词)以外的文学形式俱可纳入“文”的范围,但主要还是指实用文。《王致君司业文集序》云:“……议论驰骋于千百载之上,而究极利害于四方万里之远。其为歌诗,慷慨忧时,而比兴存焉。他文宏辨该贯,直欲措诸事业,所谓援古证今,黼黻其辞,特余事耳。”(卷五二)除了“歌诗”外的“他文”,要求“宏辨该贯,直欲措诸事业”。可见,与诗并举的文,多指经世致用的实用文。
周必大从创作角度认为诗歌是最难创作的一种文体。《衫溪居士文集序》云:“登文章之箓固难矣,诗于其中抑又艰哉。……古者造士以四术,教子于过庭,皆以诗为首。……盖得于天者气和而心平,勉于己者学富而功深,故于所谓至难者既优为之,则其制诰有体,议论有源,铭志能叙事,偈颂多达理,固余事也。”(卷五四)周必大认为诗是“至难者”,只要把诗写好,他文诸如制诰、铭志、偈颂等都只是“余事”。这种观点前人已有论及,如刘梦得云“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为诗”、司空图云“文之难而诗尤难”等等。应该承认,以创作角度来论诗文之辨,终究只是一种尝试。
就一般情况而言,诗文的表现对象不同。文更适合表达思想、议论,诗更适合于陶冶性情。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云:“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 ”[23](P763)明代王文禄《文脉》更明确地说:“文以载道,诗以陶性情,道在其中矣。 ”[24](P1693)宋诗在明代遭到普遍不满的原因之一,便是宋诗喜议论,未免越俎代庖,把文的对象当作诗的对象。这在周必大的论述中也有体现。周必大对诗文之辨虽有较为明确的认识,但并不反对诗歌的议论化倾向。《程洵尊德性斋小集序》云:“合古、律诗百余篇,记、序、书、铭各二,跋四,说一,志、表、行状、祭文、序事劄子五,启、表五十一。大抵议论正平,辞气和粹。”在周必大看来,诗歌像记、序、书等实用文体一样也可以发议论,“议论正平,辞气和粹”的诗也不失为好诗。这种观点既是宋人“以议论为诗”的创作倾向在文体观上的投影,也表明周必大并不认为“议论”是诗文之辨的根本要素。
周必大的文体观还表现在对笔记小说等文体的态度上。周必大认为笔记小说不入流,不能登大雅之堂, 原因在于难以取信,“多妄”、“荒唐”:“小说多妄,其来久矣”(《二老堂诗话》)、“小说难信如此”(《玉蕊辩证又跋》)。《题刘丞相沆追封衮公制》亦云:“……魏泰《东轩笔录》所记岁月序位存亡皆差谬,小说固难信也。”(卷一八)周必大认为笔记小说难以取信,固然体现了他作为学者求实严谨的治学精神,然从文学批评角度言之,也透露出其正统保守的文体观念。
五、余论
周必大重视文章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强调政治教化,另一方面强调明道见性。这其实是儒家“內圣外王”政治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体现了周必大作为政治家要求政治与道德的融合统一。周必大“气全理正”的理气说,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南宋中兴时期官方的文学思想,具有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就文学批评角度言之,周必大的理气说可视为宋代“尚理”说和“文气”说的融合统一。在“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周必大的理气说与理学家的理气说迥然有别。在创作主体个性问题上,周必大以“气”、“学”并举,迥异于宋人的“才”、“学”相对,对“气”的强调,既与“理气说”遥相呼应,也是其独到的文学识见的体现。在文体观问题上,周必大的诗文之辨时有精辟之见,然对笔记小说等文体流露轻视之意,这反映出周必大作为严谨求实的学者正统保守的文体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