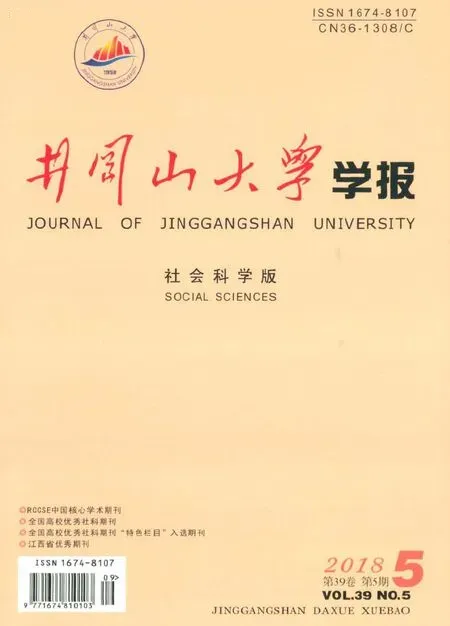文学语境中的《威克利夫圣经》300年学术史研究与反思
王任傅
(黄山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公元596年罗马教皇格雷戈里(Gregory)派遣奥古斯丁(Augustine)向英吉利人宣讲圣经,从那时起英国便逐渐地成为基督教社会[1](P61)。然而直到14世纪上半叶,英国教会和神职人员所使用的圣经版本一直是罗马教廷所规定的权威拉丁文译本(the Vulgate),而用英语所书写的圣经仅见于个别章节的翻译。由于大部分英国普通民众对拉丁语所知甚少,因此圣经长期掌握在少数教会人员的手里,他们也由此掌控了基督教的全部话语权。事实上,语言成为罗马教会控制世界的工具[2](P18)。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及其门徒于14世纪末第一次将基督教的圣经完整地翻译成了英语。他们的译本被称为《罗拉德圣经》(the Lollard Bible)或 《威克利夫圣经》①《威克利夫圣经》包括早期(the Earlier Version)和后期(the Later Version)两个译本。人们通常所指的是它的后期译本,这也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the Wycliffite Bible)。这次翻译成为英国宗教史与英语语言文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3](P17)。 直到16世纪晚期,仍然有人在阅读《威克利夫圣经》的前后两个译本[4](P193)。
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英译本圣经,《威克利夫圣经》不仅将整本圣经用日常语言呈现给英国人,它实际上也确立了英语本身的地位,并将英国人的思想和英国文学纳入了圣经的轨道[5](P144)。胡适曾评论说,威克利夫将基督教的《旧约》(the Old Testament) 和 《新约》(the New Testament)译成了英国的“中部土话”,该译本连同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诗歌“把这‘中部土话’变成英国的标准国语”。后来随着莎士比亚和无数文学大家都用国语创造文学,这一部分的中部土话“几乎竟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语了! ”[6](P45)的确,《威克利夫圣经》后期译本尽量采用当时流行的英语方言,文字浅显流畅、通俗易懂,“为英国民族语言的统一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7](P65)。 不 仅 如此,该译本在语言表达和散文风格上也达到了一定的文学高度,其成就堪与乔叟的诗歌相媲美[8](P27)。 可以说,《威克利夫圣经》与诗人乔叟的作品共同开启了英语文学的新纪元[9]。
然而,尽管《威克利夫圣经》在英语语言和英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该译本文学史价值的梳理与研究还很不充分。在已有的研究中,早期学者大多是将《威克利夫圣经》作为威克利夫神学思想及宗教改革理念的一项成果而加以论及。进入20世纪以后,学术界对威克利夫及其圣经给予了更多的重视,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威克利夫圣经》的研究,但仅就该译本文学史意义展开探讨的专著仍暂付阙如。
一、20世纪之前的 《威克利夫圣经》研究
早在16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福克斯(John Foxe) 在其著作 《殉道史》(Foxe’s Book of Martyrs,1563)①这部作品本名《丰功与伟绩》(Actes and Monuments),但通常被人们称为《殉道史》,最初于1559年用拉丁语写成。中就谈到了威克利夫对圣经的翻译。福克斯指出:“在他为改革英国教会所做的所有努力当中,威克利夫最为看重的就是把圣经翻译成英国人民的共同语言,并使之为大众所普遍使用。 ”[10](P323)不过,严格说来,专门针对威克利夫及其圣经展开的学术研究最早出现在18世纪初。1719 年,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出版了专著《可敬而博学的约翰·威克利夫生平及受难史》(The History of the Life&Sufferings of the Reverend&Learned John Wiclif)。书中,刘易斯充分肯定了圣经翻译在威克利夫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价值。在他看来,威克利夫对天主教会“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与别人一道将圣经翻译成了英语”[11](P83)。
继刘易斯之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该领域没有出现其他重要的研究成果。直到1828年罗伯特·沃恩(Robert Vaughan)出版了《约翰·威克利夫的生平与主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John de Wycliffe),并于 1853 年以《威克利夫专论》(John de Wycliffe:a Monograph)之名对研究内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在《威克利夫专论》中,沃恩以独立的章节讨论了“威克利夫与英语圣经”。沃恩提出,威克利夫晚年一直思考的就是基督教与圣经的关系。威克利夫看到,从人民的手中拿走圣经就是拿走了光明,因此他立志为英国人提供完整的以母语书写的圣经。沃恩认为,尽管无法准确判断威克利夫本人在经书翻译中所具体承担的工作,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参与了圣经翻译,并且这项工作的完成必须主要归功于他的热心、支持与指导”。[12](P324-333)罗伯特·沃恩的作品长期被视为威克利夫研究领域详实而可靠的学术成果,成为后人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
19世纪关于威克利夫及其圣经翻译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还有查尔斯·韦伯·勒·巴(Charles Webb Le Bas)的《威克利夫传》(The Life of Wiclif,1832)、玛格丽特·考克斯(Margaret Coxe)的《约翰·威克利夫传》(The Life of John Wycliffe,1840)、蒙塔古·巴罗斯(Montagu Burrows)的《威克利 夫 的 历 史 地 位 》 (Wiclif’s Place in History,1882)、艾米丽·霍特(Emily Sarah Holt)的《约翰·威克利夫:第一位改革家及其贡献》(John de Wycliffe,the First of the Reformers,and What He Did for England,1884)、 亚瑟·彭宁顿(Arthur Robert Pennington)的《约翰·威克利夫:生平、时代及 学 说 》(John Wiclif:His Life,Times,and Teaching,1884), 以 及 刘 易 斯·萨 振 (Lewis Sergeant)的《约翰·威克利夫:最后的经院学者与第一位英国改革家》(John Wyclif:Last of the Schoolmen and First of the English Reformers,1893)等。考察这些成果可以明显地发现,早期《威克利夫圣经》研究主要被涵盖在关于威克利夫的传记类作品之中。这些作品延续了罗伯特·沃恩的成果,强调的是威克利夫作为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的身份,重视的是威克利夫圣经译本的宗教意义。其中,巴罗斯与彭宁顿等部分学者在各自的作品中简单提及了该译本在英语语言文学层面的价值,对后世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巴罗斯称,对于英语语言、英语圣经以及英国的宗教改革来说,“威克利夫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一位可以叫得出名字的人。 ”[13](P6)他还承袭历史学家约翰·格林(John R.Green)的说法,把威克利夫称为 “公认的英语散文之父”[13](P7)。 艾米丽·霍特注意到了《威克利夫圣经》后期译本的语言特点。她说:“威克利夫将圣经翻译成了他那个时代清晰、有力的英语,像孩子般的简单质朴,又时而有动人之美。 ”[14](P96)亚瑟·彭宁顿更为明确地意识到《威克利夫圣经》对于英语语言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指出,“当我们谈论人民大众怀着热切的心情阅读神圣书卷,认真思索那些带给天使们无限惊奇与喜悦的真理之时,我们决不能忽略《威克利夫圣经》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即它在英语语言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15](P171);“若说乔叟致力于在上层社会稳定英语语言,那么威克利夫则通过将英语和所有同胞永恒的希望联系在一起,为英语语言的确立发挥了更为长久的作用。 ”[15](P173)可以说,尽管以上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主要强调的是《威克利夫圣经》的宗教意义,没有详细而具体地论证该译本如何影响了英语语言文学的发展,但他们的认识无疑开拓了学界对于《威克利夫圣经》的研究视野,从而使后来的研究者对该译本的文学史价值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除以上研究成果之外,19世纪在 《威克利夫圣经》学术领域一件不能忽视的大事是,弗歇尔(Josiah Forshall)与马 登(Frederic Madden)经过22年的辛苦工作,于1850年合作出版了前后两个译本平行对照的威克利夫圣经译本,并首次赋予了该译本“《威克利夫圣经》”的名字。事实上,从弗歇尔与马登开始,威克利夫及其追随者的圣经译本才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称呼——《威克利夫圣经》。不仅如此,两人的呕血之作为人们深入研究《威克利夫圣经》文本及其语言和风格特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在正文的前面,弗歇尔与马登还详细列出了170份现存《威克利夫圣经》手稿的信息,并收录了译本的“总序言”,这对后世的《威克利夫圣经》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弗歇尔与马登合作出版的《威克利夫圣经》堪称此领域的一座里程碑。
二、20世纪以来的 《威克利夫圣经》学术研究
进入20世纪以后,威克利夫及其圣经翻译受到了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因而也把对《威克利夫圣经》的研究推向了深入。新时期,尽管学者们对《威克利夫圣经》文学史价值的认识有所不同,但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大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该译本同英语语言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虽有个别学者持论谨慎,学界的主流意见则表现出一种肯定的态度。
谨慎的态度甚至否定的声音主要来自于 《剑桥英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1908)的相关作者和英国文学史家艾弗·埃文斯(Ifor Evans)。 惠特尼(J.P.Whitney)在《剑桥英国文学史》中认为,关于威克利夫圣经译本的文学史研究还远远不够,需要从文本和语言学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评判之后,才能得出更为确实的结论[16](P60)。惠特尼的意见其实是相当中肯的,毕竟在当时乃至今天,学术界对于《威克利夫圣经》的文学史价值还没有做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流行的说法中多有推测的成分。相比于惠特尼的谨慎,《英国文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1940)的作者艾弗·埃文斯则明确提出,“约翰·威克利夫在十四世纪时已经努力去译出一个英语文本,但他的译文是根据公认文本即拉丁文本,而他的英语也是刻板而生硬的。他在英国散文发展上的影响一直是被过分夸大了。 ”[17](P342-343)虽然埃文斯对《威克利夫圣经》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作用持有消极态度,但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他的看法仍有一定的价值:一方面他提醒了该领域的学者在研究中应保持冷静的头脑,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另一方面这也再次暴露出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能令人信服地展示出《威克利夫圣经》之于英国文学发展史的意义。
实际上,虽然迄今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在文学语境中对《威克利夫圣经》的重要价值做出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但长期以来众多的学者还是根据有限的资料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使人们对该译本文学史价值的认识越趋成熟。美国历史教授乔治·英尼斯(George S.Innis,1907)在他的著作《改革晨星——威克利夫》(Wycliffe:The Morning Star)中像巴罗斯一样,认为 “所有英国的杰出人物中,威克利夫对英语语言、英语圣经以及宗教改革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人”[18](P201)。 他同时提出,威克利夫的圣经译本“似乎被用作了《钦定本圣经》(our Authorized Version) 的基础,(后者)使用了许多相同的词汇和表达”[18](P201)。 显然, 英尼斯不仅强调了《威克利夫圣经》对于英语语言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还模糊地注意到了该译本对于英国后来圣经翻译的影响。次年,卡里克 (J.C.Carrick)出版的《威克利夫与罗拉德派》(Wycliffe and the Lollards,1908)一书更为清楚地强调了《威克利夫圣经》对于英语语言和圣经英译的重要作用。他说,虽然译本不是出自希伯来和希腊语原文,但其翻译相当准确,“它不仅将圣经交到了普通民众的手里,还稳定了英语语言,赋予了它前所未有的坚实与连贯性”;因此,《威克利夫圣经》“成了纯净和正确的英语书写与言谈的标准”[19](P143)。考察圣经英译的整个历史,卡里克认为,“《威克利夫圣经》是所有译本之母。尽管它本身只是对拉丁文圣经译本(Vulgate versions)的朴实翻译,它有偏差、有缺陷,甚至有矛盾之处,但却构成了那本伟大圣书(指《钦定本圣经》)的基础,这本书塑造、确定并指引了英语语言和文字。 ”[19](P157)这样,借由《钦定本圣经》的巨大影响力,卡里克实际上赋予了《威克利夫圣经》更为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20世纪初,文学评论界也开始有人高度评价威克利夫与《威克利夫圣经》的历史地位。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授乔治·克拉普 (George Philip Krapp)在其专著 《英语文学散文的崛起》(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Prose,1915)中称,如果英语散文必须要有一个“父亲”,那么没有谁比威克利夫更值得拥有这一称号。威克利夫本人虽算不上散文风格的大师,但他是第一位清楚地意识到散文表达一般原则的英国人。[20]通过威克利夫及其追随者的作品,“英语散文逐渐用来表达英国人的思想,且其效果和深度远胜从前。”[20](P1-2)在克拉普看来,威克利夫等人不仅提升了英语散文的文学地位,他们对于英语散文风格的确立也影响深远。他认为,作为一部文学艺术作品,虽不能说《威克利夫圣经》为英语风格树立了一种新的更高标准,但这部作品却是出于高尚的构想,旨在追求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学术标准和最庄重的英语表达。[20](P229-230)克拉普还提出,要在大众思想与情感的潜流中来探究《威克利夫圣经》的影响,而非通过任何直接的文学继承者。这种思想与情感是该译本以行动所建立起来的,并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得到秘密滋养。以这种方式确立的风格传统,对于后代政治与宗教界公众领袖的思想以及英语文学艺术形式都发挥了强有力的影响。[20](P32)
1920年剑桥大学研究员、历史学家玛格丽特·迪恩斯利(Margaret Deanesly)出版《罗拉德圣经与其他中世纪圣经译本》(The Lollard Bible and Other Medieval Biblical Versions),这是第一部专门探讨《威克利夫圣经》的学术专著。迪恩斯利首先从中世纪欧洲整体背景下考察了当时俗语圣经的阅读与翻译,然后详细介绍了英国在威克利夫之前对圣经的翻译、研究和阅读情况。她确认《威克利夫圣经》是第一部英语圣经全译本,并指出,威克利夫派的圣经翻译,其根本新意在于他们旨在向更为低下却更为广大的社会阶层提供母语圣经,这也是威克利夫 “神恩统治论”(dominion by grace)神学思想的必然结果[21](P227-228)。迪恩斯利还详细讨论了两个译本大致的翻译时间和译者身份,以及《威克利夫圣经》诞生后的传播、查禁与阅读情况。迪恩斯利以《威克利夫圣经》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在相当宽泛的视野下丰富了人们对于该译本的认知,她的许多结论为后世学者所采信。遗憾的是,迪恩斯利的研究对于《威克利夫圣经》在英语语言文学发展方面的价值基本没有涉及。但到了1951年,在她为伦敦大学所做的学术报告中,作为威克利夫翻译圣经的重要意义之一,迪恩斯利指出,“尽管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计划并不成熟,但他确实将对母语圣经的喜爱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内心,且(这种喜爱)是由于母语的缘故 。 ”[22](P23)这一论断再次提醒人们《威克利夫圣经》与英语语言之间的实质性关联。
在20世纪,对罗拉德派(威克利夫教派的别称)及其圣经的重要研究还有英国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阿斯顿(Margaret Aston)的《罗拉德派与改革者》(Lollards and Reformers:Images and Literacy in Late Medieval Religion,1984),它涵盖了作者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在这一领域的许多重要学术成果。正如作品的副标题所示,阿斯顿特别关注了罗拉德运动与英国民众识字水平的关系。她提出,15世纪人们的识字水平普遍得到提高,而作为识字的途径决不能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宗教启示[23](P193);换言之,宗教目的激发了人们学习语言的热情。在这个过程中,罗拉德运动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作为一种白话识字运动罗拉德派集聚了动力,也正是作为一种白话识字运动该派受到了怀疑和迫害。 ”[23](P207)罗拉德派对于人们识字水平的贡献尤其体现在他们对圣经的推崇并将其翻译成了通俗易懂的英语。在阿斯顿看来,罗拉德派“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研习圣经与学习俗语的坚实传统,虽经多种阻遏却持续不断”[23](P198)。 自从罗拉德圣经译本流传于世,一群又一群热诚的读者、听众和学习者聚到一起参加圣经集会构成了罗拉德派的一大特征[23](P199)。他们对于英语圣经译本的热情贯穿整个15世纪,直至帮助开启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牛津大学教授、文学史家安妮·哈德森(Anne Hudson)发表于1988年的《早产的宗教改革:威克利夫文本与罗拉德历史》(The Premature Reformation:Wycliffite Texts and Lollard History)堪称20世纪罗拉德运动和《威克利夫圣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综合前人研究对整个罗拉德历史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探讨与展示,特别是哈德森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专门探讨了罗拉德运动对于当时文学创作的影响。她发现,乔叟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 中,那位穷牧师实际上体现了诸多威克利夫关于神职人员的理想形象,而且一些罗拉德派的语言也反复出现在该作品之中。哈德森同样发现,“乔叟的情况在这个时代颇具典型意义。 ”[24](P394)当时的重要作家朗格伦 (William Langland)、 高尔(John Gower)和特里维萨(John Trevisa)等人的创作都与罗拉德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哈德森的研究不仅为人们全面了解威克利夫派的历史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对于学界深入挖掘《威克利夫圣经》的文学史价值也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迄今,将罗拉德思想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进行深入探讨的重要成果来自于美国学者安德鲁·科尔(Andrew Cole)。他于2008年出版《乔叟时代的文学与异端》(Literature and Heresy in the Age of Chaucer),无论是就罗拉德运动的历史还是关于威克利夫派的文学史地位都提出了新的见解。科尔指出,许多证据告诉人们,教会和俗界几次主要的反对威克利夫派的倡议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某些情况下还事与愿违地使这场异端成为人们强烈而持久的兴趣[25]。 在这种认识前提下,科尔对威克利夫派的文学影响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来,中世纪晚期是英国文学和宗教史上最有趣、最激烈的时期之一,罗拉德运动构成了这段时期英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5](P188)。 乔叟、朗格伦以及玛丽·肯普(Margery Kempe)、托马斯·霍克利夫(Thomas Hoccleve)等人不仅没有因为惧怕制度审查或派别偏见而规避威克利夫教派,他们反而把威克利夫思想当作了崭新的知识资源。与其说罗拉德运动是事件的“语境”或者“背景”,不如说它本身就是文化转变过程中的一部分。他们突然带来的思想观念、艺术形式和修辞方法,帮助不同的中世纪作者重新思考过去和现在、传统和惯例、美学与政治,以及从根本上思考写作的意义。[25](P186)因此,在某种程度上,“14 世纪晚期之后,英国文学根本上是由约翰·威克利夫异端所塑造的。”[25]可以看出,安德鲁·科尔赋予了威克利夫及其教派非常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他甚至提出,威克利夫派以其自身的成就和影响,成为“塑造英国文学史的核心力量之一”[25]。
除以上这些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外,20世纪以来,在《威克利夫圣经》研究领域较为重要的学术成果还有布鲁斯(F.F.Bruce)的《约翰·威克利夫与英语圣经》(John Wycliffe and the English Bible,1984)、艾德文·罗伯逊(Edwin Robertson)的《约翰·威克利夫:宗教改革的晨星》(John Wycliffe:Morning Star of the Reformation,1984)、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编著的《威克利夫与他的时代》(Wyclif in His Times,1986)、 菲奥娜·萨默赛特(Fiona Somerset)等人编著的《罗拉德派及其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影响》(Lollards and Their Influence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2003)、 伊恩·利维(Ian Christopher Levy)编著的《约翰·威克利夫指南》(A Companion to John Wyclif,2006),以及玛丽·多芙(Mary Dove)的《第一部英语圣经》(The First English Bible:The Text and Context of the Wycliffite Versions)等。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人们对该领域的认知,为后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学者对威克利夫与《威克利夫圣经》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这一领域也受到了各界的重视。已有的学术成果主要出自宗教历史以及翻译学的研究,成果形式多为期刊论文和硕、博士学位论文。如张绪山 《论威克利夫宗教改革思想对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1989)、毛丽娅《试论英国罗拉德派及其与威克利夫学说的关系》(1995)、李自更《论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思想》(2002)以及霍红霞《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思想及其影响》(2006)和王宗华的《威克利夫〈圣经〉翻译研究》(2014)等。除此之外,一些翻译理论著作和文学史也介绍了威克利夫圣经翻译的意义,如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谢天振等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和李赋宁、何其莘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6)等。
国内从语言文学角度对《威克利夫圣经》展开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三篇期刊论文,分别是龙彧《英语语言变迁中的威克里夫——以〈圣经〉英译风波为例》,王任傅的《〈威克里夫圣经〉译者考辨及其文学史意义》以及陈桂花、王任傅《英语文学视野下的〈威克利夫圣经〉》。龙彧提出,威克利夫英译圣经的主张从三个方面对英语语言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即“提高了英语语言的地位”,“丰富了英语语言并促进了英语标准语的形成”,以及“对后世英译圣经的译风产生了深远影响”[26]。王任傅与陈桂花认为《威克利夫圣经》的文学史意义主要体现在,1、该译本的文风通俗易懂、明晰质朴,堪称中古英语的经典;2、《威克利夫圣经》的译文风格为后世的圣经翻译树立了典范,并由此深刻影响了英国文学的发展趋势;3、该译本的广泛传播推动了圣经知识在民间的普及,从而丰富了英国文学创作的内容与素材[27]。三篇文章都明确地讨论了《威克利夫圣经》对英语语言文学发展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但限于篇幅,作者对《威克利夫圣经》文学史价值的探讨还不够系统与深入。
三、《威克利夫圣经》研究现状的反思
历史表明,英语民族自诞生之初就被纳入了基督教的轨道,因此长期以来英国社会形成了十分浓厚的宗教氛围。圣经所承载的基督教思想和文化内容不仅深刻影响了英国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对于英语语言文学的发展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为英语民族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英文圣经译本,《威克利夫圣经》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通过对该译本300年来学术史的细致梳理发现,国内外知识界对于《威克利夫圣经》的研究视野,特别是文学语境中的探索,还存有明显的缺憾。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威克利夫圣经》对英国后世圣经翻译的影响
虽然学术界对《威克利夫圣经》在英语圣经翻译领域发挥了开启山林的作用已达成基本共识,但对于该译本如何具体影响了后世的圣经英译尚未做出细致的探究。正是由于缺少深入具体的考察与论证,当前学界就《威克利夫圣经》对圣经英译的影响表达出了三种不同的意见。克拉普与玛丽·多芙等人认为,《威克利夫圣经》译者的翻译理念与翻译原则对以廷代尔为代表的16世纪圣经翻译者的影响要多于译本本身的贡献[4](P192)。塞缪尔·麦库姆(Samuel McComb)教授则努力探寻《威克利夫圣经》后期译本与廷代尔译本在表达上的高度相似之处,并总结说,“凡在契合其目的之处,廷代尔都使用了威克利夫译本的语言。”[28](P135-140)以美国语言学家乔治·马什 (George P.Marsh)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威克利夫圣经》在具体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方面都对后世的圣经翻译产生了影响。马什评论说,廷代尔的翻译“不仅保留了《威克利夫圣经》译文总体的语法结构,也保留了译本中大部分贴切的言语组合”。更为突出的是,廷代尔甚至在翻译中“保留了《威克利夫圣经》语言的句读节奏”,而 “这种节奏又在1611年的《钦定本圣经》中重现”。所以,马什总结说,必须承认是威克利夫 “开创了那种500年来已构成英语语言中神圣话语的措辞与表达方式”[29](P537)。 考察圣经的英译历史并参照典型译本,应该说,学术界的这三种意见都有其合理之处。然而,若不经过深入的考证并做出细致具体的文本分析与对比,学界的这些观点也主要视为推测,不能成为定论。
(二)《威克利夫圣经》对英语语言发展的具体作用
中古英语是英语语言发生巨变,并为英语最终走向民族标准语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时期。特别是14世纪出现的一些重要人物、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极大地促进了英语语言的普及和使用功能的提升。在英语语言迅速发展并逐步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威克利夫圣经》无疑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也早已被国内外学界普遍认可。例如,牛津大学的蒙塔古·巴罗斯教授称,威克利夫对英语语言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超过任何一个人们能够叫出名字的人[13](P6)。 李赋宁也认为,乔叟和威克利夫的作品对于 “英国民族标准语和文学语言的确立与传播”意义重大[30](P5)。
然而,以上学术史的梳理同样清晰地表明,在这些肯定的声音乃至赞赏的态度背后,尚缺乏一种专门而系统的论证,即迄今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哪位学者的成果专门致力于《威克利夫圣经》译本在英语语言发展过程中具体作用的探讨。因此,为使人们明白该译本之于英语语言发展的重要贡献,研究者还需要通过具体的史料并结合译本内容对如下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论证与澄清:1、在怎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威克利夫及其追随者的圣经英译大大提振了英国人对本民族语言的信心?2、《威克利夫圣经》如何及在何种程度上推动了英语语言的使用和普及?3、如果说《威克利夫圣经》丰富了英语语言的词汇与表达,它具体表现在哪些内容?4、《威克利夫圣经》提升了英语作为宗教语言的使用功能,这又是如何体现的?等等。
(三)《威克利夫圣经》对英语文学的具体影响
文学史家一般把14世纪视为英国文学新纪元的开端。学界如此定义,往往看重的是诗人乔叟、高尔和朗格伦等人的诗歌创作与成就,认为主要是他们共同推动了英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通常只有乔叟被视为英语文学的奠基人;威克利夫与《威克利夫圣经》的文学史地位却因为突出的宗教史意义而被忽略了。现在随着人们对《威克利夫圣经》文学史价值的日益关注,该译本在文学语境中的地位也逐渐得到正视。“如今,语文学家开始承认威克利夫的散文是最早的中古英语经典,乔叟与他并肩而立。 ”[8](P27)而且同威克利夫的其他英语作品相比,《威克利夫圣经》在表达上“清晰明白、优美有力,达到了罕有的高度”[8](P27)。 安德鲁·科尔也说,“必须把乔叟和朗格伦等当时深受欢迎的作者们放在罗拉德语境下进行阅读,我们才能对他们作品中所探讨的话题获得更为全面的理解”[25]。
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充分肯定 《威克利夫圣经》对英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但作为英语文学发展关键时期唯一一部完整的圣经英语译本,学界对于《威克利夫圣经》文学史意义的探究尚处于起步的阶段。无论是就该译本与14世纪至16世纪初英国具体作家作品的直接联系,还是就该译本对英语文学发展更为深远的影响,国内外学术界远未做出深入与系统的研究。例如,哈德森在她有限的篇幅中指出乔叟和高尔等诗人们与威克利夫派的密切联系,但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罗拉德派的思想、翻译理念及其语言风格影响了14世纪的英国文学创作?这种影响又呈现出了怎样的共性和特点?关于这些问题,学界显然并没有做出系统的回答。透过中古英语神秘主义文学的文稿,人们发现,圣经在15世纪的神秘主义文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31](P87)。 作为一种文本,它不仅要求人们来阅读,还要求人们来生活和实践[31](P94)。 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神秘主义文学中的圣经与《威克利夫圣经》有着多大意义上的联系也有待人们做出深入的考察。不可否认的是,圣经在英国文学发展史上一直都发挥了重大而无可替代的作用,英语语言文学通过圣经的翻译被深深地影响了十几个世纪[32]。那么,置身于整个英国文学史的连续传统之中,《威克利夫圣经》到底扮演了怎样的一种角色?英国文化传统中这种宗教与文学的紧密关系,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宗教的文化价值、发挥宗教因素在我国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又有着怎样的现实启发意义?这些无疑都是《威克利夫圣经》文学研究领域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也必将为该领域的研究开辟出一片新的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