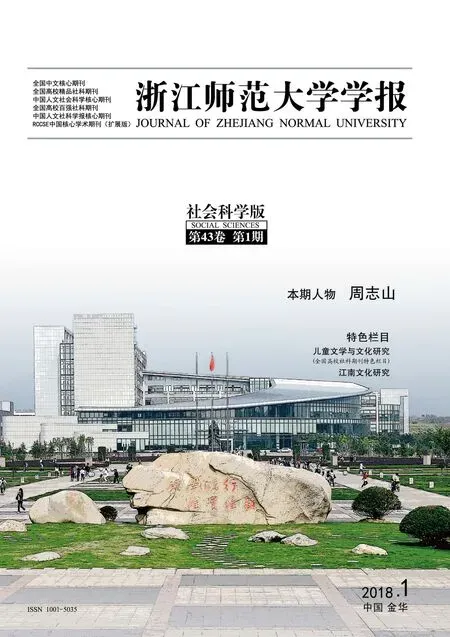文化认同与清代前期的丧葬礼制建设
沈宏格
(湖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00)*
清初,绝大多数士人对满洲贵族入主中原是相当抵触的,“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1]因此,清代前期的文化认同对于维系满汉统一政权就显得格外重要,它是凝聚这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但问题是,满族虽然掌握了国家政权,可满族在长期游牧中形成的骑射文化相较于中原儒家文化却处在低势地位,从文化势差的角度来看,清代前期文化势差必然导致文化的正向流动,因为无论是从时代的经还是地域的纬来看,儒家文化都处在高势地位,①表现在文化认同上就是清代前期构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而丧葬仪式作为一种群体性行为,是实施文化认同的理想载体。故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满汉文化,建构清代的丧葬礼制是清前期实施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从顺治到乾隆近百年的时间里,清代逐步建立较为完备的丧葬礼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清代前期实施文化认同的过程。考察其礼制建设过程,对于我们认识清代前期文化认同中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入关前满族的丧葬
死亡,是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的事情,各民族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丧葬形式、祭奠仪式及丧葬禁忌等,它是民族文化、民族宗教信仰等民族意识的综合体现。满族先民(史书称其先世有挹娄、肃慎、勿吉、女真等)长期生活在我国的东北部,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满族特点的丧葬习俗。与汉族丧葬礼仪相比,满族及其先民的丧葬有如下特点:
1.从殡来看:满族先民不仅时间非常短,甚至“死即日便葬于野”,而且特别强调男子以无忧哀相尚。《北史·勿吉传》载“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湿,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2]即父母去世,春夏则“立埋之”,秋冬死却将尸体用来当作捕貂的诱饵,更谈不上哀伤;《肃慎国记》则明确记载其俗:“父母死,男子不哭泣,有泣者谓之不壮。死即日便葬于野,以绳系椁头,出土以灌,绳腐即止,无四时祭祀之也。”[3]《晋书·四夷传》也载:“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谓之不壮。”[4]直到清朝建立前夕,努尔哈赤第五子(三贝勒)莽古尔泰去世,第二天即葬。“至申时,贝勒薨。次日巳刻,即将贝勒及福晋尸骸分别入殓出殡……是日,子时三鼓,汗方入室,诸贝勒亦各自还家。”[5]261
2.从葬来看:满族先民曾有不同的葬式。满族有土葬,但与汉族不同,土葬不重棺殓之具,甚至无棺。《旧唐书·北狄列传》载:“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6]《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死者埋之而无棺梆,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所有祭祀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7]除了土葬外,还有天葬:“满洲地处东夷……风俗乖谬,多有为汉人梦想不到者……人死后赤身露体,敷以牛油,悬之林杪,投之幽谷,以招鸟兽食之。食尽,则戚亲相贺,剩有残余,谓此人生前罪恶大,上帝不收。必再请喇嘛念经,再敷牛油,务求食尽乃已。”[8]满族入关前,其葬俗以火葬为主,《黑龙江外纪》卷六较详细地记载了满洲火葬风俗:“人死焚尸而瘗,曰熟葬。熟葬之法,舁棺至郊野,置柴上,请师举火。火炽尸起,挺而仆之,须臾肉尽,骨仅存,然后拾贮所谓净匣中而瘗之土。”[9]这里所谓火葬实际上是先以火将肉烧尽,然后埋骨土中。清朝雍正皇帝解释火葬的原因是其民“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徙无常,遇父母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10]其解释似乎有点牵强,因为最终还是入土葬之,与“迁徙无常”关联不大,应与宗教信仰有关,天葬中请喇嘛念经可以看出宗教对满族丧葬的巨大影响。清太宗皇太极去世(1643)还是先火化,然后葬骨灰于沈阳照陵。
3.从居丧看:满族在入关前已受汉族丧葬文化影响,但居丧守制尚未有定制。努尔哈赤与包括诸贝勒在内的众人商议守孝之礼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初二日,努尔哈赤与诸贝勒、蒙古诸贝勒及众人商议:“若使后代守孝者斋戒过之,哀丧之礼亦过之,则守制之礼难矣。其礼仍令存之,善乎?为现存之人从轻议礼如何?着尔等将此二礼定议奏复。”众贝勒皆回奏称是,汗定之。并下书曰:“后代守孝重服之人,若途中邂逅,乘马则下马跪叩让过,于坐处则避让过之,筵宴则于坐处叩拜。守孝之礼倘劳苦过甚,则我等皆非长生不老之身,何苦如此劳累此有生之身也。人之寿皆天定也。故生生死死,循环往替。若仍此守制,作践其身,尚有何闲暇之时耶。诸贝勒大臣之亲戚皆居一处,死丧服孝,生者守制,若皆免之,则为善也。”[5]664可见努尔哈赤并不主张居丧守制。
由上可以看出,入关前满族的丧葬与中原汉族的丧葬差异很大,这种差异不只是表现在操作形式,更主要的是牵涉到两种丧葬方式背后的文化与伦理精神的冲突。在葬式方面,对中原汉人而言,焚烧父母肉体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曾颁布禁令:“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孙,于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②并将焚烧尸柩的禁令纳入明朝律例。儒者也极力反对火葬,王廷相曰:“世有火其柩而归其烬者,何如?曰:斯悖谬之大者也。且夫爱其亲之肌体,故敛而藏之,焚之是戕其亲矣。何忍乎?斯悖谬之大者也。”[11]王廷相将火化与戕杀其亲等同,将其视为极其悖谬的事。明代南京光禄寺卿茅瑞征则认为火葬与儒家孝子事亡如存之义相悖:“今世俗人死不三日则五日,遂委而付之一火。当有骨肉未寒,哭泣未绝而亲之体已无孑遗者矣。孝子不死其亲,即死犹冀其或生,如是又可冀乎?今人试灼尺寸之肤,其容有蹙,死而有知,宜未有恬然甘受其烬者。即其无知,亦非孝子事亡如存之义。”③从丧的角度看,儒家丧礼强调的是以哀戚表达孝道,故对居丧的容体、声音、言语、饮食等都有详细规定,以回报父母无极之恩德,亦是用以节制邪淫不肖者哀情不足,促使其在三年期限内勉力以服丧。“将由夫患邪淫之人与?则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从之,则是曾鸟兽之不若也,夫焉能相与群居而不乱乎?”[12]1374在儒家看来,满族那种即日安葬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是鸟兽之行为,这也是儒家敬老与满族敬壮文化的差异。“满洲地处东夷,本女真遗种,行为野蛮,风俗乖谬,多有为汉人梦想不到者。如若祖若父,七十不死,子孙则不顾瞻,自亦无颜于世。即请喇嘛念经,经毕,乃备丰馔与食,名曰飨神,食终,或坐空斋饿死,或赴舍身崖,坠崖而死。”[5]664老人七十则“子孙不顾瞻,自亦无颜于世”,这在儒家讲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孝道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故将此称之为野蛮行为。由此可见,满汉在丧葬方面的文化势差是客观存在的。
二、清前期丧葬礼制建设中的汉文化认同
由于满族与汉族文化的巨大差异,清入关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作为一个被汉人视为夷狄的异族统治者如何才能得到汉民族,特别是汉族士人、士大夫在文化上的认同,不仅要让他们首肯清朝代明而立、鼎故革新为名正言顺,而且更要承认清朝是历史上推尊服膺儒家文化的正统皇朝合法的延续”。[13]为此,清初统治者“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通过对儒家的文化认同,赢得汉人的好感,换取汉人服从清朝统治,实现国家认同”。[14]随着两种文化的调和,丧葬礼仪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必然影响满族对丧葬伦理精神重新认识与操作形式的改变。下面我们考察从顺治到乾隆期间儒家文化影响逐渐深入情况下清统治者对其丧葬礼仪制度的调整。反过来,从丧葬礼仪的调整也反映出清统治者对汉族儒家思想文化认同实践的逐步深入。
1.顺治时期
对汉文化的吸收从努尔哈赤就已开始,皇太极更有“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的谕旨,顺治在皇太极文化政策的基础上于顺治十年(1653)将“崇儒重道”定为国策。在礼制方面,顺治元年(1644),工科给事中朱鼎藩以言官的身份上奏《请明纪纲定人心疏》,建议朝廷申明纲纪以“安定民心”“奠万世之业”,指出:“礼仪为朝廷之纲,而冠履侍从,揖让进退,其纪也。”④“顺治三年,诏礼臣参酌往制,勒成礼书,为民轨则。”[15]1483这说明顺治初年,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朝廷已经开始重视礼制建设,其在丧葬礼制方面的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完善丧礼的等级性。儒家礼制的基本原则是“尊尊”与“亲亲”。“尊尊”就是强调礼仪的等级性,顺治时期对丧葬改革最突出的是等级性的强化。天聪六年(1632)三月,皇太极曾制定了诸贝勒、大臣各官祭葬例,只将贝勒、大臣官员粗略地分为六级:即管旗诸贝勒与不管旗议政诸贝勒,五备御总兵官,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顺治元年(1644)正月制定的诸王以下官民人等祭葬礼则将其划分为二十三级:即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和硕福金,多罗福金,多罗贝勒福金,固山贝子福金,镇国公妻,辅国公妻,异姓超品一等公,一等公、二等公、三等公、和硕额驸,固山额真、尚书、昂邦章京、多罗额驸,内大臣、大学士、梅勒章京、侍郎、护军统领、前锋统领、贝勒婿、多罗额驸、镇守盛京总管官,甲喇章京、一等侍卫、前锋参领、固山额驸、学士、满州启心郎、理事官、盛京副守官、守外城三品以上等官,牛录章京、二等侍卫、镇国公、辅国公婿、汉启心郎、副理事官、都察院、理藩院启心郎、赞礼郎、祭酒、镇守盛京固山章京、哨长、镇守各外城官、迎送官、两翼管台官,半个牛录章京,民。除了等级更细之外,内容更具“礼”的特征,如皇太极时贝勒的祭葬内容为“凡管旗诸贝勒与不管旗议政诸贝勒薨,上赐纸万张、羊四只、酒十瓶”,⑤只是规定了“上”赐予的数量,而无其它“礼”的内容。而顺治时和硕亲王祭葬内容为:“上辍朝三日,礼部官视祭葬。和硕亲王以下,奉国将军以上,固山额真、昂帮章京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固伦公主,和硕福金以下,奉国将军妻以上,皆会丧。设亲王仪仗,鞍马十五匹,空马十五匹,王属下官员及妻俱丧服,用彩棺,内衬五层,王属下官员及妻大祭毕,除服,王属下在部院衙门及闲散各官未毕祭,入署戴缨帽,穿常服,上坟日,仍去缨。其茔垣享殿,皆王府及所属牛录下人夫起造。初祭赐牛一、羊八、酒九瓶、纸钱三万。次祭,赐亦如之,加封谥勒石茔所。初祭、次祭日,除上赐外,自增入引幡一杆、金银锭七万、纸钱四万、羊九只、桌三十张。百日周年,金银锭一万、纸钱一万、羊九只、桌十五张。”⑥从上可以看出,辍朝、视祭葬、会丧人群、仪仗、初祭、次祭、百日周年祭等都有了详细的标准,而且汉族丧葬中最常见的词汇“丧服”“除服”“周年”“仪仗”等已在顺治时的丧葬礼制中出现,最为重要的是规定“祭物逾分者,坐以应得之罪”。这正是儒家丧礼“尊尊”伦理精神的体现,也是满清统治者对儒家丧葬文化伦理认同的体现。后来顺治五年(1648)四月辛未又制定了殡殓发引安葬例:“和硕亲王以上殡于庭内,候造坟成,发引,期年安葬。多罗郡王、多罗贝勒殡于庭内,五月发引,七月安葬。固山贝子、公殡于庭内,三月发引,五月安葬。会丧各官候殡毕,乃退。至致祭、发引,俱照旧齐集。官民人等殡,一月发引,三月安葬。凡发引焚葬,俱不得过所定之期。”⑦对发引安葬时间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且要求各等人群不得逾期,这是对顺治元年所定丧葬礼在身份等级方面的完善。
其次是确定了居丧之制。在儒家文化里,“父母之丧,天下通义。治丧守制,人子至情”,居丧守制是儒家丧礼中体现孝道的重要部分,它“从哀的角度对居丧的容体、声音、言语、饮食进行详细规定,以回报父母无极之恩德”,[16]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朝廷首先制定了宫中丧制,规定了大丧及其妃丧守制二十七个月(三年):“凡大丧,宫中守制二十七个月,不悬门符,不张彩灯,京以内诸王同。惟官民不禁。其妃丧,本宫及妃之子守制二十七个月,余妃之子不守制。”⑧随着国家政局的稳定,顺治十年(1653)二月,都察院广东道监察御史陈启泰上疏《请行通制以重大伦事》:“今汉臣仍遵往制,丁艰二十七月,满臣不在丁忧之例。守制之礼,满臣何独与汉臣殊?”[17]可见此时满官仍无丁忧定制,上疏得到顺治的重视,顺治十年(1653)四月,经九卿会议确定满汉官员一体离任丁忧。但一个月后,清廷对此又做了调整,“满洲、蒙古、汉军官员,有管旗下事者,有在部院理事熟练者,不便照汉官一例丁忧。议于在家居丧一月,即出办事,仍私居持服三年”。⑨虽然最后满汉异制,没有实现满汉一体丁忧,但满族毕竟有了丁忧之制。顺治十八年(1661)八月,朝廷谕吏部详察太祖、太宗时旧例,参酌时宜,议定大小官员治丧守制之礼,结果吏礼二部却未找到太祖、太宗满洲守制旧例,“惟顺治十年三月礼部覆原任广东道御史陈启泰请行通制一疏,奉有三年丧礼,著照会典定例遵行,有难拘常制者请旨定夺之旨。又顺治十年六月,臣部题满洲、蒙古、汉军各官,不便离任丁忧。奉有依议之旨,遵行已久”。⑩可以看出,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满清官员还是按顺治十年(1653)议定丁忧守制。不久吏部议得“在京部院,满洲、蒙古、汉军,大小文官仍应照定例,守制一月,服满即出理事。私居持服尽三年丧礼外,其奉差出兵文官,以回京闻丧之日为始,亦照定例遵行,至各省驻防及在外出仕,汉军文官,伊父母在任病故者,仍应照例遵行。父母在京病故者,准其解任回京,以至日为始,守制半年,仍私居持服,尽三年丧礼”。这次将丁忧的范围扩大到外任官员,这样满蒙汉文官居丧之制基本确定。
最后是对坟墓的保护。在儒家丧葬文化里,墓是祖宗骨骸之所在,子孙命脉之所关,保护好祖宗的坟墓也是孝道文化的要求,故墓葬也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如大明律就明确规定:“凡发掘坟冢见棺椁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开棺椁见尸者,绞;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流三百里。”[18]如发掘坟墓惩罚最重者可以是绞刑,可见国家对祖先坟墓的保护程度。顺治二年(1665)二月丙寅命户部传谕管庄拔什库等:“凡圈占地内,所有民间坟墓不许毁坏……违者治罪。”此时虽未明确如有毁坏坟墓,究竟如何处罚,但至少表明了朝廷对祖先坟墓的保护态度。
2.康熙时期
康熙亲政之前,以鳌拜为首的守旧势力民族思想较强,文化政策有所波动,康熙亲政后,将“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具体化为“圣谕十六条”,儒家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在丧葬方面最突出的影响就是葬制的改变,由火葬改为土葬。另外还禁止殉葬,并将居丧守制、丧服等进一步儒家化。
满族入关前主要是火葬,入关后顺治朝对此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而是听其自便。顺治九年(1652)九月,还制定了从亲王到官民的火化时间:“异性公、侯、伯以下,民人以上,不许盖造墓室,如有旧造者,次年清明俱行拆毁。和硕亲王薨,停丧于家,俟造坟完毕方出殡,期年而化。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停丧五月出殡,七月而化。固山贝子以下,公以上,停丧三月出殡,五月而化……官民停丧一月出殡,三月而化,不许逾定期。”康熙帝时虽未要求满族必须土葬,但却以行动打破火化的习惯。康熙二十年二月,康熙帝的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与第二位皇后钮祜禄氏以土葬方式葬入清东陵;海淀门头村1961年发现的死于康熙三十六年的康良亲王杰书墓也是土葬;[19]康熙帝去世后也采用土葬。“因为在农耕传统悠久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土葬被视为是最尊贵、最正统的方式……葬制改革正是文化交锋与融合的真实见证。”[20]“康熙皇帝崩逝时,清朝统治者汉化程度日深,故因时定制,开创了清代帝王土葬之先河。自此以后至光绪帝为止,八朝帝王均沿用土葬,就连朝野臣民也随之一改塞外火化风尚。”[21]火葬改为土葬,正是清统治者对儒家葬式伦理的文化认同,对后世影响深远。
居丧守制方面:康熙期间居丧守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居丧守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父母丧守制三年的普遍实施、居丧(送葬)行为开始严格。康熙七年(1668)十月丙寅,康熙“命内外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武官为其父母、祖父母及过继父母、祖父母居丧三月,私居仍持服三年”。康熙将居丧范围由原来的父母扩大到祖父母、过继父母、过继祖父母,虽与儒家服制还有差距,但毕竟在原来守制对象上有所突破。康熙十二年(1673)八月庚申,康熙准宗人府等衙门遵旨议复:“凡王以下至奉恩将军及满洲、蒙古、汉军文官以上,遇有父母丧事,不计闰,准守制二十七月。又承重孙,为祖父母亦守制二十七月。若长房无子,次房之长子,亦应承重守制二十七月。俱准其百日剃头,照旧进署办事。仍在家居丧二十七月,满日除服。”至此,丁忧三年在满汉官员全面得以实施,不过后来在乾隆时又实行满汉差异化管理。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的圣祖母太皇太后崩逝,他决定持服二十七月,虽大臣劝说,“帝王之孝,与臣民不同,愿皇上仰遵遗诰,博稽古制,上思天地祖宗付畀之重,下慰群臣百姓仰赖之忱,以礼节哀,易月之典,守而勿更”。康熙以“朕意己定,不必更奏”回复,坚持三年之丧。同时,康熙要求居丧要遵守礼制,康熙十二年(1673),要求“未除服之前,凡穿朝服等处,停其朝会。凡有喜庆事处,不许行走,不许作乐,违者照定律议处”。康熙二十六年(1687),又“禁居丧演戏饮博”。[22]送葬时应该步行,不能乘马坐车。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一月,淑惠妃发引,公普照、贝子苏努、公星海等在后乘马而行,康熙闻之后,着宗人府查实,查得公普照、贝子苏努、公星海、登色、额尔图、吞珠、门度、赖士等俱乘马往送,最后处置为“普照,星海俱著革爵,禁锢宗人府。另择袭封之人承袭。其苏努等六人,皆已年迈,著从宽免议”。
禁止殉葬:满族有殉葬的习俗,康熙十二年(1673)六月,康熙接受汉官朱斐的请禁止人殉上疏。康熙二十七年(1688)五月乙亥,“大学士等以礼部具题山西省烈妇荆氏等照例旌表一疏,请旨”。康熙皇帝不仅不予旌表,还指出殉葬是反常之事,“夫死而殉,日者数禁之矣。今见京师及诸省殉死者尚众,人命至重大,而死丧者,侧然之事也。夫修短寿夭,当听其自然,何为自殒其身耶。不宁惟是,轻生从死,反常之事也,若更从而旌导之,则死亡者益众矣,其何益焉”。不过对儒家倡导的守节却给予旌表。康熙五十一年(1712)九月,镶红旗闲散瓦色之女,许配给正红旗护军陆格,但陆格未婚却病故了,女至夫家,为其夫剪发守孝,奉姑三年,服满自缢而死,康熙同意礼部题请,予以旌表。
3.雍正乾隆时期
雍正、乾隆时期,朝廷积极复兴儒家伦理,大力建设社会礼制,礼制对国家社会的积极作用雍乾都是十分清楚的。“以礼言之,如化民成俗,立教明伦,使天下之人,为臣皆知忠,为子皆知孝,此礼之大者也”。“夫礼之所为,本于天,截于地,达之人伦日用,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斯须不可去者”。[23]故乾隆元年即开“三礼馆”,命儒臣修纂《三礼义疏》。具体在丧葬礼仪方面,主要体现在“礼”的严格化与法制化。
康熙时将火葬改为土葬,但并没有入律。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将土葬定为国法,十二月的上谕不仅禁止火化,而且按违律治罪。如果族长、佐领隐瞒不报,也要受到处罚。“旗民丧葬,概不许火化。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归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有犯,照违制律治罪。族长及佐领等隐匿不报,照不应轻律,分别鞭责议处。”[24]乾隆初年即明令满族民间须行土葬,火化者按律治罪,并解释满族先祖实行火化的原因是游牧生活所致。
在礼仪规范方面:雍正要求满汉官民遵照丧葬之礼,不得僭越。“雍正元年五月己丑,九卿等遵旨议定:凡公、侯、伯、满汉职官以及兵民一应殡葬婚嫁之礼,毋许僭越,请著为令。”按照儒家丧礼的要求“父母之丧既殡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齐衰之丧疏食水饮,不食菜果;大功之丧不食醯,小功、缌麻不饮醴酒,此哀之发于饮食者也”。[12]1366雍正元年(1723)十月,雍正帝接到副都统祁尔萨的奏章,满洲在丧礼中“多备羊豕,大设肴馔”,雍正帝“著大臣等考稽丧礼,定为仪节具奏”,不久议定“嗣后不得以馈粥为名,过情弃礼,致失当年淳朴之俗,违者查出参处”并要求将谕旨“传示八旗,遍令遵行”。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壬戌,朝廷下令“严禁兵民等出殡时前列诸戏,及前一日聚集亲友设筵演戏”。居丧时更不能演戏为乐,即使亲王也不例外。雍正十年(1732)十月,雍正得知裕亲王保泰在圣祖服制未满时在家演戏为乐,最后革去了保泰亲王的爵位。乾隆帝一即位,立即发布了《命丧葬循礼谕》:“著各省督抚等通行明切晓谕,嗣后民间遇有丧葬之事,不许仍习陋风,聚饮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类,违者按律究处。务在实力奉行,毋得姑为宽纵。”
4.《大清通礼》的制定
清代经过顺治、康熙、雍正等近百年的发展,礼制也逐渐成熟,不过很多礼的要求是以令的形式出现,《会典》虽有礼制内容,但难以到达老百姓手上,编订通行全国的礼书以规范官民的生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为此,乾隆上台(乾隆元年)就着手纂修《清通礼》,“前代儒者,虽有《书仪》、《家礼》等书,而仪节繁委,时异制殊,士大夫或可遵循,而难施于黎庶。本朝《会典》所载,卷帙繁重,民间亦未易购藏”。故期望:“将冠、婚、丧、祭一切仪制,斟酌损益,汇成一书。务期明白简易,俾士民易守。”[25]经过二十多年,最后于乾隆二十四年纂修完成,共五十卷,按吉、嘉、军、宾、凶的顺序编排,其中凶礼从卷四十五至卷五十,具体分为列圣、列后大丧,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丧,皇太子、皇子丧,亲王以下、亲王福晋以下、公主以下乡君以上丧,品官丧,庶士丧,庶人丧。至此,清代前期的文化认同完成了丧葬礼制由骑射文化为核心向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建构。
三、丧葬礼制汉文化认同中的满民族意识
以上考察了清初在文化认同背景下进行的丧葬变革,整体来说其变化过程展示了满族统治者将丧葬礼仪逐渐儒家化的过程。但这绝非单向的——满族单向地接受,或汉族单向地给予——满族逐渐汉化,直到被同化的简单过程。从清代前期统治者的角度看,认同中原儒家文化是统治的需要,是一种为我所用的策略。但文化认同也是重塑自身传统,在认同的过程中贯穿着民族意识,即对原文化的认同,这也是清代丧葬礼制既继承了儒家丧葬礼仪的伦理精神又具有自己特色的原因,如丧礼中的割辫、殷奠、百日剃头、摘冠缨等,实际上是满汉两种文化认同的融合。那么,民族意识在清前期的统治者中具体究竟指什么?丧葬礼制又如何调和二者之间的差异呢?
我们先看《清太宗实录》所记的一件事: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癸丑,皇太极到翔凤楼,集诸亲王、郡王、贝勒、固山额真、都察院官,命宏文院大臣读《大金世宗本纪》,上谕众曰:“尔等审听之,世宗者,蒙古、汉人诸国声名显著之贤君也,故当时后世咸称为小尧舜。朕披览此书,悉其梗概,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照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唯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皇太极在学习吸纳汉族文化时就开始为“子孙万世”感到忧虑,害怕子孙效仿汉俗,忘记旧制而亡国。从他最后总结的话来看,其民族意识就是以骑射为核心的满族文化,因为骑射是满族强大并最终获取统治、稳固统治的根本,皇太极的这一思想为清前期的几位皇帝所继承。一方面是对骑射文化的坚持。顺治十三年(1656)二月,福临谕礼部时指出:“八旗各令子弟专习诗书,未有讲及武事者,殊背我朝以武功混一天下之意。”康熙帝依据古代天子礼制,实行“木兰秋狝”,以训练八旗兵骑射作战能力,康熙曾先后北巡秋狝40多次,乾隆更是把秋狝立为家法。康熙帝曾针对满洲贵族包括八旗人等耽于享乐,不愿行猎的情况指出:“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计久远者哉?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26]另一方面加强满族文化建设。康熙十二年(1673),他谕翰林院学士傅达礼等编纂《御制清文鉴》,其缘由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来满族的语言文化不为汉语所湮没。上谓侍臣曰:“此时满洲,朕不虑其不知满语,但恐后生子弟渐习汉语,竟忘满语,亦未可知。且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可通用者甚多,今之戳译者尚知辞意,酌而用之,后生子弟未必知此,不特差失大意。”[27]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代第一部官修词典《御制清文鉴》编撰完成,以它为蓝本编纂而成的还有康熙朝的《御制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乾隆朝的《御制满蒙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等,这些文献为保存满族的语言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从皇太极到乾隆,他们强调以骑射为核心的民族文化意识正是出于满族国家统治的考虑,也是对满族文化的认同。丧葬礼制作为其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自然也要符合其维护民族文化意识的需要。以此为标准,强调丧葬礼制“重孝道、明宗法、显等级”的儒家伦理精神(礼义)为清统治者所认同,但具体操作(礼仪)与其有所冲突时,自然只能对丧仪进行调整。那么,儒家丧葬礼制操作层面对满族究竟有什么影响?我们看几条史料:乾隆十二年(1747)谕:“满洲官员丁忧后三年内并无差使,闲散安居,不但于伊等生计无益,人亦渐至怠惰。”乾隆十四年(1749)又谕:“其用于外任之满洲、蒙古官员,遇有亲丧照例丁忧离任,回京后亦令守制二十七月。但满洲、蒙古不似汉人众多,且旗员亦不应听其闲居不得当差。”[28]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谕云:“国俗于亲丧,服缟素百日而除。朕昔遭皇考大故,欲持服三年。”但圣母皇太后并不同意,谕云:“满洲旧俗,服缟素即不薙发,故只能以百日为断。若百日外仍服缟素,亦不当薙发。经二十七月之久,蓄发甚长,不几如汉人之蓄发户乎?此必不可行之事。且国俗不薙发即不祭神,而旧制从无三年不祭神之事。缟素百日,已为得中,不宜太过。钦此。朕因敬遵慈训而行。”从这三条材料可以看出儒家丧葬礼制丁忧三年对满族统治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守制三年不剃发与汉人无异,且影响其祭神习俗;二是三年闲居在家,“人亦渐至怠惰”,影响骑射训练;三是满、蒙人数少,守制三年影响其对政权的控制。正因为这样,一方面满族一些标识性的丧葬习俗融入儒家丧礼,如割辫、殷奠、百日剃头、摘冠缨等;另一方面在居丧守上采取满汉双重标准,即汉族官员要求严格按照儒家礼制服丧,满蒙离职服丧时间则短得多,直到宣统元年,“礼部议画一满、汉丧制,自是满官亲丧去职,与汉官一例矣”。[15]1857
四、结 语
文化认同是文化形式认同、文化规范认同和文化价值认同的文化认同体系,其中文化价值认同是核心,文化认同实际上是一个价值选择的结果。满清统治者在丧葬上从火葬到土葬,从“死即日便葬于野”到居丧守制以及严密的等级规范,有学者认为这种变化的背后是清前期统治者“处心积虑地裁量、陶铸、重塑、支配着汉文化,从而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最终达到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的融合”。[13]但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恰好是对儒家文化在价值立场、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上的肯定和认可。割辫、百日剃头、服丧时间等操作形式作为文化认同的表现层,它既受文化精神的影响,也是文化精神的实践形式,它的可变性为儒汉文化在丧葬上的融合提供了条件。形式与价值认同最终会形成一种规范,从顺治到乾隆一百多年里形成的丧葬礼制就是一种文化规范的认同,规范最大的特点就是约束性,文化的制度认同就是约束各种不符合丧葬操作规范的文化认同,使整个丧葬礼制按照规范运行,从而实现以文化将满汉各族凝结在一起,维护政权的稳定与统一。
注释:
①时代的经意指人类发展的五种形态,地域的纬意指清由关外转移到中原.从社会发展形态来说,中原儒家文化高于满清游牧文化;从地域来说,清从关外来到被儒家文化所包围的中原,儒家文化也处于优势地位。
②参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53),1962年。
③参见茅瑞徵:《义阡记》,收入张园真编《乌清文献》(卷10),台北图书馆藏清初刊本。
④参见《清实录·顺治朝实录》(卷十,顺治元年十月丙寅条),台湾华文书局1970年影印本。
⑤参见《清实录·太宗实录》(卷十一,天聪六年正月己亥),台湾华文书局1970年影印本。
⑥参见《清实录·顺治朝实录》(卷三,顺治元年正月己酉条),台湾华文书局1970年影印本。
⑦参见《清实录·顺治朝实录》(卷三八,顺治五年四月辛未条),台湾华文书局1970年影印本。
⑧参见《清实录·顺治朝实录》(卷一二,顺治元年十二月),台湾华文书局1970年影印本。
⑨参见《清实录·顺治朝实录》(卷七六,顺治十年六月辛酉条),台湾华文书局1970年影印本。
⑩参见《清实录·顺治朝实录》(卷四,顺治十八年九月庚寅),台湾华文书局1970年影印本。
[1]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
[2]李延寿.北史·勿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3124.
[3]张楚金.翰苑[M]//金毓绂.辽海丛书.沈阳:辽沈书社,1985:2522.
[4]房玄龄.晋书·四夷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3543.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太宗朝[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6]刘昫.旧唐书·北狄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58.
[7]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8.
[8]车吉心.中华野史·清朝(卷4)[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3500.
[9]西清.黑龙江外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66.
[10]刘厚生.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家法礼仪[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0.
[11]王廷相.王廷相集(2)[M].北京:中华书局, 1989:652.
[12]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J].清史研究,2000(2):24-35.
[14]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J].清史研究,2011(4):1-17.
[15]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沈宏格.礼记——丧礼孝道教化的建构[J].社科纵横,2014(3):123-127.
[17]仁和琴川居士.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皇清奏议(1)[M].台北:文海出版社,2006:669.
[18]怀效锋.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14.
[1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213.
[20]王宇.千年古墓之谜[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237.
[21]于善浦,张玉洁.清东陵拾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249.
[22]赵尔巽.清史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857.
[23]清高宗.御制三礼义疏序[M]//四库全书:第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2.
[24]张晋藩.清代律学名著选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94.
[25]刘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钦定大清通礼[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2.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639.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93-94.
[28]吴廷燮.北京市志稿·礼俗志[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12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