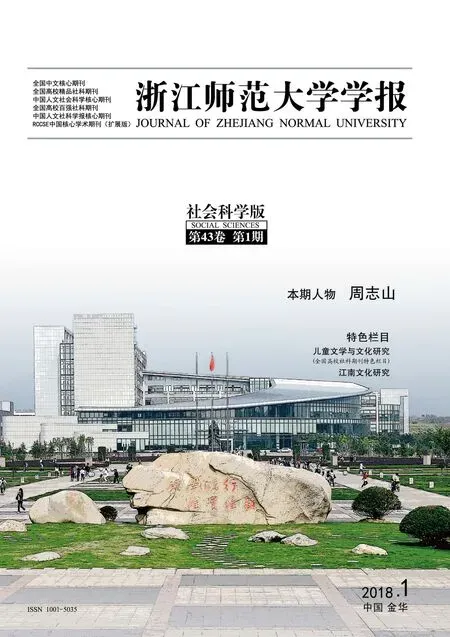创伤视角下凯瑟琳·安·波特“阴暗寓言”中的场景意象与人物群像研究*
魏 懿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442)
作为获得过全美图书奖与普利策奖的双料女作家,美国作家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890—1980)以其精致的小说为读者与评论界所熟知。波特的小说以反映现代人内心的孤独、恐惧、暴力、敌视等负面心理状态为主,揭示人们的异化心理与潜意识活动。她的小说有时也被称为“阴暗的寓言”,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对世界的看法不是光明的,而是阴暗的”。[1]除了小说人物对于外部世界所持的悲观情绪之外,波特的小说被称为“阴暗寓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的小说中存在着一系列阴暗的意象群。这些意象群有的以似真似幻的场景呈现,有的则以典型的人物类型展现在读者面前。某些意象群更是多次反复出现在波特的作品中。正是有了这些意象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人物阴郁的内心世界以及波特本人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所持的悲观情绪。研究这些意象群有助于了解波特小说的思想内涵以及作者的创作初衷,从而更系统深入地了解波特这位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2]的独特魅力。
一、场景意象群
波特擅于营造富有神秘阴郁气氛的场景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捕捉神秘莫测的潜意识活动。充满某种氛围的场景既可烘托人物的心理,又可使读者身临其境地走入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正如波特自己所说:“读者必须发现自己沉浸在作家为他所创造的情景氛围之中,无论那种氛围是快乐的、痛苦的、或甚至是令人厌恶的。”[3]692波特将能否成功营造场景和烘托场景氛围作为一位作家是否杰出的评判标准。
(一)梦境场景
美国现代小说就其描写对象和主题而言可以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超验世界的问题,而另一类则是关于经验世界的问题。[4]波特的小说尤其短篇小说显然关注的是前者即超验世界的问题,例如梦境、幻觉、灵肉分离的虚幻感等。因此其作品中的场景也必然与超经验世界相关联,从而烘托出作者所要营造的场景氛围。在波特的小说中有些场景意象多次反复出现,从而构成固定的模式,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梦境场景。
梦是人类潜意识的表达,“梦境是试图掌握在第一次遭遇中没有充分掌握的东西”。[5]波特小说中所塑造的梦境场景往往都是人物孤独、恐惧、抑郁等异化心理的反应,带有十分明显的创伤性质。在《开花的犹大树》中主人公劳拉发现革命同志欧亨尼奥的死亡是由于过量服用自己带给他的麻醉剂后产生了深深的自责,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自责幻化为以犹大树为主体意象的梦境,“从那棵犹大树上,他摘下暖乎乎、淌着鲜血似的汁水的花,递到她的嘴旁。她看到他的手是没有肉的,几根又小又白的木化石似的枝条,他的眼窝里没有光,可是她狼吞虎咽地吃花,因为那些花既消饥又解渴。”[6]341-342梦境中“淌着鲜血似的汁水的花”、没有肉的手、没有光亮的眼窝等现象都与死亡意象紧密相连,揭示的是劳拉面对革命同志死亡事实的恐惧,而恐惧的根源来自劳拉潜意识里将自己与欧亨尼奥的死联系起来。梦境中欧亨尼奥的鬼魂对劳拉大喊:“杀人犯!”[6]342劳拉在梦境里无疑已将自己与杀死欧亨尼奥的刽子手形象等同起来。梦境中开花的犹大树是一个极具宗教意味的意象,犹大树据说原是一种紫荆属树木,犹大由于出卖耶稣而感到羞愧并最终在这种树上上吊自杀,于是该树被取名为犹大树。可见犹大树具有忏悔赎罪的象征性。梦境中淌着血的犹大树正是劳拉潜意识里对欧亨尼奥的忏悔与赎罪行为的意象化表露,从而使读者发现比起残忍无情、自私自利的革命领导者布拉焦尼,劳拉的灵魂深处仍然闪烁着良知的光辉。波特通过淌血的犹大树、无肉的手、无光的眼、愤怒的鬼魂等具有宗教与死亡寓意的形象,构建起恐惧与忏悔相互交织的梦境,并通过红色和白色这两种极度反差的冷暖色调的组合以及鬼魂愤怒的叫喊声,营造出一幅充满神秘诡异气氛、令人毛骨悚然的梦境场景。
波特小说中的梦境场景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它们对于揭示小说的主题思想起到了提示和呼应的作用。上述《开花的犹大树》中的梦境场景即是一例,梦境中的犹大树揭示了小说的主题——良知的忏悔。又如在《斜塔》中主人公查尔斯·厄普顿在目睹了德国柏林各种蠢蠢欲动的社会现象——严重的贫富差距、青年人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推崇效仿、严重的通货膨胀、以战争洗刷一战战败之耻的企图等——之后做起了梦,“查尔斯朦朦胧胧地睡着了,梦见这所房子快要烧光,处处都是无声无息地在颤动和跳跃的火焰。……他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望着那所象塔一样高的房子的黑沉沉的骨架屹立在熊熊烈火中。”[6]483查尔斯梦境中熊熊燃烧的房子是他在清醒时所看到的德国社会的缩影。它寓意着即将爆发战争的德国,它不仅把周围的一切拖入大火之中,也将把自己烧得只剩下“黑沉沉的骨架”。这是查尔斯先前的所见所闻在梦境中的形象化再现,是其潜意识中对于德国乃至欧洲前途焦虑情绪的集中释放。梦境中被大火烧得只剩下躯壳的房子与小说中另一个重要意象——摇摇欲坠的斜塔石膏模型——形成了现实与潜意识中危机四伏的欧洲社会的意象呼应,从而将超现实的梦境世界与现实中的经验世界联系在了一起,预示着一个即将爆发大灾难的岌岌可危的西方世界。又如在《马戏》中,主人公米兰达在看完一场怪异的马戏之后做起了噩梦,梦中她看到的是“快要摔死的穿邋遢的白罩衣的男人那张吓得没命的脸”。[6]405“穿邋遢的白色罩衣的男人”是米兰达在看马戏时见到的一个“脑壳白得象骨头,脸白得象白土”[6]401的小丑,梦境中这个小丑形象以全身白色的男人形象出现,它象征着死亡,暗示着米兰达的死亡意识的开启,同时也预示着米兰达的童真已经变质。[7]波特通过梦境场景中这些神秘莫测又具有高度象征寓意的意象不仅营造出梦境虚幻诡异的特质,同时也揭示了小说的主题思想。
(二)闪回场景
闪回是潜伏的记忆在某种状态下的忽然重现。它可以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闪回,也可以是以“幻视”或是“幻听”形式出现的闪回。现代创伤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创伤的潜伏期并不意味着忘记现实,而且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它;创伤存在于经验自身的内在潜伏期中。”[8]闪回与噩梦一样,其本质都是一种心理创伤,但闪回多发生在人们的意识相对清醒的时刻并且人们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而梦则发生在人们的潜意识层面。
波特的许多小说关注超验世界,这使得她的小说作品除了描写潜意识的梦境之外,也自然地关注发生在意识层面的闪回场景。在短篇小说《坟》中,九岁的米兰达在一次外出游玩过程中目睹了哥哥保罗打死一只怀孕的野兔,然后将其剥皮并取出母兔腹腔内已经成形的小兔崽。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极大地触动了当时年幼的米兰达。尽管后来这件事在米兰达的脑海中渐渐被淡忘,但二十年后的某一天,往事以闪回的形式再次出现:“她莫名其妙地吓了一跳,蓦地张大眼睛站住,一阵幻觉把眼前的景象搞模糊了。……这天天气酷热,集市上一堆堆生肉和发蔫的花朵散发出的气味,就跟她那天在家乡空荡荡的墓地里所闻到的那股腐烂的芬芳掺混的气味完全一样。”[6]415波特在描写这一闪回场景时动用了视觉、体感和嗅觉等多种感官感受来营造和烘托闪回瞬间米兰达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将两个时隔相差二十年的时空场景联系在了一起。
与梦境场景一样,波特笔下的闪回场景也是具有高度象征寓意的意象群。二十年前米兰达所目睹的那只被哥哥杀死的母兔的闪回意象象征着米兰达童年对于死亡以及性的意识在二十年前已被开启。在小说结尾处,米兰达在闪回的记忆之中“清晰地看见哥哥,他那童年的脸盘儿她早已忘记,如今他又站在灼热的阳光下,还是十二岁那副模样,两眼流露出得意而从容的微笑,一再在他手心里翻弄那只银鸽子”。[6]415那只原本作为棺材上的装饰物的银鸽子象征着米兰达的童真也早已随着二十年前哥哥杀死母兔的那次事件而丧失了。小说中处于不同时空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动物意象群将小说的主题——天真的堕落——隐秘而含蓄地传达给了读者。波特为了凸显闪回的真实性有时会使用声音效果,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例如在《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成年后的米兰达在听说了有关一战的惨烈战况后出现了闪回,“所有的尖叫声和嘶哑的吼叫一起响起来,把空气都震得颤抖了,在她头上翻滚和猛撞,好像响声刺耳的暴风云,后来,那许多声音变得只剩两个词儿,一起一伏,在她耳朵旁叫嚷。危险,危险,危险,一切声音都在说,打仗,打仗,打仗。”[6]424随后米兰达的脑海中出现了“戴着德国钢盔的骷髅”,“刀尖上挑着一个在扭动的赤身裸体的婴孩,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个大石罐,罐上用黑体字表明有毒。”[6]229这些亦真亦幻的闪回意象透露出米兰达对于战争的恐惧与厌恶。尽管她并没有经历战争,但他人对于战争的描述足以对米兰达的心理产生剧烈的创伤影响。小说的反战主题通过米兰达意识中的闪回场景呼之欲出。
值得一提的是,波特小说中的人物在经历闪回场景之后会出现某种顿悟或是人生态度的转变。与梦境场景中人物醒来后尖叫或是“直打哆嗦,害怕再睡熟”[6]342等消极态度不同,经历闪回场景的人物往往能冷静积极地面对自己内心的创伤。如《坟》中米兰达在闪回意象中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早就丧失了童真并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而《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米兰达在经历战争恐惧的闪回场景之后变得更为坚强,意识到“啊,不行,这样可不对头,我再怎么也不能这样失魂落魄了”。[6]242-243又如《老人》中成年后的米兰达在回忆自己的童年以及了解死于令人窒息的老南方家族的艾米姑妈的悲惨人生之后,脑海中闪现的是走入坟墓的南方美人。米兰达意识到“我不会再在他们的世界上住下去了”。[6]97闪回场景使原本遭受打击的个体变得成熟并开始思考如何把握自身的命运,这使得读者在波特的“阴暗寓言”中见到了难得的一丝光亮。
(三)暴力场景
暴力场景在波特小说中颇具特色,总能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在《一天的工作》中,哈洛伦先生由于经济大萧条而丢了工作,在酒精作用下误将熨斗丢向哈洛伦太太,导致了哈洛伦太太“额头上凸起一个肿块,青一片紫一片的”。[6]443面对这样一个不争气的丈夫,哈洛伦太太忍无可忍,长期的精神压抑需要得到释放,于是她采取了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方式予以反击。“她把浴巾绞干,在一头打了几个很硬的结,试着在桌子边上啪地抽了一下。她走进卧房,站在床旁,使出全身劲儿把打结的浴巾劈头盖脸地向哈洛伦先生抽去。”面对妻子的抽打,哈洛伦先生则陷入麻木状态之中,“他把枕头拉过来盖在脸上,又平静地躺着,这一回干脆睡熟了。”[6]444作为弱势一方的妻子通过暴力的方式来报复丈夫对于自己肉体上的伤害,但她并没有像其丈夫那样使用熨斗之类的硬物件,而是使用了绞干并打成结的浴巾。绞干打结的浴巾这一意象在哈洛伦夫妇的肢体暴力场景中具有双重寓意。一方面,它象征着夫妻生活的枯燥与纠结,是哈洛伦太太对于丈夫现状的不满与愤恨;另一方面,浴巾比起熨斗而言算得上柔软的物体,打成结的浴巾既能好好教训丈夫一顿,但又不至于对他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从中读者能体会出哈洛伦太太对丈夫的关爱。即使在怒火中烧的情况下,女性比起男性似乎更能保持一份理性。哈洛伦太太对于丈夫既爱又恨的复杂情绪通过浴巾这一意象得到了微妙的展示,这也使得这场夫妻间的肢体暴力场景显现出女性化的特质。
在长篇小说《愚人船》中也有一个类似于哈洛伦夫妇的两性肢体暴力场景的描写。特雷德韦尔太太在被喝醉酒的丹尼误认为舞女帕斯托拉时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她用包着金属的高跟鞋鞋底抽打丹尼:“她打他的时候感到的愉快是那么强烈,一阵敏感的痛感从她的右手腕开始,往上射去,直痛到她的肩膀和脖子。那尖尖的包着金属的高跟每打一下,他的脸上就会出现一个慢慢地呈现猩红色的、半圆形的小印子。”[9]634比起浴巾,高跟鞋这一意象更具有鲜明的女性特质。特雷德韦尔太太抽打丹尼的力度也远比哈洛伦太太大得多。波特在描写这一暴力场景时完全站在了特雷德韦尔太太的立场上,似乎饶有兴致地描绘着她抽打丹尼时的快感。强烈的快感、敏感的痛感、丹尼脸上猩红色的小圆点都在宣泄着某种压抑已久的情绪。在波特营造的暴力场景中,施暴方是女性而被施暴方却是男性。比起梦境场景与闪回场景,波特对于暴力场景的描写似乎更具性别倾向。究其原因或许与波特的四段不幸的婚姻有关。在第一次与第三次婚姻中波特曾声称自己受到了丈夫的暴力威胁。[10]229或许波特正是想通过这些为自己的尊严而“搏斗”的女性来宣泄自己对于男性以及失败婚姻的愤懑。这也使得波特小说中的暴力场景具有了激进的女性主义倾向。
综上,作家往往会选择不同的意象来描写场景,表达自己的思想。波特在她的场景描写中常常选择体现恐惧、阴郁、血腥、暴力的意象。这些意象群组成一幅幅散发着浓重阴郁气息的场景,衬托出人物压抑扭曲的内心世界。这是波特的小说被称为“阴暗寓言”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波特在描写这些场景意象群时调动了各种感官体验,例如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等,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氛围感,使得原本神秘或是转瞬即逝的场景变成了可见、可触、可听甚至可嗅的画面。这大大增强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也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性。
二、人物形象群
波特认为自己的小说是“当这个世界在千年变化中步入膏肓,全社会处于怪异的混乱之际,我以秩序、形式和叙述的方式所能实现的成就”。[9]12-13可见,波特的小说所要表达的是现代人在怪异混乱的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而其小说中的各色人物形象正是表达小说主题思想的重要媒介。波特小说中的人物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大都表现出惊恐、矛盾、无助等消极反应。即使有些人物对自己的命运做出过反抗,他们最终也会变得消沉或是付出巨大的代价。从本质上而言,波特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创伤性质的悲剧人物。尽管波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众多,但可以归为以下几类:受伤的儿童、矛盾的女性、消沉的男性。这些人物构成了波特“阴暗寓言”中的人物形象群。
(一)受伤的儿童
在波特发表的26篇短篇小说中直接以儿童为主人公的作品就有七部,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比重,可见波特对于这一人物类型的偏爱。童年是人一生中最美好,同时也是最需要关爱的一段时光。但波特笔下的童年却充满着无助和爱的缺失。例如《他》中那个不会说话,没有自己姓名,始终被父母和兄弟姐妹当作无偿劳动力的孩子。在生病无法继续为家庭劳动之后,“他”无情地被母亲送去了县救济院。又如《下沉通往智慧之路》中的男孩子史蒂芬在母亲与继父之间周旋,却始终得不到他们真正的关爱。波特小说中的童年常与恐惧、抑郁、甚至仇恨联系在一起,儿童形象也大都表现出面对成人世界的惊恐与不知所措。例如《处女维勒塔》中的维勒塔在被自己的表兄卡洛斯亲吻之后表现出极度的惊恐,“她听到自己在难以克制地发出尖叫。”[3]37过早开启的性意识在维勒塔原本天真烂漫的童年上掘开了一个缺口,维勒塔拒绝阅读原本十分崇拜的卡洛斯写的诗歌,她感到“一种令人痛苦的不快乐感时不时地占据着自己,因为她无法解决盘绕在脑海里的那些问题”。[3〗38童年对于性的过早接触使得维勒塔失去了“处女之身”,也使其对异性和性爱充满厌恶。这对于维勒塔成年后的人生观、爱情观、婚姻观所造成的破坏影响可想而知。类似的情况在《马戏》和《坟》中也可以看到。当初次面对外部世界中蕴含着死亡、性、生育等意象时,主人公米兰达或是表现出惊恐、尖叫、不敢入睡,或是表现出精神恍惚、不知所措,极力将自己所见到的场景压制于潜意识之中以至于二十年后相似的场景闪回对成年后的米兰达造成二次伤害。这些处于惊恐恍惚中的儿童表明他们已经处在了性和死亡的边缘,并正在从天真中堕落。天真堕落的后果往往是变得邪恶。长篇小说《愚人船》中被称为“小恶魔”的双胞胎兄妹拉克和力克便是过早丧失儿童天真后的产物。他们恃强凌弱、偷窃、抢劫、相互厮打甚至将哈巴狗贝贝丢进大海并间接导致跳海救狗的埃切加拉伊溺水身亡。成人世界中的暴力、残忍、邪恶等特质都集中出现在这对年仅六岁的兄妹身上,这是儿童过早失去童年天真后所产生的可怕后果。波特在谈论自己的童年经历时曾说:“我不相信童年是一段幸福的时光。相反,童年充满绝望的、无法治愈的、苦涩的悲伤与痛苦的岁月,充满支离破碎的破灭了的幻想。”[3]1016波特认为,童年是人生一切绝望、悲伤与痛苦的开端,童年所遭遇的一切都会对今后的人生产生持久的影响。通过这些失去天真的受伤儿童形象,波特试图从人类创伤的源头,“努力了解西方世界人的生活中这个巨大而可怕的缺陷逻辑”。[3]781
(二)矛盾的女性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波特在其小说中自然会关注现代西方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波特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具有独立的女性意识以及叛逆的性格。这主要体现在她们能敏锐地意识到周围环境与自身女性身份的格格不入。例如《开花的犹大树》中的女主人公劳拉一开始便已经意识到革命领导者布拉焦尼是一个打着革命幌子为自己谋私利的家伙,自己只是布拉焦尼意欲控制玩弄的尤物,劳拉从而萌生了逃跑的念头。在《老人》中米兰达在了解到艾米姑妈的悲剧之后,意识到老南方家族“吃人”的本性。她成年后毅然远离家族,明确表示“我不会再在他们的世界上住下去了”。[6]97到了《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米兰达独自一人面对来自生活、工作、爱情、社会乃至死亡的种种压力,俨然已是一个具有强大内心的女性形象。《愚人船》中的主人公珍妮更是一个具有时代叛逆精神的女性艺术家。她为了自己的理想,毅然离开自己的家族与爱人戴维私奔前往欧洲学画,过着当时被认为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式的流浪生活。即使是在像《一天的工作》中的哈洛伦太太和《愚人船》中的特雷德韦尔太太这些传统女性人物身上,读者也能看到她们毅然捍卫自己女性尊严的举动。在面对男性的暴力与侮辱时,她们不再是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而是敢于以牙还牙、以暴制暴。正如查理斯·阿伦分析波特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时所指出的,这些女性人物是“孤独的女英雄”。[11]这些叛逆的女性形象既是波特作为一名具有独立女性人格的作家的意识反映,也是当时西方社会对于普通女性影响的真实反映。
然而,鲜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些“孤独的女英雄”的叛逆常常并不彻底。例如在《开花的犹大树》中劳拉的“叛逆”更多时候是停留在意识层面,她并没有真正采取行动远离虚伪的革命领袖布拉焦尼。在《一天的工作》中,尽管哈洛伦太太对于丈夫与麦考克里之流的投机政客厮混表现出极度不满,但在小说结尾哈洛伦太太还是默许了丈夫的选择。在《愚人船》中女画家珍妮虽渴望保持女性艺术创作的独立性,但在戴维的影响之下她还是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画风,向男性审美情趣做出了妥协。即使对于那些真正将叛逆付之于行动的女性,波特似乎对她们的行为也表现出质疑。例如《老人》中的米兰达为了摆脱家族的束缚,毅然离开家族,但这也意味着她抛弃了家族,以致于深爱她的父亲对她变得冷漠甚至仇视。在《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米兰达独自在纽约忍受着孤独,在濒临死亡时没有一个家人在身边,可谓处境凄凉。米兰达最终并未获得她所渴望的自由与爱情。这些“孤独的女英雄”与波特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一样也是悲剧人物。戈伟那在评论波特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时认为,这些叛逆的女性人物所体现的一大特征就是“复杂的矛盾性”(complicated ambivalence),即“波特一方面赞扬19世纪20年代所宣扬的女性独立……与此同时,她又从未动摇过这一信念即家庭、婚姻、生育是女性成功的标志”。[12]“复杂的矛盾性”使得波特小说中诸多女性人物兼具叛逆与妥协的双重特质。即使对于像米兰达这样大胆背叛传统的女性人物,从在小说中为她设计的“众叛亲离”的结局来看,波特似乎对这一类“叛逆”女性的认同也有所保留。这些矛盾的女性形象真实地反映出二十世纪上半叶追求精神自由与独立的女性所处的尴尬处境。
(三)消沉的男性
与女性形象相比较,波特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则显得较为消沉。他们有的始终沉浸在自己扭曲的内心世界里不愿与外界交流,例如《中午酒》中的赫尔顿;有的在经受了生活的不如意或打击之后变得自暴自弃或是一蹶不振,例如《一天的工作》中的哈洛伦先生和《中午酒》中的汤普森先生;有的则明显缺少男性应有的担当和责任感,例如《玛丽亚·孔塞浦西翁》中的胡安。作为一名丈夫,胡安抛弃了自己的妻子玛丽亚,与自己的情人罗莎私奔。在无法维持私奔生活的窘境之下,胡安又回到了妻子玛丽亚身边。胡安虽有忏悔之心,但却没有任何忏悔的行动。在得知妻子杀死了情人罗莎之后,胡安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对于两个女人所带来的伤害,而是将这一切归结为神秘的命运捉弄,“本来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欢乐、如此单纯,而突然变得如此混乱不堪。”[6]262《愚人船》中的大部分男性形象更是“消沉的男性”的大集合。弗赖塔格先生由于娶了一位犹太妻子而陷入自我身份认同的尴尬处境之中。他甚至异想天开地认为,自己的日耳曼血统能够净化自己妻子犹太人的血液。面对船上德国乘客对于自己以及妻子犹太人身份的讽刺与羞辱,弗赖塔格先生所做的只是沉默。船上其他的乘客,例如戴维、舒曼医生等则是缺少主动去爱的能力。当女伯爵向舒曼医生表达爱意的时候,舒曼医生却始终躲躲闪闪,显得犹豫不决。当女伯爵被押解下船之后,舒曼医生又陷入深深的内疚与自责之中。戴维对于珍妮的爱情也是纠结不清。尽管戴维深爱着珍妮,但他却不知如何维持这份爱情。他所做的只是彼此伤害,正像珍妮对戴维喊到的那样:“难道非闹成一场痛苦的分离不可吗?难道非要我们闹得筋断骨折不可吗?”[9]652船上另一位男性乘客约翰为了能和西班牙舞女孔查寻欢,但又苦于经济受到自己的舅舅格拉夫先生的控制,在孔查的怂恿下曾一度想置舅舅于死地。但由于胆小与良知的发现,约翰始终不敢跨出谋财害命这一步,但又始终无法割舍对于孔查的情欲,从此陷在肉欲与良知的分裂之中无法自拔。约翰的舅舅格拉夫先生更是将波特笔下的众多消沉男性的特质集中于一身。格拉夫先生深信自己拥有上帝赋予的神力,能为世人消除肉体乃至精神上的痛苦。但他自己却肌肉萎缩、气息奄奄、连行走的能力也已丧失,只能坐在轮椅上,由外甥约翰到处推着走。他对上帝赋予自己的神力与勇气感到自豪,但面对步步靠近的死亡他又感到无比恐惧,“他像一个待决的囚犯看到行刑的斧头那样吓得缩成一团”。[9]249他想要拯救他人,但自己的性命却时常受制于他人。格拉夫先生故作强大的意志与他萎靡孱弱的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讽刺。波特小说中的主要男性人物身上表现出的无能、犹豫、孱弱、消极回避、缺少担当等特征是波特作为一名女性对于男权文化的旁观审视。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些消沉的男性无法承担起自身的职责。这或许也是波特对于整个20世纪上半叶陷入一片混乱的西方世界的一种反思。
综上,波特小说中主要的三类人物是具有现代悲剧特质的人物群像。童年的创伤是成年后创伤的源头,而女性的矛盾性与男性的消沉特质又是创伤的延续与深化。这三类主要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互为补充,表现了波特对于病入膏肓的西方社会的深入观察,并丰富了波特“阴暗寓言”的表现力。
三、阴暗寓言的产生与意义
波特小说中众多的创伤特质的场景意象群与人物形象群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作者的个人原因与社会原因。
波特有着一段充满创伤的成长经历。波特的母亲在生养波特的妹妹时,由于难产而死。母亲的意外死亡对于当时年仅两岁的波特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波特相信是她自己导致了母亲的死亡。……波特始终无法将自己从这一想法即自己是母亲死亡之罪魁祸首中脱离出来。”[13]83母亲去世后,父亲带着波特和刚出生不久的波特妹妹来到祖母卡特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农场生活。波特的父亲在丧妻之后始终郁郁寡欢,对于孩子缺乏物质上的照料与精神上的关怀。波特由于童年生活的贫困而责怪父亲,认为他没有担负起作为父亲的责任,甚至将自己后来无法适应婚姻生活归咎为童年时父爱的缺失。[10]50-51幼年父母之爱的缺失导致波特一直处于惊恐无助的状态之中。其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惊恐、害怕、不知所措的儿童形象正是波特自身童年的真实写照。成年之后四段失败的婚姻也使得波特心力交瘁,“我所经历的每次爱情和婚姻不仅在肉体和物质方面折磨着我,而且对我的精神也造成了损害,使我对人类爱情天生的信仰完全被打碎了。”[3]209此外,波特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独自在外打拼,微薄的小说稿费也常使她的生活变得异常拮据。正如她调侃庞德所说的那样,“他(指庞德)时常会抱怨自己难以支付房租,但你立刻就会明白,付不出房租和成为一名作家是紧密相连的。”[3〗576这些成长和生活经历中的种种不幸与创伤使得波特始终缺乏安全感。当这些负面情绪幻化在文学作品中时,便成为了波特“阴暗寓言”中各种充满死亡、创伤、暴力、恐惧、扭曲的场景意象和人物形象。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波特的“阴暗寓言”也不例外。波特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正值美国乃至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使得人心惶惶,人们普遍生活在恐慌与焦虑之中。波特小说中充满恐惧、死亡与暴力的场景以及那些面对外部世界显得惊恐焦虑的人物都是那个特定时期人们对于战争、破坏、屠杀、死亡等重大创伤事件的艺术化表现,正如波特自己所说的,“生活在这世界上是一种恐怖的经历、人类的想象力也能产生恐怖。艺术家应该指引你用你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视角进行观察。”[3]692波特完成长篇小说《愚人船》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但却卷入到与苏联的冷战之中。核战变成了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人们对于核战的恐惧绝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疯狂的原子弹成功地使世界各国人民达到了道德愤怒的最高点;许多以前从来没有理由感到恐惧的人现在变得极度恐惧。对于这个星球上绝大部分居民而言,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令人绝望的危险之地”。[3]828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让波特感到恐惧和焦虑的话,那么以核战为威胁的冷战则让波特对这个世界感到了绝望。《愚人船》中那些孱弱、无能的男性正是波特对于以男性为统治阶层的各国政府一次次将世界推入恐惧深渊的形象化展现。波特曾声称,“从有意识和有记忆的年纪起,直到今天,我这一生始终处在世界性灾难的威胁之下”。[3]718可以说,恐惧伴随着波特的一生,这种恐惧感来自她的成长经历与时代背景。波特笔下的“阴暗寓言”体现的正是她对于人类以及世界命运的焦虑。
值得一提的是,波特的“阴暗寓言”是揭示和描写现代人类阴暗心理的美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比波特略早的福克纳就在其小说中描写了不少扭曲阴暗的人物形象。国内学者钱青指出:“波特是第一位杰出的南方女性小说家。她的小说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为尤多拉·韦尔蒂所继承,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又为弗兰纳瑞·奥康纳所继承。”[14]波特之后的一大批作家(例如:杜鲁门·卡波特、乔伊斯·欧茨、索尔·贝娄等)也都以刻画人类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恐惧、孤独等阴暗心理而著称。
波特的“阴暗寓言”展示了现代人在急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状态与走向。如何应对、纾解和调整这些人类负面的异化心理仍是当今处于急速变革中的社会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就这一意义而言,波特的“阴暗寓言”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人的心理和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价值。
[1]MUHLEN N. Deutsche, Wie Sie im Buche Stehen[J].Der Monat, 1962(12):38-45.
[2]GARY E R. Death and Katherine Anne Porter——A Reading of the Long Stories[M].Stillwater: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3.
[3]PORTER K A. Collected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M].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2008.
[4]钱满素.美国当代小说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14.
[5]CARUTH C.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 and History[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43.
[6]波特.波特短篇小说集[M].鹿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7]魏懿.天真的堕落——凯瑟琳·安·波特《马戏》与《坟》的创伤视角解读[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4):4-7.
[8]CARUTH C. Trauma: Exploration in Memory[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8.
[9]波特.愚人船[M].鹿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10]HENDRICK G.Katherine Anne Porter[M].New York:Twayne,1965.
[11]ALLEN C.Katherine Anne Porter:Psychology as Art[J].Southwest Review,1956(Summer):223-230.
[12]GIVNER J. Katherine Anne Porter: A Life[M].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6.
[13]TITUS M.The Ambivalent Art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M].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5.
[14]钱青.美国20世纪文学选读:下册[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