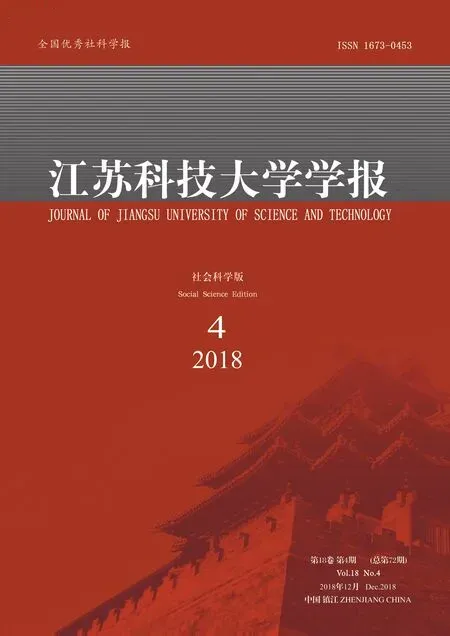性别表演视域下《野草在歌唱》的主体建构解读
仇湘云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1925年,年幼的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跟随父母来到了南罗德西亚(现津巴布韦),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期。她的父亲在一战中失去了右腿,终身饱受“炮弹休克症”的折磨。她的母亲放弃了护士职业,希望与丈夫在非洲大陆能够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处女作《野草在歌唱》(TheGrassisSinging)便是以其母亲艾米丽·麦克维格为原型创作出来的,莱辛借此表达了对坚强勇敢的母亲的无限同情与深深敬意。正如作家在自传《刻骨铭心》中写的那样:“母亲就是一个悲剧人物,心怀勇气和尊严地过着自己那不尽如人意的日子。”[1]15《野草在歌唱》中的女主人公玛丽·特纳正是一位像莱辛母亲一样苦苦挣扎的穷苦白人女性。她穷苦而聪慧,虽然经历了不幸的童年、压抑的婚姻以及畸形的恋情,然而在每一个命运的关口,这位勇于抗争的女性都曾试图打破生活的枷锁,开辟寻求自我的全新道路。为此她不断对自我身份进行重塑,试图挑战男女性别秩序,希冀生发新的机遇,拓展自我生存空间。
《野草在歌唱》向世人展示了一幅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社会生活画卷,“南部非洲的社会现状被第一次毫无遮掩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充满激情和震撼力”[2]95。国内学界在提及这部作品时,往往聚焦于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或者空间叙事等视角,不断拓宽阐释女主人公玛丽人生悲剧的研究路径。在2001年到2018年这十余年间(截止7月5号),“中国知网”上发表的有关这部作品的期刊文章有197篇,硕博士论文125篇。其中论述“主体建构”的文章有3篇,分别采用了拉康的象征界论、福柯的规训权力论和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来进行阐释。以上研究均未关注到玛丽性别身份的动态特质和流动性,忽视了玛丽在性别和社会建制的缝隙中不断调整、妥协甚至是抗争的自我重构努力。在堪称经典的《性别麻烦》(GenderTrouble)和《身体之重》(BodyThatMatters)这两部理论巨著中,著名的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揭示了性别的建构性质和机制,提出主体的性别身份,无论是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并非制度、话语以及实践的原因,而是它们的结果[3]40。不是主体创造了制度、话语和实践,而是以上这些因素通过决定主体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倾向创造了主体。鉴于此,笔者试图从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入手,研究玛丽主体建构悲剧的根源、过程和必然性,剖析文本对于“主体本质论”的解构式隐喻,籍此揭示社会机制与文化权力对于身份认同的深刻影响关系。
一、 “凝视”与逆向“凝视”
玛丽从十六岁起就来到城里,过起了未婚女性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她热爱并享受这样的日子,以为这样就可以逃离没有爱的原生家庭,与肮脏嘈杂的故乡和整日争吵的父母一刀两断,从此独立自主了。然而,年过三十还未结婚的玛丽俨然成了世人“审视”的对象,成了别人口中奇怪突兀的他者存在。人们“凝视”着这位有些古怪的老姑娘,看到“她的头发依然梳成少女样式披在肩上,她也常常穿着浅色的少女式上衣”[4]30,孤傲刻板,不合时宜。福柯认为,“无声的压制、监视性注视和规训性力量在现代西方文化和整个社会范围中无所不在”[5]71。“凝视”是权力运作的方式,在现代社会这一“大监狱”里,人人都可以成为被“监视” “察看”与“审视”的对象。换言之,被观看者沦为了“看”的客体,感受到来自观看者的权力压力,从而内化了观看者的价值判断而实施了自我物化。然而,主体的性别身份是动态的,具有流动性,并非固定和既定的,用巴特勒自己的话来说,具有表演性。她认为主体是一个表演性的构建,具有过程性、暂时性、重复性等特征,这就开启了抵抗主客体管控的霸权话语的可能性。
众人“凝视”背后的制度支持、规训、建构产物以及压迫性让玛丽隐隐感到不安,这种忐忑的羞愧感用萨特的话来说是玛丽意识到“我的确是他人正在注视着和判断着的那个对象”[6]286,然而玛丽本能地拒绝这种“供认”,拒绝将他人的凝视结果体验为“自己的各种可能性的凝固化和异化”[7]85。她模模糊糊地感觉“需要另一种生活”[4]31。于是她在社会规范的许可范围内进行了妥协和调整,“解下了头发上的缎带”,放弃了“童式上装和裙裤”[4]33,最重要的是,“她开始注意周围有没有可以和她结婚的人”[4]34。玛丽的行为体现了她的性别表演策略:社会地位和主体身份的确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既然主体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是通过反复表演建构起来的“过程中的主体”,那么如果想要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必须在社会规范下进行“合乎时宜”的协商和妥协。
玛丽与丈夫迪克的最初相遇始于影院中后者对前者的一次无意的“凝视”。“从他头顶上方的什么地方投下一团光亮,照见了一张脸蛋儿和一头亮闪闪的浅棕色头发。那张脸蛋儿好像浮在空中,渴望向上浮去,在那奇怪的绿色灯光之下,显得艳丽非凡。”[4]37-38这一幕令迪克心猿意马、浮想联翩,急切地想要知道这位可人儿的名字。而出了影院的大门,玛丽看上去老派又普通,与刚才灯光下的形象相差甚远,令迪克大失所望,连多看一眼的兴趣也没有,更谈不上去主动接近。在又一次邂逅时,“他不断地斜瞅着她,发觉灯光真是奥妙无穷,能够把一个并不十分富有吸引力的平平凡凡的姑娘照得那样美,那样稀奇”[4]40。在这些表示“看”的方式里,看与被看的行为构建了主体与他者,而女性就是男性社会的“附属的人,是与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8]11。顺着迪克的视线,人们只看到一个性情模糊、思想扁平以及灵魂缺失的雌性物体,其本来面目被掩盖、遮蔽和扭曲,只剩下肉欲的躯壳呈现在男人的视觉判断里。由此可见,在男性的“凝视”之下,女性沦为被观赏把玩、论值估价的对象,变成物化了的他者,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正如多恩(Doane)所言,“女性被剥夺了‘凝视’的权利和主体性,一次又一次地沦为男性窥视欲的客体”[9]2。而迪克最终决定要迎娶玛丽,并不是因为他深深地爱上玛丽,而是基于“他孤寂,需要一个妻子,尤其是需要子女”[4]39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显而易见,父权制下的女性仅仅充当了男人欲望发泄的工具和生儿育女的机器,是一个“无生命的、无形的、无法被命名的非物体(no-thing)”[10]36,就这样,女性的主体存在完全被无视和抹杀了。
在巴特勒看来,主体和客体的位置并非固定不变,通过对过去单一中心的解构与置换,原本处于边缘的、甚至被埋没的身分完全可以走向中心。女性的主体性总是“与凝视的结构以及权威之眼的定位密切相关”[11]13。倨傲的凝视者同时也可以是被凝视的对象,被凝视者可以通过逆向凝视的手段实施主客体位置的对调,存在着“在社会文化话语下主体颠覆自身身份的可能性”[12]92。这就是巴特勒理论的核心所在,即性别乃至一切身份都具有表演性。通过性别表演,主人公玛丽的身份建构是动态的,具有反客为主的位移能力。玛丽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一个女人来到这里,点缀了这所空无一物的小屋”[4]46。这里的“点缀”一词清楚而又残酷地点出了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赘生物那种可有可无的客体属性。自然,婚后的玛丽也就不可能成为家庭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只不过和添置的家具摆设性质一样,是男人的财产和物业。玛丽不甘心被定格为一个平庸无能、需要依附丈夫的家庭主妇,因为她一直害怕重蹈母亲的覆辙一辈子无力主宰自己命运。她渴望摆脱男性单方面投射的“凝视”,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构建主体身份。巴特勒认为,性别身份或者说人的主体性是可以“重新利用、重新部署”的[13]86,是通过对各种行为标准的不断重复一步步建构起来并小心呵护的暂时身分[14]140。对此,玛丽进行了种种尝试和努力:首先她决定学会土语,这样可以直接和黑人交流,不需要丈夫从旁翻译。客人来访时迪克理所当然地让玛丽谈谈女人家的话题,“料定她对于人生并没有多大的奢望”[4]71。这样低看自己的话语让玛丽很气愤,于是她开始学着规划农场,打理家业。玛丽买了小册子回来学习如何养蜂,为农场开辟新的盈利项目;她主动跟着迪克下地,协助管理黑人;她接管了家庭账目,掌握财政大权。
性别表演理论解构了男女性别身份和主客体,对其合法性、自然性和永久性不断进行质疑和批判。因为性别具有“未完成性”和“可模仿性”,玛丽就必须通过不断重复来获取合法的地位。因此,随着玛丽持续不断的积极表演性做法,她的主体身份也似乎进一步得到确立。玛丽不仅“脑子里对整个农场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一下子就看清了他们贫困的原因”[4]109,更开始“好奇地”凝视起了自己的丈夫。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分析过两性带有探询意味目光的不同指向:“在欧洲文化和神话中,好奇一直与特定的女性观看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观看欲可以混同于求知欲。男性的窥淫性观看是主动的,指向被动的、情色的女性客体。女性的好奇性观看也是主动的,但指向的是一个秘密、一个谜、一种神秘。”[15]111这个秘密就是玛丽身上被逐渐唤醒的自我身份意识,或者说是她下意识主动以审视者的立场来廓清眼前这个男人的面目,从而实现主客体身份逆转的意图。在与丈夫从邮局回来的路上,“她不停地斜瞟着迪克,在他身上看出了她早就该看出的小地方。当他抓着方向盘的时候,他那双被太阳晒成咖啡色的瘦手不停地发抖,不过抖得很轻微,几乎让人看不出。她觉得那种颤抖是软弱的标志”[4]79。在迪克养蜂失败又大谈养猪时,玛丽“觉得他不仅是一个又瘦又长、弯腰屈背的男人,而且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满腔热诚被泼了冷水以后,还要一股劲地要拼命干到底”[4]82。至此,玛丽完全看清了丈夫的本质:怯懦无能、保守固执。经营农场毫无章法,做事总是异想天开,最终往往半途而废。她用犀利的目光洞察了迪克的一切,对于丈夫、对于他们夫妻间的关系以及农场的前途更是看得明明白白。
性别表演让玛丽发挥了对“凝视”的反向作用,获得了全新视角,力图避免“身体自我被投射进视觉他异性(visual alterity)之场域”[10]127。然而父权制的根深蒂固使得女性的这种自觉身份重塑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玛丽试图在社会规范允许的框架内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改变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但发现“她好像有两副面具,这一副和另一副是矛盾的”[4]84,她深陷自我矛盾、苦苦挣扎的身份认同囹圄,其表演策略在当时的严苛社会环境遭遇巨大阻力,根本无法完成对自我主体性的构建。在邻居查理夫妇第一次造访时,他们“目光锐利地望着整个房间,把每一个坐垫都做了评估”[4]69。他们扫视着玛丽的住所,打量着她的家居布置,居高临下地施舍对玛丽窘迫生活的 “同情”。在玛丽第二次去城里求职时,老板“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她,仔细地瞧着她的脸,接着,老板又望望她的鞋子,鞋子上还沾着红色的灰尘”。老板带着有些反感的神情拒绝了她,因为玛丽不再是那种“穿着漂亮的外套,头发修得整整齐齐”的年轻姑娘,玛丽“又一次地感觉到受了侮辱”[4]94。查理第二次登门时,“粗鲁”地盯着玛丽看了又看,认为对方是在向自己“笨拙地做出一副卖弄风情的姿态”[4]171,对女主人丝毫没有尊敬。玛丽被黑人杀害后,陈尸卧室。德纳姆警长和查理来到现场后,带着极端“憎恶和鄙视的神气”“弯下身来瞪眼看着”[4]9-12玛丽的尸体。他们面对受害人满是刀伤的遗体,不仅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惋惜,反而极端忿恨与厌恶,如此举动实则是对女性恶意“凝视”的还魂,也是对玛丽的终极侮辱。警长为代表的白人男性头脑中深植菲勒斯中心主义观念,因此他们全力捍卫男权文化,坚决镇压并驱逐试图挑战男性主体审视者地位的努力。莱辛在此揭示了这一惨痛的事实:在父权阴影笼罩下的南非,女性的任何积极表演和抗争都是徒劳的。
二、 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
年轻时候的玛丽容貌秀美、羞怯天真,总是把头发梳成少女样式披在肩上。在轻松做好秘书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就是去参加落日晚会、跳舞或者看电影。与迪克结婚之后,她把家庭主妇的分内事处理得妥妥帖帖:用自己的积蓄买了花布做成门帘和窗帘,又买了麻布和陶器来布置,“希望迪克干活回来,看见家里焕然一新,会对她显出赞美和惊异的神气”[4]54。她喜欢做针线活,整天坐在家里缝制衣装、装饰内衣,“把凡是可以刺绣的东西都一一绣上图案”[4]55。她身上还充盈着母性,非常渴望与迪克生儿育女,甚至有时丈夫也成了她呵护关爱的对象,比如在新婚之夜,玛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睡着了,好像以保护人的身份摸着一个被她所伤害了的孩子的手似的”[4]48。应该说,玛丽身上散发着典型的女性气质——甜美温柔、体贴顺从。
然而生活的残酷迫使玛丽不得不寻求生存下去的出口,她必须为自己的性格注入男性强硬的因子,以此来对抗命运的挑战。根据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理论,所谓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都非天生,实则后天获得,是由特殊社会环境造成的。福柯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是话语的产物,是异性恋霸权的产物,是在性别实践中形成的,也就是巴特勒说的“社会性别本身成为一个自由流动的设计”[16]9。在迪克生病之际,农场的管理面临巨大挑战,玛丽在此时展现了强悍的管理手腕,实现了策略性的性别表演。在出发前,她做了以下一系列事情,从中可以看见玛丽对于承担这种新角色的忐忑但同时又义无反顾的心理:
她拿着卡车钥匙站在阳台上,把几条狗唤到了身边,正准备走时,又重新回到厨房里去喝了一杯水,随后坐上了车,一只脚踏上了油门;可就在这时,她又突然跳下了车……她看见了那条长长的犀牛皮皮鞭……现在她把它取下来,绕在手腕上……自己独自开着车向雇工们干活的地方驶去。[4]101-102
可以看出,女主人公为了与生活的磨难抗争不得不克服顺从柔弱的天性,试图借助外在工具(皮鞭)来助力表演的顺利进行。经过了这样“内心的重构”[1]63,玛丽勇敢走出了家门,进入了传统上由男性把持的公共领域,为自己的人生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和可能性。
南方农场主秉持一个管理原则,即“这些黑鬼需要男人来对付才好,女人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是不买账的”[4]16。然而,玛丽打破了农场管理的禁女令,克服了从未直接跟土人打交道的困难,展示出与懦弱的丈夫截然不同的管理作风。她行事果断,做事干练,惩戒严明。黑人雇工想趁迪克生病时偷懒不干活,玛丽亲自前往他们住的棚户区督促他们按时出工。那里环境恶劣,到处都是腐烂物和乱飞的苍蝇。玛丽全然不在意这些,直接用土语命令工头即刻召集工人。对于工头的阳奉阴违,玛丽冷静下达不按时集合就扣工钱的指令,亮出严明纲纪的姿态。发工资时,面对雇工们的骚动,玛丽不为所惧,毅然维持自己最初的说法,体现了临危不乱的气势。在黑人摩西不服从管理时,玛丽举起鞭子朝他脸上狠狠抽了下去,震慑住了众人,彰显出主家的威严。应该说,玛丽的手段远比丈夫冷酷严苛,展示了男性般的铁腕和魄力。这正是巴特勒理想中的开放性别身份空间,即模糊性/性别的边界,对原有不合理的性别区分机制进行置换。巴特勒认为,“通过持续的社会表演而形成的性别现实本身表明,所谓本质的性,所谓真实的、永久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都不过是建构策略的一部分,它掩盖了性别的表演性特征,否定了在男性主宰制和强制性异性恋体系之外增加性别构型的表演可能性”[12]141。在这种社会建构论的理论框架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重建主体的实践过程中会变得不稳定,存在表演性的可能。
跟从前轻松惬意的秘书工作相比,农场的活计显然艰巨辛苦多了,连丈夫迪克都“不愿意想玛丽成天跟那些土人打交道的情景,那不是女人家的事情”[4]105。在他看来,女人不属于非洲农场,唯有男人才能驾驭得了那里的炎热、灰尘和成群的土人。然而玛丽意志坚定,不言放弃,根本不把体力上的辛苦和管理的繁琐放在心上,表示“宁可死,也不愿意示弱”[4]107。昔日娇柔的秘书小姐如今变成了冷静粗犷、意志坚定的农场管理者,她“一心盘算着该如何毫不示弱地控制土人,如何料理家务,安排各种事情,使自己不在家的时候,迪克也能感到比较舒服”[4]109。可见,玛丽积极进行着身份的转变,自觉扮演着强有力的农场主人的角色,下意识地将丈夫置于自己的照顾和保护之下。这种20世纪40年代南非白人女性身上逐渐苏醒的“新女性”意识冲击着男性至上的性别秩序,削弱了男人的阳刚气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性别表演其实是男女角色的微妙转换与糅合过程,并非泾渭分明的非此即彼。这种性别角色或者男女气质的模糊和融汇状态“抛开了单一的、永久的和连续性的‘自我’,以这样一种自我的概念取而代之:它是表演性的、可变的、不连续的和过程性的,是由不断的重复和不断为它赋予新形式的行为建构而成的”[17]26。故而,玛丽身上依然流动着女性特有的细心精明的气质,她仔细研究农场各方面的情况,琢磨可以栽种什么作物来提高收益。所以,性别表演使得玛丽打破了男女分工的固有格局,在她身上融合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在这样高效严格的管理之下,没有迪克掌管的农场被玛丽经营得有声有色。
到了最后,玛丽甚至产生了这样一种全新的自我认知,“她感觉自己好像打了一场胜仗。这一场胜仗战胜了土人、战胜了她自己……也战胜了迪克和他的迟钝愚蠢和没有主见”[4]133。坦白而言,这是玛丽的幻觉,如此的性别表演在父权制的南非社会注定没有出路,她绝无可能构建自己的主体性。正如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女人永远不可能“存在”,因为她们是差异的关系,是被排除者[18]55。不难预料,虽然玛丽积极进行转换定位和置换角色的表演,但依然时刻体会到转变过程中存在的撕扯和分裂:“她觉得自己好像在演戏一样,本来她演的是一出她所了解的戏,扮演的角色也是她适合的,可是现在却突然要她改扮一个陌生的角色。使她不寒而栗的是她自己所演的角色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并不是因为自己改扮了角色。”[4]91这里的“不相称”实质上是“不允许”,是一个强调性别、秩序和身份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制度里的禁忌。作为丈夫,迪克对于妻子跨越性别分工的做法心生不满,因为她这样做伤害了他的男性自信心。他感受到妻子的才干对自己地位的威胁,思忖着“她的精力这般充沛,做起事来又这样能干,到底要做到什么地步为止呢?”[4]56毫无疑问,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玛丽的表演策略根本不被现实世界认同,因为它实际上触犯了父权价值体系的规约,挑战了男性的统治地位,必将遭到世人的众多非议与合力镇压。这种“规约”就是小说中提到的南非社会的首要准则,即“社团精神”[4]3,因为没有顺从这种精神,玛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当地白人的集体抵制与排斥。人们用尖刻和随便的语气谈论她,“好像在谈什么怪物”;他们“极其怨恨玛丽,好像她是什么令人厌恶的肮脏的东西”[4]2-3。在周围人看来,女主人公各种离经叛道的做派冲击甚至颠覆既定的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父权制社会秩序,“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稳定,随之而来的是男性气质出现危机”[19]138。这一点是保守的主流社会绝对无法容忍的。可以看出,玛丽为改变生活境遇所做的表演与环境和时代极为格格不入,处处碰壁,时时受辱。
正如《性别麻烦》一书的书名所言,巴特勒指出了从“表演”的维度对建立在社会权力关系网络之上的“性别区分机制”制造麻烦的身份建构路径。但在现实中,这种对性别本质的“自然化”和“固化”的解构行为还是有着相当的局限性的。作为生理性别的文化诠释,社会性别的建构性决定了女性的身份建立是运行在社会语境中的。社会政治、文化和话语秩序最终决定了女性对自身主体建构是否能够成功。美国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的“性/社会性别体制”(Sex/SocialSexSystem)论认为,性别的社会属性决定两性行为深受社会风俗、社会规范、社会身份、社会角色、社会期望和社会评价诸多因素的制约[20]55,女性在这样的秩序规范下会产生极强的心理劣势,限制了自我意识的发展,导致主体建构的失败。因此玛丽对于自己超越男性的聪明能干充满了罪恶感,因为“如果她经常帮他的忙,显示出她的能力明显优于他,那必然会触犯迪克的自尊心”。于是玛丽不愿再过问农场的事,为的就是“挽救迪克最大的弱点——骄傲自负”[4]120,然而丈夫的无能和固执让玛丽深感抑郁狂躁,陷入了与黑人男仆的不伦恋情之中,最后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毁灭。在男权文化里,女主人公始终是一个“他者”,在不断被规约、束缚和改造过程中,她一直无法在现行的社会结构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定位。她的悲惨结局“验证了对权力之社会地图(social map of power)的一种悲剧性误读,一种由这份地图所编排的误读。根据这份地图,幻识性的自我超越(self-overcoming)总是以失望而告终”[10]121。
根据巴特勒的观点我们可以得知,社会性别是一种虚构,真实的社会性别是在身体表面上的建制和铭刻的一种“幻想”(illusion)。性别在霸权语言里是以一种实在的面貌存在的。我们不可否认这样的事实,即“女性在社会活动中,角色先于个人而存在,社会主流的生活规范和思维方式约束了女性乃至两性活动的自然进行”[21]15-16。玛丽是生活在父权制南非的白人妇女的典型代表。她不甘沦为男性“凝视”的物化客体,也努力消弭两性气质差距,积极进行着性别表演。尽管她从内在自我需求的驱动下作了试图摆脱从属地位的努力,通过不断的行为标准重复进行了构建自我主体性的尝试,但这样的性别表演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现实世界中遭遇了惨败。玛丽身份建构的挫败是那个年代南非女性身份构建失败的缩影,折射出社会体制和文化权力对性别认同的深刻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固然有其值得称道的颠覆性和创新性,是对“性别本体论”的积极批判,但同时也存在着某种理论上的理想化倾向。在现实中,这种表演的可行性是有局限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里,它注定要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