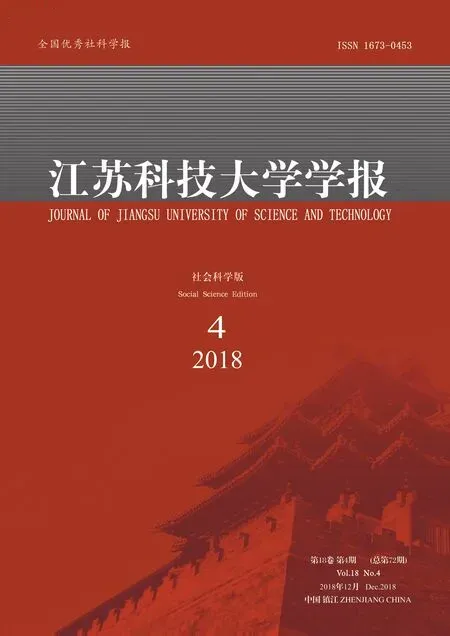春秋邦交战争及其影响
——从“联吴制楚”到“联越扰吴”
罗 君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西周初年确定的“封建关系”在东周时期彻底礼崩乐坏,周王室徒具虚名。西周社会以血缘为纽带,构建出天子、诸侯和贵族的分权时代,历史呈现出“统一”和“破碎”的双重特征。进入东周时期,血缘关系开始缩小,地缘社会开始放大,虽然社会呈现“破碎”的局面,但是开始孕育出新的“统一”倾向。春秋初期,诸侯国恃强凌弱,打破制约兼并他国。司马迁在分析春秋时期的历史指出:“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3297之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和越王勾践相继称霸[注]学术界关于“春秋五霸”存在许多争论。笔者同意《墨子·所染》和《荀子·王霸》的观点:齐桓、晋文、楚庄、吴阖庐和越勾践。因为霸主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会盟诸侯、天子赐命以及诸侯朝往,而上述五人均具备这些条件,故称之“霸主”。。在春秋称霸的政治军事斗争大环境之下,各国也采取了特殊的联合结盟策略。
关于春秋时期各国联合结盟的历史现象,长期存在“邦交”和“外交”两种说法。但是,春秋时期各国的“邦交”联合问题,与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外交”概念是不同的,最大的差异就是历史主体和背景的不同。“邦交”[注]“邦交”指在“春秋特定历史阶段,各个诸侯国之间为求得生存、发展乃至争霸而开展的活动。”参见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1页)。关于“邦交”研究综述参见徐杰令《春秋邦交问题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5期)。关于“外交”的定义,中国学者认为“外交”是“国家为实现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构等进行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鲁毅等主编《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绪论第2-3页)最早出自于《周礼·秋官·大行人》“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是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交流活动。此外,历史叙述采用“邦交”更为合理:首先,因为“邦交”一词使用已久,部分学者在写作时更多使用这个词汇,而“外交”一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两者历史背景具有明显差别。其次,因为春秋时期的“邦交”是有其鲜明特殊形式和历史特点的,明显不同于后期的中国古代社会。最后,出于尊重历史史实的需要,春秋典籍大多采用“邦交”一词进行记述,我们应当尊重其历史书写。因此,无论是从使用时间还是历史背景和史籍记载三个层面来看,“邦交”更符合历史叙述。
一、 “联吴制楚”及其影响
在春秋早期,中原地区面临着“北狄”和“南蛮”的夹击,呈现“南蛮与北狄交,中原不断若线”[2]的危险局面。齐桓公对中原诸侯国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获得中原地区政治意义的领导权,并通过数次战争大大提升他的威望。齐桓公在召陵会盟诸侯,“一匡天下,九合诸侯”[1]1491成为春秋首霸。齐国抑制住了楚国的北扩,却没有对楚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楚国继续在南方扩张,并不时北扩。楚国依靠兼并迅速扩张成为一个强大的“蛮夷政权”[注]学术界对于楚国的民族组成存在争论,但普遍认为楚国主体民族楚族是荆蛮中的一支,也是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之一。春秋时期楚国境内更有卢戎、罗、戎、庸、群蛮等民族见于史籍。此外,楚国数次北上攻掠中原,受到中原诸侯国的排斥和抵触。楚国民族的内部整合和中原诸侯国的“外部构建”促使楚国政权呈现“蛮夷化”特点。。反观齐国,因为内耗不断已经失去霸主地位。
楚国和晋国几乎同时崛起,成为继齐国之后的新兴势力。当时,晋文公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作三军六卿,晋国国力大增。对外联合秦国和齐国进行伐曹攻卫、救宋服郑,平定周室子带之乱。受到周天子赏赐,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又一位“强主”。一般而言,诸侯要具备下列几项条件, 才表明他已被公认为霸主:第一, 会合中原诸侯, 被推举为盟主;第二, 获得周天子赐为侯伯之命;第三,诸侯往朝,并向他献纳贡赋。晋国仅有天子赐命和部分诸侯朝往,并未会盟诸侯,所以称为“强主”,而非“霸主”。同时,因为南方崛起的楚国时常向北攻掠,晋国的地位并不稳固。南北同时出现两大争霸力量,一个是楚国,一个是晋国。两者之间必然会爆发激烈的霸主之争。在晋楚争霸的大背景之下,晋楚之间的争斗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军事战争,另一种是邦交战争。
晋国与楚国之间早期主要是军事战争,先后爆发有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鄢陵之战(公元前627年)、邲之战(公元前597年)。晋国在城濮大败楚军,召集齐、宋等国于践土(河南原阳县西)会盟,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但是晋国在文公死后却因内耗而不断衰落,难以进行庞大的军事战争,转而采取邦交联合的方式,试图维持霸主地位。城濮之战前,晋国有齐国和秦国两大“盟友”。但是,大战后合作关系迅速瓦解,齐国因为“短暂的利益”而决定参加,亦因战争的结束而完结。
秦国与楚国的联合使得晋国遭到进一步的孤立。齐、秦两大诸侯国的背离无疑是对晋国霸主地位的极大削弱。战后,楚国元气未伤,迅速恢复,积极联合秦国和齐国构筑针对晋国的包围圈。不久,“秋,楚人灭六……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冬,楚子燮灭蓼”。至此,楚国东部辖境直抵淮河之滨,中原诸侯多次受到进攻,中夏诸侯惊呼“楚不可遏矣”[3]506-507。
楚庄王时期,在邲之战大败晋军,并控制了西线的主动权,河南之地尽为楚有。楚共王在西疆稳固的情况下,楚与齐结好。此时,南方的陈、蔡、郑、许,北方的鲁、宋、曹、卫,大国有齐、秦,小国有邾、鄫,都成了楚的盟国,对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包围圈,使得晋国陷入孤立的境地。由此,楚国从军事上和外交上都取得了主动地位。公元前589年,楚共王会盟诸侯,“晋避楚,畏其众”,晋国不敢轻举妄动[3]702-705。
由于受楚国包围圈的压制,晋国陷入孤立的处境。晋国为发展盟友打击楚国,开始推行“联吴制楚”策略。楚国叛臣申公巫臣[注]申公巫臣,生卒年不详,春秋时人。楚国申县(今河南南阳北)县尹。芈姓,屈氏,名巫,一名巫臣,字子灵,与申叔时是亲戚。“巫臣叛国”和“屈原被逐”更多表现为楚国公族内部倾轧的牺牲品。关于楚国公族势力的扩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是贵族势力对平民阶层的倾轧,另一个是贵族内部相互倾轧。详细参考2011年武汉大学田成方的博士论文《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在“联吴制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本来是楚庄王的重臣,因为与楚国令尹子重有怨,担心为其所害,借机出使齐国时逃奔晋国。楚共王知道后,杀其族人,分其家财。巫臣大怒,发誓“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10]728。于是,巫臣主动要求出使吴国,《左传》记载:
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 通吴于上国。[3]728
“两之一卒”是指巫臣使吴带来的兵车三十辆,“舍偏两之一”是指留下一半的兵车给吴国。就当时争霸的力量而言,晋国带来的十五辆兵车并没有多大作用,可是如果和巫臣使吴之前的军事装备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重要意义。当巫臣出使吴国时,中原诸侯国已经大规模地使用战车,军事战争主要是以车战为主,各国都以兵车的拥有数量来评判国家武装力量,这是当时军事变革的潮流。巫臣携带战车入吴,不仅带来中原地区先进军事装备和军事思想,更重要的是带来“反叛”思想。“联吴制楚”很快见效,吴国频繁侵袭楚国,自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吴始伐楚”到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吴人伐慎”为止,吴楚总体上处于战争状态,时间长达一百零五年。吴楚之间的战争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明显超过同时期的晋楚战争。自巫臣使吴后的七十多年中,吴国一跃而为军事强国,长期压制楚国,灭掉楚的属国徐和舒,吞并楚国的大片东部领土。尤其是柏举(湖北麻城)之战,在吴国主导之下,联合唐国和蔡国从淮水流域分三路进军,五战五捷,一度占领了楚国的郢都(湖北荆州市西北)。
在吴楚的多次战争中,“柏举之战”(公元前506年)是奠定吴国霸权的决定性战役。柏举之战实际上是一场“运动战”,吴国利用战车的灵活机动性,进行迂回奔袭并快速推进,进而取得胜利。这场战争中,战车可以说起到战略决定性作用,而战车的使用和制造源于晋国的帮助。同时,吴国开始从晋楚之争的“附属国”转变为联合江北淮南多国的“主导国”[4]。
“联吴制楚”虽然是晋楚争霸的历史产物,但是影响并不局限在晋国和楚国双方,还扩散到吴国和越国,“联吴制楚”的多维面相和“历史二律背反”[注]二律背反(Antinomies)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的哲学基本概念,是指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但却相互矛盾的现象,又译作二律背驰,相互冲突或自相矛盾。参见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历史二律背反”是对康德观点的发展,注重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各类历史现象中的矛盾现象。特点深刻影响春秋历史走向。
首先,晋国“联吴制楚”既成功又失败。这一邦交政策是晋国霸权衰落的产物,晋国已经对楚国的“北进”冲击感到力不从心,楚庄王“问鼎中原”晋国不得不避其锋芒。楚国强势崛起与晋国的发展迟滞呈现强烈反差,中原诸侯国的“尊王攘夷”不再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华夷关系日益淡薄,甚至出现华夏中原小国“一边倒”的态势。晋国“联吴制楚”的失败之处在于没有压制住楚国的扩张,因为楚庄王确实完成了“饮马黄河”的霸主之业,晋国希图维持霸主的目的被打破,所以是失败的。“联吴制楚”又有其成功之处,正如申公巫臣所言“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3]728。晋国确实使楚国实力大减并达到战略目的,使楚国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迅速将楚国拉下霸主之位。
其次,楚国“联吴制楚”既有破坏性也有建设性。楚国遭到晋国和吴国的联合夹击,在多国掣肘之下楚国短暂称霸之后迅速衰落,这是其政治破坏性。“联吴制楚”的经济以及军事破坏性具体表现为吴国的“西进”伐楚,五战五捷并且直捣郢都(湖北荆州市西北),在吴国领导的江北淮南多国联军“水陆并进”的进攻下楚国东境防线全线崩溃。但是,楚国作为华夏诸侯国传统认知上的一个常常以武力慑服他国的“蛮夷化”国家却开始模仿学习晋国采取新的策略。楚国在晋国“联吴制楚”基础上发展出“联越扰吴”的策略,在邦交上采取联合的方法进行斗争,这种对暴力传统和武力压制的背离就是对晋国的直接学习,也是楚国自身文明化的重要表现。此外,吴国的进攻有助于清除楚国贵族专横以及任人唯亲的历史弊端。因为楚国国内公族贵族集团势力庞大,贵族内部互相倾轧是其发展滞缓的重要原因。腐朽的贵族集团在国内肆意侵吞土地和侵犯王权,并压制平民阶层上升,以至出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人才外流局面[5]。吴楚之间的长期战争对腐朽贵族势力有一定的消耗。特别是吴国直捣郢都,对楚国贵族集团是一次巨大削弱,贵族的衰落助长了王权的抬升,从而为楚国平族势力兴起减少阻力,并推动楚国后期改革变法。
最后,对于吴国则是利弊兼有。初期,吴国是晋楚斗争中最大的受益者,不仅学习到先进的战车军事技术和教育理念,还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领导江北淮南诸侯。具体表现在:第一,吴国伐楚,灭掉了徐国和舒国,吞并了楚的大片东部领土,极大提升吴国的军事主导性;第二,吴国在多次战争中联合江淮诸侯,提升吴国的地区政治军事主导性。这两大因素既为吴国“横兵江淮”提供条件,更为以后吴国会盟中原诸侯将霸权北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正是由于吴国四处攻伐,数次与越国交战,吴越关系迅速恶化。越国常常乘虚而入进攻吴国,特别是后期越国与楚国开始合作后,吴国陷入被夹击的处境。越国不断崛起也埋下了吴国衰亡的伏笔。
二、 “联越扰吴”及其影响
楚国国都被吴国攻陷后,楚国国内一片救亡之声,准备展开战略大反攻。此前,当秦晋关系恶化时,楚国主动和秦国结好,频繁通婚和馈赠。更有秦楚联合作战的历史记载,公元前611年,秦国在楚受到戎蛮侵叛时出兵帮助楚国联合灭庸[3]564。此外,东周时期的夷夏观念,主要是以我族与他族之分以及是否加入诸夏联盟作为标准,使得夷夏观念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因此,齐桓公和晋文公利用“尊王攘夷”把中原华夏诸侯国紧紧联合在一起,也将“蛮夷化”的楚国和秦国排除在体制之外。而政治学理论表明,“每一个未被吸收到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挫败一个集团的要求并拒不给它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有可能迫使它变成革命的集团”[6]。因此,政治军事合作利益以及地区文化认同感助推了秦楚联合,从而为楚国反攻奠定基础。
楚国遭受吴国重创,秦国立即派出大将子蒲和子虎率领五百兵车前往救楚,楚国同时策动越国进攻吴国后方。楚国本地军事力量也同仇敌忾,迎击吴国进攻。
吴越之间经历了反复曲折的战争。《左传·定公十四年》记载:
吴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槜李……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将伤指,取其一履。还卒于陉,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3]1600-1603
吴王阖庐因为对越国作战不力而丧命,越王勾践趁吴国新丧贸然出兵攻吴。阖闾之子吴王夫差闻讯,迅速组织兵力,派遣精兵击越,两军战于夫椒。越军大败,只剩下五千余人,退守会稽山。吴军乘胜追击,攻陷会稽城(浙江绍兴),包围会稽山(浙江绍兴南)。勾践无奈,以美女、财宝贿赂吴国太宰嚭,请其劝吴王准许越国附属吴国,夫差应允。
夫差自恃武力强大北伐卫国和鲁国,并开凿沟通南北的邗沟进攻齐国。公元前485年,吴王率领鲁、郯、邾国联军分海陆两线进攻齐国。“十年,春,邾隐公来奔,齐甥也,故遂奔齐。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十有一年……甲戍,齐国书帅师及吴战于艾陵,齐师败绩,获齐国书”[3]1652-1653。吴国趁机迫使晋国和齐国盟于黄池(河南商丘市南),吴国霸权达到顶峰。
越国遭受夫椒战败后,在范蠡和文种的辅佐下国力日渐恢复,并在吴国北上会盟黄池时大举进攻吴国。“越王闻吴王伐齐,使范蠡、泻庸率师屯海通江,以绝吴路。败太子友于始熊夷,通江淮转袭吴,遂入吴国,烧姑胥台,徙其大舟。”[7]越国的偷袭取得巨大成功。夫差在知晓后十分无奈,由于国内民力日竭,前线军覆将死,只好派遣使者与越国讲和。越国也明白自己现在没有能力灭吴,同意议和。公元前478年,越复伐吴,吴士民疲弊,精锐尽死于齐晋。
文种劝谏越王勾践不可再次放过吴国,但是越王不听劝告,答应吴国的“附邑”请求。可是勾践并未完全遵照约定,不久之后,勾践再次举兵伐吴。这次越国大破吴国,并且围城三年之久,吴王夫差派遣王孙雄前往请和。这次勾践接受范蠡的劝告不再“心软”放过吴国,最后夫差自杀。
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吴师败,越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吴王使王孙雄肉袒膝行而前,请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异日尝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勾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范蠡乃鼓进兵……勾践怜之,乃使人谓吴王曰:“吾置王甬东,君百家。”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1]1745
越国最终取得吴越斗争胜利,勾践趁机北上争霸,“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1]1746。在吴越争霸中,吴国先称霸,越国继之。吴越之斗也成为春秋后期的基本态势,如果再将楚庄王称霸时期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争霸重心在“南移”之后呈现“由西向东”的态势转移。
春秋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存在楚国、吴国和越国三大诸侯国。纵观整个春秋时期的楚越关系基本处于“和平共处时期”[8]。越国对吴国的反击主要得益于楚国的帮助。楚国“联越扰吴”策略的主体并不明确,但是借助三种措施对越国施加影响:其一,采取通婚的手段交亲;其二,采用军事联盟的做法,楚国让越国士兵进入楚地,绕道从背后夹击吴国;其三,派遣谋士到越国,在越国有著名的“六千君子”,是越国赖以崛起的庞大人才集团,其中又以范蠡和文种二人最为重要。
范蠡和文种可以说是“联越扰吴”的直接实践者,他们均为楚国人。但是,他们二人的到来并非楚国官方派遣,而是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偶然性因素。范蠡当时声称“见霸兆出于东南”,预测今后霸主在东南方向,就是指现在的吴越。两人决定先到吴国去,这就具有自发性因素。偶然性因素则是基于吴国人才现况的考虑。当时,伍子胥和孙武辅佐吴国国君,范蠡和文种感觉在吴国可能才干发挥不出来,而且人才之间的人际关系也难于处理。由于当时吴越地区风气相近,范蠡判断日后争霸“非吴即越”,所以范蠡和文种决定到越国去。勾践在二人的辅佐之下,使勾践由败君俘囚得以复兴灭吴,所以越国灭吴得到楚国的间接帮助。
楚国的“联越扰吴”表面上是对晋国“联吴制楚”的发展,实则是晋楚争霸的延续。斗争的重心从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长江下游地区,吴越两国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争霸格局。同样,“联越扰吴”这一策略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楚国是“联越扰吴”的制定者和实践者。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楚国的人才外流,楚国在人才“国际流动”中长期处于一种“出超”状态,即大量人才外流,如伍子胥、范蠡和文种,他们均是楚国人,他们难以在楚国的政治土壤中生存,所以被迫离开;另一方面表现在楚越联合方面,楚越两国的联合明显具有主动性和不等性特点。就主动性而言,联合的动力主要在两国上层贵族集团的推动;不等性体现在越国对楚国的朝贡,越国要以钱币玉帛子女贡献于楚。“联越扰吴”对楚国是有利有弊的。这是楚国对晋国的直接学习,扩大了楚国的战略同盟,进一步孤立晋国,牵制住了晋国的盟友吴国。但是,楚国也将越国培养成为强国,楚国的谋士和战车资助极大增强了越国的武备力量。之前,楚国同意越国绕道楚国东部边境进攻吴国,使得越国知晓楚国东部边防虚实,使得越国在后期对楚战争中抢占先机,攻占楚国东部大片土地。
其次,吴国是“联越扰吴”的牺牲品。晋国实施“联吴制楚”只是战略决策,并未与吴国结盟。这就使得“联越扰吴”必然对吴国造成极大的伤害,因为吴国在遭受楚越夹击的同时晋国却可以置身事外。吴国由于早期和晋国合作,虽然使自己变得强大,但是也陷入被动地位。初期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封锁,后期则是由于自己争霸的扩张受到周边国家的敌视,特别是越国的偷袭,吴国长期处于不利的战略包围中。此后,吴国北上争霸不仅劳民伤财进行自我削弱,还给越国制造了可乘之机。吴国内外交困的局面本就难解决,再加上楚越的联合夹击自然无力应付。纵观春秋时期几位霸主都有“一世称霸”的经历,但是夫差的霸主地位却骤然衰落,落得“掩面”自刎的下场。
最后,越国是“联越扰吴”的受益者。越国最终击败强邻吴国实现了称霸的目的。《史记》记载:“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水,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礼于周王。周元王使使赐勾践胙,封为伯。”[1]1746越国得到周王室赐命,也与诸侯会盟中原,只差诸侯往朝了。勾践吸取了夫差不能“与邻为善”的教训,当他离开徐州时,把淮河流域送给楚国,把吴国侵占的土地归还宋国,把泗水以东百里的土地给了鲁国。当时,越军横行江淮,诸侯贺毕,勾践号称霸王。
三、 余论:态势转移
春秋争霸的历史叙述习惯按照战争进行书写,这既忽略了战争的多维面相,又淡化了战争以外的其他因素。因此,邦交与战争的结合成为理解春秋历史演进的新颖视角,“联吴制楚”与“联越扰吴”两大策略无疑是阐释春秋历史的一把密钥。春秋历史的特殊性又融合在两大策略的共性和差异性之中。在共性上,两大策略都是晋国和楚国试图维持霸权的历史选择,都采取了“邦交战争”的形式,结果都是先成功后失败并利弊兼有。在差异性上,“联吴制楚”是在晋国官方力量主导下由申公巫臣负责实施的,“联越扰吴”则是楚国民间自主开展的。民间力量与上层主导构成邦交策略的两个视角[9]。
春秋中后期,晋国和楚国争霸中衍生出“邦交战争”,他们采用联合盟友进攻或者压制敌国,而非自己直接诉诸战争。这种做法使得春秋后期的战争呈现明显的“集团化”趋势,晋国为打破包围圈和打击楚国率先提出“联吴制楚”的策略,楚国为进一步遏制晋国打击吴国顺势推行“联越扰吴”的策略。“联吴制楚”是晋国突围的必然之举,“联越扰吴”是楚国争霸的策略选择。
“联吴制楚”表面上是晋楚争霸的“次生品”,实则是晋楚双方争霸力量衰落的必然产物。晋楚两国都不再具有争霸战争的压倒性优势,只有采取联合策略发展盟友,希望形成以自己国家为主导的战略平衡,从而维持衰落的霸权。此外,这一策略包含着历史脉络发展的线索。从楚国的崛起就开始出现霸权重心的“南移”,“被边缘化”的楚国一直试图冲击传统华夏诸侯[10]。楚国完成称霸也表明争霸重心从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长江中游地区。
“联越扰吴”看似是楚国对晋国邦交策略的“机械模仿”,实为挽救霸权的尝试。虽然晋楚双方将斗争的重心转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但是他们仍长期掌控争霸战争的幕后控制权。这却促成了吴国和越国的迅速崛起并使之具备了争霸的实力,最终使得争霸重心完全转移到长江下游吴越地区。
综上,“联吴制楚”与“联越扰吴”的意义在于:首先,两大策略成为春秋时期的两条线索,将整个春秋争霸和邦交格局连接起来,使得霸主之争自然过渡。其次,两大策略不仅使得春秋争霸得以继续,还将争霸重心从黄河中下游转移到长江下游,为春秋时期找到历史出口。最后,春秋时期“联吴制楚”与“联越扰吴”的南北争霸深远影响着战国时期东西对峙的“合纵”与“连横”[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