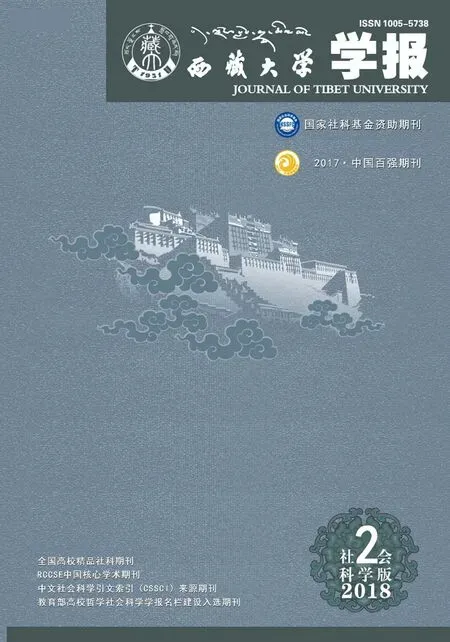青藏高原牧区信仰礼仪中的“互惠”关系研究
白玛措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西藏拉萨 850000)
一、导论
(一)人类学视野的礼物交换
对礼物交换文化性的研究始于人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当“物”作为“礼”被送出之后,为什么收礼者会“回赠”?是什么原因让人与人之间的物品交换产生这种互惠呢?或者,这种“互惠”是否存在?
礼物交换不但是经济的转换和物质的获得,也是一种既定社会关系的建立以及与不可知世界建立意义联系的延续,更是一种精神特质的转化。例如,莫斯阐述“礼物”携带有送礼者的精神特征,虽然送礼者是“自愿”将某种物品送给收礼者,对于收礼者而言,必须归还这种精神特质。故,收礼者在接受礼物的同时也意味着他接受了回礼的“义务”。这种附在礼物中的神秘力量被莫斯称之为“礼物之灵”(the spirit of the gift),即礼物之互惠机制的产生源力[1]。
马林诺夫斯基和莫斯,将那些非商业社会中的经济交换行为描述为没有非常明显的机构化特质。所以,礼物交换不但具备了资源再分配的功能,同时也具备了亲系、宗教和政治的文化功能,它们之间彼此互动相互影响[2]。
“礼物”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在那些非商业化的社会中,礼物交换不但是资源的再分配,同时对不同的交换方式有其特定的文化解释和社会功能[3]。即便在商业化的社会里,帕里(Jonathan Parry)和布洛赫(Maurice Bloch)指出,在一个家庭中资源再分配时使用货币仍然是避免的。因为,家庭仍然延续着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它依旧为宗教礼仪、婚庆、丧葬及礼物交换提供着社会文化最基础的平台[4]。
不论以何种理论角度诠释物品交换,礼物的经济作用、社会功能及文化价值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西藏畜牧社会及礼物研究
在转向西藏畜牧社会的礼物研究前,有必要对人类学在西藏畜牧社会的研究做一简单梳理,通过这些文献来了解有关西藏畜牧社会研究的趋势及其中有关礼物研究的状况。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藏区畜牧社会的研究也多以“传统与挑战”为视角[5]。这些研究中,格尔斯坦(Melvyn Goldstein)教授对西藏牧区的一系列研究最被广为提及和引用。
关于那曲畜牧研究方面,西藏那曲地区政协尼达活佛等编著的西藏那曲文史资料丛书提供了解放前那曲一带早期的部落历史、民俗习惯、草原畜牧生产经济方面的翔实的资料。这一丛书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本参考资料[6]。格勒等编著的《藏北牧民》成为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提供的那曲牧民社会生产状态的民族志[7-9]。
然而,以上研究中无一专门涉及西藏畜牧社区礼物经济的研究,即便多以畜牧文化的变迁与重构为主,但通过对牧区礼物交换及互惠功能的记录和分析来展示这种变迁和重构的研究在英文、藏文文献中都寥寥无几。但庆幸的是,这些研究都涉及到了地方社会组织互惠、互助功能的重要角色,而本文将要展现的正是礼物互惠如何在信仰礼仪中得到呈现。
二、研究点概述
本课题入户调查的地点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嘉黎县。县城距那曲镇211千米,距拉萨市537千米。S村距离县城3千米。据2013年驻村工作队的统计数据,S村共有78户,293人①该数据由斯定卡驻村书记丹增曲珍提供,2013年。。这份统计数据应该包括了那些户口保留在村中,但并不居住在村里的户数和人口。依据这次田野谱系调查期间所得数据,固定居住在村里的户数为56户。因而,本研究的田野数据仅来自这55户。
三、信仰礼仪中的“互惠”
游牧社会日常情景的礼物交换中,信仰礼仪的“互惠”活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种“互惠”在信仰礼仪中的表达与佛教的一些基本理念有着紧密的联系。
藏传佛教作为佛教体系的一个重要传承派别,强调信奉者在修行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如供养和布施。佛教信仰体系以“无常”和“一切皆空”诠释宇宙万物的存在。作为佛信徒,供养和布施是实践这一哲学观的重要修行及修心过程。
布施一词引自梵文Dana,即意含有给予、赠送和舍弃,同时也指供养、施舍。藏语中“乔巴(纀翿繻་繽།)意为供奉,Chod.pa的对象一般是出家的僧人或是寺院;Chod.pa是出于恭敬之心的向上的给予和赠送,这是一种对佛法僧三宝的供奉。金巴(腤繼་繽།)意译为布施②“布施分为财施、法施和无畏施三种。密宗将之视为三昧耶戒中最主要的部分”。(参见华智仁波切.大圆满前行[M].索达吉堪布,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250-251.),Sbyin.pa的对象一般为弱势群体,如乞讨者”(付吉力根,尕藏尼玛,2015:101)[10]。供奉和布施作为佛教徒的一种修行,佛教理论中有关为什么供奉和布施以及供奉和布施的内涵及其分类、供养和布施对象的层次、阶位上的分类、供养和布施所达到的修行度等有着一套非常详尽的描述和解释(宗喀巴,2003)[11]。
简单来说,供养和布施强调信奉者以善心为出发点,以尽己所能的方式实践供养和布施,而通过供奉和布施积累的资粮则会通过“回向殊胜”将这一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无上菩提。这一境界应该是修行者的最高精神追求和达到的思想境界。对于普通的信众,不同的供养者及布施者,所能达到的修行境界以及境界的层次则因人而异。
如果以交换互动方式的角度来看,“回向殊胜”这种境界则是一种“无私”的“不期待”回赠的“纯粹赠送”行为。不管是“回向殊胜”的修行境界,还是其他境界层次,供奉者和布施者作为“赠送者”的角色,则通过其一系列的“赠送”行为,积累和获得今生的以及来世的福报资粮和智慧资粮因此,这一“赠送”行为就此和供养者及布施者的资粮产生了微妙的“赠送-回赠”的互动关系。对于普通的信众,他在实践供奉和布施仪式的时候,会期待自己可能获得的资粮能够在今生以物化的方式出现:如,今世家庭的和睦;或者,实践者可能期待这种资粮能够在来世以某种自己期望的状态出现;或者,实践者可能期待自己积攒的资粮能够回向给所有众生。如何达到不同的境界则取决于实践者的自我意识活动、付诸实践的方式以及诸神的世界。
“供养”和“布施”所产生的“回赠”可能即刻发生,也可能延迟发生,甚至可能发生在布施者、供养者的来生。显然,这种“回赠”存在于一个解释范围极其广泛的时空中。这种“回赠”可以超越时空概念的维度,或以非物质形态的存在,或以物质的形态存在。
故,供奉和布施以一种系列性的赠送仪式构成了牧民日常信仰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赠送仪式通过以下不同的仪式场景获得展现和构建。
(一)信仰礼仪的开支
信仰礼仪是S村牧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个仪式场景,信仰礼仪所产生的开支也成为家庭开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55户家庭中,信仰礼仪开支占家庭总收入3%的户数最多,共有10户;其次有6户的信仰礼仪开支占家庭总收入的4%;信仰礼仪开支占家庭总收入2%和1%的户数各有5户;信仰礼仪开支占家庭总收入21%,10%,9%,7%和5%的各有2户;剩余户数按照每一户的分布,其信仰礼仪开支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比分别是127%,96%,29%,27%,25%,24%,17%,16%,15%,12%,11%和8%。
然而,有两户家庭其信仰礼仪开支分别占家庭总收入的127%和96%,为什么这两家与其他家庭的情况悬殊如此之大?S17(2)的信仰礼仪开支支出远远高于其家庭总收入,高达127%。S17(2)是一个由6口家庭成员组成的扩大家庭,没有牲畜,被列为低保户。访谈S的家庭收入时,他只提供了国家提供的低保配额,并一再强调低保收入是这家唯一的收入来源。但从其他村民的交谈中得知,S17(2)家的女儿和女婿采挖虫草,有一定的虫草收入。从S提供信息的方式推断,他应该认为访谈者收集收入数据会对其低保收入资格有所影响,故低报其家庭总收入。另一个家庭C15(1)的信仰礼仪开支也高达96%(总收入1,324,信仰礼仪开支1,270)。C15(1)是一个由4名家庭成员组成的扩大家庭,没有牲畜,也属于低保户家庭。C是位90多岁高龄的老妇,访谈数据由其女儿Q提供。这家只有C的户口在S村,故家庭收入仅仅纳入了C的收入,Q的丈夫则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有着稳定的工资收入,Q也有着一些零散的收入。因而,如果将Q和其丈夫的收入列入这家的总收入中,信仰礼仪开支所占比例应该远远小于96%。
有3户家庭的数据显示没有信仰礼仪开支,这份数据真的代表实情吗?有时,仅仅数据是无法反应田野中复杂的文本情景。当我们分析访谈这3户家庭的田野情景,不难推断出信仰礼仪开支零开支并非实情:G5(4)的家庭毛收入为230,000元。G一家三口,以这样的收入是S村中相对富裕的家庭,G表示其信仰礼仪开支仅有1,000元,占其总收入的0.004%。G平常住在镇上,故而对访谈者的身份可能有着某种猜测,对访谈者数据收集的用途亦有所怀疑。或者,个别年轻一代的牧人的信仰礼仪开支确实占很小的比率。
后来,在和村民的闲聊过程中,有几次听到关于G5(4)的议论:“G自己的收入很好,吃穿都很殷实,但是对自己的母亲不怎么样。”我接着问道:“G在参与佛事活动方面舍不舍得花钱?”聊天的村民笑了一下,说道:“现在的年轻人,第一不大懂自己的信仰;第二也不是全身心的虔诚。G在信仰礼仪方面应该花得不多,要不怎么会对自己的老母亲那么不孝顺。”
信仰礼仪零开支的C11(1)家则是另一种缘由。这是一家四口的核心家庭,家庭总收入143,800元,C曾经是村上的干部,并且任有一职。最重要的是,C是一名资深的共产党员。当问到信仰礼仪开支时,C告诉访谈者:“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是不信教的,所以也不参与任何信仰礼仪活动。”C的儿子Z11(3)是供奉零开支的另一个家庭。Z所提供的信仰礼仪开支为零的考虑,应该与其父亲的身份有关。
信仰礼仪零开支的这两家让笔者想起pubic space and private space,显然对于C而言,他和访谈者的对话代表了一种公共场合式的对话场景。这种场景下,谈话者会以一种公共场合认可和宣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认可和身份归属。然而在私下场景中,是否有信仰礼仪开支,只有C及其家人知道。至少从和其他村民的交流中,类似家庭与信仰礼仪活动并非完全绝缘。
(二)八类场景
S村的信仰礼仪开支大致可以归为七类。比较这七类开支,朝佛期间供养的开支在所有分类中所占比例最高,达34%;修缮尼姑庵时供养开支占信仰礼仪总开支的第二位,为19%;修建佛塔时供养的开支占信仰礼仪总开支的17%;每年一度的灌顶供期间供养的开支占总开支的13%;
1.朝圣
朝圣具有与朝佛一样的功德,朝圣也是一种向佛祖求请神力、自我忏悔和行善积德的善行。对S村的牧民来说,朝佛的地点以那曲和拉萨为主,其中以拉萨为重点。经济殷实的家庭也许每年都会去拉萨朝佛,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则可能为某个特定的目的专程前去朝圣。这一朝圣过程由一系列的物质支出和布施组成,到了拉萨必定要前往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等大寺做布施。最常见的就是购买用以点酥油灯的酥油以及在各个寺院朝佛过程中用以供佛的现金布施。
S村中共有55个访谈户,其中仅有8户明确表示近两年去过那曲和拉萨朝佛供奉,其余47户所提供的朝佛供奉数据均是依据其以往经验的估算数,不能代表实际开支,不同户数之间所提供的开支数额仅作为参照。这55户的朝佛供奉开支共计133,500元,平均下来每户的布施开支为2427.2元。
有的家庭其朝佛供养开支占年总收入比例较高,则有家中特殊的原因。Z3(1)是一个由8个家庭成员组成的核心家庭,年收入约为81,450元,朝佛供奉开支为20,000元,占其年总收入的25%。Z在谈及供养开支时,特意提到了家中老者过世,专门去拉萨为过世者朝佛期间的供养开支约有20,000元。为亡者的朝佛供养的开支并不一定总是居高,如G1(1)家。G1(1)是一五口之家的核心家庭,年收入约为108,000元,家中老者过世,朝佛布施花费主要是供佛灯开支,约为3,000元,占其年总收入的3%。
家庭经济条件的优越与否与其朝佛供养的开支有着必然联系。根据牧户所提供的朝佛开支从100元到8000元,同时参照这些家庭的年总收入,他们所提供的数据是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其朝佛开支的多与少的一种参照。
2.修缮尼姑庵
修缮尼姑庵需要供养资金的信息,是该寺通过各个村子的负责人传达到每户牧民家的。供养金在3000元以及3000元以上的牧户作为施主获得了尼姑庵赠与的护身符,S村作为供养的整体单位得到了尼姑庵回赠的一副佛像图。
尼姑庵修缮资金的赠与也是一种自发自愿的供养行为。S村所供养的现金共计有73,690元,所访谈的55户中,供养额度在1000元到5000元之间的达21户,供养额度在100元到500元的有26户,8户家庭的数据显示没有为尼姑庵的修缮实施过供奉,其中有3户家庭明确表示实施过供养。M说他是当时村中的联系人,牧民们本着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力所能及地发起布施,主要的施主布施额度大,小施主的布施则相对少些。S村当时共筹得近9万元,尼姑庵用此资金引请了一尊佛像。
3.佛塔
修佛塔的功能在《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①“密宗经籍。全书三十六章。十一世纪初,译师释迦洛追由梵译藏。宋代天息灾由梵译汉。”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词典[Z].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888.中提到:修佛塔不但能忏悔,甚至还有净除犯五无间罪的恶业。佛经中讲只要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把佛塔、佛像、佛经视为利益众生的佛祖本身,那么必定有与佛同等的威力和加持力。
S村的佛塔约建于2004年。牧民D作为负责人,在S村传达活佛建议,就此每户人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赠与了供养金。供养金在3000元以及3000元以上的人家作为施主,在佛塔修建完成的祈福仪式上获赠护身符。
修建佛塔所需的资金是通过牧民自发自愿的供养行为筹集而得,S村为修建佛塔所筹现金共计有66,785元。所访谈的55户中,供养金额在5400元至1000元之间的达22户,供养金额在885元至100元之间的有28户,有5户的数据显示修建佛塔时没有供养过现金。
4.灌顶供
灌顶供,是接受灌顶时供养上师和佛的物品(2015:1935)。这是通过物质的赠与对信仰体系认同和表达的又一重要仪式。灌顶供仪式之一是迎请活佛到村中,活佛及其随从一般会由村中一个威望较高且条件较为殷实的家庭接待。活佛会为迎请他的村民做一系列相关的诵经祈福仪式,以及为前来朝拜的信众摸顶。从出家人(活佛)的角度而言,为他众灌顶、传法属于密宗三昧耶戒中的“法施”[12]。
参加灌顶供的信众主要是本村的牧民,也有邻村专程前来的牧民。摸顶过程中,信众会敬献给活佛现金或实物作为专门的供养。然而,这样一次灌顶供仪式还包含了一系列其他的赠与过程。
灌顶供仪式的准备包含了每个牧户自愿赠与的现金和实物。这部分现金和实物,按照每户家庭人口数和所养牲畜数的比例来决定其供养的额度。在2013年的一次灌顶供仪式中,S村负责人按照村里有畜户和无牲畜户分摊所需物资及现金。有牲畜的牧户按照每户每人100元,和酥油及奶渣收集。无牲畜者按照每户每人100元,以200元现金代替酥油和奶渣份额的算法来收集。此次灌顶供仪式中所收集的现金有36,552元,收集的酥油和奶渣按斤折合成市价约为13,107元。为这次灌顶供仪式捐赠金额超过2,000元的户数仅有一户,20户家庭所赠供奉在1,760元到1,000元之间,31户家庭所赠供奉在955元到350元之间,3户家庭的供奉为零。Q16(1)的供奉开支为2,170元,这是一家有畜户,供奉的现金为600元,酥油20斤(折合市价为1,400元),奶渣10斤②此户所报奶渣的市价为17元。。在收集供奉的酥油时,是按照每头母牛0.5斤酥油来折算,因这家的母牛头数较多,所以分摊的供奉酥油斤数也多。
赠与现金及畜产品是灌顶供仪式的一种供养行为,另一供养行为则通过劳力的自愿付出体现出来。仪式的准备过程中,村里的每一户都会参与到这一过程中。这一准备过程由S村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统一安排部署。负责人会召集几个能干的牧民安排在接待活佛的牧户家中,提前准好备活动期间所需食材。牧民也可以自发自愿地在自己家中将专门做好的食物送到接待活佛的家中。
灌顶供仪式举办了两天,这两天均包含了一系列的劳力付出,如食材的准备等。C1(3)告诉笔者,灌顶活动那天,她和村里几个能干的妇女准备了近十道菜,活佛及其随从专门享用的牦牛肉包子。仪式第二天是“央阔”诵经及招“央”仪式,仪式持续了数个小时。期间,需要有劳力完成一系列的食材准备。
灌顶供仪式期间所准备的这些食材,最主要是供养给活佛及其随从的,同时也被仪式期间参与者们共同分享。如,招“央”仪式结束后,准备好的食物会供奉给活佛和随行人员。也会分给在客厅里参与准备这次活动的本村牧民,以及一部分外来的客人。
灌顶供仪式完成后,活佛及其随从人员在下午离开,村里每户有车牧民都自愿驾车前去护送活佛。浩浩荡荡的一列车队,甚是壮观。这代表着这次仪式活动的重要部分圆满结束。
灌顶供仪式结束后,还包含了供养物的回赠。回赠的物品一般是仪式期间准备好的,余下的食材。回赠者以主持仪式的东家为主。如,目送活佛离开后,留下的一部分牧民回到举行仪式的东家的客厅中。这时,负责接待这次仪式活动的东家媳妇R从柜子高处拿出一精致瓷碗,里面盛满尚好的酸奶。R说,这是刚才敬给活佛的酸奶。坐在一边的老爷爷Q应声道:“给我分享一小口活佛碗中的酸奶,会有其啦并且敬畏地伸出自己的手。R用一干净的汤勺从碗里取出一勺酸奶,倒在了Q的手掌中心,如此,分别给在座的每一位客人都分了一勺酸奶。这种场景中,食物(酸奶)已转换成分享一种共同意识的文化解释(其啦),并且以回赠的方式回归到了参与此次仪式的供奉赠送者。
仪式后的回赠多分布在那些为此次仪式付诸劳力的供奉者中。如,仪式结束后的随后几天内,东家N分别将一块酥油(5斤)回赠给在此次仪式活动中负责取水、供水的L19(2);将一块奶渣蛋糕回赠给负责此次煨槡仪礼的A4(2)。就此,剩余的供奉食品均以类似的方式回赠给了大部分参与这次供奉仪式的牧民。
5.化缘僧人
对佛法僧三宝的供养,视为是一种善念和善行,有无量功德。对化缘僧人的赠与也是一项自愿的供养行为。前来化缘的僧人着僧装,每到一家只要报上自己所属寺院名,村民都会供奉奶渣、酥油或者现金。在访谈的数据中,81%的牧户都提到了每年赠送给化缘僧人或者化缘尼姑的供养开支。仅以一年为例,S村的牧户在这一项的现金支出共计9,440元,供养的酥油折合市价为17,790元,奶渣折合市价为3692.5元。饲养牲畜的牧户多以供奉奶渣和酥油为主,占16户,有畜户中有2户则供奉了现金,一户有畜户不但供奉了现金同时也供奉了奶渣和酥油,有一户的数据不是很明确是否实施过供奉;在没有牲畜的牧户当中则以供奉现金为主,占29户,没有牲畜的一户则供养酥油和奶渣,另一户则同样供养现金的同时也供养了奶渣和酥油。
6.诵经
诵经祈福是村民们每年自愿例行的祈福经事行为,赠送给寺院的现金,或食材供奉给寺院里的僧人,祈请诵读《甘珠尔》获得一年一度的诵经祈福。S村的牧户以供奉现金为主,占总户数的69%,既供奉现金同时也供奉米、面、砖茶及酥油①这种酥油指市面上出售的从植物提炼的植物酥油,一般用于点酥油灯。的占24%,只供奉米、面、砖茶及酥油的占7%。如果将供奉的这些食材折合为市价约有4,563元,供奉的现金约有15,200元,S村为诵经祈福所供奉的总金额约为19,773元。80%的户数其供奉额度分布在100元至860元之间,13%的户数其供奉额度在50元及无供奉,7%的户数其供奉额度则在1,020元至1,000元之间。其中,供奉总额最多的家庭G10(1)达1,020元,其供奉的现金为500元,供奉的食材折合成市价有520元。
7.丧葬
丧葬期间涉及到一系列为亡者诵经的仪式,以及为亡者去寺院祈福的仪式。家庭G1(3)是访谈期间唯一涉及到丧葬经事的家庭,该家庭在这一项的支出为12,500元,占其宗教总开支的70%。其中
8.下施乞丐
下施的缘由,塔波拉杰·琐南仁钦②塔波拉杰·琐南仁钦:(1079年—1153年)宋代西藏著名佛学家,噶举派的一代大师。著有《解脱道庄严论》。张怡荪.藏汉大辞典:上册[G].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1312.的解释如下:没有积布施之资粮的人必会常受贫穷的苦难,来世将转为饿鬼,即便生为人也会受尽贫瘠之苦。
布施分为财施、法施和无畏施三种,这是密宗解释系统中“三昧耶戒”中最主要的部分。在牧民的日常生活中,财施可能最为常见。“财施又包括普通布施、广大布施和极大布施三种。普通布施,指包括一把茶叶、一碗青稞以上的财务施舍给其他众生。”财施中对乞丐等弱势群体的布施则称之为下布施。下布施中,又分为几种场景(术语中称为“度”)。这几种场景中,强调了布施者、所施之物、布施对镜之间的不同关系[13]。
对乞丐的施舍正如大卫·格雷贝尔(David Graeber)指出的“当双方处于一种不平等关系时,物品的赠与是不会产生互惠的。如,当某人A给乞丐B施舍钱或者物品后,他并不会从乞丐B那里得到相应的回赠。相反,当A再次遇到B时,因为这种不平等关系,乞丐B会向A再次央求施舍”(Graeber,2001:225)[14]。不过,佛教教义则让这种不平等关系通过“赠与”和“资粮回报”的互惠关系建立了平等关系。
S村中本村没有行乞者,偶尔前来乞讨者多来自日喀则农区或其他偏远些的牧区。这种情况下,村民们会给前来乞讨的人赠送旧衣服,食物或者现金,其中以现金为主。其他情况中,如牧民们去朝圣期间路遇乞讨者,或是其他场合有行乞者均会实施或多或少的财施。
即便本村中没有行乞者,但这种财施也会针对村中部分弱势群体,如那些年老多病且子女不孝的老人:C1(3)说,2016年过年前以“过年礼”为名给G1(3)赠送过100元。在C1(3)对我描述这段赠与场景时,她特意用了“布施”一词。
布施者和行乞者之间也存在微妙的抗拒关系,当布施者所赠与的物与行乞者所期待的物不相吻合时,行乞者会以其他方式表达拒收这种布施。如,C1(3)和其邻居给前来行乞的几个乞讨者赠送了一袋穿旧的衣服,一些风干的旧牛肉,一点现金。第二天,当C路过村子与镇的马路时,却看到那一袋旧衣服被扔在了路边。布施过程中这种抗拒关系的产生,与经济模式的变迁不无关系,旧衣服作为布施的媒介已经不是行乞者所期待的布施物;这种抗拒关系也反应了对于普通信众而言,布施境界的种种分层都具有难以达到的理论高度。
四、供养、布施与家庭经济
物质作为供奉或布施的重要载体,经济条件不同的家庭其所赠出的物质会有多有少。佛教的解释体系中针对不同经济条件的个体或者家庭,最为强调的是其“发心”,而不以供奉或者布施的多寡为取向。如,要供养,要积累资粮,不见得非要很多的钱。如,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可能不会参与每个供养场景,而会选择某个特定的仪式场景赠与其供养。
类似经济条件相对拮据的家庭,其供养的次数及额度均不如经济条件宽裕的家庭。例如,在访谈家庭收入数据时,有几个经济较为拮据的家庭视访谈者为可能带来潜在福利收入的倾诉对象,所以在描述其消费开支和收入情况时,数据落差极大,如D19(1)。有趣的是,在描述其信仰礼仪开支时,D19(1)所提供的数据却较符合其经济状况(信仰礼仪年开支为2,635元),没有呈现出夸张之谈。但在描述其信仰礼仪开支时,数据比例则比较接近其家庭经济情况,仅为2,400元。显然,访谈者在谈到信仰礼仪的供奉和布施行为时,都表现出了相对坦诚的心理。对这类供奉次数及额度相对少的家庭,其他村民对此却有着不同的解释:“类似这种家庭的经济情况,正因为他们的信仰不够虔诚,没有多少供奉,所以才会导致家庭如此落魄。”
有关这种供养和布施行为的解释,凯瑟琳·波维(Katherine Bowie)在信仰小乘佛教的泰国农村的研究中指出,不能纯粹以宗教信仰的角度进行解释。她提出了经济条件不同所造成的阶级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家庭的供奉及布施行为。例如,波维指出,那些经济贫瘠的农民对乞丐的布施较之那些富有的农民群体更为普遍。波维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则借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观点,指出贫穷农民之所以如此是借这种“隐含”的表达方式表达对富者的不满,也借以佛教的教义减轻今世的苦难[15]。虽然,在S村的田野中没有发现经济拮据的家庭布施的支出多于经济优越的家庭,但从所收集的资料来看,经济条件的不同确实对信仰礼仪的供养程度(次数及额度)有着直接的影响。
(本文特别感谢嘉黎县索朗嘎瓦书记、尼玛扎西主任、格桑旦增书记、顿珠加拉院长;感谢给予我田野支持的S村妇联主任措佳旺姆,门巴村长、尼玛副书记及S村所有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