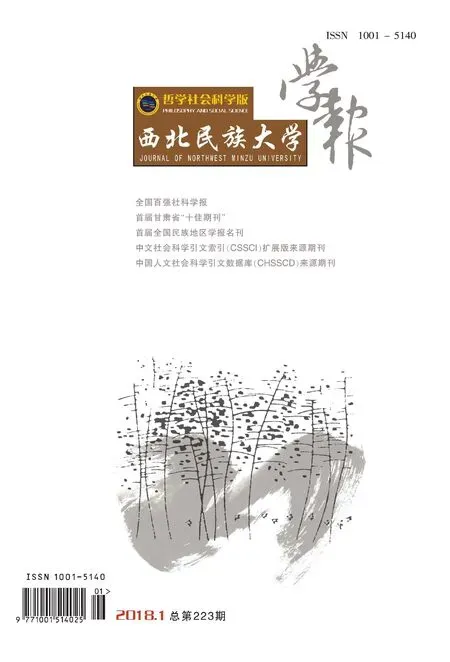新世纪以来回族文学中的朝觐书写
——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重建的未来思考
林 琳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回族素来和伊斯兰宗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伊斯兰的天命“五功”*“天命五功”分别是,念、礼、斋、课、朝。念功指信徒要口中常念清真言,礼功指信徒一天五次的礼拜,斋功指信徒在伊斯兰历的“莱买丹”月的白天进行封斋忌口,课功指信徒将自己财产的2.5%贡献出来救济穷人,朝功指有能力的信徒应该到圣城麦加进行一次朝觐。作为基本功修要求同样也在回族信众中被执行。而朝觐作为天命“五功”最后一项,既是穆斯林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仪式,也是最难完成的功课。《古兰经》中明确记载:“你们要为安拉而完成正朝和副朝”(2:196),*即《古兰经》第2章第196节。下文中有关《古兰经》的经文叙述均采用如此表述方式。“凡能旅行到克尔白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克尔白的义务”(3:97)。因此,朝觐成了穆斯林的法定宗教功修,每个穆斯林只要条件允许,一生中必须到麦加朝觐一次。
以朝觐为内容的文学记载在回族历史上源远流长。例如,明代马欢所撰《瀛涯胜览》中“天方国”篇目及清代马德新的《朝觐途记》都是古代中国回回穆斯林到麦加朝觐的专著。到了近代,穆斯林马松亭、赵振武等人组成的访问团于1932年到麦加完成朝觐功课,随后赵氏出版了《西行日记》,对该次朝觐见闻颇多记述[1]。1938年,中国回族救国协会为了宣传抗日派出一支中近东访问团,途经香港去到麦加朝觐,回国后于1939年出版了《中国近东访问团日记》,详细记载了该次朝觐的各项事务与经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民族宗教事务都得到渐次恢复,穆斯林到麦加朝觐事项也在中断了14年之后得以恢复。穆斯林朝觐事务获得了以伊协为代表的国家集体力量的重视,朝觐人数增多,这为回族朝觐书写的日渐增多提供了前提:一开始是零星的单篇小短文见诸报刊,接着在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中出现了与朝觐有关的“故事”,后来就出现如长篇小说《朝觐者》,短篇小说《朝觐》《耶其目的老房子》,游记式散文集《环游克尔白》《虔敬的行走:一位穆斯林妇女的朝觐手记》《朝觐心路》,诗歌《朝觐者之歌》《信念》《朝觐》等以穆斯林到麦加朝觐为主要内容的作品(集)。其中对朝觐过程中异域景物的感受、朝觐过程中的感悟以及对朝觐的反思的内容,不仅可以唤起同样有朝觐经历的穆斯林的归属感和回忆,也帮助“举意”要去朝觐的人了解了必要的事项,还能让其他不了解伊斯兰文化的人从中感受到伊斯兰精神的特色。回族这种融合了世界穆斯林的伊斯兰教信仰和中国少数民族的具体语境之书写,无疑拓宽了文学的表述空间,又在一定程度上以族群记忆和身份共建的二维叙述参与到族群的族性建构当中。因此,研究回族文学中朝觐的书写,对把握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的发展、厘清宗教与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关系,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朝觐书写的外在结构
(一)作为媒介的身体
由于谒见天房是所有穆斯林终生夙愿,因此,回族朝觐书写中有不少内容会体现出作为一名朝觐者在朝觐过程中的激动与虔诚。而身体的反应是一个人内心受到触动后最直接的体现,所以在回族朝觐书写中,以身体反应直接描述朝觐者内心感受是最常见的写作方式。
有关身体的描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多数是避而不谈的。身体以及身体所联系的无数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直接被忽视或闲置了,只剩下道德一类的内涵,成为超身体之外的意义一直获得首肯。只要身体(个人)与道德之间出现冲突,舍生取义就成为首选,否则就是不仁不义。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文学中身体和身体的细节以及这个词语背后所涵盖的思想(身体最直接受思想导向),依然处于可以忽略不计的境地。而近十年,恰恰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一批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堂而皇之地穷尽了此前一直被忌讳的领域。从天平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的结果就是,身体被简单地等同于肉体与欲望,身体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和伦理性都被忽视了。如果说旧有的身体与“仁义”总被二元割舍是一种身体专制,那么身体等同于肉欲的这种书写取向不外乎又是新一轮的身体专制,人存在的全部真实性以及多样性全部被取消了[2]。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文学中一直被扭曲的“身体写作”却恰恰在连着装都有讲究的回族文学中获得了另类的注脚。
据笔者统计,在海俊亮的《朝觐心路》中,描述穆斯林激动内心感受的篇幅超过200字之处有11处,而在阿一纱的《虔敬的行走:一位穆斯林妇女的朝觐手记》(以下简称《行走》)短短的238页篇幅中,超过200字详细描述作者内心的激动、感恩之处多达23处。该书中,作者身体感受的冲击总与眼泪相伴。像作者描述到在朋友家的第一次开斋时的礼拜:“我像一个婴儿般无措和茫然,心中涌起的强烈的敬畏感和神圣感将我击倒。”[3]135随后,看朋友父母朝觐带回来的实况记录,作者禁不住泪流满面,那是她萌发朝觐之心的最初因由。而在整个朝觐路上,从最初的拜谒圣陵到整个朝觐结束后离开麦加,汹涌的感觉不断拍打着神经,撞击着心灵,朦胧了泪眼——此时,身体不再等同于某种权力,而是直接与信仰相联系,扯住了灵魂的衣角,直面具体、活力、此在的种种真实,也从真正意义上面对存在。在这个层面上,朝觐书写中不厌其烦地描述“环游克尔白”、“投石射鬼”*“环游卡尔白”、“投石射鬼”等都是朝觐过程中朝觐者必须完成的功课。等功课项目之时,穆斯林“有的眼睛里含着热泪,有的已在抽泣。那种激动中的幸福,幸福中的敬畏,敬畏中的虔诚,虔诚中的恐惧,毫无遮掩……”[4]125“我意识到我膝盖在动,严格说是抖动,想抬起脚来,却很难……眼前的一切像汹涌而至的潮水,把我冲得七零八落。真主啊,我有些站立不稳,我要倒下了,我要窒息了。”[4]125——在这些直观的身体感受描述中,肢体语言形象地传递了宗教信仰与人性本真直面接触之时的巨大感染力。
除了身体带来的激动,还有身体带来的辛苦感,也一并出现在朝觐途中。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一般是选择“享受朝”,即先履行副朝功课,再进行正朝。*“享受朝,享受朝亦称分朝,这也是将正朝与副朝连在一起进行的。先立意小朝,礼两拜到功拜。享受朝只有三件功课,即受戒、环游克尔白和在索法与麦尔沃两山之间奔走。完成此三件功课即可开戒。而后等到正朝日期到来时(即十二月八日)再次受戒,并举行正朝,然后按规定时间开戒。享受朝在副朝开戒后,此间不受任何戒规,有自由享受之意,故名享受朝。”该解释引自2011年伊斯兰协会内部印制《穆斯林朝觐手册》。副朝包括受戒、环游天房和在萨法和麦尔沃之间来回奔走7次。正朝的仪式包括受戒、站驻阿拉法特山、在穆兹代里法停留、射石打鬼、宰牲和辞朝。这几项功课基本都是一天完成一至两项——如此下来加上朝觐前的繁琐准备,旅途的劳顿加之复杂激动的心情,朝觐者的身体违和感也相应增强。尤其我国朝觐中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因此在朝觐书写中,写到身体的辛苦,甚至有人因此归真(逝世)也并不鲜见。在阿一纱的《行走》中,作者作为朝觐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年轻人都不时感觉到旅途的奔波以及朝觐繁琐紧凑的行程所带来的身体的疲惫,“身子是那么沉重”经常“一沾床就沉沉睡去”。“这几天下来,生病的人很多,由于疲劳,由于寒冷,由于人多空气流通不畅”[3]175。在《朝觐心路》中,哪怕是健壮的中年人,“只身地环游天房,无牵无挂,此时已然气喘吁吁,筋疲力尽”[4]171,有些人为了做副朝,劳累了大半夜才回来,说话都有气无力,疲惫不堪。
伊斯兰教义把朝觐中肉体的苦累转化成真主对自己的考验,受到的苦累越多,真主的喜悦就会越多。就像《朝觐心路》中所说,“在拥挤的人潮中,人们身挨着身感到湿漉漉的,很不舒服……但是,面对天房这种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氛围,人们在拥挤中体会着来自真主的考验,在游转中体验着接近真主时的幸福与喜悦。”[4]204因此,朝觐者在身体违和感中寻找到明确的自我情感安置位置,反过来也促进了对宗教本身的归属感。
所以,在信仰空间里的个人身体,就像是一种特有的语言,既能跨越无数来自于社会、欲望、性别的藩篱,又能在其中促进宗教对信众的支配作用,并使得信众的归属感得以加强。
(二)时空交叠的复合叙述方式
穆斯林朝觐是一件时空特点颇为突出之事。一方面,朝觐有严格的时间规定——每年伊斯兰教历的第12个月的前十天。另一方面,朝觐的地点同样有明确要求——以麦加为中心的几处场所。朝觐过程不仅包含了穆斯林从外地进入麦加城,也包括穆斯林在朝觐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场地转移。时空序列互相复合构成朝觐书写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质。
朝觐书写的时序性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维度。一般文学作品多以时间为序,串联起各个情节。随着时间的推移,朝觐各项内容次序展开。无论是第一天的“环游克尔白”还是到最后的“辞朝”,时间次序里依次清晰出现的是朝觐作为一个整体的每一个部分的内容。
与时序性同时进行的还有空间性的描述。在空间转换的描述中,首先,是直观的地理空间场域的转换。因为中国的朝觐者是经过伊协的统一整合、安排后分批奔赴麦加参加朝觐,因此,在许多游记式散文中都有写到朝觐者都会经历从自己居住地出发,集中于北京、西安等城市,最后到达麦加这么一个空间转移的过程。其次,伴随着地理空间转移的是朝觐者从世俗现实的物质生活到宗教信仰的精神追求的空间变换。穆罕默德曾说:“为真主而朝觐者,在朝觐的过程中既没有胡言乱语,也没有胡作非为,那么,他归来的时候,犹如初生的婴儿一般。”[5]随着告别亲人,踏上朝觐之路开始,朝觐者就摒弃了他或她作为一名丈夫、妻子、儿子或女儿的过多世俗情感牵绊,首要之事就是完成朝觐事项,怀揣着真主的喜悦归来,成全一个全新的自我。所以不乏行文会描述“踏进阿拉法特平原、登上拉哈曼特山峰的每一位朝觐者思绪万千,顿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4]50。等朝觐者既激动又忐忑的内心感受。这些感受都来自于朝觐者身份与信仰复合所搭建出的一个特殊的空间,这是一个不同于外界社会的空间。而“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6]83。就像福柯认为的“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7],列斐伏尔也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6]48。在朝觐这个不同于外界的空间里,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有意无意降至最低,种族、民族的边界都减弱了,个人的,社会、政治的,甚至文化的身份都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穆斯林之间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可以转化成一种“集体”权力,并且必然产生一种集体“向心力”。在一篇文章中就举到一个例子,“一位中国的退休官员在游过天房后,因有一个路口被封而向执勤的警察说明自己身份的重要,希望获得例外通行,但他没有如愿。”[8]此时世俗等级背后的权力结构往往失效,起作用的通常是穆斯林作为整体的利益诉求。因此在这种空间内,朝觐者会有一种心灵得到净化的感受,能够保持一种生活有方向、有归属的感觉。正是在这么一种时空交叠的复合式描述中,朝觐者的内心世界得以被关照,伊斯兰宗教的“世界性”意义得以彰显,朝觐带来重要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朝觐书写的内部精神价值
在回族朝觐文学的书写中,虽然身体感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的,但这些感受通常都只是作为一个能指符号,背后所指是朝觐与伊斯兰文化合二为一的作用,因此体现在朝觐小说中,不仅是朝觐本身的知识,也有很多伊斯兰文化、民俗、教义等方面的内容。
伊斯兰教出现的时间较基督教、犹太教晚,民智的开发以及早期文明的传播已经使得伊斯兰宗教神圣性难以以一种过于虚拟的象征性以及模糊性呈现。这就意味着伊斯兰教教义要转而落实在生活所有细琐层面,成为指导生活、塑造道德的指南,才能召唤更多的信众。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各族穆斯林分布地区辽阔,社会文化背景和自然生态环境不同,各民族的来源和形成、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的时间、途径也不一样,因而其(中国伊斯兰文化)内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和特色。”[9]譬如说族源形成的外来性、融合性和族体发展的本土化,都让回族表现出它在华夏各种族群中的独特性——伊儒双重文化融会。
首先,在朝觐书写中体现出伊斯兰“认主独一”(tawhid)的核心思想价值。“认主独一”即认为真主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是世界的本体。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教的‘认一说’代表了人类信仰‘一神论’思想的高度。”[10]朝觐者自然都是持有此认识论的信众。在朝觐书写中,穆斯林来到麦加,心中都要无数次激动地默念“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以示自己认主独一的真诚度。但这样的一种认识论并没有脱离中华实际,在古代回族的许多典籍记载中,都有信教和忠君并行的言论。如王岱舆在《正教真诠·听命》中说:“所以人单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而不能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者,则事亦不足为功;如徒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者,而不能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前事仍为佐道。”[11]敬主是基本信仰,忠君是处世态度,孝亲是伦理道德原则,三者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回族社会的基本文化支撑。
其次,朝觐书写中也体现了穆斯林对“两世吉庆”伦理观念的坚持——既强调本世的努力,又强调后世的归宿。因此强调人们切不可沉溺浮华享受,而应在“耕耘现世”的同时,通过宗教功修“营谋后世”[12]。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浪潮的涌动,中国人遭受着普遍的精神质疑、信仰危机,置身其间的回族人尽管多了一种内生性的信仰,但现代性的冲击依然不可避免,此时朝觐书写的增多无疑在以另一种方式坚持传统文化的传承。《朝觐心路》中一名朝觐者坦言,他由于一直经商在外,许多拜功都没法一一完成,但这不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伊斯兰信仰,相反,只要时间允许,自己都会一一把错失的拜功补回[4]187。又如网上披露的一个统计,1985年,甘肃全省仅有10多名穆斯林群众参加朝觐,而到2010年已达到2 460人[13];就全国来讲,朝觐人数“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人,2012年达1.38万人,创历年新高”[14]。在这些与朝觐者的叙述中,不仅可以窥见中国许多穆斯林的生存状态和宗教感情,也折射出谋求两世吉庆始终是回族主体的日常伦理核心理念,它始终伴随在民族的现代性进程中,“既指导着回族人珍视生命,积极进取,又提醒着他们要有所禁忌,以信仰约束过度膨胀的世俗欲望,去除人性芜杂,提升道德境界”[12]。
再次,在朝觐书写中透露出回族文化中对“清洁”的喜好。在伊斯兰教伦理观念中,崇尚清洁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古兰经》和圣训中明确强调穆斯林应当爱好清洁。在朝觐纪实散文书写中,不少都提到了身在圣城麦加,哪怕语言不通,但只要到了礼拜时间,如果要寻找水源进行净身,通过比划,人们总能理解出大概意思。在阿一纱《行走》中就提到因礼拜时间逼近而又找不到做小净的地方,“我”和女伴都很焦急。但通过向一位土耳其朝觐团的女士比划,“她愣了片刻后突然明白了,拉起我的手就跑……”直至找到水源,看到“我”与女伴都没有错过礼拜时间,她“虽然站在那大喘气,真是上气不接下气,累得够呛,但满脸是慈祥和快乐……”[3]58通过这样的例子,穆斯林喜好净身礼拜以示对真主的虔诚敬重以及穆斯林之间无私的帮助,都跃然纸上。在同样的诉求之中,跨越了语言、国籍、肤色的界限,穆斯林之间的感情被一个个这样相互帮助的例子打造得栩栩如生,这是一个真实的共同体。当然穆斯林对清洁的喜好不仅仅体现在礼拜前的净身仪式上,还现在饮食、衣着等等方面。可以说,对清洁的追求,已经成为回族一个明显的文化特征,这个清洁不仅是实体方面的生活习惯,还有精神层面的追求,甚至成了一个少数族群自我区隔的重要符号。
通过研读回族的朝觐书写,可以看到,在固有的叙述模式下,体现的是一个变化中的精神文化内核。回族这一民族实体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存在,它对本族传统文化既不是一味固守,也非全盘否定,而是既有个体日常行为层面的淡化,又有群体风俗礼仪方面的坚守多元复合的杂糅情况。
三、朝觐书写对多元一体文化的意义
张承志在其撰写的马甸寺碑文中写道,“自古中国回民,虽身居棚户泥屋,而心怀真理高贵。盛世乱世紧靠清真寺求生,温饱饥寒仰仗伊斯兰迎送。”[15]一句话道出了回族文化的个中要义——信仰于回族生活须臾不可分离。从根本上来讲,回族的宗教信仰已成为本族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生态。如果说,文学的作用既是“对全面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进步力量的肯定性评价,又要关注人的良知、道德、尊严,那么回族文学的朝觐书写明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示范价值。”[16]尤其作为中华“多元一体”中“多元”的一部分,回族既与传统伊斯兰文化相互依存,(朝觐正是这“不可割舍”的集中体现之一),又与中华其余的民族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这一实体的血肉之躯,朝觐从整体上赋予了回族穆斯林世界某种“世界性”的话语力量,指向一种民族寻根过程中理想化的集体记忆想象[17]。新时期以来的回族文学正是在不断的探索中,拼凑这种本族的文化身份形象,而回族朝觐书写无疑是凝聚和反映回族伊斯兰信仰文化、呈现回族在现代国家发展历程中族性建构之集中体现之一。就像海俊亮的《朝觐心路》一书,书写过程就是在论坛中和广大网友的互动中进行的。这一方面可以为未朝觐过的穆斯林朋友解答疑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听取更多人有关教义的意见和建议,甚至吸引到不少汉族人阅读,这无疑是回族文化族内族际互动的一个生动例子。所以,即使是着力于本族族性建构,回族的朝觐书写并没有指向固定僵化的一味肯定本族文化的模式,更没有树立起“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必然对立。相反,是比较理性地看到,朝觐书写的出现得益于朝觐行为的发生,这在根源上与国家意识形态、宗教政策的支持是无法脱离关系的。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直接导致在朝觐书写中,不少内容都是在中华文化大格局之下铺开的。
就像在《穆斯林的葬礼》一书中,朝觐的内容在开头和结尾分别通过梁亦清与吐罗耶定的交谈和韩子奇临终“讨白”的叙述中得以彰显。除此以外,小说还分别以“月”和“玉”的意象设置对应回汉文化,正是在这种烘托下小说曲折的情节中不露痕迹地融伊斯兰文化和中国回族文化于一体,实现了对当代回族族群记忆身份追寻的二元复合叙述。
如果说在《穆斯林的葬礼》一书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体现得还不算明显的话,在小说《朝觐者》中则多次提到政治高压年代,个体面对真实语境之时试图从宗教功修中找到解脱的尝试,“父亲只有更加地沉默,虽然自己无法礼拜,但他依然嘱咐母亲要坚持礼拜、封斋,每到礼拜的时候,他总会到外屋去作掩护。”[18]75不难看到——回族穆斯林即使在极端的年代中冒生命的危险礼拜也不愿彻底荒废宗教功修,伊斯兰信仰的作用依然保存在内心深处。到了“粉碎四人帮”之时,母亲催促父亲找政府平反,父亲生气了,说:
“四人帮”垮了,我出来工作,不就是平反吗?别人不知道,你难道也不知道,这么多年,真主给了我们那么多恩典我们承领了,真主给了这么点灾难咱们就不能忍受,咱们吃的亏,他们能补得了?真主会给我们补的。[18]76
父亲的回应再一次证明了伊斯兰文明对回族的重要作用,也在另外一个层面尝试以宗教的作用化解两种异源文化在民族—国家进程中的冲突,为国家机器或者理解为“主流”的历史做法提供了一个具有可原谅性以及非激烈冲突性的“软处理”。
这种“软处理”办法到了纪实散文中则呈现出当代中国穆斯林在麦加朝觐过程中与世界穆斯林的对比与反思的面貌。像在阿一纱的《行走》、海俊亮的《心路历程》中,都描写了对比起许多外国的穆斯林,中国穆斯林许多方面都是处于弱势,所以一开始确实给朝觐团工作人员的管理、统筹工作等带来了不少难题。但随着朝觐进程的推进,到最后完满结束,朝觐者获得了“哈吉”的称号,并且也开始以一个哈吉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这时,“哈吉”称呼,已是一个宗教文化符号,也是朝觐者一种宗教功修的象征。朝觐者因从尊贵神圣的地方完成朝觐功课,朝觐者本身也因身份符号的改变(由朝觐者→哈吉)而变得“贵重与神圣”。所以哈吉们也自觉谨言慎行,维护自己得之不易的称号。哈吉回国之后,回族社区通过“接哈吉”、“请哈吉”等仪式,进一步使哈吉的身份得到确认。哈吉在回民社会这种仪式性质的作用在维系宗教情感的同时,也在回族社会形成一些反思,这无疑对贯彻落实政府新时期以来的宗教政策,建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新型关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的说来,朝觐不仅是穆斯林的宗教功课,还是融入了华夏沃土的穆斯林对祖上异源文化的倾全力保留,是回族穆斯林群体对身份寻求按图索骥的“钥匙”。回族文学中的朝觐书写尽管在有意识地突出回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但并没脱离中华“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的思考。在行文中,回族知识分子对本族群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审思,不仅有如何应对改革开放浪潮带来的冲击的思考,也有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人如何在冲突与矛盾中自处,怎样在物质的裹胁下保有一份精神的独立。对于此,文学又该怎样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蒙昧与繁琐的生存和心态,或许在回族的朝觐书写中有另外一种阐释的可能。
[1]马晓琳.19世纪以来回族朝觐的历史及昌吉地区回族女性朝觐方式探究[J].科教导刊—电子版,2004(9).
[2]霍格尼.提倡一种争胜性女性主义:汉娜阿伦特和身份政治[M]//性别政治:朱荣杰,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63.
[3]阿一纱.虔敬的行走:一位穆斯林妇女的朝觐手记[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
[4]海俊亮.朝觐心路[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
[5]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一部)[M].康有玺,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454.
[6]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83.
[7]福柯.另类空间[J].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6).
[8]丁宏.朝觐者的心路——兼谈宗教仪式的意义[J].西北民族研究,2010(2).
[9]马启成,丁宏.中国伊斯兰文化类型与民族特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119.
[10]张文建.信主独一——伊斯兰教[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34.
[11]余振贵.伊斯兰教义与儒家传统思想的显著结合——试论著名汉文译著<正教真诠>的特点[R]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宗教室内部资料.
[12]王继霞.白年回族文学价值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1(博士论文).
[13]冯志军.甘肃2460人分8批赴沙特朝觐总人数创历史新高 [J/OL].http://hews.xinmin.en/sheht:i/7284816.html/2010/10/19.
[14]史竞男.2013年度我国最后一批朝觐人员启程[J/OL].http://news.163.com/13/0928/20/99SUELIR0014JB5.html.
[15]张承志.百五十年后再修马甸清真寺碑记[J/OL]网络资源:http://www.baidu.com/link url=F87_W3lKIKjoz82ASmpXpVWZpB6YBJcyqCN_jNMjX8yctd3HOPJplzDoh68BmXBbYBjCniHeaxJDMr_ZEgBPnq&wd=&eqid=8329dd84000037f30000000656744105.
[16]童庆炳.现代诗学问题十讲[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148.
[17]杨秀明.《穆斯林的葬礼》中朝觐亚叙述层的功能分析——兼论当代回族流散写作[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18]郝文波.朝觐者[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