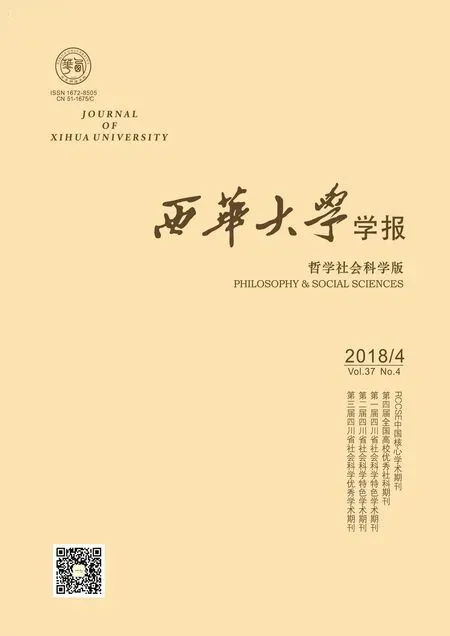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与发展意识
张思齐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一、人格与文格
扬雄(前53—后18)以其丰硕的建树而堪称世界文化名人。《艺文类聚》卷二六人部十言志:
汉扬雄自叙曰:雄为人简易佚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浄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无担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1]464
这段话概括了扬雄一生的大节。虽然这段话出自扬雄《自叙》,但是它经过了欧阳询(约557—约641)在编撰《艺文类聚》时的审慎选择。上海古籍出版社《艺文类聚·前言》:“《艺文类聚》以三年的时间编成,在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公元624年11月3日)奏上。”[1]2从扬雄去世至欧阳询奏上《艺文类聚》,其间经历了六百余年的时间。作为历史人物,扬雄的形象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扬雄的文学批评占有重要的地位。朱东润(1896—1988)撰《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四章《西汉之文学批评》:“汉代文人,自相如外,当推扬雄。”[2]16虽然在这一章中朱先生也论述到司马相如、司马迁和刘向,但是这几位批评家所占的篇幅都很小,而且其中的论据有的还采自扬雄的文章。在这一章中,朱东润用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篇幅来专门论述扬雄。这就说明,在朱先生看来,西汉时期的文学批评主要就是扬雄的文学批评。虽然西汉的其他文人也有文学批评方面的言论,但是他们都没有扬雄那样地量多质高,那样地直截了当,那样地鞭辟入里。这种情形恰如朱文振(1914—1993)著英国文学史一样,他将书名定为《英国文学史——从乔叟到莎士比亚》。在朱文振先生看来,把握住乔叟和莎士比亚两位作家,就得到了绵绵两千年英国文学史的精髓。可惜由朱文振所著的这部英国文学史仅在四川大学内部以英文讲义的形式印行,而未能更加广泛地流布全国。
郑振铎著《文学大纲》第十章云:“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死于公元18年)。善作赋,亦善为论文,辞意甚整练温雅,但甚喜摹拟古人,没有自己的创作的精神。”[3]220乍一看,郑振铎对扬雄的文学创作不甚满意。原因在于,郑振铎的这一番话是以整个世界文学为参照系而言的。陈福康《重印〈文学大纲〉序》:
郑振铎一生著作等身。本书是他青年时代用力最劬的心血之著,也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厚的一本书。同时,这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前期一部非常重要而且其重要意义尚未被人充分认识的学术巨著。这样一部包罗古今中外的世界文学通史,完成于郑振铎之手,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有着历史的必然性。[3]2
原来郑振铎著此书的时代,正是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影响到中国学术界的时代。郑振铎敏锐地看到了比较文学学科的生命力,那就是,它采取全新的研究方法来处理文学问题。比较文学教导人们学会在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场域中来观察事物,庶几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郑振铎对扬雄的评价,乃是将扬雄与维吉尔(Virgil,70—19 BC)和贺拉斯(Horace,65—8 BC)等世界大文豪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之后才得出来的结论。维吉尔是古罗马的大诗人,其所作《伊尼德》(Aeneid)被誉为第一部文人史诗。然而,这一著作带有强烈的摹仿荷马史诗的痕迹。贺拉斯是古罗马的文艺理论家,他提出紫斑(purple patches)说。贺拉斯《诗艺》(De Arte Poetica)第14—16行:
Inceptis gravibus plerumque etmagna professis
Purpureus,late qui spleandeat,unus et alter Adsuitur pannus.[4]185
为了厚重的事业和伟大的目标
经常将紫色的布片缀上一两条
远远就能够展示出文章的美好。(拙译)
贺拉斯认为,好文章应该有秾丽的修辞色彩,就像古罗马人所穿的长袍一样,那是要故意补缀上几块紫色布片作为装饰,才显得华贵气派而富丽堂皇的。由此而观之,郑振铎对扬雄的评价实际上很高。它告诉我们,扬雄的创作具有世界一流的文学品格,扬雄的文学批评达到了世界一流的高度。
以上论述了扬雄的文格。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扬雄的人格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
赞曰:雄之自序云尔。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5]872
西汉末年,国内阶级矛盾加深,对外一再扩充疆土,民众的生计日益困穷,社会危机四伏。有鉴于此,王莽遂以符命自立为皇帝,国号新。王莽代汉,其出发点本来不错,周谷城《中国通史》第二编《中世前期》第一章《阶级的剧烈冲突》:“因为他是贵族的外戚,故能结交权贵;因为他处境特贫,故亦知民间疾苦。他凭着这等阅历经验,要来解决危机;故其所施行,在当时实是崭新的而有革命意味的政策。”[6]246然而,豪民、富商与各地的县令相互勾结,他们借新政之名而行自肥之实。结果,王莽的新政彻底失败了。在那些秉持传统历史观的人们看来,外戚干政是很不好的事情。何况王莽直接代汉自立,这就更被人们认为是大逆不道了。在王莽新政期间扬雄得到升迁,这件事本来纯属时间上的巧合。然而,不明真相的人们便认为扬雄的人格有问题。《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扬侍郎集》:“《剧秦美新》,谀文也,后世劝进九锡,皆权舆焉。元后诔哀思文母,盛誉宰衡,犹然美新。岂有周人申后之思乎?予尝疑子云耆老清浄,王莽之世,身向日景,何爱一官,自夺玄守。”[7]30《剧秦美新》是扬雄的一篇重要文章,内容关乎时政,并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为《昭明文选》和《艺文类聚》所收录。《剧秦美新》表现了作者的勇气和胆识,那就是敢于就国家的命运和时局而坦然地表达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期望。较诸那些写游戏文章的人,扬雄不知道要勇敢多少倍!《剧秦美新》的精华在于其序文,该序文为散体,便于直抒胸臆。扬雄作《剧秦美新》,其本意在于劝诫皇帝“以至圣之德,龙兴登庸,钦明尚古,作民父母,为天下主,执粹清之道,镜照四海”[8]206。由于王莽的新政与个人的野心交织在一起,故而他无法执粹清之道而镜照四海。假如王莽听从扬雄劝诫,那么其新政的结局当完全不同。从文章的实际内容看,扬雄《剧秦美新》是一篇劝诫文,而并非谀文。篇中那些歌功颂德的语汇,属于书写同类文章必须使用的套话,这是一种文学“惯例”(literary convention),否则就不成“体统”。这样的语汇,在维吉尔的史诗《伊尼德》中更多。其实,扬雄之所以得以升迁,真正的原因是他服务朝廷的时间太久了。他的同事们早就升迁过多次了。不予扬雄以升迁,实在说不过去。从《汉书·扬雄传》看,在官场里势利眼多,而扬雄是个老实人。既然官场势利眼多,于是扬雄索性以著文章为人生的目标,并期待以文章而流芳于后世。这个人生目标,扬雄完满地实现了。
扬雄《法言》卷二《吾子》云:“古者,(扬)〔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9]45孔子是圣人也。孟子也是圣人,号称亚圣。向孟子学习,争取达到孟子的人格高度,这是扬雄对自己的一贯要求,也是扬雄对自己的人格评价。这个评价是公允的,人,毕竟还是自己最了解自己。
二、征圣和宗经
征圣和宗经是扬雄文学批评观的两大基石。征,原作“徵”。汉·许慎《说文解字》:“凡壬之属,皆从壬。徵,召也。”[10]389召,这是“徵”字的原初义,不过此义与“征圣”之“征”尚有相当的距离。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召者,也。《周礼》司市典祀注,乡饮酒礼注,乡射礼注,皆曰:徵,召也。按:征者,证也,验也,有证验斯有感召,有感召而事以成。”[10]389一看段注,豁然贯通,原来“徵”的意思就是征验,证验。证验,即验证。征圣,以圣人为标准来验证。既要以圣人的标准来验证,就免不了时常征引圣人的著作。作为一个基本的技术手段,征圣,也就意味着征引圣人的言论。这样的理解,似乎简单了一些,但是它切中要义。圣人之道在哪里?圣人之道就在圣人的言论里。道即是言,反之亦然。
当人们有了某种看法的时候,如何知道它对与不对呢?在扬雄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圣人为标准来进行验证。《法言》卷二《吾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
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
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
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9]46
扬雄善于运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来展开论说。他假借“有人”来发问。有人说,每个人都肯定自认为正确的东西而否定自认为不正确的东西,那么谁来纠正他们的是非呢?回答如下,万千事物错综复杂,那么就由天来决定它们。众人言论无法统一,那么就由圣人来评判它们。有人又说,怎样才能见到圣人并请圣人来做评判呢?回答如下,如果圣人活着,那么就直接请教圣人。如果圣人去世了,那么就用圣人的书来做评判,因为圣人和圣人所著的书乃是相互统一的。扬雄认为,他自己就对圣人的思想有很好的继承。由于扬雄曾经将自己比作孟子,因此扬雄在这里所云之圣人,指的是孟子之前的诸如周公、孔子等伟大的思想家。《淮南子》卷二一《要略》:
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11]728
周公是周代文化的主要建设者,礼乐制度就是周公制定的。孔子述而不作,他的功劳主要是阐释周公的思想。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有七十二人造诣较高而被称颂为贤人。周公和孔子这样的圣人生活在轴心时期,他们距离扬雄的时代已经有了距离,他们对于后来的人们则有更大的时间距离。因为圣人早就去世了,所以谁也无法再见到他们。那么,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应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阅读圣人的书。
征圣,这是扬雄提出来的文学批评观念,它直接响了后来时代的文学批评。到了南朝的梁代,文学批评家刘勰出现了,他撰写了文学批评的专著《文心雕龙》五十篇,该书第二篇就叫做《征圣》。刘勰《文心雕龙·征圣》: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12]11
所谓圣,指的是具有独立的创造性的人物。所谓明,指的是那些善于继承圣人学说的人。圣人的著作能够陶冶人的性情,能够将人们的道德品质引入向上一路。我们虽然见不到孔夫子本人,但是我们能够读到他的书。孔夫子的思想和感情体现在他的文章里。古代圣王的教化存在于他们的典册中。虽然圣人去世已久,但是他们的风采还是看得见的。在圣人的精辟言论中就洋溢着他们的风采。唐尧的时代是盛世,那时的文化已然兴盛。周代文化发达,为我们留下了学习的榜样。一个时代的政治教化如何,可以从遗留下来的文章中寻觅到踪迹。
宗经,这是扬雄文学批评观的又一基石。宗,动词,宗法。经,名词,经典。宗经,宗法经典,尊崇和效法经典。宗经与征圣,二者密不可分。周公是圣人,然而只有那些生活在周公身边的人可以直接征圣。孔子是圣人,然而也只有那些生活在孔子身边的人才能够直接征圣。即使与圣人生活在同一时代,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直接征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征圣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宗经。《法言》卷二《吾子》:
观书者譬诸观山及水:升东岳而知众山之峛崺也,况介丘乎!浮沧海而知江河之恶沱也,况枯泽乎!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9]35
宗经,就是读圣人的书。那么,如何读书呢?读书是一种精神的游历活动,它在本质上与观山览水相似。
登上东岳泰山之巅,就看得见周围群山逶迤了,何况那些小土丘呢。登上巍峨的泰山而感觉得周围的山峰渺小。孟子自称为孔子的私淑弟子,他曾经转述过孔子的登山感受。《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13]356当孔子登上东山的时候,他便觉得鲁国小了。当他登上泰山的时候,又觉得天下也小了。杜甫也有这样的体会,《杜诗详注》卷一《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14]3开元二十四年(736),杜甫参加了科举考试。落第之后,他开始了在齐鲁大地上的漫游。当时杜甫的父亲杜闲(684前—742?)在兖州任司马。杜甫前往齐鲁漫游,既探望了父亲,又游览了泰山。在泰山顶上,杜甫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看见山脚下有云朵在飘逸,群山小得像一个个青葱头,于是他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有趣的是,《圣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旧约《以赛亚书》2:2—3写道:
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15]660
迈动双脚,攀登高山,一步一步接近真理,此事何其佳美!
在湛蓝的大海上航行就知道江河的水有多么浑浊了,何况那些干涸的小池塘呢。《历代赋汇》卷二四王粲《游海赋》:
乘菌桂之芳舟,浮大江而遥逝;翼惊风而长驱,集会稽而一睨。登阴隅以东望,览沧海之体势。吐星出日,天与水际。其深不测,其广无臬。寻之冥地,不见涯泄。章亥所不极,卢敖所不屇。怀珍藏宝,神隐怪匿。或无气而能行,或含血而不食;或有叶而无根,或能飞而无翼。鸟则爰居孔鹄,翡翠鹔鹴,缤纷往来,沉浮翱翔;鱼则横尾曲头,方目偃额,大者若山陵,小者重钧石。乃有贲蛟大贝,明月夜光,蠵鼊瑇瑁,金质黒章。若夫长洲别岛,棋布星峙,高或万寻,近或千里,桂林聚乎其上,珊瑚周乎其趾。群犀代角,巨象解齿,黄金碧玉,名不可纪。[16]102
以航海喻读书的确是高妙的比方。由此而观之,“留洋”的确是必要的。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兴起又一次出国留学的高潮,可喜可贺!没有船舶,无法渡过大江大河,正如《诗经·谷风》所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17]30
自然界中的小溪可以淌水而过,小河可以游水而过,然而大江大河,水深流急,必须凭借舟船才能够渡过。知识的海洋更是如此。书籍众多,一个人无论多么努力,也是读不完的。既然如此,就必须有选择性地阅读。任何学科,真正紧要的书并不是很多。就中国文史哲诸科目而言,最重要的书就是《五经》。
与登山览水相仿佛,没有《五经》根本就无法达到真理。放弃正常的美味而癖好稀奇的食物,那是没有办法懂得食物的味道的。一般而言,圣人的著作水准在诸子之上,放着圣人的书不读,而只读诸子的书,那就是本末倒置,是根本无法认识真理的。由于圣人的著作难度较大,因而许多人不愿意阅读原著而只看辅导材料。其实,这样做是根本无法领略圣人著作的精髓的。
征圣和宗经又是扬雄进行文学批评活动的出发点。《法言》卷二《吾子》: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君子言也无择,听也无淫。择则乱,淫则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9]41
就数量而言,没有谁的书有书商那么多,然而很少有书商是真正的学者。喜欢读书是好事,但是读书要有所选择。那么,如何选择呢?孔子就是最好的选择标准。喜欢议论不是什么坏事,但是议论也要有个标准,否则就是胡乱地说一气,或者如铃铛一样叮当作响。那么,议论的标准是什么呢?议论就是发表意见,发表意见必须有个标准。最好的标准还是孔子,议论时以孔子为标准,就能做到正确的取舍了。自己说话和听人家说话,都要有标准,否则就造成混乱。传述正道的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传述正道,而不要传述歪理邪说。这是因为,传述歪理邪说的人绝不会走上正道。
扬雄的宗经说对刘勰有直接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第三篇就叫做《宗经》。
三、对偶状范畴
扬雄的文学批评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喜欢采用呈对偶状态分布的范畴来建构其文学批评的体系。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特征。任何一种民族的语言,除了少数几个连词之外,其他的词都是概念。一个民族的语言包含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单词。在建构一门学科的时候,不可能也没必要将所有这些单词都作为概念来研究。通常的做法是,将那些能够反映某一学科的普遍本质而又概括性强的概念挑选出来,作为研究的对象。这种能反映学科的普遍本质而又概括性强的概念,有个名称,叫做范畴。关于范畴,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写道:
Wenn alles Wirkliche die Erscheinung des Geistes ist,so fällt die Metaphysik mit der Logik zusammen,welche die schöpferische Selbstbewegung des Geistes als eine dialektische Notwendigkeit zu entwickeln hat.Die Begriffe,in welche der Geist seinen eigenen Inhalt auseinanderlegt,sind die Kategorien der Wirklichkeit,die Gestalten des Weltlebens,und die Philosophie hat dies Reich der Formen nicht als gegebene Mannigfaltigkeit zu beschreiben,sondern als die Momente einer einheitlichen Entwicklung zu begreifen.[18]526
如果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精神的表象,那么形而上学与逻辑就一致了,因为逻辑不得不作为辩证的必然性去发展精神那创造性的自我运动。在精神将其自身的内容解析开来的那些概念中,存在着这样一些现实的范畴,它们是世界生命的样态。哲学所拥有的这个关系到种种形式的王国,并非作为杂多而被描述,而是作为统一发展的要因而被把握。(拙译)
这是对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关于范畴的学说的概括。黑格尔还认为,文化的进步,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会使得较高级的思维关系逐渐显露出来,并将这些关系提高到更大的普遍性,从而引起人们更密切的关注。即使是经验的和感性的科学,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它们一般都是在最习见的范畴之内活动的。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1870—1924)在研究黑格尔的过程中对范畴有了更深的认识。列宁写道:
“在这面网上,到处有牢固的纽结,这些纽结是它的”精神或主体的“生活和意识的据点和定向点……”
如何理解这一点呢?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9]78
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一书中,列宁称范畴为“小阶段”“纽结”“环节”“梯级”“据点”和“定向点”。列宁指出,人对自然的认识(=观念)的各个环节,就是逻辑的范畴。由此可知,欲透彻地研究一门学科就必须把握一些重要的范畴。在对一门学科进行史的考察时,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史的考察要求我们注重阶段性。
虽然范畴与概念的关系密切,但是它们产生的时间先后不同。一经有了语言,概念就产生了,然而范畴的产生却要晚得多,因为范畴是高级思维关系逐渐显露的结果。学科的进步,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频繁出现的概念上。随着这些概念的范围逐渐明朗化,它们所包含的内容逐渐具体而稳定,于是范畴就被确定了。由于学科的进步是无止境的,范畴按理说也可以无限地多,然而,过多过滥就会失去概括性。因而,一门成熟的学科,其范畴一般被框定数百个之内。同时,有的范畴经过长时期的使用就会化为常识,于是它们就会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学科的进步,又会有若干新的范畴形成。任何一门学科的范畴都只是一个大体稳定的体系,而不是恒定不变的语汇堆积。卓越的学者会将自己的思想凝练为范畴,并用新的范畴组织起精彩的命题来,由此推动学科前进。
中国学者提出来的范畴,有许多呈对偶状态分布。这是因为,汉语具有强烈的对偶思维特征。中国人喜欢作对联。四联八句的律诗,其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百韵长律,除开首联和尾联之外,其他各联,必须对仗。日本亚洲史家宫崎市定(Miyazaki Ichisada,1901—1995)曾经风趣地说,在汉语中只有一个“渴”字才找不出其对偶来,而其他的汉字都能够找出对偶。至于扬雄,他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文学批评家。扬雄提出了三组呈对偶状态分布的范畴,简称对偶范畴。
(一)事理与文辞
扬雄将事理与文辞作为一组对偶范畴而展开了精彩的论述。《法言》卷二《吾子》:“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9]34扬雄认为,君子重视事实而轻视虚辞。在写文章的时候,如果事胜于辞,就难免有率直的毛病;如果言辞超过事实,就难免有夸张的毛病。事实和言辞相称才合乎文章的轨范。在写文章的时候,言辞要足够,事实也要足够。所谓足够,指不多不少。《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3]89这是孔子关于文质的言论。文,文采。质,质朴。孔子所讲的是事实与言辞的关系。扬雄说:事辞称则经。经,作为名词指经典。扬雄将名词“经”(classics)当作形容词(classic)来使用。赋,作为名词指一种文体,赋的特征是夸张和富丽。扬雄将名词“赋”(rhapsody)当作形容词(rhapsodic)来使用,这与他轻视赋的言论所透露出来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扬雄认为经典著作是事与辞相称的典范,这与他宗经的思想是一致的。扬雄通过文章体类的辨析而发展了孔子的文质论。
扬雄还通过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比较来阐述他对事理与文辞关系的看法。《法言》卷五《问神》:
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面相之,辞相适,捈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9]110
言,指口头语言。书,指书面语言。文学属于语言艺术。口头文学注重声音的运用,书面文学注重文字的表达。至于绘画,则属于造型艺术。文学和绘画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尽管如此,它们都能够表现人的精神活动,表达人的情感。言为心声,书为心画,这是扬雄在论述事理与言辞关系的时候提出来的两个美学命题。言和书,既包括文学艺术,又包括学术著作。
尽管扬雄重视文章的内容,但是他认为言辞也是必须讲究的。《法言》卷七《寡见》:“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9]152扬雄用比喻来告诫作家们,在文辞上必须下功夫。未经雕琢的玉,仅仅是一种石材,而不是玉器。缺少文采的言辞,不可能完美地传达经典的内容。刘勰赞成扬雄的观点,《文心雕龙·宗经第三》:“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12]19宗法经典离不开征引圣人的著作。要征引圣人的著作,就要学习圣人对言辞的态度。《法言》卷五《问神》:“或问圣人表里。曰:威仪文辞,表也;德行忠信,里也。”[9]244为人,要有庄严的仪容。作文,要有优美的言辞。仪容和言辞都是内心的流溢。圣人们都是表里如一的。既然如此,我们也应该表里如一,努力做到仪容庄严、言辞优美。
在扬雄之前,孔子论述了事理与言辞的关系,这是文质论。在扬雄之后,六朝的批评家们进一步讨论了事理与言辞的关系,这是文笔说。扬雄既是文质论的后继者,又是文笔说的先驱者。而且,扬雄的心声心画说,不仅涉及文学作品,还涉及学术著作。扬雄之所以能够成为联系圣人与一般文学批评家之间的桥梁,乃是因为他本身也部分地具备了圣人的品格。从历史上看,扬雄未曾被尊为圣人,但是他至少算得上是一位圣徒。圣经新约《以佛所书》3:8—9云:“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能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15]216这是圣徒保罗奉差传播福音时讲的话。扬雄在弘扬孔子学说方面的功绩,完全比得上圣徒保罗在传播福音方面的功绩。
(二)温润与深沉
温润与深沉,这是扬雄提出来的另一组对偶范畴。《法言》卷十三《孝至》:“或问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观《书》及《诗》,温温乎其和可知也。”[9]352和,指刚柔相济。泰,副词,指在程度上非常充分。泰和,指刚柔相济达到了非常充分的地步。唐,唐尧。虞,虞舜。成,周成王。周,周公。帝尧、帝舜、周成王和周公,都是儒家称颂的圣人。扬雄说这一番话的时候,其思路如下。唐、虞、成、周所处的时代是太平盛世的顶峰,其时代特征是泰和。《尚书》和《诗经》正是唐、虞、成、周时期的产物。既然如此,那么《尚书》和《诗经》也就体现了唐、虞、成、周时期的时代特征。质言之,在扬雄看来,《尚书》的审美特征是“和”,《诗经》的审美特征也还是“和”。扬雄对《诗经》的审美特征的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扬雄所言的《诗经》主要指《小雅》《大雅》和《三颂》,而不包括《国风》中那些讽刺社会现实的作品。传统的《诗经》学说认为,《小雅》中《南有嘉鱼》至《菁菁者莪》诸篇,《大雅》中的一部分作品,以及《颂》中的《周颂》,都产生于周成王和周公时期。《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其文本质地都是温润和煦的。“温温”二字叠用,表示温润得恰到好处。通过叠用表示样态的形容词来表达某种审美品质恰到好处,这是扬雄的行文风格,在扬雄的文章中还有不少这样使用形容词的例子,比如《法言》卷五《问神》:“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谯乎!”[9]106今存《尚书》包括四个部分,它们是《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分别产生于虞、夏、商、周时期。浑浑,浑厚得恰到好处。灏,通浩,灏灏,浩瀚得恰到好处。噩,通愕,噩噩,严敬得恰到好处。扬雄还说,周朝以后的各个时期就没有产生出具有那般文本质地的著作了。
和,即中和,儒家的审美观以中和为美。《诗经》的审美特征是中和美,这是没有争议的。《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3]53无邪,即中和之意。《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3]66古人认为,在一系列的事物中,排列在第一位的就是最重要的。《关雎》是《周南》的第一篇,又是全部《国风》的第一篇,还是整个《诗经》的第一篇,因而《关雎》是非常重要的诗篇。淫,过多。快乐的时候,当以不过头为宜,快乐过头也会招致悲伤。伤,毁伤。悲哀的时候,当以不毁伤身体为度。因为《关雎》的审美特征是以中和为美,所以《关雎》就向示人们昭示了《诗经》的总体审美特征。尽管在《诗经》中有些作品因辛辣地讽刺社会现实而不那么中和,但是《诗经》总体而言还是以中和为美的。《尚书》的审美特征是否也是中和美呢?这是有争议的。韩愈《进学解》云:“《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20]131诰,告戒,劝勉。诰是一种文章体裁,一般用于上级对下级。在《尚书》的《周书》中,有诰六篇,它们是《大诰》《康诰》《酒诰》《诏诰》《洛诰》《康王之诰》。在《尚书》的《商书》中,有含“盘”字的文献三篇,它们是《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盘庚,商王,名旬,盘庚是庙号。盘庚是汤的十世孙,祖乙的曾孙,阳甲的弟弟。《书序》云:“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21]223殷商是同一朝代的两个阶段,以迁都为划分阶段的节点。盘庚继阳甲即位,将王都从奄(今山东曲阜)迁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盘庚》上中下三篇是《尚书》中篇幅最长的文章,读起来费劲。《尚书》是出了名的难读,连唐代大文豪韩愈都觉得它佶屈聱牙。不过,这是就《尚书》各篇的文本质地而言的。在审美的理论主张方面,《尚书》所提倡的毕竟还是以中和为美。《尚书·舜典》:
帝曰:“夔,命汝典乐,敎胄子,直而温,寛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21]78
和,指各种音乐要素之间的相反相成、相辅相成。在文学发展的初期,诗歌、音乐和舞蹈尚未分化为三个独立的艺术部门,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发挥言志和育人的作用。在这一阶段,各个艺术部门之间的和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诗歌和舞蹈都含有音乐的要素,它们只有在和的状态下才能够完美地结合。后来,诗歌、音乐和舞蹈逐渐分离为三个不同的艺术部门。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和还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言志要求完美地表达思想和感情,育人的目的在于指引人群和美共处。
《尚书》的文本质地是佶屈聱牙的,而《尚书》的美学主张却是“和”。这两者之间的反差让人难以理解,于是扬雄撰文进行解释。扬雄《解难》云:
扬子曰:“俞。若夫闳言崇议,幽微之涂,盖难与览者同也。昔人有观象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昔人之辞,乃玉乃金。彼岂好为艰难哉?势不得已也。独不见夫翠虯绛螭之将登乎天,必耸身于苍梧之渊;不阶浮云,翼疾风,虚举而上升,则不能撠胶葛,腾九闳,日月之经不千里,则不能烛六合,耀八纮;泰山之髙不嶕峣,则不能浡滃云而散歊烝。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臧,定万物之基。《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煕。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今夫弦者,高张急徽,追趋逐耆,则坐者不期而附矣;试为之施《咸池》,揄《六茎》,发《箫韶》,咏九成,则莫有和也。是故钟期死,伯牙绝弦破琴而不肯与众鼓;獿人亡,则匠石辍斤而不敢妄斲。师旷之调钟,竢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8]201-202
扬雄认为,真正的“和”是温润与深沉的统一。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道理。
其一,从自然界看,温润与深沉是统一的。龙有多种,有的龙有角,有的龙无角。在无角的龙中,有一种叫虯,还有一种叫螭。虯的颜色青翠,螭的颜色绛红。虯和螭飞升天宇都得凭借大风的力量。无角的龙,无论是虯,还是螭,都比一般有角的龙形体小一些。由于它们是小龙,所以显得温润。然而,扶摇直上九天的大风却不温润,它是积聚于深沉之处的力量之运动。
其二,从著作史看,真正的“和”是温润与深沉的统一。《易经》是《周易》的经文部分,它采用卦和爻来占卜和象征自然界与社会变化的吉凶。卦的基本符号是代表阳性的直线和代表阴性的断线。将这两种符号每三个配成一卦,一共得到八个“经卦”(基础卦)。将八个经卦两两相配,一共得到六十四个“别卦”(衍生卦)。每一别卦六爻,一共三百八十四爻。解释卦的语句叫卦辞,解释爻的语句叫爻辞。卦辞和爻辞一共四百五十条。卦和爻的图像叫做卦象和爻象,它们都很简单,这是《易经》温润的一面。卦辞和爻辞的语句非常艰深,这是《易经》深沉的一面。由于《易经》是经书的一种而经书的总体风格是“和”,因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易经》的审美风格是“和”。由易学史可知,“和”的确是温润与深沉的统一。《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写的《鲁春秋》并参考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史官的记载而作的一部编年史。《春秋》由一些条文组成,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条文仅有一个字。《春秋》纪事非常简约,这是温润的一面。《春秋》的内涵深奥,这是深沉的一面。然而,对于《春秋》的解释却是浩瀚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本来是用来解释《春秋》的,然而在后世的人们看来,《三传》本身也十分艰深。历代以来产生过大量的阐释《春秋》和《三传》的著作,它们不仅没有把问题阐释得简单,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加艰深了。可是,又有谁敢说《春秋》的审美风格不是“和”呢?艰深,就是奥义的深沉。由春秋学史可知,“和”也的确是温润与深沉的统一。其他的儒家经典,诸如《尚书》和《诗经》,也同样如此。
其三,从音乐史看,真正的“和”是温润与深沉的统一。《咸池》《六茎》和《箫韶》均为古乐的名称。《咸池》是黄帝之乐,《六茎》是颛顼之乐,《箫韶》是帝舜之乐。按照当时奏乐的规矩,这些古乐均须演奏九遍,而每一遍的曲调都要有变化。古代的圣贤都说,古乐是最完美的音乐。聆听古乐使人心情宁静,这是古乐温润的一面。尽管如此,演奏古乐的时候却没有人唱和。这是因为,古乐中包含着深刻的难以言说的含义。不晓得一支曲子的含义,又怎么能够唱和呢?从音乐史可知,“和”同样是温润与深沉的统一。
其四,至于老子所著的《道德经》,那就更能说明“和”是温润与深沉的统一了。《道德经》七十章云:“知我者希,则我贵矣。”[22]183希,稀疏,少。老子说,了解我的人越少,则我就越难得。老子为什么这么说呢?答案见于王弼注:“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无匹,故曰‘知我者希,则我者贵也。’”[22]183由于老子所讲道理深奥,因此了解他的人就少。“(老子)晚年过着隐居生活,‘著书言“道德”五千言’,即今流传的《老子》一书,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是用韵文写的哲学诗。”[23]104这是《道德经》温润的一面。在《道德经》一书中,老子提出了以“道”为最高实体的宇宙观,以“静观”和“玄览”为方法的神秘主义认识论,以“反者道之助”为基本命题的辩证法思想。此外,在《道德经》一书中还保存了许多古代关于天文、养生、生产技术、军事理论和用兵方法的知识。《道藏》中的许多著作都是围绕《道德经》而展开的,道教经典,浩如烟海,艰深屈折,大都难读。这是《道德经》深沉的一面。从道学史可知,“和”是温润和深沉的统一。
(三)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与图政事,故可以为列国大夫也。”[5]342赋这种文学体裁是古代文人的爱物,尤其是文学家的爱物。赋是一种介于文章与诗歌之间的文体。古人编文集,大都把赋列在全集之首。比如,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就将赋列在每一家诗集的首位。徐鹏《前言》:
此五十家诗集版式一律,线黑口、单鱼尾。鱼尾下为集名、卷、页。左右双边,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版式宽疏,清朗悦目。所收均为初、盛、中唐诗集,无晚唐人作品。作品收诗、赋两部分,先赋后诗。[24]2
较诸诗歌,赋的篇幅更长,更宜于呈才,故而许多古代文人都把作赋当成自己的基本文学训练之一。围绕赋这一文体,扬雄提出了很好的见解。在扬雄建构关于赋的文学命题时,他提出了一组对偶范畴,即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这是扬雄提出来的第三组对偶范畴。《法言·吾子》云: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
曰:必也淫。
淫、则奈何?
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9]27
针对汉赋,扬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内容上看,汉赋失去了讽谏之指归。从形式上看,汉赋徒尚靡丽。在此基础上,扬雄提出了著名的命题:“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以,并列连词,意为“而且”。欲透彻理解这一命题,就必须弄清楚以下五个问题。
其一,诗人之赋,其作者是怎样的人?这个问题涉及到赋的流变。《文选》卷一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25]1赋起初并不是一种文体,而是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系六义之一,即不用比喻,不假象征,而直书其事。战国时期的荀子创作了《赋篇》,这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荀子《赋篇》兼具诗歌与散文的性质。汉代常把“辞”和“赋”统称为辞赋。辞,因为产生于楚地,故而又叫楚辞。屈原的作品是楚辞的大宗,《离骚》是其中最辉煌的篇章,因而称为骚体赋。屈原之后,写作辞赋的人越来越多。到汉代,辞赋形成一种特定的体制,它讲究文采、重视韵律。一般认为,此后辞赋或骈偶化,或散文化。接近骈文的为骈赋、律赋,接近散文的为文赋。扬雄所云“诗人之赋”,主要指屈原的骚体赋,其特点是直谏。除了屈原之外,那些以赋直谏的作家都是“诗人之赋”的作者。那么,为什么称他们的作品为“诗人之赋”呢?《史记》卷八四《屈原传》: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26]505
屈原的辞赋符合《诗经》的写作精神,因而被称为“诗人之赋”。简言之,诗人之赋,如果严格地施予新式标点,那么当写成“《诗》人之赋”。
其二,辞人之赋,其作者是怎样的人?《史记》卷八四《屈原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26]507扬雄点名批评了宋玉、唐勒、景差、枚乘。这四人中,前三位并非汉代人,而是战国时期的楚人,只有枚乘才是汉代人。不过,缺少直谏精神的汉赋却是模仿他们四人辞赋的结果。虽然此四人都学习屈赋,但是他们没有学到屈赋的精神,而是仅得其皮毛。学习屈赋而弃其精神,其结果必然滑稽可笑。《法言·吾子》有云:
或曰: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
曰:其文是也,其质非也。
敢问质?
曰:羊质而虎皮,见草而说,见豺而战,忘其皮之虎矣。
圣人虎别,其文炳也。君子豹别,其文蔚也。辩人狸别,其文萃也。狸变则豹,豹变则虎。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君子言也无择,听也无淫。择则乱,淫则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
孔子之道,其较且易也。”[9]39-42
所谓汉赋属于辞人之赋,是就汉代多数辞赋作家而言的。在汉代的辞赋作家中,也有少数人相当优秀。他们当属于写作“诗人之赋”的那些作家之列。比如,贾谊和司马相如就是如此。贾谊的辞赋以《鸟赋》和《吊屈原赋》最有名,且具有一定的讽喻作用。司马相如的辞赋以《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和《长门赋》最有名。司马相如作赋,目的明确,即用以讽谏。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扬雄自己的赋,属于哪一类赋呢?扬雄的辞赋有四大名篇,即《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和《河东赋》,它们均为讽喻汉成帝广建宫室、沉溺游猎而作。扬雄的四大名赋以皇帝的奢侈腐化生活为讽喻的对象,较诸司马相如的赋作,它们显然具有更大的讽喻意义。由此而观之,扬雄的辞赋属于诗人之赋。
其三,辞赋的共同特征是什么?《文选》卷五二曹丕《典论论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25]720由于赋是从古诗中变化衍生出来的,所以诗歌和辞赋都有追求华丽的趋向,只不过辞赋在这方面更加突出罢了。《文选》卷四五皇甫谧《三都赋序》:“玄晏先生曰: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25]640皇甫谧(215—282),字士安,号玄晏先生,是生活在魏晋之间的文学批评家。美丽之文,赋之作也。这是皇甫谧对赋的界定。将这句话稍加整理,即可得到其现代汉语之表达:赋是美丽之文。皇甫谧抓住了赋这一文体的突出特征:丽。“丽”有多种,包括富丽、华丽、艳丽、秾丽、靡丽等。这些美质在各家的赋中均有所体现。其中,富丽最得赋的文学体征之精髓。朱熹《诗集传》卷第一《葛覃》一章注:“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27]3敷陈,铺叙和陈述,简言之,即铺陈。铺陈是赋的另一形式特征,而“富丽”一语可将“美丽”与“铺陈”统合起来。
其四,辞赋的功用应该是什么呢?《文选》卷四五皇甫谧《三都赋序》:“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25]640根据先王的教导对社会上的负面现象进行讽刺,本诸忠臣之心对君主的不当行为进行劝戒,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讽谏。如果辞赋作家一味堆垒华丽的辞藻,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一介善于呈才之士,这样的辞赋作家对于社会是没有多少作用的。只有那些通过写作辞赋而进行讽谏的作家,才能够有益于社会,才能够尽忠于君主。这是因为赋的社会功能就是讽谏。从历代辞赋的具体情形看,对君主进行劝戒的作品多于对社会负面现象进行讽刺的作品。那么,赋这一文体实现了讽谏的双重功能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劝戒了一国之君,也就同时完成了对社会的负面现象进行讽刺这一工作。国君得到劝戒之后,便会勤于政事,设法去消弭社会上的各种负面现象,而这正是政事之一项。
其五,两类辞赋的差异在哪里呢?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其共同点为“丽”。这是因为,辞藻华丽是赋这一体裁的文体规定性,它具有范畴的力量。如果某位辞赋作家写出一篇文字来,而其文辞不华丽,那么很显然这篇文字就不是赋了。即使这篇文字很好,也只能算是其他体裁的文章,而绝不是赋。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其间的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一个“则”字上。则,法则、法度。诗人之赋有法则,有法度。辞人之赋缺少法则,没有法度。由于缺少法则,没有法度,就会造成华丽辞藻的过多堆积,这就叫做“淫”。辞人作赋,没有原则,一味呈才,烦冗、泛滥而又放荡,这是不好的。人们常说“妙语连珠”,其实这并不是文章的高境界。上好的文章不当妙语连珠。连珠般滚落出来的辞藻,往往带来过度甜熟的滑稽的效果。中国文章学史告诉我们,入宋以后辞藻华丽的赋实际上逐渐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文赋。文赋的突出特征是辞藻不华丽,而以平淡出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方面,这是以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1007—1072)大力提倡平易文风之缘故。宋·吴充《欧阳修行状》:“嘉祐初,公知贡举,时举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公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髙第者,黜之几尽,务求平澹典要。”[28]1339欧阳修一向主张为文流畅自然,他强烈反对古奥艰深的文风。虽然扬雄与欧阳修相距千余年,但是他天才地预见了辞赋在体制上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长时期的过多的华丽辞藻的堆积造成了人们的审美疲劳。换言之,“淫”使人受不了。由此而观之,以“丽以淫”为特征的辞人之赋实在要不得,扬雄之反对辞人之赋,不仅正确,而且具有历史的远见。
四、发展的曲线
扬雄是一位具有发展意识并且能够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文坛上的各种现象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观,发展意识主要体现在三条变化的曲线之上。
(一)从童子到壮夫
扬雄从辞赋家转型为哲学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身心成长的过程。扬雄把昔日的“吾子”称为“童子”,把新生的“吾子”称为“壮夫”。这样的认识,颇类似陶渊明的人生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29]391扬雄的一生,是不断地追求进步的一生,是不断地寻找变革的一生,是不断地谋求发展的一生。《法言》卷二《吾子》: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
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或曰:赋可以讽乎?
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或曰:雾縠之组丽。
曰:女工之蠧矣。
《剑客论》曰:剑可以爱身。
曰:狴犴使人多礼乎?[9]25
吾子,本义“我的先生”,这是扬雄的自称,带有调侃的语气。通过吾子和某位对话人之间的问答,扬雄讲述了他的身心成长历程。
少年扬雄喜欢作赋,后来他认识到这好比雕章琢句罢了,只是一种小本领。待到成长为壮夫之后,他就不喜欢作赋了,因为他决心干一番更大的事业。有人问:赋不是可以用来讽谏吗?回答说:赋本来可以用来讽谏,但实际情况表明,赋所起的作用其实是怂恿而非讽谏。有人说:薄雾般柔曼的轻纱漂亮得很呢!回答说:正因为织品漂亮才阻碍了纺织女工的进步,人心毕竟易于满足啊。有人说:《剑客论》这本书讲过,刀剑可以用来护身。回答说:突刺和推挡,只会招来杀身之祸。君不见,刀客刀下死,剑客剑下亡么?可以说,这一番论辩发自扬雄的肺腑,可谓他的心声。扬雄酣畅淋漓地嘲笑自我,他在嘲笑自我之中得到了灵魂的升华。
扬雄身心的成长历程对大诗人杜甫也有所启迪。《杜诗详注》卷九《堂成》:“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14]291杜甫《堂成》诗作于上元元年(760)末。这一年杜甫四十九岁,他携家人从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经由同谷(今甘肃省同谷县)来到成都。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成草堂一座。在长期的漂泊中,杜甫的身心经历了一番变化,他早已从青年时代对朝廷充满希望变成了而今的能够洞察社会现实了。《堂成》一诗,与其说为庆贺草堂建成而作,不如说为其身心之已然筑基而作。扬雄写作《太玄经》后,本该有所封赏,但是他并未得到什么禄位,于是他遭到人们一阵又一阵的嘲笑。在此情况下,扬雄挥笔写下了《解嘲》一文,声言他虽然未获得禄位,但是获得了淡泊不动的心境。在成都建成草堂的杜甫也具有这样的心境。
杜甫常常将自己与扬雄作比较,《杜诗详注》卷一《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歘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14]33-35
韦左丞,指韦济。丈,这是对比自己年长的男子的尊称。韦济(688—754),唐京兆杜陵人,宰相韦嗣立第三子,于天宝九载(750)迁尚书左丞。此诗作于天宝十一载(752),杜甫时年四十一岁。杜甫在诗中感谢韦济对自己的推奖,并直抒个人抱负,故而诗中充满了壮志难酬的郁愤。在诗中,杜甫对自己的文学才华做了评估:其辞赋与扬雄匹敌,其诗歌与曹植接近。杜甫的人生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在国级官员的层次上干一番宏大的事业。蔡梦弼撰《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二:
葛常之《韵语阳秋》曰:“子美高自称许,有乃祖之风。上书明皇云:臣之述作,沉郁顿挫,扬雄、枚皋可跂及。《壮游》诗则自比于崔、魏、班、扬,又云:‘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赠韦左丞》则曰:‘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甫以诗雄于时,自比诸人,诚未为过。至‘窃比稷与契’,则过矣。唐史氏称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岂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其忠荩亦可嘉也。”[30]166-167
杜甫七岁时就会做诗了,算是优秀的童子。不过,童子毕竟还不是壮夫。欲有贡献,须炼身心,以成壮夫,方有作为。杜甫的个人抱负与扬雄类似,其遭际也与扬雄类似。不仅如此,在史籍上都有一些贬损他们的话。理解伟大的人物需要时间。尽管在生时遭人误会,但是扬雄最终成了伟大的哲学家。尽管在生时历经磨难,但是杜甫最终成了伟大的诗人。他们都经历了从童子到壮夫的华丽转身。
(二)从辞赋到学术
就世界文学史而观之,作家们在青年时代大都偏好辞藻富丽的风格。英国大诗人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就是如此。莎士比亚一生中创作过两部长诗,它们都以辞藻富丽著称,并带有浓厚的模仿风格。莎士比亚于1592至1593年间创作了第一部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Venus and Adonis),该诗长达1194行,是一本书的规模。关于此诗,《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主编写道:
It is an early example of the Ovidian erotic narrative poems that were fashionable for about thirty years from 1589;the best known outside Shakespeare is Christopher Marlowe’s Hero and Leander,written at about the same time.[31]223
这是一部奥维德式的性爱叙事诗的早年的例子,奥维德式性爱诗从1589年起风行了大约三十年。除了莎士比亚之外,这类诗歌中最著名的是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海洛与勒安得尔》,它写于同一时间。(拙译)
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43 BD—AD 17)是古罗马大诗人,著有《恋情集》(Amores)、《爱的技巧》(Ars amatoria)和《情伤良方》(Remedia amoris)等长诗。维纳斯是罗马神话中专司爱与美的女神。阿都尼是美少年,他渴望得到爱情,但却莽撞冲动,一再贻误“战机”。海洛是一位女祭司。勒安得尔是海洛的情夫,为了见到海洛,他每晚横渡达达尼尔海峡。
莎士比亚于1593至1594年间创作了第二部长诗《卢克丽丝受辱记》(The Rape of Lucrece),此诗长达1855行,更是一部书的规模。《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主编写道:
Like Venus and Adonis,The Rape of Lucrece is an erotic narrative based on Ovid,but this time the subjectmatter is historical,the tone tragic.[31]237
与《维纳斯与阿都尼》一样,《卢克丽丝受辱记》也是一部以奥维德的作品为基础而创作的性爱叙事诗,只不过这一次的题材是历史的了,而叙事的口吻却是悲剧的。(拙译)
此诗的本事为发生在古罗马的一个历史事件。公元前509年,优雅的少女卢克丽丝被皇子强奸,之后她因羞愧而自杀。此事件引起公愤,民众奋起,推翻了暴君的统治。
扬雄也是如此。青年扬雄,喜爱辞赋。他羡慕司马相如赋“弘丽温雅”的美质,并且以之为典范来进行模仿。《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5]870
优秀的辞赋以讽谏为旨归。司马相如的四大名赋,如此;扬雄的四大名赋,亦如此。然而,这些辛苦写出来的辞赋,在讽谏方面竟然收效甚微。《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赞曰:“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5]585那些受到辞赋家批判的东西,反而受到帝王和贵戚之流的追捧。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辞赋这种文体使用大量的美丽辞藻和对偶句式来修饰,并通过尽可能的夸张来叙事。就一篇辞赋来说,往往百分之九十九的篇幅被用来描写和铺叙那些受批判的对象。其结果就是该受批判的东西反而占据了主位,而应当提倡的东西只是轻轻一笔带过。辞赋家创作的原来意图被阉割了,批判的武器受到了武器的批判,辞赋家们一个个成了教唆犯。扬雄的神思,回到了翩翩少年时。自己年轻时,曾经那么虔诚,虔诚地学习司马相如的赋。然而,学来的本领,不仅无用,反而有害。每当想到这些,他就禁不住一阵心酸。于是,他下定决心,不再作赋了。此后,扬雄转向学术研究,他写出了一系列学术专著。仿《论语》,扬雄作《法言》,凡十三卷。仿《尔雅》而又别开生面,扬雄作《方言》,原本十五卷,今本十三卷。仿《周易》,扬雄作《太玄》,此书又称《太玄经》,凡十卷。从辞赋家到学问家,扬雄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三)宗经抑或崇道
诚如莎士比亚所言:存在抑或不存在,这就是问题之所在。(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Hamlet,III.i.57)[32]1733宗经抑或崇道,这就是理解扬雄之奥妙。扬雄的思想是在宗经与崇道这两极之间往复运动并螺旋式上升的。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扬雄是一个人物。这表现在扬雄天才地认识到辞赋这一文体必然发生变化的趋势之上。在这一方面,扬雄严格地区分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并高扬前者而抑制后者。除此之外,扬雄还有一个大动作,即写作《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扬雄《反离骚·序》云:
雄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
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8]157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扬雄的这个大动作呢?笔者以为,写作《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是扬雄革新辞赋文体的举措。它有三方面的进步意义。
其一,在《离骚》的基础上发展辞赋。《离骚》可不可以反?扬雄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可以反。扬雄《反离骚》共100句,层次分明。具体的分段和小标题如下。
第一部分一段:
1—12句,写作缘起。
第二部分,一共九段:
13—32句,缺乏远见;
33—40句,遭人嫉妒;
41—48句,霜打零落;
49—56句,不知避害;
57—64句,行动矛盾;
65—72句,不从吉占;
73—76句,自沉无益;
77—84句,心情矛盾;
85—88句,夸张失实。
第三部分一段:
89—100句,反骚理由。
扬雄在述说写作的缘起之后,针对屈原《离骚》,分九个方面逐一反之,最后讲述他何以反《离骚》的理由。扬雄写道:“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于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溷渔父之餔歠兮,洁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跖彭咸之所遗!”[8]171扬雄《反离骚》的最后十二句讲述了他反对屈原《离骚》的理据:屈原违背了圣人孔子的教导。孔子热爱自己的邦国,他既能够离去,又能够回归。孔子知道君子须因时而动,然而屈原只慕高洁而不知个人理想的实现有待于时机成熟。自沉汨罗江这一行动,虽然高洁,却违背了“明哲保身”的道理。《诗经·大雅·烝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17]302扬雄的思路是这样的。《诗经》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其中的道德教训理应得到遵循。《诗经》教导人们明哲保身,屈原却没有做到这一条,他违背了圣人的教训。鉴于以上理由,扬雄认为《离骚》可以反。
其二,在《离骚》的基础上拓展骚体赋。除了《反离骚》之外,扬雄还作有《广骚》。从标题看,扬雄作《广骚》,其目的在于发展《离骚》。中国的诗歌传统有两大源头,统称风骚。风,《国风》,代表《诗经》。骚,《离骚》,代表楚辞。扬雄之所以反《离骚》,目的在于扬《离骚》,本质在于发展中国的诗歌传统。可惜《广骚》文多不载,我们无法窥见扬雄高扬《离骚》的那一面。有趣的是,尽管朱熹对扬雄颇有微词,可是在《楚辞集注》一书中,他还是收录了扬雄的《反离骚》,将之列于《楚辞后语》卷二。须知,朱熹的审美标准是定得很高的。由此可知,扬雄《反离骚》是一篇具有高度成就的作品。
其三,在屈赋的基础上拓宽表现人类情感世界的范围。除了《反离骚》,扬雄还创作了《畔牢愁》。人的情感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屈原《离骚》较为详尽地描写了他在自我流放的途程中的悲愤心情,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屈原已经将人类的情感世界描写穷尽了。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33]137即使是“愁”这样的感情,也是述说不尽的。《反离骚·序》告诉我们,扬雄是根据屈原《惜诵》至《怀沙》部分来写作《畔牢愁》的。扬雄的创作意图非常明显,他就是要光大屈赋,发展屈赋。可惜《畔牢愁》文多不载,我们无法窥见扬雄在《畔牢愁》中对人的情感世界所作的发展式描写的那一面。
扬雄作《反离骚》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创作行为。试想,如果一部优秀作品产生之后,人们永远找不出其缺失,那么文学还能发展吗?屈原《离骚》是一部长达372句的政治抒情诗。扬雄《反离骚》,其篇幅不及屈原《离骚》的三分之一。除了开头和结尾,扬雄《反离骚》只用了76句来反《离骚》。扬雄有概括事物的高超本领,这得益于他的哲学修养。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扬雄是一个人物。扬雄的贡献在于,他建构了一个以“玄”为中心的宇宙生成模式。扬雄以玄为中心的宇宙生成模式包含五方面的内容。其一,玄就是道。《太玄经·玄图》:“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妻之道。”[34]625质言之,扬雄所云玄,就是老子所云道。扬雄将书名定为《太玄》,修饰语“太”,意谓至高(the supreme)。其二,玄是本体。《太玄经·幽攡》:“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资陶虚无而生乎规,关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开类。摛措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天日回行,刚柔接矣。还复其所,终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茔矣。”[34]619扬雄以玄为中心建构其宇宙生成论。天地人三才均由玄生出。天地人的运动和变化也由玄来加以规定。其三,息消贵贱。《太玄赋》:“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8]138扬雄认为,事物总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此消彼长,对立面之间具有统一性。其四,戒盈防满。《太玄经·从锐至事》:“锐,阳气岑以锐,……陵峥岸峭,锐极必崩也。”[34]602在此方面,扬雄与老子的观点完全一致。此外,扬雄《解嘲》亦云:
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蔵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黙,守道之極;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8]191
老子重生,扬雄亦然。始建国二年(公元10),扬雄六十三岁,在天禄阁校书。治狱使者欲逮捕扬雄。扬雄吓坏了,纵身跳楼,不过没有摔死。痊愈之后,扬雄复见召为大夫。其五,因循革化。《太玄经·玄莹》:“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34]621扬雄认为,运动发展是道的重要特征,因而他重视事物的变化发展。老子认为,道生万物,而万物复归于道。由此可见,老子陷入了循环论。扬雄则不然,他认为万物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因而世界是前进的。就此而言之,扬雄超越了老子。
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扬雄更是一个人物,他具有崇道思想。扬雄爱道、好道、崇道,这不仅丰富了道学的内涵,也拓宽了儒学的范围,增强了儒学在话语样态上的思辨性。《太玄经》以道学为主,并融合了儒学和阴阳家思想的精华,具有深刻的辩证法因素。扬雄著、司马光集注的《太玄经集注》六卷,收入正统道藏太清部。《太玄》和《法言》均作于西汉哀帝(前7—前1在位)时期,不过两书的内容各有侧重。《太玄》是纯粹的哲学著作,而《法言》侧重讲修身立命。《太玄》为道学名著,而《法言》以儒家为主,兼采道家。《太玄》的思辨性明显高于《法言》。此外,作为儒者,扬雄在生平行事方面遭受过不少非议。作为道家,扬雄未见訾议。这就是扬雄,其为人重生命,俨然一代大家;这就是扬雄,其著作立太玄,巍然一座丰碑。由此而观之,扬雄的思想底蕴主要属于道家。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说,他经历过由儒入道的转型。这是因为,扬雄的思想,其运动之轨迹,并非由宗儒家之经典,朝着崇道家之秘要,一路延伸。扬雄的思想具有很高的自由度,它总是在宗经与崇道这两极之间飞翔。然而,其飞翔的路线并非平行地往复来回,而是螺旋地上升的。扬雄的思想越飞越高,最后飞进了大思想家的畛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