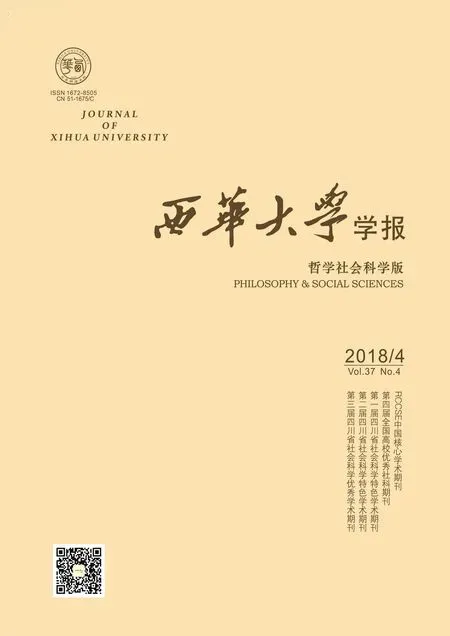叙述如何倒转:叙述媒介的时间之箭
何一杰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叙述是感受时间的方式,也是传递时间经验的方式。在实在世界的时间流逝中,受述者通过叙述文本,透过变形的时间,体验到行为世界的另一个时段,由此形成对时间的认识。“时间变成人的时间,取决于时间通过叙述形式表达的程度。”[1]叙述本身便是一个时间中的时间问题,是时间阐明自身的中介。
人们通过叙述感知且明确时间,对时间无意识的认识便必然遗存在叙述文本中。溯源至远古的壁画或者刻印文字,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文本都默认了一个“事实”:时间总是沿着一个方向流逝。叙述总是“服从”这个唯一时间方向性,即使是倒述(flashback),如《荷马史诗》《呼啸山庄》《复活》《茶花女》中出现过的一样,也不过是将时间段的先后顺序颠倒,后发生的先叙述,其中每段的时间方向依然是唯一的正向。正如艾里阿德(Mircea Eliade)在《永恒返回的神话》一书中写道的一样:“远古人的生命,虽然发生在时间里面,却不担有时间的重担,不记录时间的不可逆性;换句话说,对时间意识中最明确的特征,它完全置之不理。”[2]无论是基督教树立的线性时间观,还是佛教的因果轮回,都是先生而后死,前因而后果。叙述构建出的此种时间观与我们能在行为世界感知到的时间现象完全符合,由此在大多数的论述中,时间的方向性不是讨论的重点,甚至无可置疑。
然而,既有“覆水难收”,亦有“破镜重圆”,时间的方向在极少数的叙述文本中被倒转了,产生了倒转叙述(Reversing Narration)①。稍加考察便可发现,时间倒转的文本几乎只出现在高度成熟的人造特用媒介与经过技术改造的现成非特用媒介之中。进一步而言,在不同叙述媒介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倒转集中出现的时段截然不同:历经数千年时间发展的文字叙述,直到20世纪才零星出现了倒转叙述;而电影则不同,在卢米埃尔兄弟的时候就出现了倒放的影片;在网络文化中,音乐媒介也出现过“倒放”的文本,而音乐文本的倒放却没有使叙述倒转。出现时段的差异是媒介本身异质性的体现,都是时间的倒转,不同媒介在实现方式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异。
一、文字媒介中的倒转叙述
用文字对一个倒转的时间中的事件进行叙述,会遇到系统性的问题:很多词语(特别是动词)本身带有一个固定时间方向的解释项,这个解释项与需要描写的事件矛盾。例如,“穿衣服”的倒转不应当是“脱衣服”,因为“穿”和“脱”这两个动词都对应了日常生活中同样方向的时间;“跳下去”的倒转不应是“蹦上来”,“跳”与“蹦”分别对应了不同方向的动作。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任何一个词语、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都是对实在世界中某个对象的指涉,并且在整个符号系统中区别于其它符号。一个健全的、高效的符号系统不会将实在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的对象进行抽象,产生新的、效率极低的新符号。这便是文字叙述虽然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但也只在20世纪末才出现了系统的、持续的倒转叙述[3]的原因。
文字的倒转叙述必须有意识地避开那些为数众多的带有时间方向解释项的词语,其方法之一就是将一个带有时间方向的词语进行解释项展开,用更多的词语进行描写。举例而言,“吃饭洗碗”这一系列动作在转换成倒转叙述的时候就变成了:首先,我要把干净的盘子堆在洗碗机中,然后挑(select)一个脏盘子,从垃圾桶里找(collect)些残汤剩饭放在上面,接着歇一会儿,等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涌上(gulped up)我的嘴里,经过舌头与牙齿一番娴熟的摩擦(massage)后,我把它们弄(transfer)到盘子里,再接着,用刀叉额外雕刻一番。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是耗时费力地将食物冷却、组装、储存,然后推着购物车将这些食物一包包、一罐罐地放回超市里他们应该放的地方去[4]。
这是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91年的小说《时间之箭》(Times Arrow)中的一段描写,作者将“吃”这个动作展开到足够的程度,写出了足够让读者疑惑的情节,逼迫读者解释为时间的逆转。实际上,艾米斯的这部小说完全使用倒转叙述进行构造,通过部分离奇的描写后,读者便能够领会倒转叙述的意图。
用文字进行的倒转叙述总是承受着文本的解释压力,去掉原来带有时间方向的词语或者使其成为比喻。如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回归种子》中描写的:“蜡烛慢慢长大,烛油不见了,当他们恢复到原来的大小时,修女移走了一盏灯,吹灭了其他蜡烛。烛芯慢慢变白,又长了出来。”[5]或者阎连科《日光流年》中的描写:“家里的抽屉桌越来越高,高到了司马蓝举起胳膊还拿不下来桌上的油瓶儿。水缸越来越粗,搬一张凳子放在缸下去舀水,掉进去就可以游泳了。时间叮叮当当地飞快着,日头有时从东边出来,又朝东边落去。”[6]读者感受到文本与时间之间,经过了两次符号衍义:日常词语——行为对象;行为对象(作为修辞的喻体)——倒转的行为(本体)。这种双重间隔既产生了诗意,又让形式本身充满了反讽的意味,迫使读者不断体会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文字能够进行倒转叙述,因为文字是足够成熟和发达的符号表意系统,“任何一个语言单位,总是在与人、与社会、与语境、与语言结构自身、与其他异质符号的关联中定义自身的”[7]。文字通过语言修辞与伴随文本,突破了自身的局限。
二、影像媒介中的倒转叙述
影像具有文字难以达到的直观性,而在倒转叙述中,影像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用文字符号来解释时间的方向性。影像本身就明示出了时间的方向性,因此在用影像进行倒转叙述时,只需要对本身携带时间方向的影像(非静态的)进行操作,观众就能直观地感受到时间的倒转。
影像可以是静止的,如照片、绘画,也可以是动态的,如电影、动画。静止的影像只对应一个时刻,是零时段的。对于这种“零时段文本”,需要文本接收者进行时段延展[8],而一张图片,如果它没有明确标示出一个时间方向,那么接收者必定按照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进行解释。例如:即将洒出的咖啡的图片,在没有任何文本注释的情况下,很难被理解为“溅起的咖啡会回到咖啡杯里”(见图1);跳下跳台的运动员,即使呈现出了数个清晰的瞬间,也难被看做“飞上跳台”(见图2)。

图1 高速摄影:咖啡

图2 频闪摄影:跳水运动员
静止的图像难以进行倒转叙述,它同文字一样,是记录类的非特用媒介。静止图像的时间方向性依赖于解释者进行时段延展的行为中,没有如文字一般可供展开的带有时间方向性的解释项。不作说明,解释便是约定俗成的。静止图像的修辞难以准确明示出时间倒转的意义,只有借助文字才能让图像时段的解释逆行。
动态影像则完全不同。电影放映员一次失误导致的胶卷倒放,便让观众见识了废墟复原的“奇迹”②。电影的每一帧固定了一个时刻,电影的放映规定了时刻的先后顺序,而倒放,哪怕只是一场事故,都轻而易举地改变了这个顺序。
用动态影像呈现时间倒转的例子非常多,最著名的便是捷克导演奥德里奇·利普斯基(Old rˇich Lipský)1967年的作品《快乐的结局》(Happy End)。这部电影旁白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刑场上出生的成年人,将他已被肢解的妻子组装起来,并屡次摆脱妻子的追求,和自己的前任生活在了一起。然而一开始字幕便打出“剧终”,以及电影画面中完全异常的现象很快让人明白故事情节是:一个丈夫发现妻子有了外遇,杀掉了妻子并将其肢解,随后丈夫被判处死刑。在这部电影中,画面、音乐、对白、旁白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观众从画面的时光倒转中直观的杀妻故事与旁白叙述的找回真爱的故事完全相反,使得影片“超出我们对喜剧的理解,认识到其中的反讽”[3]。
这部电影通过动态影像的倒转叙述,再现了前文提到的数个其它媒介中的例子。例如:男女两人一边调情,一边从嘴巴里“吐出”一块块完整的甜点;水面上水花不断变小,最后从水里飞出一个人,落在了码头上。事实上,在笔者数次查阅这部影像资料的时候,任何一个暂停的画面都没有产生异样感——胶卷上的每一帧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而一旦按照导演规定的方向运动起来,就产生了这个奇特的叙述。动态影像对时刻顺序的简单控制能强烈影响受述者对时间方向的感知,这是其他媒介难以达到的。
三、音乐叙述中的“伪倒转”
音乐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十分复杂,以至于音乐如何叙述,甚至音乐是否能够叙述至今仍然存有争论。从广义叙述学的角度看,音乐叙述被理解出的时间和意义向度都没有明确的标准。曾有人给未曾接触过西方音乐的中国农民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乐曲的主题被理解为“鬼子进村”,副主题被理解为了“八路军战士掩护群众安全转移”[9]。显然,没有人能说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任何解释都是解释”[10],评判解释就是至少两个文化系统产生冲突。音乐叙述的多样性和模糊性使音乐文本本身必须提供足够明确的指示才能使得被叙述时间倒转,而明确的指示又难以融入音乐(而不是其伴随文本)的多样性和模糊性之中,音乐文本的倒转叙述实际上是一种“伪倒转”。
从音乐文本本身来看,倒转变换原本就是作曲的一种方式,例如,音阶的上行变成下行,动机乐句的变形处理,或者更大范围的蟹行卡农等等。音乐文本倒转之后与原文本差异很大,例如下面这个乐句:

这是法国歌曲《妈妈请听我说》(Ah!vousdiraije,maman)的开头,乐谱中只不过将每一个音倒着写了出来,这段众所周知的旋律就变得十分陌生了。音乐的回文曲与文学中的回文诗一样,是一种文本构成的技巧,其所形成的叙述,在音乐体裁中没有形成时间倒转的解释压力,也就无法形成倒转叙述。
电影《莫扎特传》中,年轻的莫扎特能够倒着说出一句话:“Say I’m sick”或者“Eem-iram”(marry me的倒转)。这是用声音的形式重现了《时间之箭》中的第一段对话。对已有声音文本进行的倒转,并不能成为倒转叙述。标示主要来自影像,而且音乐经过倒转过后,并没有将原来叙述的内容倒转,而是变成了一个需要另行解释的新文本。当这个新文本没有任何的说明时,其与原文本的关系可能会完全断裂。
音乐并非不可能进行倒转叙述,任何音乐都可以理解为某种情节的倒转。只不过,如果这种叙述希望得到阐释社群的认可,所需的伴随文本注释量将远超过与之类似的静态影像,甚至,音乐只能成为倒转叙述的伴随文本:为一段倒转的影片加上米老鼠步般的配乐后,音乐便能够描述一段倒转的时间了。
四、叙述媒介与方向时素
在以上列举的几种媒介中,只有文字和动态影像凭借媒介自身的特质实现了倒转叙述。静态影像和音乐需要依靠伴随文本,而这些伴随文本无非又是文字或者动态影像。同时,文字和动态影像在倒转叙述的实现上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文字借助人的抽象思维塑造了倒转的时间观,而动态影像则依赖直观体验。分析这诸种的异同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什么确定了叙述时间的方向?
叙述文本用“时素”(chronym)来标记被叙述时间[11],而无论是“明确时素”还是“伪时素”,都是对被叙述时间的方位标记——从某个点开始,在某个点结束,或者处于某个时段。本文认为,除了这种“方位时素”外,还应该有“方向时素”,在前者确定的时间点上,规定了叙述行为时间的方向,方向时素就是至少两个时刻的先后关系。
文字的方向时素不均匀地分布在不同类型词汇的对象之中。在上文列举的《时间之箭》的例子中,“堆”“挑”“找”“涌”“摩擦”“弄”“雕刻”“放”等动词都暗含着时间的方向:“堆”“涌”意味着由少变多,“挑”“找”意味着由未知变为可用或不可用。这些动词描绘出的动作代替了原本“拿”“扔”“咽”“切”应描绘的动作,文字呈现的不是这些动作的反向,而是一个与反向类似的动作,并且动作出现在时间轴上的先后顺序相反。
数个文字符号映射着数个共同的时间方向,这些单个的映射前后一致,即A对应的时间在B对应的时间之前,那么文本中A在B之前(咀嚼对应的行为动作在吞咽之前,那么咀嚼在文本中的位置在吞咽之前)。前后一致,没有矛盾的,便形成了正向的叙述;如果交叉对应,与被叙述时间出现矛盾,文本便在时间方向上出错,但错误的文本也需要解释,这种解释便由叙述倒转接手。所以,在文字媒介的倒转叙述中,文字文本所呈现出的实际上不是真实的倒转时间,而是荒唐的时间,是胡言乱语的时间,迫使受述者用时间倒转来解释。
静态影像媒介的方向时素则不是映射出文本的,而是投射进文本的。就静态影像而言,一幅照片就是一个时刻,或者是多个混合在一起的时刻。照片文本无法提供方向时素,于是解释者在解释的规范中找到了符合此类文本需求的方向时素。例如,上文中的咖啡照片,咖啡是溅出还是回到杯中没有在图片中说明,只是我们根据行为的经验提供了一个解释的规范——咖啡必然溅到桌子上。同样的道理,混合多个时刻的频闪照片也没有提供这些时刻的先后排序,它甚至连时刻的邻接性都没有提供。解释者曾经观看跳水的经验告诉他,这个图片的“正确”阅读方式是从右向左,从上到下,如此才能感受到一个起跳动作的完整叙述。
方向时素投射进文本同样是音乐媒介的特点。不同的是,静态影像投向的是一个未知其时间方向的时刻,而音乐投向的是时段。这段时间不仅方向未知,而且位置和长度都未知。于是在解释音乐文本的时候,我们需要时间方向的指示,同样还需要时间位置、人物与情节的指示。音乐文本只能通过结构和元素的变换提供模棱两可的“建议”,大部分叙述都出现在伴随文本中。
最后,在动态影像媒介中,文本本身携带方向时素。动态影像是在静态影像的基础上加入了对时刻关系的控制,两个不同时刻的先后顺序被固定下来,由此形成时间的方向。媒介化是意义符号化的前提[12],文本的倒转会导致方向时素的倒转,这也解释了文字与动态影像出现倒转叙述时间差异的原因:文字媒介的倒转叙述是在文本形成过程之中构建的,而动态影像则是对现成文本的操作;文字媒介需要作者运用精巧的结构和比喻来引导受述者,而动态影像需要的仅仅是技术的成熟。
五、叙述行为与时间观念
在文字、动态影像、静态影像、音乐这四种媒介中,时素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面:对象、文本与解释规范。就方向时素而言,文字的时间方向是对象的映射,动态影像的时间方向在文本中确定,静态影像和音乐的时间方向由解释规范投射进文本。而就方位时素而言,“纪年时素”由文本提供,“形象时素”则来自解释者对这种形象元素所在时段的观念。这三个层面对应着保罗·利科对叙述行为的三个分类。
利科在《叙述与时间》中构建了叙述与人类时间观的联系,通过叙述的三层模仿行为,即:“涉及到行为世界的‘前理解’结构、被意义结构、象征系统与时间特征所覆盖的模仿行动Ⅰ;处于行为世界与虚构之间,具有中介功能的模仿行动Ⅱ;标示了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真实行动发生的世界)之交叉关联的模仿行动Ⅲ。”[13]处于模仿行动Ⅰ中的时间是第一性的,它是时间的品质,是对象的时间,我们只能隐隐约约感受到其存在,“它们自身只是诸种‘可能’”[14];而第二性的时间是叙述行为II中的时间,通过叙述文本的选择与控制,时间“实在”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经验面前,是文本的时间;而第三性的时间是叙述行为III中的时间,它成为一种规律,因果关系般的存在而被我们经由叙述行为把握,是经验的时间。
从时间的方向性来看,实在世界的时间与我们通过叙述文本建立起的时间经验之间,Ⅰ、Ⅲ的时间方向总是一致的,倒转叙述在II行为中可以将时间逆行,但这不过是加固了实在世界的第一性时间和观念时间的联系,为观念的时间添加了反讽和诗意。而若某个可能世界,时间真实逆流,所有的箭头都指向左侧,这个关系也依然存在。即使我们通过实在世界的倒转叙述文本认识到这样一个可能世界的存在,即I和II的时间都是倒转的,那么正向的Ⅲ也不与Ⅰ相关,因为我们通过可能世界认识到的是可能世界的Ⅲ,Ⅰ与Ⅲ的方向关系并没有变动。
叙述行为II中呈现出第二性的时间,是被选择过后的时间。选择最初由作者主导,作者在创作文本的时候决定了何时发生、何处发生、如何发生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对时间进行拉伸、压缩或者重组。一旦选择完成,时素也就固定下来了,读者只能认为这是一种可知的时素或者不可知的时素。
到了现代诸叙述文本中,时素的选择权一部分交给了读者。比如在游戏文本中,玩家可以选择游戏的时代背景,角色的衣着服饰,甚至可以让古代人穿着现代的服装;游戏可以有存档,可以有不同的结局,不同的玩法。电影游戏化,有了如《罗拉快跑》一般的可能时间模式。小说也给予了读者选择的权利,例如马克·萨波塔(Marc Saporta)实验性的小说《作品1号》(Composition No.1)以不固定章节先后的方式,让读者来安排事情的先后顺序。时素与时间构成从作者可选转移到了文本可选,而时素的选择也由方位时素的可选拓展到方向时素的可选。
在现有虚拟现实的观影环境中,观众代替导演控制了部分镜头的运动,在情节发生时,观众可以选择不让画面出现在自己的视线中;而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尚未出现的媒介,其使用者可以改变该媒介叙述的时间长短,由数个小时变成几分钟——现在这种变化由不同的媒介完成,比如文字简介、海报与电影原文;而由游戏延伸而来的互动关系,则在正反两个方向的时间中进行,比如经由倒转的时间寻找线索,连接因果关系等等。叙述行为II的时间变为可正、可逆、可选、可控的状态,时间位置因素的选择与位置之间关系的选择不再固定。这种新的叙述方式将如何更新人们的时间观,现在还不得而知,但经由现代媒介制造的碎片化的时间观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猜测,这种在时间中全浸的、双向的体验或许会引起一场新的时间变革。
文字叙述经过数千年的演化发展,到20世纪才系统出现了倒转叙述。静态影像、音乐发展到现在,还不能独立进行倒转叙述。然而我们不能否定的是,这些媒介在未来发展进程中,能够不断更新叙述的可能,产生新的叙述方式,带来新的时间观念。叙述分析不仅仅针对经典文本,针对单纯的文本现象,更是面向我们所处的世界,所在的文化。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的是,叙述研究以“人类全域叙述的开阔视野为参照系”[15],不讨论技术的可能性,而讨论人本身的可能性,讨论人在所有可能的技术条件下能够构建的思维体系和文化系统。由此观之,下一个麦克卢汉式的预言,很可能不是来自互联网技术圈或者媒体从业者,而同样是来自文字与诗歌之中。
注释:
① 关于倒转叙述的定义,参见笔者《时光逆流:音乐电视及电影中的倒转叙述》一文,载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第72页到77页。
② 早期的这种叙述时间的倒转并没有用来连接一个保罗·利科意义上的经验时间,而是作为电影特技使用——观众经验到的时间依然是正向的,由此产生惊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