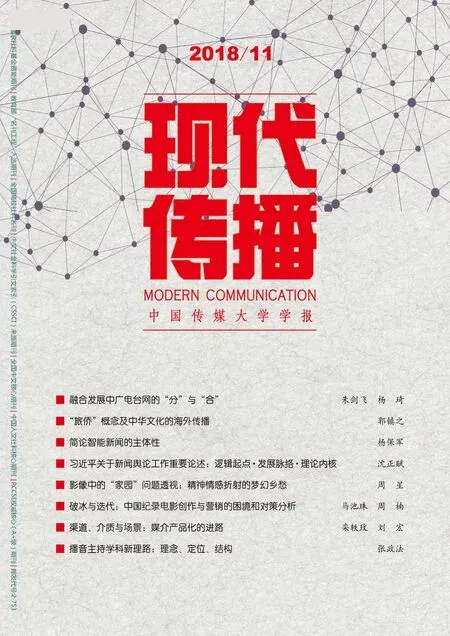论“后情感社会”真人秀节目的情感规则、偏误与调适*
■ 晏 青
一、问题的提出
情感是一种关于个人感情状态的复杂的心理经历,是内在生理机制与外在环境刺激共同作用的结果。柏拉图倡言公民泯灭情感,在节制中实现理想国的愿望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孔德、涂尔干、韦伯、齐美尔等对情感问题的讨论,揭橥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情感曾经沦为“剩余范畴”而被忽视。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兴起的“情感研究的革命”,从大脑结构研究到基因图谱的绘制,从情感机制到微表情(micro-expressions)的表情技术,都试图研究在现代性背景下的情感问题,直到现在仍方兴未艾,成为反观人与社会的重要议题,在社会学领域因此还形成“情感的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霍克希尔在1983年出版的《情感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标志着情感社会学的成熟。①Patricia Clough和Jean Halley在《情感转向》一书中提出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正在经历“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②情感成为各个领域实践规范的一种重要视角,自此出现从多个维度切入该问题的研究。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在《情感地缘政治学》一书从情感地缘政治学角度切入,指出21世纪是“意识形态的世纪”和“身份的世纪”,“全球化导致的身份问题,为情感的繁荣甚至急速扩张提供了基础”③,这为现代社会情感形态考察提供了新视点。无独有偶,社会学者梅斯特罗维奇(Stjepan G.Metrovic)在《后情感社会》提出“后情感主义”概念,用以反思只关注人类主体的知识和技能而忽视人类赖以生存的情感,他认为“西方社会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合成的、构拟的情感成了被自我、他者和作为整体文化工业普遍操作的基础”④,断言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后情感社会。后情感社会不是指情感的消失或终结,而是指情感的社会性转化,情感生活机械化、可操纵化,它“更为准确地捕捉到了当前混乱、伪善、歇斯底里、情旧、反讽、悖谬,以及其他在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中凡事都过分地用情感来渲染的状态”⑤。“后情感主义”范式为理解当代情感提供政治、社会视域。
在消费社会无远弗届的今天,传媒产品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孕育情感。瑞典学者阿维森(Adam Arvidsson)指出,“生产”一般当作工资劳动,“消费” 则包含再生产、娱乐休闲和超越了工资关系的各种享乐活动。消费总是被当作生产的对立物,是一个价值被耗尽或摧毁的场域。在他看来,消费实际上是一种创造认同、社群和共享的意义体系等非物质性使用价值的生产实践。⑥美国学者哈特(Michael Hardt)甚至认为,娱乐工业和各种文化工业的焦点都是创造和操纵情感(affects)。⑦其中明星体制(Star system)就是吸引受众对明星进行情感投入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传媒娱乐工业中的一个基本营销策略。⑧对此,詹金斯甚至在《融合文化》一书中提出“情感经济”(affective economic)的概念,用以强调情感在受众在观看选择和决策行为中的作用。⑨在情感经济中,广告商和电视网全面调动受众的参与和投入。情感经常被认作是媒体娱乐的中心,不管这种媒体是电影、小说、电视节目、音乐,或者电脑游戏等形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大众媒介采集、重新语境化和压缩的信息与情感,与受众建立起联系。“通过‘全球性的’传播技术传来的媒介化了的情感挑逗,可能被看做远比本地的、未媒介化的感情更为紧张刺激。”⑩
在大众传播意义体系中,从规制和表征到控制和信息,情感已然成为观念生产、内容建构的重要维度,并在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博弈中进行调适与再生产,“许多看似个体的感受其实既跟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强化的相互依赖和交互影响有关,也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发展所致”,情感的传播“直接将个体贯通于社会整体氛围”。
具体而言,传播学研究主要关注这几个层面:一是作为媒介要素或内容的情感,关注大众媒介中情感如何被呈现、谈论,包括从视觉上对情绪的微观剖析,以及注重情感的社会隐喻、委婉语意义的讨论。二是作为方法的情感,情感是舆论、谣言的传播效果达成的重要使用方法。比如情感共振、情感共鸣是群体性事件的情感动员机制,诸如愤怒、同情、戏谑等情感是集体动员的催化剂。
在这样的语境和功能影响下,情感生产与传播成为现代娱乐的生产与意识形态传播形式。从新世纪初广东电视台播出国内第一档真人秀节目《生存大挑战》到现在,尤其在消费主义、娱乐文化的刺激下,真人秀节目“质”和“量”都有很大提升,成为观众重要的娱乐体验之源。除契合时代精神外,议题营造、微观设计也是此类节目获得高收视率的重要原因。其中,情感叙事便是真人秀节目的符号呈现、整体架构和价值引导的重要元素。真人秀的情感呈现与叙事成为现代受众情感宣泄、谈论社会现实的途径。情感是真人秀的核心元素,甚至有创作者认为“所有真人秀做到最后都是情感节目”。在劝服实践过程中,情感往往通过影响认知反应,对态度的变化起中介作用。情感成为真人秀节目创作、意义生产与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尤其应对国家政策提出的传播“正能量”准则下,在有限度的娱乐和价值增量之间的平衡过程下,需要以情感为中介,在移情作用下实现节目艺术发展。可以说,忽视真人秀情感叙事形式与策略,就意味着忽视现代娱乐节目意义的丰满性与可能性。
因此,基于情感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以真人秀节目为例,讨论情感在现代社会的状况与发展,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1)社会学家阿里·霍克希尔德(Aalie Hochschild)认为文化和亚文化有其特有的“情感规则”。在不同的情境中要有不同的情感模式,并随之调整自我情感管理或具体感情表达方式的控制。那么真人秀节目在富有公共性领域中为受众呈现及讲述了怎样的情感规则?(2)在受众与媒介的主客体二元关系模式中,真人秀节目如何修正或调适情感的现代编码,促进现代娱乐节目的情感符号转向社会化实践?
二、公共空间中的情感形态
尤尔根·哈贝马斯讨论了文学期刊、沙龙等公共领域如何孕育着当代意义上的政治讨论的最初形态,他提出的“公共领域模型”为我们考察媒介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分析框架。英美国家的相关研究通常忽略公共领域由两个部分组成: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它们通过不同的体裁(genres)强调不同的议程。前者通过事实体裁(factual genres)表达政治和经济的“集体”事物,后者主要通过传统文学、电视、电影作品等表达文化和艺术的“个体化”事物。例如,情感调解类的真人秀节目,议题分布在婚姻危机、经济纠纷、子女抚育、老人赡养等,俨然是开放性媒介公共领域中的家庭政治。以情感为话题的议题讨论,不仅涉及到资源的配给、义务的承担、观念的碰撞,背后指向作为个体幸福和作为主体的尊严,还关涉着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有着强烈的公共性。
情感常被视为单一装置或者单一类型的情感(例如情绪、欲望或注意力),其组织和结果的多重性不被承认,在很多研究中,情感被认为非建构的,无组织的。理性主义范式把情感排斥在外。麦圭根(McGuigan)就在讨论文化公共领域指出,公共领域的研究倾向于关注认知层面,忽略或者轻视情感性的传播。但是在文化公共领域中,公众对议题的讨论则常常是以审美的和情感的方式。并且情感能够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元素。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文化研究的未来》一书中认为情感的话语维度,即一种表达制度,它们调动和组织情感作为习性、生活和想象,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话语结构。并且强调“情感状态和感觉制度的生产从来都不是随机的”,“情感通过多种机制和形式运行,产生许多不同的方式和组织,包括感情、情绪、欲望、归属感、感觉结构、物质地图、意义地图(意指),以及表征系统(或意识形态,作为声称代表世界的特殊意指的情感投入)”。
情感多维视点和意识形态是理解公共领域中的真人秀节目运作的支点。将真人秀节目视为公共空间平台的原因如下:一方面电视媒介本身具有公共性,真人秀节目存在对话交流的空间,形成各种议题。比如《中国达人秀》就涉及家庭、教育、健康、儿童等话题,这些话题就是在评委、观众、选手等节目主体讨论中生成或呈现。另一方面,真人秀的低门槛性容易向大众敞开,最大限度调动平民参与讨论。重要的是,人们乐于在这些娱乐节目上讨论公共话题,并且乐于相信这种娱乐形式。另外,真人秀节目的假定情境与规则,使得所建构的协商对话远比“日常生活中纯粹社交性质的交谈更为正式,受到特定规则的制约,而且具有公共性的属性”。
从不同的考察视角可以窥见真人秀节目的情感形态多样性。从节目构成来看有这样几种叙事形态,一是以情感作为整个节目的结构,包括节目策划、选题、拍摄与后期制作都将核心定于情感,情感是节目的底色。《爸爸去哪儿》之父子情、《情感密室》之夫妻情、《非诚勿扰》之男女情等。节目主要围绕这些情感进行整体性叙事。另一种是情感作为元素。节目以其他主题为主,但情感在节目衔接中不可或缺。比如《挑战不可能》中穿插的爱国之情、亲情平衡了节目的娱乐性。节目叙事利用多种手段调动感官,运用蒙太奇手法让叙事能够更自由地在时间和逻辑顺序两个维度转换,实现灵活多变的叙事图景。这种转换体现在镶嵌式叙事中形成的多线性叙事。在展开情感讲述时,插入一段视频或互动,将情感叙事插入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序列,产生内容多层化、审美多样化等效果。据笔者统计,《非诚勿扰》2017年共嵌入了262个情感故事、《朗读者》第一季嵌入108个朗读者故事。这些情感叙事形成了与各个主题平行或交叉的多线性叙事。
娱乐节目有一套讲叙情感的视觉技术。“娱乐艺术的构造精巧得好像一件工程技术品,而创作过程的配制则复杂得好像一瓶医药的成分,它的目的在于生产确定的、预期的效果,以及在某种观众身上唤起某种情感,并在一种虚拟的范围之内释放这种情感。”19世纪以来,视觉的主导话语和实践有效地打破了视觉机制的古典王国的束缚,改变了现代知觉结构,并成就了视觉规训王国。视觉叙事是一种区别于文本叙事的话语模式。真人秀节目的情感叙事,根植于创作者的文化背景、情感深度、艺术造诣,其文本呈现在事件的择取、沟通方式、光影构成、景别、景深,以及镜头之间的组接和影片的整体结构等方面,一个好的叙事策略往往通过节目的铺陈烘托将情感具象化、细节化和结构化,实现产品生产、价值引导与公共议题的讨论。
不过由于市场竞争引发收视率狂潮,真人秀因过度娱乐化而出现“三俗”现象、虚假宣传、自编自演等负面现象影响观众的精神生活,与主流价值脱嵌,弱化真善美的主流价值的公信力。传播的市场驱动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平衡成为不同国家和文化语境下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作为当代最具娱乐精神的代表性传媒产品,真人秀节目避免媚俗化、庸俗化、私密化成为考察其与主流价值、社会议题互动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国家出台系列措施对此进行调控。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等政策,对真人秀节目的播出时长、时段和数量等做出明确规定。广电总局的数次调控,都给真人秀节目生产上了“紧箍咒”。不少节目为规避风险,在内容生产与播出环节设置契合“安全法则”的内容生产机制。真人秀过度娱乐化现象有所遏止,很多节目探索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节目形式,节目的人文主义意识更强。越来越多的节目关注人性及人性化的传播。真人秀的这种人性化转向是市场逻辑与文化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娱乐话语重组和传播路径的二次调整。所以可以看到,情感的话语框架接合了很多社会意义和价值。《爸爸去哪儿》的结构性框架里设定父子矛盾与成长历程,将亲子教育、文化培养等主题推向观众。《非诚勿扰》由“宁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的婚恋观转向现代婚姻观的引导,将爱情限定在正确价值观的轨道上。《中国好声音》中导师与歌手的“师徒之情”、歌手之间的“友情”,将歌手“一举成名”的功利追求转化为对青春和理想的追求,同时辅之以亲情、友情、爱情等主题,将其营造为主流价值的仪式现场。
除了国家政策规制,情感还是人性当中感性、基础的一个维度,选其作为重要色调,不但吻合真人秀的本体特征,也基于人性。尽管情感叙事出现过度利用和叙事偏差的现象,但是情感叙事成为一些真人秀节目的重要节点,甚至结构性框架。情感既是一种生理唤醒也涉及认知评价,涉及对价值观的辨识、涵化与构建。比如《中国梦想秀》重梦想、奋斗,《天使在行为》重爱心等主流价值。注重理想、奋斗、爱心等主流价值使得这些节目的公益传播的价值输出能力大大提升。情感就这样以“软手段”切入主流价值观的认知和传播。社会活动中的分散的物理空间实时相连,本地情境融入交流与交互的全球化循环。一切社会交往的基本构成皆以技术为中介或技术嵌入的内容。所以,新媒介建构的交往模式下的社会领域(商业)和私人空间(家庭)或私人情感的界线趋于模糊,在这种认知更新和重新构建的过程中,情感也由隐私到公开。自古中国人的情感是一座“秘密花园”,埋伏于心或以隐喻方式作曲折性表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私人生活公开化,公共生活私人化,因为私人和公共这两个集合是历史的设置,本来就是多变的、流动的,是互相沟通的,而不是封闭世界。电视关注个体的现实经历,通过假定更平等的供求,尝试建立情绪共享的社区。
大众传媒为情感的呈现、互动与建构提供了平台。作为一种节目资源,情感很快就成为了真人秀节目编码重要的符码,围绕它的画面设计、人物对白、事件营销等崛起为构筑市场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构件。情感叙事成为公共事件,供全民凝视、谈论和娱乐。情感的私密性被打破,它成为一种可供大众传媒“享用”的人性资源:作为一种饱含人文主义的文化底色,它是传媒产品的重要构件;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成为媒介功能、主流价值的合法性佐证。私人化的情感进入真人秀节目的公共空间,经过节目本身的多维交流、讨论,或者在国家政策、主流价值观念的规约下,情感的形态有所变化,体现在情感的话语过滤、认同与形塑。
三、情感话语偏误及调适
真人秀节目成为现代观众的情感触发器,也成为主流价值传播与建构的重要阈口。但是从作为平台的电视媒介、人性的精神表达的视角来看,情感的媒介话语需要克服或调适内部逻辑或外在制度设计的缺陷,实现情感的社会价值。
1.情感话语偏误
首先,从媒介属性来看,大众传媒内在逻辑削弱情感叙事强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认为传播具有持续文化(time-in culture)和停滞文化(time-out culture)的二元性,它时而产生于反思的瞬间,时而产生于行动的瞬间。“无论是对于专业知识与俗民理论,或是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而言,传播均思考其结构,并预测行为。不同的媒介与体裁则使得不同形式的思考与行动成为可能。”
一般来说,电视被认为不适合传播深度知识,因为电视符号系统线性的“流传播”,不利“反刍”知识、沉淀思想。节目播出严格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各种信息层层覆盖。情感在这种线性结构的意义生产机制与咀嚼、反思的内在节奏不契合。更重要的是,广告、新闻、电视剧、娱乐节目等节目风格迥异节目,每个真人秀节目的情感铺垫和弥漫因线性安排结束时情感体验戛然而止。正如波兹曼所描绘的:“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新闻播音员说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马上从我们的脑海中消失。”节目中被激发的“感动”或“美好”情感,在资本时间规划和统筹的流程中覆盖,成为没有经过主体沉淀、反思性的瞬间体验。除大众传媒系统的这种异质性因素外,真人秀节目本身就是娱乐节目,那么情感生产注定只是“死亡唇边的笑”。例如,在展现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之后,选手泪眼婆娑、嘉宾动容,而几帧画面后,这些情感叙事瞬间又被“秀”“邀请”到娱乐的狂欢系统。故事性、人文性等因素在作为基础性配置的娱乐话语面前无法全面铺开或独挡一面。从节目外部环境看,不同广告此时作为情感的异质话语嵌入,比如60—120秒时长的广告内容,诸如洗车、网游、电子产品等广告或赞助商品,皆可谓是大众传媒内在缝合的认知裂缝对情感呈现的反讽。大众传媒本身的结构性特征与真人秀节目的本体底色,使得情感叙事循环播放,同时又在这种循环中完成自我的消解。
其次,从发生机制上看,情感叙事的生产机制不完善,“刺激—反应”生产模式过度运用。这就造成这样几个特征:一是情感的预设性。选手的成长故事、嘉宾之间矛盾设置等,这些都让情感成为一种预设在那里的,不管是情之所至,还是无法动容,到了节目某个环节,就需要大家把情感调动起来,而后不断漫射出去。二是情感的表演性。因为情境和感受的错位,情感并不能招之即来,情感表现显得很生硬。比如《中国好声音》中歌手唱歌前后,主持人用类似“你感动吗”的语言问及对方感受,将歌手裹挟到这种预设的情感叙事框架。《中国梦想秀》出现的情感绑架。在这种简单的“刺激—反应”下,情感叙事显得生硬、粗暴,情感的直接经验的丧失也导致现实感和确切感的丧失。
所以我们看到,节目演播厅或户外场景是精心布置的,音乐是专业筛选的,选手台词是被反复打磨的,程序是百般推敲的。在现场灯光、音响等现场氛围和主持人引导的种种情感“异质”:催化性、预设性和无主体性。资本逻辑与技术程序下的情感成为一种“类情感”。随着人的劳动被货币数量化,人的观念、情感、知识也开始被货币数量化。
再次,从外在作用机制来看,这种异化还表现在资本逻辑的情感规训或规划。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产业化和市场化会影响情感生产,前者改变了劳动过程中的情感意义,后者改变了意义赋予和价值认定方式。异化主要体现在真人秀情感生产程序上。即对“真”的夸张式“秀”。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大面积渗透资本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领域是无处不在的。马尔库塞指出,后工业时代,异化以更为隐蔽、更温柔的手段进行。因为很多开始“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与满足”。文化的人性化目标被物欲化目标所取代,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摆脱资本的规定性。
严格来讲,资本逻辑催产、预设的情感,是一种情境再造中的非客观,不具备自主性、反思性的情感。“人已经完全远离了自己的生命创造性本质,人与其对象的积极的创造性关系由此而丧失殆尽。”基于生理反应的情感,在节目中成为符号编程、规划设定的程序化的情感,异化为无主体的流水线情感。“情感体制”这一概念很好地概括这点,即“一套规范的情感以及表达和灌输它们的正规仪式、实践和述情话语(emotives)”,情感体制涉及情感的养成和表达,符合一定的规则,并通过一定的仪式和实践予以强化。而“情感中的道德、宗教乃至社会意涵,日渐遭到剥离,剩下的只是短暂的个体情绪”。很显然,囿于商业体制下的短暂个体情绪并非节目的终极目标。
其中,明星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讲,明星身体是一种消费资源,公共效应决定明星的商业价值。原本属于私密空间的情感,因为明星本身属性以及资本逻辑的影响,成为公共领域的景观。明星的情感是一种基于品牌的生产链延伸、资本再生产的过程。平民情感也被“献祭”。大众情感是消费社会逻辑使然。尤其真人秀聚拢了在社会阶层中占据最大比重的社会成员。节目对普通人话语权的象征性肯定,满足受众从“明星”的仰望者转变为“民星”的制造者的心理需求,带动其深度卷入节目。在注意力技术下,平民的情感这座原本不被关注的荒岛被投以聚光灯,成为大众反观自我、娱乐漩涡的场域。尤其在媒体融合的趋势下,情感的公共叙事的转变,成为现代大众信息传播开放性、多节点的内容,汇入大众传播渠道,经过转发、评论等行为成为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成为公共视野下的一场“盛宴”、情感狂欢中的一种体验强化策略。
优化营销渠道,尽量采用直营模式、减少加盟模式,或者力争实现直营模式与其他合作快递公司合作模式的完美结合,实现战术4Ps中的渠道策略与4Cs中的便利策略、4Rs中的反应策略相结合。对于实力雄厚的快递公司而言,可以采用直营模式,即不通过中间商,直接将消费者的快递在消费者要求的时间内送达指定地点并实现按不同服务产品进行分类收费。此类快递企业对渠道的控制力很强,可尽最大可能地实现消费者的便利性(4Cs中的便利策略),且一旦出现快递问题可及时处理和消除(4Rs中的反应策略)。对于有些地区不能到达的快递企业,可以采用与其他快递企业进行签合同合作的方式解决。
综上,媒介属性、发生机制与外在作用机制这三个从内容生产到接受链中的情感偏误容易造成情感能指与所指的偏离。欧内·拉克劳提出“漂浮的能指”揭示符号与意义的不稳定性和易变性。不管是“表情帝”“哭泣女”这类观众反应,还是歌手的“瞬间泪下”,嘉宾“频频哽咽”,都没有找到具体所指的意义承接,从而让情感叙事落空,成为所指的飘浮。能指与所指的随意性编码体现为:情感调解类节目存在以揭露当事人私密情感为能事的现象,整个结构围绕窥探私密而设置;才艺歌手类节目中歌手多次泪洒现场,嘉宾摇头晃脑认可,观众泪流不止等,这些叙事都可以说是一种能指与所指的偏离,一味刺激的满足视觉和娱乐效果,造成无实际意义的“空叙事”。对此,鲍德里亚就认为消费逻辑渐渐卷入这样一种状态:“能指” 已经丧失了与“所指” 之间的确切关联,并成为一种“自由的” 和“被解放了的”“能指”,成为“对符号进行操纵的系统性的行为”。因此“这种新的技术不但没有成为解放大众的技术创新,反而带来欺骗和控制”,“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创新,并没有成为文化创新的利器,反而成为遏制文化创新的工具”。
有观点认为受众可以规避商业和权力规训,从而避免真人秀节目的情感生产的上述弊端,其最重要的理论观点支撑是观众具有积极接受、富有意义生产力的一面。阿尔文·托夫勒提出“生产消费者”(prosumer)的概念,描述生产者与消费者角色的糅合。费斯克也认为受众能够做出自己的解读,并进行象征性地抵抗。实际上,这种观点实现的基础是受众拥有很高的媒介素养,尤其在信息冗杂、利益诉求编织越来越精巧的情况下。所以,积极有效抵御资本与权力的影响,仍然是传媒消费中有待商榷的议题。
2.传播系统中情感话语的调适
社会学者成伯清聚焦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工作、消费和交往三个核心领域,提出整饰体制、体验体制、表演体制等三种情感体制,认为“情感体制以相应的方式强化合乎规范的情感,排除与之不符的情感”。摄影、电影等大众媒介的审查机制与资本诉求等营建起一道严密的过滤网,把过于个人化、“私情感”内容过滤掉,或转换成“共情”,从而高度个人化的情感在种种整合机制糅合成新的情感形式,成为大众情感。
但问题是,作为情感的符号系统的大众传媒应该怎样更好生产并传播这种大众情感?现状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由近及远扩展的传统情感体系解体,以自我想象性生存(虚拟空间中的生存、目的性生存)为基础的由远及近的后现代新型情感世界逐渐形成。真人秀节目将稀缺情感变成我们能够更轻易体验到的服务性产品,也就是说,真人秀节目生产的不是作为情感的产品,而是“情感激发装置”。在后现代新型情感生成的背景下,情感的媒介生产如何最大化弥补媒介的内在缺陷和人性编码漏洞,提供更佳的社会传播方案呢?
第一,走出生理刺激模式,走向符号互动与意义共享。传播发展中存在从“训示”到“对话”这样一个过程,在这条线索中,在网络社会体现为从工业资本主义过渡到信息资本主义,嵌入到新的数字基础结构中。旧有的大众传播系统在新媒体的刺激或倒逼下重新升级,比如互动性这一传统媒体的异质配置的重新媒介化。
人对自我情感的认知是在与他人交往、与社会相互关系中形成的。真人秀节目接受中的情感表露是观众自我表演的印象管理的一个节点。而在这个大众情感形成过程中,部分观众很容易出现不加批判或没有判断能力地接受这种电子化的情感,从而推动自我情感释放。一方面,真人秀节目传播除了作为电视场域之外,还与整个大众传媒系统相联系。真人秀节目可能作为视频在互联网上播放,也可能作为原始素材被编辑成小视频,更可能成为话题,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社交媒体上传播。另一方面互动能激发情感。在互动仪式论看来,互动能够提供最为积极的情感能量,个体在际遇中有权力(支配他人做事的能力)和地位(获了被参照和尊敬的能力)时就会激发更高的情感。真人秀节目外的受众掌握着“点赞”“转发”等奖掖之权,同样也能够极尽贬抑之辞。所以,符号互动论认为传播能够导致参与者间不同程度的共享意义和价值的符号行为。
因此,克服单纯的“刺激—反应”模式,走向媒介与观众的深度互动。节目的主题议程设定、引导与观众的主动解读是一个意义生产与交换的过程。这就造成个体情感对一般社会结构的屈从,屈从于霍克希尔所认为的“感受规则”(feeling rules),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规范,会指导个体如何体验、解释自己的情感,包括在特定情境中应该感受到何种情感并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
第二,从情境再造到反思性的情感构建。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认为情感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情境。真人秀的情境再造模式运用较广,比如《爸爸去哪儿》里的宁夏沙漠、云南文山、山东鸡鸣岛等户外场地;《中国好声音》的演播厅情境。各种音响、特效、剪辑等手段,为模拟、推动情境再造进行技术支撑。情境为情感的生产与传播有很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能第一时间催化感受,并强化之。在这种情境催生出来的情感往往陷入感觉的催化、堆积、感觉化与非反思中。仪式互动理论解释了情感在微观层面的运作机制,个体总是寻求最大化他们积极的情感能量——他们参与到仪式中去,这些仪式可以引出明晰的关注点、共同的情绪、情感的激励、情绪和激励的共鸣节奏以及所有这些的符号化。因此要让这些情感融入主体意识,形成价值观,反思性活动是必需的。
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反思或反省是人心对自身活动的注意和知觉,是知识的来源之一,人通过反省心灵的活动和活动方式,获得关于它们的观念。身体在场这一概念既是从空间(客体在场)意义上,又是从时间(现在的时刻)意义上意指存在的问题框架,包括主体的重新整合的活动,具有明显的创造性。而情感没有重新整合主体的这一后续过程。真人秀节目的情感叙事,建立主体自觉的反思性活动,实现“娱乐—情感—价值”链条的重要一环。在这个过程中,在保证观赏性的前提下,减缓节目节奏,或设置反思时间或环节。情感互动是情感的主体间通过相互作用而进行的情感转让,使一个人情不自禁地进入对方的感受和意向性感受的过程。通过主持人的话语引导,电视画面的排列整合,以实现情境中反思性情境的生成与构建。
第三,从符号化到社会化的情感生成。“同一社会成员的情感属于意义、社会准则、仪式性、语汇等开放的体系。”情感文化并非永恒不变,具有历史性。感知体系与行为相联系的社会准则会发生变化而且改变情感的表达。所以,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情感表达、意义,甚至主观感受。关于情感的社会建构问题,克劳特(Robert Kraut)有过详细研究,他认为既然语言意义出自约定俗成,那么意义就并非依附脑袋中的东西,从而认为社会文化决定情感生产。正如格雷戈里·贝特森1936年在《纳文》一书中描给了由文化建立起来的情感体系。
每个时代皆有其独特的情感特征与生成机制,农业时代的情感是以土地为归依的,形成综合性、内敛性和封闭性的情感;工业时代是以生产为基点的,从而形成了游离于生产与消费的多重人格,形成分裂、游离的情感特征。那么当下信息化时代的情感,更多是一种电子化、中介化、抽象化的。不管是被裹挟进入现代传媒体系的“数字移民”,还是得心应手的“数字原著民”无疑都进入了数字化生存。在城市空间里,大众传媒几乎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它已镶嵌在社会系统里,浸漫于每个人的生活。在这种传媒环境下,情感的生存与表达趋于中介化、电子化、虚拟化,并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因技术中介引发的情感疏离感;个体情感上升,群体性情感下沉;或者如舍勒所说的“情感参与”和“情感一体”的缺席,缺少对公共事务的情感认同。表现在真人秀节目上便是“符号化情感”与社会现实中的“社会化情感”相脱节,出现“情感泡沫”。
那么,如何提升节目中情感的社会化程度与实践?这里涉及到受众的主体建设问题。有学者指出,从不同角度看,自我是一面多棱镜。有笛卡尔式的绝对中心自我、胡塞尔的“责任自我”、弗洛伊德的本我、泰勒的社会主义自我:“这个光谱的一端,是人心隐藏的本能、非理性的、自由无忌的‘无担待自我’(unencumbered self),克里斯蒂娃称之为“零逻辑主体”(zerologic subject)。另一端可以是‘高度理性’的由社会和文化定位的个人(socially-situated self)”自我是一个纵横移动的存在,即由自我到超我的滑动的过程。这其实也可以说是社会化过程。社会化总是在一定环境中完成的。大众传媒和家庭、学校等都是社会化机构。人在各种矢量图、电脑游戏、虚实现实系统、数字电影和电视等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自我定义的机会,主要体现在文化规范习得、人格塑造。所以说真人秀节目中的情感符号社会化,也是“自我的再媒介化”(remediated self),从表达的基本形式推断普遍的心理后果和社会后果。
节目以各种符号呈现的公共性的情感具有可转译性,尽管意义的某些元素和层面可能在转译过程中遗失。但是符号互动论者认为,我们将不同情境的内在规则内化于自身,并依此来建构我们的行为。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认为,符号创造我们对意识的经验、对自己(自我)的理解,以及对更广阔的社会秩序的知识。从这个逻辑来看,真人秀节目建立的“真”与“秀”的情感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我们感知和阐释情感规则的能力,能够作为中介并建构我们的情感经验与知识。那么在符号促成认知的过程中,将一部分正确的情感观念内化为经验体系尤其必要。社会学领域舒茨的“典型化”、米德的“图式”指的就是这种重要的知识形式。典型化或图式能让我们快速地将节目中的情感符号或观念进行归类,然后迅速和常规化地建构我们的回应行动。
综上,从有限的文本到话语实践,从物质媒介到文化传播的分析,媒介内容的生产系统的效果维度、个体维度和社会维度来调适娱乐节目中的情感生产与传播思维与原则,以更好的符号在大众传媒系统中进行良性互动,实现情感仪式中的“符号互动”,以嵌入更规范的“情感结构”,并在不断循环进行调适,实现在娱乐中建构认知层面的情感主体与社会联动机制,可能更有利于建设健康的情感话语,融入全球化的情感版图中,真正实现价值的流转和文化的涵养。
注释:
② Clough,P.T.,& Halley,J.(Eds.) (2007),TheAffectiveTurn:TheorizingtheSocial.Duke University Press.
③ [法]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姚芸竹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④⑤ Stjepan G.Mestrovic(1997).PostemotionalSocie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p.xi,p.40.
⑥ Adam Arvidsson(2006).BrandManagementandtheProductivityofConsumption,ConsumingCultures,GlobalPerspectives:HistoricalTrajectories,TransnationalExchanges,ed.John Brewer and Frank Trentmann,Oxford:Berg.pp.71-72.
⑦ Michael Hardt(1999).AffectiveLabor,Boundary2.p.95.
⑧ [英]格雷· 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⑨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2页。
⑩ [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明川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