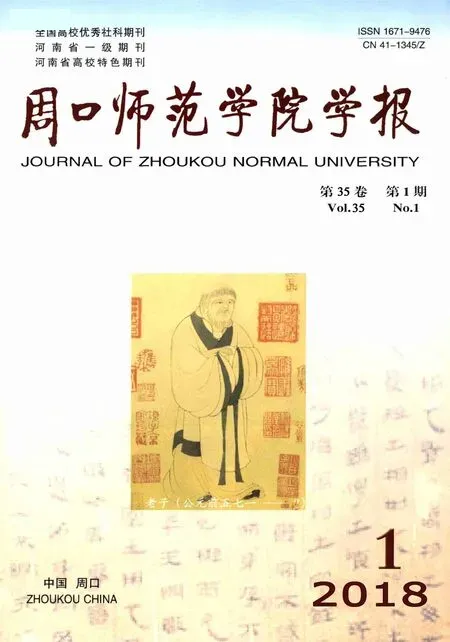论元人序跋的直接引《诗》
余秀娣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元人序跋直接引用《诗经》的篇、章、句俯拾即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用“诗曰”“诗云”“诗不云乎”等方式引出《诗经》篇章中的内容,并对其进行简单的分析,我们姑且称之为“显性引《诗》”。其作用不言自明,无论是使得表达更为委婉,还是说理更为有力,都具有直接的作用。另一种是引用《诗经》内容但不做任何分析,由于没有冠以“诗曰”“诗云”“诗不云乎”这些明显的引诗标识,我们暂且称之为“隐性引《诗》”。隐性的引诗方式表现出作者对自己和读者的充分信任,对于增强其作品的可读性和思想内涵的深度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暗示了《诗经》文本内容的统一化,对于同一首诗,学者的观点趋同。
一、显性引《诗》
元人序跋中直接用“诗曰”“诗云”“诗不云乎”“《诗》所谓”“《诗》之《XXX》”等情况出现在210篇序跋文章里。元人或对《诗》句进行解释阐发,或借《诗》句进行劝诫,或借《诗》句发表自己的见解,含蓄隽永,文辞款款,令人叹服。下面分别举例来说明。
1.对诗句进行解释和阐发。此种方式通常先引述《诗经》文句,然后进行阐发。如杨奂《正统八例序》:“《诗》之《皇矣》:‘乃眷西顾,求民之莫’,斯其旨也。商、周之交,纣德尔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潜德言也。”[1]1册:130上文化用《诗经·大雅·皇矣》的第一章“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和“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大雅·皇矣》是周人叙述开国历史的诗篇之一,该诗叙述了太王、太伯、王季、文王开创周朝的事迹。《毛诗序》曰:“《皇矣》,美周也。天鉴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2]诗序说明该诗是美周,更为强调的是该诗赞美文王,重点在文王身上。与三家诗差别不大。王先谦说:“三家无异义。惟据鲁齐之说皆直言此诗为陈文王之德。”杨奂引用该句后,对第一章的内容做了解释,意思是商朝朝政混乱,德行消弭,上天不忍心百姓遭受商朝的暴虐,替百姓寻求新的安生之所,周的先辈勤恳忠诚得到上天的眷顾,在文王这一代,成为上帝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杨奂并且还对此句做了定性的判断:以潜德言也。这就说明,世世代代德行的积累最终会由量变达到质变。对该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说,并没有越过前人解释的界限,只是更为具体和详细。
再如,陈谟《书养蒙刘先生墓志后》:“《诗》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盖不稼不可以得禾,不狩不可得貆,孺子非其力不食,其心盖出此也。”[3]47册:282《魏风·伐檀》本是批评统治者不劳而获。此处陈谟对“不素餐”进行展开,认为要自食其力,不能尸位素餐,并对隐居南阳的徐孺子自力更生,亲自养蚕、耕种表示赞赏。
2.借用诗句进行劝诫。如《送何心传序》:“《诗》云:‘既景乃冈,相其阴阳。’则冈之阴阳,亦有系于相与之便不便者。”[3]41册:319上文引用《大雅·公刘》的诗句,与本文的何心传向作者所序的相书正好相关联,杨维桢批评相地的无稽之谈和迷信做法,不主张何心传拿着该书招摇撞骗,坑骗老百姓。
又杨维桢的《题石伯玉万户乃祖雁荡诗》中:“《诗》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招讨公以之。又曰:‘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安侯以之。”[3]42册:223引用的是《大雅·江汉》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来赞美石公的美德,引用《大雅·文王》的诗句“毋念尔祖,聿修厥德”来告诫石公的曾孙安泰不花侯要遵从先人的德行,提高个人的修养。再如谢应芳《送刘文可序》中的“《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君子慎之”[3]43册:182。刘文可归乡,作者作序言赠之,告诫其要谨小慎微,防微杜渐。引用《大雅·荡》的诗句,告诉文可不可以让自己有私欲,令心灵蒙尘。
3.借用《诗经》诗句表达自己的见解。如方桂的《饯郭候诗序》:“《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斯言何谓也?盖牧民之官,与民好恶之心相近,推其爱民之心如爱子之心,痒疴疾痛,必先知之,此之谓父母。”[3]47册:348此处引用《小雅·南山有台》。方桂所送友人郭太守,是一个廉洁自守、爱民如子,获得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因此方桂以此表达自己对于父母官的认识:与百姓同心,体察百姓的好恶,爱民如子,关心民生疾苦。这里,《诗经》章句只是一个引子,而作者表达的重心在于自己对于某件事情的认识和态度。又胡翰的《送袁知州赴宁都序》:“《诗》不云乎‘四牡騑騑,周道倭迟’,言行役之远也。又曰‘岂不怀归,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不固也。虽臣子之孝思根于天性,乌能以私恩废公义乎?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义非忠臣也。权其轻重而行之,故曰:‘不遑将母。’虽行之,父母之爱曷已哉!故曰:‘将母来谂’。”[3]51册:183作者对《大雅·四牡》的引句进行了解读,提出私恩和公义同样重要,在不同情况下,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认真的权衡比较再选择服从回报父母还是国家公义。
二、隐性引《诗》
元人序跋当中,应用《诗经》的手法十分灵活,隐性引《诗》用《诗》随处可见。隐性引《诗》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诗经》的章句的直接化用;二是对《诗经》典故、成语的运用,贴切圆融,丝毫看不出刻意为之的痕迹,反映出《诗经》已经内化成元人文学血液里流淌的一部分。
1.对章句的直接化用。如胡祇遹的《送监司之济南序》,是胡祇遹送彰德路总管达噜噶齐嘉议去济南上任而作的序文,文章盛情称赞达噜噶齐嘉议在彰德的政绩和当地百姓对他离开的依依不舍之情。文中的颂词:“民心怀悲,东望依依,三年来归,东人得仁,户户阳春。愿公回顾,念我西人。祖考松楸,邦人敬修。公无久东,孝思悠悠。”[1]5册:252很自然地化用《诗经》里的词语和情调。其中“东望依依,三年来归”很明显套用《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而“祖考松楸,邦人敬修”和《召南·甘棠》百姓善待召公种植的树木,不忍伤毁的睹物怀人之情如出一辙。“公无久东,孝思悠悠”里“悠悠”一词,更是在《诗经》里多次出现,如《终风》的“终风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雄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泉水》“思须与漕,我心悠悠”,《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子佩,悠悠我思”,《鸨羽》“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等等。此文中的“悠悠”正是《诗经》多数篇章里形容思念悠长的“悠悠”。
再如李冶《七真传序》有言:“于斯时也,不有至人济之无假之津,返之邃古之宅,则日填月积,积习生常,氓之蚩蚩,将为异物。”[1]2册:21“氓之蚩蚩”出自《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此处用在文中形容老百姓憨厚无知。又王恽《清香诗会序》“今夕何夕,余膏媵馥,沾丐如是,有不可思议者”[1]6册:189。“今夕何夕”出自《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用法和《诗经·绸缪》一样,形容时间正好。再如《跋陈同年信学去官本末》“人孰无缁衣巷伯之心,为区区一官计而泯其天者,今之世夫岂少哉!”[1]7册:192朱熹《诗集传》有“故曰‘好贤如《緇衣》,恶恶如《巷伯》’”之语。此处正是对此句的简缩,意为人人都是好善恶恶的,但是由于名缰利锁,很多人违背初心,丧失气节。何孟贵《鲜于夫人李氏手帖序》中“岁月云迈,悠悠我思,我须我友,一旦有以枕中故藏归我伯机者,生前遗墨,手泽如新,鼪鼬藜蕾之墟,闻似人足音以喜,况惹蒿凄怆,若有僾然以见乎其位者,有不一动其心乎?君子是以重叹”[1]8册:78。“悠悠我思”化用《终风》“莫往莫来,悠悠我思”,《雄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等,意思一样。“岁月云迈”化用《小宛》“我日斯迈,而月斯征”,都是形容时光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不可复返。而“我须我友”则化用了《匏有苦叶》“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一章,“卬”即“我”之意。三个小短句天衣无缝地使用了三个《诗经》中的语句,手法娴熟,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自然贴切,毫无穿凿。此外,化用《诗经》语句的,还有如家铉翁《送崔寿之序》“于今政将成,翩彼飞鸮,乃或鸣其不善,亟委而去之,士论共惜”[1]11册:727。“翩彼飞鸮”出自《泮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黄公绍《诗集大成序》:“‘彼稷之穗’,方永慨于《王风》;‘何草不黄’,又增伤于变雅。”[1]14册:35“彼稷之穗”化用《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穗”之句。“何草不黄”化用《何草不黄》“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之句。胡行简《竹山隐居诗序》“环其居之竹,则先世手植而勿翦勿伐也”[3]56册:8,则是化用《召南·甘棠》“勿翦勿伐”。王礼《送沙本中入蜀序》:“死生契阔,感叹何极。倚门在念,急急遄归。”[4]“死生契阔”则是直接化用《邶风·击鼓》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元人序跋里对《诗经》章句的化用还有很多,兹不多举。
2.对《诗经》典故、成语的运用。如元好文《新轩乐府引》:“横门之下,自有成乐,而长歌之哀,甚于痛哭。”[1]1册:311此处化用的是《陈风·衡门》“横门之下,可以栖迟”,《毛传》“横木为门,言浅陋也,栖迟,游息也”。衡门为浅陋之地,栖迟为玩乐放松的状态,正是隐者自乐的表现,与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的忘贫自乐状态一致。毛序虽然言明此诗是为“诱僖公也,愿而无立志,故作是诗以诱掖其君也”之作,但对该句的解释暗含衡门所蕴“隐者安贫自乐”的意味。郑笺“贤者不以衡门之浅陋则不游息于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国小则不兴治致政化”,其中隐晦地表达了相似观点,但都没有突破经学的桎梏。朱熹大胆表达此诗的诗旨:“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辞。”自朱熹提出贫者自乐的观点,宋元的诸多解《诗》家纷纷跟从,如宋王质、辅广,元许谦、朱公迁、刘玉汝、刘瑾、明梁寅、朱善等人。而此处元好问使用的贫者自乐的观点同样来自于朱熹。
再如胡祇遹《送张飞卿序》“以声律诗赋道德途说为文,以抚剑疾视、暴虎冯河为武”[1]5册:252。“暴虎冯河”原本出自《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冯河”,意思是不敢赤手空拳去打老虎,不敢不凭借舟楫渡过河水。后来被人反其意而用,脱化成“暴虎冯河”,即敢于徒手搏击老虎,不依靠舟楫渡过江河。“暴虎冯河”四字成语最早见于《论语·述而》:“子曰: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5]孔子认为赤手空拳打虎,赤脚过江涉河,是十分鲁莽的,是不明智的做法,不可取。他与之合作的搭档需要是一个遇事不慌不忙、冷静沉着,三思而后行,做事有把握的人。《中华成语熟语辞海》:“[暴虎冯河]暴,空手搏击;冯,通“凭”。空手打虎,徒步过河。比喻鲁莽蛮干,有勇无谋。”胡祇遹用在这里,想要表达文官不能只会舞文弄墨,武将也不能只会拼命蛮干、鲁莽无谋。两者要结合起来,文武双全,全面发展,才能真正成为文武兼具、德才兼备的人才。很明显,胡祇遹的“暴虎冯河”是使用孔子的观点,其根本则来自《诗经》。
还有王恽的《燕山王氏庆弄璋诗引》[1]6册:208,文章讲述的是史馆检阅王子宪生下儿子,众人作诗庆祝,王恽写序,并为婴儿取名。所以该诗集名称里使用到“弄璋”。“弄璋”一词原出《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意思是生了男孩,把他放到床上,用大人的围裙包裹好,再给他一块璋玉玩耍。古代社会里,把生男孩称为“弄璋之喜”,把生女孩称为“弄瓦之喜”。这里同样使用了《诗经》典故。
元代文人的序跋,汲取了《诗经》经久不息的艺术经验,其接受形式丰富多彩。元人序跋《诗经》应用情况十分丰富。如此广泛全面地引诗和用诗,反映出元人对于《诗经》的熟稔和推崇。
[1]李修生.全元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2]孔颖达.毛诗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66.
[3]李修生.全元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
[4]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220册:461.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