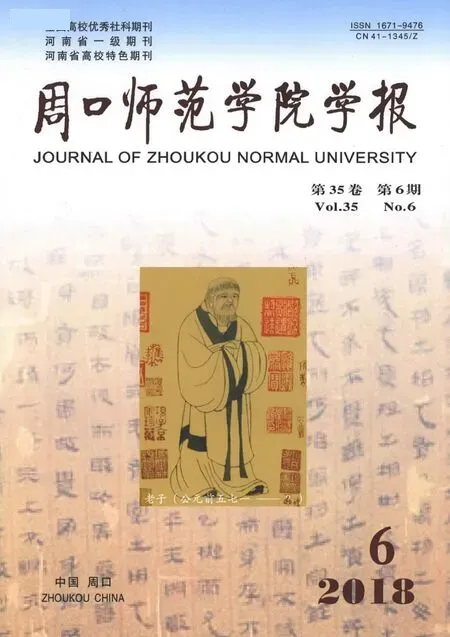在生活之河上拖拽渔网的人
——读陈一军诗集《孤旅诗绪》
周显波
(岭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人类不可避免地要给所置身世界里的事物贴上一个个标签。标签是命名符号,为归纳和分类的方便,进而让人得以找到围绕对象展开的言说话语范围与界限。与此同时,标签也往往构成对言说对象的一种遮蔽,或者说,对象也以自身的丰富性逃避甚至拒绝着标签的概括,所以才有了人类对对象的多重标签命名的冲动,于是我们只好无奈甚至有时是笨拙地为对象贴上更多不同的标签,以方便对其精准地识认和分析。当下流行词——“斜杠青年”,就是这种主体拥有多重标签的例子之一,“斜杠青年”本身的含义就是指青年所拥有的多种身份。陈一军是这样一位标准的“斜杠青年”,他的身份是高校的学者,而且是在本专业领域取得了相当成绩的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陈一军出版了一本原创诗集《孤旅诗绪》(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版),诗集的出版又给陈君添上了一个新标签:诗人。诗人陈一军比学者陈一军显然让人陌生得多。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孤旅诗绪》是“对生活还算有心的一个人经历的点点滴滴”[1]。这本诗集可以视为抒情者的陈一军对自己生活关键阶段的“感觉”“体验”的“点滴”汇聚,经验的“反刍”以及心灵的剖露。我们通过阅读这些或者直白或者隐晦的诗作,可以看到学者陈一军身上多种角色的转换:由农村子弟到城市人,从刚刚硕士毕业继而到博士和高校教师,从出租房里挣扎的底层知识者到小有成就的当代文学研究者,更能够看到在这些转变背后的内心隐秘、情绪波澜以及审美主张。因此,《孤旅诗绪》是陈一军在新世纪的个人“心史”,但从他有代表性的经历里又明显可以发现,这种个人“心史”也带着底层知识分子的群体性情绪的典型特征。
一、乡之愁:故土的眷恋与反省
陈一军作为西部乡村之子,乡土基层的经历既是促成他学术的起步动机之一——关注底层、关注弱者——这一点在陈君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他的诸多学术论著中都可以清晰看到,同时,乡土也是《孤旅诗绪》的重要书写对象。西部乡土中国的风景——风、老牛、田野、野花,各式庄稼,“歇缓”的农民乡亲,那燃烧羊粪生出“呛人的烟”,“每吹一下就会泪流满面”……阅读这些乡村图景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穿行在诗集中朴素和澄明的句子间,西部乡土那朗明的天和厚重的黄土带着被太阳炽热烘烤的温度和气味瞬间扑面而来,让人为之着迷。西部乡土用它那些粗糙的手掌轻抚着身为游子的诗人,于是在诗人的笔下,乡土用一副满带质感的烟嗓自顾自地吼着沧桑的歌词,歌词质朴却也不乏赤裸的生活底色。有时候,乡土是充满温馨的,比如晚霞、西天、“箭一样穿过眼前”的乌鸦,让“多年在外漂泊的游子”“欣赏”和挂念(《乌鸦》)。有时,乡土是一幅静止的风俗画:“青堂瓦舍间冒起青烟,/母亲开始呼唤贪玩的孩儿回家吃饭。/有个不知疲倦的耕夫还在劳作,/一声悠长的吆喝声萦绕在山间……”(《九月的故乡》)诗人笔下九月的故乡不再是海子笔下深沉的哀歌,而是带有毛茸茸质感的日常生活片段。这种生活片段与温暖交织在一起,熔铸成一片对乡村眷恋的深情,时时跳跃在诗行里。有时,诗人笔下的乡村又是富有传奇性的,比如《复活的故事》里穷汉娶亲的传说也被诗人饶有兴致地写进了诗行,读后陡然在心底升起一种莫名的震撼。
不能忽视的是,陈一军并非一名传统意义的乡村知识分子,乡村只是他的底色之一,是其生命中的一段经历和生命体验,而随着他外出求学、任教,乡村愈加变得对象化了。因而,乡村一方面被诗人囊括在诗句里变成凝聚乡村记忆、抒写眷恋的所在,另一方面,诗人的知识系统和知识分子身份也时时地提醒他,不能把乡村彻底地变成一个想象的存在、审美化的存在。毕竟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乡村也被卷入其中,乡土原来相对稳固的形态愈加变得分化,因此,那个想象中的寄托乡愁的所在,无法再保持一种因远观而形成的澄澈与单纯的风景。或者说,那个拥有单纯风景的乡村,一旦进入知识者现代眼光与真实体验交互的多重审视之下,农村内部的苦涩、滞重、呆板,甚至无序也成为它密不可分的一部分。陈一军时时刻刻都在清醒书写着一个坚固地建立在他体验和感受下的乡村,那个乡村当然有诗性的一面,但更多的则是一幅有力量、有美丽也有污秽的现实图景。与那些展示审美化乡村的诗歌写作不同,诗人心中的那种底层经验时时浮现上来,最终左右着他诗歌的方向,因而,极其富有真实质感的劳动场景也常常被诗人摄入笔下。比如,《同样是麦地》里写道:“大地干裂着嘴唇,/像没牙老人的黑洞。/麦禾如将死的茅草,/穗子被压缩成纸张一样的平面。/农人们绝望地收割,/他们是食草家族吗?/脸上汗如沟,/足蒸暑气热。/明晃晃的蓝天,/云都不留一片羽毛。/诗神可能早已殒命,/海子,你能让他复活吗?”在诗里,劳动不再是以一种审美的意义而存在,相反,是以一种赤裸裸的,与血、与汗水联系在一起的,诗人眼中的劳动者是“绝望”的,因而,在真实的体力劳动面前,那种带着距离感的、美学意义上的劳动失去了浮夸的颜色和质地。在这里显然诗人并不是意在颠覆海子笔下由诗神主宰的麦地,而是与诗人海子进行了一次隔空的精神对话,同时更是一种对已然经典化的、审美化的麦地的一种补充:在赤裸的真实体力劳动中,在挥汗如雨的形而下的生活里也有诗,所以那句“诗神可能早已殒命”更像是说旧的诗神在这里“殒命”,新的诗神可能就孕育在这里。乡村一方面有让人眷恋的诗意的风景,另一方面杂乱、困窘也是它的日常状态之一:“老墙下面,/男人对男人,女人对女人,/小孩对小孩,/撕扯在一起。/辱骂喑哑了每个人的喉咙。/唾沫潮湿了对方的脸。/铁青的面孔雷公般扭曲。/下流的言语,/轮奸了共同的八代祖先。”(《回忆·邻居》)再如,“几家兄弟妯娌,/如羽毛膨胀的斗鸡。//青色的睡眠发出阴冷的笑,/为我争是你黄土地人的命!”(《回忆·水窖》)当回忆和生活里真实的一面共同浮现上来时,那单调的颜色和蛮荒的故乡大地,以及掺杂着鸡毛蒜皮和真假人性的内容就构成了诗人对故乡的真实印象:“故乡的颜面/和它的主人一样吝啬。……荒芜的土地全都是草场。/羊群铺展开来,/牧羊人攒在一起闲扯起久远的话题。”(《故乡》)诗人也尝试着为“故乡人”的命运出路做出预言:“然而这不过做了习惯的奴隶。/干瘪的黄土地不会给他们多少慰藉。/圆圆的天际是一个紧箍咒,/觅寻新途就得跳出千年怪圈。”(《怪圈》)
面对成为故土而又带着杂乱甚至落后的农村,离家的知识分子该如何还乡?怎样寄托乡愁,怎样想象和思考主体与乡村的关系是一直困扰现代知识分子的话题。陈一军从自我经历出发,通过他的诗做出了尝试性的回答,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把一种对故乡农村的眷恋与困惑共同呈现给了我们。
二、城之感:城市的文明之思与文化追慕
有故乡可以回的人是幸福的,但现代社会的矛盾之一就是我们往往要主动地做一个漂泊的异乡客,奔波忙碌在自我角色和社会角色的设定里,并且只能在这种设定里思考并处理自我与所置身的环境的关系。这个环境从根本上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又常常只能无奈地把他乡认作故乡。
陈一军的笔下,除了乡村生活之外,另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其作为西部乡土之子的身份置身于城市,在城市化的进程里,他所获得涓滴感受和体验。这些感受和体验,首先表现出对城市内部人事纷扰的感慨、喟叹及由此而来的抑郁。“文明的都市”里的孩子们,“少的是童年”,所以在诗人的观察中,这些孩子“少的是伙伴。/一个家庭一个孩子,/摆弄积木他早已腻烦”(《别咒》)。而成人世界呢,“一排雪片剁在娱乐厅的墙头,/壮志未酬慷慨赴死。/淫荡依然在墙内继续,/雪片不懈地在天空飞旋;/不能清净这个世界,/似乎就要周旋到底”(《雪片》)。雪片与“污浊”的街区、娱乐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静一动,一白一阴,一明一晦,一清一浊,一丑一美,让诗歌倒是显示出一种类似阅读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感受。与乡村的天然和质朴景色相比,城市连风景也是“造假的世界”:“仙来居冷落了一群神仙,/桃花源的木格飞檐是水泥涂了一层颜面;/老水车汲着自来水,/空转的石磨吐不出白面……”(《造假的世界》)陈一军在面对城市,面对充满着塑料玫瑰、“污染的灵魂”“污浊”的城市纷扰时,那种批判意识来自于他的观察,来自于他的知识背景和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更来自于他朴素的乡村经验。与城市的现实比较起来,诗人心中的乡村理想一面往往浮现上来,其理想之地和乌托邦显现出城市不具有的光芒、柔软和温馨:“遥远的农村可不一样,/那里人的生活依然和你紧紧相连。你会领着老奶奶从麦地回来,/又怜爱地照看孩子游玩,/复呵护疲惫的农人安然入眠。”(《月亮》)
陈一军并非一味地谴责、批判现代都市,知识的理性和文化的传统没有让他成为弃城还乡的归人,哪怕是在精神上还乡。正如我们在前文谈到的那样,乡村的现实让诗人自己有很清醒的认知,远在乡村的故土并非是可供膜拜的乌托邦。所以,诗人陈一军在面对城市的时候,更加注意的是城市的文化线索与历史脉络,在他或者居住或者客居的城市,抛开好奇的游客身份而自觉地成为一个挖井人和考古者,在城市的文化之井里淘洗尘土,在城市所负载的历史陈迹里找寻文物。上述这种倾向在他的晚近诗作里体现得愈加明显,于是,在这种身份与心态的双重转变里,诗人变得越来越容易与城市和解。但这并不是诗人不再以人文精神关注城市的压抑甚至异化,而应视作随着阅历的增加和丰富,诗人对城市的文化性加以重视,所以在他晚近的诗作里,一座座国外或国内的城市在笔下“崛起”。北京、徐州、山海关、西安、兰州、汉中,这些城市大都有着文化与历史底蕴,诗人将之抚摸、膜拜和拆分,放置在自己的诗歌地图里,与笔下现代城市的缺陷加以对比,在此显示诗人的立场。于是乎,兰州,这座与诗人有着那么多“纠葛”的城市,因为诗人自己的经历,也因为“铁桥”、黄河母亲像等变得不再那么让人压抑,而慢慢升起了“如此陌生”的感觉。汉中作为“中国的心脏”,以及作为中国的中心的北京都以其文化魅力和历史厚度令诗人折服。所以,陈一军笔下的城市虽然呈现出两种风貌,但是不应该将之视为泾渭分明、静止的,而应该视为动态的。
从晚近的诗作来看,陈一军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对城市文化和历史的挖掘上,一个城市底层者渐渐被一个文化和历史的挖井人和考古者所取代,这是我们继续期待着他诗作的理由。
三、“旅程”:知识分子的观察和领悟
如果要寻出《孤旅诗绪》整部诗集的文眼,我想“旅程”是比较合适的。这不只是说“旅程”和诗集标题相符,也不只是说“旅程”是诗集的代表诗作之一,而是说“旅程”首先是对诗人新世纪以降的生活状态、思想情绪和创作心境的概括。新世纪以降,诗人陈一军有着几次关键性的人生转折经历,由硕士到博士,再到高校教师,身份和角色多次变更,其间的付出与辛苦,失落与收获,这些都在其诗作之中可以窥见一二。乡村里的少年时代,随后负笈兰州,继而任教汉中,间或在国内外旅行,诗人新世纪以来可谓始终“在路上”。诗集标题“孤旅诗绪”中的“诗绪”正是诞生在这人生旅途之中。因此,整部《孤旅诗绪》,我们不妨将之读解为诗人心史的“密码”,按照诗歌创作的时间顺序能够观察到诗人在其人生旅途中的生命历程变迁与心态的微妙变化。整部诗集截然分成两块:一是2007年6月23日—2009年3月30日,二是2015年1月31日—2016年8月24日。两段时间有近6年的空白间隔,造成明显时间间隔的原因,作者并未说明,究竟是敝帚自珍,还是真的未曾写作,抑或是诗作里有不便公开披露的自我真实心态?其中缘由恐怕只有陈一军自己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正如作者所说,这些诗作“都是出于心的,自然包含了曾经有过的寂寞、惆怅、遗憾、困惑、焦灼、悲凄或者伤痛,当然也不乏欢快、欣喜、梦想、思念、慰藉、感悟与感恩”[1]。很明显,诗人正是把诗歌写作当作人生之旅的一部分来看待,而之所以如此,大概就是出于诗作与他个人生活的直接相关性。
陈一军作为诗人的状态正是书斋里研究者的自觉延伸——众所周知,文学研究者都是孤独的——孤独地驰骋在文学世界里,孤独地摸索着人类精神的峰顶,孤独地在文本间小心翼翼地思考、假设、求证,并编织成著作。诗人在旅程中的状态正是把书斋里研究者的存在方式延伸出来:一个冷静的、独立的、理性的观察者式的诗人悄悄地行走在诗行之中,品味着孤独,乐于寂寞,在时空的跳跃里表达着也小心地吐露着心声和体悟。“时空变化最适合容纳故事和丰富感受。时间流逝有故事可讲,空间的对比更是抒发各种复杂感受和思考的最好场所。”[2]的确,诗人虽然处身于人生之旅与具体的旅程之中,但他作为观察者的角色从来未曾变更。而旅途又是最具有时空迁移特征的,这一静与一动的意外碰撞,就让许多诗作悉数落地,而这些诗作也因此具有了在旅途中观察者的血统:冷静、独立、富有思考性,所以陈一军的诗歌是力求在布满具体现象的生活之流里提炼、描画出隐秘的真相和本质。时间是旅程的一部分,诗人在《深刻》里对时间的宏伟之力进行了体察:“时间还把猿变成人,/又把人变成奴隶,/做祭祀的殉葬品;/又让他站起来,/重新做人。”离家—回家对于游子来说必然是旅程,诗人有对离家中年游子之心的细致描摹:“父母老了/离家难了/不敢回首/脚步流星/就像逃兵”(《离家》)于是,监考也被视作一段特殊的旅程,可以令诗人观察和领悟。诗人作为监考教师在考场巡游时突然有对存在意义的领悟:“似乎这是宣示权力的经典时刻,/你却沦为虚无/……监考,/一个凝定的时刻,/让你看清一副生存的面影。”(《监考》)诗人在文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敏锐的观察者形象是自觉的,是贯穿于、呈现在诗集始终的。这个观察者是他作为人文知识分子身份的延伸,这种延伸决定了陈一军这一次跨界所收获果实的丰盛。
四、小结:“孤旅”状态与“诗绪”表达
《孤旅诗绪》是陈一军多年诗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和总结,诗集虽然名为“孤旅”,但诗人自己却未因“孤旅”而自我隔绝,也未因孤独而让诗歌内容变得自怜自恋。作为诗人的陈一军从“孤旅”状态中提炼出对于世界的思考和判断,因而,“孤旅”更像是他观察世界、理解周遭的一种角度和方法,诗人正是从“孤旅”出发,在时空交错的旅程里有意无意地收获一次次的“诗绪”表达。显然,作为诗人的陈一军在意的并非“孤旅”,他更在意的是记录并书写自己绵延的“诗绪”。这些“诗绪”不是浮光掠影的,而是来自交织着生命感受与理性思辨的诗性升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理解了他在诗集自序中的说法:“考虑到时间的延伸和感受对象的变动不居,所有这些出自同一主体的感受,便有了一把拽起一拖渔网的感觉。”[1]上述引文里,那个试图在生活之河上耐心地拖渔网的人不正是诗人最好的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