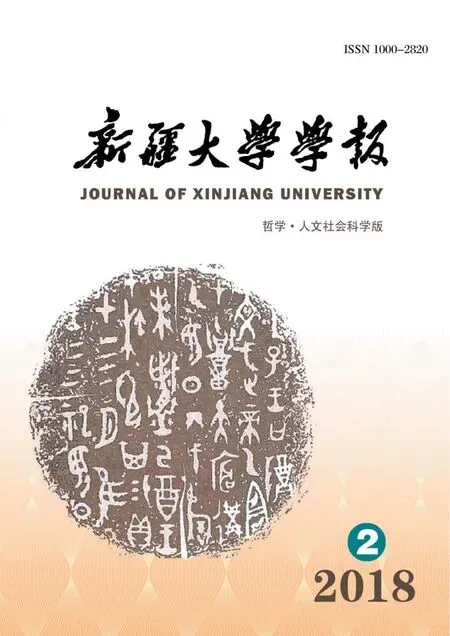刍议审美与感恩意识的培养
——以中国哲学与文化为例*
汪韶军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海南海口570228)
尽管我国不像西方那样有专门的感恩节,但我国传统文化本来就富有浓厚的感恩精神,“饮水思源”“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等成语便是感恩精神的很好体现。
感恩意识的培养,途径可有多种。笔者在此关注感恩意识与审美活动、审美教育的关系。可以说,感恩意识在审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审美活动对感恩意识的培养也有着重要作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年)提出过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一说。高峰体验也是一种美感经验,而且是最高层次的美感经验。据他描述:“经历高峰体验后的普遍后果是一种感恩之情油然而生,这种尤(‘尤’当作‘犹’——笔者注)如信徒对于上帝,以及普通人对于命运、对于自然、对于人类、对于过去、对于父母、对于世界、对于曾有助他获得奇迹的所有一切的感激之情。”[1]270叶朗先生指出:“特别是马斯洛关于高峰体验会引发一种感恩的心情,一种对于每个人和万事万物的爱的描述,指出了美感(审美体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同时又为很多人忽视的特点。把握美感的这一特点极其重要。因为只有把握美感的这一特点,我们才能深一层地认识审美活动(美和美感)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2]笔者拟先就感恩意识进行理论反思,然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一些元素,来对感恩意识与审美活动的关系做一初步探索,最后提议审美教育应成为培养感恩意识的一条必要途径。
一、感恩意识的界定及其特性
一般都会把感恩意识理解为道德良知,此举不能说有错,但未免有点狭隘。笔者以为,感恩意识非仅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知恩图报,我们应该对之作一扩大的理解。据笔者体会,感恩意识有如下一些特性:
(一)敏感性
一颗敏感的心,是主体产生感恩意识的必要条件之一。麻木不仁便不能感,也就产生不了感恩意识。
如我们所知,日常生活中的感恩行为就是知恩图报,与忘恩负义相对。一般都是先有那么一个比较具体的施惠者,然后是受惠者想着去回报。不管这种回报是止于意念层面还是发于实际行动,也无论是还报施惠者还是转报他人,感恩行为通常都会带上一定的功利色彩。但我们可以看到,感恩意识强的人,不仅会在顺境中感恩,尤能在平凡中、在看似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恩惠的情况下感恩,甚至在逆境中感恩。
这一生活现象提示我们,感恩意识是可以超越有限自我的功利考虑的。事情往往是,一个人越是注重利,越是不知足而一味索取,就越不容易萌生感恩意识;相反,这样的人总是不把他人对自己的付出看在眼里,而把自己的获得视为理所当然,并动辄怨天尤人。对此,有人做过很好的表述:“感恩,让我们以知足的心去体察和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感恩,让我们在渐渐平淡麻木了的日子里,发现生活本是如此丰厚而富有;感恩,让我们领悟和品味命运的馈赠与生命的激情。”[3]的确,知足才能敏感。镜若布满尘垢,就不能朗现外部世界;心若被贪欲蒙蔽,也就感受不到世界对他的馈赠。而一个人如果有“不思八九,常想一二”的心态,就很容易萌生感恩意识。唐君毅先生《说中国人文中之报恩精神》一文曾就再平常不过的饮食说:“人若能于其饮食之事,皆视为上帝所赐与、其他人或天地之所赐与,而时时生一感恩之心,人即可超凡入圣。”[4]
鉴于感恩意识有超越功利的面向,而这一面向通常被我们所忽视,我们有必要将感恩意识与日常意义上的感恩行为做点区别。我们不宜把感恩简单地看成是对施恩者的物质回报或还债,否则将无法与功利活动划清界限。再则,如果非得等他人给予恩惠才意识到需要感恩,那就只是利的往来,而不是这里所说的感恩意识。
(二)崇敬性
感恩意识常伴有受者对施者的崇敬之情。这施者可以是相对具体的对象,也可以是若有若无甚或假想的对象,诸如父母、师友、先祖、英烈、往哲、天地山川、鬼神与上帝,等等。
《诗经·小雅·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①为避免繁琐,从《诗经》《周易》《老子》《庄子》《论语》等先秦经典性古籍中引出的材料,本文只在正文中注明所出篇目。此诗已把父母的养育之恩渲染得淋漓尽致。儒家突出孝道,这是对父母的感恩。“士为知己者死”,是感于知遇之恩。我们的一些节日,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父亲节、母亲节、教师节等,主要就是为了表达感恩之情。还有一些具有审美意味的节庆活动,如春节、元宵等等,它们就像从日常生活之流中截出的一个个时间片断,人们在此时从事一些看似非实用甚至“劳民伤财”的全民性活动,其实这些活动有协和社会、传承文化的功能,而且也是感恩意识的表达。另外,在中国历史上,祭祀经历过一个从狭义宗教性到广义宗教性、从重在祈福消灾到重在缅怀感恩的发展过程,它已不是搞什么迷信(淫祀除外),而主要是与祖宗、先烈、往贤、天地社稷之神的精神交通和对他们的感恩。比如我们现在祭祖或敬拜烈士的亡魂、英灵,就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感恩之情,多数人都不会真的认为有这么一个灵魂实际存在着。以孔子为例,“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给很多人的感觉似乎是,孔子只是“不语”“远之”,而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但这样理解的人,实在没有看到孔子骨子里对鬼神观念的反对。《论语·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孔子只是说,祭祀一定要虔诚,一定要投入,否则祭了等于没祭。“如”字很微妙,但实际只能理解为若有而实无。为什么要用“如”字?原因很简单,明确肯定鬼神的存在,会导致人们重视“事鬼”而忽略“事人”;明确否定鬼神的存在,则又导致人们丧失敬畏精神。这两种情况孔子都不愿看到,故将鬼神观念“虚悬一格”。②《孔子家语·致思》有段材料颇能说明问题:“子贡问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详见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51页。
(三)激励性
感恩意识常伴有幸福感。“懂得感恩的人,总是觉得自己幸运地得到了这个世界的许多恩赐,而沐浴在这不尽的恩赐中,生命自然也就会体味到甜美与幸福。”[5]人沉浸在幸福感中时,会感觉世界无比美好,并生发出创造人生价值与意义的冲动。马斯洛观察到:“每个超越者能够如此轻易地、直接地觉察到现实中每个人的神圣性,甚至觉察到所有生物,或美丽的非生物等等的神圣性”[1]65,“感恩之情常常表现为一种拥抱一切的对于每个人和万事万物的爱,它促使人产生一种‘世界何等美好’的感悟,导致一种为这个世界行善的冲动、一种回报的渴望、甚至一种责任感。”[1]270此论道出了感恩意识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它能催人奋进,激发出珍惜美好事物、善待一切的冲动。
感恩意识引发的行善冲动决不限于日常所说的知恩图报,而是用爱心去拥抱生活,用宽容去与世界相遇。这种爱意不是对恩惠的被动偿还,而往往是一种主动的、无条件的慷慨精神。在此,感恩者完成了由受者向施者的角色转换。感恩者似乎已向某个终极原因(可以是宇宙全体)敞开,在这敞开与对话中,将自己提升至一个崇高的境界。
二、审美与感恩意识的互动
(一)感恩意识有助于审美态度的形成
我们知道,审美活动不是功利活动。审美发生的先决条件是,主体必须有审美的态度、审美的眼光;而要有审美的态度,就必须抛弃实用功利的态度。如前所言,感恩意识有非功利性的一面,感恩意识中的“我”,可以是无关乎个人利害的“我”。感恩意识强的人,因其功利需求少、容易知足,故容易超越功利的束缚,以非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这样一来,感恩意识在提升一个人道德境界的同时,也有助于审美态度的形成。
审美的人有一颗一触即觉的心。朱光潜先生曾形象地说:“诗人所以异于常人者在感觉锐敏。常人的心灵好比顽石,受强烈震憾才生颤动;诗人的心灵好比蛛丝,微嘘轻息就可以引起全体的波动。”[6]而感恩之心恰好是一颗敏感的心,与审美心胸有其重合处。感恩意识可使人养出一颗恬淡闲和的平常心,故往往能于平凡中觉出不凡,促成美的发现。方东美先生曾说:“宇宙,从中国哲学看来,乃是一种价值的境界,其中包藏了无限的善性和美景。”[7]这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可以感受到: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周南·葛覃》)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召南·草虫》)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卫风·淇奥》)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卫风·硕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小雅·鹿鸣》)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小雅·出车》)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大雅·旱麓》)
这些极富表现力的诗句,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生香活态的世界。《文心雕龙》开篇一段脍炙人口:“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踰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8]1在中国古代诗人、艺术家眼中,世界是丰富华严的。他们多认为美乃造物者之无尽藏,盈天地间滔滔皆是。这种观念的形成,与他们对天地山川的崇敬与感恩之情有关。相比于一般人,感恩意识强的人更能以一种悦乐的精神、欣赏的态度来看待一切,因而更容易对世界做出审美的反应。可以说,感恩意识强的人,必定是善于发现美的人。
(二)审美过程中的感恩意识
人在面对美的事物时,常会因一种自觉幸福的感受而进一步产生或强化感恩意识。以下择取中国哲学的万物一体观、比德观,来揭示审美活动与感恩意识的隐秘联系。
其一,万物一体观。据马斯洛的观察,凡是经历过高峰体验的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更具有整体性。人类是一体,宇宙是一体,诸如‘国家利益’、‘我祖先的宗教信仰’、‘人的不同等级’、‘智商的不同等级’诸如此类的概念不再存在,或者很容易被超越。”[1]61这段描述正合于审美所达成的物我一体境界,也正合于中国哲学所主张的万物一体观。
中国哲学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保持一种存在论的亲和关系。《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认为,在天地的呴育覆载之下,万物托寄于天地之间,万物生来并不是为了作对,本可以相安无事地并立而不对立。这是一种万类并生、各适其天的生命太和之境。“我”与他者共徜徉嬉戏于太和之宇,完成一次生命的共舞。①马斯洛论述高峰体验时,常引道家思想为佐证。总体看来,他对道家的理解没有什么大的偏差。儒家方面,北宋理学巨子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识仁篇》“浑然与物同体”都是为人所熟知的著名话头;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大学问》亦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9]
这种人与世界通而为一的高峰体验含有道德体认,同时也是审美体验。丰子恺先生甚至断言:“‘万物一体’是最高的艺术论”,“所以‘艺术家’不限于画家,诗人,音乐家等人。广义地说,胸怀芬芳悱恻,以全人类为心的大人格者,即使不画一笔,不吟一字,不唱一句,正是最伟大的艺术家。”[10]在万物一体的体验中,人们常会产生一种“源承神恩、三生有幸的特殊感怀”[1]269。
其二,比德观。在对天地山川等自然物象的欣赏中,中国古代存在着迥异于西方且影响至为深远的比德传统。比德是认为自然物的某些特性似若德性的显现,因而去欣赏它。孔子说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但为什么是这样?《论语》未言及,不过在其它文献里可征。《孔丛子·论书》:“子张曰:‘仁者何乐于山?’孔子曰:‘夫山者,岿然高。’子张曰:‘高则何乐尔?’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鸟兽蕃焉,财用出焉,直而无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无私,兴吐风云,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咸飨,此仁者之所以乐乎山也。’”[11]这里山被认为有着无私奉献的德性,因而对它充满了感恩之情。
再以天地为例。有学者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天为中为极的文明。”[12]这一论断颇为精到。古人谈“天”常连带着“地”,《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对天地乾坤的这种礼赞与欣赏,实蕴涵着一种发自深心的感恩之情。宇宙万物的生命都源于天地造化,所以天地造化是广义上的父母。在古人看来,天地造化不仅是人的衣食父母,还馈人以审美享受上的资粮。杜甫《题桃树》:“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王夫之《诗广传》卷四:“天不靳以其风日而为人和,物不靳以其情态而为人赏。”[13]抱持这种认识的古人,怎会不对天地万物感恩呢?朱良志先生指出:“中国艺术家对万物,对世界,几乎富有一种宗教性的情怀。”[14]深入体会可发现,这种“宗教性的情怀”也缘于对天地造化的一种感恩之情。
(三)感恩意识能推动审美创作
感恩意识也是推动审美创作的一种心理内驱力。《诗经》中《蓼莪》《凯风》之类的诗自不必说,而感谢知遇之恩的诗文在中国古代也是很多的。当然,我们不想谈什么感谢“皇恩浩荡”的作品,而主要结合古人对天地造化的感恩情结来谈。
青山本自媚,微吟酬物华。《文心雕龙·物色》:“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相召,人谁获安?”[8]566身处这个富美的世界中,人怎能无动于衷呢?怎能没有美的创造呢?我们不妨说,诗人和艺术家正是有感于天地之间的大美,才激起了将其泻落笔端的冲动。清初画僧石涛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15]在精神上与山川冥合为一,成为山川的知音,是“予脱胎于山川”;将山之精神、水之意思泻落绢素,是“山川脱胎于予”。山川絪缊之气象与跳荡之态势,激发着画家去代山川立言。
在中国美学史上,我们常可见到类似言论,如柳宗元《邕州马退山茅亭记》:“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闽岭,佳境罕到,不书所作,使盛迹郁堙,是贻林涧之媿,故志之。”[16]柳氏是说,茅亭所在本来即美(“佳境”),然非有识之士表而出之,则终将埋没,不为世人所知。柳氏前辈独孤及在《琅琊溪述》中亦云:“人实宏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游汉之涘,岘山寂寞,千祀谁纪?”[17]羊公指西晋名臣羊祜。据《晋书·羊祜传》所载,祜性乐山水,常登襄阳之岘山远望,甚至希望自己死后犹有魂魄登临此地。所谓“物不自美”,不是说物本身不美,而是说物本身不会言说自己的美,物的美期待着知己去发现、去表述。山水遇骚客,不异于士遇知己。岘山引羊祜为知己,岘山因羊祜而驰名。没有知己,便会空辜负眼前一片大好清光,无人能赏,也无人能彰。①清初张潮曰:“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独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渊明为知己,梅以和靖为知己,竹以子猷为知己,莲以濂溪为知己……”(张潮《幽梦影》,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中国古人多认为现实世界中触处有美,人需要做的只是去发现它、表现它。他们从未像西方美学那样去思考美在心还是在物、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类问题。
三、审美应成为培养感恩意识的一条途径
由以上分析可知,感恩意识与审美活动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它们之间还有一种相互促进的作用:前者是后者得以展开的一个辅助因素,后者的心灵转化功能或者说“兴”的功能又反过来巩固和深化前者。审美所以能够提升一个人的人生境界,一定程度上也缘于感恩意识的强化。
感恩意识淡薄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景观。感恩意识的提升需要教育。但是,如果直接通过说教的方式强行灌输,会很难奏效,甚至引起人们的反感,误以为教育者在市恩责恩。因此,我们需要另觅它途。笔者以为,鉴于审美活动与感恩意识之间有着交互影响关系,审美教育可以成为培养感恩意识的一条有效途径。遗憾的是,学界单言审美教育者比比皆是,单言感恩教育者更是不计其数,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者几乎没有。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有一种挡不住的力量。在真、善、美三大价值中,真和善本身并不一定惹人喜爱,本身就惹人喜爱的只有美。孔子感慨地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好色”可以理解为爱美,爱美几乎是一个人的本能反应,往往情不自禁;“好德”就不一样,往往要压抑本能。一个是本能的释放,一个是本能的压抑,要想让众人都“好德如好色”,当然很难。正因为如此,孔子主张借助美的力量来帮助实现道德的完善,此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同样道理,我们也应该尝试通过审美教育来提升感恩意识。美不是善的附庸,但美亦能助成善。审美活动的“善”就体现为提升人生境界。境界是一个人精神与思想所达到的高度,这种高度将指引他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当然也会影响到感恩意识的强弱。审美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审美的态度,而审美态度的非功利性有益于感恩意识的形成。美的发现以及物我一体的体验又会进一步激发感恩意识。另外,鉴于崇高感和道德感最相接近,崇高是最具伦理道德内容的审美形态,我们可以多让学生走近崇高、体验崇高,这将有效地唤醒他们沉睡的感恩意识。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只是提议通过审美来培养感恩意识,至于如何具体地开展,则需要我们进一步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