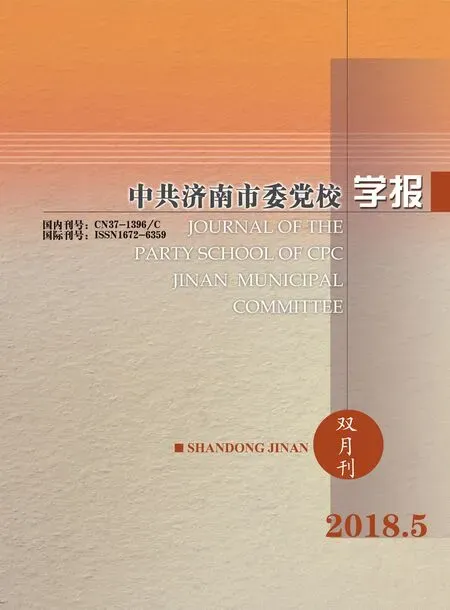浅析陶渊明诗歌的玄言成分
王立阳
一、独特个性造就隐逸情怀,隐逸情怀成就玄言思想
陶渊明的玄学思想大部分蕴含在他的隐逸诗中,他自身特有的性格以及归隐情怀造就了他的田园诗以及诗中的玄学思想。陶渊明在《命子》中谈到过自己的家族渊源,并赞颂自己先人的高尚品德,“於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是自己的父亲。他的祖父是曾作过武昌太守的陶茂,陶渊明赞扬他“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陶渊明的曾祖父是有名的东晋名臣陶侃,官拜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陶侃其人品格高尚,名望很高,“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功遂辞鬼,临宠不忒”,陶渊明很以自己的家族为傲,从曾祖父到父亲都保持了淡薄不以名利为念的高尚品质,不论从遗传还是家风,陶渊明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种特质,为他日后的归隐奠定了基础。
陶渊明少时所受到的教育是儒家思想,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中“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而儒家正是提倡“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陶渊明看来,自己身处的社会正是无道之时,也就是自己应该归隐之时。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他把关乎生命的衣食与涉及内心正义的道并举,突出在自己心中道的地位。可见儒学思想已经在陶渊明心中深深地刻下烙印,加之对先人遗风的珍视,这些都坚定了他对道的坚持以及对归隐的志趣。陶渊明笃信老庄,他能坚守儒家的道,亦有道家的虚静淡薄。种种因素造就了陶渊明特有的淡薄宁静、向往归隐的性格。后来陶渊明出任彭泽令本就不是出于本心,只是为了日后归隐赚些俸禄,折节迎见督邮一事使其对周遭的社会更加失望,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所想所要,坚定了归隐的决心,于是毅然辞官归农。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可见他的归隐就是他的性格使然,陶渊明的志趣不在于官场,而是在于有山有水之处、在于可以隐逸之处。
二、继承前代玄言思想,玄学观在诗歌中自然流露
玄学产生于魏晋正始年间,是以儒家思想解释道家思想的“玄远之学”。即不去探讨具体的道理和事物,而是追求精神上、人格上的玄远。[1]玄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就是玄言诗,因玄学主张从山水中探寻理趣,所以玄言诗客观上是描绘山水景色的山水诗。陶渊明和谢灵运的出现,是晋、宋时期诗风转变的重要标志,他们从不同角度终结了淡乎寡味的玄言诗。二人共同的特点是使诗中的理趣融合于自然,摆脱玄理的束缚,山水诗发展到此时才算是真正的山水诗,陶渊明田园诗的特色是平淡自然,在自然的笔触下将自己的精神与田园景象融为一体,体现悠远自得的意境。但是陶渊明的诗并不是完全没有玄理的成分,他的诗大多表达自己的隐逸情怀和隐居生活,不可能一点没有玄学的影子。相反,陶渊明的诗既摆脱了玄理的束缚,又深化了对玄理的体悟。在阐述老庄哲理和玄学的众多诗什中去寻找一位艺术上的成功者,这个人就非陶渊明莫属了。[2]陶渊明的田园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深刻体悟玄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自然风格。陶渊明诗歌最突出的风格是平淡自然,他很伟大之处,就在于诗中将玄理成分与田园风光完美结合,毫无雕琢之迹。萧统评价陶渊明诗“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
三、承继老庄清净隐逸之风,抒发隐逸情怀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玄学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人们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道家崇尚自然,玄学家们也倡导从自然中探寻理趣,所以隐逸之风一时盛行。当然陶渊明的隐逸不完全是受这个因素的影响,但他的隐逸诗总是多多少少地反映出当时的某些玄学思想。陶渊明对玄理的表述不是主动地、生硬地阐述老庄语录,而是将玄理与田园风光融为一体,丝毫不露雕琢之迹。“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第一句正是玄学倡导的那种清净自然的生活方式,第二句强调隐逸的最高境界“心远地自偏”,这正是道家强调的一种超然的隐逸心态,晋代王康琚之《反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就是阐述这个道理,真正的隐逸不等于隐居于有山有水之处,如果心中超然物外,那么居住在哪里都可以是隐居,东篱采菊亦体现诗人隐居的悠然自得与内心的宁静。此时与诗人内心相呼应,远处山林的云雾与归巢的飞鸟形成一幅和谐的景象,以至于陶渊明想要抒发这种宁静之趣却难以用语言表露。全诗散发出一种老庄哲学所倡导的自然宁静之美,虽然客观上来看,全诗像是描绘出一幅田园生活和谐景象的田园诗,但更像是歌颂隐逸情怀、散发着浓厚老庄玄理的玄言诗。
四、面对社会现实,思考生与死
魏晋时期人们的人生观与前代相比,发生巨大变化,战乱以及政治迫害是人们人生观改变的重要原因。魏晋时期的社会动荡极大地冲击了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儒家所倡导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努力提升自身修为达到“平天下”的最终理想。在儒家生死观中,生的价值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死作为与生对立的另一端却被忽略,即所谓“未知生,焉知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本主义,是儒家学说的唯一基础。[3]战乱使儒家贵生的生死观难以站住脚,死亡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玄学的生死观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的自然论,主张脱离现实以追求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另一种以郭象独化论为代表,主张每个个体都是对立的,各自封闭成一个小系统,只需脱离矜夸和贪婪,在有限的生命中体悟生活,陶渊明也正是这一类型。
陶渊明生于乱世,动荡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对当时的社会深恶痛绝,而以退居归隐来抵御社会的浑浊,但他并没有像嵇康、阮籍那样彻底归于玄远虚无,而是以真诚的人生态度对待时代的虚伪。他求安避患,抛弃“名教”,却又面对现实和人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4]陶渊明正视生的虚幻性,肯定死的必然性,“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连雨独饮》)。“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神释》)。在这些诗句中能看出来陶渊明对生死的看法以及对体悟自然的努力。现实的悲哀与生死的不可抗拒,促使陶渊明从有限的生命中寻找解脱的态度,既然死是不可抗拒的,所以索性以一种自然的态度坦然面对,“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对死亡的肯定使陶渊明更加重视现实生活的乐趣,他在《饮酒二十首·其三》写道:“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能看出陶渊明抱持一种达生贵我的态度,既然生命有限,所以他在处世之中更注重跟随自己内心,“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二十首·其八》)。陶渊明的生死观有着深刻社会历史性,社会现实与玄学思潮从不同角度影响了他的诗作。
五、注重精神自由,强调养生修为
魏晋玄学家出于保养身心的需要极力推崇养生。他们崇尚自然,追求身与心的调和以及服食养生,何晏就曾带头服食丹药。这一时期倡导养生的代表有嵇康,他在《养生论》中主张:“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只要节制欲望保养身体,清心寡欲就可以“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总之就是要顺应自然之道。与他的观点相反,向秀认为顺应自身的欲望才是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道,“且生之为乐,以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食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之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
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集中体现了他的养生观,他在《形赠影》中将草木与人对比,感叹草木可以冬消春长,但人只有一世,不相信有“腾化术”,主张“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如此看来他的主张类似于向秀。而《影答形》则体现陶渊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理,“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形”有消逝的时候,但是立功立言的“影”却可以长存,立下的名声可以在形体消逝之后继续流传后世。然而陶渊明的兴趣在于田园,对于功名利禄是不屑的,所以在修养精神的方面,更加注重自由,所以在《神释》中他表达了自己还是选择精神上的无拘无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对精神世界的要求与前代玄学家相比,陶渊明的养生观更加注重精神上的修为,而不只是像嵇康和向秀那样着重强调欲望的问题,陶渊明的养生思想与前代玄学家是一脉相承的。
六、直面理想与现实,抒个人与时代之悲
陶渊明本是“性本爱丘山”之人,由于生计或建立功业之心所使,曾几次出仕,他不愿屈从于种种与己相违的现实,所以总是在出仕与归隐之间徘徊。陶渊明受儒家影响很深,内心深处有着建立功业的出世理想,“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虽然魏晋时期原有的名教体系受到极大冲击,玄谈盛行,但儒家思想对士人们的影响依然深刻。陶渊明的独特性格与坎坷经历使他有意或无意地思考玄学中的各种问题,玄学一大主题是探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在个人与时代的交汇点上陶渊明不得不在“越名教而任自然”或是维护名教中做出选择,如果选择“越名教而任自然”则违背自己入世思想和精神,如果选择名教则又会“世与我而相违”。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可以顺遂自己内心的生活方式,两种思想占据着陶渊明的内心,即使归隐,他也始终对个人理想与社会有着深深的焦虑,他的诗中可以看到对事物变迁之哀思。与前代的淡乎寡味近乎说教的玄理诗所不同的是,陶渊明作品中玄理的痕迹大大地淡化了。一是语言艺术发展到陶渊明这里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备受诟病的玄言诗恰好可以在此时进行本质的转变;二是陶渊明的儒学思想根深蒂固,在诗作中与玄学思想中和,即使诗中蕴含着玄言,也是较为弱化的状态。
陶渊明早年有着强烈的功业理想,只是现实的黑暗使他极度失望,“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志欲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他心中的“道”难以实现,陶渊明心中难免有对社会现实的忧虑,这种忧虑加上自身的困窘又促使他向往上古传说中的理想社会。他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写道:“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陶渊明对人生的迁逝之感体现在自身垂垂老矣却一事无成之中,他一面怀疑自己“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贫贱”(《与殷晋安别》),一面又感到岁月已逝容颜易老,“市朝悽旧人,骐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岁暮和张常侍》)。“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杂诗十二首·其七》)。诗人对人生的变迁之悲很多体现在《杂诗十二首》之中,他的人生之悲有时表达得十分凄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同时季节的变迁亦使诗人生发感物之情,“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诗》)。日运月旋,寒风落叶,内在的迁逝之悲和外在的景候变化的结合,使得渊明同建安、正始、太康诗人一样,有物变惊心之感。[5]
七、陶渊明的生命境界与诗歌的玄言思想
在陶渊明的一些诗歌和辞赋中,多处表达对远古之世的深切向往之情,“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赠羊长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而辞荣”(《感士不遇赋》)。陶渊明的思想受儒家与道家的影响颇深,在躬耕田园的过程当中,加深了对道家所赞颂的原始社会和谐的认同,“黄唐”、“黄虞”、“羲农”、“轩唐”等都表示上古的原始时代。陶渊明有时在诗中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上古的向往,“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陶渊明对上古社会的向往之情往往简单又朴实,“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陶渊明向往上古社会的朴素自然,显然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陶渊明诗文中透露出来的这种慕古倾向,表明诗人对生命原初的真朴境界的追慕、对人类童年时代的向往之情。[6]可以说,陶渊明的思想虽然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双重影响,但作品中主要还是道家思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陶渊明的隐逸诗中多能看到玄言成分。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以宽广的情怀拥抱自然,在躬耕的农事中体悟远古先民的生活方式,他的归隐不是消极避世的归隐,而是基于理想,同时融会诗人对社会及人生的体悟从而做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他将永久地为后世确立一个躬行“安道苦节” 终极目标和营构出独特生活境界的人生范式。[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