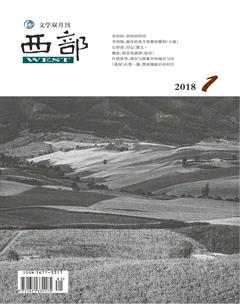权力的美学表情(外一篇)
张艳庭
颐和园,中国清代皇家园林,坐落在北京西郊,是皇家园林美学的集中代表。皇家所表征的是权力,而园林,主要表达的是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自由的自然观。两种思想体系本是矛盾的,皇家园林试图对它们进行统一与融合,让权力与自由进行协商。但两者并不是地位平等的协商。从字面上看,“皇家园林”中的皇家只是园林的形容词,园林是主体;但事实上,皇家对园林所起的不是修饰作用,而是统摄、限定作用,皇家才是真正的主体。因此即使在倡导自然的园林中,权力也不可能退场。颐和园就是这种“协商”之后的结果,看似两者之间的矛盾得以化解,其实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由此,产生了一种畸形的皇家园林美学。
进入园林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高大的太湖石。这块太湖石遮挡住的是更为高大的宫殿——仁寿殿,这是乾隆与光绪皇帝理政的地方。这样一座重要的大殿被一块石头遮住,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比如故宫。故宫中的理政大殿太和殿远远地就能望见,因为它是权力的最高象征,需要的是文武百官的景仰与朝拜,成为他们目光的中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权力的中心必须成为视觉的中心,这权力才能够得到彰显;而且须是仰视的,巨大的须弥座就是在确保这种仰视的角度。而在颐和园中,虽然仁寿殿也是皇帝理政之所,但它对权力的象征色彩已经变淡,它也不是举行官方仪式之所,一块秀美太湖石的遮挡,并不触犯皇家权威。作为皇帝私人的花园,它需要顾及审美。于是皇帝在办公之前,绕过一块山石,就成为了一个审美行动,而不会有损权力的威严。大殿前的院落中,同样在四面擎举着秀美的太湖石,虽然体量较门口的小,却更加玲珑端庄。不过与江南园林中太湖石略显随意的放置相比,它们有着鲜明的秩序,被方正的底座托起,矗立在相互对称的几个角落。即使在一座园林中,空间秩序依然重要,它们需要体现皇权的理性。空间秩序就是一种理性的表现。
而它们的对称也是对仁寿殿的呼应。中国单体建筑的对称之美在这个大殿上得到了完美呈现。这种对称同样是一种理性象征,可以从中国古典哲学强调的阴阳平衡中找到最初的依据。而作为皇帝理政之所,它的阔大并没有超出我的想象。即使在园林之中,它也仍然需要以宏大庄严来喻示皇帝的威权。乾隆和光绪皇帝曾在此理政,当然,还有慈禧。乾隆一朝营建的清漪园被毁之后,慈禧又在清漪园的基础上花费巨资修建了颐和园;她也是当时国家权力的最高执掌者。这是一个园林所拥有的双重历史。在这双重历史背景下,每一处景致都有历史的双重显现。如果说乾隆时期正是大清王朝的一个高峰,那么到了慈禧主政的时期,清朝已经内外交困。这两段历史,几乎走向了两极。它们的交错叠加,注定充满了戏剧张力。而这充满戏剧张力的历史,也让这些风景具有一种美学张力。
仁寿殿旁就是德和园。这座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戏楼,分为三层,都有华美的装饰,几乎将戏楼之美升华到无以复加。戏楼每一层都有它的名称:福、禄、寿。与其说这是为空间命名,不如说是空间对这些话语的配合;同时空间的高度也是一种规格的象征。建筑空间就这样迎合了权力的表述。这三层戏楼并不仅仅用来表意和装饰,还有戏剧的实用功能:戏楼各层之间有机关相通,可供演出上天入地的神魔戏。从这座专属于慈禧的戏楼的高大华美与复杂精巧中,可以看出慈禧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和对演出效果的挑剔。京戏虽然成形于乾隆时期,但却在慈禧主政期间达到鼎盛,成为宫中演出的主体,在社会上也声誉日隆。在电影《霸王别姬》等与京剧有关的电影中,“老佛爷”成为了较高欣赏水平的代名词。她既是权力的,又是专業的。两者的结合,成为了一种奇妙的权威,而这个“权威”所彰显的仍是集权时代艺术对权力的依附。
慈禧看戏的位置在戏楼正对面的颐乐殿之内。这的确是最佳的看戏场所,能够将戏台一览无余,但又因在殿内,在周围廊座内看戏的臣子们看不到她。这能够保证她在看戏入迷时产生忘情的举止而不会有失尊贵。这一个空间之中,权力和禁忌同时得到了保障。事实上,禁忌的产生正是因为权力,看台就是权力空间的集中呈现之地。大殿两侧的廊座是王大臣王子贝勒们看戏的地方,它们拱卫着中轴线,呈现出鲜明的权力秩序。
玉澜堂是光绪皇帝的寝宫。清漪园时期,这里曾是乾隆皇帝的书堂,嘉庆皇帝也曾在此办公。相较而言,这里不管是建筑规格还是摆设都无法呈现出皇家气度;作为皇帝的寝宫,也显得有些寒酸。这一方面是因为光绪皇帝当时并没有实质掌握最高权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戊戌变法”之后,这里成为了他的幽禁之所。而后者正是因为他威胁到了慈禧的利益。慈禧如果是真得推崇变革,那么对“戊戌变法”应该支持,但她却将它扼杀,将维新主将斩首,将皇帝幽禁。她其实只是想要能够被自己掌控的变革,不威胁到自己权力的变革。如今仍然留在玉澜堂的砖墙,是当时权力争夺的见证,也喻示着慈禧政治手段的强硬。在那几座相对低矮的殿堂之内,仅陈列了日常用品,保留了光绪被幽禁时的陈设模样。它们像一面锈蚀的铜镜一样,照见一个皇帝几近沦为阶下囚的悲苦时光。
玉澜堂之外,即是可以用浩瀚来形容的昆明湖。如此阔大的水面,让人顿时心胸开阔,眼界宽广。这种巨大空间是皇家园林的特色,是专制权力的标配,江南园林中几乎没有。江南与之相似的,就是西湖了。西湖并不归个人所独有,这昆明湖却是独属于皇家。只是有一个皇帝在自己帝王生涯的后期却享受不到这样浩瀚苍茫的景观,因为他失掉了自己的权力。这样的景观在帝制时代只能是权力的风景,自然景色与权力媾和后才能形成的风景。现代文化理论在论述“凝视”时把它表述为一种和视觉有关的权力形式,因为凝视与其他观看形式不同的是,当我们凝视某个对象时,目标是控制它们。正因为这种凝视的权力意味,慈禧阻隔了光绪对这面湖的凝视,因为它象征着颐和园,进而象征着皇权。就这样慈禧不仅剥夺了光绪皇帝的权力,而且阻断了他对权力象征性运作的尝试,最终阻止了他产生对权力的欲望。
当光绪皇帝于幽室之中面对砖石墙壁时,依然在享用这无边美景的是慈禧。慈禧居住的乐寿堂是颐和园居住生活区中的主建筑,南临昆明湖,背倚万寿山,东达仁寿殿,西接长廊,是园内位置最好的居住和游乐之所。相较于玉澜堂,乐寿堂可谓雍容大气,院内陈设也不同凡响。铜鹿、铜鹤和铜花瓶,取谐音为“六合太平”,精美华贵。古器物的象征色彩,在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正对着乐寿堂大门的山石体量巨大,横卧在院落之中,像一枚巨大的灵芝,名为“青芝岫”,是乾隆营造清漪园时放置于此的。它长八米,高四米,宽两米,重达二十多吨,似乎在彰显着乾隆盛世的辉光。据说石头最初的发现者是一位明代米姓官员,为运石而耗尽家资。后来乾隆皇帝见到此石,将之运往京城,安放在清漪园中。明代官员耗尽家产,乾隆轻易就将之运达京城,似乎不仅仅是皇权与官权之间的差异,还有时代的差异。清代由康熙开创的盛世局面到乾隆时代抵达高潮,同时也到了尾声。乾隆之后,清王朝就逐渐衰败了。这其中不能不说与乾隆后期的好大喜功、奢靡腐化有关。巨大的昆明湖就是在乾隆时期挖筑而成。虽然乾隆以汉武帝挖昆明池操练水军的典故,将此湖更名为昆明湖,但它与水军操演毫无关系,也不是利国利民的水利工程,而仅仅是用来供皇帝赏玩。它面积的巨大,与其说是用来满足皇帝巨大的审美胃口,不如说是用来装饰皇权的巨大审美配件,满足着权力的虚荣心。事实上它的巨大就像一面镜子,照到的不是无边风月,而是一个王朝肥胖臃肿的脸庞。
这块巨石同样是这样一个配件。据说乾隆为了把它安放在已建成的乐寿堂而破门扒墙。太后听闻,说:“既败米家,又破我门,其石不祥。”后人因此将之称为“败家石”。乾隆皇帝也的确是因为后期的奢靡而败了清王朝的家。在乾隆后期沉醉于奢靡享受之时,清王朝吏治日渐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乾隆后期不仅仅只有巨贪和绅一人,整个官僚体系都陷入了贪腐的泥淖。乾隆之后,嘉庆皇帝再整顿吏治、严治贪腐,也无法把清王朝从这个泥淖之中救出。
当许多年后这个院落传承到慈禧手中,她似乎也继承了乾隆后期的衣钵。她重修颐和园,就挪用了海军经费。当年乾隆皇帝以汉武帝挖昆明池操练水军的典故将此湖更名为昆明湖,慈禧也在颐和园昆明湖畔设立了一个水师学堂,而且常在湖上操练。但这更多只是个名分。后来这支在昆明湖上建立的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戰中全军覆没。这构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这个水师学堂的建立,不仅仅是因为大清统治者对大海的认识,只能以昆明湖的经验来类比构成——恐怕她也明白,湖泊再大,在海洋面前,也是小巫见大巫。只是她更愿意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为这种自欺欺人,清廷与海上列强们的碰撞,也像是湖泊与海洋的碰撞,其结果只能与鸡蛋碰石头相似。
慈禧又有许多与乾隆的不同之处。其中一个较大的不同在万寿山上的佛教建筑群中得到了体现。乾隆为了母亲六十寿辰在这里建成了大报恩延寿寺,清漪园也是孝敬其母孝圣皇后动用四百四十万两白银改建而成。这个园林成为了乾隆皇帝彰示其孝道的一面旗帜。在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重要治国手段的君主集权社会中,对孝道的弘扬显得尤其重要,皇帝的表率更是意义重大。在帝王之家,孝道不仅仅是骨肉血亲的情感表达,更是一种国家礼仪。但在乾隆以此园彰显对母亲的孝道之后,慈禧却在此园中完成了对名义上儿子的幽禁,并致其死亡。帝王之家的伦理道德在这种截然相反的行为中,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成为了颇具讽刺意味的笑料。这个充满了戏剧张力的颐和园故事,让这个园子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讽刺剧舞台。
慈禧在修建颐和园时,将延寿寺改为排云殿,这成为她居住和过生日接受朝拜的地方。这个愿意自比为“观音菩萨”、被称为“老佛爷”的人,却在这个园子中展示了她毒辣的政治手腕,成为令人惧怕的掌权者。这种双重身份标识构成了一种尖锐的矛盾,两者在历史的舞台上拼命厮打。她一个人就构成了一种尖锐的戏剧冲突,成为一出绝妙的历史剧。中国古代历史舞台上,充满了这种一个人的戏剧。乾隆皇帝同样是其中一出剧目的主角。这个被称为“十全老人”的人,对母亲极尽孝道的人,却也用文字狱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也造就了摧毁盛世的贪腐之风。这种一个人的戏剧,有时甚至比千军万马的厮杀还要激烈、精彩,也更令人震撼、感伤。
在这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发生地之外,颐和园的许多景观中也留下了权力的阴影。在乐寿堂通往延寿寺的路上,有一条长廊,长度应该是古代园林长廊之冠。与江南园林中的长廊相比,这条长廊显得冗长乏味。它不是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而是在湖边水平甚至是呈直线状地向前漫无边际地延伸。与其说它在彰显园林美学,不如说它彰显的是皇家礼仪的刻板与僵硬。另一方面,还因为它是这面巨大湖泊的配件,湖泊的巨大导致了它畸形的长度。江南私家园林总是向小处生长,在有限空间里进行内在的美学分裂与增殖,朱大可将之称为“细小美学”。而皇家花园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无限扩大着花园中湖山的面积,也扩大着建筑的体量,营造着一种“硕大美学”。这种硕大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导致许多时候物的象征意义突破了物的形式限度,成为一种畸形美学。这条长廊即是这种畸形美学的典型代表。工匠们又在努力弥补着这种畸形美学,努力调适着权力与自然的冲突。长廊上的彩绘就是对它美学缺陷的一种弥补。有些体量硕大的建筑物对人的压迫感,也在整体空间环境中得到了缓解甚至释放。由此,美学缺陷也得到了弥补。佛香阁就以它硕大的体积成为一座山与一面大湖之间的视觉支点,是这两个自然景观的人造对应物。如果将它放在闹市之中,无疑是不和谐的。但置身于空旷的湖山之间,它的硕大被山水化解,不再显得突兀。
十七孔桥一定程度上也与佛香阁相似。如果与江南园林的中的小桥相比,它显得过于冗长硕大,但巨大的湖水面积又在绝对比例上将它缩小,也提供了远观的视角。桥本身的孔洞也化解了这种呆板,让十七个圆孔承担了它的美学功能,让它的功能性、象征性与艺术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融合。
园林的建筑工匠就这样费尽心机,用建筑的形式美化解了其上附着的意识形态的沉重与笨重。这其实也与整个建筑群落的语境有关。如果说那些单体建筑都是一句句话语,那么园林便是这种话语的语境。从功能性的角度来说,园林的休闲审美功能是大于权力表征功能的。虽然皇家园林首先是权力的表征物,但建筑工匠努力美化修饰它们,使权力与审美获得了统一,为帝王提供了精神的放松甚至对权力的短暂遗忘。它们成为帝王的精神调节装置,试图确保僵硬体制中的帝王的精神健康。在这样的功能定位之中,园林的权力与自然得到了相对有效的协调与融合。有时候审美成为这些建筑表面上的意识形态,而权力表征则成为这审美荫覆之下的暗流。在当代的时间链条上,这种园林语境更加凸显。所以,当代游客在脱离权力语境之后,可以不顾及甚至忽略那些权力因素,将之视为纯粹的审美对象——虽然还有很多游客是以对权力美学的崇拜来观看那些风景的。
从这个视角和当代的语境来看,园中景物的美学意义更加突显了出来。与那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相似,园林中的风景本身也充满了对比,以及由这种对比所呈现的美学张力。颐和园的多处景色都有鲜明的对比,但这种对比在我登上万寿山之后达到了高峰,也让我遗忘了这园中似乎无处不在的历史。我抵达万寿山时,山下的寺院已经关门。我绕道拾级而上,想去看能否近距离看到佛香阁,却撞到了智慧海。事实上,是智慧海撞到了我。这个镶满琉璃的宗教建筑,让我见识了一种宗教式的华美。它的屋檐处遍布斗拱,却看不到一根木头;它总体上是一座中式建筑,却又充满了藏传佛教建筑的独特气息;它既神秘,又恢宏;既灵巧,又厚重。这几乎是中国古代砖石建筑的一个代表。它自身的这种对比,还不足以达到对比的高潮。我上到它旁边的山石之上,看到了高墙后的佛香阁。这是我最近距离,也是不用仰视就能看到的佛香阁。它用八面三层四重檐的构造向我展示了一座如此高大的建筑如何拥有玲珑之美。同样是佛教建筑,如果说智慧海几乎穷尽了砖石结构建筑的美,那么佛香阁则几乎穷尽了木结构建筑的美。与佛香阁相比,智慧海的所有轻盈都变成了厚重;与智慧海相比,佛香阁的所有厚重又都变成了轻盈。如果真的用轻盈和玲珑来形容佛香阁,那么这两个词语里所含的所有贬义就都被剔除,成为对一座木结构建筑的最高褒扬。这也是中国古典建筑美学的对比。这两个建筑单独来看,虽然都有各自的美妙,但一经对比,就仿佛把各自的优点放大了许多倍。分别看时,它们只是自己;把它们放在一起看,一座园林的美则张力十足地呈现了。而这座园林美的张力在佛香阁上呈现得更多,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它与昆明湖之间构成了一种视觉张力,它与万寿山之间也构成了一种视觉张力,对皇家园林的硕大美学进行了矫正与修饰。
夜色真正地降临,我才离开山石,顺着林荫小路走下山去。山下同样是景观的森林,更是历史的森林。纯粹的观景之感性又渐渐被历史的理性排挤。我想绕湖一周,却无法绕过渐深的夜。我的脚步终止在玉带桥上。在它高高的桥拱上,我看见的是现代北京的灯火。那是这些历史风景的背景。晚上九点钟,我从这些历史风景中,走到了它的背景里。走出颐和园,它的大门关闭,把我深深地关进了现代社会中。
紫禁城的权力阴影
我是在一片阴郁的心情中走入故宫的。如同当时阴沉欲雨的天空,我心头的乌云也长久没有散去;我在午门前站立了很长时间,阴郁的心情并没有散去。如同专制皇权已经倒塌百余年,权力所塑造的忠颜媚骨、勾心斗角以及奴性意识等等都没有逝去一样。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时时刻刻上演着权力争夺的戏剧,各种微观权力也被这种意识染指,甚至人生的价值也被定格为权力争夺的输赢,成王败寇的文化传统千年流传,仍然不衰。许多时候,这种争斗,只要参与,就已经失败。
这里曾是权力的最中心,也是权力的文化表征集大成之地。在这里最能够感受到权力的荣耀,也最能够感受到权力的文化塑造以及如何作用于人。
午门依然高大、华丽、威严、端庄。这个紫禁城的正门,建筑样式是中国古典大门体系中最高等级的。整个城门平面呈凹字型,正门两侧凸显出来的部分,就像是古代阙的变体,但却用高大的城台将阙与门连在了一起,保持了一种对正门的拱卫之势。曾经的礼仪建筑拥有了防卫功能,对人的威摄也得以加强。正面城楼为黄瓦庑殿顶,面阔九间,呈现出端正庄严的气势。东西城台上为庑房,形如雁翅,也被称为“雁翅楼”。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精致与繁复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午门“五凤楼”俗称的由来,虽然主要是因为它如三山环抱五峰突起的形状,应该也与木结构建筑的特点有关。凤本来就是多种鸟类形态、色彩的叠加与组合所构成的图腾,而木结构建筑能够表达精巧的叠加与组合;这种经过组合后的精巧与繁复仍然显得轻灵,于是“五凤”“雁翅”这样的称谓便格外恰切。城台使它有了最大程度的坚实之感,也是它的防御功能所在;台上木结构建筑则又巧妙地修饰了这种功能,让它成为了一种反修辞:表面上看来,这高台仅仅是为了抬升那些木结构建筑的高度,让它们显得更加庄严威风。它们在实际防御中功用并不大,却成为视觉的中心。
从一个现代游客的眼光来看,它的造型体现出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巨大魅力。作为一个现代看客,如果稍加联想,也许会想起“推出午门外斩首”这句民间古装戏台词。虽然这里并不是真正常规的斩首之地,但在那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人们进入这象征着最高权力的空间仰望这宫门的一刻,已被专制的威严斩了首。个体在这里显得渺小,不仅仅在肉体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精神方面。
走进宫门,巨大的太和殿广场呈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广场的巨大一方面是因为这是皇家礼仪举办之地;另一方面,也是对太和殿的一种烘托。因为广场的烘托,太和殿不仅显得高高在上,更显得它所俯瞰以及统摄的范围之大。这正是权力所需要呈现的空间距离和范围。只有太和殿能够拥有并驾驭这个面积巨大的广场,正是对它权力性质的建构与说明。这个广场也就成为了太和殿权力的空间证词。
我对太和殿广场最初的印象是从电影《末代皇帝》中得来。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获准进入北京紫禁城实景拍摄的电影,影片中紫禁城的场景都为实地取景,最大程度地还原了这个独特空间的权力意味。电影镜头里,溥仪登基大典时,广场上站满了太监、兵卒,场面壮观而辉煌。太和殿高高俯瞰着他们,通过对人的凌架,皇权的至高更得以彰显;这座大殿置于所有人仰视的目光中,皇帝的威仪就得以彰显,即使这个皇帝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这正是太和殿的视觉权力美学。这种视觉特征还被种种手段加强,较为显著的一点是:它处在故宫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中心的位置,让人的视线自然聚焦到它的身上,两旁殿阁的作用也像是在彰显它,突出它。空间与人的关系,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如果再将这空间置于特定的时间维度中,更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我站在广场上,看到脚下的青砖早已风化,大大小小的坑洼遍布其中,甚至有野草在风中摇摆,一种荒凉感爬上了我的心头。真正荒凉的是历史,这个空间一个独特的维度已经永远地向人们关闭,唯一能作见证的,只有这腐烂的砖头。
走过一座桥,就走向了权力这个概念曾经登峰造极的太和殿。大殿依旧辉煌,依旧那么高高在上。巨大的木柱擎举起高高翘起的屋檐,走到近前,人的渺小更为彰显。太和殿能拥有这样的高度,不仅仅因为擎举屋顶的木柱。中国木结构建筑受建筑材料的限制,往往无法修建太高。为了对这个缺陷进行弥补,工匠会先在下面修建高台。太和殿就座落在须弥台上,拥有了一个更高的相对高度。
事实上,这座大殿不仅高,宽度也超越常规。它开间多达十一间,为古代建筑之最。这个宽度,不仅仅是为了实用,更是一种严格的权力表征。在帝制时代,建筑开间是一种严格的规范。官员修建住宅,不能超过七间,百姓则不能超过五间。超越这种界限,就被视为对权力的觊觎。清代臣子和绅被赐死的罪状之一,就是“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樣,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
古人用“法式”来表达建筑规范,表明了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规范。建筑空间的大小,不仅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受到权力和律法的严密监视。这种“空间立法”成为一种空间垄断,也保证了权力的空间特征。空间的社会属性在帝制时代成为一层坚硬的膜,紧紧包裹着它的自然属性。
这个大殿用来表征权力的,不仅有空间的高低大小,还有建筑样式。太和殿殿顶为重檐庑殿顶,是清代所有殿顶中最高等级的顶式。庑殿顶本有五脊四坡,将殿顶空间分割开来,已显得端庄又繁复;重檐庑殿顶在庑殿顶之下,又有短檐,四角各有一条短垂脊,共九脊。九脊为所有古代建筑物殿顶中脊数最多的了。九脊的数字也带有象征色彩。古人认为,九在阳数(奇数)中最大,因此,常用“九”表示“多”,也含有最尊贵之意。“天为九天、地为九洲、月行九道、日有九光”中的“九”也都代表了多的意思。但在太和殿的空间装饰中,“九”还不足够表达这种多和相应的尊贵。在中国古建筑的岔脊上,一般都装饰有一些小兽,这些小兽有着严格的规定,按照建筑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不同,装饰物越多,建筑等级越高。皇家建筑檐角的装饰物大都为九个,太和殿的檐角的装饰物却达十个。除了鸱吻、狮子、海马、天马、狎鱼、狻猊、獬豸、斗牛、行什之外,还有一个骑凤仙人。这种巧妙的数量逾越,使太和殿成为唯一檐角有十个饰物的建筑,拥有了一种超越性的至尊。经过这一系列空间规训和加持,太和殿终于成为了帝制时代中国最尊贵,对权力象征达到极致的空间。
要抵达这样的空间需要登上层层台阶。仅仅是台阶不足以表现这个空间的尊贵,还要有相应的装饰:这些台阶中央丹陛上就浮雕着腾云驾雾的龙。这是曾经皇权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图腾。这种重合让我感到错愕,由此想到权力的阴影不仅覆盖了这个国家曾经的疆土,甚至也覆盖了整个民族的心理。龙在石头上飞得潇洒飘逸,却又勇猛有力。这是这个民族真实的心理象征吗?不是,在专制皇权的阴影下,百姓一辈辈地苟活,对一个人的基本权利都不在意。几千年里,无数底层劳苦大众所想的只有三个字:活下去。而这龙真得完美地象征着皇帝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早已被皇家独占,成为皇权的表征,得到了整个文化系统的辨识和确认。但在真正的历史中,这个表征符号的内涵和外延却不断产生着冲突。清王朝虽然曾经谛造过康乾盛世,但随后的贪污成风、衰颓腐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也出自这些真龙天子们之手。电影《鸦片战争》最后一个镜头是道光皇帝跪在列祖列宗的牌位画像前,门外大雨正在冲刷着一头张牙舞爪、怒目圆睁的狮子。与这个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有人把当时的中国比喻成一头睡狮。权力的跋扈狰狞,与民族的沉睡不醒,这些象征与它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一种充满反讽的对比;甚至不只是对比,而是有着进一步的因果联系。而在这些权力象征符号包裹的背后,藏着的其实更多是残缺或孱弱的人。游客们还在欣赏这潇洒飘逸、勇猛矫健的龙,也欣赏这孔武有力、虎虎生威的狮子。对于蜂拥在这个昔日皇宫的游览者们,这些似乎都褪去了历史的印迹,而仅仅变成了一种雕刻艺术品或者文物或者是历史八卦的实物证据。
太和殿敞开着大门,皇帝的宝座虽然仍在,但已没有在上面端坐的人。在阴暗的大殿内,我恍惚又窥到了历史的原貌:一个永远高高在上的人,下面是整整齐齐几排低着头的顶戴花翎。这是权力一词最生动的原型。然而另一个场景却又不断地在我脑中浮现:电影《末代皇帝》中,奄奄一息的慈禧太后坐在仪鸾殿中,大殿一角的锅中煮着一只巨大的乌龟,有太监将巨龟的汤喂慈禧喝下,最终慈禧咽气,太监将一颗夜明珠塞进她的嘴里,大殿内外的人们开始哭泣。在故宫想起这个场景,依然有震憾之感。这个依照权力语法构筑起来的建筑空间,其堂皇与美奂都是在神化权力,更是在神化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慈禧虽然没有当上皇帝,却是当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神话所构筑起来的只能是神,“神”的死所产生的就是神话崩塌的效果,神话空间仿佛也随之崩塌。慈禧临死之前,让溥仪当大清嗣皇帝。而在她死之后,小小的溥仪还是跑到父亲那里说要回家。他不知道一旦成为这个权力神话的传人,就要住在这个神话空间里,被它神化,被它禁锢,无法再拥有一个孩子应该拥有的生活甚至亲情,因为他已成为天子,成为“神”。而一个人被强行升格为神,只能是人的悲剧。溥仪的大半生都是一个残缺的人,虽然这与那个时代有关,但也说明,这种神话的真正覆灭,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制度,还有人们意识的解放与觉醒。
一路走下去,中和殿、保和殿,一样地宏伟壮观、金碧辉煌;乾清宫、坤宁宫,一样地富丽堂皇、庄严肃穆。卡西尔在阐释神话空间时,说到神话空间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结构的同一性。卡西尔所说的神话空间就是紫禁城这样的象征空间。而紫禁城也是中国古代象征空间发达的一个典型例证。因此,这些宫殿虽然大小不同,功能不同,却都与太和殿有结构上的同一性。
不同的是,我抵达时,却听到那些同样金碧辉煌的大殿之上,有乌鸦的啼叫声不断响起。在这叫声中,苍凉、荒芜之感仿佛大雨一样淹没了大殿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丝瓦檐墙缝。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仿佛一茎立于秋风中的枯草。是的,象征着权力极限的宫殿早已在历史中倒塌,留下的只是它美学意义上的存在,只是历史的一纸证据。
坤宁宫之后,就是后宫了。大门两侧的墙壁上有美仑美奂的浮雕,但不是象征权力的龙,而是花卉。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在生活面前也是会放一放架子的,但不可能全部放下。后宫门前有两尊狮子,与其他狮子相比,没有一丝狰狞之意,两只耳朵朝前方垂下,竟像是狮子狗。这个动物形象从狰狞到温顺的转化,似乎暗示了权力意识的弱化,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后宫与前朝相比,最大的不同也许是,偌大的后宫只有一个男人,那就是皇帝。而要从这两只狮子中间进入后宫的,多是妃嫔、秀女、宫女。这两只狮子的作用,就是告诉她们如何学会俯首帖耳,即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国古语中有“后宫佳丽三千”,三千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来概括皇帝所拥有的女性数量之巨大。这三千女子的俯首帖耳,证明了皇帝所拥有的庞大的性权力,而这正是极致皇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面对大臣和子民,皇帝还把他们当人看的话(虽然有着等级差别或主奴之分),对这三千佳丽,则有更大的物化意识,她们变得更加工具化:这只是三千个身体。如果说对臣子百姓剥夺的更多是政治权力,对这些女子们,剥夺的则是个体幸福的权力。相较于前者,这种剥夺也许更为彻底。
到御花园,我的心情稍微缓和了。美是永存的。自然经过人为的搭配,形成了美丽的园林景观。藉由自然,那些妃嫔们甚至皇帝在这里也感受到那种人天性中的自由吧。虽然这自由是短暂的,但也弥足珍贵。在这花园中,不再那么等级分明,也不再那样遥不可即地高高在上。有一座假山和上面的凉亭是高高在上的,但有通向它顶端的石阶。凉亭的开放性,也不会使人联想到专制,因为专制必然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这也是太和殿为什么不会四面敞开的原因之一。这种开放性,不光体现在这假山上的凉亭里,也体现在其他建筑中。它们的开放指向的是自然事物。不管是水、天,还是植物花草,真正的自然是讲求平等的。能在这自然之中感到放松(这正是花园的功效),也许正是因为人最自然的状态是一种平等平和的状态。人与人平等,人与万物平等,但花园所揭示的这一真理并不是弥足轻重的,就像花园本身也只是庞大的等级森严的宫殿群的附庸。它的作用只是缓解森严等级给人带来的精神压力。尤其是掌权者本身,在缓解之后继续投入这压力而乐此不疲。
这精妙绝伦的花园本身也是权力的产物。正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召来了技艺最为精湛的工匠,召来了最珍贵奇特的花草木石。这是为极权所打造的自然盛宴,体现了中国园林文化的精髓。关于中国古典园林,我曾在书中看到过外国人的两种评价,一种是精妙绝伦,一种是矫揉造作,后一种观点认为它想用人造的自然来代替自然本身。用这一观点来看待这个御花园,也是非常贴切的。它虚拟了一副自然的面孔,固然这面孔很美,但也并不是真正的自然。自然本身是人造物所替代不了的,就像綿延了几千年的专制权力也不能抹杀人类的本性。当时间穿越无数个朝代来到现代,虽然对权力的崇拜仍然有很大市场,但独立与自由精神越来越成为更多人的共识和追求。曾经被故宫征服、现在又对它进行批判的我,也经历了一个被权力征服、又对它进行批判的过程。
游览结束,我走过步道,走过台阶,走过长长的门洞,走出了紫禁城的大门。真正要想从权力的阴影下走出来,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再次回望那辉煌却又衰朽的宫殿,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