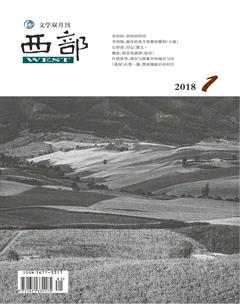程川的诗
程川

春雨
真好!夜色具体,黑暗弥散开来
还有一盏灯,悬在窗户旁,面朝春天淋不熄的寂静
沉默着,一株海棠的敌意
渡
日子渐渐淡了,需要解释的地方越来越少
很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坐着
枯木一样,不值得思考的东西越来越多,除了年轮
我体内已不再有多余的眩晕
拷问
凋零,浸没在冬天的景象里
犹如一段弓腰驼背的山坡,顺着清瘦的弧线
渐次滑翔
尔后,我把视线缓慢挪向一株废弃的荒草
在此过程中
尘埃扬起,没有理由
只能是
一阵风,推翻了我的想象力
沉沦
为什么还在沉沦,写不出来的那首
替我在尘世坚持着什么?
为什么还不肯舍弃,这缥缈的虚无,决绝和你所偏执的孤独
止不住堕落;为什么闭眼后,黑,还亮着
这翻来覆去的人间,对光明盯久了,也会有眼泪砸下来
火车记
攥紧拳头,扭向窗外
夜色中的南京,旧烟囱,民房和稻田……像他面前的画板
闭着眼睛,空,还能看见什么?
多年的流浪生涯
时至今日仍害怕
安定,一个被强拆反复蹂躏过的词
肃穆时,可以听见纸上悲怆的哭声,潮湿、阴冷
这一阵阵的梅雨时节!
他用一张车票,将自己押解至异乡
我没有向他提及画家梦
就像古典技藝中的留白,在北京西,戛然而止
武汉行
逛晴川阁,户部巷,黄鹤楼,寄明信片
顺便摸了一把长江
没能够抓住她的魂魄,满手的尸体
是死的
是我曲折往复的少年,穿过鄂西北层层隧道
饱受黑暗和光亮的一次次剥削
最终遗留下来的
——既不是荷花,也不是垂柳
当你咬住嘴唇,轻轻戳破那个词时
瞬间的电击,譬如昙花一现
是痛的、青春的。有关小学课本中谈及到的
有时叫它历史,有时却是诗歌
有时是一个地名,这辈子就只去那么一次而已
乙未年中秋的那只萤火虫
在那所偏僻的乡村实习中学,一只萤火虫
悄悄潜进了同行女生宿舍
她们惊讶这卑微的光,对黑暗的领悟,还是透明的
像是熄灯后,被窝里毛茸茸的窃窃私语
久居省城的她们,自然感到新奇
提着一只萤火虫蹦到男生宿舍
向我们展示她们的发现:一只斗志昂扬的萤火虫
正率领着秋天向事物深处缓慢滑去
亡灵书
电击而亡的小纪,老婆将他葬在高高的信号塔下
据说,可以接收到死亡讯息
在这惨淡的人间,亡夫抽走了她体内的平衡
之后,总有人习惯背地里喊她:
寡妇、遗孀,乃至婊子
好像她身体里有烂的成分,还未经过缝合
亟待拱破夜色,慢慢溢出来
那些不怀好意的石块
纷纷打着投石问路的噱头
叩打着她紧闭的门窗
其实她早已千疮百孔,百口莫辩
像是那张过期的结婚照,在褪了色的爱情里
每天和衣而睡,她与自己为敌
遐想
此时,还有多少景致即将被夜色吞噬
玻璃帷幕,盛水的池塘,酒瓶,寻人启事,黢黑的左脸
挣扎的光线只需扭动一下
世界便可重返安静。熄灯之后
建筑工地的男人们簇拥在狭小的相框里
多像一座搁浅的坟墓,耗尽一身磷火,总也无法点燃这大面积的寂静
夜未央
已经很安静了。窗外嘶嘶作响的空调
筒子楼里渗漏的美声独唱
成都北一环沙湾铁路新村,抚摸我食指的香烟,拼命往三楼漫漶
已经很安静了,秋菊、细叶榕、爬山虎
纷纷停止摇曳,可我还醒着
翻箱倒柜,为了追查那枚使我重新回到我体内的安眠药
我匿名,让一场躲在黑暗里的雨,合上身体里的闪电
比如,青海
很多地方还没抵达,比如:青海
地图上的空旷,小于一个省的慈悲与信仰
比如:牧场。一匹打着响鼻的马
把蹄子伸进草原的心脏
比如云朵,伸出太阳
天空,在一只鹰的翅膀上搁浅
比如:二十四个小时的车程
闪电和雷声回应着孤独,唯独雨声在窗外走着
白天惦挂的母亲,今夜一片死海
默念及发呆
栖息在枝头的暴雪弹奏着万籁俱寂的寒冷
空旷,正在发芽——
一只不合时宜的寒鸦向后
让出了整面天空
而田野里,欢腾的麻雀不时用喙挑拨着
这由来已久的孤寂
很长时间没有到雪地里走一遭了
黎明前,趁着昏暗
由着性子的风推醒了火塘里嗜睡的火苗
我摸着那些明灭可见的温暖
从泥泞的远方,慢慢伸出了一条蜷缩的羊肠小道
冬日与父母在火塘旁
青冈木坚硬、熬火……
欲盖弥彰的留白,逼我们掏出寒冷的供词——
这一年的聚合别离
仿若坐落在盆里的灰烬,风干的体温
等待一把铁钳重新撬开
战栗的火光
更多时候,我们攒聚起熄灭的过程
在穷途末路的话题中
翻捡那些不肯自焚的沉疴
烟雾填补了局促的空间
沉默、假象……通通露出孤独的本质
面对尚未走远的严寒
我有足够的耐心,倾听他们身体里衰老的细节
就像一截喂进火塘的木头
发出“呼呼”的呜咽声——
燃到尾声的火苗
始终以咳嗽声回答我:寂静过后
突兀的事物各有千秋
访连城山
那些没忍住招安的枫叶
纷纷落草为寇,长成秋天的气候。远山孤高
对于山顶来说,我们在时间的褶皱里
东躲西藏,亟待认领一条
隐匿于未知的歧途
朽木填平了皲裂产生的聒噪
仿佛藕断丝连的杜仲
拉长的灵魂使我深信,枯萎的源头一定埋藏着一口
不易察觉的深井。渗水的命运
沿着腐烂的方向
修正自己的不堪和困顿
而挂在枝头的几枚秋叶
被天空领读着,经幡一样猎猎作响
暗下去的时间构成某种宗教
在这秋日的原野上
压抑着体内金黄的火苗。温暖
有了片刻的柔韧,好似夹在书册中的往事
撕咬着,一页无辜的纸张
暮色过柯寨
菜地里,几根木棍支撑起倾斜的光线
黄昏慢慢漏下来
滴在合拢的那本书封面上
故事有些斑驳,他写到母亲的失踪,就像这样一个傍晚
星星还没有升起来
大地像是一张撕裂的布匹
骨头里有缝隙溢出来,挽成一道不规则的边界
那条通往县城的公路随之模糊起来
浮在瓦砾上的余晖
抽空了她细碎的等待
在等身后镂空的声音吗?带着滚烫的哭腔
沙哑,焦急……
像风按住扬起的尘埃,平静
微微荡漾
多少个傍晚,只敢蘸着月光读这一页
凉凉的,“自此,再未相逢
而这么多座热闹的城市,她究竟流落何方?”
没人给出答案
抬头时,黑,棱角分明
青山守着沉默的轮廓,她有起伏的美
也有黯淡下去的忧伤
密林深处
砍伐声时常从青冈林递来
铁锯深入浅出,毗邻成年的位置,是生活的横截面
百十年光景,早已立地成佛
如今,却在刽子手的威逼利诱下
吐出淤积的骨屑
身材姣好的视为椽梁,以顶天立地的姿态
改变命运;次之为桌椅板凳
经过斧劈、刀凿、打磨、抛光……
为人类鞍前马后
剩下的多半良莠不齐,被火炉和造纸术瓜分殆尽
沦为灵魂的殉葬品
多年后,当我在纸上划下:疼痛、温暖
那些熟悉的符号,陌生的感受
汇聚、逗留,继而又马上分离
就像一次未遂的出逃
我先是失败了自己,后来便是对故乡的认知:
在纸张尚未变成命运之前
那些真相,总是与轮回保持着很远的距离
我将对我的生活持否定态度
思想里有怎样的崎岖,才能统治着失眠
和平年代,调色板上的主义
还是粗粝的生活。这是一个大词,鱼钩一样
扼住咽喉。得谦虚谨慎,战战兢兢
得折断身体里的钙
沉默,提著衣领走上天堂
得在照片正面乐观,背面空荡
得永不褪色,就像这每晚降临的黑
就像这黑里四面楚歌的哀嚎
倘若春天尚未到来,我将对我的生活持否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