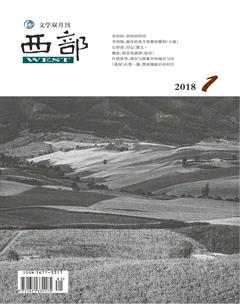马骥文的诗
马骥文

练习
——给马小贵
致伟大的羞怯与一切圣光
二十六岁,他以残缺对抗完美
当众人银色的背影徐徐隐没
在初雪后的海边,他发现
自我即挽留,那永久的有限
使黄昏的天空弥漫赤雨的光晕
无数的你走入那道渺小的闸门
又一次会面,你发现自己的舌根
因赞美而颤抖如一把明亮的焰火
在空旷之穴,他无法与绝对之光的
显现交汇,更多的翅膀飞走
而后,“他以自身抨击自身”①
你正变得完美如轻盈的海面
在人群之中诱引那些迷人的星点
积聚成另一座纯洁的系谱
但他并不怨恨这如野草的告别
像落难者手中的暴雨
正与那隔世洁白的石镜契合
在我们并肩散步的冬季田野上
更多丰盛而巨大的神秘之物在生长
“也许我追求的就是消失。”②
那孕育过他的生的开阔,此刻
也在孕育着他的死
①出自马雁《天赋》。
②出自张承志《心灵史》。
炉火
不存在完美的背影,折叠的光束
在他漆黑的手臂上跳跃,如夭折的灰雁
“永恒的法图麦,那雪中扑簌的是什么!?”
无辜之人挺立在天际,伞状的语言飞入
一座遗忘的城市,死亡啊,他浮动的心
没有人——没有人可以关闭那道坠落的闸门
我们在有限中弥散,比如蓝藻般的饥饿
滑入你银勺的耳:幽闭之人在暮光中咯血苏醒
除了父亲的睡眠,日渐稀少的
还有雪的强硬,一切都晚景般碎裂
你说,让我们拥抱吧!并沉入这萤火的夜色
让我们沉迷在爱的细沫,与陨落的梦
请擦亮它,爱人,在这星球的火焰上
学习它,抚摸它,并折损它
大门被打开,他走入其中,消失在强光内
如一道玫瑰的凝视,在海边忘记所有的不安
这狂野之心,呼喊弥赛亚的喉咙是金黄的虎
细浪似的,给我,一个颠倒的星系
还有什么是在黄昏变得寒冷?
忘记它,抹平它,让它连同翻涌的罪感睡去
顺着炉火的指引,走入一片圆形之地
渴望!什么在分裂这无限的爱?
并使更多的你冲向宿命的暗石,火花般飞溅
鸽群
你常常闪现在边缘之地
手中,是漩涡般的星云
二十七年,你在风中一次次
扼倒,又细雨般苏醒
就如此时,你看见一大群灰鸽扑入
你的心,并射穿它
在那些未完成的瞬间
仿佛一切都因为这爱的渴慕
而变得明亮如银
你拍打着它,亲吻它
并把那冷却的事物
重新赋予雪崩般的颤动
它们从一个白昼飞入另一个白昼
并将那彻夜的雨季赠给你:
低沉而金黄,泛着众人的容光
而那在消逝中擱浅的,将
把你引入一道更阔大的缝隙
在无限的折射与翻涌中
不存在海浪的吮喋与呼告,而只有
迎面如暴雨的振翅和星辰的簇生
焰火
美使我们合为一个。傍晚的爱人
拥抱在辽阔的星空下,将夜的余温
降临给对方。四月之火,在暗暗的
传递中发出年月般持久的光柱
并提升着他们中的每一个
似乎,唯有寂静才能让我们变得洁白
你注视那瞬间的事物,迷人的碎裂
正把更深的爱引入你的手中,如狂泻之雪
而什么是抵达?不可能的才是真实
除了你,在颤动、节制与熄灭中
照亮我的将属于另一种完美的例外
此刻,飞旋如命的火花
在空气中涌聚着你我的激荡与消亡
可它仍是美感,与每一个被它所引照的人
交换着最终来临的形式和词语
在瀑布般的未来闪现为诗人的荣耀
叙利亚之死
辩士与诗人会从伊德利卜来看我们吗?
又一个晚上,月光陷入一场古老的敌意
在四月的云端,致死的迷雾把目光
从一个优美的黎明夺走,并留下罪恶的吻
叙利亚,连火也泛着耀眼的绝望
熄灭在白昼的人,手持乌黑的无花果
在土地上闪烁着只属于死亡的荣辉
一个人,该如何拯救自己?
并使生命不再成为那持续陨落的一瞬?
从阿勒颇到大马士革,流亡的幽灵
第一次拿起笔记载自己的历史,血与泪
在阿拉米人的古道上喷涌,像节日和信仰
为什么?无数人在问,无数人在死
可是,海水托起阿丹的子孙
他们的面容却永远隐没在灯火与阴影之外
在叙利亚,呼吸就等于毁灭
元音、孩子与绿色纷纷扼倒在水泊中
一个民族是他自己的拯救者,也是行刑人
当又一轮新月升起,那庆祝的难道
不再是篝火前闪动的身影?而是虚无?
春心
在玉兰与桃花林下,他
在他生命的搏动中天使般消耗
那些健壮、丰饶的人群
在你的周围划出一道温情的界限
关于美、尊严和正义
它们是存在的,真实而紧张
而你却总是显得孤零零
如一只迷失于罪感的山羊
在那些对称与弧度的身体上
泛出这个季节唯一而持久的色情
你,一个厌世的同情者
只钟情于它,在妄想内浅浅地上瘾
所有的事物都在助长着欲望
同时,又反对它
你的手臂、革命理想和爱
都在这青年的时代成为更高的疲倦
和死,难道你要否认吗?
“一种单方面的激情正在毁灭他”*
你在种种繁花中卸下词语的铠甲
而后收获所有亲吻和泥土
在黛玉般忠实的凄美中
你与你的反光,正共同
沉醉于一次永恒般的离去和苏醒
*出自卡瓦菲斯《一位二十四的青年诗人》,黄灿然译。
食堂
冷雨漫过熟睡的众人,降临在
完美的此地,你看到你的肉体
银器般垂悬在这个国度,发胀如石榴
空气,连同其后的影子
正徐徐进入又一个艰难的黄昏
你,一个失群的人,早已落单成铁
你所渴求的不过是一个与你共饮的人
交谈、互吻,然后恒星般死去
有一瞬间,你忧伤得仿佛一头金黄的鲸
那存在的荣耀,即是另一番取消
因为,生命的成立是无数次迷人的
否定,比爱还深邃
渐渐的,雨水穿过夜晚的灯光
消失在更远的记忆,十九点
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餐桌上和好
沿着神圣之河,黑色、白色与黄色的人
交汇、旋转成人主的面目:
一种伟大而自洽的形式,泛着绝对之光
你道士般咽下最后一口素食,窗外
单独的一片叶子正醒悟般坠落在雨地
在弥散的年代,你恪守一种禁忌
如同自由,爱,以及无限孤洁的唯美
日出
可爱又短促的告别
在春风中战栗出桃花的死
不足一年,爱人已是
一份哲学提纲的欢娱
你拿出一只黄梨,比命还亮
人生几多愁?只是
那抹光从来没有如此温柔
浅浅的,如我稀薄的心
在洁白之床,睡美人
品尝着空梦中微渺的盐粒
该如何去爱?去毁灭?
你以你完美的呼吸淹没着我
看啊,被囚人和他绝望的秘密
此刻,成为更高的不存在
而在你我之间,黎明
正把所有的残缺和骄傲
变为一场古老火海的注视
这是完成,闪荡不宁的美
颠倒
在昼夜递交之际,在光
开始投射的瞬间
一切的人,一切的风景都是颠倒
过去的成为当下,新变成旧
那振栗的转为宁静,明亮是漆黑
你从矮床上醒来,看见
狮子的眼中闪烁未来的幻象
一次,两次,三次,无数次——
那颠倒的还有你的心与爱,风中
所有爱人都是完美,而你只消耗自己
当新月出现,为了更高的来过
你力图克制以近于死亡
在群山,月下,以及无人之境
你看交汇之星,看那绝望的绿色
谁使你,成为你和你的障碍?
而又一个黎明,悬浮如一个母亲
逃亡的心,1901年的失子之痛
正成為他们身上新的影子
在不真实的此刻,你并不存在
而那一轮一轮闪过的人,是
光点,河水,海底的召唤与永别
人景
阁楼下,三月的冰雪正在酝酿柔情
树干以漆黑的静止提示一种久别的沉思
人与人,他们在庙堂上取走纸符
便把自己想象成一阵超脱的风
草药冒着热气,在原野上寻找路过的
伤心,还是?
当一个人走过,另一个人又接着走
姿态是潜在的美学
操持异乡话的喉头在瞬间爆破
于是,我们、你们和他们都成了墙下的矮人
丈量宇宙
是一份苦差事
你不敢写下一个大
如同,你宣告自己已不属于这个圆
规针刺中白色的中央
就像飓风吸食大地上不合时宜的轻
此刻,北风将天空高高地吹起
没有云,也就看不见穿行于其中的鹤
于是,你放弃了死
永久注视窗外这寂静又残忍的人景
河滩
我已习惯了一个人出门
空寂的滨河公路上,晚风渐息
无数雷声都在诱引着我
多少次远行,我还是钟爱这片河滩上的黄昏
远处的对岸是几座灰白的泥屋
白杨林则在更远的山脚
我已经忘了我来这里的本意
那也许是因为我在晚餐后与哥哥争吵
或者是我没有找见那枚心爱的海螺
丰饶的芨芨草忘情地摇曳,似乎
我该走入它们中间,成为它们的一部分
一辆旧卡车疾驰而过,随之带来了雨声
无数肥硕与温煖的雨滴,击醒着我
它们使八月的河滩升起热腥的雾霭
此时,我的体内只剩下我
在这片松软的沙土上,我仿佛才破土新生
雨水顺着发梢和手臂又流入了河中
此刻,我觉得自己是真切的
这里再没有多余的爱的侵扰,我与那些
树丛、山地和人共同成为这雨的根须
但愿我不会再想起你,那会是另一种劳累
雨在最绝望时停歇了,遗留种种暧昧的水洼
乌云已退向了山地的另一侧
在傍晚的昏沉中,我感到完美
一些脆嫩的灯火在夜幕里悄悄长出
我想我并没有捡回那些已丢失的事物
那就让它们沿着河水流走,而我
只能用我涉过一个个冷冽的镜面的脚步
来涉过我这同样冷冽的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