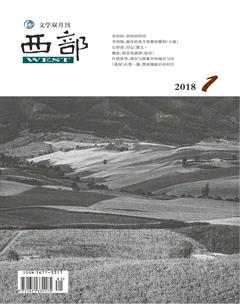呼啸而过
衣水
1
火车只在一瞬间,就飞过一个城市、一片田野、一座荒山。此时此刻,火车已经飞进一个无限辽阔的夜幕。我看不清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但我知道它在悄悄孕育、生长着。它孕育了什么?它生长了什么?是花鸟虫鱼、飞禽走兽,还是葱郁的森林和蓝色的湖泊?
火车飞进夜幕就像飞进我的梦境,那些隐藏起来的城市和村庄,山川和田野,只是一片又一片的暗影,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墨点。这些无限生机开始荒芜了,就连村庄的狗叫和城市的喧嚣也都影影绰绰起来。这时候,一张地图闯进我的梦境,所有的城市和村庄都只是一个名称,所有的田野和荒山都只是一个词语。无论黑夜还是白天,它们都兀自沉默在虚空里。只有一根又一根冰冷的铁轨卷曲起来,卷曲到今夜,也卷曲了明天。
火车只是在一张地图上飞行,仿佛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二维动画。我们都在彼此的无趣里生活,完成自己的表演,无论滑稽还是庄严,我们都在求索生命里的另一个自己。此时此刻,哪一个“自我”才是最初的那个人呢?
一列火车只运动过一条短小的线段,是它在盗取我的想象,逼迫我在一张纸上前进。可是我不会屈服,那些存在于火车之外的空白,那些无趣和灰暗的沙漠,统统消灭被我消灭。现在,我回到喧嚷的车厢,看见一切最生动具体和最具感召力的面孔。我融入活物之中,我仿佛也复活了,各式各样的价值亦为之诞生。我以为,飞驰而过的火车,载满了伟大的寓言。我知道,隐喻已经弥漫了我所有的空间。
2
这时候,火车缓缓驶进一个车站。一拨人,拉着行李箱的,扛着蛇皮袋的,早排着长长的队伍,无论是着急忙慌的,还是神闲气定的,都像被一根绳索串上了一样,被一只我看不见的手缓缓拽到火车之外的夜幕里了。
这一拨人里,谁要回家,归心似箭?谁要外出,雀跃憧憬?
我不得而知。
我只是这个车站的过客。我不想知道这个车站的名字,也不想知道我这是飘忽到哪里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走到或是光亮或是暗淡的终点,这便是抵达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又一拨人仍旧像被绳索串上了一样,被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不由分说地拽到这列火车上来了。
这一拨人从夜幕里冒了出来,就像一群野鬼被驱赶到了太阳底下,眨着惊恐的眼睛。我知道他们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些座位,可他们的脸扭曲着,车厢里的白炽灯光漂浮了他们一脸惊愕或是焦虑。我感觉他们不像是在寻找一些座位,而是在探寻早已等在火车上的那个不知所踪的自己。
有谁在这一时刻提醒一下呢,火车上的他们,多年前就被荒野的风吹得七零八落了,也被城市的喧嚣淹没得没有一丝痕迹了。我想知道,这个提醒他们的人是我吗?我看着他们,我是在搜索人堆里“哪一个”是我的另一个自己吗?
我跟他们一样,都是求索答案的人,也都是惊魂甫定的人。没有答案,只有不断逡巡在每一个质疑里,去追踪梦境之中那个有点像“我”的人。这是无数个隐喻的坑,埋藏着无数个惊恐的我,也是勇敢的我。也有你,也有他。
3
火车上的人越聚越多,如同集会的麻雀,叽叽喳喳,简直吵沸了一整列火车。我感觉他们确实是麻雀,蹲着的、坐着的、站着的,在每一节车厢的座位上或是走廊里,都大张着尖嘴声嘶力竭地叫着。
我想倾听这些叫声,我想弄明白他们在吼叫什么。可是他们的表情和动作都像画在了一张雪白的纸上,雪白得沉寂了,雪白得连一点声响都没有了。我感觉他们像是在我的梦境之中,被超能力给压扁了。
火車再次出发,它满载欢笑或是忧伤,又一次驶进夜幕的辽阔。我开始松弛下来,从我一直紧绷的神经上,一下子抖落了满车厢的鹅毛大雪。
簌簌地落下来。
那声音美妙极了,我感觉就是天籁之音漂浮在每一位乘客的脸上。我开始注意一个个活生生的乘客,而不再是被抽象出来的灵魂。
脸。我只注意到一张张的脸。
我的脸,你的脸,他的脸,都是特写的脸,都像一只只麻雀的脸,特写而不具有特征,无辜至极也是无趣至极。
我真的如此不堪吗?
看着这张或那张触手可及的脸,这些真实得有点虚假的脸。难道我的那两张脸也漂浮在这样的尘世吗?
伸出左手的食指和拇指。
我这是在干什么?
狠狠揪起一张脸的感觉,哦,还有疼痛;哦,汗涔涔的。这不是一张百变的面具,也不是一张硅胶制作的高仿脸,它确实是一张有血有肉的脸。
我不敢相信自己。“一张张麻雀的脸。”我嘀咕着。我想从这一张张脸上,发现一张或是两张不一样的脸。“麻雀”,我们都是麻雀吗?我突然惊骇,突然明白“麻雀的脸”不是至关重要了,“麻雀”才是我们的致命要害。
“草堆之上的麻雀”“屋檐之下的麻雀”,随处可见的麻雀,毫无疑问就是我们。
我环视每一位乘客,仿佛都是一只宿命的麻雀。我所乘坐的车厢,再次荒芜,再次成为野鬼的旅行箱,再次成为麻雀的喧嚷之地。
4
我睁再大的眼睛,也瞅不出自己内心的鬼。可是车厢的玻璃窗仿佛是开启内心的一扇门。这时候,火车已经驶离城市的灯火,那或明或暗的想法,都淹没在黑黢黢的村庄、平原、山川或是河流。我看不见它们,但我知道它们在悄悄地生长,生长成麻雀的样子吗?我只能看见“我”,那镜像里是另一维度的“我”,“确实是一张麻雀的脸”,我看到一侧的脸,一种怪异,极端不舒服,难以忍受。
“这是一种讨厌”,我讨厌自己有一张这样的脸。
侧过身体,我想瞅一瞅另一张脸,“也许它会如花似玉”,“至少它不是一张麻雀的脸”。可是我太乐观了,它确实还是我的脸,不过多了一个伤疤,丑陋的伤疤。我依然感觉这张脸平庸得令人讨厌,不过讨厌中它却生动起来,仿佛那流逝的沧桑复活了,跟影像一样显现。这时候,我感觉有一只美丽的苍蝇,从丑陋的伤疤上翩然飞走了,飞进镜像里,飞到窗外的黑夜里,也飞到车厢的白炽灯光里,仿佛嗡嗡地歌唱未来。
“未来啊,只有明天才能抵达。”
一列火车仍旧飞向真实的明天,我听见一只苍蝇在歌唱。
这个夜晚仿佛被控制了。这里没有真实的我,有人陷进了夜晚白色的泡沫里。明天是什么?明天是我么?是你么?是他么?镜像里这个老汉就重叠在我的身后。让我惊愕的是,他在打瞌睡,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这是一位醒着睡眠的人。”
我回头一瞅,发现他就坐在我对面。一个真实的老汉,呼噜呼噜地打着响亮的鼾声。嗬,他在对我怒目而视。
这个老汉,他就是“我”吧。
我好像立刻找到了某一个失散多年的自己。
我认真地打量他,灰暗的眉毛,左侧有好几根白了。哦,是八根白眉毛;右侧呢,一、二、三、四、五、六,是六根。我较上劲儿,想查清楚他的白胡子的数量。一二三,四五六……我好像查不过来,他下巴上的胡子几乎都白了。我凑近一点,他脸上的胡子也看清楚了。有多少根呢?有多少根白胡子呢?现在我只能数一数黑胡子了。一根……两根……一共还剩下九根黑胡子。哦,这个老汉,头发已是灰白相间。
这个老汉就是将来的我吗?我真不敢相信,真实世界的我竟然是这样栩栩如生。我喜欢真实,我喜欢这个衰老的明天。
这老汉身旁,一个三十多岁的美人,她昂首挺胸。她挺起来的是一雙高耸的乳房,像两只想抓住你的手,狠狠地横在了我的面前。
“胸是一个器官。”
它好像把我的两只眼睛摘走了,我得亦步亦趋地跟进它,跟着它的起伏,来破译弥漫过来的密码。我潜意识下抬起手臂,把手伸出去,想着伸到一个凸起上。不过我隐约感觉,那是一个藏着陷阱的诱惑。我只得让伸出的手缩放在自己的胸上。
这地方什么也没有,空空如也。摸到自己的身体时,我突然想起了曾经给自己画上一个傲然乳房的游戏。用彩笔精巧地绘制一双乳房,它们就跟美人的一样光彩夺目。这是一种行为的欲望,它才是最真实的,它此刻就在我的血液里奔涌。
我知道这喂饱嘴巴的乳房,从童年起就潜入每一个人的内心了。
5
火车穿行,像飞驰而过,也像静止不前,我总感觉它是在夜幕里漂浮。什么也看不见,而火车之外,仿佛是一片片过期的面包不断被火车扔在身后,碎屑乱飞。我出神地瞅着,被我抽象的和暂时放弃的世界。
我却只能看到车厢里正恹恹入睡的人和漂浮的一张张模糊不清的脸。
“咕咚……咕咚……”
一连串的车轱辘声,一下子惊醒梦境之中的我。
是一个兜售午夜加餐的人,好像只有她是一个活物,而我只是她叫卖背景里的装饰漫画。那些睡去的人呢?或许在他们的梦境之中,正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香喷喷的饭菜和午夜的寂寥呢。
我总感觉,这是冥界里的一个个场景。
那铁皮车的轱辘声也轻飘得无聊。像什么呢?像一朵一朵颓废的白云。我感觉这个叫卖加餐的女人,推着她的铁皮车,不断重复着从廊道里走过。刚才,我没看见那人的脸,等我回头瞅她,她已经走到车厢的那一边了。
她的背影,由上而下的弧度,这异性的吸引是多么令人不安。
她推着铁皮车,再次走过来。我可以欣赏她的晶莹剔透的脸蛋。
她推着铁皮车,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吆喝着:“盒饭,盒饭喽。”这个声音太好听了,简直珠圆玉润,像百灵鸟的唱歌。“素的盒饭,青椒鸡蛋、白菜豆腐,六元;荤的盒饭,青椒肉片、青椒鸡蛋、白菜豆腐,十元。鸡腿另卖,一只五元。”
她一直瞅着铁皮车里的盒饭,也许还有各种饮品,仿佛这铁皮车就是她的生命,就是活着的憧憬。她在不遗余力地推销,推销就是她实现价值的方式。我看着她,我们都静止了似的。这仿佛是一个永久性的动作,她从铁皮车里拿出一个盒饭,递给午夜的乘客。
这个叫卖像唱歌一样的女人,轱辘轱辘地走过来了。
我远远就看见她涂抹过口红的嘴,她叫卖的时候嘴就是一个红得发黑的洞口,好像在吞噬她眼前的一切。我好像也被她吞噬了,我仿佛就在她湿漉漉的口中,感觉黑色的甬道正向无限之中绵延而去。
我挣脱它,我从它的吞噬里回到起点。
我远远地看见她走过来,我不看她的嘴,我只看她的脸。
她的脸无限大,无论我怎么努力,只能看清她脸上的细小部分。我忍住不去想也不去看她的红红的嘴巴,免得被引领到另一个陷阱。我仿佛在拿着显微镜,在她的脸上一点一点地勘察。我在干什么?我在探秘一个宝藏吗?哦,宝藏,没有丝毫声音的一个真空。
我突然看见一座巨大的山,突兀地耸立在我跟前。
哦,我心里明白,在她脸上,这不是一座大山,这是一颗大大的黑痣。这不是画在一张白纸上的黑点。这是一个活物,我感觉它扇动了一下翅膀。过了一会儿,好像又扇动了一下翅膀。
它终于在我的注视下翩翩然飞走了。
6
这个叫卖的女人,轱辘轱辘地走了过去。
就是刚才,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为什么那么费劲研究这女人的一张嘴和脸上的一个黑痣呢?我错失良机,我错过欣赏一个女人容颜如花啊。我只能看着她的背影,她的由上而下的弧度再次让我不安起来。
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是认识一个女人,应是从识别她的脸开始的;欣赏一个女人的美,应是从她千娇百媚的脸开始的。可是,我始终看不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在梦境之中,我们都像麻雀一样,面目不清地困于一节又一节的车厢里。我们的脸曾经都像麻雀一样,没有差异,没有可供识别的特征。可现在,这不是梦境,这是在现实的火车上,我们依然是男人和女人啊,我们依然是人啊。
我看不清她的面目。我怎么认识她呢?我怎么欣赏她的美呢?我怎么知道她是谁呢?
我焦虑不安,看着那个叫卖的女人,我感觉她的背影越来越像我了。我恐慌起来,难道她就是另一个失散多年的“我”吗?难道我也像她一样没有清晰的模样吗?我忐忑不安,我也像唱歌一样叫卖这么多年吗?我知道,我已经把自己丢失在城市的喧嚣里了。
我不相信这黯淡的现实,我总感觉这是在镜像里或是在我的梦境之中。
7
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噩梦而已,不过是我睡意朦胧罢了。这个世界不会有我看不清面目的人,我也不愿意做一个脸面模糊的人。我正庆幸这一切都是幻想之物,却听见一声脆脆的铜锣。
我怎么也想不到,在一列飞向未知的火车上,还会有耍猴卖唱的游戏。
一位老人,牵着一只猴子或是两只猴子,敲着铜锣,哐哐哐地聚集一圈人。他开始拿着鞭子,抽打着猴子表演,翻跟头、戴帽子、敬礼或是骑单车。
我知道这是一种谋生,一种生命存在的形式。
听到这声铜锣响,我立刻就想到这样一个特写。
“耍猴的游戏。”我嘟哝着回过头,立刻呆若木鸡了。
这不是在梦境之中,我告诫自己,这是一列飞驰在午夜的火车。我乘坐这一列火车,明天就抵达Z城。我这是从故乡飞回我所旅居多年的Z城。我这不是睡意朦胧的幻觉。我知道我在惊骇。我看到一个庞大的怪物,拿着一个大铜锣,就是它刚才敲响的铜锣。正是这一声铜锣响,我才惊愕,现在却惊骇它是一个巨大的怪物。我知道怪物不值得惊骇,让人惊骇的是这怪物的肩头上坐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男孩脖子里套着一根绳圈,绳圈的另一头就在这怪物的腰上捆着。
哦,這个八九岁的男孩,莫非真是一只猴子?
我仔细瞅上一阵儿,看得更真切一些,这个男孩不是一只猴子。这个男孩确实就是一个男孩,我看到他正对廊道里的乘客说着话。哦,这确实是一个男孩,人类的男孩,不是猴类的男孩。这个男孩,头顶一个大大的托盘。这个大托盘,几次都跟着男孩的身体歪斜了,我以为它会滑落,可是没有,这个大托盘仍旧稳稳地顶在男孩的头上,就像长在了他的头上一样。
这个大托盘,突然让我想到乞丐乞讨的那只大碗。
大托盘是一个盛器,是一个生长金币的聚宝盆,被高高地顶在高贵的头颅之上。
我看着大托盘,它仿佛在闪耀着亮闪闪的金光。
这一团团的金光笼罩在大怪物的脸上。
啊,我惊骇的时候,就看到了它的脸。我看不清人的面目,却能看清它的脸面。这个怪物,就是一个放大数十倍的大猴子。这么大的猴子,应该叫超级大猩猩,超大号的大猩猩、肥硕的大猩猩。大猩猩走过去,一个个干瘦的人占据的位置,像被犁开了一道深沟一样。大猩猩犁过去了,它在人堆里播种了人类的未来么?
8
大猩猩驮着他的人类玩偶,犁进另一节车厢。火车载着他们,也载着我们,飞向一个我不确定的未来。我要去Z城,他们要去哪里呢?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犁开一个幸福的明天吗?我看着他们消失在狭长的廊道,可是那个男孩头顶的托盘开始清晰和膨大,慢慢,它占据了一节车厢,接着就占据了我辽远的梦境。
我感觉,这大大的托盘就像顶在我的头上一样。无论怎么晃动身体,它都稳稳地被我顶着,好像与生俱来就长在我的头上。这让我莫名其妙,也让我感觉一支支嘲讽之箭正接二连三地向我射来。
头上顶着一个大大的托盘,无论你做什么营生,都像是在乞讨。
大猩猩和他的人类玩偶,是猴耍人还是人耍猴,都无关紧要了。要紧的是,他们以自己别开生面的方式乞讨。我不敢想象,我是在乞讨吗?这一火车的人,那位睡着的老汉,那位叫卖的女人……都是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乞讨吗?
我已经难以忍受头顶一个大托盘这样糟糕的意象了。
我闭着眼睛不再看车厢里的人,可是车厢里所有的人都像是排着队从我面前经过。所有的人都在晃动着脑袋上的大托盘,熟悉的人还用指关节相互敲打着对方头上的大托盘,发出叮叮当当的清响。
我告诫自己,这个场景特写不是真的,它只是我噩梦的延续。
这个令人恼火的大托盘,它现在开始折磨我了。
你看看这火车上的每一个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仿佛我真的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似的,他们都顶着大托盘向我行礼。行礼就行礼吧,我们握握手或是点点头就是了。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错了。一个年长的礼仪官告诉我,我们最尊贵的礼仪是两个人面对面碰三次头上的大托盘。
“要记住,”礼仪官说,“托盘撞击的声音越响亮,彼此就越真诚。”
这是什么鬼礼仪,我有些愤怒,可是我不能不面带微笑,与每一个给我行礼的人碰上三响。
哐哐哐……三声铜锣一样的声响,几乎震得我头晕眼花。
哐哐哐……哐哐哐……越来越多的人,走过来行礼。
或许我的脑袋真的麻木了,耳朵真的震聋了。一车厢的人都过来行礼,我听到的这哐哐哐的托盘相撞的声音,都带了金子的光芒。我开始惊喜,我富有了。我感觉每一次托盘撞击,我的脑袋都会沉重一些。直到我的脑袋不能承受这伟大的托盘之重,我才意识到每一个给我行礼的人,都在为我施舍三枚金币啊。
我把这些金币都收拢起来,藏进我背后的布袋里。
呵呵,沉甸甸的一布袋金币,数以万计的金币,我简直富可敌国。
或许还会有更多的人,向我行礼,也会把他们的三枚金币都撒进我的大托盘里。或许火车上的人,不是在向我行礼,而是在向我纳贡?
难道我真的就是一个国王?
我嘿嘿直乐,嘲笑自己做的白日梦。白日梦,白日梦里做国王。啊,国王,我突然想到大猩猩和它的人偶男孩,它们是在以自己别开生面的方式乞讨。这一火车的人都头顶着托盘,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乞讨。我呢,这个白日梦里的国王,这头上的高高托举着的大托盘,不也是一个乞讨的大碗吗?
一个国王,哎,他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乞讨啊。
9
这时候,我听到铁皮车轱辘轱辘地走过来。之前我没看清那位叫卖女人的脸,我当然也看不到自己的面目。那个沉沉入睡的老汉是我失散多年的自己,这个叫卖女人也是我失散多年的“另一个”,我感觉我已经看到自己的真实和本质了。
我睁开眼睛,看看真实世界的男人和女人。
嗬,这是第几重梦境呢?怎么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每一个人的头上都顶一个大托盘呢?我姑且承认,我仍旧在一个梦境之中。我再也不能错过这个叫卖女人了,我已经准备好跟她搭讪了。
我撅撅嘴巴,努努鼻子,眨眨眼睛,清清嗓子。
我摩拳擦掌,热血沸腾。我又摸向身后,我背着一袋子金币呢。我摸上一阵儿,却什么也没摸到。我背后什么也没有,我明白了,只有在另一个梦境,我才有那一袋子金币的。
我呵呵自嘲一阵儿。
这个叫卖女人已经推着铁皮车轱辘轱辘走过来了。
我慌忙从钱夹里摸出一张人民币,拿在手里准备递过去。铁皮车在一点点地爬过来,轱辘轱辘的声音也一点点地爬过来。我站起身,远远地瞅着她,这个叫卖像唱歌一样的女人,我渴望她走近一点,那样我就能看清她真实的如花似玉的面目了。
我可以以此类推,即使自己面目可憎,但我也可以知道自己面目的形状。可是这个叫卖女人已经走到我的跟前,我依然看不清她的如花似玉的脸。这不是一张脸,我死死地盯着它,我确定它没有被无限放大。可是这两张脸,好像始终被马赛克覆盖。被覆盖的模糊不清的脸颊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渴望知晓,却没有清晰的答案。
我开始焦虑不安了。
可以预见,我很快会看见她的背影,她的由上而下的弧度就会像一只手紧紧抓住我的眼睛,也会把我引入另一节车厢的陷阱里。
我慌忙截住她,把那一百元人民币使劲扔进她头上的大托盘。
我看到通红的人民币像秋天的落叶一样,飘飘然落下去了。
我没想到的是,落叶会悄无声息地飘落大地上,而一张人民币落进大托盘却是哐当一声响,好像砸出了一个大坑似的。叮叮咚咚,这一张人民币仿佛变成无数个金币,叮叮咚咚地钻进她的口袋里去了。
这一刻,我放下心来,我感觉她不会只给我一个背影的。
我感觉她开始注意到我。她推着铁皮车,仍旧像唱歌一样叫卖,她离我越来越近。我注视着她,聚精会神地瞅着她的脸。
她的脸依旧模糊不清。我只能看见她的嘴巴一张一翕,像一个正在吞没食物的洞口。
10
那叫卖像唱歌一样的女人,我終于看清楚她了。
原来它是一个仿真机器人,怪不得我看不清它的面目。它本就没有面目,只是一个个类似器官的零件组合。即便如此,它的脸,也要仿制成两张如花似玉的脸吧。它这么模糊不清,是仿照何人所制呢?难道它仿制的模板就如此不堪吗?
我再看它,它的面目就更加毛糙粗粝,两张脸就像灰暗的抹布沾满污浊的灰尘。我不忍触目。我希望的如花似玉的美人脸上,似乎有一只巨大的苍蝇嗡嗡地朝我飞过来。
我的矿泉水,我的果粒橙,我的小麦啤,我的午夜盒饭……
我一口气从她的铁皮车里取出好几件我喜爱的美味。我这才后退一步,想看着它轱辘轱辘从我身边走过去。这个女版机器人,不是我失散多年的“另一个”。我不是机器人,我不是面目不清的大猩猩。我是一位有着血液和肉体的人,我是一位有着自由思想和独立个性的人。我抱着一大堆美味愣愣地看着它,目送它从我身边轱辘轱辘走过。
可是它没有,它就站在我面前,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零钱,是小面值的人民币,而不是金币。我这才清醒,我这是在一列飞驰的火车上,我这是在飞回Z城的路上,我这是在绝对真实的生活里,而不是在自己或是别人的某个梦境里。
我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吗?
我接过机器人找回的零钱,又看它远去,我感觉我跟它好像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
“难道我也是一个机器人吗?”
我被这个猜想吓坏了。
我慌慌张张退回自己的座位,把一堆食物凌乱地扔在面前的茶几上。一片空白,一片慌乱;一阵儿憋闷,一阵儿恶心。我像是瞬间把自己扔在一个不毛之地,凄凉、无助、绝望和愤怒,一下子就胀满我的身心。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气球,在空中飘来飘去,等待某一时刻嘭的一声,炸裂成无数碎片。
这个结局让我坐卧不安。我坐到座位上,又站起来,再次坐下,两只手较劲儿地搓来搓去。我感觉两只手的冰冷,两只脚的冰冷,然后是脊背的冰冷。我感觉浑身哆嗦。我害怕看见自己,害怕看见自己真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可是我又忍不住想看看另一个“我”。
身边的窗玻璃里,我真的不想是那个面目模糊的家伙。
他真的就是我吗?
我看着他,额头上一粒豆大的汗珠,晶莹剔透的汗珠,正从高处滚落。滚落,滚落,它好像一直在滚落。冰冷的滚落,好像是一条静止的河。我在这个家伙的脸上,再也看不到别的,只有汹涌的浪头吞噬一切,吞噬我心里呼喊着的声音。我在恍惚,我在飘荡,我在坠落,我在裂开,我在自己的一条河流里,逐渐沉溺。我也在挣扎和证明,我有情感,我有体验,我有思考,我不是那个叫卖女人,我不是机器人,我也不是梦境之中的漫画人物。
午夜如此诡异,我仿佛被困在现实的壁垒之中。火车飞进虚幻的夜色,它在帮助我们——这一火车又一火车的人——完成某种人生的自我乞讨的宿命。
11
火车玻璃窗外,浓密的黑暗越来越陈旧。我的恐惧也越来越巨大,它逐渐弥散在过去和未来的场景里。我知道火车会呼啸着抵达终点,一切自我迷失都会终结。
我或许是自己,或许是别人,或许是种种猜测里的某种可能。
这让我不再祈盼终点。那是一种结束,一种征程的归宿?这时候我需要一种无与伦比的强大,来减缓一种结束,来抵制一种归宿。
我知道前方的Z城在日新月异地布局呢。这让我想起儿时玩耍的积木游戏,每一种组合都会诞生一个崭新的自我。为何我不进行自我塑造呢?我这是在自我救赎吗?或许我可以逃脱那被控制的宿命。
这或许真是在梦境之中,我只得对自己下狠手了。
耳朵,眼睛,嘴巴,脸,鼻子,胳膊,手,腿,脚……我把这些各自独立的器官拆卸下来。我是让它们毫无目的地四处散落。我知道,这势必会组合一个个崭新的“我”。机器人没有自己的脸,我也一直看不清自己的面目。这一下好了,我拎着自己的两张脸,左看右看,像两张随风飘荡的被单。我看着它们就来气,如此清晰和坎坷的脸,怎么一装在脑袋上就模糊不清呢?怎么就看不到自己呢?我一只手拎着它们,一只手狠狠地拍打着它们沾染的风尘。
我本以为,这两张脸一经拍打就会灰尘弥漫,可是我想错了。这虽是两张破旧损耗的脸,令人惊奇的是,它们没有溅起一粒细微的尘土。我只听得啪啪啪的声音响起,那两张脸只是青一阵儿,白一阵儿,紫一阵儿。不知是什么情况,按说我是没有感觉的,可是我却感到自己的身体火辣辣的。
这时候,那一件件具体生动的器官都欢快地跑了,跑到其他车厢躲藏起来了。我知道它们在同我捉迷藏,它们一旦从我的思想里解放出来,就分别逃至它们以为最安全的角落里。可是它们藏好了,也不给我一点点信号,而是让我在焦急中等待。我等得不耐烦了,只好自己动身,前往每一节车厢搜集它们。
我感觉我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之前的质疑,当然也是每一位旅人的质疑。
我看到,这些藏起来的器官分门别类地藏在各自的车厢里。这一节车厢里藏着的全是耳朵,那一节车厢里藏着的全是嘴巴,还有一节车厢里藏着的全是脸。
我感觉这是一种游戏,是捉迷藏啊。
我立刻兴奋起来。
我知道,只有找到那两张属于我的脸,一个崭新的人才会自动走出来。两张脸啊,脸啊,那是人的标志,那是认识自我的开始。可是这一车厢的脸,我自己的脸已经是那么模糊不清又面目全非,这让我去哪里寻找呢?
这太诡异了。
我曾经的脸上有一颗黑痣,跟那叫卖女人的一模一样。凭着这一特征,我在到处都是脸的这一节车厢里一个一个查看。扒开一张脸,细皮嫩肉的,肯定不是我的,把它扔出去;再扒开一张脸,满脸都是疙瘩,也不是我的,把它一脚踢飞。
12
真是疯了,我真是疯了,我在拳打脚踢一群脸。一群脸愤怒了,它们飞回来围攻我。
它们的围攻,不像我们现实世界的围攻,不是拳打脚踢。它们不会拳打脚踢,而是满脸堆笑地贴近我,不断地试探我,不断地亲昵我。
它们这是在干什么?
它们想俘获我,想占据我那两张脸的位置吗?
我得抵抗它们,我得搜索那两张我的遗失多年的脸,我才算是“我”啊。可是我的那两张脸,它们藏得真是隐秘,我竟然没嗅到它们一丁点儿的气息。我实在焦急,便朝窗外看了一眼,窗外依然是虚空的陈旧的黑。我在感受这样的黑,脸——那两张带有黑痣的暗淡的臉,就像这午夜的虚空一样,它们真的不愿意回来了吗?
我转身走了,不再搜索那两张迷失于路途的脸了。
我去寻找耳朵、眼睛、嘴巴、鼻子、胳膊、手、腿、脚、内脏……
这些器官,我很快就找了回来。可是那两张具有识别意义的脸仍旧毫无踪迹,它们压根就不想回来。我搓搓手,感到惋惜和难过。不过除了脸之外,其他器官都确确实实是我自己的。我用清水,把它们各自洗干净,洗掉黑暗、懦弱,或者缺陷,使它们纯洁、干净,然后一件一件组合起来。
嗬,一个崭新的自我,就这样诞生了。
可是这个崭新的自我他的两张脸依旧没有回来,依旧在躲藏。它们愿意过着东躲西藏的流浪生活,也不愿意再回到我的脑袋上。
我的脸就这样丢失了,或许只是一个瞬间,或许已经好多年。
Z城里,很多人都没有了脸,很多人的脸都安装错位了。就像此时此刻,我脑袋上的那两张脸是多么陌生啊,它们像打了马赛克一样,一直模糊不清,迫使我一直焦虑和恐慌。
我感觉再次陷入危机,我不能认识自己了。我只是一个个独立、具体的器官,却不是一个独立、具体的人。一车厢的人好像都不是了。
火车在午夜的虚幻里呼啸而过,每一个车站都下去好多好多器官,而不是人。它们蹒跚而去,消失在绵延无际的黑暗之中。可是从那扑朔迷离的空间里,有更多更多人的器官涌入这火车。
我们继续飞着,飞向一个或许真实的世界。
或许只有每一个器官才是真实存在的,而“整体的我”并不存在。
我在思考,我只好从一个个撕裂的器官,反复地思考自己。我是一个在封闭空间飞行的器官,一车厢或一火车的人也都是以一个个器官活着的人。我现在是一个人形的整体,人模人样,可是我感觉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在离我远去,悬浮在我不知道的幻想里。
火车在哞哞地叫着,显然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它是把我们拉进一个邪恶的深渊,还是一个希望的明天?火车在晃动着,我感觉我也在晃动。我是在颤抖,浑身都在颤抖。我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在颤抖。
我知道这是火车的节奏,也是这个午夜的时间节奏。
呵呵,时间的节奏。你看见时间了吗?
我只看见了火车,我只看见了自己,我只看见了飞舞着的形形色色的器官。时间只在我们的身体里,时间只在每一个器官里。我已经感觉到,时间就像一只睾丸,它一直在晃动着、震颤着。火车晃动,它也晃动;火车不晃动了,它仍旧晃动。我是说睾丸,它自己在晃动,它晃动出特有的节奏,它晃动出独特的声音。
这声音就是时间,我在俯身聆听,这世间最美妙的韵律,这世间最动人的天籁。我仿佛已经看见,所有的人都在聆听着滴滴答答流失的时间。我逐渐感觉,时间也最像一只卵巢,在孕育一个纯净的小孩。
只有我们是分裂的。那些最后的分裂的人,将会在某个睾丸和卵巢的合谋里,孕育成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我,一个完整的我们。
13
我好像已经找到自己。所有人只是活在一个寓言之中。是寓言在开启整个世界的按钮,而我在这个系统里完成自我的宿命。有人说这是以倒立的姿势反观这个世界。这是换一个角度能撑住的外延吗?这个虚幻的午夜,一列注定不会有终点的火车,不是靠姿态迥异就能解惑的。
我得把每一个器官用时间缝合起来,我得用时间的睾丸或卵巢重新认识另一种人生。我绝不倒立,我只是把一只睾丸或是一只卵巢生长在人类的脑袋上,重新记录我们的寓言空间。真实而不会虚假,孕育而不会仿制,这就是创世。
我感觉轻松多了,火车在一个巨大的钟表里飞向崭新的Z城。我从梦境之中醒悟过来,从扁体的哲学概念里飞到具体的一节车厢里。一列火车正冲破寓言的大屏障,疾驰而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一片田野又一片田野,抵达一座城市又一座城市。
我感觉这些都不再是一张地图,不再是一片荒芜,不再是一个墨点,不再是一片暗影。它们再也不是我的幻觉,再也不是我的梦境。它们是实在之物,具体之物;它们都明眸善睐,熠熠生辉。
我仿佛回到童年,回到最初的乐趣和真实。
我不再是器官。我不再是一个具体的耳朵、一只眼睛、一张脸皮,也不再是一个睾丸或一个卵巢。我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人类,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和人类,一个面目清晰的人和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