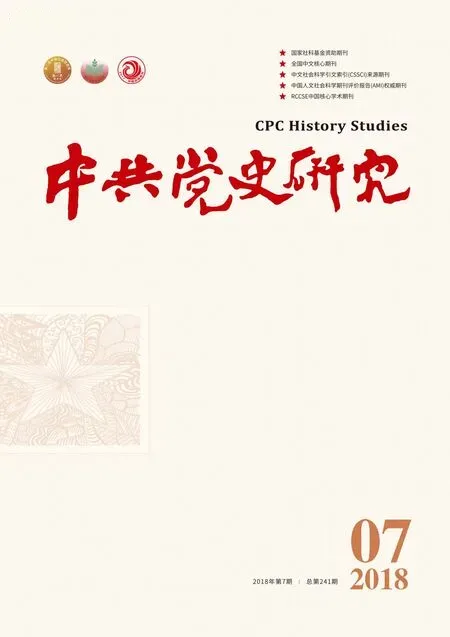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心理战略委员会涉华档案评介*
赵 继 珂
随着文化冷战史研究的不断推进,诸如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PSB)等多家尚未引起学者特别关注的美国文化冷战机构越来越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与之相关的档案资料逐步得到系统搜集和整理。最近几年,国内学者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也开始尝试对心理战略委员会加以研究,但就所用史料来看,他们更多依靠的是网络资源特别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FRUS)以及美国解密档案在线系统(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USDDO)数据库提供的档案资料,而对与之相关的其他档案资料仍缺少使用。有鉴于此,本文特别对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馆藏的心理战略委员会涉华档案资料加以推介,以此方便国内学者深入考察心理战略委员会的机构发展史,进而助力国内文化冷战史研究早日实现与国际研究的同步发展。
一、心理战略委员会档案的整体馆藏介绍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文化冷战与波匈事件研究”(16CSS031)的阶段性成果。
地位*Walter L.Hixson,Parting the Curtain:Propaganda,Culture,and the Cold War,1945—1961,Basingstoke:Macmillan Press LTD.,1997,p.18;Wilson P.Dizard Jr.,Inventing Public Diplomacy: The Story of the U.S.Information Agency,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04,p.52.。该委员会的心理战官员更宣称“要通过心理战来‘赢得’冷战”*Kenneth A.Osgood,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6,p.44.。
那么,这家新成立的机构究竟采取了哪些行动?它开展的行动是否实现了总统杜鲁门的预期?心理战略委员会为美国文化冷战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受多方面因素干扰,这些问题过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杜鲁门总统图书馆收录的心理战略委员会档案,向读者完整呈现了该机构自成立至杜鲁门总统任期结束的具体运作情况,有助于对上述问题提供一些新解释。该馆馆员将这批档案资料按照陆军部十进制文件系统(The War Department Decimal File System)进行了初步整理,划分为整体档案、财务档案、人员信息档案、管理档案、供应服务和设备档案、交通档案、建筑场馆档案、医疗卫生档案、河流港口和水域档案以及附表等八大类,将之集中收录到“心理战略委员会档案总集”(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Files)中,总计4万多页。从整体上看,这些资料可望在如下历史问题的研究中获得应用,并为其中涉华档案的有效利用提供直接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资源。
关于心理战略委员会的成立原因和创设过程。虽然国内一些学者在论及战后初期美国对外信息文化交流机构的发展演变时,对心理战略委员会的成立原因、背景以及创设过程等都曾尝试作出回答,但由于档案资料匮乏,已有研究提供的解释仍略显简单,甚至还有一些研究空白有待填补*相关研究作品包括郭又新:《从国际新闻署到美国新闻署——美国对外宣传机构的演变》,《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5期;史澎海、王成军:《从心理战略委员会到行动协调委员会——冷战初期美国心理战领导机构的历史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等。。心理战略委员会档案总集第22档案盒收录的部分档案资料,便涉及二战以来美国对外心理宣传机构的发展演变历史,有多份档案资料更直接介绍美国决策层如何成立特别委员会评估美国对外信息交流活动,并最终决定成立心理战略委员会的内容等。
关于心理战略委员会的具体运作图谱。整个杜鲁门总统任期,心理战略委员会共经历了戈登·格雷(Gordon Gray)、雷蒙德·艾伦(Raymond H.Allen)和阿兰·柯克(Alan Kirk)三位主任的领导。记录三位主任日常活动以及往来信件等内容的档案资料,分别保存在第1、41、45档案盒中,第29档案盒则特别收录了多份艾伦和柯克公开演讲等方面的讲话记录。此外,第16、17、18、19、42、44档案盒还收录了心理战略委员会其他重要官员的档案资料。由于心理战略委员会的重要职能是协调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和部门落实心理战行动,这使得该机构需要经常同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共同安全署、美国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经济合作署以及中央情报局等政府机构交流沟通,与此相关的档案资料较为集中地收录在第2、3、21、23、38、39档案盒中。第4、5档案盒还部分收录了该机构同诸如福特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红十字会等非政府机构合作交流的档案资料。当然,在筹划具体的心理战略计划时,该机构有时也会同其他美国政府部门或非政府组织甚至是个人联系沟通,这些档案资料则分散放置在相关的心理战略计划档案盒中。
关于心理战略委员会筹划、制定心理战略计划并评估其实施效能的工作流程。档案显示,为更加准确地制定心理战略计划,心理战略委员会重点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德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国内动态和舆情变化等开展了评估考察,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心理战略计划。由于其考察的国家数量众多,这些档案资料分散收录在第5、6、7、8、9、10、11、12、13、15、32、33、34、35档案盒中。按照心理战略委员会的工作流程,在制定具体心理战略计划时,该机构一般会成立特别工作组来负责计划起草工作,记录这些工作组具体运作内容的档案资料,集中收录在第24档案盒中。
从事心理战研究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评估其活动效能,它同样适应于心理战略委员会。既然该机构负责制定了如此多的心理战略计划,那就需要评估这些计划的落实情况和活动效能及其对美国整体冷战进程的影响。第31档案盒收录的多份由心理战略委员会评估和审查办公室制作的评估心理战略计划实施效果的报告,应该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些答案。但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该机构在实施自我效能评估时,很多时候出于官僚政治考虑,特别是为了谋求获取更多的活动经费,可能会夸大其活动效果。因此在使用这批档案资料时,最合理的利用方式就是将这些评估报告同其他渠道获取的资料比对研究,以便更为客观真实地评估其活动效能。
二、心理战略委员会涉华档案的特色内容
据笔者了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专门研究心理战略委员会针对中国开展心理战的问题,缺少相关史料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系统梳理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馆藏心理战略委员会涉华档案,它至少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如下三方面的档案史料。
第一,宏观呈现心理战略委员会如何在国家心理战略层面审视中国问题并提出应对举措的内容。作为美国“国家心理行动的神经中枢”*FRUS,1951,Volume I,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Foreign Economic Policy,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9,pp.178—180.,心理战略委员会自认为它应该从全球视角筹划制定美国的心理战略计划,并协调相关机构予以落实。同时,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目的,该机构在分析美国面临的心理战局势、讨论美国心理战的目标和任务、研究制定国家心理战略计划以及评估心理战实施效能时,非常关注中国可能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机构在考察中国问题时,并非单纯就中国讨论中国,而是选择将其与国际共产主义问题以及东亚局势问题相结合,并最终提议美国应尝试通过发动隐秘的经济战、心理战等加以应对。这些档案资料类型包括会议记录、往来信函、笔录、演讲稿、备忘录和研究报告等,份数众多,内容庞杂,如《针对苏联和中国发动隐秘经济战的战略计划》《我们能否仅凭思想就战胜共产主义》等*Harry S.Truman Library,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Files(以下简称PSB Files),Box 14,U.S.Psychological Warfare Objectives and Tasks,November 7,1952;PSB Files,Box 14,First Draft of Mr.Carroll’s Paper on a Basic Strategic Concept,November 1,1951;PSB Files,Box 14,Notes on A Grand Strategy for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November 1,1951;PSB Files,Box 14,CIA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Psychological Strategy,May 15,1952;PSB Files,Box 15,Over-all Strategic Concept for Our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May 7,1952;PSB Files,Box 14,Memorandum for Admiral Stevens:Phasing of Covert Operations Designed to Reduce and Retract Soviet Influence and Power,February 4,1952; PSB Files,Box 14,A Strategic Plan for Waging Covert Economic Warfare against the Soviet Bloc and China,Undated;PSB Files,Box 15,Can We Fight Communism with Ideas Alone?June 12,1952;PSB Files,Box 15,Preliminary Estimate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US Psychological Strategy,May 5,1952.。
第二,细致探讨心理战略委员会为扩大美国对华宣传和实施文化渗透采取的具体举措。虽然心理战略委员会并不直接从事对外宣传活动,但为了更准确地制定心理战略计划,该机构高度关注社会主义阵营宣传力量的发展变化,并认真考察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手法和技巧,第5、9、21档案盒收录的部分档案资料便涉及此话题。在考察中国的对外宣传活动时,该机构强调应该将之与苏联的对外宣传捆绑考察,因为它们都是所谓“仇美运动”*“Hate Campaig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简称“Hate Campaign”或“Hate-America Campaigns”。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战略委员会认为,1951年1月21日,苏共高级官员波斯佩洛夫(Pospelov)在苏共全体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美帝国主义的血手伸向苏联人民》的演讲,之后所有的苏联报纸都围绕“美国迫害苏联民众”这一主题展开报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都采取了相似行动,这实际是苏联和中国在全世界发起的一场“仇美运动”。究竟心理战略委员会缘何会将中国的对外宣传活动视为“仇美运动”的一部分,该机构认为中国为落实“仇美运动”采取了哪些举措等内容,分散收录在第5、8、37档案盒中。
心理战略委员会还对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等地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群体予以重点关注,并尝试将他们作为对华心理战的重要资源。第5档案盒就收录有诸如“就香港中国难民知识分子工作同麦康瑙希(McConaughy)的非正式会谈”“援助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人中间宣传美国民主”“有关在港中国难民知识分子、学生、技术员和专家的备忘录”等资料*PSB Files,Box 5,Informal Discussion with Mr.McConaughy.RE:The Work in Hong Kong on Chinese Refugee Intellectuals,August 26,1952;PSB Files,Box 5,Aid to Chinese Intellectual,Re:Assisting a Refugee Program for Chinese Intellectuals,August 27,1952;PSB Files,Box 5,Propaga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September 15,1952;PSB Files,Box 5,Memorandum on the Chinese Refugee Intellectuals,Students,Technicians and Professionals in Hongkong,December 17,1952.。应该说,冷战时期美国利用海外华人开展心理战并非新鲜事物,但该机构将关注重心专门聚焦于海外华人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反映出早在50年代初美国便已考虑对海外华人加以分类利用。国内学者在研究海外华人问题时,应该对这一动向略加关注,这实际上是美国谋求全面提升对华心理战效能的一个缩影。
第三,完整记录心理战略委员会在朝鲜战场发动心理攻势,试图在心理战略层面帮助美国赢得战争的内容。美国决策层之所以设立心理战略委员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应对朝鲜战争的需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方面很快便发现,依靠当时的运作体制,难以有效应对中朝在国际舞台和朝鲜战场上发动的强大心理宣传攻势。换言之,美国当时需要成立专门机构,以便从心理战略层面筹划打赢朝鲜战争。受此影响,心理战略委员会涉华档案的很多内容都与朝鲜战争相关。
(一)展示心理战略委员会为帮助美国赢得战场胜利所做的直接努力。虽然受部门性质所限,心理战略委员会并没有直接参与地面战斗,但这并非意味着该机构想置身事外,第8档案盒就收录了多份该机构尝试通过自身努力帮助美国取得军事胜利的档案。档案显示,该机构积极派员参加朝鲜观察委员会(Korean Watch Committee)等机构的活动*PSB Files,Box 8,Participation of PSB in Activities of Korean Watch Committee,June 26,1952.,并对中国和朝鲜在朝鲜战场的能力和动机予以评估,尤其积极为美国准确制定第55/1号国家情报评估(NIE-55/1)建言献策*PSB Files,Box 8,Proposed Terms of Reference for NIE-55/1.Re:Communist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in Korea,June 23,1952;PSB Files,Box 8,Proposed Terms of Reference for NIE-55/1,June 13,1952;PSB Files,Box 8,Proposed Terms of Reference for NIE-55/1.“Communist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in Korea”,June 23,1952.。同时,心理战略委员会着力研究如何扩大针对中国和朝鲜的心理战行动,制定了题为《在朝鲜的心理战行动》的文件,并特别向美国心理行动协调委员会(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Committee,POCC)提议考察是否可以安排将中国国民党军队投入朝鲜战场,以便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心理战效果*PSB Files,Box 8,Psychological Warfare Operations in Korea,May 6,1952;PSB Files,Box 8,Increased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Measures in Korea,May 29,1952.。作为补充,该机构还评估了美国和联合国在朝鲜战场实施的政策和行动的心理效果。
第37档案盒收录的部分档案则重点介绍了心理战略委员会指导美国应对朝中细菌战指控的内容。以往学界在考察朝鲜战争期间的细菌战问题时,更多地是辩论其真伪,对美国政府部门如何筹划应对之策并没有予以重点考察。在1952年2月朝中方面正式指控美军在朝鲜战场开展细菌战后,心理战略委员会便迅速行动起来,除分析朝鲜和中国发动此次指控的动机和效果外*相关档案如PSB Files,Box 37,Korea Plague Epidemic,March 3,1952;PSB Files,Box 37,Propaganda Campaign on Biological Warfare,March 21,1952;PSB Files,Box 37,Preliminary Estimate——Communist Charges of Germ Warfare,April 8,1952.,还特别要求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为其提供信息,最终制定出幕僚研究报告《初步分析共产党的细菌战宣传运动(附建议)》(PSB D-25/b),对如何弱化朝中方面发起的细菌战宣传活动提出建议,要求美国应该在宣传和其他行动领域采用新方法来掌握和保持主动。
(二)还原心理战略委员会参与朝鲜停战谈判、寻求帮助美国在谈判桌上占据心理优势的历史画面。诚如英国学者罗斯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所言,“尽管停战谈判的过程是漫长的和复杂的, 但是和分析研究战争第一年的成果相比,对战争结束过程的研究还是被忽略了”*Rosemary Foot,“Making Known the Unknown War:Policy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Diplomatic History,Vol.15,No.3(Summer 1991),p.424.。最近几年,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停战谈判问题,但已有研究更多地是考察谈判被长期拖延的原因、大国关系对停战谈判的影响以及诸如中立国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在停战谈判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鲜见有学者尝试对美国谋求利用心理战来影响谈判进程的内容加以研究*相关研究作品包括宋晓芹:《试论苏联对朝鲜停战谈判的影响》,《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邓峰:《追求霸权:杜鲁门政府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牛军:《朝鲜停战谁主沉浮?——中苏朝联盟与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冯东兴:《朝鲜停战中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东北师大学报》2015年第1期。。然而,档案资料显示,在停战谈判期间,心理战略委员会同样展开了积极活动。甚至早在1951年8月6日,它便迅速成立了A特别工作小组(Ad Hoc Panel “A”),由其负责制定紧急心理计划,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停战谈判破裂。有关该小组的成立过程、人员配备及其具体活动等档案资料集中收录在第24档案盒中。1951年9月18日,A特别工作小组制定的《朝鲜停战谈判破裂的起飞紧急计划》(J-19-d)正式获得批准。*PSB Files,Box 35,Emergency Plan “Takeoff” Break-off of Korean Armistice Negotiations,September 18,1951.
尽管从一开始就制定了应急计划,但由于谈判问题的复杂性,谈判进程并未完全遵循心理战略委员会的预想行进,这导致该机构在整个1952年不得不持续跟进考察该议题。出于知己知彼的考虑,心理战略委员会首先研究了中朝方面如何利用停战谈判寻求心理优势的内容,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对朝鲜停战谈判的心理宣传利用》等多份研究报告供美国决策层参考*PSB Files,Box 35,Psychological Propaganda Exploitation of Korean Armistice by Chinese Communists,May 1,1952.。此外,根据谈判形势的变化,该机构后续又先后制定了多份紧急指导文件和宣传指导文件,并向决策层提议考虑针对中国实施“宽边帽计划”,试图通过发送传单的方式打破中国国内对公共舆论的所谓“控制”*相关档案如PSB Files,Box 35,PSB Approved Plans “Broadbrim” and “Affiliate”,January 10,1952;PSB Files,Box 35,“Broadbrim”Proposal for Leaflet Drop on China,May 1,1952;PSB Files,Secretary of Defense Approval of the Plan that the Leaflet Drop over the Mainland of China as Outline in PSB Plan be neither Planned nor Prepared for at this Time,January 23,1952;PSB Files,Box 35,Implementation of Plans “Broadbrim” and “Affiliate”,March 19,1952;PSB Files,Box 35,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Plans Dealing with Truce Negotiations,May 1952.。有关1952年该机构如何跟进考察该问题的档案资料,集中收录在第35档案盒中。
(三)反映心理战略委员会就战俘遣返问题向决策层建言献策的情况。朝鲜停战谈判之所以迟迟没能达成协定,战俘遣返问题是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正因为不能就以何种方式遣返达成协议,朝鲜战场才没能早日实现休战*赵学功:《美国、中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孙学宝:《试论抗美援朝时期中朝与美国在“遣俘”问题上的斗争》,《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3期。。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馆藏档案资料显示,心理战略委员会对中国和朝鲜方面就战俘遣返问题可能采取的立场和举措进行了预估,并从心理层面对如何谈判提出了建议。考察伊始,该机构便对强制遣返中朝战俘表示反对,认为这“将会对美国未来多年的心理战行动造成严重后果”*PSB Files,Box 32,Repatriation of Prisoners of War,December 28,1951.,在此后漫长的谈判过程中它都坚持这一认知。第28档案盒重点收录了该机构如何开会讨论战俘遣返问题的档案资料。除在认知上不愿依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18条规定的在实际战事停止后便将战俘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外,该机构甚至还将中国和朝鲜战俘视为实施其“叛逃者项目”的重要资源,第32、33档案盒收录的部分档案资料就涉及该机构讨论利用中朝战俘在亚洲启动“叛逃者项目”的内容。此外,第35档案盒还收录有心理战略委员会同美国其他政府部门官员沟通,筹划利用朝鲜难民发动请愿运动来污蔑中国出兵朝鲜是“侵略”和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朝鲜的档案资料*相关档案如PSB Files,Box 35,Plan for North Korean Refugee Petition,December 29,1951;PSB Files,Box 35,Memorandum for Mr.John Sherman:Plan for North Korean Refugee Petition,January 2,1952;PSB Files,Box 35,Memorandum for Brig.General J.D.Balmer,January 7,1952.。毋庸置疑,心理战略委员会的上述判断和行动,进一步增加了战俘遣返问题解决的难度,无形中拉长了停战谈判的时长。深入解读这些以往并未引起学界关注的档案资料,有助于部分扭转一些欧美学者提出的正是中朝方面政策导致谈判长期拖延下去的错误指控*诚如有学者提出的那样:“美国学者在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早期研究中,只要不是从纯学术角度出发来探讨停战谈判,几乎都认为中朝方面的政策导致谈判长期拖延下去,美国的谈判政策就是要确保获得公平公正的停战协议。”参见邓峰:《美英学术界对朝鲜停战谈判的研究》,《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0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60页。。
三、心理战略委员会涉华档案的主要价值
鉴于国外学界对心理战略委员会的研究刚刚起步*到目前为止,除仅有少数几篇论文专门研究心理战略委员会外,国际学术界还没有出版讨论该机构活动的专著,一些论述50年代美国海外宣传的著作同样较少提及心理战略委员会。相关研究作品如Scott Lucas,“Campaigns of Truth: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and American Ideology,1951—1953”,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18,No.2 (May 1996);Mario Del Pero,“The United States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Italy,1948—1955”,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7,No.4(March 2001).,国内学者如果能够在史料搜集整理方面做好跟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保障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的同步发展。这既有助于推动国内文化冷战史研究深入发展,亦可以打破西方学者在该领域的话语权垄断,建构起中国学者自己的文化冷战研究话语体系,这应该是对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馆藏心理战略委员会档案资料加以推介的最重要的宏观价值。而将考察视角细化至其涉华档案部分,通过前述介绍不难看出,该机构制定的这些涉华档案资料涉及主题多样,且以前少有学者关注,对其开展系统的整理与研究,至少可以帮助研究者实现以下几方面突破。
首先,有助于完整重塑美国对华开展文化冷战的具象图谱。随着文化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对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以及其后美国对华开展文化冷战的内容开始受到学界重视,但对冷战初期阶段杜鲁门总统任期美国如何发动对华文化冷战的相关内容,到目前为止还鲜有学者进行具体研究,这就导致有关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研究出现了断层。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相关档案资料难以查找。但如同前文所述,心理战略委员会涉华档案资料不仅包括美国如何在心理战略层面考察中国问题并对中国海外宣传的特点、技巧等予以分析研究的内容,而且呈现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发动文化冷战的具体细节。而比对研究中美之间在朝鲜战场的心理战交锋,更是可以向读者直观展示二者各自开展文化冷战的特点,亦有助于研究者从中归结出二者各自的得失成败及出现这些结果的原因。
其次,为深化中美关系史研究找寻新的学术切入点,促使相关历史研究更加系统全面。虽然意识形态是影响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最重要因素,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在考察冷战初期的中美关系时,更多地还是选择从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角度予以阐释,鲜有学者通过挖掘双方心理、观念上存有的分歧和矛盾以及洞察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举措产生的心理效果,来分析它们对中美关系走向的影响。然而,心理战略委员会制定的系列档案资料特别是那些涉及国家心理战略计划讨论的档案资料,很好地呈现了当时美国决策层内心深处对中国的偏见和错误认识。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些偏见和错误认知,导致中美关系更加敌对、恶化。系统整理这些档案资料并对之展开认真解读,势必会对中美关系史论题提供新的研究选题和阐释内容。
再次,为研究传统的朝鲜战争问题提供新视角和新史料。朝鲜战争长期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此背景下,如何推陈出新,对已有研究加以补充和完善,抑或实现对已有研究的修正和创新,就成为研究者不得不考虑的难题。杜鲁门总统图书馆收录的心理战略委员会涉华档案中的很多内容恰巧与朝鲜战争直接相关,且其考察内容尚未引起学界太多关注,对之加以系统整理与研究,无疑会为朝鲜停战谈判、战俘遣返等旧有问题提供一些新的解读路径。例如,以往学者在研究朝鲜停战谈判问题时,更为关注的是美国白宫、国务院、军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多地是考察战场局势演变对停火谈判的影响,而对美国如何尝试在心理战略层面进行系统谋划,以迫使中朝双方在谈判过程中作出让步的内容,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但这些内容正是心理战略委员会的活动重点。
当然,在强调这批档案所具有的独特史料价值的同时,需要提醒研究者注意的是,该机构存续期间,正值冷战刚刚兴起,对抗双方可谓神经紧绷,该机构制定的系列文件不可避免打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烙印,亦使该机构所作的一些研究和评估并不是特别客观。在利用这些档案资料考察相关问题特别是研究较为敏感的朝鲜战争问题时,最好将其与中国和前苏联的档案资料加以比对考察,进而更好地提升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此外,本文介绍的是杜鲁门总统任期心理战略委员会运作情况的档案资料,但该机构一直运作到1953年9月,才被新成立的行动协调委员会代替*尽管杜鲁门政府成立心理战略委员会,很大程度上是希望由该机构来做好行动协调工作,将美国心理战效能最大化。但同美国决策层初衷大相径庭的是,由于心理战略委员会并没有强制力,加之该机构为凸显其重要性,不断扩大心理战的内涵和外延,导致它制定的系列心理战略计划并没有得到切实落实,这也成为该机构最终被裁撤的根本原因。有关心理战略委员会缺少执行力等内容的更多论述,可参见赵继珂、贺飞:《冷战初期美国对法国的心理战研究——以PSB D—14c的制订与实施为例》,《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心理战略委员会档案资料,被集中收录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图书馆中。因访美期间的时间限制,笔者并没有前往该馆搜集这部分档案资料,希望其他学者以后可以对此部分档案资料加以搜集并略作推介,助推国内学界更为全面地开展心理战略委员会的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