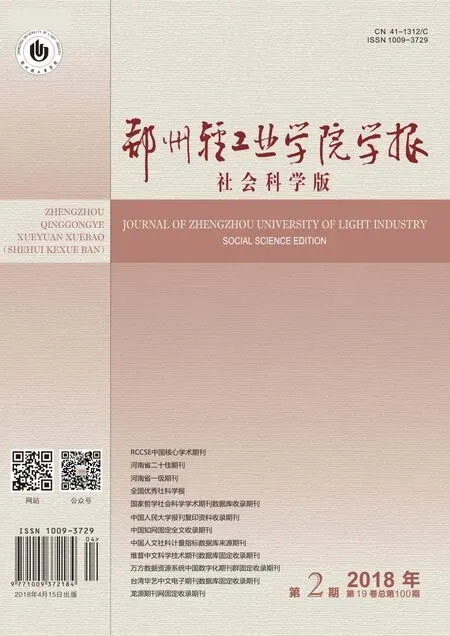感受促发的行动有可能是道德行动吗?
——基于马克斯·舍勒对感受的现象学分析
黄晶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00025
康德在其道德学说中坚决拒绝把感受促发的行动当作道德行动,从此,“道德不能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这一原则几乎成了支配伦理学研究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情感的本质缺乏了解,不加区分地把情感领域的所有现象都视作一种混乱的感性状态。假如救将入井之孺子的不忍感受本质上与促使人进食的饥饿感受是一样的,谁又会把由不忍这种感受促发的救人行动视作道德行动呢?但是,由不忍促发的救人行动与由饥饿促发的进食行动显然有着本质区别,因而,不忍的感受与饥饿的感受也相应地具有本质的差别。这个案例引发了一个普遍的问题:由某种特殊感受促发的行动有没有可能是一种道德行动呢?本文拟借助舍勒对感受的现象学分析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对行动促发动机的不同解释路向
一个行动是如何发生的,人们往往会有两种解释路向:机械因果论和动机促发论。机械因果论是把人们的行动界定为心理—生理意义上的行为。比如,某人挥拳打人,机械因果论会认为这是此人的愤怒作为一种力量作用于神经、带动肌肉然后做出了挥拳这一动作。这种解释路向只触及人之作为心理—生理的存在,而没触及其作为道德的存在,因而根本不能区分道德行动和非道德行动。人可能是为了获取利益也可能是出于同情而做出了救人的行动,如果这两种行动表现相同,照机械因果论的解释,它们就是性质完全一样的行动。而动机促发论的解释模式则是另外的路向,它根本不关心行动发生的心理—生理过程,而只关注促发这个行动的动机,即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动机促发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这种解释路向,能够使我们在具有相同外表的行动之间做出区分。按照这种解释,出于履行职责的动机而救人和出于获利的动机而救人,即使这两种行动表现得一模一样,它们在本质上也是两种不同的行动。动机是不是道德的,决定了由动机促发的行动是不是道德的。因而,考察一个行动的道德本质实际上就是考察促发行动之动机的道德本质。照此而论,不是机械因果论而是动机促发论才能通达行动的本质。
问题在于,由感受促发的行动又是怎么回事呢?毫无疑问,感受的确能够促发行动。因不忍这种感受而救将入井之孺子,这当然是由感受促发的行动。但是在这里,动机促发论的解释遭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救孺子之人既不是出于“纳交孺子父母”的动机而救了孺子,也不是出于“邀誉于邻里乡党”的动机而救了孺子,他只是因为不忍。乍一看,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动机不动机的问题。但是进一步考量会发现,由感受促发的行动照旧可以纳入动机论的解释范围。人们因饥寒感而进食加衣,在这里,人们做出进食加衣的行动是出于追求不饥不寒的动机。同样,在孺子将入于井这个案例中,救人者虽然没有其他外在的动机,但也是出于“消除不忍”这一难受感受的动机而做出救人行为。这种解释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出于不忍而救人的行动与因饥寒感而进食穿衣的行动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因饥寒而进食穿衣的行动不是道德行动,因不忍而救孺子的行动自然也就不是道德行动了。这种解释也恰恰是康德拒绝把任何由感受促发的行动当成道德行动的原因。而且,基于这一看法,康德走得更远。在他看来,消除饥寒的动机、消除不忍的动机与主动追求快感的动机没有本质区别。所以,他把任何由感受(对道德律令的敬重感除外)促发的行动都归结为出于追求快乐这一动机而做出的行动。康德的这一论断预设着两个前提:一是除敬重感之外,所有情感现象共享同一个本质,即所有的情感都是一种感官状态;二是所有由感受促发的行动都可以归结为以追求快乐为动机的行动,即不是感受本身促发了行动,而是追求消除某种不爽感受或获取某种爽快感受而带来的快乐促发了行动。因此,对于康德来说,救孺子的不忍感受与欲进食的饥饿感受没有本质差异,因为前者只是出于消除不忍感的动机,而后者也只是出于消除饥饿感的动机。
二、舍勒基于感受与感受状态区分的行动价值分析
我们可以将舍勒对感受所做的现象学分析之结论,概括为以下四点:其一,并非情感领域的所有现象都是感官状态,而是可以区分为具有不同性质的感受状态和感受;其二,感受状态是纯粹的感官状态,而感受则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特征;其三,具有意向性特征的感受,其意向对象是价值;其四,感受具有实践的特性,它可以促发意志并带出实际的行动。
舍勒认为,“我们首先将意向的对某事物的感受区别于所有单纯的感受状态”[1]379,在情感领域内部有两种绝然不同的东西:感受和感受状态。英国经验论者和康德所说的那种纯粹感官意义上的情感是身体的纯粹感觉,即不带有意向性的感官状态。但感官状态不能囊括情感的全部,在情感领域内部还存在着一类与感受状态迥异的东西,即感受。对于这一区分,舍勒列举了下面这个关键性的例子[2]:
当我“痛于那种疼痛”“忍受它”“挺受它”、甚至可能“喜悦它”时,这里所涉及的更多的是一些变换不定的事实组成。在这里,在感受功能知性中发生变更的东西,肯定不是这个疼痛状态。
这个例子表明,感受和感受状态是不同的东西,非常直观。对于疼痛,我们可以有4种不同的感受,即我们可以痛,可以忍受,可以挺着,甚至有人因为某种原因还可以喜悦。疼痛是我们身体的某种感受状态,对身体疼痛的痛苦或者对身体疼痛的享受是我们的感受。但是能否将疼痛和对疼痛的痛苦或喜悦都归结为身体的某种状态呢?疼痛是一种身体上的感官状态,但享受疼痛的喜悦绝不是,它是心灵或者情感能力对疼痛的一种态度。基于此,舍勒将疼痛这类感官状态称为感受状态,将心灵这种反应称为感受,并认为“感受状态与感受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属于内容和显现,而后者属于接受它们的功能”[1]380。
对待同一种疼痛竟然可以有4种感受或者说有4种接受态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4种感受所意指的对象都是疼痛呢?人们痛于疼痛、喜悦于疼痛,但痛和喜悦的意向对象并非疼痛,而是疼痛所承载的东西。因疼痛而痛苦的人会把疼痛视为糟糕的、坏的东西;因疼痛而喜悦的人会把疼痛视为好的、有利的东西,如医生告诉疼痛的人,疼痛是大病将愈的征兆。在这里,疼痛仅是好或坏的载体;在这里,与痛和喜悦这两种感受对应的不是疼痛,而是疼痛所承载的好或坏的价值意蕴。可见,感受并非没有任何指向的身体状态,它们总是意向着某些东西,在这里痛苦所意向的是坏,而喜悦所意向的是好。但是感受状态是无客体的,就算它与客体有所关联,也不是一种原初的意向关联,而是通过联想后补地与对象建立联系。比如,一位工人在施工过程中突然出现疼痛,这种疼痛只能通过工人的观察才能将它与某种导致疼痛的东西联系起来,而不是疼痛本来就有一个原初的客体,因为疼痛不具有意向性特征。所以舍勒这样描述感受的意向本质:“感受并不是要么直接和一个对象外在地被放置在一起,要么通过表象(它机械偶然地或通过单纯反思关联而与感受内容结合在一起)而和一个对象被外在地放置在一起,相反,感受活动原初地指向一个特有的对象,这便是价值。”[1]382
因此在舍勒看来,同一个载体可以承载不同的价值,同一个东西对于不同的人显示的价值亦不一样,这就使得人们有可能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态度。但是,感受和感受对象的这种意向性关系具有严格的对应性。你在把握到事物的“坏”时,不可能有“喜悦”的感受;当你“喜悦”某事物时,它对于你来说不可能是“坏”的。你也不可能“恨”你的朋友,当你“恨”他时,他绝不是以朋友的身份展现给你的;你也不可能“爱”你的敌人,当你“爱”他时,他肯定不是以“敌人”的身份展示给你的。当我们听到有人说他恨友爱敌时,我们显然知道,至少在这一刻对于他来说友已变敌、敌已成友了。在这个例子中,这个人只是“朋友”和“敌人”的载体,他的“爱”和“恨”这两种感受指向的不是这个人,而是指向在他身上承载着的“朋友”和“敌人”的价值属性。而感受所意向的对象,比如好、坏、敌、友,就是舍勒所说的价值。
舍勒明确指出,“所有对某物的意欲都已经预设了对这个某物的价值的感受”[1]110,“感受性的察识直接规定着我的意欲”[1]314。这表明在以价值作为意向对象的感受与促发实际行动的意欲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关联,这意味着感受具有实践特性。从日常经验来看,感受的这一实践特性很容易被察觉到。比如,对“有人掉落河中”这个事态之负面价值的感受,直接地激发“救人”的意欲;在救人意欲兴起的情况下,救人的行动也就被带出来了。因此,具有意向性特征的感受通过意欲这一中介而与实际行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通过舍勒对感受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感受并非混乱的感受状态,而是一种感受性的认识,并且任何感受都蕴含着价值指向性;同时,感受也并非纯粹的认知,它是一种能够促发行动的认知。基于对感受的这一现象学的洞见,我们可以说,由感受促发的行动绝非一种盲目的行动,而是基于对价值的明察基础之上的合乎情理的行动。这一点将在下面的这个例子[3]中得到印证。
特洛伊的国王普里阿摩斯深夜去到阿喀琉斯的营帐中,想要回自己儿子赫克托耳的尸体。作为与特洛伊敌对的希腊联盟中最勇敢将领的阿喀琉斯,对于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杀死自己亲人之凶手的父亲、敌对国的国王,他是非常憎恨的;但普里阿摩斯说,他不过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来为战死的儿子收尸的,于是阿喀琉斯对他产生了深深敬意,并且把赫克托耳的尸体还给了他。
在这里,阿喀琉斯对普里阿摩斯产生了恨和敬两种感受,但这两种感受并非无缘无故的。这里的恨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且也是一种认识,因为在恨的同时,普里阿摩斯必定是被阿喀琉斯视作“凶手的父亲和敌对国的国王”,因为在此情境中,恨这种意向的对象必定是敌。假如阿喀琉斯对待普里阿摩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恨转变成敬重,那么,普里阿摩斯已经不再是敌人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爱敌人而恨朋友。倘若这时阿喀琉斯杀掉普里阿摩斯,那么这一由恨促发的行动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对敌人这一价值明察之上的行动。同样,阿喀琉斯因为敬重普里阿莫斯而放了他,这一由敬重促发的行动也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对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情感这一价值的明察之上的行动。
基于此,我们认为,康德将所有由感受促发的行动,全都无差别地视作以追求快乐为动机的行动的观点无法成立。因为基于价值明察的感受及其行动,并无动机因素参与其中,在这里体现的是感受与行动的直接的本质关联性。比如,在“孺子将入于井”这个情境中,救孺子之人的行动哪里还用得着由“消除不忍这种难受状态”作动机来促发呢?此时应是这种情形:对“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事态所承载的负价值之明察,必然伴随不忍之感受,并直接地促发救人的意欲,而后就产生了救人的实际行动。
通过对从价值感受到实际行动的实施这个完整序列及其逻辑的揭示,我们就慢慢地了解了现象学意义上的“道德行动”这一概念。在舍勒看来,只有基于价值感受之上的实际行动才是真正的道德行动。这一界定实则是将价值感受作为伦理的基础,从而将情感与道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感受与伦理的结合,对于感受理论和伦理学来说都是一种突破。它破除了以往伦理学不能建立在感情之上的教条。这一教条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所有的情感都是某种杂乱无章的感官状态。出于这一偏见,人们将所有的情感现象都视为均质的、平面的某种肌体上的状态。这就意味着,某种崇高的和神圣的感受与冰水浇在身上带来的冷的感官状态处在同一平面而没有高低之分;这也意味着,审美的愉悦与肚子饥饿这种感官状态是同类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照此而论,道德的或者伦理的行动就当然不能建立在感受之上。比如,人们总不能说由饥渴等一些感官状态所促发的行动是道德行动吧,并且,由感官状态所促发的行动很可能还是罪恶的,如一个人因饥饿而偷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偏见,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是因为人们误解了感受的本质,是将感受与感受状态混淆了。殊不知,感受是人的情性能力,而感受状态则是肌体对外界刺激的纯粹接受,其在本质上是一种感官能力。同时,人们也误解了感受与行动之间的本质联系,以为是感受状态而不是感受引发意欲进而促发行动的。比如,饥饿是肌体受刺激的结果,对于这种感受状态,人们可以有多种感受,人们可以难受于饥饿,也可以享受于饥饿,只有当他对饥饿感到难受时,才会做出吃东西的行动。因而,不是饥饿本身而是对饥饿这一事态的价值感受促发了意欲从而引发了行动。感受必定有其意向价值,而价值自身则有着严格的秩序和高低等级。由于价值有着性质上的差异和高低等级,所以与价值相对应的感受也有差异和等级。
三、由感受促发的行动在何种意义上具有道德的意蕴?
通过对感受这一特殊意向行为的分析,舍勒指出,由感受促发的行动与价值有着本质关联,由此这种行动就蕴含着某种深刻的情理,而不是简单的动物式的刺激—反应的行动模式。舍勒把这种基于价值感受(明察)之上的行动称为道德行动。这一做法的实质是基于现象学式的伦理学对道德性这一重要概念的重新界定。将这一界定与康德对道德性的界定进行对照,我们就更能看清现象学意义上的道德性的内涵及其在伦理学上的意义,由此我们也更能辨析由感受促发的行动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道德性。
康德认为,“道德性的唯一的原则存在于对法则的一切质料(亦即一个被欲求的客体)的独立性之中,同时也存在于通过一个准则必须能够有的纯然普遍立法形式而对任意的规定中”[4]。这段话集中地展现了康德对于道德性的界定。他认为,道德性包含了两个条件:其一,任何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必须独立于被欲求的客体(质料),即任何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都不能直接由欲求对象来激发,如努力工作的意志不能由安度晚年这一目的来促发,否则努力工作这一行动就不具有道德含义;其二,任何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必须由“纯然普遍立法形式”来进行规定,即任何促发实际行动的意志必须由形式性的普遍道德法则来促发,如努力工作的意志必须要由道德法则来促发,否则努力工作这一实际行动就不具有道德含义。由此可见,只有由道德法则促发意志而引发的行动才是道德行动——道德行动与道德法则的这种本质关联构成了康德道德性概念的核心内涵。
基于康德对道德性的这一界定,情感自然就被排除在了道德之外。因为,任何情感促发意志的行动都不可能符合道德性的规定,不管这种情感是感官性的,还是精神性的,在道德性面前,所有的情感都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由感受促发意志而引发的行动,既不可能是道德行动,也不可能具有道德含义。
然而现象学视域中的道德性概念与康德对它的界定完全不同,舍勒截然相反地把情感作为道德性的本质属性。在舍勒看来,道德行动就是基于对价值的感受促发意欲而引发的行动。感受并非一种杂乱无章的感官状态,比如身体的疼痛之类,而是具有意向性特征并且以价值作为对象的意向行动。这样的意向行动因其能够促发行动而具有实践意义,因此它不同于纯粹的认知意向行动,而是具有道德含义的伦理意向行动。这也意味着,在舍勒眼中,一些公认的道德行动若不是由出于价值明察而来的感受引发出来,它们就没有道德涵义。以此而论,康德意义上的由道德法则促发的行动根本不能算作道德行动,因为这类行动不是由具有伦理意向特征的感受所引发的。
下面我们仍以孟子“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来说明康德式的道德性与舍勒式的道德性之间的差别。在“孺子将入于井”的场景中,对于舍勒来说,一个人救了将要落井的孺子,他若是试图交好孺子父母或者邀誉于乡里,则此救人行动绝非道德行动。因为他不是感受并明察到“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事态的价值而采取的救人行动,而是通过对一个目标的设定(获取名誉或者取得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引发的行动。另外,假如他在看见这一场景之时虽没有一种“怵惕恻隐”的不忍之情,但尚有一种应当救人性命的意识,即出于“应当”这一强制意识而救了孺子,这一行动照样不是道德行动。因为他没有感受并明察到这一事态的价值,同时也没有关于“孺子将入于井”这一事态的急迫感受,他实则处在一种价值盲目状态。看到“孺子将入于井”,他不假思索,恻隐不忍之情油然而生,立马促发他救人的意欲,然后飞快地跑过去救孺子脱离危险之境。他这么做既不是为了要交好于小孩的父母,又不是要在邻里获得好名声,也不是由于某种应当意识的强制,而纯粹就是出于不忍,出于看到“孺子将入于井”之时油然而生的某种价值感受。在舍勒看来,这样的行动才是真正的道德行动。而对于康德来说,只有出于“我应当救人”的纯然的“应当”,才是道德行动;而且这一行动越是纯粹即越不夹杂情感因素,它就越具有道德意蕴。该如何把握康德的“道德性”概念呢?对此,我们或许可以假设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场景中,假设某人与孺子的父亲有仇,见“孺子将入于井”,他不但没有不忍之心,而且还有些幸灾乐祸,此时出于应当救人的道德法则意识,在这一法则的强制之下,他仍旧做出了救孺子的行动。对于康德来说,这一行动就是比较纯粹的道德行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依照康德对于道德性的规定,感受促发的行动不具有道德的意蕴;但是,依照舍勒对于道德性的界定,感受促发的行动具有道德的意蕴。
:
[1] 马克斯·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 SCHELER Max.Der formalismus in der ethik und die materiale wertethik[M].Franke Verlag Bern Und Müchen,1980:261.
[3] 荷马.伊利亚特[M].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570.
[4]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C].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