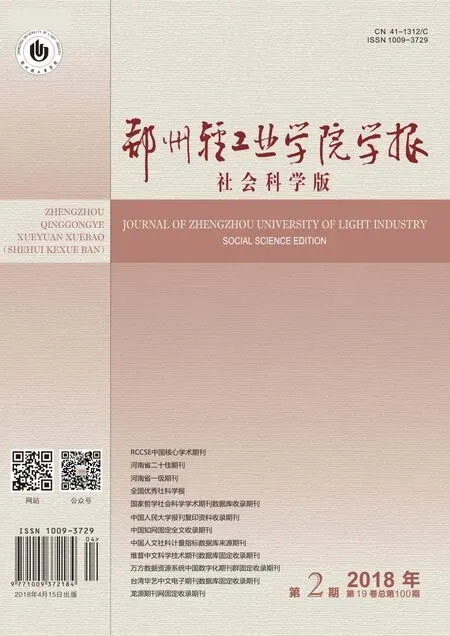论科技与伦理相契合的价值原则
詹秀娟
安徽大学 哲学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价值活动是人们在接受价值的过程中做出的具体选择,这类活动包含有多个要素,不仅有价值选择的主体和客体,还有价值选择的方式和背景,这些要素都会影响到价值的选择与展现,这就是价值多元化的原因。价值从不同角度区分,有经济价值,还有人文价值;有理论价值,还有实践价值;有当下价值,还有未来价值。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对这些价值进行不同选择,与我们怎样回答“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做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是善的和幸福的生活”[1]这一系列问题紧密相关。科技与伦理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两者之间的契合关系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当然也面临着质疑。这种质疑源于这样一个重要难题:如何界定“应当”与“善”。鉴于此,本文拟基于由多元化的价值而建构起来的选择机制来回应这种质疑,并论证科技与伦理相契合的价值原则。
一、公益性与功利性的统一
科学社会学的奠基者、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R.K.默顿认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作为惯例的规则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2]。科学的宗旨是认识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就是认识的成果(结论),科学活动不带功利性,其成果属于全人类。科学的这一本质属性表明,公有性和无私性的精神气质奠定了科学的公益性。科学的目的不在于谋取自身的利益,而在于通过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来为人类谋幸福;科学家和科研团体在无私利的前提下进行科研活动,并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公布于众,与人类共享,以期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幸福。因此,公益性不仅是科学的品性和根本,也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进行科研活动的前提和主旨,是科研活动的精神魅力之所在。
现代科学的公益性不同于古希腊科学的理论品性。古希腊科学作为一种纯理论活动,其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所以其目的不在于改变世界,而在于认识世界。而现代科学的公益性直接体现为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这是其与古希腊科学的最大区别。小科学时代科学的公益性也不同于大科学时代科学的公益性。小科学时代的科学活动基本上是科学家个人的活动,其与技术、生产、应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速度远不及大科学时代科学活动;小科学时代科学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世界,提高人们生活品质,其改变世界和人们生活的速度缓慢,有的甚至会经过几千年才能对世界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而大科学时代科学的公益性非常明显,世界和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受到科学的影响。这不仅与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活动的组织性即政府性有关,而且还与大科学时代的科学与技术、生产、应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速度既快又频繁有关。科学的公益性主要是针对大科学时代的科学而言的,大科学时代科学的公益性不仅有益于人们科学地认识世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而且还能较为迅速地改变世界,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给人类社会带来幸福。
技术不同于科学,其品性在于它的功利性。在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技术显然远远不单纯是思想的具体化。从根本上说,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3]。通过发明和使用技术,人们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爱好、欲望,也体现出了对价值的追求,这两点决定了技术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表达着一种建立在人们的需要和欲望的基础之上的价值诉求。人们不可能满足自己所有的需要和欲望,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去制造器具、发明和使用技术,因而当他人用技术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和欲望时,我们只有提供相应的服务、进行等价交换,才能享用这种技术。这是技术功利性的最根本的表现方式。无论是古代的技艺(经验的技术)、近代的技术(设备的技术),还是现代的技术(科学的技术),技术的功利性都没有发生改变。技术的功利性虽然也表现在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为人们的生活创造幸福,但它不同于科学的公益性。因而技术不是完全基于大众的幸福来使用,甚或会因一己之私利而对他人造成伤害。
不过,科学的公益性和技术的功利性的区分在现代渐渐模糊,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趋势导致科学和技术的性质难以明确区分,公益性和功利性也很难截然分开。当科学为实现自己的理论目的开始向技术订购工具时,科学的公益性已经与技术的功利性联系在一起;当科学的理论研究离不开既精巧又具有强大功能的技术时,科学的公益性日渐为技术的功利性所影响;当技术的“座架”之本质完全支配着我们改造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方式时,向技术订购工具的科学亦将落入此渊薮。在这种境况下,科学的公益性会向技术的功利性发生偏移。在此过程中,科学的公益性不会遭到完全的抛弃,但在技术功利性的熏陶之下,“‘为科学而科学’的清高和超脱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4],科学的无条件的公益性的精神气质将会发生某种变化,成为有条件的公益性,从而与技术的功利性融合在一起。在大科学时代,个人需要若想得到满足,必须与他人进行合作以共同完成某项研究,其中必然会涉及多方的利益,并且由于研究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需要巨额的资金,投资者可能是个人、企业和组织,也可能是政府。这样,科研必然会受到投资者的制约,科研的功利性就会因此变得更为明显,科学的公益性会向技术的功利性发生偏移,使得科学无条件的公益性成为有条件的公益性,从而与技术的功利性逐渐融合在一起。
从当下来看,科学的公益性向技术的功利性的偏移,有益于促进科学的理论研究和技术的应用研究水平的提高,但从长远来看,则不利于科学的理论研究。当科学的纯粹理论研究受到技术功利性的巨大影响时,科学研究将会夹杂着更多的私利,有悖于科学的公有性和无私利的精神气质,从而从源头上玷污科学的理论研究;一旦这种科学研究成果投入到技术、生产之中,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将直接危害人们的安全和幸福,使科学和技术的本性发生扭曲。这一点正是当代科技发展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些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根本上乃是“源于不同利益主体在利益竞争中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利用”[5]。惟有改变这种境况,才能提升科学的理论研究和技术水平。公益性是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但对公益性的追求也不能脱离科研活动的现实境况。现代科研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力量即技术手段的支撑,因而其势必会受到功利性的影响。在现代科研活动中,我们既不能仅坚持科学的公益性原则,也不能忽视在科研活动中科学对功利性的追求,只是对功利性的追求要以公益性原则为前提和基础。唯其如此,才能坚守科学的学术灵魂,体现其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
公益性的价值原则体现了整体性的文化特征,功利性的价值原则体现了个体性的文化特征。科研在现代的双重特征,要求我们在进行科研活动时,必须体现并且贯彻公益性与功利性相统一的原则,不仅要坚持公益性的价值原则,还要坚持功利性的价值原则。公益性是科学家价值选择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他们价值选择的归宿,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在于为人们的幸福谋福利,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功利性是在公益性的基础上根据科研的现代特性而提出来的,科学研究应立足于公益性原则去谋取个体的利益和幸福。在对某一领域进行研究和开发的时候,其科研方向应符合公众和整个人类利益,当自身的研究或者投资者的利益与公众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相悖的时候,科研工作者应顶住外部投资者的压力,坚守自己的学术灵魂,坚持公众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人类社会创造幸福,以体现自身的根本价值。
二、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统一
科技与伦理相契合的第二个价值原则是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统一。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关系是在公益性与功利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公益性与功利性统一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幸福生活是公益性的具体展现,也是公益性的根本目的,坚持公益性的目的在于创造幸福生活;科研价值是功利性的具体展现,功利性通过科研价值的体现而得以通达和贯彻。公益性和功利性的这种关系,决定了科研价值要以幸福生活的实现为评价标准,一旦二者之间发生冲突,惟有放弃科研的功利价值,选择幸福生活。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其一,混沌的统一关系。这种关系与科学的内在性质及其社会地位紧密相关。古希腊的科学作为一种理论,与当时的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理解直接联系在一起。古希腊人认为,幸福生活不在于用行动来改变周围的世界,而在于通过对事物自然本性进行理解和观察,由沉思抵达幸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沉思是唯一因自身之故而被人们喜爱的活动”[6],沉思作为合乎自身的活动,它必定是完善的幸福,这种幸福通过神思即对事物本质的沉思而体现出来。虽然沉思式的幸福生活超乎世俗生活,却为凡人所向往,故而也奠定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理解的基调。以这种基调为根本的早期科学,服膺于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理解,其科研价值在于通过沉思来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服务。所以,在古希腊重视沉思的精神气氛中,科研价值和幸福生活混沌地统一在一起,没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明确区分。
其二,又统一又分离的复杂状态。这与科学在近现代内在性质的变化密切相关。近代社会的变革与科学密不可分。科学不仅加快了近代社会的变革速度,而且提高了近代社会的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人们创造幸福生活提供了动力和活力,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统一性得以极大提高。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态发生了变革,以研究型的方式呈现出来,“任何一门科学作为研究都以对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的策划为根据”[7],作为研究型的科学在对对象区域的筹划之际,首先设定的是对存在者的筹划,其通过专门化的方法来操纵存在者、预测存在者的状况,从而支配着存在者。通过这种筹划,作为研究型的科学摆置着存在者,在此摆置中,人将自己摆置成存在者关系的中心。这样,人在不断地摆置中,最后也把自己作为对象进行摆置;存在者整体只有被人摆置,它才是存在着的。换句话说,作为研究型的科学支配着对人类和世界的摆置。于是,人和存在者整体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直接改变着人们对现实的幸福生活的理解。从这个层面来看,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开始处于分离的状态。
其三,有机的内在统一关系。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之间的分离并非一直持续下去。科学之所以有时与幸福生活相悖,其原因就在于作为研究型的科学在对对象的支配中把对象视为可摆置的对象和手段,但生活并非手段而是目标,而且此目标并非中期目标,而是一个终极目标、一种自我目的[8]。在当代,科学被嵌入在生活本身之中,现实生活是科学的出发点与归宿。幸福生活不在于对作为手段的对象的控制和实现,而在于把对象作为一个终极目标去认识和理解,进而借此实现一种自我目的。科学活动不是通过计算、计划和研究对生活施行暴力,而是在对生活本身进行解蔽的过程中,完成生活的托付,实现生活的目的。于是,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又实现了有机统一。
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在历史中呈现出来的三重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科研价值的不同维度。古希腊科学的价值与希腊人对幸福的理解内在统一,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直接融合在一起;而近现代的科研开始偏离幸福生活这一目标,其科研价值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根本;当代科技发展对人们生活世界的渗透,从某种程度而言支配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目的的理解,但科研工作者固守初心,坚持科学的原初价值追求,即以幸福生活作为自己最高的价值标准。“科学研究是运思无禁区、验证有禁区”[9],在理论上,科研工作者可以随意进行理论设想,但在现实行动和对象性活动中,则要受到相应的伦理规则的限制,以使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保持和谐的状态,从而使科研在促进幸福生活的维度上实现自身的价值。
今天,科研工作者借助精深的科学理论和精巧的技术手段,可以无止境地去探索研究,科研的能力与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科研活动的开展不仅与对享乐欲望的合理认知有关,还与对能力、完成的冲动的正确态度有关。“当我们从抑制享乐欲望过渡到抑制能力与实施,过渡到抑制完成的冲动时,我们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10]科研工作者不能任由研究能力和完成的冲动泛滥,在科研中应该基于对幸福生活的沉思,对能力、冲动进行规约,促成能力的实施、完成的冲动与生活目的的和谐统一。在幸福生活的价值维度内,当代的科技发展在研究能力与完成的冲动方面,应该设置相应的界线,坚持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的内在统一。
三、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统一
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统一是对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内在统一关系的进一步延伸,是基于当代与未来对科研价值与幸福生活之关系的阐释。生活是一个统一整体,我们无法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完全割裂开来,否则,生活将是破碎不堪的。价值的意义与作用不仅影响着当下,还影响着未来。因而从生活和价值的本性来看,我们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即关注生活和价值的持续性影响,关注未来,而不能仅仅专注于当下。可持续发展应以公平为前提,这种公平,“既指代内公平,又指代际公平”[11],价值理想着眼代际公平,从未来的视角进行审慎的选择,理想的价值形态不仅包含当下的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和谐,而且还包含未来的幸福生活与科研价值的和谐。因而价值理想的现实必然要求当下的行为者在双重的和谐状态下审慎地行动,做出选择;价值现实须从未来的视角去进行度量、采取行动。因此,价值理想和价值现实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进行选择,但两者在现实选择过程中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关系样态,以致无法在两者之间作出简单的割裂处理。
从生活和价值相统一的视角来看待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科学理论都面临着处理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关系,但由于科学理论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样态,因而在不同时期,科学理论对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之关系的处理也不一样。古希腊科学的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内在地融为一体,其价值理想高于价值现实。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慢慢改变了古希腊科学的这种理念,这种改变在当代科学中表现得最为彻底。当然这种改变并非完全抛弃了价值理想,而只是意味着观察问题的视角发生了转移。近现代科学和当代科学虽同样面临着从理想层面出发来提升现实高度的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不仅仅是纯粹地表现为理论,而且还在于它们是在对理论进行超越和创新的基础上去改变世界。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人类知识的增加使我们能够准确地预见我们自身的行为对后代生存的影响”[12]。由此可见,与古希腊科学相比,近现代科学、当代科学在理解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之关系的维度上发生了偏移,即它们开始从当下与未来的关系视角去看待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的关系和存在的问题。
从当代科技发展走偏方向所带来的可怕后果来看,“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就是在技术文明时代下对全人类行为的否决性任务。人类行为已经变得无所不能,即使不在其创造性的潜在方面,至少在其破坏性的潜在方面是这样的。作为人类自身生存的必备条件之一,这种关注显而易见包括对这个行星上的所有物质的未来的关注”[6]136。当代科技的发展无论是在资源利用方面,还是在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方面,都对未来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威胁,削弱了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可能性,生活的整体性要求当代科研活动在对价值的追求中也要考虑到其自身价值的整体性。科研活动在与当代人的幸福生活保持和谐的同时,也要顾及到未来人们的幸福生活。科研工作者在做出价值选择时,必须把对未来的关注作为自身生存的必备条件,以维护未来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和能力。
对未来的关注不仅是由于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对下一代的责任,而且还关系到我们自身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既是我们的生活不可缺少的力量支撑、我们的生存力量的展现,也是我们的生活得以延续的动力。生活的意义之内涵极其丰富,并且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中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在科学、技术、生产日益一体化的时代,我们在赋予生活意义的同时,不能在相对狭隘的层面对待赋予意义的能力,不能在相对自我封闭的空间中进行发掘和培养,否则它最终会损害人们对意义的追求和获取。在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我们获取意义的能力也必须保持开放,这种开放不仅包括在空间上对全球保持开放,而且包括在时间上对未来保持开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开放和坦诚的环境中,不仅关照当下生活的意义,而且关照未来生活的意义,从而使我们在整体的意义上维护生活的和谐。
当代科技发展对未来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我们生活的意义与未来生活意义的开放关联,要求当代科技在规划和发展中一定要引入未来的维度。这就对科研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在科研活动中一定要把未来人类的幸福纳入自己的所思和所行中。在价值理想与价值现实之间,人们不能为了科研的现实价值而损害未来人类的权利和幸福,而应在对未来的关照中,在价值现实不损害价值理想的前提下,创造自身的现实价值;在对科技的研究和应用的风险评估中,应该在价值现实的面前捍卫价值理想,不削弱和侵犯后代子孙的利益和幸福。科研工作者既不能无止境地摄取资源,抢夺未来人们的生存资源;也不能一味地开发,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给后代的生存留下后患无穷的烂摊子;更不能随意应用科学理论更改对生命本身和生活意义的理解。
:
[1] 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
[2] MERTON R K.The socilology of science: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269-270.
[3] 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200.
[4] 曹南燕.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J].哲学研究,2000(1):48.
[5] 程现昆.科技伦理研究论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3.
[6] ARISTOTLE.The nicomachean ethic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65.
[7]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M].孙周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893.
[8] 奥特弗利德·赫费.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M].邓安庆,朱更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20.
[9] 韩东屏,欧阳康.疑难与前言:科技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0.
[10]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M].张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7.
[11]陈昌曙.哲学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54.
[12]廖小平.伦理的代际之维——代际伦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