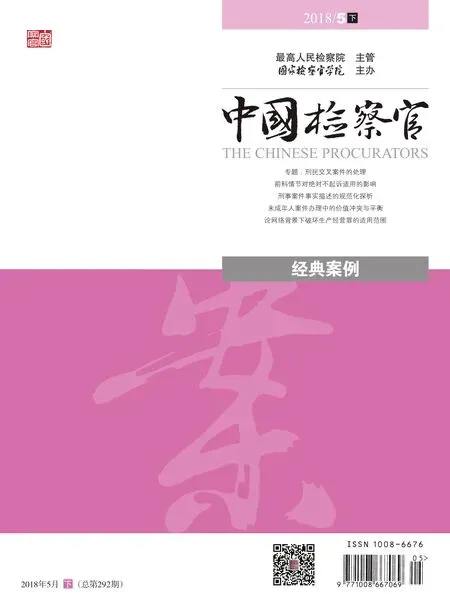高速公路闯卡逃费行为入罪分析
文◎程绍燕
一、基本案情
2017年7月25日凌晨1时许,犯罪嫌疑人朱某驾驶一辆车牌号为京AM06XX的蓝色货车通过京平高速某收费站出京出口时,不交费直接撞杆通行后,被高速公路员工和民警当场拦截。
经查,朱某生活在河北省三河市,平时驾驶自家蓝色货车进京给各个工地送砖。案发前,朱某已经以该种方式闯卡逃交高速费56次,直至第57次被抓。
被抓获后,朱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顺义公安分局以朱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其刑事拘留。因不清楚朱某每次上高速的具体位置,根据规定要按照全程收费,朱某家属共计补交高速费15390元。[1]
二、分歧意见
关于高速公路闯卡逃费行为,一线司法实务部门有过不少探讨,观点莫衷一是,由于缺乏权威学术观点支持,司法解释亦未明确规定,因此,对其定性问题一直争议较大。但实际上,除了定性问题,该类案件在数额认定、入罪路径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就定性方面的争议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诈骗罪。关于定性为诈骗罪的观点较多,这里选取其中相对较为严密、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即认为“肇事者(事前预谋)隐瞒在高速公路出口处闯关逃避缴纳过路费之事实而对高速公路入口处的收费员实施欺骗行为→收费员基于信任而陷入行为人会在高速公路出口处全额缴纳过路费之错误认识→收费员基于该错误认识而允许车辆有偿通过高速公路→车辆通过高速公路且闯关逃避缴纳过路费→高速公路公司遭受财产损失。”[2]
第二种意见:寻衅滋事罪。这也是本案中公安机关所持观点。该观点认为,朱某多次闯卡逃避缴纳应缴过路费,本质上是强拿硬要公私财物,客观上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因而,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第三种意见:抢夺罪。因为行为人“客观上表现为在没有付出对价通行费的基础上强行闯关离开高速公路,来达到消灭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收费权利的行为。司机在闯关的同时将作为结算凭证的收费卡带走,和‘抢夺借据、欠条等借款凭证,以抢夺罪论处’在法理上是一样的。 ”[3]
第四种意见:盗窃罪。该观点认为,盗窃罪并不以秘密窃取为必要,如张明楷教授便主张“盗窃行为并不限于秘密窃取……刑法理论必须面对现实,承认公开窃取行为构成盗窃罪。”[4]基于此,朱某的行为事实上是一种公然窃取行为,即窃取了应缴纳的过路费。
第五种意见:破坏生产经营罪。该观点认为“高速公路公司属于提供高速公路通过服务之主体,其收取费用提供过路权的行为无疑属于生产经营活动。以逃避缴纳过路费为目的,通过驾车闯关的暴力方式破坏高速公路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成立破坏生产经营罪。”[5]
第六种意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观点认为“驾车闯关逃费行为是与放火、决水、爆炸等危险性相当的行为,具有危害多数或者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极大可能性,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6]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但在具体分析路径上与原论者有一定差异;同时认为,此类案件尤其应重视其中的情形变化、数额认定、入罪路径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一)偷逃高速通行费现象分析
要给高速闯卡逃费行为以正确的定性,首先需要对偷逃高速通行费现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事实上,偷逃高速通行费的行为分为很多种,典型的有冲岗逃费、换卡逃费、司机影响称重数据、假冒优惠车辆逃费四种[7]。因此,需要区分不同情形给予针对性的说明论述,而不能张冠李戴。
其中第四种情形“假冒优惠车辆逃费”,事实上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应认定为诈骗罪。[8]按照司法解释的逻辑思路,上述第二种“换卡逃费”和第三种“司机影响称重数据逃费”事实上都可以认定为诈骗罪,应无疑义。故而,本文重点讨论的便只是第一种情形“冲卡逃费”。
所谓冲卡逃费,即本文所说闯卡逃费,事实上至少又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尾随前车闯卡,强行通过,未撞坏通道栏杆或造成其他人身财产损失;第二种情形,直接或尾随前车强行闯卡,撞坏通道栏杆,但未造成其他人身财产损失;第三种情形,直接或尾随前车强行闯卡后,为逃匿又不顾及其他车辆安全,连续违规驾驶,冲撞车辆或行人,造成其他损失。其中第三种情形,与前两种情形截然不同,很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事实上也应是前述第六种意见所主要针对的情形,对此也有相应判例[9]。而基于该种情形,认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论述“一、被告人疯狂逃逸的客观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方法具有同质性……二、被告人对其强行闯卡并逃逸造成的具体危险状态具有放任的间接故意。”[10]是完全成立的。但是该观点如果针对前述第一种、第二种情形,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第一、第二种情形,虽然未造成额外的严重损失,但单就偷逃高速费一项,其危害性也是巨大的。据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仅济聊高速王辛收费站一个四车道普通收费站,一晚逃费车辆就达百余辆,每月通行费保守估计损失20万元,且还不包括价值6万余元被撞坏的电动挡车器等器材。”[11]就北京地区而言,据笔者了解,近年来闯卡逃费现象亦较为严重,如本文所列举的被纳入刑事处罚的案例甚至有一定程度上增多的趋势。因此,至少从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将第一、第二种闯卡逃费情形纳入刑事打击范畴,还是有其必要性的。但入罪的路径、数额的认定等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并寻求充分的理论依托。由于第三种情形几无讨论的必要,下面将针对以本案为代表的第一、二种情形进行入罪分析。
(二)闯卡逃费应认定为抢夺罪
笔者认为,闯卡逃费行为客观上虽然存在争议,但抢夺罪的定性最为妥当。
1.案件的核心事实与诈骗罪、寻衅滋事罪、盗窃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犯罪构成均不相符
(1)诈骗罪无法解释取财或者说逃费的关键原因。诈骗罪的核心构成是受骗者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但是,就闯卡逃费案件而言,受骗者并未处分财产。诚然,入口收费员受骗将行为人放进高速,但入口收费员显然并未做出财产处分的任何表示,实际上其也无权做出这种表示。而闯卡行为发生在出口,此时行为人面对的是出口收费员,出口收费员并未被骗,其并未给行为人抬起栏杆,行为人偷逃费用得逞的关键是其尾随其他车辆、趁阻拦杆未落下,或干脆撞断阻拦杆,趁出口收费员未及采取阻拦措施之前冲出。因此,持诈骗罪观点的核心论证过程,即“收费员基于该错误认识而允许车辆有偿通过高速公路 (即处分高速公路公司提供的有偿服务)→车辆通过高速公路且闯关逃避缴纳过路费 (应交而未交)”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其首先错误的认为(入口)收费员处分了高速公路公司提供的有偿服务,其次循环使用“闯关逃避缴纳过路费”来搪塞闯关偷逃过路费的关键环节。因而,诈骗罪的定性是无法成立的。
(2)寻衅滋事罪在客观行为方式和主观目的上与闯卡逃费行为不相符。如果将闯卡逃费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只能适用《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3)项“强拿硬要”的规定,但强拿硬要客观上需要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有意思沟通与交流,但显然,闯卡逃费者与出口收费员之间不存在这种交流,因而,客观行为方面两者并不相符。而就主观目的上看,寻衅滋事罪要求行为人具有寻求刺激、逞强耍横等蔑视社会管理秩序的动机,但闯卡逃费者的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偷逃过路费。因此,综合两方面,寻衅滋事罪的定性亦不能成立。
(3)盗窃罪面临“公然性”的质疑,且无法契合闯卡逃费取财或逃费的关键行为。首先,虽然有学者主张公开窃取行为也应构成盗窃罪,但难言通说或主流意见,刑法理论历来的通说都是将盗窃罪的行为表述为秘密窃取。
其次,即便采纳公开窃取也可以构成盗窃罪的意见,“窃取”行为也与闯卡逃费行为相契合。“窃取”必然带有某种非公开性、秘密性,不予被害人、相对方公然对抗。而闯卡逃费不仅是公开的问题,关键其包含公然对抗成分,尤其在撞坏阻拦杆逃费的场合,这种公然对抗性更为明显。而这显然是“窃取”所无法涵盖的。
(4)破坏生产经营罪则无法解释闯卡逃费行为的主观目的。破坏生产经营的关键在于破坏机器、耕畜或其他生产经营赖以依靠的软硬件设施等生产资料,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泄愤等目的而进行破坏。但闯卡逃费行为主观上显然不是为了破坏,逃避缴纳高速通行费是其唯一目的。至于是否造成阻拦杆破坏等财产损失,只是附随考虑,甚至不做考虑。因此,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定性亦不成立。
2.抢夺罪的犯罪构成与闯卡逃费行为完全契合
从客观方面看,抢夺罪的犯罪构成显然与闯卡逃费行为最为契合。抢夺罪的本质是通过对物实施暴力方式强行夺取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具有造成人员伤亡、其他财产损失的可能性,这几乎完美诠释了闯卡逃费行为的本质。认为闯卡逃费不能定性为抢夺的主要原因,在于犯罪对象上,认为抢夺罪要求“具备的要件之一就是行为人所夺取的财物必须是被害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刑法意义上的占有重在事实上的支配,抢夺罪中 ‘紧密占有’的财物应理解为必须是被害人握在手中、背在肩上、装在口袋等与人的身体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财物。”[12]其依据则是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但是,张明楷教授近年来对其观点做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正,其在最新版的《刑法学》中采用的表述是“虽然从法律上说,抢夺罪的对象并没有排除财产性利益,但从事实层面来说,抢夺行为通常表现为夺取狭义财物。”[13]这说明,张教授也认可抢夺罪的对象中并没有排除财产性利益。而从刑法条文表述看,盗窃罪、诈骗罪、抢劫罪、抢夺罪的犯罪对象均为“公私财物”,在刑法条文、司法解释对各罪“公私财物”含义进行区分,且司法解释明确了盗窃罪、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14],也无充分理由限缩抢夺罪中“公私财物”的范畴,其当然包括财产性利益。尤其考虑到,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过路费可以成为诈骗罪的犯罪对象,那么理应也可以成为抢夺罪的犯罪对象。
但是,对于开篇所引持抢夺罪观点认为“司机在闯关的同时将作为结算凭证的收费卡带走,和‘抢夺借据、欠条等借款凭证,以抢夺罪论处’在法理上是一样”观点,笔者并不赞同。因为这里的收费卡事实上基本不具或者是其重心不在于借据、欠条等借款凭证证明债务关系存在的功能,其只是为了方便收费、记账,尤其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全程探头、联网的情况下,收费卡证明债务关系的功能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三)犯罪数额认定应注意
开篇案例中报道“因不清楚朱某每次上高速的具体位置,根据规定要按照全程收费,朱某家属共计补交高速费15390元”,但笔者认为不应将补交的高速费15390元认定为犯罪数额。因为,这里补交的高速费数额明显是基于地方性行政法规甚至政策规定的惩罚性数额,而不是行为人实际的偷逃数额。如《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第44条第3款规定:“对于强行冲闯收费道口、交换通行卡、假冒减免通行费车辆等逃交、拒交通行费的车辆,高速公路经营者管理单位有权拒绝其通行,并要求其补交应当缴纳的车辆通行费;对里程难以确定的车辆,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可以要求其按照待交费收费站与网内最远站点间收费里程交纳车辆通行费。”据笔者了解,各省级人民政府基本均有或实行类似规定,但目前尚没有全国性的行政法规专门规定这种按“网内最远站点间收费里程交纳车辆通行费”的补交费方式。
如果说行政法规、规章上规定这种惩罚性补交费数额无可厚非,那么,由于刑法本身的谦抑性,以及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那么,按惩罚性补交数额认定行为人的犯罪数额则是不妥当的,尤其是在行为人的实际偷逃数额完全可以查清的情况下。目前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已经实现联网,所以,案例中高速公路的管理者可以查清朱某共闯卡逃费57次,那么,高速公路管理者查清朱某驾驶车辆每次从哪一入口进入高速公路,进而明确其每次偷逃费数额,至少在技术上看应该并不困难。如果目前的技术或网络建设存在不足,导致无法认定其具体偷逃费数额,这需要高速公路管理者改进技术,完善网络设施。
如果确实无法认定行为人实际逃费的准确数额,也不应将高速公路方面的惩罚性数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在入罪时可以考虑通过《刑法》第267条规定的“多次抢夺”入罪。但采取此思路做入罪处理时应极为慎重,如果嫌疑人每次偷逃费额不大,比如应该仅有几十元,则应考虑其次数较多,比如朱某的57次。如果每次偷逃费额仅有几十元,实际偷逃仅有数次,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出发,对行为人宜作非犯罪化处理。
注释:
[1]基本案情系根据《北京晨报》2017年8月4日A13版报道《司机高速屡闯卡 被抓补交全程费》整理。
[2]龚晓明、刘明智:《“驾车闯关逃费”行为如何定性》,载《中国检察官》2011年第2期。原文针对的案例是三人三车,所以论证过程略作修改。
[3]邱雨云、韩春平:《撞坏EtC通道栏杆闯关逃费行为的定性》,载《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4期。
[4]张明楷:《刑法学》(第 5 版),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第949-950页。
[5]同[2]。
[6]同[2]。
[7]第一种,冲岗逃费指车辆选择直接或尾随前车闯卡强行通过收费站的违法行为。第二种,换卡逃费指两车通过互换通行卡或半挂车互换车头,以达到长途车变短途车或重车变轻车,少交通行费的目的。第三种,司机影响称重数据指存在遮挡光幕、垫钢板、‘S’形扭磅、跳磅、冲磅、压磅、安装液压装置等方式达到减少称重数据逃缴通行费的目的。第四种,假冒优惠车辆逃费指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我国对运输鲜活农产品、军车、抗震救灾等车辆免征通行费的政策,伪造车牌、证件、证明文件,农产品车辆混装等手段,企图蒙混过关,逃缴通行费。详见王海云:《浅析高速公诉查验处置偷逃通行费工作》,载《科技与企业》2014年第16期。
[8]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2款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266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9]2015年被告人陈学建于2015年3月20日23时许,驾驶一红色丰田牌轿车至上海市曲阳路、中山北二路处,遇民警设卡例行检查时,不接受民警示意停车接受检查,强行驾驶车辆闯卡逃逸。在民警汪鸣杰驾车追截下,连续闯红灯、剐蹭行人、在非机动车道逆向快速行驶。当逃至广灵二路近广纪路口处,被追截警车碰撞仍不停车,又驾车撞到位于广灵二路5号的可颂坊面包房店面玻璃墙后,弃车逃跑。次日,被告人陈学建向公安机关自首。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陈学建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详见张金伟、葛立刚:《强行闯卡并逃逸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载 《人民司法》2016年23期。
[10]同[9]。
[11]陈轶群:《将闯卡车辆惩治到底》,载《中国公路》2005年15期。
[12]同[2]。
[13]同[4],第 994 页。
[14]就盗窃罪而言,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4项明确将通信费用作为盗窃的犯罪数额。就诈骗罪而言,前述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2款明确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应当定性为诈骗罪,确认了通行费可以作为诈骗罪的犯罪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