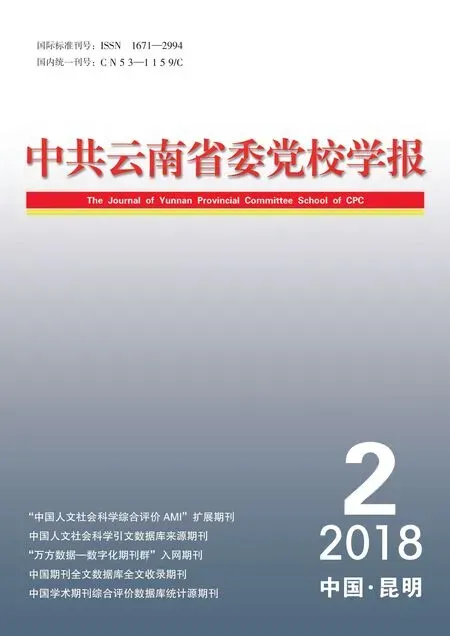从“三个世界划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陈金星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思政部,云南 丽江 674100)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方略。五十年代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七十年代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八十年代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断、胡锦涛关于“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习近平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这些战略的不断实践和创新中,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方略和国际关系价值取向。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奠定了“和平与发展”“和谐世界”理论的思想基石,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外交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必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中国外交起着指导作用。
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的理论特质
(一)两者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新
“三个世界划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我国领导人在把握世界发展脉搏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提出的宝贵成果,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反映。毛泽东对旧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入分析,重新对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行定位,即以广大贫穷落后的亚非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战略新支点——“第三世界国家”,来抗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打破当时对我国形成的包围和封锁等不利的国际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它所面对的是,在国家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竞争和文明冲突的现代国际体系条件下,回答世界向何处去、崛起的中国向何处去、新形势下中国怎样办外交等重大命题。随着中国自身影响力的扩大和在国际上所承担的责任义务的增加,如何引导全球治理成为国际上关注中国的一大热点问题,“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对国际社会整体观和前景方向观没有提出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类似的思想。”[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实践、善于创新,在对中国和全世界发展前景进行完整、清晰的认识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回答了新形势下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国外交的新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了国际外交新理念——互利共赢;确立了中国的国际新定位——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极为创新的将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联系在一起,寻找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交往的“最大公约数”,开创了国际合作的新纪元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两者都极大地改善了中国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增强了自身影响力
1974年,毛泽东确切地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了争取和联合第二世界共同反霸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明确指出:“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2]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为契机,使得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在此基础上,中国同日本及西欧国家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与此同时,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政治的交流更加深入和广泛,建交国家越来越多,使得20世纪70年代成为我国与三个世界国家关系大发展的年代。“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诞生排除了我国同这些国家正常交往的障碍,从而极大的缩小了打击面,避免了四面出击,为中国摆脱不利局面,改善日渐严峻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契机。当今,中国已经进入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不断发展完善,面对一些西方国家大搞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面对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改革失去方向的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产品。”[3]中国把“共赢”大大地写在外交旗帜上,用互惠互利替代丛林法则,相对于有的国家奉行的“本国利益至上”,孰高孰低,谁更顺应世界大势,是显而易见的。自2017年初以来,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多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进了有关问题决议,这些事实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在全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并成为了中国对世界提供的重要价值贡献,今后必将对我国自身和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三)两者的核心和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追求和谐发展,是各自所处时代的最优策略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诞生的20世纪70年代,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于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特别是来自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尤为严峻,提出建立旨在称霸亚洲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大举进入蒙古、印度、越南和阿富汗等国,在我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并叫嚣要“先发制人”,毛泽东认为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已转向苏联。在此判断的基础上为了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国家安全和改善外交困境,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中日、中欧开始交流,中国将苏联归入“第一世界”而不再跟随它的指挥棒而动,有力的制约了战争危险的增长。与此同时,我们抛弃了在第三世界追求世界革命的“左倾”幻想,将我国定位为第三世界中的一员,大力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使我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威信日益提高,朋友愈来愈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其实践归宿是增进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倡导在当下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和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当下,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气候问题、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浪潮抬头,恐怖主义、难民潮、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了世界各国“利益汇合点”的理论依据,它超越了某一国、某一地、某民族的狭隘利益,着眼于全人类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从物质和理论两个层面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提供给国际社会“搭便车”,在成就别人的同时也能发展壮大自身,是最符合我国根本利益的战略抉择。
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不同价值考量
(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突破的是意识形态的桎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打破“国强必霸”的怪圈
“三个世界划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外交理论和实践上的一次伟大创新,原因在于它打破了我国以往以意识形态为藩篱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束缚,改变了单纯用社会制度和阶级属性为标准划分世界政治力量的传统做法。第一,明确了对苏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以革命人特有的大无畏精神对抗苏联施加于我们的压力,对苏共领导人的指手画脚明确说不,在“左”的指导思想盛行的“文革”年代其意义影响深远。第二,改变了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认识,开始学会分析、认识、利用资本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打破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分清楚“敌、友、我”,形成团结第三世界、争取中间派、反对第一世界的基本认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论新实践,其创新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总有人相信大国政治必然导致悲剧的发生,把国际关系比喻成一个你死我活的角斗场。如何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成为了热门议题。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中国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方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4]中国倡导共赢,走和平发展之路,对“国强必霸”的传统大国崛起之路进行了质疑,绝对不搞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与零和博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和实践证明,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世界和平人类发展而奋斗的伟大政党。
(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侧重于矛盾的对立性和国家间的对抗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侧重于矛盾的统一性和国家间的合作性
“三个世界划分”是毛泽东在面临严峻的国际战争威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原理对世界局势分析的结果。在当时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和国际矛盾中,他准确而敏锐地抓住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世界渴望和平自由人民的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各自的内部矛盾,对矛盾的普遍性、斗争性有着异常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对建立国际反霸权的统一战线时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有了更加清晰准确的判断。毛泽东在预测形势时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5]对矛盾的斗争性和战争危险性的警惕与判断成为了那个战争阴云密布年代决策的出发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更重视发现矛盾中的统一性和国家间的合作性。当今世界,是一个彼此互相依存的“地球村”,矛盾虽然存在,斗争也层出不穷,但是任何个体如果妄想用“斗争”解决一切问题,已经不现实,合作、共赢才是分析和解决矛盾的一剂良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6]
(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指导下的中外交流仅限于政治、经济、军事的初步交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的是国家间全方位的深度合作
为了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走向自由独立之路,抵制苏联的扩张和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狂热的解放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道德责任感的气氛下,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对外援助工作。援助的主要内容是提供无息贷款或无偿援助,方式主要是成套项目、技术援助、物资援助及现汇援助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外交关系的发展。但是,这些援助方式简单,基本都是我国对其单方援助,双方的互动交流有限,援助的规模也脱离了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加重了国民经济的负担,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的是国家间全方位的深度配合而绝对不是脱离国情的单方援助,它的内涵和途径要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中外交往都要更为复杂和丰富。就现有的实践来看,已经有大量中国制造、中国建设、中国服务、中国产品、中国技术、中国资本走出国门,参与多国建设,中外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气候、安全、人才等交流越来越持久深入,中外交往“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7]习近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勾勒的中国方案和行动路径,这个路径上的中外交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深入、更全面、更具有可持续性,让人们看到了一条通往理想世界的美好图景。
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三个世界划分”面临的是在美苏两极争霸,严重威胁我国安全的格局,核心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共同寻求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的方案。“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诞生,是晚年毛泽东高超政治智慧的展现,其诞生背后有着严密的历史逻辑、高远的国际视野、经典的伟人气质以及对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定律的深刻理解,当下依然是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范例,在深入学习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时,我们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它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脉络,为我们理解新时期我国的对外政策,看清复杂的国际形势,提供了许多启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当求真务实
国际外交策略选择的基本出发点毫无疑问应当是本国的核心利益,务实、实事求是应当是外交的一个基本态度。“三个世界划分”打破画地为牢的意识形态桎梏是务实,但是忽视本国发展水平,在第三世界以大规模对外援助入手,搞极富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外交却又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我们应当首重“务实”,作为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全新世界观的新时代理论,它的实现应当是一个历史过程,绝不可一蹴而就、由哪一国一力承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需求,其推进的步骤、需要达到的层次应当求真务实、严格论证,在对自身国情和国际环境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做出合理决策,绝不能忽略当前世界依然是一个以利益划分的世界现实,搞理想主义。“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8]在发展、建设、成就自身的同时,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当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理解、认同,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我们要大力宣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要怀疑千年积淀的文明的生命力和说服力,进一步深入挖掘和传播“天下主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达则兼济天下”等中国文化的内涵,用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来完善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在搞好“自我”的话语建设的同时,“从‘他者’视角看,分析‘他者’的真实心理、有效需求与差异理解。在‘自我’与‘他者’的二元视角下,立体把握建构中国优质国际话语体系的生成条件。”[9]充分尊重他国人民的心理差异和认知规律,绝对不搞过去西方媒体颠倒黑白、断章取义、双重标准那一套,实事求是,用外国民众容易接受的方式、故事、作品来打破文化交流的隔膜和屏障,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聚集正能量,散发更强的感召力。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当多领域全方位综合推进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绝对不能像20世纪70年代我们和第三世界国家交往那样,重经济援助而轻深层次交流互动,导致有的国家“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在享受搭乘中国经济发展便车的同时,如果对中国缺乏价值认同那我们的合作无异于构建在沙滩上,是经不起风吹浪打的,70年代南亚某些国家对华政策如小人般反复无常就是前车之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毫无疑问是以经济发展来建立强有力的纽带,但是,决不可忽视各种软实力及其价值,不可小看双方人民深层次交流构建的基础。为此,应当加强对各国的意识形态、文化差异以及传媒体制与政策的研究,进一步提高对孔子学院、来华留学生培养等工作的认识,真正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科技等各领域、各层面来推进中外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在点滴中增进互信理解,以积跬步至千里的劲头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体建设。
[1]张历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容、价值与作用[J].人民论坛,2017(03).
[2]《人民日报》编辑部.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N].人民日报,1977-11-01.
[3]李向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全球治理改革方向[N].人民日报,2017-03-08.
[4][6]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09-29.
[5]彭远.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探讨[J].史学月刊,2017(03).
[7]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01-23.
[8]习近平.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核心利益做交易[N].人民日报,2013-01-30.
[9]陈锋.二元视角下的中国优质国际话语体系建构研究[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