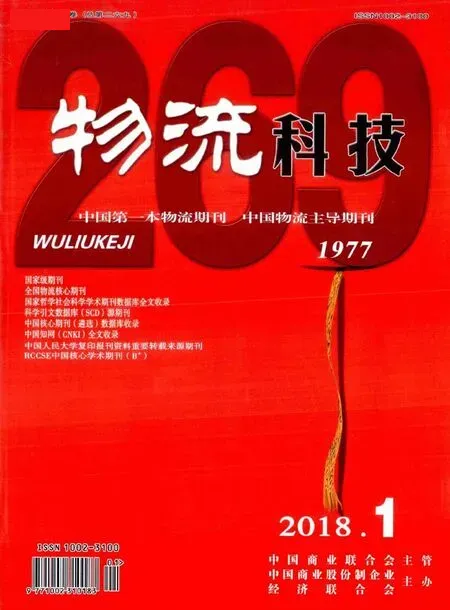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刘 芹,陈玉璞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200093)
0 引言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是为其他行业提供信息化产品和支持的基础与保证,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提出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作为有力支撑将推动发展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明确未来3年以及10年的“互联网+”发展目标,提出包括智慧能源、便捷交通、普惠金融、协同制造、绿色生态等共11项重点行动,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展,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需求会进一步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产业质量的重要指标,它的提高有利于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能不能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如果能,那么最优的集聚规模是多少?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国建设产业链完善、创新能力强、特色鲜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有很大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有很多学者就产业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来展开研究。Chia-L.C.,Les Oxley(2009)[3]利用Herfindahl指数来测算台湾242个四分位行业的集聚水平,并研究了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产业集聚以及研发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显示正效应。范剑勇、冯猛等(2014)[4]用LP半参估计法测算了我国通信设备、计算机与其他电子设备业企业县级层面的数据,研究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专业化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多样化集聚不具有这一功效。吴明琴与童碧如(2016)[5]通过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之间表现的尤为显著。杨浩昌、李廉水等(2016)[6]通过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的集聚能促进了其技术进步的提升,这一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的表现更为显著。Ren Lu,Min Ruan和Torger Reve(2016)[7]基于我国珠江三角洲1993~2012的数据研究不同阶段的集群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新生的集群对集群内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负面的影响,而成熟的集群则会对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的影响。
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研究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线性关系研究上,对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研究比较少,针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研究则更少,但是由于产业之间的差异性,特别是作为高技术产业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合当代尖端技术,需要更多研发投入,对其他产业渗透性强,它的专利保护意识也会更为强烈。所以专门针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相关研究,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和产业自身发展战略的制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所以本文将基于我国大陆地区省际面板数据来研究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1 模型设定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减少了交易费用,节约了生产成本,产生了外部规模效应和外部范围效应以及较为完善公共设施和公共秩序,这些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利用效率,对技术效率有积极的影响;集聚所创造更为有利的知识经验传播环境,以及企业的竞争所促使的技术改进与创新,对技术进步起着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业过度集聚所带来的拥挤效应以及集聚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产生的锁定效应,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的秩序,资源配置得不到有效的配置,企业管理效率大打折扣,技术进步受到阻碍,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消极影响。所以本文假设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为了考察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拆分项如何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本文在选取控制变量时加入了纯技术效率(PECH)、规模效率(SECH)、技术进步(TECHCH) 三项,此外还有技术知识溢出(TS)、政府补助(GS)、人力资本水平(HL)、R&D投入(RD),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j表示控制变量的个数,agg是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集聚程度。
技术知识溢出(TS)指企业进行科技开发活动后产出的新知识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扩散到其他企业中,对周边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所以技术知识的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本文参考王弓(2016)[8]研究选择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来衡量,预期符号为正。
政府补助(GS)是政府无偿对企业进行的财政拨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资金问题,对企业研发活动提供支持,激发企业研究与创新的热情,本文选用政府对研发活动提供的资金来衡量政府补助,预期符号可能为正。
人力资本水平(HL)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劳动者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较为熟练的专业技能掌握以及运用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第二,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研发水平、技术知识的吸收能力,从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参照孙慧(2016)[9]的做法选取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指标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预期符号为正。
R&D投入(RD)会促进技术的创新与进步,从而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本文对R&D的衡量指标选取的是R&D经费的内部投入,预期符号为正。
2 数据来源与指标测算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09~2015年全国大陆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重点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到数据质量与数据可得性,删除了数据不完整的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海南、青海,选取剩余的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因变量全要素生产率用Malmquist指数,通过DEAP软件计算。自变量中专业化集聚水平的测度借鉴Glasser et al(1995)[10]的测度方法计算得出。
(2)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本文选用DEA-Malmquist方法,运用DEAP软件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将不同的省份作为不同的决策单元。本文参考杨清可、段学军(2014)[11]基于DEA-Malmquists模型对高技术产业发展效率的时空测试与省际差异的研究,在投入指标的选取上从人力、物力、财力三方面投入入手,选择了企业数、从业人员年平均数、固定资产投资额、R&D经费内部支出四个指标;在产出指标的选择上,既要考虑电子与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总体产出水平,也不能忽视了它的技术创新能力,所以本文选择主营业务收入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两项作为产出指标。本文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投入和产出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电子与通讯设备制造业TFP测度指标体系
(3)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的测算
本文选用专业化集聚水平作为产业集聚的衡量指标,大量研究文献对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的测量做出了贡献,本文沿用Glasser et al(1995)的测度方法,并参考陈劲、梁靓(2013)[12]的做法采用以下方法来测算专业化集聚水平:

公式中,aggij代表j地区i产业的专业化集聚程度;L是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Lij代表j地区i产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Lj代表j地区高技术产业的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Li代表全国范围内的i产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L代表全国高技术产业的年平均从业人数。
3 计量分析
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种,本文先分别采用三种不同的模型整体来进行回归分析,然后通过Hausman检验和似然比检验(Likelihood Ratio)来确定最适合的模型形式。
首先基于上文确定的计量模型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用混合OLS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中的第一列模型1所示。解释变量专业化集聚水平的系数为0.50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专业化集聚水平的平方项系数为-0.348,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回归方程呈现倒“U”型曲线,拐点为0.73,即最优的专业化集聚水平为0.73。
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中的第二列模型2所示。解释变量专业化集聚水平的系数为0.5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专业化集聚水平的平方项系数为-0.343,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同样,回归方程呈现倒“U”型曲线,拐点为0.743。
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中的第三列模型3所示。解释变量专业化集聚水平及专业化集聚平方项的系数分别为0.611和0.432,且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回归方程呈倒“U”型曲线,拐点为0.707。
综上三种模型的分析,我国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与其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大概在0.7到0.8之间。也就是说对于我国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来说并不是专业化集聚程度越高全要素生产率就越高,其中存在一个最优的集聚水平,达到这个水平之前,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集聚对其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的影响,达到最优的水平之后,集聚便会对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消极的影响。本文进行Hausman检验和似然比检验(Likelihood Ratio)来确定最适合分析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对其全要素影响情况的模型形式。结果表明随机效应模型即表2中的模型3更适合本文的研究情况。

表2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整体估计
确定了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及其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显著的倒“U”型关系,以及适合本文的模型形式之后,本文采用逐步代入控制变量的方法来进行下一步的具体分析,以考察各控制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倒“U”型曲线的具体影响情况。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分步分析
通过对模型1~5的分析,在逐步加入变量的过程中,倒“U”型的曲线关系是存在的,解释变量专业化集聚水平符号一直为正,且至少在5%水平下通过检验,集聚水平的平方项系数一直为负,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主要的控制变量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拆分项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符号持续为正,其他控制变量除了模型2、模型3中的变量GS(政府补助)不显著外,其他控制变量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所有变量符号均保持不变,证明本文假设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与其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和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是十分稳健的。
模型1除解释变量选取的是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平方项之外,控制变量选取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回归结果显示为倒“U”型曲线,拐点为0.708。
模型2增加了控制变量政府补助,其符号为正,从单个控制变量来看,政府补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政府在对企业进行补贴的时候有可能存在“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罗雨泽,2016)[13],针对性的补贴部分企业,造成社会福利的流失;另一方面企业在收到政府补助款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利于研究开发,导致政府补助并不是资源合理、有效的分配,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模型3增加了控制变量TS(技术知识溢出),回归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知识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也验证了之前的猜想。
模型4增加了控制变量HL(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并且促进了拐点值的后移,表明高素质的劳动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模型5增加了控制变量RD(研发支出),是本文最终完整的模型形式,和预期相反研发投入的系数为负,并没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原因可能是一方面企业进行研发投资可能是出于寻租的动机,而不是致力于真正的技术进步与创新(罗雨泽,2016)[13]。申香华(2010)[14]也指出企业为了获得政府的补贴,或者仅仅是为了完成政府分配的指标,会发送“虚假的”创新信号;另一方面,我国的专利保护制度还不是十分的健全,尤其是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这种高技术行业,企业花费大量的成本进行的技术创新研发后,技术成果会被模仿,从而使得最终企业获得回报远远低于预期,甚至可能面临亏损,企业不会真正的对R&D进行大量的投资。罗雨泽(2016)在对我国高技术产业TFP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指出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位已经对我国国内企业的自主研发和FDI的自主创新绩效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除此之外,我国的研发投入所带来的专利产品虽然多,但是专利向实际生产的转化率还比较低。
4 结束语
本文利用2009~2015年中国大陆地区25个省份(除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海南、青海)的面板数据,控制了其它可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技术溢出、政府补助、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之后,分析了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最终得到以下三个结论:
(1)无论采用总体回归分析还是逐步代入分析,专业化集聚水平系数都显著为正,集聚水平的平方项系数都显著为负,这表明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与其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十分稳健的。在最优集聚程度之前专业化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作用,超过最优的集聚水平之后专业化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消极影响。
(2)从最优的集聚规模来看,本文分析结果表明,对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来说最优的专业化集聚规模在0.7左右,控制变量的加入会导致最优的专业化集聚规模产生小范围的波动,但结果维持在0.7~0.75之间。
(3)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TECHCH),纯技术效率(PECH)和规模效率(SECH)之后,三项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就影响程度来看规模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科技含量高,技术和产品更新速度快,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长期的人才积累和技术积累,对技术和人才的有效管理和利用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我国相关专利保护和转化体系还不完善,相关研发成果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此外企业自身管理水平、结构模式尚有不足之处,没有达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可能是纯技术效率存在不足之处的原因。
本文研究尚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比如控制变量的选取方面,仍有很多因素会对全要素生产产生影响,本文只选取少量的指标进行研究,期待在后续研究中更加全面地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以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和其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全面的把握。本文用宏观数据对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集聚和其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期待以后可以从企业等微观层面出发对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此外,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对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园区进行对比分析,和国际接轨,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为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出更多贡献。
[1]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成刚.数据包络分析与MaxDEA软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3]Chia-Lin Chang,Les Oxley.Industrial agglomeration,geographic innovation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he case of Taiwan[J].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2009,79(9):2787-2796.
[4]范剑勇,冯猛,李方文.产业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世界经济,2014(5):51-73.
[5]吴明琴,童碧如.产业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的证据[J].产经评论,2016(7):30-44.
[6]杨浩昌,李廉水,刘军.高技术产业聚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比较[J].科学学研究,2016(2):212-219.
[7]Ren Lu,Min Ruan,Torger Reve.Cluster and co-located cluster effects:An empirical study of six Chinese city regions[J].Research Policy,2016(12):1984-1995.
[8]王弓,叶蜀君.金融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6(1):174-175.
[9]孙慧,朱俏俏.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1):121-130.
[10]Glaeser.E L,Kallal H D.Growth in citi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03(5):1065-1090.
[11]杨清可,段学军.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模型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效率的时空测度与省际差异研究[J].经济地理,2014(7):103-110.
[12]陈劲,梁靓,吴航.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产业集聚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J].科学学研究,2013(4):623-629.
[13]罗雨泽,罗来军,陈衍泰.高新技术产业TFP由何而定?——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6(2):8-18.
[14]申香华.成长空间、盈亏状况与营利性组织财政补贴绩效——基于2003~2006年河南省和江苏省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J].财贸经济,2010(9):6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