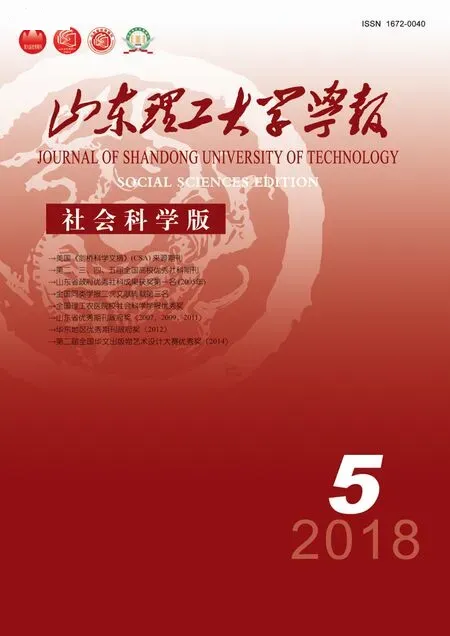由“生生”结构探入生态问题的研究
——评《生态境域中人的生存问题》
吕 逸 新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生生”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个根基性表述,它探到了人与万物之生命存在的“根”,也用极简,且极为形象的话语表述了这种根性及关联性。“生生不息”作为一个一语中的,且家喻户晓的命理,形象地指涉着这样一个世间最为根本的事实存在。应该说,中华文化即顺延着这个“脉”行进,使其博大精深始终不离对生命的关注,或者这本就是关乎生命的文化。盖光教授多年潜心研究所著的《生态境域中人的生存问题》(由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的主旨研究,便是沿着这个理与脉,探求生态,探求人,并深度体认人何以在生态条件下的生存问题,认识人类如何能够沿着这个“生生”进向而走向生态文明。
《老子》的“道生”性运演序列,《周易》所言“生生之为易”,以及“天地之大德曰生”,等等,都精准地阐释了关于万物,关于人之生命存在基本状貌。但这又缘何能够与“生态”连接,或者如何由此而精准探究“生态”何谓呢?通观该著,细细思量,实际这部著作是从生命的实在,到学理体认;从人的生存结构到人与万物生命相联的必然性;从中华文化到西学逻辑等方面,较为全面,且能够系统化、整体性地解答这一系列性问题。事实上,生态问题并非仅仅局限于人们常常表述的那样,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要深度探求生态问题,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对“环境”所造成的种种不和谐现象,也并非仅仅限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生态”最核心的脉象是“生”,是生命,而生命之所以能够存在,地球生命之所以能够亘古传承,关键是“生”之态,是“生生”,实际就是地球生命多样性何以能够相关连接,以其成就一条生命活动的链条。这必须是一条“有机”的,多向联系的链条。这种“生”的本样及“生”之态就是最根本意义上的“生态”。“有机”的根是“生生”,必然趋向“和谐”;只有“和”,才能使链条不至于断裂,才能永续。人的生命从个体到人类整体,乃至地球万物生命一切的一切,都必须活动于这个链条上,并共同促成这种“有机”之“和”。自然万物,地球生命是沿着本有状态行进的,其“和”是其自检、自护、自修、自整而成永久运演。人类于其中,本应是有机融入的,但亘古的人类活动却往往不尽然,往往会与之产生诸多不和的状态。这实际是指人类活动亘古延续的过度性,会对这种“和”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诸如人们常常说的,所谓破坏自然、生态危机;所谓生物多样性减少,草原沙漠化、资源短缺,等等,实际是人类活动的过度性,所背离了这个“有机”之“和谐”的链条的表现而已。事实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首先是要明晰缘何能够“有机”,如何能够归复“有机”,回到“和谐”。简单说来,就要求人类活动有“节制”。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又是极为复杂,且难以确定的问题,对这系列问题的明确及构建解决的方法,以至于有效及合理措施,理应是我们关注“生态问题”的最根本理路。
该书就是沿着这个路向展开,构建着一个可以为人接受的逻辑运演过程,其逻辑的起点即为“生生”。如果说,这是一个事实与逻辑原初形态的“生生”的话,那么,通过人类活动的亘古实在,到学理及逻辑探究的最终运演,继而行进到最高层次的“生生”,就是“生态文明”。因此,该书最后一章的“走向生态文明”,就是一种必然了。这不仅是人类活动的必然事实,也是我们思考人类应该如何活动,且能够沿着“生生”之链而“有机”运行的必然。于是,该书在开篇第一章就以“生生:生态系统的和谐指向”为题,明确标识其所研究及其展开的基本路向,并且由“‘生生’之态与‘生生’之和”地细致阐释而步步推演。应该说,该书并非泛论“生生”,在其分析中华文化典籍中所言“生生”的基本思想基础上,还对“生生”给予全面,也较为详实的结构性分析和阐释。故该书从八个层面析分了“生生”所内聚的极为丰富的,多层次的含义。这就是:生命存在的特性、意义本性、万物的联系与时空构成、话语的结构特性、人类学的征象、人的精神性存在、审美的意义以及价值论的构成。由此,该书进一步明证了:“无论结构多么复杂,内涵多么丰富;无论是与自然生态搭界,是与人的生存活动搭界,还是在自然生态与人的和谐共存中搭界,‘生生’运化必然是不断生成及其创生的,其演替的节律必然是由‘和’而起,而又归于‘和’的。不论是自然生态之‘生生’,是人的‘生生’,还是自然生态与人有机谐交融的‘生生’,这一切都必然运演着生与和、和与和、和与生的循环往复,进而呈现永无止境的生命的创生。”(见该书11页)
当然,对于人而言,探求“生生”,或者研究“生态”,体察“生态”变化,无疑会深度思考自身,把控人的活动,并最终能够理清人如何能够在生态的,有机的状态下生存,且必须是和谐的,运演“生生”节律的生存。这其中,必然关涉两重指向,一是人自身的活动怎样归复有机、和谐,一是自然万物,乃至地球生命如何能够在不被变异的有机、和谐之链上永续。这两重指向实际是归一的,即站在人类活动的角度说,这两重有机与和谐最终的决定权不在自然,不在地球,而在人类。人类活动过度,影响的不只是自然,不只是地球生命,更是人类自身。我们所进行的,所有的关乎生态问题的研究,乃至我们致力于建设的“生态文明”,无非就是在理清人类的活动特性,致力于调控、调节人类活动,使之能够以有机、和谐的节律行进,能够回到与自然万物,与地球生命交往、互动的家园共生状态。应该说,该书就是沿着这个基本思路展开研究,并由此提出了关于“人的生态性生存”的命题,这不是一般形态的,而是关乎“人的生态性优存”的问题。该书的第四章就以“人的生态性优存”为题而系统阐释了这个命题,并指明:“只有合理地认识人的生态化存在,才能真正认识人的自我性,才能有效把握人的主体性存在的意义;只有从生态优存的视阈中认识人的自我性和主体性存在的意义,才能合理的把握人的存在本质,才能深层次地认识人类如何才能永续发展的问题,才能合理与有效地设计人类生存发展的路向,打通人类走向未来的生存之路。”(见该书99页)该书还指出,优存离不开审美化生存,因为审美本就是生命存在的形态,或者是活化、优化,以至美化生命活动的人类行为,如果能够达到生态性的优存,那么,就必然是审美化的生存。于是,这就成就一个“链”,或者是书中论及到的:“‘适者生存—美者优存—生态者优存’的人类优存结构的演替节律。”(见该书3页)该书对于人、生态、生生以及与美的关系的探求,并非就此止步,这种思想不只始终贯通于全书,而且最终由事实与逻辑层面而推向最高层次。这就是在“走向生态文明”的思考中,明晰了生态文明是一种“情理构合”的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的“大爱”施放。当然,这种“爱”不止于人类的自爱,而是在地球家园中与万物之间的共同之爱,由此,“大爱”必然是“大美”的。该书结尾这样论述到:“生态文明作为有情意的文明形态,其情意的表现在‘情’与‘理’的构合中把爱施放于全人类,施放于与人类生存活动朝夕相伴的大自然,施放于地球生命共同体,施放于大地之母;不仅施放于当代人的生存,更应该施放于人类的未来,施放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并以融通人类的‘大爱’展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大美’之境。”(见该书339—340页)
之所以说《生态境域中人的生存问题》这部著作全面、系统及整体,还因为它不只在起点到终点过程进向方面符合逻辑,而且在探究人类生态系统结构方面有新意,同时又结合关于生态思维特性的方法论、价值论及主客体结构的研究,丰实了学理研究内容。此外,还须提及的是,该书用了“生态支持”这种提法,这应该是生态学的阐释方式,以此来研究生命特性,继而延伸至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及文化生态的观照,显然这系统性地合成,必然使之具备全面性及整体性。该书关于走向生态文明的进程是就这多重生态结构的探究,尤其是从文化生态层次进入的,应该说,这是符合人类活动特性,尤其人类的文化存在特性的。鉴于该书过于突出了这种理论阐释及其概念、逻辑的演进,而对生态、生命,乃至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的实践性、具体性的把握则显得单薄,例证也欠充分。一定意义上说,解决生态问题,关注生存问题,实践更优于理论,全社会、全民的接受及行动更重于抽象的学理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