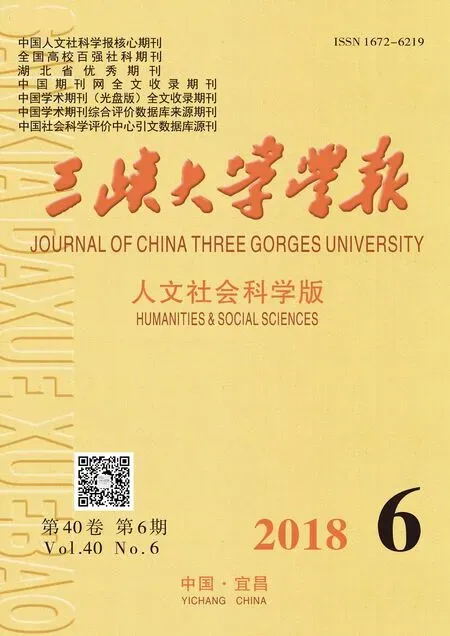从“周旨荡而史意贪”看刘熙载的诗学思想
邓莹辉, 程翔宇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他是清代晚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其《艺概》是一部重要的文学批评论著,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等6卷,分别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的体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和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等,是刘熙载多年来玩味品鉴传统文化艺术的心得之谈。其中《艺概·词曲概》被学术界视为近代批评史上与王国维《人间词话》齐名的词学专著。
他在《艺概·词曲概》中提出“周旨荡而史意贪”这一评价:“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1]507他一方面肯定了周邦彦用律精审,史达祖造句警炼,另一方面却认定周词“旨荡”,而史词“意贪”,称不上“君子之词”。
何为“周旨荡”?《艺概·词曲概》第二十八则云:“周美成词,或谓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1]507然而他在评价刘克庄的词时,称其“旨正而语有致”:“刘后村词,旨正而语有致。真西山《文章正宗·诗歌》一门属后村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知必心重其人也。”[1]519后又引后村词一首《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云:“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刘克庄是南宋末期著名的文坛领袖,同时也是一位理学家,是故其词极力避免涉及“闺情春怨”,恪守儒家诗教之传统。而周邦彦有一部分词作是抒发男女之情和离愁别恨之意,并且“以乐府独步,学士、贵人、市侩、妓女皆知其词为可爱。”(陈郁《藏一话腴》)另据《宋史·文苑传》记载,周邦彦少年时“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所谓“疏隽少检”,主要是指周邦彦与异性交往时,行为语言不够检点,生活放浪,不守礼节。且宋人笔记小说中也多有关于记叙周邦彦与歌伎交往的逸闻趣事,如李师师、岳楚云等人。可以看出,刘熙载所论之周邦彦不得“贞”,乃是其不得性情之“正”,未领风雅之旨。
何为“史意贪”?刘氏曰:“蒋竹山词,未极‘流动’、‘自然’,然‘洗练’、‘缜密’,语多创获。其志视梅溪较贞。”[1]520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叙论》亦云:“梅溪才思,可匹竹山。竹山粗俗,梅溪纤巧……梅溪好用偷字,品格便不高。”[2]13史达祖作词喜用“偷”字,其志便落人一等,而“偷”字正好为此增添了“说服力”。又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雷孝友上言条云:“苏师旦既逐之后,堂吏史达祖、耿柽、董如璧三名,随即用事。言无不行,公受贿赂,共为奸利。”史达祖为权相韩侂胄之堂吏,实际上掌握左、右丞相的权力,趋附权奸,暗中谋私,遂为士大夫所不耻。是故刘熙载、周济二人的评价并非从词的技巧、意象、境界等方面入手,而是以人品来定词品,用道德批评替代艺术鉴赏。
总之,周邦彦词之“旨荡”是因其“疏隽少检”,丧失性情之正,痴迷于“闺情春怨”;史达祖词之“意贪”乃是其依附权相,“公受贿赂,共为奸利”,好用“偷”字之故,品格便不高。
一、“周旨荡”之辨
周邦彦确有以绮语渲染闺情春怨,描摹刻画男女之情的词作,并有一些出色的作品为人所称道:
一落索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莫将清泪湿花枝,恐花也、如人瘦。 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倚栏愁,但取问、亭前柳。[3]10
意难忘
衣染莺黄,爱停歌驻拍,劝酒持觞。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檐露滴,竹风凉,拚剧饮淋浪。夜渐深、笼灯就月,子细端相。 知音见说无双,解移宫换羽,未怕周郎。长颦知有恨,贪耍不成妆。些个事,恼人肠,试说与何妨。又恐伊、寻问消息,瘦灭容光。[3]49-50
风流子
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绣阁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黄。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近清觞。 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说与,佳音密秏,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3]109
《一落索·眉共春山争秀》将年轻女子的相思之愁和知音难觅的深深悲哀刻画得惟妙惟肖,整首词婉转多情,感人至深。《意难忘·衣染莺黄》将男女之情描绘得洒落有致,“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引人遐想连篇,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男女诉说衷肠,亲密无间之情景,沈谦《填词杂说》亦云:“长调中极狎昵之情者,周美成之‘衣染莺黄’,柳耆卿之‘晚晴初’是也。”《风流子·新绿小池塘》则将相思之情借女子之口吻娓娓道来,低吁婉转,“欲说又休”,欲见而又不得,思念到深刻处,竟叹梦中魂魄亦难与佳人同床,极具缠绵柔情之态。叶申芗《本色词》云:“此词(《风流子·新绿小池塘》)虽极情致缠绵,然律以名教,恐亦有伤风雅也。”可见此词极为情爱之能事,以至有伤风雅之嫌。张炎《词源》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如‘为伊泪落’(《解连环》);如‘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风流子》);如‘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风流子》);如‘又恐伊寻消问息,瘦损容光’(《意难忘》);如‘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庆春宫》);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陈廷焯也说:“美成艳词,如《少年游》、《点绛唇》、《意难忘》、《忘江南》等篇,别有一种姿态,句句洒脱,香奁泛语,吐弃殆尽。”[4]162二人都认为周邦彦存在不少“一为情役”,充满香艳绮语的词作。而更有甚者,彭孙遹认为美成词如同少女,极具“软媚”之特点,他评价说:“美成词如十三女子,玉艳珠鲜,政未可以其软媚而少之也。”(《金粟词话》)这便和刘熙载论词“娇女步春”之说有不谋而合之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周邦彦除了为人所褒贬不一的闺情词之外,还有数量众多,表现词人跨过“闺门”,游离于“情怨”之外,展现出对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作出深刻思考的词作。龙榆生先生《清真词叙论》尝谓:“清真软媚之作,大抵成于少日居汴京时”;又谓:“三十后始出京教授庐州,旋复流转荆州,侘傺无聊,稍捐绮思,词境亦渐由软媚而入凄婉”;又谓及知溧水,“其人自遭时变,漂零不偶,即性情亦因之而变化,无复少年疏隽少检之风矣”;又谓“《齐天乐》秋思、《西河》咏金陵之作,沉郁顿挫,已渐开官溧水后之作风”;又谓“邦彦词学之最大成就,当在重入汴京时,盖异地漂零,饱经忧思,旧游重忆,刺激恒多,益以年龄关系,技术日趋精巧。”有关美成词创作时地的资料,有明文可征者少,但龙先生之论,以意逆之,或亦较为接近实际情形。其软媚之作的创作当是在青年时期,居住在汴京的时候,这仅为周邦彦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比较短的阶段。笔者根据对美成词的整体把握,将其主要分为感时伤怀、针砭时事、写景记事等类型,通过考察这几类词作,对于全面把握美成词的主旨内蕴、艺术价值,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如《瑞龙吟》: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 黯凝竚,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惟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3]146
这是一首访旧感怀之作,抒写词人回京后访问旧友的复杂心情。全词三段,上阙写初春访旧的环境氛围;中阕回忆当年初来时所见所爱,忆念伊人,当年万种风情,宛在目前;下阕抚今追昔,极写物是人非之悲哀。吴梅《词学通论》云:“即如《瑞龙吟》一首,其宗旨所在,在‘伤离意绪’一语耳。”[5]整首词,极尽缠绵婉转,沉郁顿挫,感人至深。又如《黄鹂绕碧树》:
双阕笼嘉气,寒威日晚,岁华将暮。小院闲庭,对寒梅照雪,淡烟凝素。忍当迅景,动无限、伤春情绪。犹赖是、上苑风光渐好,芳容将煦。 草荚兰芽渐吐,且寻芳、更休思虑。这浮世、甚驱驰利禄,奔竞尘土。纵有魏珠照乘,未买得、流年住。争如盛饮流霞,醉偎琼树。[3]187
此词是针砭时事,刺徽宗及蔡京党人之作。词云:“双阕笼嘉气”,又云:“犹赖是、上苑风光渐好,芳容将煦。”乃感时刺君之意。自崇宁、大观以还,蔡京久擅权柄,结党谋私,权倾中外,党羽遍天下,其党又皆小人,趋炎附势,竞逐名利,不顾廉耻。词云:“这浮世、甚驱驰利禄,奔竞尘土。纵有魏珠照乘,未买得、流年住。”便是讥讽此辈。词人含蓄委婉地透露出忧君怀国之意,痛恨小人当权,败坏朝政,显示出深切的爱国之情。再如《花犯》:
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去年胜赏曾孤倚,冰盘同宴喜。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 今年对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脆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3]131
这是一首咏梅佳作,词人以梅花自喻,错综时空,写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阶段的梅花,实际上也委婉曲折地抒发了自己宦游无定,四处漂泊的寂寞感伤之情,亦有一种孤芳自赏的慰借,匠心独运,颇显词人才思之高妙。黄升评曰:“此只咏梅花,而纡余反复,道尽三年间事,昔人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余于此词亦云。”[6]极为称道此词之构思精巧。况周颐更是盛赞此词,称“此为梅词第一”(《蓼园词话》)。叶嘉莹先生《论周邦彦绝句》云:“早年州里称疏隽,晚岁人看似木鸡。多少元丰元祐慨,乌纱潮溅露端倪。”[7]周邦彦历经宦海浮沉,四处漂泊,晚岁所作之词中饱含感时伤怀、英雄迟暮之感,也有壮志未酬、忧君怀国之意,凄婉哀怨,沉郁顿挫,绝非仅擅长写闺情春怨。只有充分梳理周邦彦之词作,体味其深刻意蕴,才能打破人们对他的误解。
二、“史意贪”之辨
史达祖存词一百一十二首,据笔者统计,“偷”字存在其十二首词之中,共出现十二次,以存词数目计,仅约占十分之一。今列举如下:
(1)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梅花。(《绮罗香·詠春雨》)
(2)巧沁兰心,偷黏草甲,东风欲障新暖。(《东风第一枝·咏春雪》)
(3)讳道相思,偷理绡裙,自惊腰衩。(《三姝媚》·烟光摇缥瓦)
(4)应念偷剪酴醾,柔条暗萦系。(《祝英台近·柳枝愁》)
(5)正凝佇。芳意欺月矜春,浑欲便偷许。(《祝英台近·落花深》)
(6)坠絮孳萍,狂鞭孕竹,偷移红紫池亭。(《庆清朝·坠絮孳萍》)
(7)冷截龙腰,偷拏鸾爪,楚山长锁秋云。(《夜合花·赋笛》)
(8)轻衫未揽,犹将泪点偷藏。(《夜合花·柳锁莺魂》)
(9)向黄昏、竹外寒深,醉里为谁偷倚?(《瑞鹤仙·赋红梅》)
(10)更暗尘、偷锁鸾影,心事屡羞团扇。(《玲珑四犯·雨入愁边》)
(11)犀纹隐隐莺黄嫩,篱落翠深偷见。(《齐天乐·赋橙》)
(12)阑干斜照未满,杏墙应望断,春翠偷聚。(《齐天乐·湖上即席分韵得羽字》)
根据词意不难发现,(1)、(2)、(6)、(12)四处都是在描写春景,一个“偷”字,将春雨、春雪润物无声,生意盎然之态刻画得极为巧妙,突出了在春雨、春雪的滋润下,万物生机勃发之迅速。也道出了春天的色彩是翠绿的,在不经意间便映入眼帘。(3)、(8)、(10)则是运用“偷”字将少女怀春、思妇闺情描写得惟妙惟肖,很好地表现出了女子心系故人的含蓄羞怯之态,以及深沉的思念之情。(4)“偷”字的运用,刻画出了词人回忆往昔的点点滴滴,“偷剪酴醾”应是和意中人一起做的甜蜜之事。(5)则巧用“偷”字,表达了词人被满目春色所迷,心醉其中之状。(7)、(9)、(10)“偷”字则是用来描写物,分别刻画出了制作笛子之精巧、以美人喻红梅之娇艳、橙子成熟时让人惊喜之情,让人顿觉所写之物的可爱之处,实乃画龙点睛之笔。史达祖词中运用“偷”字来写景抒怀,恰是展现了他高超的炼字功力,在表情达意上十分精当。以此字的运用观之,周济认为“用笔多涉尖巧”[2]7,确有几分合理之处,但认为以“偷”字足以定其品格,以至对其词有“意贪”之论,笔者以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史达祖艺术创作之价值。
史达祖的词以咏物见长,其中不乏身世之感。《满江红·书怀》云:“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又云:“思往事,嗟儿剧。怜牛后,怀鸡肋。奈棱棱虎豹,九重关隔。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8]132《湘江静》云:“酒易醒,愁正苦,想空山、桂香悬树。三年梦冷,孤吟意短,屡烟钟津鼓。屐齿厌登临,移橙后,几番凉雨。潘郎渐老,风流顿灭,闲居未赋。”[8]105《齐天乐·白发》更云:“人间公道惟此,叹朱颜也恁,容易堕去。涅了重缁,搔来更短,方悔风流相误。郎潜几缕,渐疏了、铜驼俊游俦侣。”[8]115-116从这些词句中,不难看出,词人是怀才不遇的,有官职卑微的不平之声,有仕途坎坷的辛酸之味,也有归隐而不得的哀叹。以至于天涯倦客,奔波于旅途,时光易逝,而事业无成,其境遇正如同潘岳那样的拙宦,壮志难酬。邓廷桢《双砚斋词话》云:“(梅溪词)大抵写怨铜驼,寄怀毳幕,非止流连光景,浪作艳歌也。”可谓公允之论。
他在宁宗朝还有一段北行使金的经历,这一部分北行词充满了沉痛的家国之感。《龙吟曲·陪节欲行留别社友》云:“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复,阑干静,慵登眺。”又云:“今日征夫在道,敢辞劳、风沙短帽。休吟稷穗,休寻乔木,独怜遗老。”[8]145故土尚未收复,即使倚栏可观美景,也不愿登临眺望。见稷穗悲旧京,见乔木思故园,便具有兴亡之感,然词人曰休吟,曰休寻,更平添无限愁绪与悲痛之情。《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云:“缓辔西风,叹三宿、迟迟行客。桑梓外、锄耰渐入,柳坊花陌。双阕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鸯翼。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这首词是在出使金国回程中过北宋旧京汴梁时写的,抒发了词人在秋风中缓辔而行,不忍仓促离去的复杂感情。昔日热闹的都城,此时连倚墙吹笛之人都不见了,只留下碧绿的青苔。但是词人于悲痛之中发出恢复故土之意:“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臣离德。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8]134在目睹金国现状之后,重燃收复河山的希望。
由此观之,史达祖因为是韩侂胄之堂吏,而历来饱受讥评,但是从词作来看,他仍有满腔热血,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并非真如陈廷焯所言:“其才虽佳,其人无足称矣。”[4]132我们应当对他给予客观合理的评价,称他为南宋爱国词人,或无可厚非,其人品当不至于为人所不耻,其词也并非是“意贪”之作。
三、刘熙载词论思想及其理论溯源
1.刘熙载的词论思想
(1)三品说。刘熙载之所以认定“周旨荡而史意贪”,乃是因其以人品论词品的缘故。《艺概·词曲概》云:“论词莫先于品”[1]506,“品”在这里指的是人的品格,也即是说探讨词人的思想和道德品质是论词的前提条件,人品的高低决定了词品的优劣。因此他建立了独具特色的词三品说:
“没些儿媻姗勃窣,也不是峥嵘突兀,管做彻元分人物”,此陈同甫《三部乐》词也。 余欲借其语以判词品。词以“元分人物”为最上,“峥嵘突兀”犹不失为奇杰,“媻姗勃窣”则沦于侧媚矣。[1]573
刘熙载将词品分为三等,“元分人物”最上,“峥嵘突兀”次之,“媻姗勃窣”则为“侧媚”之末流。“媻姗勃窣”出自《汉书·司马相如传》:“媻姗勃窣上金堤。”颜师古注曰:“媻姗勃窣,谓行于丛薄之间也。”“元分人物”尚未有明确出处,但是结合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对苏、辛二人的推崇,其意亦不难辨明:
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华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以从此领取。[1]498
辛稼轩风节建竖,卓绝一时,惜每有成功,辄为议论所沮。观其《踏莎行·和赵兴国》有云:“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其志与遇概可知矣。[1]508
苏轼的“雪霜姿”、“风流标格”,辛弃疾的“忧道怀国”之志,当是“元分人物”的应有之义。《艺概·词曲概》中还有一段话可作为“词三品说”之注脚:“昔人论词要如娇女步春。余谓更当有以益之,曰:如异军突起,如天际真人。”[1]561“娇女步春”见王又华《古今词话》引毛先舒言:“长调如娇女步春,旁去扶持,独行芳径,徙倚而前。一步一态,一态一变,虽有强力健足,无所用之。”此可谓“行于丛薄之间”的具体描绘。而“峥嵘突兀”与“异军突起”相近,“天际真人”即为“元分人物”。苏轼生性放达,随遇而安,宠辱不惊,辛弃疾忧国忧民,为南宋著名爱国将领,二人同为豪放派词人,常并称为“苏辛”。刘熙载之“词三品说”推崇豪放、飘逸之词风,有意贬低婉约、香艳,以其“沦于侧媚”,而无所用之。这实际上是以道德标准来评判词品,认为词作应当体现“道心”,讲求“风流标格”,反对“绮罗香泽之态”,重视词作的人伦教化作用。
(2)“词莫要与有关系”。刘氏所论,将人品作为考察词品的试金石,因此他特别注重词之“有关系”,即词品的优劣与词人的遭际和对现实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词莫要于有关系。张元干仲宗因胡邦衡谪新州,作《贺新郎》送之,坐是除名,然身虽黜而义不可没也。张孝祥安国于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致感重臣罢席。然则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1]571
认为词也具备兴、观、群、怨的社会教化作用,作词必须立足现实,表现出词人的人生志趣和生活态度,即词亦当“言志”。
(3)“情志”之辨。既然认为词以“言志”,那么自然少不了对“情志”关系的辨析,刘熙载论词特别强调性情之正,认为词应与诗一样,兼具六义,有雅郑之分,“词导源于古诗,故亦兼具六义。六义之取,各有所当,不得以一时一境尽之。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词,乐章也。雅郑不辨,更何论焉!”[1]458是故他不同于历来论家所持守的诗庄词媚,“诗言志”、“词缘情”的观点,对词中之情作了深入明确的辨析:
词家先要辨得情字。《诗序》言“发乎情”,《文赋》言“诗缘情”,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世间极有情之人。流俗误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倚声一事,其小焉者也?[1]576-577
词尚风流儒雅。以尘言为儒雅,以绮语为风流,此风流儒雅之所以亡也。[1]572
耆卿《两同心》云:“酒恋花迷,役损词客。”余谓此等只可名迷恋花酒之人,不足以称词客,词客当有雅量高致者也。[1]576
这不但划清了尘言绮语与风流儒雅的界限和俗人与词客的界限,“欲长情消,患在世道”之说,标举情之“正”者,以忠孝节义扩大了词体之内涵,也更见其褒贬的鲜明态度。他将词品与人品并论,认为词应具有正情、进德的作用,故论曰:“词进而人亦进,其词可为也;词进而人退,其词不可为也。词家彀到‘名教之中自有乐地’,儒雅之内自有风流,斯不患其人之退也夫!”[1]577刘熙载认为词人应是有真性情,有德行的人,词作也应具备情、德之正,反对“欲长情消”之词风,不喜迷恋花酒之人。又谓:“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1]509“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刘熙载认为词应符合儒家诗教之旨,词人当为“至情至性”之人,其词才能有“潇洒卓荦”之高标。
要之,刘熙载以道德批评为论词之原则,标举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飘逸之词风,而贬低婉约一派,将人品作为检验词品的标准,认为词人当为“至情至性”之人,其词才能符合儒家诗教之旨,“言志”而发乎“正情”,以至于“天际真人”、“元分人物”之最高词品。
2.刘熙载词论思想溯源
(1)儒家传统诗教观的熏陶。刘氏之所以形成以诗论词,以人品定词品的批评理论,其词论思想之远源乃是儒家传统诗教观。首先是“有德者必有言”的“文德观”。《论语·宪问》云:“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9]215孔子阐明了德与言的关系;《礼记·乐记》云:“和顺积中,英华发外。”认为内在的道德修养由人的外在言语和行为所反映;孟子则进一步将此观点绝对化,认为“有诸内,必形诸外”。刘熙载所谓“至情至性”之人,即为道德修养完满的人,在这“完美”人品的保证下,其词也当为上品。其次,受到了“兴观群怨”文学作用论的影响。《论语·阳货》云:“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9]279孔子对文学的社会作用做出了明确而系统的阐释,“兴观群怨”论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熙载以诗论词,认为“词莫要于有关系”,强调词应当感时而作,有为而发,以词“言志”,注重反映社会现实,以及抒发词人的人生态度,正是继承了此论。最后,也受到了“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原则的影响。《孟子·万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0]孟子所论,本是关于修身的问题,但也有为后世文学批评可资借鉴之处。“知人论世”意即想要真正地理解作品,那就必须对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情感、人品等方面做充分的研究,以达到对作者本人全面的认识。同时,也还要对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文学背景予以观照。只有做到知其人,才能论其世,从而能够客观准确地理解和批评作品。刘熙载云:“词当合其人之境地以观之。”[1]525他推举“苏辛”,而谓“周旨荡而史意贪”,即是从词人的生平经历出发,以人品代替了艺术评价,从而定词品的高低。
(2)有清一代词论思潮的陶冶。刘熙载之词论,同样也离不开其身处时代之词论思想的影响。有清一代,词论家致力于推尊词体,突出词“史”的地位。早在明末清初,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便以词并肩“经”“史”,推尊词体,摒弃“小道”和“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认为“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今词苑序》),故其词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赌棋山庄词话》)反映明末清初的国事,以词记史。清代中叶,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在《词选序》中阐述了他的词论思想,认为词的内涵是“意内而言外”,即主张词要有深厚的寄托;词的内容应当“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志。” 也就是说,必须用含蓄、曲折、深婉的手法加深词的立意;词的表现手法上,推崇比兴寄托,认为“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应是词之典范。是故他认为词当“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之也”,将词置于《诗》《骚》同等的地位,继续推尊词体。常州词派后继者周济,他认为“诗有史,词亦有史。”[2]4更加突出了词的“史”性,推尊了词体;也认为词“感慨所寄,不过盛衰。”[2]4强调词应当抒发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政治感慨。并且,在张惠言倡导“意内而言外”的基础上,提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2]12的观点,要言之有物,旨趣高远。时至清末,词的创作基本是在常州词派理论的笼罩之下推尊词体,既讲求词的传统艺术规范,又重视词的厚重内容,不再把词视为“诗余”小道。刘熙载作为清末的文艺理论家,其词论无疑受到了有清一代词论思想的熏陶,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他统合各派之说,推尊词体,以传统儒家诗教观来观照词的创作,强调词要“有关系”,要感时而发,有为而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品说”,以人品论词品,以道德批评取代了艺术鉴赏,将词以“言志”发挥到了极致。
综上所述,所谓“周旨荡而史意贪”,乃是刘熙载持守道德批评的原则所下的结论,并不能完全反映周、史二人词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其以诗论词,以人品定词品的词学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来源,远接儒家传统诗教观,近承有清一代推尊词体,重视比兴寄托的词论风潮,创造性地提出了“论词莫先于品”的“三品说”。可以说,刘氏之词论是对清代传统词论的总结,对王国维等近代词论的提出具有启发意义。其词论之道德批评特征具有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也应看到刘氏为理论创新所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