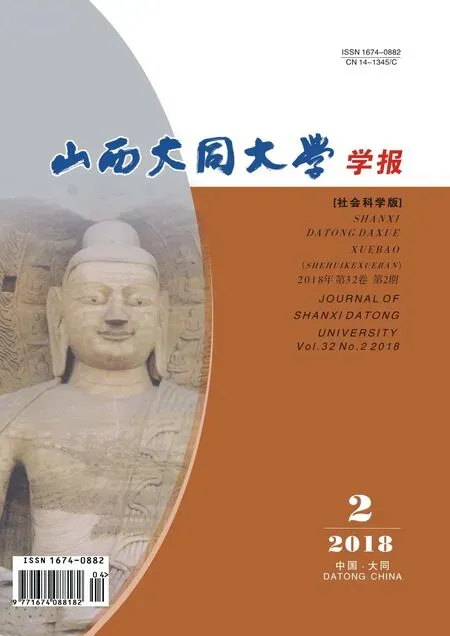辽金崇佛与云冈石窟的修缮
宣 林
(云冈石窟研究院,山西 大同 037007)
佛教自公元1世纪东汉明帝时期正式传入我国,建立了第一座寺庙——白马寺。佛教刚传入并不被国人接受,也无人信奉更无人出家当和尚。寺院只是作为外国人朝拜或是歇脚的地方。到了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人们就开始反思儒家思想。这时佛教的“苦的根源”、“善恶因果”、“修行”等的内容就被深处苦难中的人民所接受,成为精神寄托,所以这个时期佛教大规模发展。以至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况。从此佛教便开始被统治者所重视,尤以南朝后梁武帝崇佛更甚,曾三次舍身同泰寺。佛教便在我国大规模发展起来。
第一个大规模重视佛教的少数民族是建立北魏的鲜卑族,鲜卑族建立北魏政权后,在其都城平城修建了雄伟壮观的云冈石窟,这座石窟依山开凿,规模宏大、巧夺天工,造像众多,石窟主体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大小窟龛252个(其中大窟45个),共有大小造像51000多尊,其中最高的高达17米,唐朝人道宣记载道“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容三千人”,最小的仅1厘米。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记载“栉比相连三十余里”,根据调查发现云冈石窟除主体1公里外,东西相延15公里,西起焦山寺,东至观音堂。云冈石窟以西主要开造了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青磁窑石窟等,以东为佛字湾,建有众多寺院,规模之宏大,历代史书屡有记载。是中国石窟艺术的名副其实的杰出代表,是中西方佛教文化交流的伟大结晶。
鲜卑族为什么要修建规模如此浩大的石窟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佛教统一民众思想,来达到其实现统治的目的。北魏是迁都平城以后才开始接触佛教,当时佛教也在寻找政治上的依靠,他们把皇帝称作是佛祖在人间的代表,皇帝即如来佛祖,北魏统治者很欣然就接受了这一称谓,这样民众就把对佛祖的崇敬很自然地就转移到了皇帝的身上,巩固了其的统治。统治者当然重视佛教的发展,所以修建石窟、寺院。当时仅京城僧尼就达2000人,寺院100多所。而武周山石窟寺又为皇家佛教活动场所,僧尼众多,寺院相连,《水经注》中所载,“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寺,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状,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景,缀目新眺,栉比相连三十余里”,[1](P121)这是何等壮观的景象。云冈石窟群的建造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我国的发展,此崇佛习俗一直到被辽金时期的统治者所接受。
一、辽代崇佛与大修云冈石窟
(一)辽代崇佛 辽代统治者重佛崇佛比之北魏鲜卑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辽自太祖耶律阿保机在912年“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我雄武。”[2](卷1)便开始重佛。之后太宗即位,更为笃信佛教,祈佛活动,屡见史籍。继太宗之后,世宗、穆宗、景宗,多崇佛,“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2](卷8)侍中为朝廷命官,任命一个僧人为侍中,可见对佛门的重视。辽圣宗、兴宗时期,崇佛达到了鼎盛,修建了大量的寺院,重熙八年(1039)“十一月……戊戌,辽命皇子梁王召僧论佛法。辽主重佛教,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3](卷42)“辽主溺浮屠法,务行小惠”。[3](卷48)刊印佛经更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留下了大量的佛家经典,如《辽藏》、《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由此看来,辽代统治者崇佛已成一种习惯。仅在西京大同府就修建了上下华严寺、观音堂、南堂寺大佛、禅房寺塔,扩建了邓峰寺,数次重修灵丘觉山寺,还在应县修建了文殊寺,寺内的应县木塔是现存的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寺塔,其建筑之精美,无与伦比。辽代崇佛还有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某些有地位、有名望的人起名字与佛有关,如辽圣宗的皇后萧菩萨哥、辽道宗的皇后起名为萧观音,还有名耶律观音,大定府少尹尚暐的孙女名文殊,太和宫副使耶律弘益的夫人名萧氏弥勒女,静江军节度使萧孝忠的一女儿名萧天王女、一女名萧观音女,这充分说明了佛教在其生活中的重要影响。
辽代统治者之所以崇佛,一是政权建立初期利用佛教来完成移民政策。辽代占领了幽云十六州后,由于此地战乱频繁人口锐减,所以辽统治者便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其他民族(包括汉族、渤海人、女真人)强制移民到此,而这些民族都是信奉佛教的,所以辽统治者便广造佛塔寺庙用佛教来安定移民、稳定人心。二是缓和统治阶级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辽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其与汉族在生活习惯、思想文化存在明显的不同,难免会有民族矛盾。而辽统治者重视佛教,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都信奉佛教,这样不同民族的人通过佛教这一共同的信仰联系到了一块,这样就极大地缓和了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辽崇佛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大修云冈石窟 辽对云冈石窟的修缮,便能很好地反映出其对佛教的重视。云冈石窟的开凿在北魏时已基本完成,历代屡有毁坏、修缮。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平城即被遗弃,且大同地处苦寒之乡,戎马生郊,所以乍盛乍衰。北周武帝在建德三年(574年)进行灭佛运动,使得“数百年来官私佛寺,扫地并尽”,“关陇佛法,诛除略尽”。[4](卷23)唐武宗在会昌年间(841-846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灭佛,这次灭佛运动被佛教徒称为“会昌法难”。云冈石窟在灭佛运动中也饱受摧残,且历经百年的风雨侵蚀,云冈石窟难免残败。但到唐朝也未有大的修缮动作,一直到辽时期,由于统治者崇佛,大同被定为西京,且西京又是辽重要的佛教要地,云冈石窟才得到了大规模的修缮。
云冈石窟的历代修缮以辽代皇室的重修为最具规模。今天我们如果去云冈石窟参观,就可以在五华洞看到大型、细致的辽代泥塑修补工程遗迹,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当时是尽可能依照北魏时期的原始风貌进行补塑的。其中最明显的重修实例是第八窟中心塔柱南壁下龛,主佛被包泥彩绘,真正的容貌已经难以看见,但两侧的侍从菩萨补刻为辽代风貌的塑像,菩萨浮雕的身躯变薄,右像头顶高冠被截掉,大概是当年因旧像毁坏严重而重雕的。
再者,根据金代人曹衍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碑》记载,辽代确在云冈有过规模相当大的修缮工程。根据宿白先生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碑〉校注》中记载有“辽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天庆十年赐大字额,咸雍五年禁山樵木,又差军巡守。清宁六年又委刘转运监修……屡次重修”[5]的字样。可见,辽代对云冈石窟的修建工程,是多么的宏大。据《辽史》可知“辽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之“母后”者,辽圣宗钦哀皇后,兴宗母萧氏,也称章圣皇太后。钦哀皇后早年比较暴戾,犯下许多过错。重熙三年,欲废兴宗而立少子重元,被废幽。后帝召僧讲《报恩经》后,悔悟。迎奉太后回京。十八年时,重修云冈石窟,盖是兴宗为母后祈福。这是有明确纪年与由来的辽代重修云冈石窟比较大规模的一次。由此可见,佛教修庙祈福在辽统治者的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又根据近年来的调查、清理、发掘,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的发掘,逐渐证实了辽代在云冈确有浩大的修缮工程,与《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碑》中所记载的屡次重修符合。辽代的修缮工程自云冈主体1公里以迄与东西15公里都有涉及,具体工程如下。
1.对云冈石窟主体部分的修缮
对云冈主体部分的修缮主要是石窟造像前的佛寺营建。据曹衍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碑》记载及宿白先生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碑〉校注》“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示(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教(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这十名也分别见于《魏书·释老志》、《续高僧传》卷1、《开元释教录》卷6、《古今译经图纪》卷3、《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9等,北京图书馆藏的成化《山西通志》卷5所记:“石窟十寺,在大同府城西三十五里,后魏时建……其寺,一同升,二灵光,三镇国,四护国,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华严,九天宫,十兜率。寺内有元载(“载”疑为“魏”之讹)所修石佛二十龛。”根据宿白先生推测此“十寺”约自辽代开始,约在明中期以后“十寺”荒废。由此可知,云冈石窟并非今日所见之石窟洞佛,在1至20窟窟前都曾修有木结构的寺庙,即后面是原有的窟室,前面是后建的木结构窟室,这种前木后石的特殊建筑结构,就称之为佛寺,“十寺”之称也便由此而来。其形状与原貌大体类似于清朝所建的第5窟、第6窟的石佛古寺,我们现今所见的是木制建筑被毁后的露天佛龛。且根据发现,第1窟到第20窟上面的崖面上,的确都分布着曾经容纳木结构的梁孔、椽眼等的痕迹,所以由此可推断出当时确实在石窟造像前有木结构的建筑。自1933年起到建国后,在云冈石窟的第5窟、第8窟、第9窟、第11窟、第12窟、第13窟的窟前及昙耀五窟的窟前分别发现了大量的辽代的石础、铺地方砖、满文砖、兽面瓦当、指纹板瓦当和陶片[6]等。因其发现位置在石窟前面,所以就可以和安装在窟前的木结构联系起来。由此,我们便可推断出辽代在这些石窟前确实都兴修了巨大的木结构。
2.对云冈石窟以东寺院的修建
主要是对观音堂、佛字湾一带的修建。根据《乾隆大同府志》卷15所载“观音堂,府城西十五里佛字湾,辽重熙六年(1037年)建。”[7]观音堂、佛字湾都为云冈石窟东西15公里延伸的范围内。
佛字湾因其悬崖上有一个约2.5米见方的巨大“佛”字,因此而得名,但此崖壁上除了这个“佛”字外,再没有任何刻字、题名,究竟这个“佛”字是刻于何时、又是出于谁人之手,翻遍大同县志及各种典籍,均无明确记载。因此这一“佛”字的由来便众说纷纭。一直到1933年,经梁思成先生考证此“佛”字为辽代遗迹。根据大同学者姚斌先生称:大同自古就为少数民族集散地,是古之交通要道,塞外少数民族各部落向中原王朝朝贡、互市、通商、和亲都要经过此路。辽代战争不断,百姓生活困苦,在此交通要道上盗匪猖獗。于是修建观音堂,又刻“佛”字,以规劝世人诚心向佛、与人为善。
据史料所载,观音堂始建于辽重熙六年(1037年),屡次焚毁、重修,现在所看到的观音堂是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总督佟养量重建的。现今观音殿内尚存一尊辽代砂岩石雕的观音大像,且根据发掘,在观音堂及其附近又发掘出许多辽代的满文砖,这些都是辽代修建所留下的痕迹,在观音堂西石崖壁上留有高丈余的双钩“佛”,据考证此双钩“佛”也是辽代遗迹。对于为什么刻这些双钩“佛”,张焯先生在其所著的《云冈石窟编年史》一书中提到:观音堂为众多寺院的门户,建观音堂、书大“佛”字,即有到此步入佛境之意。
3.对云冈石窟以西寺庙的营建
主要是鲁班窑石窟前寺庙的营建与焦山石窟的寺院营建。曹衍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碑》中所载:“十寺之外,西至悬空寺,在焦山之东,远及一舍,皆有龛像,所谓栉比相连者也。”按云冈石窟以西,傍武州川水,现存的北魏石窟遗迹共有三处:一、鲁班窑石窟,在云冈石窟西南。二、吴官屯石窟,从云冈石窟西行,上溯约四公里。三、焦山石窟,从云冈沿武州川西行约15公里。即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焦山石窟都位于云冈石窟以西15公里内,焦山寺石窟距离云冈石窟主体最远。根据1952年的在鲁班窑石窟前发掘出大量的辽代砖瓦,且在石窟崖壁上残存有建制的窟檐的痕迹。由此可以断定,在辽代,鲁班窑石窟前确实曾经建有木结构的屋檐。后毁于辽末天祚帝保大年间,明代在其上面建有烽火台,并没有重修寺院。所以鲁班窑石窟自辽末毁坏后,再没有修复,荒废一直到今。
焦山石窟位于云冈石窟西15公里处,根据现存遗迹可知,其建造大体可分作三期:第一期是北魏时期,主要开凿了大量的石窟。第二期为辽金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北魏所造石窟在窟前建造木结构寺庙。第三期是明代以后,主要为大规模的重修,现今所见的主要为明代嘉靖年间所修缮的焦山寺。1950年在焦山南坡及焦山寺东侧都发现了辽代的满文砖,说明了辽代对焦山石窟有过修建活动,且碑刻中也有“辽大安五年(1089年)重修”的记录。在焦山寺内现存一座实心结构的砖塔,据考证,此塔为辽代修造。根据宿白先生的考证,辽人不仅在此营建了寺庙,而且还就北魏石窟中被毁的佛像进行了重新泥塑。焦山寺第二层东大窟中的释迦塑像上还残存有五代北宋时期常见的石绿彩色。
辽代重修云冈石窟除了统治者崇佛、重视佛教发展,用佛教达到缓和民族矛盾实现其统治的目的外,据南宋《佛祖统计》记载:“西京龙门山石龛佛岁久废坏,上命沙门栖绘工修饰,凡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九尊。”[8](卷44)可见,辽代重修云冈石窟,也一定程度上受了宋朝修龙门石窟佛像的影响。
二、金代崇佛与重兴云冈石窟
(一)金代崇佛 金代为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其基本沿袭了辽代对佛教的政策,其崇佛的原因与辽类同。女真族的祖先就有崇佛的习惯,《金史》中就有“金之始祖讳函普,初从高丽来,年已六十余矣,兄阿古遒好佛”[9](卷1)的记载,《三朝北盟会编》中有女真人“奉佛尤谨”[10](卷3)的记载。金灭辽时,把辽代兴建的寺庙大半毁了,这一方面是战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对佛教的淡漠有关,但紧接着在夺取政权后,第二代太宗完颜晟执政后很快对佛教热衷起来,这与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民族自卑感有关,少数民族由于其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文化建设相对比较薄弱,使其不得不吸取中原民族的文化来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来强化民族认同感。这种文化上的劣势在战争时期体现的不明显,一旦夺取政权后,就必须利用文化来加强各民族的认同感,达到统治的目的,这时少数民族文化上的劣势就暴露无遗,所以,其统治者便开始注重文化建设,佛教便是少数民族强化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工具。所以,为了促进佛教的发展,金太宗完颜晟不但自身皈依佛门,还每年设立斋会,熙宗时,对僧侣颇为优渥,在上京修建了储青、庆元等6座寺院,到金世宗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全盛,很多寺院都是在这一时期修的。对佛经最大的贡献是刊印了《大藏经》的金刻本。女真族建国以后在五京都修建了大量的寺院。其对西京云冈石窟的修缮也是崇佛重佛的表现。
(二)金代重兴云冈石窟 《三朝北盟会编》卷5中记载:辽天祚帝在保大二年(1122年),自中都西逃到云中(今大同),经云冈入天德军。随后金兵又追逐天祚帝,官军所到之处,大同府城内寺院都遭到毁坏。金大定二年(1162年)僧省学在《重修薄伽教藏记》中云“至保大末年,伏遇本朝大开正统,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灰之”。曹衍的《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碑》中记“先是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都记录了凡是辽天祚帝沿途所经过的地方,寺庙楼阁都遭到了焚毁,况史书中明确记载天祚帝逃到了石窟寺,那云冈石窟遭到金兵的毁坏确属无疑。金代在取得政权后随即开始崇佛,云冈石窟也得到了修缮。
1.完颜宗翰对云冈的保护
金朝沿袭辽代设置陪都的制度,继续设大同为西京陪都。而且还设置了元帅府。《金史》卷55《百官志》一:“都元帅府,掌征讨之事……天会二年(1124年)伐宋始置。”[9]金代把西京大同府作为南下征伐宋朝的前沿阵地,设置元帅府总领西京的一切事物。而且史书中有“非亲王不得主之”的记载,说明了金代统治者对西京大同府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根据《金史》卷2《太祖纪》的记载,“故元帅晋国王……己巳至西京,壬申西京降……(七年六月)宗翰为都城……驻兵云中”,同书卷3《太祖纪》“(天会三年)十月甲辰,诏诸将伐宋……宗翰兼左副元帅……自西京入太原,……(闰十一月)癸巳,宗翰至汴,丙辰,克汴城……(五年四月)宗翰、宗望以宋二帝归”,同书卷74《宗翰传》记载“是时,河东寇盗尚多,宗翰乃分;留将士夹河屯守,而还师山西……(六年)以宗翰为国谕右勃极烈兼都元帅”,同书卷4《熙宗纪》“(天会)十三年,以国谕右勃极烈都元帅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封晋国王。……十五年……七月辛巳……宗翰薨”。即完颜宗翰(粘罕)在天辅六年(辽保大二年,1122年)攻下了辽的西京大同府,后在天会五年(宋靖康二年,1127年)灭了北宋,俘虏了北宋徽、钦二帝北上,之后,由于山西地区盗贼较多,所以还师山西,一直驻在西京。史书上说明了完颜宗翰从辽保大二年(1122年)至天会十五年(1137年)这16年间,一直是掌管着西京。
因此据曹衍的《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碑》记载“本朝天会二年,大军平西京,故元帅、晋国王到寺随喜赞叹,晓谕军兵,不令侵扰。并戒纲首,长切守护。”说明了完颜宗翰对云冈石窟的喜爱,并加以了保护。之后此碑又记有“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根据时间推断,正好是宗翰总理西京的时期,所以改拨河道应与宗翰有关。宗翰改拨河道即改变武州川水的流经方向。在金代以前,武州川水由西北流向石窟,到了石窟的最西面改为由西向东流径直从石窟底下流过,可以说是紧邻着石窟从西往东流的,在武州川水中可见石窟及寺庙的倒影,然后武州川水右转向东南,所以才有《水经注》中“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情景。今天在云冈石窟的前面立着一个“北魏河坝展示”的碑刻,碑上记录了曾经的武川水从石窟下面流过的事实。完颜宗翰担心武州川水离石窟像太近而侵蚀石窟,所以发动人员将东西走向的流经石窟的河道整体往南改拨了大约四百米,就形成了现在的样子,至今,武州川水(今十里河)以南无任何石窟建筑。
2.禀慧修复灵岩寺
曹衍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碑》记载:“皇统初,缁白命议,以为欲图修复,须仗当仁,乃请惠公法师主持。师既驻锡,即为化缘。富者乐施其财,贫者愿输其力于是重修灵岩大阁九盈,门楼四所,香厨、客次之纲常住寺位,凡三十楹,轮奂一新。又创石垣五百余步,屋之以瓦二百余楹。皇统三年二月起工,六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皇统三年至六年,惠公法师即禀慧禅师,在任主持期间,通过化缘,富者出钱,贫者出力,用了长达6年的时间修复了灵岩大阁。灵岩大阁,即今云冈石窟第3窟前曾经的木结构建筑,其有别于今天的灵岩寺。第3窟是云冈石窟最大窟,其石窟为特殊的前后室形制,其雕刻风格,营造样式也都比较独特,从今天石窟上留下的容纳木结构的梁孔、椽眼等的痕迹可以看出灵岩大阁非常雄伟宏大的。但考古发掘从未在此发现金代的遗物、遗址,只是在第3窟的前面有较大面积的平地,由此可推断出在第3窟前曾经有过较大规模的建筑。符合《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碑》中有关第3窟前灵岩大阁修建的记载。金代从统治者到皇戚贵族都重视佛教,大量施舍钱财、土地给寺院,极大的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辽金民族在他们进入华北地区并建立政权后,就大量吸收了中原汉族文化,其中,对佛教的重视,就是对汉族文化的吸收。辽金民族崇佛与其民族自卑与民族自尊的矛盾心态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其自身是游牧民族,在文化建设方面与中原民族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其用武力征服了中原民族后,马上重视其文化建设,吸收中原的文化以缓和民族矛盾,以增强民族认同。所以,佛教对巩固辽金统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辽金统治者也因佛教对其统治的作用而重视佛教的发展。
辽金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使得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其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寺院的修建,而云冈石窟是我国佛教石窟艺术中的杰出代表,辽金时期对云冈石窟做出大规模的修缮活动,是其崇佛的最好例证。对这一时期的佛教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刻的了解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也对佛教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参考文献:
[1](北魏)郦道元.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清)毕 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唐)释道宣.续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
[5]宿 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J].北京大学学报,1956(01):76-89.
[6]水野清一.云冈石窟调查记[J].东方学报,1989,第九册、第十一册.
[7]吴辅宏.乾隆大同府志[M].大同: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2007.
[8](宋)释志磬.佛祖统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9](元)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